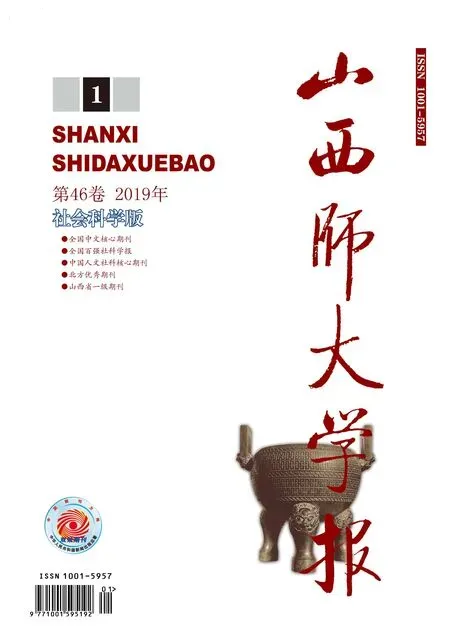《潜夫论》引《诗》的理论建构与《诗》史价值
2019-02-22赵玉龙
赵 玉 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潜夫论》是东汉中后期思想家、政论散文家王符的名著,十卷三十六篇,是东汉议论文章的典型和代表。《后汉书·王符列传》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1]1630王符虽是被边缘化的一介失意儒生,隐居僻乡,终身不仕,但其作《潜夫论》在汉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潜夫论》大量征引和化用《诗经》语句,笔者据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统计,书中直接或间接引《诗经》达97次之多[注]由于统计标准和方式不一,各家统计有出入。刘文英统计,《潜夫论》完整引用《诗经》44次。(参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刘毓庆、郭万金统计,《潜夫论》引《诗》共110处。(参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蒋泽枫统计,《潜夫论》引《诗经》共计111条。(参蒋泽枫《王符〈潜夫论〉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李晓敏统计,《潜夫论》引四家《诗》104次。(参李晓敏《王符〈潜夫论〉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2页)。王符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和学说,在引《诗》上别具一格。有关王符的《诗》学思想,学界虽早有论及,但《诗》学思想作为王符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对于全面解读王符《潜夫论》,以及深入理解《诗经》在汉代的传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诗》与王符的著述动机
汉代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期,许多文人士子多受其影响。东汉中后期是经学的大发展、大变革阶段,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王符,虽不是经学家,《潜夫论》也非经学著作,但亦多受经学影响,《潜夫论》对《诗》文献的征引和《诗》义的阐发就说明了这一点。
《潜夫论》引《国风》18次14篇,《小雅》38次26篇,《大雅》33次17篇,《周颂》5次4篇,《商颂》3次2篇。除去重复,涉及篇目达63篇。总体上看,《潜夫论》对《诗》句的征引和化用灵活多样,体现了王符深厚的诗学修养。无论引《诗》发表政治观点、阐述己见,还是作为理论依据,增强说服力,都与王符的著述动机相联系,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同情民瘼,为挽救东汉弊政而积极寻求解决对策的创作精神。
(一)王符的诗学修养
《后汉书·王符列传》载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马、窦、张、崔都是当时的文章大家,能与他们一起交游论学,王符也一定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否则就不可能有《潜夫论》这样影响深远的巨著。《潜夫论·赞学》(下引该书,仅注篇名)中所言“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就表明了王符长期坚持学习的态度。
那么,王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潜夫论》对“五经”《老子》《论语》《孟子》《韩非子》《孝经》及纬书等文献的征引来看,王符的学习内容非常驳杂,兼容并包,视野开阔。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的是,王符的诗学修养非常好,功底扎实,《潜夫论》几乎每篇都有引《诗》,最后一篇《叙录》亦如此。这首先是由王符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汉代孩童的启蒙教育就很重视对《诗》的学习,如冯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后汉书·冯衍传》)。东汉中后期,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利禄的引导,社会上普遍形成了研习《诗经》的风气,《潜夫论》引《诗》丰赡,王符也一定是熟读掌握了《诗经》的要义。
王符善于发挥引申诗语的内核,借助诗义进行现实批判。且不死守经义,将诗之内涵运用于说理之中,突出个人的意愿,达到引《诗》以资治政的目的,这也是王符著述动机的一个方面。如《浮侈》引《诗》:“《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2]164引《诗》见《陈风·东门之枌》。诗的主旨本来是写男女相遇相悦的,但《毛诗序》曰:“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王符袭用《毛诗序》之义,且用“刺”字表明了态度,这与他对东汉衰世虚浮奢侈之风的批判正好相合,也十分贴切。
王符对先秦“赋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其诗学修养的重要体现。先秦时代长期有“赋诗言志”的传统,借《诗》中作品来交流情感,表达思想。王符所处的社会显然已经脱离了“赋诗言志”的时代语境,但“赋诗言志”的话语实质在王符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成为他行文说理的必备素材。王符引《诗》能够结合社会现实对诗意作出新的阐释,并将诗作为诱发引申现实问题的基点,大大扩展了“赋诗言志”的使用范围和功用,这是与他的诗学素养密切相关的。如《相列》中引《诗》:“《诗》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卜列》:“《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等等,王符都能将其与所论主旨相联系,为所述事理提供理论依据。
王符认为《诗》是圣人之道的载体,当时社会又常以经来决断是非,所以他常引《诗》说理,并将生活经验及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注入其中,从有利于个人修养、国事、民事等方面去阐发诗意,不仅丰富了诗的内涵,而且与所论主题融而为一,建构了独特的引《诗》体系。这也可看出王符对诗文本的熟稔。
(二)以义系《诗》,今古文通用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时主要以今文经学为主,到了东汉中后期,今古文经学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并最终由古文经学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而居于统治地位。
王符的时代,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皇权旁落,政局动荡,社会衰败。受经学思潮的影响,王符的主导思想属于儒家,正如汪继培所言:“王氏精习经术,达于当世之务,其学折中孔子。”(《潜夫论笺》前言)王符的思想深深打上了经学时代的烙印。“白虎观会议”之后,经今古文学渐趋融合,许多经学家表现出了今古文经学兼通之势。特别是在王符学术活动的和、安、顺、桓年间,儒生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严格地固守家法师门,对今古文经学采取兼容的态度,王符亦如此。刘文英就指出:“从《潜夫论》的内容来看,王符确实对‘今学’‘古学’双方均有所取,而采取一种融合而用的态度。”[3]43《潜夫论》虽大量称引儒家典籍,融通今古文经,但并非简单地进行经意解说和章句训诂,而是用儒家典籍直接剖析社会弊病,“指讦时短,讨谪物情”。
就《诗》文本而言,《潜夫论》多采《鲁诗》说。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就将王符归入《鲁诗》学派,而且“从王符的为人到其《诗》学观点以及其现实批判精神来看,确实像《鲁诗》学者的作风”[4]384。如《论荣》:“《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2]4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解说是:“引《诗》以明修身俟命之义,盖《鲁》说如此。”[5]199也即王符是采用今文经《鲁诗》的说法。《鲁诗》之外,《潜夫论》还采用了《齐》《韩》《毛》三家诗义,其标准是“依需所取”,在不同主题的论述中,对各家诗说融合而用。
王符引《诗》不拘一格,有同一诗句在不同篇章语境下今古文不同者。如《爱日》《释难》同时征引了《小雅·沔水》“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一句。王先谦释义云:“言乱之既生,有父母者其忧更深,谁无父母,坐视乱兆而不肯一留念乎?言人尽放恣,大乱必成。王符用《鲁诗》,是《鲁》义如此。其《爱日》篇亦引此二句,患公卿苟先私计而后公义,谓其不肯忧国,则又与《毛》义合。”[5]637可见按照王氏对诗义的解析,《爱日》中用《毛诗》义,《释难》中用《鲁诗》义。陈乔枞也指出,《释难》篇所引为《鲁诗》义,而《爱日》篇所引义与《鲁诗》异[6]215。造成诗义不同的原因,是王符出于明理议政的需要,选择最能突显自己思想的那一家,不以今古文为限。
(三)引《诗》中典故与故实
汉代文学作品有巧妙使用《诗经》中典故与故实的传统,如班婕伃《捣素赋》:“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7]366文中接连引用《诗经》中“幽闲”“贞专”“首疾”“《采绿》”“《东山》”多个故实,不仅使赋作语言更为典雅,而且也使赋作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汉代文人的引《诗》实践深深地影响了王符的创作理念。《潜夫论》中就有许多征引诗中典故与故实的实例。如《救边》: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来享,普天思服,行苇赖德。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2]347
“行苇赖德”典出《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意在阐明君主的恩德普惠四方百姓,不能对边地人民遭遇的苦难置若罔闻。再如《遏利》:“白驹、介推遁逃于山。”这是对《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一句的暗用,喻指贤人遁逃隐居于山谷。《本政》“皇父、蹶、踽聚而致灾异”是对《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故实的引用。
通过《潜夫论》对诗文本的征引,可知王符对《诗》、诗教、诗学及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养。行文中引《诗》已成为王符创作的一种通例,其原则就是以述志抒情为导向,根据针砭时弊和议政的需要,随机加以征引,以此来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和公信度,并与行文内容浑然一体。
二、用诗旨归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王符有着深厚的诗学修养,在引《诗》上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个性。在汉代,《诗》被广泛用于政治教化之中,以礼教为旨归。长期以来,《诗》成了宣扬政治教化的工具,如王吉以《诗》谏昌邑王刘贺,刘向以《诗》谏成帝等。《潜夫论》打破了当时的用《诗》模式,将《诗》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使用《诗》表现出了更多元的旨归。
(一)以《诗》证理
诚如上述,汉代儒生往往以礼教为用《诗》旨归,而王符却独具匠心,不囿于经学的束缚,常引《诗》来论证观点,说明事理。如《三式》:“《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观之,未有得以无功而禄者也。”[2]261王符引《魏风·伐檀》中的诗句来说明,君子是不白白接受俸禄的,凡是有功德、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就应该封以列侯、赐予封邑来褒奖他们。相反,对于那些无所事事,毫无功绩的大臣高官,就应该免去他们的俸禄,必要时施以刑罚。
《潜夫论》引《诗》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常从论说需要出发随机引《诗》为据,阐发己见。如《贤难》:“《诗》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2]68自古贤人为难,好人难做。王符为贤人的遭谗遇害打抱不平,并指出贤人之所以“虽有贤材美质,然犹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的主要原因是君主昏庸,不能明察。王符用《小雅·节南山》中的诗句来说明君主的英明与否对国运的影响。引《诗》自然贴切,前后语义连贯,无丝毫强拉硬扯的感觉。
《潜夫论》引《诗》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在引《诗》后接着对《诗》句的内容和主旨进行精辟地概括和解释,进一步阐发诗义,以期使所引之《诗》能更好地论证事理。如《三式》:
周宣王时,辅相大臣,以德佐治,亦获有国。故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其诗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乐土,赐以盛服也。[2]258
王符特别重视臣子和诸侯王的德行,如果以礼仪道德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获得了太平安宁,国君就应赐予他们封地和财物。“亹亹申伯”句见《大雅·崧高》;“四牡彭彭”句见《大雅·蒸民》。王符在引《诗》后根据所谈话题,紧接着对诗义作了凝练与解释,阐明了申伯、仲山甫以礼仪道德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天下太平的伟大功绩,与前文照应,浑然一体。
(二)以《诗》明教
我国古代一直有“以《诗》明教”的文化传统,孔子就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在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和社会交际中具有重要作用。先秦时期在说《诗》、引《诗》的过程中,存在“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8]。汉代文人加以继承和发扬,王符引《诗》就具有明显的“以《诗》明教”的特点,且尽力发掘诗中所隐含的所谓“美刺”意义。
在《潜夫论》直接引《诗》当中,大多以“《诗》云”“诗曰”“《诗》刺”“《诗》美”“《诗》讥”“《诗》伤”“《诗》痛”的形式开头,相较注重诗句或诗篇有关先王道德叙说的历史意义。王符更加关注由先王道德美名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强调《诗》的政教功用,这同秦汉人对《诗经》功用价值的认识是一致的。刘立志就说:“在秦汉人看来,《诗经》是先王典则,体现的是圣贤遗迹,后又经孔子删削,微言大义更是满眼皆是,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诗经》具有史诗的特质。诗歌与历史一样,都是言治的载体,都可用作政治讽谏与王道教化的工具。”[9]123如《述赦》:“《诗》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边议》:“《诗》痛‘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德化》:“《诗》美‘宜鉴于殷’‘自求多福’。”《交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等等,都具有丰富的教化功用。
在明显带有《诗》教功能的引《诗》之外,还有一些是《诗》文本所具体包含的。如《巫列》:
故《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言人德义美茂,神歆享醉饱,乃反报之以福也。[2]394
人的吉凶祸福与德行善举相联系,德义茂美,鬼神就会降福于人。王符引《诗》颂扬祖先敬奉鬼神,德义高尚的行为,就是要借言先人的美德达到明教的目的。
总之,《潜夫论》所引之《诗》,不是关乎政事就是有涉教化,极少例外。其引《诗》注重政治的作用和教化明理的意义,强调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最终将《诗》与社会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但推动了儒学的发展,而且也奠定了王符在《诗》学史上的地位。
(三)以《诗》论政
《潜夫论》的一个重要主旨就是同情民瘼,抨击东汉王朝,挽救时弊。王符引《诗》多关涉政治,常借助于《诗》中圣君贤臣的形象和事迹揭露和批判东汉王朝的弊政,其言辞可谓字字珠玑。罗宗强指出:“诗的产生既在很大成份上出于实用的目的,诗的早期流传也主要借助于实用。”[10]如用于宗教祭祀、禳灾求福等。《潜夫论》引《诗》也多出于实用,大多数与政治和史事有关,便于引申发挥,影射时政,作为立论的依据。如《爱日》:“《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2]278王符用《小雅·四牡》中的诗句来说明,古代王事繁杂,没有穷尽,以致百姓没有空余时间来奉养父母,躬行孝道。文中巧用诗义批判了统治者随意侵扰百姓,耽误民时的行为。
王洲明指出:“王符批评当时的思想武器依然是以‘经’为准则,所以文中引‘经’的内容很多。”[11]王符与汉代儒生在具体论事时的引经不同,把经典变成了一种思想与精神,熔铸于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诗》作为“五经”之首,王符在对东汉王朝进行暴露、批判的情况下,时时将其作为论政的媒介。如《爱日》:“《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伤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禄,而曾不肯察民之尽瘁也。”[2]288王符借《小雅·节南山》中的诗句抨击了三公大臣位居尊位、享受厚禄而不肯体察民情、爱惜民力的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当时盛行的今、古文经学,他(王符)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其中有益的思想营养。但他吸收前人的思想,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用来批判现实,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12]303《潜夫论》引《诗》旨归已突破汉儒以《诗》言教的单一模式,从现实政治出发,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借《诗》之情,抒己之愤,把《诗》运用于更为广阔的语境。
三、《诗》史价值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元典著作,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诗经》研究,既包括经典和精英思想的研究,又包括受到《诗经》影响的整个思想学术文化领域。《潜夫论》作为汉代的一部子书巨著,对《诗经》的接受、阐释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一)用《诗》模式新变
《潜夫论》在引《诗》上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往往根据上下文论述的需要随机加以征引。刘毓庆、郭万金就指出:“王符以前的汉朝学者称引《诗经》,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制度’与‘人伦道德’两大中心进行的,而王符则大大拓展了通《诗》致用领域,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不涉及。”[4]384同时,王符引《诗》也从自我需要出发,对诗句内容随意取舍,体现出较明显的“六经注我”倾向,为诗的引用开创了新的模式。如《赞学》: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2]18
“高山仰止”句见《小雅·车辖》,原诗本指即将迎娶女子德行的美好,王符用来指圣人德行的高尚,后人因此也常用这句话来赞美那些值得学习的人的德行,这不能不说王符是有开创之功的。“日就月将”句见《周颂·敬之》,诗意本指告诫群臣要严于律己,王符在上句诗意的基础上指出人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从师学习。唯如此,方能不断积累知识,成为见解非凡的圣明之人。
在直接征引或间接化用诗句之外,王符还用《诗》题明理,在用《诗》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如《班禄》:
其后忽养贤而《鹿鸣》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亩税而《硕鼠》作,赋敛重而谭告通,班禄颇而《颀甫》刺,行人定而《绵蛮》讽,故遂耗乱衰弱。[2]219
文中用了《召南·采薇》《魏风·硕鼠》以及《小雅》中《鹿鸣》《祈父》(即《颀甫》)、《绵蛮》的诗题,言简意赅,内蕴丰富,表现力极强,有力地佐证了观点。
(二)《诗》通学之勃兴
经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化,西汉经学尚专,并将通儒诵经作为选官择人、入仕为官的唯一途径。经学与官员遴选制度紧密结合,成了知识分子从政的工具。官府选拔出来的太学博士大都精于专经,并由专经教授弟子,且弟子要严格恪守师门家法,仅有极少数高才兼通数经,如韦贤、董仲舒、王吉等人。到了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变革,今文经的衰弱,古文经的兴起,加之师法家法的打破,兼通数经的儒生越来越多。如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1]1217。
《潜夫论》体现出的经学思想尚博,融古今诸家于一体。如《书》,《潜夫论》主要引用今文《尚书》,也有少数引用古文《尚书》的情况,甚至有今古文交错使用的地方[13]。就《诗》而论,王符主要用《鲁诗》说,同时兼采《毛诗》《韩诗》与《齐诗》说,这足以表明王符于《诗》已经是通学了。刘立志指出:“东汉中后期之《诗经》学,也呈现出宏通趋势。”[9]143王符之外,还有许慎、马融、郑玄、仲长统等,都表现出了《诗》通学的倾向。再之后《诗》通学成为主流,如贾逵精通《齐》《鲁》《韩》《毛》四家诗,并受章帝之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1]1239。王符《潜夫论》引《诗》论事与化用《诗》中语句者,居于东汉中后期诸家之首,融古今诸家《诗》说于一体,实是《诗》通学勃兴的代表。
(三)《诗》学史料意义
《潜夫论》在引《诗》上很有特色,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本不同,这对于我们考索汉人所见之《诗》学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如《交际》中引《诗》:“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心如结兮。”[2]442文中对《曹风·鸤鸠》诗句的引用、说解与刘向在《列女传·母仪·魏芒慈母传》《说苑·反质》中所引同。刘向为《鲁诗》学者,宋代范处义《逸斋诗补传》卷六就说:“《鲁诗》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可知王符引诗应属《鲁诗》。
在具体诗篇的解说上,《潜夫论》引《诗》有与《毛诗》迥异者,这对我们了解汉代诗说的演变具有一定价值。如《德化》:
《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柅柅。”……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2]486
引《诗》见《大雅·行苇》。《边议》中说“公刘仁德,广被行苇”,《文选》收班彪《北征赋》亦云:“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可以看出,王符同班彪都认为《行苇》一诗是赞美周先祖公刘的,但《毛诗序》的解说是:“《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王符说诗与《毛诗》显异。
《潜夫论》引《诗》在考订一些《诗经》篇目的作者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如《遏利》关于《大雅·桑柔》作者的记载:“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2]35《桑柔》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在谈到《诗经》中作者可考之作时,学者们也不提及《桑柔》,甚至有学者认为芮伯(即芮良夫)所作不可考。这些都是无视文献记载的论调。早在《毛诗序》中就说:“《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云:“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左传·文公元年》也载秦穆公对秦大夫及左右说:“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罪。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孤之谓矣。”[14]516—517《遏利》的记载与《毛诗序》和《左传》中秦穆公所引之《诗》一致,虽论说比较笼统,但至少明确指出《桑柔》是芮良夫劝谏厉王之后而作,其史料意义不容置疑。
此外,《潜夫论》还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诗》说。如《爱日》:“《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引《诗》见《小雅·四牡》,其说《诗》旨意不见于他书,唯《潜夫论》所独有。综上所论,《潜夫论》引《诗》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