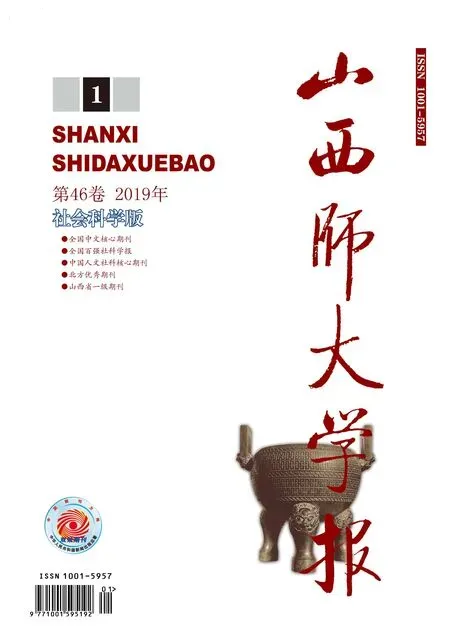“名从主人”是地名规范化的重要原则
----从畖底、洪洞、解州的读音说起
2019-02-22任林深
任 林 深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这里,我们从“畖底、洪洞、解州”三个地名的读音说起,讨论地名(有时也涉及“以地为姓”的姓氏)字的读音问题。这里所说的地名,是指行政地名(市县村镇名),偶尔会联系到自然地名(地形地貌名)。以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把地名和姓氏从字的全部义项中抽离出来单列,其余的义项称为“语词义”。也就是说,下文中的“语词”“语词义”指的是普通语词,是排除了地名和姓氏的。
一、三个地名读音引起的思考
先说“畖底”,《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以下简称《现汉》)1332页:
〔畖〕wā 畖底(wādǐ),地名,在山西。
释文告诉我们:“畖”字不是语词,也不组成语词,它是一个专用于地名,仅用于地名的字,而且全国就只有一个地方叫“畖底”,它的读音是wādǐ。
畖底在山西闻喜县的北垣,过去称村,现在叫镇,分为东畖底、西畖底、中畖底。据调查得知:闻喜北垣没有人读《现汉》标注的音wādǐ,而是“畖”读去声,“底”读轻声:wàdi。两个字的读法都和《现汉》的注音不一样,假如有外地人拿《现汉》的“wādǐ”向闻喜人寻问,闻喜人一时想不到会和村名“畖底” 联系在一起。《现汉》标注的读音没有被当地人理解和接纳,无助于人们的言语交流。
闻喜方言有个特点:古浊母上声字在北垣片与普通话相同,归去声,在城关片归了阳平,调值“213”,“畖底”的“畖”在闻喜北垣片读去声,在城关片正是读作阳平。由这个现象逆推,“畖”字应该是来源于古浊母上声字。但查《广韵》,“畖”列在平声麻韵,乌瓜切,[1]149很明显和今天畖底人的实际读法不一样。究竟是今畖底人与古畖底人的口头读音发生了变化,还是《广韵》的记载原本就另有所据?目前尚不得知。而《现汉》“畖”字注音阴平,和《广韵》一致,和闻喜畖底人的读音不同。
再说“洪洞”,《现汉》1307页:
〔洞〕tóng洪洞,地名,在山西。
这个释文表明,“洞”读tóng也是仅限于山西洪洞县这一个地名。“洞”字,《广韵》有平声东韵徒红切(今音应是tóng),又有去声送韵徒弄切(今音应是dòng)。但《广韵》徒红切有注:“洪洞,县名,在晋州北”[1]3(古晋州即今临汾),意思是县名“洪洞”字应读平声东韵徒红切。但实际上,洪洞人乃至晋南人口头是读作去声tòng。洪洞县名的来历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县城附近有洪崖古洞,“县以洞名”,依此,“洪洞”的“洞”就是指“洪崖古洞”,即“洞穴”的“洞”,这应当就是洪洞人不读阳平读去声的依据。《现汉》的注音和《广韵》的平声东韵徒红切一致,没有采认当地人的实际读音。
三说“解州”,《现汉》1444页:
〔解3〕xiè ①解池,湖名,在山西。②姓。
这里要先顺便说一下:义项①解释“解”为“解池,湖名”,没有提地名解州。按说,解池在不同时期由于属地的变化曾先后叫过“河东盐池”“安邑盐池”“潞池”,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运城盐池”[2]141,“解池”是一个历史曾用名,不是现用名,而“解州”却是一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沿用至今的行政地名(历史上有“解梁”“解县”“解州”等称,所辖区域有宽有窄,行政等级或是县级,或是州级,现在的“解州”是运城市盐湖区属下的一个镇)。作为现代汉语的词典只拿曾用名做解释,不提现用名,似有未周,这是其一。从上述湖名变化情况能够看出,湖名“解池”实得名于“解”地,因“池”属于“解”地才称为“解池”,举“解池”不举“解州”应该说是没有点中“解”字字义之本原,这是其二。再从《现汉》此处所列①②两个义项的关系看,《急就篇》注:“解,地名也,在河东,因地为姓,故晋国多解氏焉。”[3]826《宋本广韵》:“解,亦姓,自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县也。”[1]250可见,义项②的姓氏“解”是由地名“解”而产生的,而“解池”是湖名,与 姓氏“解”没有直接联系,这是其三。综上来看,没有“解州”就没有“解池”,没有“解州”就没有“解”姓,“解州”一词不在这里出现,词语之间、词义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理顺、难以表述清楚。
不过,“解池”的“解”也就是“解州”的“解”,《现汉》把它和姓氏的“解”注音为xiè,这和解州当地的读音不一样,当地人读的是hài。而且受运城解州读音的影响,其周围带“解”字的村镇,以及远一点如太原小店的西里解村、东里解村,忻州的解原,原平的解村,陕西韩城解家村,都读为hài,台湾出的关于解州关帝庙的视频片,其解说词也是读hài。当然也有些地方、有些人读xiè,或受辞书注音的影响本来读hài,后来改读为xiè。据说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有解州村和解州营村,河北保定博野县有解村、解营村,易县有解村,那些地方的人是读为xiè[4],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也读xiè。但地名和姓氏“解”的原生地是山西运城的解州,在这里向来是读hài。《现汉》地名和姓氏“解”的注音没有顾及这个实际情况。
《现汉》的注音一般代表普通话的标准音,是现代汉语的规范读音,上举“畖”“洞”“解”三个地名字“注音”和“读音”的不一致(“畖底”的“底”读轻声是连读的问题,暂不讨论)牵带出两个问题促人再思考:一是地名的规范读音从哪里来?比如“畖”,如果来自古韵书(比如《广韵》),的确,古平声字今读不可能是去声,但是在没有类比、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怎么能说明这个独一无二的村名的读音古韵书的记载是真实可信可凭的?二是地名的规范读音需要不需要、寻求不寻求得到地名主人的认可和接纳?比如“畖”字,词典的注音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或影响闻喜人“畖底”的实际读音,规范化的目的和效果如何体现?
二、复杂的地名读音
我国地名的读音情形比较复杂。有些字在现代汉语里只用于地名,不用于语词,成了专用地名字,其中有的本来就是专为地名造的字,甚至是专为“这一个”地名造的字。如“畖”字,不用于语词,且只指称山西闻喜县的一个村子;“汫”字只广东有个“汫洲镇”;“奤”“夿”字只北京有个“奤夿屯”;“岜”字用作地名,山东有“岜山”、广西有“岜谋”。像这样的地名专用字,没有语词义、语词音可比照,应该说,当地人对地名的实际读音就是这个字的唯一读音,只要它没有逸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直接认它为规范读音,比较切于实用,当地人满意,外地人也不会有异议。像“畖”字,假如一定要拿字典的“规范读音”去“规范”畖底人的“不规范读音”,可能是用力甚巨、耗时甚长而收效甚微、甚慢,有点出力不得好。
大多数地名是使用现成的、普通语词的字,这是兼用地名字。兼用地名字中有一部分其地名读音和语词读音不一样,形成地名的特殊读音,如:“犍”jiān(四川“犍为”读qián )、“铅”qiān(江西“铅山”读yán)、“单”dān(山东“单县”读shàn)、“峙”zhì(山西“繁峙”读shì)、“六”liù(安徽“六安”读lù)、“歙”xī(安徽“歙县”读shè)、“任”rèn(河北“任县”“任丘”读rén)等,就是同一个字作为地名的读音和作为语词的读音不一样,是有特殊读音的兼用地名字。上举地名的特殊读音已经被认作规范读音(《现汉》没有收“六安”)。但村镇地名目前大都没有规范化的报告,其中有特殊读音的地名字有待调查和研究。
地名的方言读音。如普通话的pei音在闻喜方言中读pi(如“陪配赔呸佩胚培沛辔”),闻喜县有名的“中华宰相村”——“裴柏”,闻喜方言读作píbiè。再如闻喜方言中有普通话的ding读作die(如“钉”)、ting读作tie(如“听”)、ling读作lie(如“凌岭铃”)、ning读作nie(如“宁”)这种鼻韵尾脱落的情形,但现在只存在于个别字、个别义,不够普遍,不成系统。闻喜方言的“丁”字在语词“甲乙丙丁”和姓氏中都同普通话一样,读dīng,唯有在“上丁、 下丁、丁店”等几个村名中却读成diē,明显是保留了方言历史音变的痕迹,研究语言的人会视此为珍贵资料。方言读音和普通话读音有对应规律,可以自动自由转换,不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和沟通,闻喜人虽然自己读“裴柏”为píbiè、读“丁店”为diēdian,但对于普通话的读音既能理解不产生歧义(可解),又能接纳而不排斥(可容),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各自在一定场合使用,形成双语现象,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特别情况下,某些地名的方言读音有进入规范读音的诉求,需要区分情况分析对待。
有一些村镇地名字读音很特别,不仅和普通话读音不同,也看不到和它所在地区的方言音系的联系。如:现时的闻喜方言音系中普通话的yu音没有读成you的规律,但“峪”(yù)在闻喜的村名中却一律读成了yōu,如“宽峪、蒿峪、西峪、东峪、吉家峪、柴家峪、峪堡、峪口”这些村名。“冰”字闻喜方言语词中音dīng,但在村名“冰池”中读成tié。 “头”字,在语词中和大多数村名(如:店头、五里头、庄儿头、寺头、酒务头、窑头沟)中,闻喜人都读tóu,和普通话读音一样,唯独在“户头”“户头庄”两个村名中读成tú。“张”在闻喜方言中读zhāng(如姓氏和“一张纸”)或zhē(如“张开嘴”和村名“南张”),唯独在村名“张石沟”中读成jiē。闻喜还有个很特别的村名“王村”,这个“王”字闻喜人读yué。临汾市区有个区域叫“坂下”,当地人把“坂”(bǎn)读成fàn。以上这些地名的特殊读音,从共时的角度看,不是方言音系的原因形成的,不能视同一般的方言读音,但是在地方范围内流行已久,难以改变,也不思改变、不愿改变,其中一定包含有人们至今未获知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信息,有待揭示和发掘,不可轻易否定和扬弃。
有些地名字只用于一个地名,可称它独地名字。像“犍”(犍为)、“铅”(铅山)、“畖”(畖底)、“洞”(洪洞)、“奤”“夿”(奤夿屯)等,至今没发现有第二个地名用到。这样的地名只指称一个地方,讨论起来总属于个案、个例,不存在异读的比较、辨正和选择等问题。
有些地名字出现在两个以上地名中,是多地名字。有的多地名字使用地方虽多,却读音一致,没有分歧。如“任”,河北有县名“任县”“任丘”,山西闻喜县有村名“任村”“任村庄”“任家山”,这些地名以及姓氏中的“任”都读阳平。有的多地名字在不同地名中读音不同,如“解”字,现实中存在“hài”“xiè”两个读音。《现汉》取xiè弃hài,以xiè为规范读音。
讨论地名读音,有一个现象一定不能忽视或轻视,那就是地方强势的影响和作用。所谓地方强势指的是地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保有丰富或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地方的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广。地方具有强势,其发言权也就有了强势,本地人对地名的读音容易被外人接纳而成为社会大众的读音;地方具有强势,地名的地方读音往往和地方文化、和当地人们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承载了丰厚的人文精神。如洪洞县有明代大移民的历史记忆,京剧《玉堂春》许多剧种有移植,唱遍全国,其故事发生在洪洞县,几乎妇孺皆知。由于地方强势的关系,洪洞人“洪洞”的读音tòng,已扩延到方言圈以外的广大地域,成为社会的共识。山西运城的解州具有悠久的历史,解州关帝庙名闻海内外,解州的盐池(解池)是历史上著名的产盐之地,运城的解州又是全国“解”姓之肇始和多处“解”地之源头,因而当地人“解”的读音hài,影响远,历时久,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地方强势使该地方进入了社会的公共话题,共用当地的读音不仅能够方便人们的互相交流沟通,而且传达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顺应了人们的感情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语言发展的约定俗成规律的一种表现。
地名的读音一定和命名之因、命名之源、命名之意趣、命名之祈愿以及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习俗有联系,有自己的缘由和理据。单纯从语言的角度看,除了方言读音如闻喜的“裴”“丁”等以外,不排除有的是为了区别而产生异读,或者说因为异读而提高了字的区别度。如“任”,语词读去声,地名和姓氏读阳平,提高了“任”的区别度;“犍”,从字形看,应是为犍牛造的字,借用为地名“犍为”,犍牛读居言切,犍为读渠言切,“犍”的音义相配关系区别明显。有的是字的来源不同,如太原西北方向有一山,现存古代文献(方志、碑刻和书画作品等)大都写作“崛山圍山”。据明末清初学者傅山(也是当地出生、在当地生活的人)的说法,此山是因山势“屈而围之”而得名的,朱彝尊考查考证认为此山名本字应该是“屈围”,累增形旁“山”成了“崛山圍”,可见这个“崛”本就是“屈”的意思,并非“崛起”的“崛”,字的来源不同,此“崛”非彼“崛”[5]。而如闻喜县的“李家庄”“王家房”“吉家峪”,闻喜人把“家”读成a轻声,显然是为了追求语速而脱落声母,是临时发生的连读音变现象,和单字音无关。另外,有的读音也许原本就是误读,起于误读,习误成俗。“繁峙县”的“峙”、临汾市“坂下”的“坂”,应该就是误依声旁分别读成了shì和fàn,而语词的“峙”和“坂”在当地又是个生僻字,日常几乎用不到,缺乏比照,误读之“误”显不出来,误读就一直延续至今了。重庆市永川区有个颇有名气的古镇“松溉”,当地人“溉”读jì。据说此镇依山傍水,山叫“松子山”,水叫“溉水”,山水各取首字而成地名“松溉”。我想,“溉”字也许和太原崛山圍山的“崛”字相类,水名原本就是“既水”,因为是水名,“既”字加形旁“氵”成了“溉”,然而它和原有的“灌溉”字撞了车,造成读音相混,这是由于字的来源不同带来的特殊读音。但当地的说法不是这样,当地传说是历史上曾有地位高贵的人来到此地偶然误读“溉”为 jì,大家崇拜名人,把这个误读和误读的故事一并当作地方文化因子,当作地方的标签和名片着意加以保留,不愿改变,这就属于误读造成的特殊读音了。当然,如上举闻喜县“张石沟”的“张”、“王村”的“王”等至今没有弄清缘由,有待后续研究的地名更是不少。
三、名从主人
地名读音的规范化是语言规范化的一个部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上述地名读音的复杂情形也正说明地名读音规范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语言规范化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规范化的观念和路径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就像语词中的“老抽”“生抽”,其构词方式同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一般构词规律完全不同,我们根本无法从它的字义推知它的词义,但现在纳入了现代汉语的词库,成了规范词。地名规范化的目的是方便人们的交际交流和沟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在观念、标准和路径上也需要适应时代要求做出必要的调整。
地名读音是当地人长期口耳相传下来的,想要知道地名的确切读音,需要深入当地做调查了解。古代辞书由于受观念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地名的实地调查、搜集整理、记录表述各环节不能保证全都科学严密周全周到。即便古书的记载是采自当时当地实际存在的读音,一千多年人们口耳相传产生音变也是可能的,而且这种音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一定遵照一般语词古今音变的规律。我们今天只有先对地名的实际情形做深入调查,然后再参考古韵书的记载,依据古今音变的轨迹和规律,综合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才是可靠的。
约定俗成是语言学研究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重视的一条规律。而“名从主人”就是约定俗成原则在地名人名(以及某些地方特产的物名)中的延伸和适用,它不是凭空制定的条例,而原本是由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自觉遵守,逐渐成为处理地名人名物名的通行原则。地名和语词相比,有特殊之处,它起源于地方,流行于地方,为地方所有,也首先为地方服务。如果说语词要强调小众服从大众,那么地名则须要大众尊重小众、接纳小众。比如“六”字,在长江沿线许多地方的方言中都读作lù,是方言读音,但数字“六”是语词,在当地可以自然转换为普通话读音liù,小众顺从大众;而地名“六安”的“六”,当地人却要坚持读作lù,于是大众理解小众、尊重小众,跟着一起读lù了。可见,语词的规范化和地名的规范化其目的相同而路径可以有别。
名从主人,简单平白地说,就是在地名读音规范化的时候,如果遇到外地人(客人)的读音和当地人(主人)的读音不一致,遇到今音和古音不相同,通行于民间的读音和古韵书记载的反切音不合,等等情形,则从主不从客,从今不从古,依俗不依书。总之,名从主人的指向在基层,在民间,在现实。
地名读音的复杂,给规范化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多彩多色的地名读音也未尝不是一笔宝贵的人文财富,它蕴含着丰富的、有待开发的社会人文资源,对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以至文学艺术各学科将会提供研究的新材料、新依据,并藉以产生新发现、新发明。调查了解、记录描写现实存在的地名读音,不仅直接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方便,也不仅为地名读音的规范化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是规范化的基础性工作,而且是对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
各县市的地方志和方言志对于本地的地名成因、地名演变、地名用字、地名读音都有相当的篇幅做记载,留有可宝贵的资料和信息,但由于编辑主旨的侧重点不同,现有的县市地方志对地名字的读音普遍关注较少,方言志对于地名读音虽然十分重视,却缺乏统一要求,往往是随机采录。基于此,全国地名普查目前就显得十分必要,需要纳入课题,统一策划部署,动员相当的人力实施。参与普查工作的人员需要掌握方言调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把全国村以上地名的实际读音一个不漏地、如实地记录下来,科学地描写出来,并通过编写地名志把地名读音的实际情形反映出来,报告出来,这是一项大工程。这里所说的“如实地记录”指的是记录描写地名存在于人们口头的真实读音,原始的读音。当然,方言读音需要按照当地方言音系与普通话音系的对应规律进行系统转换,使其纳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这是地名读音规范化的初始的也是必需的一个步骤。这样,地名志主要是地名的原始资料库,它告诉人们在当地这个地名是这样读的,至于这样读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留待下一步规范化再考虑。地名普查不等于地名规范化,但地名规范化一定要以地名普查的成果为起始点。
“名从主人”既是地名规范化需要遵守的一条规则,又不妨把它看作地名规范化可资利用的有效工具,充分利用这个原则有利于认识和处理复杂的地名读音问题。比如上文所举地名读音区别于语词的种种情况,如果站在“名从主人”的角度去考虑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名从主人”的原则去认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