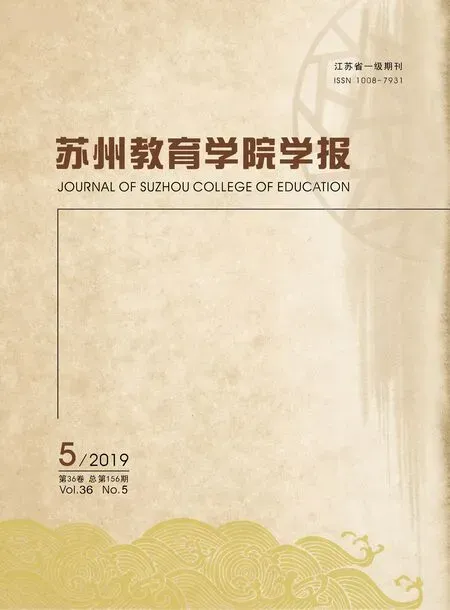“理想主义”思想方法的跨越性批判
——陈映真文论再解读
2019-02-21谭君
谭 君
(潍坊光正实验学校,山东 潍坊 261021)
从1975年出狱到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面对全球各地尤其是大陆及西方等发生的政治经济事件和局势变动,发表了不少评论性文章。从中可见陈映真的“理想主义”不断受到挑战和更新,他的“理想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情感态度到思想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陈映真对民族、国家和资本的跨越性批判之中。
一、20世纪60年代陈映真的“理想主义”
出生和成长于台湾的作家陈映真对大陆的感情与认知来自其父亲收藏的大陆文学作品,在《关于陈映真》中作家回忆到: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随着年月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老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困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1]15
由于台湾被日本殖民的经历和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形成两岸分离的格局,陈映真对大陆的认识主要来自文学作品的塑造。对于幼年甚至青少年时期的陈映真来说,其思想构型中想象出一个“苦难的、贫困的”大陆形象,从而使其形成了知识分子企图改造贫困中国的思想苦闷和精神动力。但对陈映真而言,不同的地方在于,此种“想象”缺乏此时此地的体验,也正因为如此,“想象”一旦固定下来也就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磨灭性。这也成为出狱后的陈映真在面对变化的大陆的历史现实时的认知前提,是其之后发表的一系列针对大陆历史的评论文章的基础。
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对于苦难中国的认知,与陈映真从小生活的基督教家庭环境以及从禁书中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2]20,共同构成了陈映真入狱前的三股思想驱动力,而其中对苦难中国的认知更是作为思想底色驱使陈映真走上思想激进和组织实践的道路。与此同时,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映真受到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内心希望组织运动实践的渴望越发明显,他直言不讳地剖白到:“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思潮的影响,实甚明显,而正是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1]22-23
陈映真在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国民党当局以组织读书会聚读马列共产主义、为共产党宣传为由而被捕。多年以后,台湾学者陈光兴对读书会当事人日本教授浅井文基进行了采访,访谈大体回忆了读书会的阅读内容、台湾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陈映真的思想状态。读书会阅读的基本为马克思与毛泽东等人的经典理论著作,浅井文基谈到“除了毛泽东的作品之外,我想陈映真和其他主要从他们自己的想法出发来写东西。我仍然记得,他非常关切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很想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3]。
访谈中有另一处值得注意,这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大陆“文革”爆发初期,陈映真对大陆的感情认同与共产主义追求之间的关系,这也关系到此时期陈映真的“理想主义”思想方法的内在构成与张力体系。
陈光兴: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脉络下,统或独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主要的分野,但现在则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人们试图找出这种差异是否在当时就已经生根,您对这方面的感觉和理解是什么?
浅井文基:陈映真的立场非常清楚:只要是同意统一的必要性,那个人就是陈映真的朋友,无论那个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那是当时台湾的状况,若不这样,每个人都会彼此隔阂和不团结,但其实正因为他们都是绝对少数,更需要彼此团结。这是陈映真的基本想法。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信与投入是如此一致,以致于他可能觉得必须把自己这方面的坚信藏起来不让人看到,如此他们的友谊才能维持下去。
陈:如果我的理解正确,在当时那个历史时刻,共产主义和统一是同一件事。
浅井:对,对陈映真来说是的。
陈:但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
浅井:他比较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解决之道。[3]
也就是说,陈映真对大陆强烈的感情认同在台湾还未形成鲜明的统独分裂的时期就已经非常坚定了。陈映真就是带着强烈的统一愿望,并且在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大陆“文革”风潮的感染之后,希望进行组织运动的。此时的社会主义大陆对陈映真来说,不仅是从小说中认识到的贫困的需要知识分子启蒙和解放的大陆,由于“文革”的发生,更成为陈映真可以将共产主义思想运用于实践的场所,就像浅井文基所回答的:他(陈映真)比较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但陈映真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解决之道。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的大陆作为遥远的坚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陈映真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毅然决然走向国民党专制的对立面,也因此为他带来了十年的牢狱之灾。
陈映真入狱之前的“理想主义”思考机制中的组成和张力结构,包括基督教的宗教背景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理想主义。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陈映真从小生活的基督教家庭环境所带来的宗教因素也是此“理想主义”的重要构成,但因为陈映真此时期的宗教思想因素一直处于不断被自我怀疑审视的状态,并多被统合进共产主义思考当中,其宗教因素中真正可以成为陈映真“理想主义”的抵抗力量的一面并没有成为思考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宗教、民族与共产主义这三方面的因素不断起伏缠绕,加之每个部分又有不同的理解的切入点,共同构成了陈映真“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并成为支撑陈映真面对变化的历史格局时不断扬弃和坚持的精神力量。
二、民族作为“想象”的不可消解性
以上是对陈映真入狱之前思想脉络的回顾。陈映真在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对狱中的经历,陈映真甚少提及。归来之后的陈映真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大陆与台湾现实,他的“理想主义”又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和调整。
入狱前,“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陈映真眼中是理想的共产主义运动样式,陈映真期待的结果是“文革”的风潮可以给大陆人民带来自由与解放,但在出狱后的几年中,通过对“文革”信息的接受,陈映真发现想象中的理想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结果,也就是说,之前形成的以大陆认同为纽带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方法面临冲击。这在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评论文章中有所体现:
噢,近一年来,大陆的资讯,空前大量的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报纸、杂志上。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动的影像。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然而,我终于觉得不对头。像巴金的萧珊受到那样的待遇的共产党,和我读史诺《中国的红星》里的共产党,怎么也不对头……。这半年来,我一直处在慢性的思想苦闷里头。[2]34
对“文革”真实状况的某种程度的了解给陈映真带来思想上的苦闷,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实践形式破灭,但在以大陆认同为纽带的思想底色中,民族主义的因素使陈映真在此时期面对“文革”的幻灭从而转向了以“人民”为总体的叙述。贺照田在《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一)》中,对陈映真关于“文革”的看法陷入知识分子与人民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有所批评:“这使得80年代初的陈映真虽然在情感上和极度反共的人们不同调。但他的批评大陆文字的基本内容,却与他实际非常有距离的极度反共的人们的相关文字,无论在视野聚焦上、问题的把握方式上,并没有多少实质不同。”[4]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陈映真在对“文革”反思的基础上由对大陆的认同转向对“人民”的认同,其视野聚焦、问题的把握方式上的缺陷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就是陈映真从一开始对大陆的认同就建立在缺乏此时此地经验感受的文学作品的塑造之上,其对大陆的认同可以归结为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的性质特点决定了认同的不可动摇性和连续性。陈映真对大陆的认同所反映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属性,也许是更值得关注的角度,正如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中阐述的:
民族并非资本——国家的被动产物,其本身是作为对抗资本——国家的东西出现的,我们无法仅仅在劳动力和经济利益的维度上来谈论它。相反,民族蕴含着对资本和国家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它基于感情这一维度。[5]189
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也并非是“空想”而是“想象”,这一点值得留意。换言之,它具有单靠启蒙无法消除掉的存在依据。[5]193
陈映真出狱后的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左翼思潮高涨的时期,大陆的“文革”、海外的“保钓运动”延伸到台湾本地,在反对西化的浪潮中,台湾发生了“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在文学领域,陈映真确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文学观:
“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运动……这个变化,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6]
陈映真在台湾“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中敏锐地发现了台湾内部分离主义言论的兴起,这也成为今日大陆与台湾和台湾内部不同立场之争的开端。“民族”作为感情因素在陈映真“理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构造中的稳定性,使陈映真自始至终都作为一个坚定的“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自我约束,如浅井文基对陈映真的总结——“他比较是民族主义者”。大陆与台湾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认同分歧,尤其是陈映真面对的台湾社会中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疑都证明了“民族”作为一种感情因素具有无法消解的性质,所以当不同立场的“民族”感情相互碰撞时,之间的分歧与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该思想状况一直持续存在于大陆与台湾和台湾内部之中:“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认可政治的复杂与麻烦,以及左、右、新统派在认可的必然分歧——这些分歧归根究底则是:左统认可社会主义中国、右统认可传统或历史文化中国、新统认可现实中国,以及由此分歧衍生或连带的各种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认可或不认可的复杂组合。”[7]261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方面,大陆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台湾内部的“现代诗论争”与“乡土文学论战”使台湾岛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台湾的分离主义情绪开始明显化,而这对于陈映真来说是必须要面对的思想课题。在80年代的评论文章中,面对霸权国家侵略的现实和弱小国家贫弱的社会,陈映真将作为感情存在的“民族”因素转移到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当中: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2]5
我们真该好好珍惜自己,更深入去理解第三世界和他的文学,更努力在文学上做出成绩来。……我们觉得第三世界文学家们,他们的历史、思想的焦点很明白。他们关心社会、民族、祖国的前途。他们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应有的尊严。从他们的谈话和作品中,他们向外看人和人的命运。[2]28
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认识,是对以国家为载体的民族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克服,尤其对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热烈拥抱现代化的大陆,仍有不断提起的必要,如赵刚指出的:“最近重读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我鲜明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的、台湾的也是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陈映真,他所争取的核心之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所争取的那种主体性与尊严。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心灵动力可以被今日污名化了的‘民族主义’所能适切表达的。或至少,这种民族主义和独派或台派的族群民族主义是鸡兔不同笼的。”[7]252
三、宗教批判——“真理的伦理条件”
陈映真从小生活的基督教氛围的家庭环境,也是他的小说创作和“理想主义”思想方法构成的重要一环。在入狱前的作品中,陈映真对宗教因素的理解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并对基督教信仰有侧重地进行批判、扬弃和再运用。
在20世纪60年代,即陈映真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陈映真的宗教(基督教)批判多与这一时期他获得的共产主义信仰构成某种缠绕,陈映真对基督教的侧重也放在了与共产主义的获得需要付诸实践的冲动相同的位置。比如在前期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中,作品以康雄姐姐为叙述者,康雄突然自杀,姐姐带着寻找真相的冲动阅读了康雄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弟弟思想上受到乌托邦、安纳其主义熏染,由于贫困赚取学费却爱上客寓的主妇。但是生长于基督教家庭的康雄最后以赎罪的态度选择自杀,而姐姐却以摆脱贫困为名嫁入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并且获得了康雄没有实现的行动的反叛的快感。
又比如集中体现陈映真对基督教宗教教义批判的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小说以圣经中耶稣与犹大的故事为原型,主人公犹大有解放民众于罗马统治的愿望,但缺乏行动力,只能在爱欲中获得生命力。犹大对于以耶和华名义执政的世俗政权对民众的欺骗性有清醒的批判:“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既然,冒着万险自罗马人手中图谋他们的权柄,那么将来分享这权柄的,除了你们还有谁呢?你们将为以色列人立一个王,设立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来统治。然而这一切对于大部分流落困顿的以色列又有什么改变呢?耶和华所哀哭的既不只是为着你们,那么他将复兴也不只是你们的罢!”[8]85对于以耶和华为名义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犹大深表怀疑。陈映真借犹大之口,说出了他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体会,政治只是政权更迭,却没有给民众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世俗宗教可能成为被政治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
犹大一直在寻找可以给民众带来解放的思想或强力的人格力量,在见到耶稣之后,“犹大想着现在他所找着的绝不只是一个像其他野心的十一个师兄所料想的政治的弥赛亚。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的弥赛亚。他终于找到他的思想的偶像了;他自知自己缺乏行动的魄力,如今他找到了那正是他所缺少的,极为聪明的行动家了”[8]93。犹大把耶稣看作可以领导民众获得解放的激进的行动者,但当犹大发觉耶稣没有行动的意向,他陷入轻微的失望。在数次耶稣与民众的欢聚后,犹大以为这就是耶稣带领人民行动的契机,然而民众在欢庆之后,又满足地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已经明白耶稣真正的不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抱有野心,但另一方面犹大却发现了以色列人对耶稣那绝对无可取代的爱戴。”[8]98所以,犹大决定出卖这个既无法带领民众行动却又拥有民众爱戴的耶稣。最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民众也成了送耶稣上十字架的看客。小说结尾以纪念的口吻记载了犹大吊死的结局。
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的陈映真对宗教因素的批判,多侧重于基督教促进人类解放激进的一面和世俗宗教欺罔的一面。在入狱之前的1967年,也即陈映真前期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最牢固的磐石》中,陈映真集中发表了对于宗教的看法,并且提出了“真理的伦理条件”的批判维度。
神父不在圣经中寻找“爱人如己”和施舍的这么一个简单福音,却强调财富的祝福是神所分配与应允的教训。“爱”、“正义”、“怜悯”是世界一切宗教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然而,一直到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因为肤色而拒绝一个人进入教会团体的事。
这样,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中,便有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道理,至此,真理便有了伦理条件;真理只对于那些站在正确立场——正义立场的人说话,就如真理只面对起而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却背向日本军国主义劫掠者一样。[1]96
四、自尊心与人道爱——“民族”与“宗教”伦理的共同跨越
陈映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对于宗教的看法获得了“真理的伦理条件”的批判维度,其批判维度的获得与“民族”这一“想象”作为感情因素的不可消解性有关。也就是说,陈映真在某种想象的“宗教”与“民族”的互相缠绕和互相批判中,不断确立自己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
在《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二)》中,贺照田把陈映真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贺大哥》作为其反思理想主义的重要文本,贺照田分析的前提是将小说置于陈映真经历了“文革”真相的冲击这一背景之上,但他也指出:“有意思的是,陈映真有关不理想条件下的理想主义的表述,集中在他写于1978年初的小说《贺大哥》中。其时,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在大陆开始大规模被公开、揭露,而陈映真尚无所知。”[9]
《贺大哥》中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到底应该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上。小说主人公贺大哥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经历过越战的青年,因为战争的伤害曾一度患有精神分裂。陈映真将主人公安排为一个美国青年并不是无意之举,在写于1967年的《最牢固的磐石》中,陈映真就写道:“似乎从来没有过一个民族,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需要用药剂来帮助他们生活在另一个非现实底世界里。”[1]90也就是说,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式的资本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果和生活方式对身处台湾的陈映真来说,一直是需要反思和警惕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模式,尤其是在陈映真出狱后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世界性的左翼潮流也曾在美国发生,西方式(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台湾全方位渗透,陈映真正是在这个时期创作了《贺大哥》。但陈映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左翼思潮与自己坚守以待的理想主义之间的距离,陈映真并没有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全面拥抱这种西方式的“理想主义”,因为他看到了霸权式的发展带来的战争与灾难,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美国人也同样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于是他以一位美国青年贺大哥为主角创作了这篇小说。
小说以台湾女生“我”和美国青年贺大哥的交往谈话为载体,对基督教思想和曾经左翼思潮盛行的美国社会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进行了反思。小说中,陈映真试图超越“民族”与“宗教”,开始显现了新的思考维度。陈映真首先借贺大哥之口对世俗宗教的欺罔性进行批判:
“贺大哥,你说,”我终于说,“你说你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他说。
……
“如果去爱人,如果……啊,我没法用中文说。”
他于是用英语说,如果去爱人类同胞,变得需要有一个理由,这就告诉我们:关心别人的事,竟只成为一些称为这个或者那个宗教的教徒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人的世界。”[10]275-276
紧接着,陈映真将贺大哥塑造成曾经接受过共产主义知识的青年。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波及美国,促成了贺大哥对“革命”的向往:
“在六十年代,美国也有过类似的运动。”贺大哥用英语说:“那时的美国青年,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对美国的富裕,提出道德方面的质问;对美国国家永不犯错的神话,提出了无情的批判。”
那时候还在大学读书的贺大哥,“曾以为美国的‘革命’就在眼前。”
“你简直就觉得,那美丽的世界已经在望,”他说,“一个新的、美丽的美国啊。”[10]279
但是发生在美国的“左翼运动”破产,贺大哥也被卷入越战当中,成为一名侵略他国的、加害于人的人。不管是来自宗教还是战争带来的左翼信仰的幻灭,都没有让贺大哥彻底放弃,而是在战争的残酷当中获得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
我忧愁地、笔直地望着他,说,“那么,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实现,是十百世以后的事,你从哪去支取生活的力量啊。”
……
“不,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相信,”贺大哥虔敬地说,“爱,无条件爱人类,无条件相信人类。”这样的爱,时常带着因着我们所爱的对象的不了解,而使施爱的人受到挫折、失望。“但是,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照顾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照顾自己不在你的受挫折之后,冷淡了爱的能力,”贺大哥说,“让我们也相信一切、一切的人——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着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险。但是,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他说,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贺大哥说,“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10]279-280
陈映真借美国青年贺大哥之口,揭示了西方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理想主义”的脆弱性,但是同样也是借贺大哥之口,陈映真形成了可以超越“宗教”与“民族”的新的思想维度——以人为基准的爱与希望。正如柄谷行人对“宗教”的分析:“我们不能由于否定了宗教,就把只有通过宗教才能揭示出来的‘伦理’也丧失掉。”[5]207陈映真对贺大哥思想变动的形塑基本可以概括为——对宗教的欺罔性进行批判但同时保留其中“爱与希望”的伦理成分。通过贺大哥在战争中同时作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双重心理认同,最终走向了贺大哥对于以人为基准的“爱与希望”的认同。也就是说,陈映真在出狱之初的1978年,就已经通过小说《贺大哥》的创作,对以往“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中的民族、宗教与共产主义等维度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扬弃,走向了“爱与希望”的获得。
20世纪80年代以“爱与希望”为核心的陈映真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泛的话语,可以在其当时的具体活动、文章和小说创作中得到不断确认。面对当时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业已形成的消费社会中人的处境,对宗教、民族的超越发生于“资本、民族、国家”的一体结构之中。但陈映真的“理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最终确认,得益于陈映真与印度哲学家甘地的“相遇”:
在历史和生活还没有教育甘地更深刻得认识到英殖民主义的本质以前,甘地要求取得女王之前的平等的单纯性,预告了甘地日后行动和力量最丰富的源泉:对于真理和人的尊严的单纯的、毫无假借的信仰。他单纯的相信爱。为了爱残破的祖国和水火中的人民,也为了爱在压迫的罪恶中的统治者,他坚定的走上不抵抗的抵抗之路。[11]
一方面,甘地像引路人一样给获得“爱与希望”信念的陈映真以实践上的切实的例子;另一方面,当时陈映真所处的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这一概念揭示出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将劳动者作为消费者进行认识的阶段,在柄谷行人的论述中,这一身份的转变蕴藏着人获得主体性进行资本抵抗的契机:
我的重视消费者运动,看上去与葛兰西关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重视家庭、学校、教会等文化意识形态机构之重要性的观点相似,其实不然。葛兰西依然期待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阶级的起义,而致力于发现妨碍阶级起义的各种文化霸权,我要强调的是,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看做资本为了自我实现必须经过流通过程,并将作为劳动者成为主体的“场域”来重新认识。[12]
综上所述,陈映真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论中体现出的“理想主义”,既是对60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更是面对“民族”“宗教”“人间”等诸多现实境况引起心灵深处思想激荡的结果。陈映真的“理想主义”从情感态度到思想方法的转变,不仅代表了陈映真思想的成熟,也是其思想不断通过现实来指导社会实践和进行自我改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