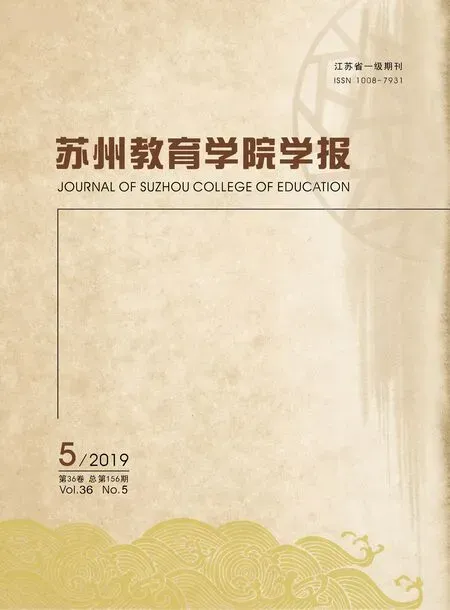穆紫荆:在东西方之间寻找表达自我的可能
2019-02-21朱云霞采访整理
朱云霞(采访,整理)
(中国矿业大学 中文系,江苏 徐州 221116)
穆紫荆,德籍华人作家,1962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德留学,后定居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作品见诸欧美华文报刊,在海内外多次获奖,被收入各种合集,著有散文集《又回伊甸》、短篇小说集《归梦湖边》、中短篇小说《情事》、诗集《趟过如火的河流》、精选集《黄昏香起牵挂来》及长篇小说《活在纳粹之后》(又名《战后》)。参与主编的作品有《东张西望看欧洲的家庭教育》《欧洲绿生活》《且待蔷薇红遍》《且待君归于侧》《流云又送南归雁》《相携日月同辉处》《天那边的笛声》《海这边的足迹》。穆紫荆现担任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欧洲华文诗歌会创始人兼会长、国际新媒体组织副秘书长、德国八音音乐艺术学校文学顾问和指导、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特聘教授(2017——2020)、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庐山陶渊明诗社副社长等。
朱云霞(以下简称“朱”):对于作家来说,个体的成长经历、生活体验、教育背景等都对文学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您的外公郭绍虞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史家,他早年是“新潮社”的成员、《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员,还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您的祖父曾在清华大学英语系任教,父母亲分别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和同济大学文学院。因此在国内有评论者如宋晓英教授说您是从上海“名门”的“闺阁”走向世界,能不能谈谈家庭背景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穆紫荆(以下简称“穆”):我的家庭背景中的文学和文化艺术元素,确实对我影响很大,也很深。首先,小学期间有三年时间我是在外婆外公家借读的,耳濡目染外公著书立说和外婆帮忙抄写的种种情形。此外,无论是外公家还是我们自己家都是藏书满壁,所以我从小就很爱看书和读古诗词。其次,我从小就学英语,从中学时开始读家里的英语小说,还有一本我父亲的英国的图画字典。最后,我父亲收藏了很多乐器、唱片和画,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姐夫是画家,我会弹钢琴、敲木琴、拉手风琴。这些都在我日后的写作中留下了痕迹。比如有读者给我写道:“喜欢读你的文章,语言朴实,很有画面感。”我想都得益于童年的熏陶。
朱:就教育背景来看,您是中文科班出身,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外联室担任翻译工作,1987年出国留学后就定居德国。可以说出国前的这些经历跟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有趣的是,您是在出国近十年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穆:我出国的头十年,一直都在为生存而努力。上学,然后工作、结婚。结婚后七年没有要孩子,就是想等自己的工作、驾照、包括户籍这些现实问题都落实稳定之后,婚姻也更稳定了,再要孩子,这样可以给孩子一个幸福生活的保障,有了孩子之后,也是在家里照顾了孩子近十年。触发我写作的冲动是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和孩子在一起的最初七年,因为孩子很需要你,所以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需求,可以说将自己的精神需求一直放在了家庭和孩子之后。但是等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他们对母亲的依赖不是那么多了,我的内心就空出了一些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存在心里,慢慢越积越多,有了想要讲出来的欲望。这里有个契机,就是我跟在美国的好朋友Rebecca Chen通信,讲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她在读我的信的时候,认为我的写作能力很好,鼓励我写作,给美国旧金山的《星岛日报》副刊投稿,我就试着通过她给报纸投稿,编辑读了后很满意,就约我每周写一到两篇800字的文章,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和发表。第三是在1994年,我信仰了基督教,这也使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待自己和生活,有了明确的观点,便更想要说出来。
朱:对,在我的阅读体验里,就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比如您和施玮,都信仰基督教,反映在作品中,便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审美风格。你们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光亮,这种光亮是有爱的温暖的向上的力量,又不同于当下流行的鸡汤似的爱和温暖,是可以穿透灵魂深处的温度感。
穆:基督教信仰确实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影响,影响了我看待世界、思考人性的角度。
朱:您最初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主要是写什么主题的作品呢?在经历了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之后,写作对您来说应该是重新发现了自己,是很愉悦的吧?
穆: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乡愁,像散文《米糕》,当时主要是想写给旧金山的老华侨们看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有浓郁的乡愁。因为是给美国的报纸写稿子,所以一方面在文章中透露自己身在海外的身份,另一方面会很刻意地隐藏自己身上的欧洲元素。这个时期的写作对于乡愁的纾解很重要,比如“米糕”这种主题,其实是我在德国无数次梦到在自己家附近的早餐店里吃米糕,可以说是把自己最真切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来。
朱:刚才您谈到了自己的婚姻、家庭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您在出国两年后的1989年嫁给了您的先生,一个德国人。您的这个决定在新移民中应该是比较独特的选择,婚后七年没有要孩子,是对跨国婚姻有担忧吗?
穆:是的。1987年我来到德国,当时在德国的自费留学生很少,我是属于第一批的。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多是公费生,他们大多都有了家庭,而且都是读理工科的,我和他们接触很少,很难融入他们那个圈子。在自费留学生中,亚洲人,尤其是大陆人极少,大多是台湾和东南亚的,我也进不了那个圈子。当然这也和我不热衷交际有关。我到德国以后在东亚系认识了我先生,他在北京大学留学过,汉语说得很好,对中国的了解也很多,对我来说,他像半个中国人。我们两个又是在同一个系里跟着同一个教授,所以和他接触的机会比其他中国人多,认识两年,彼此比较了解后,才结婚。在相处的过程中,虽然很好,但是就语言和文化角度来说,身处德国,我对德国整体上了解很差,我是弱势的,他是主导。结婚后确实面临很现实的问题,我考虑得比较多,尤其是婚姻的稳固性,生了孩子万一分开,因为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差异、制度差异,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还是选择先工作,在一家台湾电脑公司做市场开拓,先让生活稳定下来。当然,我们的婚姻中确实也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一些误解。
朱:您是1987年留学德国的,能不能谈谈当时选择出国的原因?
穆:当时选择出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留学潮,大家都寻找机会到国外去。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国家在逐渐地开放,但是人们却对国家的稳定缺乏信心。毕竟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心有余悸,所以大家都在往外跑。另一方面,我当时在作协的外联室做接待、翻译、陪同的工作,比如陪外宾看杂技,每次必看。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到了40岁,还是在做同样的事,可预见的未来使我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想要作出一些改变。所以当出国的机会来时,我就出国了。
朱:在您的作品集《归梦湖边》中有一辑“莼鲈之思”,“莼鲈”这个组合词,激起了至少是味觉、嗅觉、视觉上的想象,是不是对您来说,有关上海的记忆是渗透在生命深处,只能用细节去呈现和感受的?
穆:“莼鲈之思”出自《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后来被传为佳话,演变成“莼鲈之思”,这个词也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当一个人离开故乡之后,重新体验故乡会通过梦境、食物、穿着、看电影、唱歌、听音乐、阅读和写作等等手段去实现。因为实际的环境不存在了,所以你只能通过这些动作里所隐含和代表的意境去体验。这有点像关在狱中的人很热衷于说菜那样,他们在想肉想疯了的时候,喜欢聚在一起从找猪、绑猪、杀猪开始一路描绘下来,将一道菜的方方面面说得越详细越解瘾,这是人渴望至极和绝望之际的自救反应。我出国留学时是第一批自费留学生,每一分钱都需要自己去挣出来。所以我出国之后过了八年才得以回国,三十多年没有回国去过中秋或春节。父母在时是因为孩子这时候上学不能回去,现在孩子大了,却因为父母不在了怕回去过这样的节。这是一种深藏在心底里的无法修复的创伤,可以不去碰不去想,但是却无法使其消失。
朱:这一辑中有不少都是写您在上海的生活记忆,其中有一篇《摩登》在我读来印象非常深刻,阅读时会联想起张爱玲的《更衣记》,都是因晒衣裳引起的感慨和思考,蓦然有种历史的衔接感,张爱玲笔下的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摩登时装好像走过漫长的岁月,封存在您所写的樟木箱中,然后又复活在新中国的时空中,您在散文中说:“这每一年的暴晒日,不仅暴晒了藏在箱子里的衣服,也同时暴晒了我们驱壳里空洞的灵魂。这一日,变成了我们反复体验和考量到底什么才是更贴近我们的自我的挣扎日。”大家都觉得您的文风柔美温婉,但在这篇散文中,我读到了您的深刻和尖锐。虽然没有写大时代的大事件,但是这些日常的记忆却烛照了深刻的时代悲哀。
穆:是的,这个——家里的三个樟木箱的故事——确实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童年记忆。箱子里都是1930年代非常时髦的服装,平时都不能拿出来穿,每年晒的时候我们的试穿就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到底是更喜欢镜子里的那个穿着时髦服装的我呢?还是喜欢当下穿着统一服装的我?这样的疑问每次都呈现在自己的心里。
朱:读您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您移居德国之后对故国的依恋和思念,在《时差》中是白天生活在德国的土地上,而夜晚梦回故土,“梦中的一切都留在了故乡”,是初期离开时的割裂之痛;在《黑发鹦鹉》中,借由母亲缝制的衣服,感慨身处异域的自己犹如“一只离开家园的黑发鹦鹉,将拖曳着故土的情怀说着他乡的语言”;在《广场上的圣诞树》中,女孩简“舒展了中国的风情优雅地立在异国的土地上,却遮掩不了那孤单落寞之感”;而在《飞回家乡的蝴蝶》中,您说“发现自己虽然置身于家乡的夜中,然而自己离家乡却依然非常的遥远”,则是久居德国之后归来时情感的疏离。能不能谈谈在您的创作中,故乡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角色或者文化位置?
穆:故乡在我的创作中是罩在风灯里的一圈暖色的光环。虽然远居异国,但是故乡会一直亮在脑海里,尤其是在黑暗的时候,在你悲哀的时候,在你不快乐不幸福的时候,在你彷徨低落的时候,它会闪现,给你动力和温暖,会使你想起自己那张曾经躺过并在其中长大的摇篮。所以我写了很多关于故乡的记忆,我在回想的时候反复咀嚼那些味道,回忆那些情景,那是一种会让你泪上心头的记忆,有忧伤也有温暖,有所思有所感就想要写出来。
朱:江南故乡的人、事、物,包括非常具象的味道、色彩、形态等,因为远离,渐渐变成一种美好时光的象征、一种纪念,也成为身处异域的情感寄托。但是,作为对居住地生活融入性非常好的新移民,我们看到您的作品体现了双重视野,一方面是对故土家乡的眷恋和关注,另一方面也从各个方面展现德国生活的图景。在散文集《又回伊甸》“田园短笛”一辑中,写了较多德国的生活体验,比如写邻居、中西饮食差异、圣诞音乐会、万圣节、乡下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个生活空间对你来说是更现实、更贴近的。当然也充斥着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比如散文《选择》。您如何看待这个生活空间呢?
穆: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空间是宿命替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它是不符合美学的。故乡和异乡可以构成生命的整体,但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导致这个人有点像一棵被移植嫁接后的植物,拥有自我,却失去原我。简单点说,这个“田园”其实并非我的选择,因为当时有了孩子,我先生和我说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宽松、有花园的空间,也就是不想住在城里。而我是一个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人,如果要我自己找房子,我肯定会找在车站或商业街旁边的房子,而这恰恰是我先生认为对生活不好的地方,所以乡下对我来说,不是我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而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只能搬去乡下。但是后来发现,对一个女人来说,其实是孩子和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么对我来说,这个生活空间也一样是可爱光亮的。
朱:说到故乡和德国生活,就不能不说您作品中那些鲜活的人物群体,他们往往是非常普通的、处在两种不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比如老康、美岚、阿玲、阿潘、阿贤、阿瑞、阿珍……在中短篇小说中,单个的人物形象似乎是模糊的,他们沉入具体的日常琐事之中,但这些形象聚合起来却又非常清晰,从小小的窗口打开了生活的门,让我们看到了海外世界的丰富。能不能说说您如何看待笔下的小人物?通过他们,您想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怀?
穆: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选择哪一类人物。从基督教的信仰出发,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值得赞美的,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小人物,这是一种不从世俗出发的、不以物质为衡量的尺度。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你所看见的每一个人便都是有心跳有温度的人。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体会到他们的独特。通过他们我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在很多人眼里,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一个人和我好就是我眼中的好人,否则便是个坏人。这种简单幼稚的目光,是目前世界里所普遍运用的判断标准。人们很难会对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也保持客观理智的欣赏,而我所要展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值得你去欣赏的。
朱:所以,无论是写华人,还是写德国人,您都选取了这样的普通人,比如理发师Theo,宿舍女执掌阿塔姆女士和小村的老盲人。
穆:我在写他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去强调他们是一个小人物。可以说他们就是我的世界里所遇到的各类天使,陪伴我经过生命里的某一个或者某一段时光。在我的眼里他们很“大”,“大”到可以影响或者触摸到我的内心。
朱:此外,在您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一个筋疲力尽的女性的挣扎,家庭、孩子、自我,但是最终您所展现的都是光明和力量。请问您在这么多年的海外生活中,如何平衡自己的身份定位?这其中,写作对您来说又有怎样的一种意义?
穆:去海外就像跳入海水里,为生活打拼就好像你在拼命地游泳,不让自己淹死。但是这样的游泳毕竟会有筋疲力尽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想去抓住一些东西。我有幸遇到了基督教并接受了它,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将我从世俗中解放出来。我没有了普通人所有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没有了金钱、物质、名利、权力等诱惑,同时它让我重新发现自己。比如,当我生了两个孩子后,按照基督教的价值观,心甘情愿、认真负责地在家里教育孩子。这时候我的大学同学几乎都在职场上奋斗,如果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人们会认为这个人可惜了。可是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家庭管理员和人才培养员,我也肩负着十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用一代又一代(孩子好,孩子的孩子也好)的幸福来衡量的。可以说基督教是光明和力量的来源。
朱:读您的小说,从语言到感觉都是用诗歌的思维和方式在表述,像《何日君再来》《归梦湖边》表达情爱的纯真与美好,不注重情节,没有矛盾,只有抒情的语言和情感在流动。而读您的诗歌,我又被一种浓郁而又深沉的情感打动、感染,抒情主人公以优雅、知性、对生活和世界充满自信和爱的姿态诉说她的情绪和感受,比如《飞越欧洲》《我们的五月》等。
穆:我在写作的时候是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在写的,我会有意识地不用华丽的辞藻、时髦的语言。其实我想写的东西,是希望和地区没关系,和时间没关系,和政治也没关系,而是可以使文字能够跟不同时空的读者产生共鸣,能够打动人性。我觉得流行的小说或语言表达方式,会在时代语境变迁中被清洗。我想寻找一种永恒的东西,那就是对人性的思考。您说从语言到感觉都是用诗歌的思维和方式在表述,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喜欢巴赫的音乐有关,特别是巴赫的赋格旋律会常常在我写作的同时游走在脑海的深处。
朱:我一直十分关注您的创作,最近您写了很多古体诗词形式的诗作,为什么突然从现代诗转向了传统诗词呢?
穆:从现代诗进入传统诗词的契机是有一天捷克华文作家老木对我说,中华诗词学会可以吸纳海外会员了。这时候,他已经进入并写了一些古典诗词。我一听之下,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听他们吟诵古诗词的情景就浮现上来。我说你加入的话我也要争取加入,于是我也开始写起来。第一首写的是十六字令,因为字数少,容易琢磨。后来就选字数越来越多的词牌,并逐渐被古典诗词所具有的格律、韵律之美深深吸引,一发而不可收,这是其一。其二是2016年老木和我一起成立了欧洲华文诗歌会的群。在群里有一些也是写古典诗词的,就这样,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
朱:在您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中,我们读到您温情、阳光、爱的浓郁,可以说是用对生活热诚的爱来表现人情、人性,尤其是在《房间里的声音》中,颖在做临终关怀的义工时,为95岁老人读圣经的场景描写,那个意境非常的安详、宁静,是对生命的敬畏,又是对生命的超越。我觉得用艺术和宗教的方式把我们经验领域中很多无法言说的东西,非常好地表达出来,这种沉默的张力,使人感到非常震撼。能不能说说你觉得基督教信仰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穆:基督教信仰将我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彻底改变。我是在信仰基督教之后开始大量写作的。因为我从基督教的眼光出发,发现了很多不为世人所注目的地方反而有着人性的光芒。好像有了一支显微镜,我看见了更多更深更细致的东西。那么,看见了,就想将它写出来。我想如果我要写,就写那些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东西,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够被我的文字所打动,也就是写那些和政治物质无关的可以永恒的东西。那么只有爱是永恒的,连生死都是可以穿越的,所以我的笔触常常涉及这一主题。
朱: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您作品中柔和的、对生活细节的深刻把握,但其实您的作品不仅是写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或者琐碎,您也有大的历史情怀,如《落叶之痛》中对纳粹老兵、德国二战、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就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怀。最新的长篇小说《活在纳粹之后》(又名《战后》)可以说凝聚了您对这类话题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能不能谈谈《活在纳粹之后》的创作灵感?
穆:生活在德国的人,是离不开纳粹主题的。其实在我还没到德国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纳粹问题”的影响。很多人在一听我将要去的国家是德国时,他们第一句话会说:“德国好啊!”第二句话就会说:“就是德国有过希特勒不好啊!”到了德国以后,我了解到很多老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你会发现有的人不愿意讲那些创伤经验,其实大部分的德国家庭都有家人在二战中死去,这些是经常接触到的,很多素材已经日积月累,只是没有契机触发写出来的冲动。2015年,捷克华文作家老木请我帮他一起策划“单骑送铁证环球行”项目,我负责欧洲、美洲的主要管理工作。在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接触了更多的相关人群还有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激发了我要写一部这个主题的长篇小说的想法。
朱:《活在纳粹之后》是您第一次尝试长篇小说创作,小说以德国、中国两个国家为背景,讲述了德国犹太人瓦伦斯坦一家在二战中的遭遇。在中国经商的本瓦伦为了生存去了美国,而留在中国的两位情人衔接了故事的进展,她们经历了国共内战,并开启了1949年以后的叙事,视野宏阔。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叙事结构的设计非常精巧,以本瓦伦为核心展开顺时讲述,以王芍琴为核心进行逆向追述,这两条线索的设计非常精妙,写作的时候您是如何考虑的?此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自己预设的读者?
穆:我在写《活在纳粹之后》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用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相互交叉的叙事方式。因为我在感受到历史史料和故事冲击的时候,就是同时颠簸在当下和历史的双重时空里。我所在的时空和我被带入的那个时空交织在一起,这种感觉我将它真实地呈现在书里。这里面的故事,有虚有实,但基本都是根据我在德国的生活经验和获得的史料虚构的。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没有预设特别的读者,更多的是想要写,想要表达。如果要说有,那就是青少年以上的成年人。一切对历史对故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读这本书。
朱:我们再从文学作品回到现实语境,这两年,您跟国内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一方面是经常回国参加学院派的文学活动,参加研讨会,到大学演讲,还担任了盐城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另一方面是您的作品在国内各种征文比赛中屡屡获奖。我想知道这种“回归”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您又是怎么看待海外华文作家参加大陆文学奖评选的?
穆:这些对创作肯定是有激励的。虽然说文学奖有评选标准和征文主题的约束,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参加的一些文学奖对写作是没有约束的,比如有的奖会设立“海外”奖项。此外,通过参与文学奖,我们跟祖国的联系更紧密了,这种联系对于我们在海外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很重要,是一种支撑的力量,写作不再是孤独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写作主要是想“喂养”海外的华人读者,所以我还是把很多作品发表在海外,比如《欧华导报》。我不会刻意把作品发表在国内,因为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的责任,首先应该是滋养在海外生活的读者,我想要用自己的文字使跟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人产生共鸣,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类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我能体会并理解他们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觉得让我定义“海外华文文学”的话,我会更严格一点,应该是在海外出版、生活在海外的人的写作,写作的内容也应该以海外经验为主。如果经常生活在国内,在国内出版作品,其实可以看作是外籍作家。
同时,创作需要生活的积累。如果不参加文学活动,可能就一直呆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参加文学活动后,会有一些改变。比如,我就曾听一位老师说长篇小说字数最好不要超过20万字,否则就很少会有人愿意看了。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动笔写《活在纳粹之后》,后来写的时候,我就尽量将字数控制在20万字之内。所以也有学者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对我说:“您应该还可以写个续集,或者叫下半部。”因为他觉得没有看够,还想知道人物后来的命运。
朱: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互联网+”的模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阅读方式,在网络对文学影响日益增强的语境中,我们看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传播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您不仅以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创办个人文学平台“沁茶小叙”,2016年还在微信平台创办了“欧洲华文诗歌会”,同时您还担任了“国际新媒体组织副秘书长”。能不能谈谈,从以前的纸媒发表,到现在的网络平台,作为文学创作主体,您有怎样的感受?“微阅读”的形式对你们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穆:微阅读的方式完全是被迫的。因为手机里的微信圈让朋友之间的交流都留在了手机里,所以我也被迫开始用公众号等这些方便在手机里交流的形式。在德国,《欧华导报》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在欧洲的5个国家发行,主要是报社自己出资出版给华人看的,文学板块非常丰富,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都接纳。《华商报》是以各类信息为主,纯文学几乎没有。《欧洲新报》版面很大,新闻和文学兼具,还常年设有文学类的征文。2012年,我的短篇小说《人隔千里一梦回》在《欧洲新报》的“金凤凰杯”征文活动上获得优秀奖。在《欧洲新报》上我有个影评专栏,题目是“紫荆追剧”。至于纸媒和微信公众号,我一般会先照顾纸媒发表,然后再在公众号上发表。作为文学创作宣传的载体,我的感受是放弃了电脑博客的交流形式有点可惜,但是同时却也因为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交流而节省了时间。对我的创作来说,诗词创作可以在手机里完成,现在很多刊物也都是微刊了。对于诗歌来说,其实发表的纸质媒体并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海外园地更少,有些报纸是不愿意发表诗歌的,但是网络发表和传播带来了很多便利。不过长篇小说还是需要在电脑上完成的,甚至这个时候微信和朋友圈的微阅读对创作来说是一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