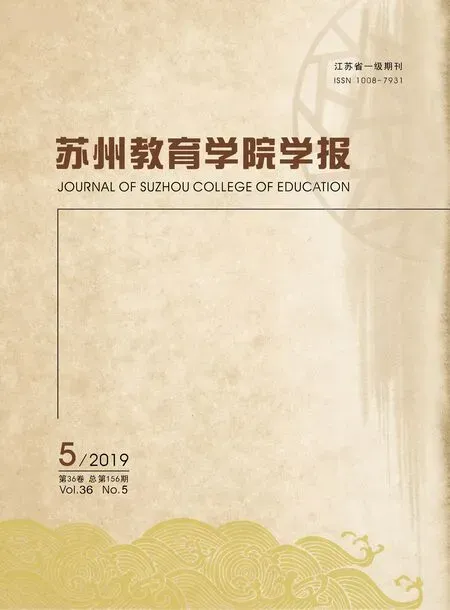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佛理隐喻
——以《天龙八部》为例
2019-02-21王诗越
王诗越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文学中看到了哲学:“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1]中国古代文学则崇尚“文以载道”,认为蕴含言外之意、文外重旨的文学作品才为上乘之作。分析来看,文学作品只有融合哲学、隐喻哲理才能越显深刻;哲学思想若能借助文学、渗透文学便能愈发圆融。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在文学创作中重视以隐喻的手法展示儒、释、道三家哲理,使其作品蕴含了更深刻的人生思考与哲学内涵。在其众多作品中,隐喻儒家哲理者当为《射雕英雄传》,隐喻道家哲理者首推《笑傲江湖》,隐喻佛家哲理者则以《天龙八部》为最。《天龙八部》可谓金庸小说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金庸想借“天龙八部”这八个有尘世欢喜和悲苦的神道精怪①金庸在正文前的“释名”中解释道:“‘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八部者,分别为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因其以天、龙为首,故称“天龙八部”。来象征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其背后则隐喻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在书中,金庸并没有直接生搬硬套佛教戒律或经典,而是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写、形象的塑造以及命运的安排,将深湛的佛理融于其中。纵观全书,其佛理隐喻可以概括为三点——华夷之辨中的众生平等之喻、善恶之辨中的因果报应之喻和我他之辨中的大乘妙道之喻。
一、华夷之辨中的众生平等之喻
《天龙八部》设定的时代为北宋哲宗时期。其时,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并立,汉、契丹、白、党项、藏等民族并存,相互之间难免会出现各国纷争以及民族矛盾。在此背景下,金庸通过塑造萧峰这样一位契丹族悲情英雄的形象来隐喻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观,更确切地说,是佛教中人人平等无差的观念。
萧峰是本书的主人公,曾用名“乔峰”。他在恩师丐帮汪剑通帮主、少林玄苦大师的悉心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个义薄云天、以民族大节为重的英雄。他出任丐帮帮主,为抵御北方辽国契丹族入侵立下了赫赫功劳。然而世事无常,在“杏子林事变”中他得知自己竟是契丹人,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他始终不敢相信。此后不久,其养父母乔三槐夫妇、恩师玄苦大师以及多位知道萧峰身世的人都惨遭杀害。在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观念下,中原群雄都极为仇视契丹人,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自认汉族高人一等,认为契丹人茹毛饮血,天性凶残,不可相信,应赶尽杀绝,这些人不加调查就将杀父、杀母、杀师之罪都归咎于萧峰,容不得他。于是萧峰与中原群雄大战一场后便离开中原,去寻找杀害自己养父母、恩师的真凶以及自己身世的真相,后来他逐渐认同了自己的契丹族身份,并不因此自贬,而是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并无高下,应和平共处。萧峰来到辽国后,官拜南院大王,希望与宋修好,相安无事,却遇到辽帝南征,为避免宋辽两国交兵而生灵涂炭,他多次劝阻辽帝南征,不惜锒铛入狱。中原群雄闻此消息,为其仁义所感动,奋不顾身前往辽都营救。最后,萧峰以死谏阻辽帝,终使辽帝改变主意放弃南征,换来两国数十年的和平,得到了所有中原豪杰的敬佩。萧峰实是一位感天动地的悲情英雄!
在金庸早期的武侠小说中,曾有很强的汉王朝为正统和汉族中心的观念,他多部作品的主角及所讴歌的人物均为汉人。如《书剑恩仇录》中,金庸正面描写了反清复明的红花会,赞赏他们试图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决心;又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在蒙古部落长大,与蒙古族兄弟亲密无间,但他却舍弃金刀驸马之位,回到中原,协助守将镇守襄阳城,以抵抗外敌,直至最后城破殉国。《射雕英雄传》中虽然也涉及到了多民族的冲突,但金庸所凸显的更多的是郭靖的忠肝义胆和为国为民。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他逐渐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并汲取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人物同样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他自己也承认:“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2]7同时,金庸开始尝试在文学创作中隐喻佛家哲理,他通过塑造萧峰这样一位异族英雄的形象,表明他对各民族平等无差、一视同仁的众生平等观念。
“众生平等”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众生”是佛教名词,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认为,“众生”应包括“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3]这九种,因这些东西都有情识,故亦称“有情”。“平等”也是佛教的常用名词,在佛经中频繁出现。《新编佛教辞典》中释“平等”义为:“无差别、等同。或谓实相平等,离任何差别相……或谓对众生应等视无别……或谓在禅定中舍分别心……”[4]可见“平等”始终是跟“差别”相对而存在的,佛教自创立就始终秉持着这一教义。在古印度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将古印度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并且严格规定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权利、义务等,极力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的观念,维护等级制度。原始佛教则提倡众生平等,主要侧重于种姓平等或者四姓平等,即认为无论什么种姓,只要进入佛门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以此反抗婆罗门的种姓特权。这也是释迦牟尼最初创立佛教的原因之一。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在佛教经典中有大量的阐释和体现,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以及传入中国后开启的本土化历程,众生平等观念的内涵和层次也在不断丰富完善,从原来的种姓平等,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众生与佛之间的平等、佛性之间的平等等多个方面。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汉族也好,契丹族也罢,他们都是人,其本质都是由地、水、风、火四大元素所构成,根本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是平等、无有差别的。然而众生迷失本性,起颠倒邪见,执着于表面之相,遂见种种差别。犹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喜欢给他人贴标签,以身份、职业、民族等差异衡量他人德行高低、区分本性高下。须知,要想真正评价人的善恶优劣,应以他们后天的实际行为举止来判断,而不是以先天的身份背景妄作定论。
在《天龙八部》中,金庸还多次通过其他角色之口来表达对萧峰的同情,并试图以此更加深刻地阐释佛教的平等观念。譬如在“聚贤庄大战”中,中原群雄围攻萧峰,其中不乏少林高僧,萧峰以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的“太祖长拳”迎击玄难、玄寂的少林绝技,少林武功源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何尝不是外族胡人?在场群雄不禁思忖:“咱们对达摩老祖敬若神明,何以对契丹人却恨之入骨,大家都是非我族类的胡人啊?嗯!这两种人当然大不相同。天竺人从不残杀我中华同胞,契丹人却暴虐狠毒。如此说来,也并非只要是胡人,就须一概该杀,其中也有善恶之别。那么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2]779又如萧峰拜访智光大师时,智光大师写一偈子道:“万物一般,众生平等。汉人契丹,一视同仁。恩怨荣辱,玄妙难明。当怀慈心,常念苍生。”[2]844同时,金庸对萧峰最终结局的安排,也贯彻了众生平等的佛教教义。萧峰虽非佛教徒,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一直践行着佛法:坚守着汉族与契丹族平等共处的观念,始终以慈悲为怀,心系两国百姓的生命。为避免生灵涂炭,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牺牲自我以换来两国和平,可谓虽死犹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在书中隐喻的第一个佛理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这是对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观的充分揭示。
二、善恶之辨中的因果报应之喻
佛教在论及人的善恶时,注重后天的道德行为与道德实践,更多谈论后天的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以“业”为基础,“业”是一个佛教词汇,梵文为Karma,意思是造作,泛指有情众生的一切活动和行为,它通常分为身、口、意三个方面,即行为、语言、思想。根据善、恶、无记三种伦理动机而引发的行为就分别被称作善业、恶业和无记业。而善业和恶业在因果作用下就形成了善业善果和恶业恶果的善恶报应观。《大般涅槃经》言:“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5]901上《佛说无量寿经》亦言:“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数之自然,应期所行。殃咎追命,无得从舍。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冥入冥。”[5]277上这些无不体现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善恶观。简而言之,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有因必有果,因可以是果,果亦可是因。在书中,金庸并没有直接论及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但他对书中几位人物命运看似无意的安排,背后却隐含着善恶有报的观念。
本书的反派人物之一慕容复就是一个例子。慕容复是大燕鲜卑族后裔,一生以复国称帝、光复大燕为志。其父慕容博更是当年造成萧峰悲惨身世之人,其意在挑起宋辽纷争,自己好趁虚而入。慕容博给儿子取名一个“复”字,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他复国。为了达成这一祖训,慕容复四处奔波,收揽人心。后来,慕容博在少林寺受到扫地僧点化,大彻大悟,皈依三宝,并感慨:“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空。”[2]1722可是慕容复却始终无法放下他的皇帝梦,深陷于复国的执念而无法自拔。为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他机关算尽、不择手段,甚至到了亲人可弃、兄弟可杀的地步,他为顺利当上西夏国驸马,抛弃了仰慕他已久的表妹王语嫣;他为了积聚复国的力量,勾结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拜段为义父,并杀死忠心耿耿的家臣以表其心。如此只为一己之私,手段卑鄙,多行不义,岂能成功复国?又岂能得到善果?慕容复最终得到了报应:一败涂地、精神失常。即使这样,他还做着他的皇帝梦,在疯疯癫癫中胡言道:“众爱卿平身,朕既兴复大燕,身登大宝,人人皆有封赏。”[2]2008金庸安排慕容复这般悲惨命运,意在告诫世人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要执著于自己的私利与妄念,放下则自在,否则只会徒生无数烦恼,自毁锦绣前途,深陷于无边苦海之中。在书中,当别人问起慕容复在什么地方最为快乐逍遥时,慕容复的表现竟是“突然间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一生营营役役,不断为兴复燕国而奔走,可说从未有过什么快乐之时。别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强,名满天下,江湖上众所敬畏,自必志得意满,但他内心,实在从来没真正快乐过”[2]1838。慕容复这样的人物,真是既可悲又可叹,最后虽生犹死。
此外,书中还有一位与慕容复极为相似、却又结局不同之人——吐蕃国师鸠摩智。从他的名字我们似乎可以略窥其生平:“鸠”是一种鸟类,令人不禁联想到“天龙八部”中的迦楼罗。迦楼罗有种种庄严宝象,可见他的地位较为尊贵;“摩”是梵文Mara的音译,全称为“摩罗”,是魔鬼的意思。这说明他曾堕入魔道或陷入心魔;最后一个“智”字,又含有他最终达到智慧的境界之意。而书中的鸠摩智确也人如其名,他原是吐蕃的一位高僧,书中这样描述:“大轮明王鸠摩智是吐蕃国的护国法王,但只听说他具大智慧,精通佛法,每隔五年,开坛讲经说法,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云集大雪山大轮寺,执经问难,研讨内典,闻法既毕,无不欢喜赞叹而去。”[2]369其地位之高、学识之精可想而知。但就是这样一位高僧,竟然醉心于武学无法自拔,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在吐蕃密宗宁玛派习得“火焰刀”一技,本来武功已十分厉害,可之后好胜之心日盛,贪恋更为精妙的武学,试图一人身兼多项绝技。对于出家人而言,习武旨在强身健体,更在弘法护法、救人济世,可是鸠摩智却妄图无敌于武林,称霸江湖,不存丝毫慈悲之念,在追求和修炼绝技的过程中,更是造了种种恶业:他在天龙寺、少林寺炫武扬威,不顾国师身份,羞辱佛门同道,甚至出手狠毒,重伤他寺僧众;他强行掳走大理世子段誉,软硬兼施,逼迫他默出六脉神剑剑谱,以便自己学习,使段誉差点死于非命。如此满身暴戾之气,完全违背了出家人习武的本义,扫地僧曾这样说他:“大轮明王原为我佛门弟子,精研佛法,记诵析理,当世无双,但如不存慈悲布施、普度众生之念,虽然典籍淹通,妙辩无碍,终不能消解修习这些上乘武功时所中的戾气。”[2]1710正如扫地僧所预言,鸠摩智后来遭到了恶果,练武走火入魔,数十年内力恰被段誉吸去才得以保住性命,而这样的恶果却又成了鸠摩智的善因,让他突然顿悟,领悟了佛教诸行无常、善恶有报的真谛,破除了对武学的执著。从此他改邪归正,广弘佛法,终成为一代高僧,可谓得了善果。
在佛教看来,人可以掌握自己的果报,倘若一心向善,多做善事,多行善业,就能不断累积善因,最终得有善报。鸠摩智正因最后放下屠刀,及时回头,并且不断行善,所以最终才得以好报;慕容复因执迷不悟,越陷越深,最终只会得到恶果。金庸通过这两个不同人物之间不同命运和结局的对比,使读者可以体会出“去恶行善、止恶扬善”的隐喻。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佛理隐喻,体现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善恶观。
三、我他之辨中的大乘妙道之喻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会存在着与他人、群体、民族、国家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这一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天龙八部》的背景处于多民族与多国家并存并立的时代,金庸对人物言行的描写和形象的塑造,背后隐喻着佛教自觉觉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
“乘”是梵文yana的意译,音译为“衍那”,是“车乘、运载”的意思,佛教以此来喻指载运众生脱离苦海到达彼岸的工具。“大乘”即大的车乘之意,可度脱大多数人到达彼岸。公元1世纪左右,大乘佛教正式形成,其力求普渡众生,以自利利人、自觉觉他为目标。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接受和发扬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虽然也宣扬一切皆苦,以涅槃寂静为最高境界,呈现出一种出世主义的形象,但是它倡导的以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菩萨道为核心的大乘精神和普渡众生的宏愿,也蕴含着积极入世的思想。而这正与中国儒家“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颇有相通之处。《添品妙法莲华经》将大乘精神概括为:“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菩萨。”[7]可见其实质为不仅自己得道、觉悟,同时还要给他人带来好处、利乐,帮助他人脱离苦海、觉悟成佛。民间广为流传的地藏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和使命,正是这种大乘菩萨道的生动体现。更有甚者,可以做到无私奉献,舍己为人,为了造福他者、拯救他人而牺牲自己,“尸毗王割肉喂鹰救鸽”的故事就是一例。因此,佛教不仅只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也有积极入世作为的一面。
在书中,作者安排扫地僧出现并化解种种仇怨与执著,其中就隐含着大乘妙道。扫地僧在书中第四十三章出现,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少林寺操执杂役的服事僧,平时的任务就是在藏经阁扫地、整理书籍,他在少林寺数十年,可无人知其来历、知其姓名。但正是这位扫地僧,将整本书的佛理隐喻推到了顶峰。当萧远山、萧峰父子与慕容博、慕容复、鸠摩智三人在藏经阁准备大战一场时,扫地僧突然出现,一语道破萧远山、慕容博和鸠摩智三人因强行修炼武学而导致的内伤和病痛,苦心劝诫:“修习任何武功之时,务须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受伤越重。”[2]1710并认为:“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方能练得越多。”[2]1711为化解萧远山与慕容博的仇怨,他一掌使二人假死,令他们由生到死、由死到生走了一遭,既消除了二人盲目修炼所造成的内伤,又将二人的王图霸业和血海深仇都消于无形,并点化他们明白了万法皆空,唯有放下妄想,放下执念,及时回头才能获得解脱的大智。萧远山与慕容博也因此幡然悔悟,遁入空门,拜扫地僧为师。在扫地僧的身上,体现了高超的佛家智慧:洞悉一切却不高高在上,超然物外而又不舍世间,自我觉悟同时普渡众生。他在藏经阁打扫数十年,翻阅无数佛经典籍,佛法高深,想必早已得道,达到“自觉”的境界。藏经阁之战他原本可以置身事外,悄然而退,但他以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萧远山、慕容博二人在魔道中越陷越深,更不忍双方决一死战、两败俱伤。因此出手点化二人,力图“觉他”。他以佛门的大悲悯、大智慧化解了武林的恩恩怨怨,化解了众人对复仇和权力的执著。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高人,竟然连名字也没有,真是达到了佛家无名、无相的境界。也许这正是金庸的精心安排,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有或者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人公萧峰身上也蕴含了这种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大乘菩萨道。譬如在藏经阁一战中,他义正辞严地斥责慕容博:“尽忠报国,旨在保土安民,而非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报仇雪恨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2]1707可以看到,他心怀他人,时刻为百姓的安危幸福着想。后来,萧峰拒任“平南大元帅”一职,为避免两国交战致使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屡次劝谏辽帝放弃南征,最终甘愿牺牲性命,给宋辽两国无数百姓带来了多年和平的大“利”。这种为拯救世人而自我牺牲的行为,正是大乘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般的大无畏和大勇猛,可见其之悲天悯人,力图为他人带来利乐。在这里可以看出,在金庸看来,信奉佛教和践行佛法不仅仅在于自我修炼、吃斋念佛或是参禅打坐,也在于积极进取,奉献自我,正如扫地僧和萧峰这般人物。而金庸所推崇和赞扬的更多的是大乘佛教,以及它的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大乘妙道。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类型,它主要叙述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描写侠客、浪子的人生经历与武术功夫。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哲学、古典诗词、戏曲、中医、音乐、围棋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使其作品具有了更高的立意与更深的内涵,展现出了卓越的艺术水准。在其多部作品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儒、释、道三家哲理的理解与推崇。而《天龙八部》一书,正集中体现了金庸对佛家哲理的领会和诠释。在书中,金庸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具有特色的人物,通过描写他们的言行举止,安排他们的命运或结局,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与对比,在荡气回肠的行文叙述中,将众生平等、因果报应、自觉觉他的佛家哲理融于其中,并从佛教的角度深刻关怀人生、关怀生命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