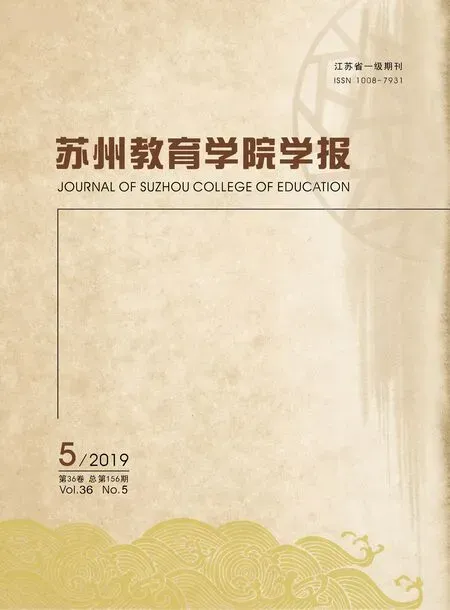“金庸小说”与“金学”
2019-02-21林保淳
林保淳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00116)
一代武侠宗师的殒落,免不了掀起一波波缅怀的浪潮,但也将是“盖棺论定”的开始。
自1980年金庸历经十年修订的《金庸作品全集》经远景出版社面世,金庸武侠小说挟着高明的商业运作手法,迅速在全世界华人地区形成一股“金庸旋风”,使原来微不足道的“武侠小说”冲决破旧有的文学藩篱,堂而皇之地高步迈入文学的殿堂,这是千古以来未有的盛事,不但是金庸的传奇,更是中国文学的传奇。
一、读者苦闷的象征
武侠小说本就是具有“传奇”性质的文体,写奇人、述奇事,而又往往以奇特的故事架构引人瞩目。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是“虚构”的,“虚构”就意味着一切的“可能”,而与现实世界的往往“不可能”形成了对峙。举凡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可能”,如“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历尽艰辛后,必然有所回报”“法律退位,杀人者不必获得惩罚”“经济淡化,侠客多数挥金如土”“武功超卓,突破人体极限”等,在武侠小说中一切都不言而喻地顺理成章起来。作者与读者共有一个默契,竭力要将“不可能”化为“可能”,而就在此一“可能”之中,纾解了人在现实中的忧虑、愤懑、沮丧、痛苦,而达到心灵上的“涤清作用”。因此,武侠小说不免有消极逃避的副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一消极,未必即是逃避,反而是带有浓厚期盼的沉潜充电功能,待心灵获得平复之后,得以重新出发,迎接现实严峻而残酷的挑战。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1]主要是从作者抒发个人情志的角度说的,而武侠小说,虽亦有作者思想、感情的投入,却主要是纾解读者苦闷的。不明白这一点,永远无法解说何以会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如此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始终为“载道”“教化”等带有浓重“功利”倾向的论点所盘踞,强调的是“文学”必须承担起严肃及沉重的社会责任,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正是自此角度而言——即便偶有抒发个人情志的“抒情”诗骚传统,也往往不敌此论。此所以古代文人在编纂、辑录作品时,总以文章在前、诗歌为后,而对戏曲、小说等不甚措意,甚至等而下之的缘故。但无论是“载道”或“抒情”,都是以“作者”为核心的文学观点,主要在提醒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创作的严肃性、真诚性以及社会的影响力,但对于“读者”层面,鲜少应有的关注。
二、“通俗”与“典雅”的异趣
以“作者”或“读者”为核心,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思路,前者强调的是文学“应该”带给“读者”什么;后者则关注“读者”“需要”或“喜欢”怎样内容的文学。思路不同,所开展的理论系统就大异其趣。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中,无疑对以“作者”为核心处着墨甚多,历代诗文理论皆阐发得相当深刻透辟;而对“读者”层面的关注,则仅在白话小说、戏曲等完全取决于读者(观众)的体裁中偶尔透露出来,并且在强大的传统观念笼罩下,未能表里俱到,至今仍未能真正开展出来。
小说、戏曲向来都被目为“通俗”,但学界却始终以“典雅”(或云“纯文学”)的角度加以论评,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大宗之一,多数研究者的取径却都援取与“通俗”大相径庭的模式加以论析,无疑枘凿难入,因此,通俗文学的本质也就缺乏更精准的认知,遑论理论的开展。
从表面上看,“通俗”与“典雅”似是各异其路,各有所偏,但其目标却是一致的,直指“文学可以如何”的重要命题。“可以”二字,显示着灵活运用的挥洒空间的,此正如行旅,欲达到某个目的地,可以走“山程”的陆路,也可走“水程”的水路,当然更可以选择“航程”的空路,完全取决于行旅者之所好。《文心雕龙·知音》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2],读者秉性各异,所好不同,作者则一如旅行业者,可以依据其所默认的不同读者对象,设计出各种不同的行程,以供读者抉择,这就是文学的“多元化思维”——文学可以“经世”,可以“反映”,可以“批判”,当然亦可提供完全与功利无关的纯智性思考(如本格型的侦探小说),乃至于纯为休闲消遣的“娱乐”效果。在此,不但读者有选择的自主权,即便是作者,也无须受到某些外在框架的制约,而可以两相得益,扩大文学的领域,活化文学的表现方法。
三、“金庸小说研究”的起步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广受读者的欢迎,主要是得力于他能同时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求,上从学有专精的学者,下至纯粹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贩夫走卒,都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各有深浅不一的收获。我始终认为,金庸的小说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不仅是过去的,也将是未来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不仅是个“异数”,更是足以打破文学藩篱的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正不妨藉其小说,分从“作者”与“读者”的角度,重新思考新一代文学理论架构建立的可能。但以目前已可算是汗牛充栋的“金学研究”成果来说,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个地步,这是亟待加强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受人瞩目,毋庸置疑的是他的小说,尤其是几部被讨论得最多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禁得起较严格的“纯文学标准”检验,多数的研究论著也朝向其“文学性”的多寡展开分析及赞誉。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传奇性成就,相信绝对不会逊色于《红楼梦》。研究者热衷于分析其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卓越、情节如何紧凑、主题如何深刻、场景如何变幻,不但“知人论世”地结合了金庸的创作历程与当代思想、局势的关系加以探讨,更不吝撷取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加以印证、阐发,诚可谓洋洋大观。但总体来说,除开若干“歌德派”或“金迷俱乐部”的“插花”之作可以不论外,其目的却完全相同——要证明金庸的武侠小说乃至于其他的武侠小说,是确有资格堂堂皇皇地立足于文学殿堂之上的。此类的研究,无疑也是极有意义与价值的,足以将向来为人目为“小道”的武侠小说提升到“大雅”的地位,这在草莱初辟的武侠研究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跃进。但是,未来的金庸小说或武侠小说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已普遍为人所认可的现在,当然不能够仅仅于此原地踏步,亟须迈开步伐,走向新的路径。
四、金庸小说研究简要回顾
在1980年之前,由于武侠小说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再加上金庸自身政治认同上的尴尬,故金庸小说的盗版虽盛,读者亦多,却很少有人敢于冒当时之大不韪加以精研细究。但自金庸小说开始解禁,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厚达36册的《金庸作品全集》,再加上沈登恩颇具商业头脑的宣传推广,金庸小说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其后的一二十年间,寖至成为通俗或武侠小说最引人瞩目的研究对象。
大体上,金庸小说的相关研究是以肯定金庸的小说具有相当充分的“文学成就”开始的,无论是单篇短论、专书论著还是学位论文,首先都必然以其文学上的优越性为讨论的基础,然后针对其所有的作品,分别展开各层面的探讨,有总论其综合成就者,亦有就单部作品、单一人物、相关场景、小说结构、小说主题,以及其特殊的技巧,包括历史的援用、掌故的运用、修辞的发挥等,展开多层面的探讨;同时,更援取了传统“知人论世”的观点,对其生平、传记与小说的关系,也有相当全面的开展。从早期不免有点“歌德式”“书迷俱乐部”式的夸赞,到后来逐渐剖肌析理、论之有据的深究,可谓步步推展,卓有成果。
以台湾的博硕士论文为例,自1994年到2016年为止,即有89部论文以金庸为题展开研究,其中5部是博士论文,总字数高达千万以上。
综括而言,截至目前为止,金庸小说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两大现象:
1.研究的层面极广。除了小说文本的各角度解读外,包含了影视、漫画、电玩、戏曲、版本(中外)等层面,可谓巨细靡遗。
2.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有自传统中国小说史发展解析者,亦有援用西方各家学派理论,尤其是叙事学、主题学、心理学、读者理论等加以分析者。
当然,这些相关的研究,良窳不齐,虽已初见体系,而未能紧密系联;虽偶具华彩,多数仍属泛论。尽管如此,总算是为“金学”铺垫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我个人认为,在金庸小说的总体研究中,陈墨以其十数种金学系列研究知名,可谓最值得肯定;就金庸小说而言,金庸小说版本的相关研究,最具意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推崇金庸的风潮中,类似霍惊觉的《金学大沉淀》、袁良骏的《金庸小说指掌图》却别持异议,也是甚可关注的。
五、金庸小说研究的“盲点”
迄今为止的多数金庸小说研究论著大抵皆以阐发金庸小说“为何”(why)可以屹立于文学殿堂为目的,着力于金庸小说中表现出“何种”(what)值得称道的成就,而明显忽略了金庸小说是“如何”(how)取得如此成就更深层内在的原因。
“如何”一语,不仅是单指其叙述策略的运用,也带引出另一层次的“为何”此一策略可以成功的问题。以金庸“历史素材”的运用来说,论者都不约而同指出金庸擅于藉历史上的动乱时期凸显其笔下侠客的丰采及伟烈,也凿凿其言地论断金庸借着历史的厚度塑造了其小说雄伟壮阔的格局,这的确是与台湾作家“去历史化”下所呈显的风格大异其趣。但是,金庸究竟是通过何种叙述策略“化实为虚”,“亦虚亦实”,“虚实融合”,让历史得以在他的小说中展现出动人心魄的魅力?金庸对史事的运用,是如何能因应其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关的变动、转换,甚至未免有些扭曲?而更重要的是,何以这样的策略运用会使其小说反而能远超于其他作家而获得肯定?究竟其与同样擅于取径于历史的梁羽生有何不同?当然,这就不仅仅是藉由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寻得答案的。
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所谓的“通俗”,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展现出其相当程度的同一性,而这一同一性,是所有的武侠作家共同缔建的。金庸小说的成就,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充分显露了其“与众不同”的高度,也极易让人聚焦于其“殊异性”的表现。但多数人却往往忘了,同样一只引颈长喙的鹤,如果置身于一群长颈鹿或骆驼之间,就未必能有如此夺目的光彩。换句话说,没有那一群小鸡的衬托,此鹤是完全无法凸显其睥睨群鸡的丰采的。然而,这群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鸡究竟呈显了怎样的“共性”?金庸这只孤高的鹤,标识出如何可以区别于群鸡的特色?见鹤不见鸡,单独标异金庸,而忽略了其他武侠小说,无疑是当前金庸小说研究最大的盲点。
六、“金学”建构的可能
金庸小说的研究风气已成,但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一门“金学”?这当然牵涉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建构需要具备何种条件。
1.研究对象的开展性如何?如果以目前蜚声国际的《红楼梦》(红学)、《金瓶梅》(金学)相较,金庸小说的文本,显然远较前两书来得更丰富,且展延性也更大,《红楼梦》与《金瓶梅》虽因其历史的悠久累积了不少相关可资研究的素材,但金庸小说在短短几十年所拓展出的层面,也未必逊色多少,尤其在新兴媒体的拓展上,无疑更远胜于前二书。
2.参与研究的群体。《红楼梦》的研究人群以目前看来,较《金瓶梅》为多,但二者皆以学者为骨干,鲜少民间学者的参与,更遑论跨领域(如影视、旅游、传播界)的支持。相对来说,金庸小说具有较雄厚的研究的可能班底,虽然目前尚嫌不足,但后劲可期。
3.研究组织的建构。相对于《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已有不少专门研究机构、刊物出版的设立,金庸小说有所不足,尽管已有不少类似海宁“金庸研究会”的组织,但玩票者众,凑热闹者为多,这倒是一大缺憾,尤其未能创建具有公信力的刊物,是最大的致命伤。
4.数据库的建立。《红楼梦》与《金瓶梅》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包含各版本、各相关人物、史料及论著搜集整理,已经颇有成果,但也是要历经多年才能完成的;金庸小说的研究,目前仍在起步阶段,还谈不上规模,数据库的建立期待假以时日予以完成。
综合前述四项,“金学”的建构于前两项是条件具足的,而显然于后两项犹待整备。
不过,金庸小说乃武侠小说之一环。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大抵都不会疏略于《红楼梦》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或“人情小说”的区别,更不乏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从小说历史的承继、开展流变中,对《红楼梦》的高度成就予以肯定,这是“红学”发展中相当重要的关键性内容之一。金庸小说研究能否发展成“金学”,我不敢臆断,但如果真有一天形成了“金学”,必将是在武侠小说研究的基柢上延伸出来的,也唯有在此一情况下,金庸小说才能真正“盖棺论定”。因而“金学”如欲真正有所成效,首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涵括金庸小说在内的“武侠研究数据库”或“图书馆”,广搜博纳,且有效率地作整编工作。目前有关武侠小说的资料,散佚于民间,而报刊上的诸多作品及信息,亦迫切需要整理,这将是未来“金学”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