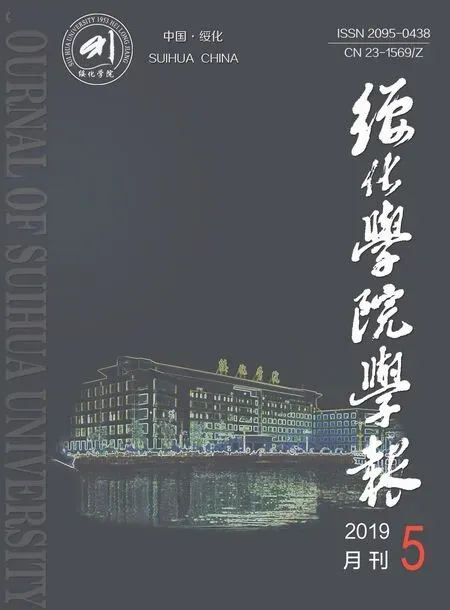人性的震颤 精神的角逐
——对施蛰存与井上靖佛教小说人物的心理透视
2019-02-21吴雪松崔雨薇王书红崔秀兰
吴雪松 崔雨薇 王书红 崔秀兰
(1.佳木斯大学外国语学院;2.佳木斯大学药学院;3.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7)
佛教教义繁复,戒规严格,佛教徒在苦修之路上常遇到各种难以解除的困惑,施蛰存的佛教小说《鸠摩罗什》形象地揭示了佛教徒在成佛意志与情欲本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过程;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宗教小说《普陀洛伽下海记》,则深刻地展现了人的求生本能与宗教风俗的激烈冲突。两者无论在选材内容、主题立意还是表现方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独特个性,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张扬了人性,丰富了人本主义文化精神。
一、选自历史题材,塑造了有道高僧的形象
新感觉派的重要作家施哲存在他的代表集作《将军的头》中,表现了他对佛理的一些人生思考和生存感受,他在宗教小说《鸠摩罗什》中就刻画了在佛性与人性剧烈冲撞的情况下,精神在平静与困窘、寂定与骚动两极中急剧摆动的一个人物形象——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佛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他是后秦时代的一位高僧,历史上实有其人,小说中故事情节大体上符合他的生活经历。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年纪轻轻就成为西域的中观大师,后来笃信佛教的后秦国王姚兴延请鸠摩罗什入长安,礼聘为国师,小说所描写的即是鸠摩罗什从凉州到长安途中以及初到长安时的心理躁动与精神不安。
井上靖擅长写历史小说,有历史小说家之称。《普陀洛伽下海记》就是一篇以日本宗教为背景的小说,小说写普陀洛伽寺的住持金光和尚在习惯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步先代住持的后尘去殉海,描绘了金光和尚的恐怖心理,衬托出和尚也是一个有人性的凡人,这是一篇把成佛的意志和对死的本能恐怖幽默地、残酷地交织在一起的名作。普陀洛伽,在印度南海岸,据说是观世音菩萨居住地。相传其对海即观音净土,修持僧人有下海舍身,往生净土之俗。到了近年,一连三代的普陀洛伽寺住持都在61 岁舍身下海,因此世间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普陀洛伽寺的住持僧一到61岁11月就得舍身下海。这种行为似中国佛教中的投崖舍身一般。佛教慈悲的至高境界是“舍身饲虎”。“舍身饲虎”中的“舍身”本意就是佛教徒牺牲自己的肉体,以表示佛法的大慈大悲的精神[1]。佛教徒“舍身饲虎”等类似行为在日本亦屡见不鲜,常出现投身、入水往生之风。
虽然两篇小说的故事原型都有历史可查,但两位作者都对历史故事加以剪裁和演义,并以佛徒作为主人公,因为在他们身上能够真正体现出佛性与人性冲突的尖锐性与深刻性,最能体现个体生命的本性,最能展现人性的复杂性。两者处理文本叙事的差别目的性不同:施哲存十分注重学理知识运用上的准确性与丰富性,如地道的佛家语汇、准确的佛教风俗的描绘,还包括对人物心理矛盾的深入刻画,以及浓厚的文学色彩的泼墨渲染;而井上靖则为揭示习惯势力对宗教佛徒的人性压迫,多写习俗与传说,并不作细致入微的考据,引用的历史资料也不是很多,如在对观众说解历史故事,不急不慢,娓娓道来,文学色彩也不是很浓。
二、描写了佛性与人性的激烈冲突,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一)在佛性与人性剧烈冲撞的矛盾中,精神急剧摆动的鸠摩罗什。佛教宣传“梵我一如”、业报轮回等教义,佛教认为人和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每个人最大的追求便是通过修行达到超脱生死、绝对永恒的玄妙境界。但是要达到这一圆满境界是不容易的,每个人在世俗中都是不自由的,受到客观世界的束缚。要达到真正的自由与解脱,要放下“我执”,放下“法执”,就是放下所有执着,返璞归真[2]。佛教的基本理论有苦、集、灭、道四圣谛说,而苦谛则是四圣谛说中的第一义谛……所以,尽管佛教教义繁复,宗派林立,但无论何宗何派,都基本遵循四圣谛的思路,其理论的根本旨归都在于教导芸芸众生认识世间苦以及求得根本解脱这世间苦的妙法途径[3]。沙门不净,古今皆然,尤其在色字上定力不足,偷吃禁果的行为更为屡见不鲜。当然,这是凡夫俗子、品位不高的僧人所为,而鸠摩罗什则是有道高僧,凭着多年的苦学潜修以及自己的聪敏智慧,鸠摩罗什对修成正果、圆满功德是充满自信的;凭着龟兹国公主的美妙庄严的容仪以及他俩从小已经萌发的恋情,鸠摩罗什对与表妹结合后将会得到的俗世幸福也并不怀疑。但是,佛国的清修与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与凡夫的爱欲,两者是不可能兼而得之的。这样,就表现为,一方面他在理智上清楚地参透了色情爱欲只是人生的幻像,另方面他在行为上又摆脱不开这一人生幻像的困绕与缠结;一方面他勇于为自己的内在需求去冒犯戒律,亵渎神明,另方面他又不断为自我功德道行的沦丧而深深忏悔。这样,在鸠摩罗什的人格结构中就有了两极的矛盾:一极是佛性,它包括佛家的大智慧、大觉悟与大苦行;一极是人性,它包括人的本能欲望与爱的追求。
小说的情节发展呈现出两条互相依托的线索,即鸠摩罗什的两种身份的交替更换消伏起长,精神在平静安稳与躁急骚动、佛性高洁与情欲魔性之间的急剧摆动,具体表现为鸠摩罗什内在心里的矛盾斗争及和围绕他周围作为反向力量的拉扯和对峙力量的种种抗衡。鸠摩罗什的生活场景主要有三个:历史的回顾、在去长安的道上和到长安后的宫中。
回顾历史:与作为龟兹公主的妻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可以说情窦初开,这是情苗初种阶段,这时是纯粹的情爱,无关乎其他;随后去沙勒国出家修道,十三年间潜修佛法,精心礼佛,这时没有表妹,只有大道佛法,这是对佛法的忠贞阶段。两种身份,两个线索各自安好,没有交织。十三年后,回到龟兹,已是满腹经纶、传授佛祖衣钵的大师,他每天站在讲坛翻动经书,间或瞥见表妹凝视他的黑色眼波,心里不觉一荡,但深晓佛家教义戒规的他知道,佛国的清修与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与凡夫的爱欲,两者是不可能兼而得之的,所以他只能压伏,这是潜伏心里、多年未果的情爱突萌阶段,也是两种身份、两个线索的正面交锋;但清修的道路上荆棘重重,充满艰辛和困苦,在这里,与他情义深种的表妹已经变成与他成佛意志想对峙和拉扯的反向力量:当他散步着静参禅法的时候,表妹追逐的脚步让他窘涩,尽管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定力和道行,觉得自己能抵制任何诱惑,但遇到明媚、聪颖的表妹就真的无法自持;他开始时尚能压伏欲念,但眼眸略处,即见表妹挥动着手中的白孔雀羽扇和月光一同微笑着,这是她充满情欲的行为诱惑,此时鸠摩罗什几乎溃不成军,他只能拜托佛祖能赐予他无限的力量,抵制俗爱的魔性诱惑,在他双手合十,喋喋不休中,表妹的语言诱惑,更是叫他难以抵挡,寂定的心被引乱,他狼狈不堪,只能将枯瘦的手掌掩住,逃进禅室,在佛像前跪下来整夜地忏悔。当龟兹国被吕氏攻破的时候,那渎圣的武夫吕光竟将他和她都灌醉了酒,赤裸了身子幽闭在同一间陈设得异常奢侈的密室里,以致自己亵了苦行,终于与她犯下了奸淫,以至于终于纳了表妹为妻,破坏了他的金刚身;娶妻后为了向世人证明他的道行高深,不是世俗力量所能撼动的,鸠摩罗什饮酒食荤,过着绝对与在家人一样的生活;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两种角色、两条线索在鸠摩罗什身上重合了,其实不然,因为鸠摩罗什心里明白,他的心理满藏着对表妹的爱恋,而表妹也是对他一往情深,尽管凉州人依然把他当作活佛,而他本人在内心却把自己定位凡人,并过着凡人生活,此时,彰显出他的是世俗凡人身份,世俗的魔性情爱已占上风。
赴长安路上:凉州灭亡后,鸠摩罗什受姚兴延请,赴长安弘扬佛法,随军东行,高架庄严的骆驼,遍看无边广阔沙漠,感受随行军士的崇拜,他的高僧意识被唤醒,平静心理又一次产生骚动,具体表现为一抱怨,半抱怨,吕光迫害他失去了金刚之身,半抱怨自己定力之不足;二担忧,担忧姚兴不是真正尊从佛法,他受不到应有的尊敬;三忿恨,因妻之故毁坏了他的戒行,但同时他也享受着她的热情;四放松,成佛与做人两种角色的矛盾冲撞激烈之时,妻子猝死,令其卸掉了人夫之责,精神立刻放松下来,这天夜里,他睡得很酣熟,人格身份由做人完全倾斜到成佛一方而去。
到达长安后,在宫中:妻的死似乎把他的自责与愧疚等等情绪都带走了,他觉得此时一切都放下了,他侦破红尘,心静如水,他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一尘不染,五蕴皆空的境地,可是,殿上的盛大饮宴,古鼎高烧的香,异域的风俗都给他带来了不尽的旅愁,他的心并不安稳,即使闭幕打坐,也不是祷告经文,而是想要心神安定,定心不得,则虔诚祈祷佛祖给予他力量,让他摒弃一切华腆饮食,盛情款待及富丽的陈设,能专心布道,宣扬弘法。可是,心还是颤颤地感到空虚,理智上觉得对于曾经娶妻这事绝不是无所容心,妻子临终遗容常常浮现,树林里,溪流旁,无处不在。他感觉似乎向佛祖说了谎话,罪孽深重,让他良心难宁,实际上是性欲压抑,无处宣泄,压抑愈久,喷发愈烈,于是就可以理解他后来宣解经文时那如画的一幕。后来,鸠摩罗什讲经时又遇到一个与妻子容颜近似的宫女,他如遭电击,脸色灰白,妻子的幻像不断与之交替出现,他的佛法再也讲不下去了。到此时,对鸠摩罗什来说,是佛性与魔性的更进一步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心灵撞击,他绝望又痛苦地明白妻子与儿子都是孽障,但他无力抗争,如果说,以往的鸠摩罗什心理斗争的结果,总是从大智的佛性回归到平凡的魔性,这次摔得更狠,直接从凡人坠入淫乱的地狱中了,他与一个宫女淫乱,发展到他同时与多个宫女淫乱,他管不住自己的心,但又不会脱离圣坛的光辉的普照,所以,他用假言狡辩,有戒行的僧人是得了解脱的,即使每夜宿妓,他还是五蕴皆空,一尘不染的;他用假术欺骗,吞针入腹,结果因为孟郊娘变成妻子的幻像的诱惑,一根针扎了他的舌头,舌头总疼着,妻子的幻像不灭,他是更加地堕落到欲望的地狱中了,虽然讲道依旧……
多年后他死了,火葬后,没有留下象征佛性高深德行圣洁的舍利子,只有他曾用来讲道,却也用来欺骗的“舌头”,它寓意很深,它告诉我们,佛教不是禁欲主义,鸠摩罗什,一个执着于是否禁欲的信徒,他不会是高僧,他有 “圣”言,没有相应的“圣”行,这是对鸠摩罗什只是一个平凡常人的裁定,也是对他的人生的正位与肯定,反映了作者的人本主义文化精神,但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没有理智约束的欲望沉沦、只呈口舌之利的修道行为的一种讽刺,以告知信仰者,成佛或成魔,只在内心,修行的路很是艰难,只要我们走在追求这的路上,俗世的所有苦痛都不再会是难以忍受的苦痛。
(二)成佛的意志和对死的本能恐惧激烈角逐中的金光和尚。宗教风俗习惯有时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但其力量影响是超人想象的,就如狂暴的龙卷风一般挟石带沙,人在其面前变得渺小无助,甚至被它毫不留情地吞噬。金光和尚就面临此种力量的压迫,他对世间为自己下海舍身的看法感到有点眩惑,曾打算找个机会向人声明,请人谅解,自己下海舍身的事还得再延缓几年,可是信定他舍身下海的人很多很多,似乎是世间所有人了,他无可奈何。世俗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旋风一般,人被包裹其中,被扭转以致变形。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会心怀恐惧或犹豫不决,就是有很深修为的金光和尚也没有甘愿舍身、义无返顾的宁静、详和的心态。世俗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的推动力,推动着金光和尚前行,但更巨大的推动力量来自他心灵深处——对神佛的崇敬,对成佛成仙的无限想往。多年来,历代舍身下海的先人的事迹撼动着他的心,他的脑海中无数次地重复演绎着他们下海的故事。先人对死亡的不同理解,临行时的不同表现,在他心中激起千层波浪:先人在紧急关头能够宁静安详时,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心如止水;先人果断勇敢时,他觉得也应该一往无前;先人忧虑害怕时,他也体验到了无法言说的恐惧与不安……
虽然怀有将失去生命的不平与不甘,但因积久的对神佛的崇敬与向往,他不能只因渺小的一身的言行,使伟大的观音蒙受瑕疵,这才是身为僧侣的对菩萨的不可饶恕的罪孽,死了也消灭不了的。他不能做不可饶恕之人,所以他庄严宣布于本年十一月下海,但宣布之后,他的心并不宁静,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常常令他精神恍惚,他常常不自觉地盯着弟子清源那剃得青青的头皮,留恋自己逝去的青春;接待来访与应酬他人时,常常表现得心不在焉;他虽整日诵经,嘴唇蠕动,而心鹜八极;停止诵经时,眼神茫然地凝视着屋子的一角,就好象变成一条恍惚鱼了,那是他又想起某位下海上人了;而当他恢复人眼的时候,那是他在责备自己的,同自己做斗争花费了他很大的精力……
金光和尚去冲撞屋形的板壁象征着向世俗力量的挑战,他的久被压抑的自我意志、自我生命力终于得到全方位的释放;船又载着活的金光和尚,重新由几个人的手推到海浪中去则说明世俗力量的强大,金光和尚临终寄语道出了成佛的虚妄,也是对宗教风俗压抑人性的有力控诉。自金光和尚下海事件后,世上对普陀洛伽寺住持的下海改变了看法,表明金光和尚的抗争震撼了世人的心灵——活人不再下海。
在耶、回、释、道数家宗教中,佛教从价值观上否定人生是最为激烈的。在对本能欲望的处理上,佛教采取的是勘破与根除的办法,强调通过苦行清修的个人磨炼断除无明与妄念,达到四大皆空,心神澄彻的境界。而达到这种大智慧、大觉悟的境界,需要的是难以克服和忍受的大苦行,它要压抑人的能量,抑制人的本性的冲动,剔除平常人正常的爱的欲望,甚至要无恋生、无惧死。遁身佛门中的僧徒就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得道的高僧,一方面却是生存于世间、吃五谷杂粮的凡人。这样,在他们的人格结构中就有了两极的矛盾:佛性和人性常常冲撞、对垒。宗教意志是体现生命运动无终止性和生命组合体可分解性对抗的结果。当人们的视线超越生命个体而认识到生命永远寓于运动之中时,就会产生让生命摆脱个体束缚而使生命走向永恒的强烈愿望。坚决地表达和执行这个愿望,即是宗教意志。宗教意志是宗教思想凝聚而成的,它将恋生情感集中为一股向超现实目标行进的力[4]。
由于鸠摩罗什与金光和尚一直把传道成佛当作自己至高追求,当平常人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流露的时候,具体地说,当面对自己深爱的人或面对死亡的时候,精神的紧张才会出现,人格的深度才会呈现。鸠摩罗什终于确定自己做一个凡人,哪怕要忍受和咀嚼芸芸众生无可回避的烦恼与苦痛,哪怕要冒着坠人地狱万劫不复的凶险,这在佛家看来是背叛,是坠落,而从非宗教的世俗化眼光看来,这却是,对人生的肯定与礼赞。金光和尚虽然最终还是走向死亡,但是他已经参透自己下海了无意义,对死的恐惧、生的渴望最终使他使出超凡的力量冲撞象征壁垒森严的宗教习俗,人性获得了完满的回归,生命能量得以自由地释放。
三、矛盾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重要作家,从其第二部、第三部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开始,创作风格有鲜明的现代派倾向,这是和他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包括无意识说(人的非理性部分)、人格说(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释梦说、本能说(生本能和死本能)、力比多说(以性欲为中心的本能欲望),等等。性的本能欲望,是人性结构中一种最强烈、最原始、最持久也最难以遏制的内在驱力,这种力量是超大的,对于普通人如此,更别说性心理压抑深重,潜藏性欲暗流的佛教徒,所以,从禁律森严的佛教历史上寻找人性力量的突围与冲撞,更能揭开佛教的神学雾纱,让人们看到在那枯寂入定平直的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揭示了鸠摩罗什——性本能压抑(本我)、想情爱与成佛兼得(自我)、修炼成纯粹的佛(超我)之间的矛盾斗争,展现出他人格分裂的激烈过程,十分典型地表现了施蛰存对精神分析尤其是性心理剖析的兴趣、手段与功力。最精彩的分析莫过于鸠摩罗什宣讲经文时,看见妓女孟郊娘时的情不自禁的反应,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凝视→流动的眼→闭眼→再闭眼的一系列动作表现出来:初见荡女孟郊娘容颜,他是吃惊地凝视,这是性欲本我的表现;对于讳莫难懂的经文,她非懂却装懂,让他有指引之感,于是他流动着光亮的眼投射过去,这是性本能与想修炼、又放不下情欲的自我矛盾斗争;一只嘤嘤的小飞虫停落住他蠕动的嘴唇上,他怕影响他的高僧形象伸手把它拂走,却一径停在荡女光亮的黑发上,完成了间接之吻,撩动了他震颤的心,他急闭了眼,匆匆收辞,无心再站,这是本我的胜利,想成佛的自我的让位;返回住宿之地的路上他闭着眼,合着掌,如同普通僧人,忏悔又祈祷,这更是自我和超我的放弃,本我的绝对胜利。整个场面,由睁眼→闭眼的眼神流动,又是外在魔性牵引力量与他想保持佛性心性对峙力量一次正面交锋,他的心理斗争很激烈,魔性的力量之大超乎他想像,他慌不择路,从圣坛坠回凡人。总之,施蛰存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汲取和借鉴主要体现在潜本能描写、联想与幻想、性心理分析、多重人格等手法的运用上,并十分得当,成功,因此称他为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新感觉派作家和心理分析小说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井上靖在《普陀洛伽下海记》这篇小说中也大量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但不像施蛰存所运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那样缜密细致,多以回忆和联想串联故事,这种通俗明白的表现方法是由它所反映的社会世俗这一生活内容特点决定的。井上靖在进行心理分析的同时,也像施蛰存一样,佐以大量的行动表现,以心理引导行动,用行动反衬心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更好地反衬主人公心理的波动和起伏。如他也不约而同地从人物的眼神的变化——闭眼→恍惚鱼眼→恢复人眼→闭眼的一系列动作中,来透视人的内心世界的风云突变、瀚海难平:接近下海的日子,金光和尚内心十分不静,他要不闭目诵经,要不,就睁开恍惚鱼似的眼睛,茫无目标地看着什么地方,此时,他准是在想哪一位自己前辈的渡海老人了;他一天几回只有很有限的时间从恍惚鱼眼睛回复到人眼睛,只能单靠诵经得到解救,从自己眼里驱除轮流出现他眼前的那些下海上人的面影,这可花了他很大的精力;当有一天,知道下海之日终于来临,他的身体是一动也不能不动了,与其说是身体不能动,还不如说是精神已彻底崩溃,他心存的侥幸终于在这一天化为乌有,瞬间变成了任人摆布的木雕泥塑。在对以往上人的下海形象的回味中,他深刻体悟到他们下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像别人想象的那样,而是各有隐衷;由对上人的崇敬到怀疑,实际上是对神佛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自然地也就对自己下海的意义产生了疑义,从而动摇了舍身下海的决心,所以,当从屋型板的缝隙中,看到波涛澎湃、充满力量的大海,他愤怒的使尽全身气力去冲撞屋形的板壁,落到海里。无数次不同的感受与认知,揭示他人格发展过程和脉络,反应出人的求生之本能与宗教风俗习惯之间的较量过程,最终,荒谬宗教习俗被遗弃。
四、对佛教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剖析,达到自我人生思考的目的
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两位作者都没有把佛教文化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来综合考察,他们只是把对佛教文化的某个方面进行剖析当作手段,来达到自我对人生问题思考的某个目的。佛性与人性的冲突与融汇,成为他们思考的主要对象,通过得道高僧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佛性与人性的冲突点的揭示,来展现作者对佛性与人性关系的理性思考。根除欲念、了无尘埃是对凡人的超高要求,常常要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也造成了无数人间的悲剧。
施蛰存通过鸠摩罗什最后的结局,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佛学问题的思索:佛性与人性不是只能对垒、冲突,它也可以达到最佳状态的圆融;佛教不是禁欲主义,而是要信徒们修炼成一种勘破红尘、五蕴皆空、心神澄彻的大人格,这种人格的修炼很艰难,前行的路上充满艰辛,不仅要抵制外来的诱惑,更需要内在心理的调衡甚至可能需要战胜狭隘自我的抑囿。只有当一个人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各种欲望、贪念、无知和喜好而带来的苦痛和障碍才能达到此种境界。
井上靖则通过金光和尚的犹疑、不安和恐惧的表现说明面对死亡人类有共同的心理表现,即使修炼很高的僧人也不例外。作为宗教,它一方面向人们展现了佛教的光辉,使它成为人们精神皈依的家园,给人以幻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虚幻性,这种虚幻性,常常成为某种陷阱,人被陷进去而不自知,可贵的是金光和尚认清了这一点,金光和尚的最后结局说明:正视自己,展现人性力量的可贵,生命的能量是巨大的,它能穿透、辐射宗教和社会共结的森严壁垒,只要心中有理性光辉的灼耀。
结语
虽然两篇小说属于不同国度,但施蛰存与井上靖二人都采用不同的非常独到的方法,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物的复杂微妙心理并触及了人性灵魂深处的奥秘,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了作为社会之人不能不有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也为其如此,才显得生命力量的可贵和人生意义的无穷,只要人类对天人奥秘的探求永无止境,那么佛教文化就永远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我们要彰显生命力度,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从而活出自我,获得完美人生,对生命力度的永恒渴望和追求,是我们挑战外部世界,战胜自我,实现完美人生的依据。只要我们存在一天,这种追求将永远不断,永无止境,这也是人类能栖居世界,诗意生存的合理方式和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