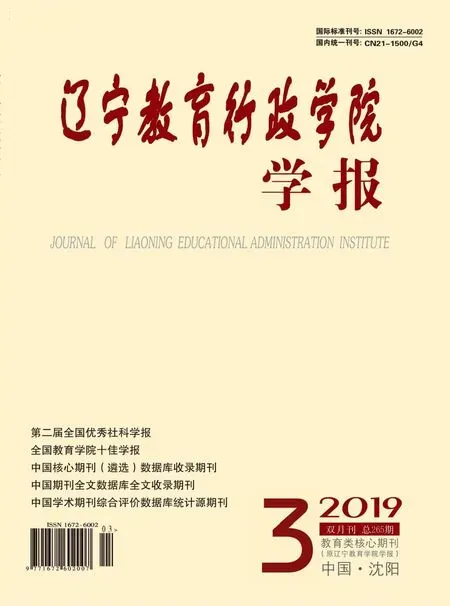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对《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的文献再考察
2019-02-21何天平
李 政,何天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美国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早期研究兴趣聚焦于16世纪的法国史领域,据此于1959年完成博士论文《新教与里昂印刷工人》,并发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其中八篇集纳形成1975年出版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此后,她跨向女性学、电影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进行史学研究,先后于1983年完成《马丁·盖尔归来》、于1987年完成《档案中的虚构》、于1995年完成《边缘女人》、于2000年完成《16世纪法国的礼物》、于2006年完成《骗子游历记》等一系列在交叉学科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从这些后续的论著中,可以找到戴维斯较为显著的一个研究旨趣偏向,即对历史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的考察。在史学视角下对电影的研究,诞生了其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1]。
在《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一书中,戴维斯进行了电影和史学的交叉研究。通过分析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吉洛·彭泰科沃的《奎马达政变》、托马斯·古铁雷斯·阿里的《最后的晚餐》、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勇者无惧》以及乔纳森·戴米的《真爱》等五部时间跨度近40年的电影作品,戴维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这些以奴隶形象及其抗争行动为主题的电影进行结构化拆解,探索“历史电影”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尝试对“电影在有意义且准确地讲述‘过去’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潜力?”[1](P12)“电影技术如何形塑历史信息?”[1](P15)“ 电影 告 诉 给 我 们 关 于‘过 去 ’的 什么?”[1](P24)等问题进行具体而细微的阐释。
一、研究背景:电子媒介和数字影像的勃兴与全面介入
在对《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这一学术文本进行阐释前,有必要对戴维斯写作这本书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个人背景进行相关解读。
从彼时大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电子媒介的勃兴让数字影像开始介入历史书写的过程之中。每一种新的大众媒介的出现,都会带来关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重构,而在当电子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载体之后,长达近百年的媒体革命便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相较于20世纪之前印刷大众传播媒介“算术级别”的缓慢发展,电子大众传播媒介呈现出“几何级数”般的增长。[2](P15)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咖啡馆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数十部影像短片,作为电影的前身并由此宣告电影的诞生。自此,人类开始走进动态图像文化时代之中。1906年,广播诞生;1925年,机械电视问世;1936年11月英国BBC电视台定时播出节目,则正式划定了世界电视广播事业的开端。不断升级的媒体革命带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在技术和文化双向驱动下的电子媒介变革,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开始全面介入人类历史的书写之中。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西方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以影视作品为代表的视觉媒介,比印刷品更能迎合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冲动。[3]
另一方面,电影诞生之后,尤其是从1960年前后开始迎来了急剧的成长发展阶段,大量的文化注意力聚焦于此,这也成为戴维斯相关研究的起点。其选择研究对象发轫于1960年上映的电影《斯巴达克斯》,也暗合着电影研究的阶段性逻辑。当前可见的电影历史分期研究中,多数将上世纪60年代至今视作电影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中经历战争后的世界电影呈现全面的振兴态势,其艺术表现手法和呈现技术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4](P157~163)
至于电影学和史学研究交叉之下产生的新路径,也与西方史学研究在20世纪的全新转向紧密相关。尤其是彼时在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和数字影像的影响下,亦催生了“影视史学”这一全新研究取向。20世纪初,“新史学”诸种流派渐兴,其主导范式在于对构建历史的各方面进行整体性研究;70年代以来历史学继而出现“语言学转向”,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其主张“自下而上”地考察历史,并在文本构建中推崇叙事性的写作方式,令史学研究中注重叙事的传统以新的姿态重回主流学术视野。戴维斯也在其书中提到,在这一时期“叙事”在电影领域中也开始处于重要地位,她援引大卫·波德维尔“电影既是显示也是诉说,表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所有手段都被囊括在叙事之中”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在看待电影再现历史这一做法的立场。[1](P14)也正由于电影等电子媒介所具有的这一叙事功能,大量影视史学的研究渐次涌现,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用“historiograph”一词来归纳对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以及人们由此获得对于历史认知过程的相关研究。[5]在戴维斯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与历史的学术研究之间出现了平行发展——都对于奴隶自发的反抗运动投注了新兴趣。[1](P22)正因为影视史学的起步发展以及奴隶电影的涌现,《银幕上的奴隶》一书的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得以具备。
此外,戴维斯其人的相关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着这一研究的诞生。本书中,戴维斯于致谢中特别提到家庭环境带给这部作品的影响——她的父亲朱里安·里昂·泽蒙热衷于撰写剧本和音乐剧,而她丈夫的父亲何瑞斯·班克洛夫·戴维斯则是废奴运动倡导者的后代。[1](P152)可以说,这些生活背景中与戏剧、奴隶发生关联的要素,不经意间成为了触发戴维斯思维火花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戴维斯的部分工作经历也与电影领域密切相关。1980年至1982年,戴维斯担任由丹尼尔·维涅执导的电影《马丁·盖尔的归来》的历史顾问。在此过程中戴维斯感受到了历史电影在处理历史上的局限性,于是她在1983年完成了《马丁·盖尔的归来》这部历史著作,以文字的方式还原这个发生在16世纪的传奇故事。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历史和电影”课程,课程中所探讨的部分案例以奴隶制度和反抗奴隶制度的行动为主题,这也从某一侧面强化了她进一步研究电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想法。[1](P8)
二、文本再解构:寻求历史与电影的“平衡点”
《银幕上的奴隶》的主体文本分为五章,第一章着重对电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诗歌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探讨。戴维斯从对希罗多德、修西得底斯、亚里士多德等对诗歌与历史的比较与区分的批判反思着手,认为这些区分在实践中往往含混不清,进而导致诗歌叙述与历史真相的偏离,并且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历史电影、历史著作以及历史真相之间。更进一步地,她论及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也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表现历史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历史电影和历史著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戴维斯的观点是,“坦诚是述说过去历史的必要条件之一”,[1](P16)并由此总结了撰写历史著作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一是史学家在搜集和评价史料时,不仅要注重其深度和广度,还要尽可能地保持摒弃偏见和先入为主思想的开阔观念;二是要准确给出史料的来源,承认模糊、不确定或者龃龉之处;三是厘清自己的作为以及提供相应依据;四是无论做出主观性判断还是规范性判断,都不能让这些妨碍他们探寻所有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参与者内心世界的努力;五是不管在多细微的角落也不能刻意伪造事件或者有意隐瞒证据而制造错误印象。[1](P16~17)这些所谓的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历史电影的创作过程。同时,戴维斯还强调了历史著作和历史电影之间的书写差异:一是参与的创作者人数规模的差异;二是创作者对于真理的坚守程度常常有不同程度的要求。[1](P18~19)正因如此,电影在处理历史过程中拥有着相对多的自由和空间,戴维斯主张将历史电影看作是一场关于过去的“思想实验”,其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手段,将历史事件、拍摄地点的围观群众以及电影的观影者统统卷入其中。本书的后续部分也可以说是戴维斯对于这场“思想实验”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必要元素,以及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的深层探索。
第二章至第四章中,戴维斯以《斯巴达克斯》《奎马达政变》《最后的晚餐》《勇者无惧》《真爱》五部电影作为个案切入分析,其中仅有《奎马达政变》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叙事作品,但还是能在南美地区的历史中找到部分依据线索。对这些个案的考察,是因为“它们所呈现的是不同的问题,它们所提供的答案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意义”[1](P25)。前三部电影主要讲述罗马、加勒比海、古巴奴隶的反抗故事,而后两部故事的主要背景则在美国。主题方面,《斯巴达克斯》讲述的是抵抗与求生的故事,[1](P22~41)《奎马达政变》《最后的晚餐》有着浓厚的宗教仪式感,[1](P42~65)并且这三部电影也都表达了“个体”寻求他者(奴隶主或者主流社会)认同的中心思想,《勇者无惧》《真爱》则着眼于奴隶群体的集体经验,以及对奴隶制度给这些非自由人所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理灾难的反思。[1](P65~109)在对个案的分析中,戴维斯结合了剧本的来源、参与制作人员(尤其是历史顾问)、创作过程、服化道、人物角色、情节内容、导演访谈、相关评论等丰富素材,并与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详尽的文本对照,尝试勾勒出电影制作者们将历史事件搬上银屏的完整过程,以及找出最终电影内容与历史事实的照应关系:哪些是合乎历史的?哪些是创作者的合理虚构、想象和诠释?哪些是虚假的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因是什么?
第五章,戴维斯提取出五部电影所引发的共同思考:“这些电影进行了何种历史调查?”[1](P110)《斯巴达克斯》呈现出了古罗马的社会差距,《奎马达政变》《最后的晚餐》展现出历史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史(如宗教仪式等)的侧影,《勇者无惧》聚焦于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而《真爱》则以文化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混合方式关照奴隶制度所遗存的历史问题,同时女性主义的光辉也在其中熠熠生辉。[1](P111~112)戴维斯也指出这些电影中与真实历史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其一,电影在呈现历史人物时存在的偏颇之处。奴隶主、统治阶级以及白人的形象被矮化,黑人常以“情同手足的英雄”的形象出现;[1](P113)其二,由于史料不足而产生的对历史的过度虚构,由此向大众提供一幅错误的历史图像;[1](P113)其三,电影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误读”。电影创作者认为观众保持着让过去符合当下预期的心态,并在呈现电影作品给观众时并没有明确提示哪些内容是虚构的,即使这些虚构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1](P119)不过,纵然历史电影在呈现历史事件时存在缺失,戴维斯仍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电影不能为我们带来希望”。[1](P123)一部历史电影不仅让观众“了解历史”,更让他们得以走入历史语境之中,采撷到对于生活有所反馈的现实力量,这便是戴维斯所言的“希望”。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书中给出的内在线索是寻找平衡点,即一部历史电影何以尽可能理解和呈现各方立场,何以对历史证据保持公正客观的处理态度,何以正确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等。[1](P112)(P118)
三、戴维斯研究影响下的史学观
《银幕上的奴隶》出版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也是戴维斯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特别的存在,总体上较为完整地再现了戴维斯的影视史学观。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在书中的研究视角深受新文化史观的影响。从书中关于历史电影的“真实”与“虚构”的探讨再出发,可以进一步对戴维斯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与“不确定性”的宏观认识进行再把握,从而来启发这一学术文本对新史学研究的思考。
(一)历史电影的“真实”与“虚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戴维斯其人的学术研究更偏重于对电影与历史的关注,并介入大量电影与史学领域的交叉研究。1983年出版的《马丁·盖尔》具有开拓意义,但其中仅仅是闪烁着戴维斯影视史观的点点微光。担当《马丁·盖尔归来》的电影顾问以及将这个故事写成学术著作出版的经历,让戴维斯回到关于“把历史形诸文字”和“用电影来述说历史”两者之间关系的再思考,而《银幕上的奴隶》一书则较为系统地对其研究脉络进行了系统化、结构化的阐释,并奠定了戴维斯在影视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事实上,历史电影的出现曾让历史学家头疼不已。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严谨、专业的史学研究,大量“虚构”手段使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场景发生了偏移。同时,这些具有通俗化、流行化特征的电影文本,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中传递的有关过去的信息。当然,也不乏支持者,他们从视觉化手法出发,论述其在还原历史事件时逼真的视听体验。
对于电影与历史的关系,戴维斯显然更倾向于积极的态度,即使她指出在呈现历史事件上,电影仍旧处于起步探索阶段,[1](P13)但也始终认为历史电影并没有让历史脱离于真相本身,“电影创作者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剽窃者,而是以历史为重的艺术家”[1](P21)。《银幕上的奴隶》的面世,大为抬升和挖掘了历史电影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为历史研究新路径的开拓作出了显著贡献。如何把握历史电影中“真实”和“虚构”的尺度,是《银幕上的奴隶》中反复论证的核心议题,戴维斯对此的回应是,要在重视历史证据中找寻平衡。只有找寻到足够的证据,才能处理好历史电影中“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当然电影创作者运用这些史料的态度也同样重要,只有其不加偏颇地呈现所掌握的这些证据,历史电影才能够真正负载“再现”过去的能力。
戴维斯其人的观点与建构影视史学这一跨学科“学术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互动。海登·怀特曾指出历史电影和历史著作在追求历史真实上都存在着局限性,且两者之间的“虚构”其实别无二致。[6](P77)戴维斯对此也进行了回应,她梳理了撰写历史著作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强调书写史学的规则,并指出在这些规则之下,史学研究还有着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关注电影研究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认为:“影视史学应有某种标准,与媒体的潜在价值相一致,而不能以书写史学的标准衡量影视史学”。[7](P1193~1199)对此,戴维斯在《银幕上的奴隶》中也做出了具体回应。而在该书出版后,罗森斯通发表了《电影书写历史是否可行?》一文,对《银幕上的奴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论,整体上对戴维斯的研究成果持积极态度,对戴维斯所划定的“好的历史电影”的标准也予以赞同。[8(]P134~144)
总体来看,戴维斯虽没有极为专门化地从事影视史学的研究,但她的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借由各种路径在影视史学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部分历史学家对于电影作为历史书写载体的看法,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二)历史的“真实”与“不确定”
对于“真实”和“虚构”这组矛盾的探讨,当然不仅囿于历史电影的范畴,同样是历史研究中的元议题。古典史学讲求“真实”,对于“真实”的执着在19世纪以兰克为首的年鉴学派抵达巅峰,其“如实直书”的观点一度被奉为圭臬。20世纪初开始勃兴的“新史学”则对传统史学做出批驳,并借鉴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为现当代西方史学开创了新局面,当然,其对历史科学性和客观真实性的反思也一度导致自身受到边缘化的局面。此后,以戴维斯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在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开辟出新文化史的研究新路径——不过度缠绵于真与假的二元争论,主张通过研究调查开掘关于历史的叙述。
在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中,便着重探讨了“真”与“假”的问题。在她看来,对于马丁·盖尔的叙述就是对于历史的“真实”与“不确定”的深层探索。而在《银幕上的奴隶》中,电影《奎马达政变》的故事是完全虚构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将其视作“好的历史电影”。一方面,她认为《奎马达政变》所描绘的事件曾发生于历史之中,同样遵循着历史的某种“真实”;另一方面,她对这部电影制作者对待历史证据的态度予以认同,即使所掌握的史料存在“不确定”之处,电影制作者通过反复推演逐渐敲定细节,对于“虚构”成分的掌握相对得当。
戴维斯在《银幕上的奴隶》中援引了梅瑞狄斯·马兰对于历史不确定性的论述——“友爱号”事件的确发生了,从电影中我们得以窥其画面、知其因果,但是始终无法亲眼见证真实的历史场面。每一个人的眼睛和心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身处历史事件现场的目击者而言,他们任何人的看法都不足以被称为“真相”。虽然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终究只是对于动态历史画面的支离破碎的“惊鸿一瞥”。
在戴维斯看来,历史是一种“难以捕捉”之物,所谓的“真实”其实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也恰恰是这些“不确定”使得历史拥有了更大的、值得探索的魅力。戴维斯的史学观念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源流,包括年鉴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妇女史和性别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戴维斯在年鉴历史学的影响下探索出了“新文化史”的道路,而其他三方面的思想源流则在其实际的历史研究和论述中涌动着活力,为她把握历史的“真实”与“不确定”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工具。
戴维斯的史学观念对于整个历史研究的脉络都影响颇深。1987年,戴维斯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以其自身的卓越成就在保守传统的领域中获得了承认。众多新文化史学家都予以戴维斯极高的评价,如林·亨特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将戴维斯称为“所有人的灵感源泉”,书中更将戴维斯与E.P.汤普森一同列为20世纪60、70年代探索文化史的先驱。[9](P81)由此,便可见戴维斯在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结语
戴维斯的《银幕上的奴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不言自明。除了对于电影和历史的探讨之外,这本书还在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中释放着更多的能量。首先,能够深刻感受到戴维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某种认同,她在书中多次强调观众的主体性,她认为当时很多历史电影的一大弊端就是“低估了观众”[1](P117)。同时,她也指出书中提到的五部电影致力于将经验传递给“一般大众”而非少数精英群体。一直以来,戴维斯所关注的都是“传统上被摒弃在权利与财富核心之外的人们”,其选择大众化的奴隶电影进行历史研究,也是在回应她的社会关切。其次,《银幕上的奴隶》书中有着显著的女性视角,呈现出大量对于女性的关照。尤其是在对于电影《真爱》的分析中,女主角赛斯、二女儿丹佛、名叫宠儿的不速之客以及祖母撒格斯登各自代表了深受奴隶制度迫害的不同的女性形象,女性叙事同样被放置于全书的主要视野之中。
当然,《银幕上的奴隶》也并非没有受到争议。但对这些“含糊”和“存疑”之处所进行的再探讨,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戴维斯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将每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和盘托出,并且就电影的内容所反映的奴隶制度本身做出大量交代和分析,这难免给读者一种龃龉之感——究竟是在讨论奴隶制度,还是在讨论电影和历史的互动。虽然能明显地意识到文本所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后者,但是似乎没有真正深入进去,而是“点到为止”。由此也导致了第二点质疑,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一方面,《银幕上的奴隶》在文本分析上树立了良好典范,但对方法论的构建却显得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其对奴隶电影的聚焦是一个可以深度切入的历史主题,但同时也构成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视野,其对于电影与历史关系这个宏大命题的探讨仅仅囿于对奴隶电影的分析是否足够,而戴维斯似乎也未能在本书中对此论述明晰,启发性有余,建构性不足。除此之外,就戴维斯的影视史观而言,也不能否认其中潜在的某种缺失,即影视文本存在话语局限性,其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本身就处在一种“浅尝辄止”的状态。
但无论如何,戴维斯其研究对历史电影的“真实”与“虚构”、对历史的“真实”与“不确定”等相关元议题的探讨,以及影视史学观的建构和反思,都延展出了丰富的再思考线索,而有如“希望之光”的存在也在事实上启发着影视研究或者史学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