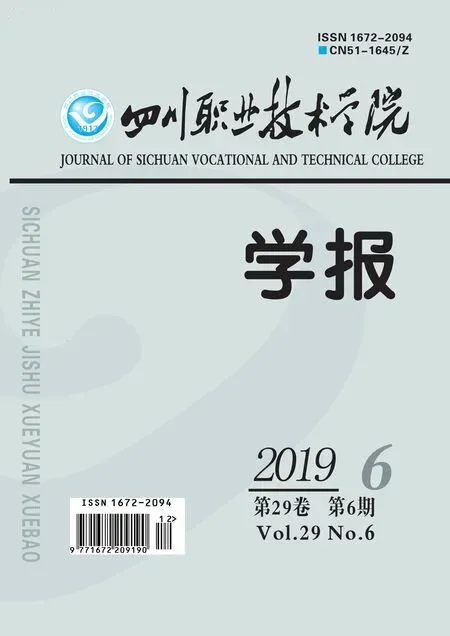先秦游侠人格与咏侠诗歌滥觞浅探
2019-02-21曾晓洪
曾晓洪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系,四川 遂宁 629000)
一、先秦游侠的人格
正史中《史记》首次为游侠列传,随后《汉书》亦为之列传。大概是因为游侠活动导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1],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礼法要求严重冲突,以后正史再无游侠传。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游侠传,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游侠这一特殊人群主要诞生在战国后期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这些人“皆藉王公之势,竟为游侠”[1]。班固对游侠产生的背景有自己的认识,即“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1],认为游侠是乱世的产物。而司马迁则认为,游侠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缓急,人之所时有”[2],为人解决“缓急”的高义催生了游侠。
《史记·游侠列传》所传侠客俱为司马迁同时代人,如朱家、田仲、剧孟、郭解之徒。而先秦侠客如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在《史记》中均有列传,未入《游侠列传》,《汉书》亦与之相似。裴骃《史记集解》认为延陵可能为赵襄子所召之延陵生,但又不能确定。但据司马迁对以上诸人“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2]的描述,延陵似应为吴国公子季札,季札贤能,封于延陵,被称为延陵季子,其传记附于《吴太伯世家》。最让司马迁遗憾的是,“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与延陵等人相较,“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湮灭不见。”[2]
司马迁说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这是司马迁概括的游侠最突出、最主要的品质,也是衡量游侠或侠客的标准。游侠“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与“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2]之徒实有本质的区别。以此标准出发,《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人,恰好符合司马迁最为心仪的古布衣之侠的形象。
游侠作为一种身份,并不具备道德或法律的标准,它并不以君臣关系这一最大的伦理规范为前提,而是有游侠自身一套“义”的标准。司马迁开始强调游侠之“义”,尽管这些“义”与主流文化的“义”在许多地方有相通之处,如都强调忠勇、然诺、报恩等,但二者却有较大的差别,它是游侠自己独特道德视境的外化,因此游侠的行为常常“不轨于正义”、“ 时扞当世之文罔”,与儒家之“义”相去甚远,其任侠之举或合法或非法。总结起来,游侠活动主要有:结客任气、藏亡匿死、报德报怨、攻讦长吏、赈济贫弱、锄暴安良、劫掠财物、走马纵犬、饮酒赌博、纵情声色等等。也有的修行砥名,甚至少游侠、长折节而功成名就。基于此,汪涌豪先生在《中国游侠史》中将游侠的人格特征概括为“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放”、“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3]。
其实,在游侠之外,先秦许多人的行为都有上述部分特征。他们虽并不以“侠”名,但却有“侠行”、“侠节”、“侠情”。《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为孔悝而死,其临死缨断,乃曰:“君子死,冠不免。”从容结缨而死。仇牧为宋闵公报仇,刺杀宋万而终为宋万所击杀,死而不悔。公孙杵臼、程婴为救赵氏孤儿,一赴难,一忍辱含垢,刘向在《说苑·复恩》中评价他们是“信友厚士”。钱穆先生认为这些人“宁愿舍其生命,至死不反顾,则皆有一种人生律则焉,在彼心中,自认为万不当逾越者”,是春秋时期“一种最高的道德精神之表现”[4]。这种“最高的道德精神”应是侠义精神的源头。
侠义精神及侠行的存在,比游侠的产生要早得多。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忠勇,临难不苟免,急公好义,珍惜名誉等,既是传统忠义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侠义精神和行为的表现。
在游侠产生以前,侠义精神及气质就已经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它分途发展,一方面使许多人成为游侠,一方面进一步积淀于民族心理,在更多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晋国赵盾,偶然施给饿倒在桑下的灵辄一饭之恩,在赵盾被灵公追杀时,灵辄挺身相救,连名字也不相告。齐人鲁仲连义不帝秦,帮助赵国联合梁、燕、齐、楚共御强秦,事成之后,拒绝平原君的封赏,他笑着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扰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5]并且“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虞卿为救朋友魏齐,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之偕逃。墨子及门人急公好义,《墨子》大讲“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颜氏家训·省事》称“墨翟之徒,世谓之热腹”,而鲁迅先生则认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6]。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不绝于书,他们的行为逐渐与为了私欲而作奸犯科相对立,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奋不顾身,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大义、忠勇,使“侠”之精神和节操得到升华。李贽就曾在《杂述·昆仑奴》中说:“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无怪乎后世常把他们目为侠客,也常作为歌咏、赞美和倾慕的对象。
现存典籍中,《韩非子·五蠹》从维护封建集权的法家思想出发,最早抨击“侠以武犯禁”。战国时期,各国对包括游侠在内的豪强的态度有所不同。“大别之,六国基本上是维护的态度,秦国是打击的态度”[7],因此战国时期游侠活动较为炽烈。汉代游侠活动进一步高涨,但从高祖开始,对于游侠以齐民而作威作福,养私名以夺朝廷官府之誉的危害性就有所认识。汉初,即开始对游侠进行抑制、监督,直至汉武帝任用酷吏加大打击的力度。这种针对各种游侠的严酷打击一直持续到西汉末,从此,游侠活动基本呈现平抑的状态,总体情况是,社会承平时,游侠活动往往少见,社会动荡时,游侠活动就相对活跃一些[8]。
二、先秦咏侠诗歌的滥觞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状态,侠客行为及侠义精神、节操,也较早成为文学或其他典籍所涉及的内容。
侠义精神和行为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记录。如《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巨子孟胜答应为楚国阳城君守城,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信义,以死践行与阳城君的约定,捍卫墨家的信誉。,演出了一幕悲壮的侠义剧。《左传》所记的灵辄、子路、仇牧等,《战国策》所记之毛遂、豫让、聂政、荆轲、朱亥、侯嬴、冯谖、鲁仲连等,或报恩而勇于赴死,或酬义而竭虑纾难。赵翼说:“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即使如孔门弟子,也以义字当头,就连韩非子也忍不住对其高义心折不已,他在《显学篇》对漆雕开之义十分肯定,《孟子》也对孔子学生北宫黝的侠义精神进行赞美。诚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尽管各家各派在对“仁”、“义”的理解上,在思想主张等方面有不同,但这些言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度却是相通的。
这种精神气度除了在像《左传》、诸子等这些书籍里有许多记载外,在《诗经》里也有所反映,可以视为咏侠诗歌的滥觞。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其作品下限不在游侠主要形成期——战国时期,然而在《诗经》中已有了歌咏侠义的影子。《国风·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周振甫先生注引《毛诗序》:“《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周先生注“王”为“周王”,可见他并不赞成此说。他又引《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山西天水、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公木、赵雨先生认为此诗“充分反映出战士团结友爱和同仇敌忾的精神,充分反映出人民开朗豪放的性格和慷慨宏阔的胸襟,是最古老的富有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9]。程俊英、蒋见元诸先生也认为此诗是“流传在民间的战歌……反映了秦风的典型风格。同袍同衣,同仇敌忾,慷慨从军,奋勇杀敌的精神充溢全诗”,并认为是“边塞诗之祖”[10]。因此这首诗,既是战前动员,又表现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精神,体现了勇与义的侠义气质。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引逸诗: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杨伯峻先生认为此诗义不可解[11]。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畏”字条有:“畏,拘禁。《论语·子罕》:‘子畏于匡’;《吕氏春秋·劝学》:‘孔子畏于匡,颜渊后’。”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畏者,有戒心之谓。”并引《史记》:“阳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但从孔子被围困时所表现的态度来看,朱熹的解释显然不太准确。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显得非常自信和镇定。因此,“畏”字不能训为“惧怕”、“戒心”之类,而应当是“围困、拘禁”。孔子不是“对匡人有戒心”,而是“被匡人围困”。以此来解释《左传》逸诗,就可以通畅了,它说的是,朋友被围困,要前往营救。这首诗比《无衣》表现的侠义思想更浓一些。
先秦最著名的侠客歌谣要数《战国策·燕策三》中的《荆轲歌》(一作《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竹,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云云。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此歌乃侠士自抒怀抱,悲壮豪迈,尽管只有短短两句,但歌者怀必死之决心、义无返顾之坚定表现得淋漓尽致。词中以“兮”字带来节奏的变化,读来显得气韵悠长,与歌者感情相契合。在形式上它和《无衣》及上逸诗整饬的四字句不同,带有楚辞的风味。
三、对后世咏侠诗歌的影响
先秦咏侠诗歌数量很少,但它和两汉咏侠歌谣一起,形成了后世咏侠诗歌的滥觞,后世咏侠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多样。
从内容上,先秦咏侠诗歌涉及到游侠生活或侠义精神的并不丰富。《无衣》及《左传》逸诗表现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思想,《无衣》更具有同仇敌忾的豪情,实为后世咏侠诗将游侠与边塞相结合的先声,《荆轲歌》是义士报恩报怨、慷慨赴死的绝唱,后世文人咏侠诗也多涉及这些方面。
先秦咏侠诗歌数量虽然很少,但在内容上多有发轫之功,实为后世咏侠诗之先导。
在诗歌体式方面,先秦咏侠诗歌还停留在民谣阶段,没有文人创作,因此语言淳朴,体制短小。
先秦歌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常具有直指人心的感染力,这也是先秦咏侠歌谣的特征。直到两汉,乐府、文人诗歌出现,咏侠诗的内容和形式才开始丰富起来。不管是游侠的生活,还是其他侠行、侠节、侠情、侠义等逐渐成为歌咏的对象。到魏晋,咏侠母题得到确立,从此咏侠诗就是较为抢眼的诗歌品类之一,为诗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