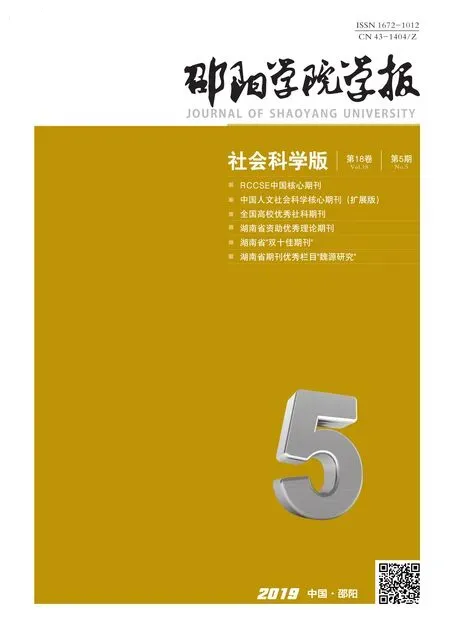丁玲抗战时期作品的身体言说
2019-02-21陈红玲龚丽群
陈红玲, 龚丽群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在当代文化中,身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这个视角下,身体不单单是一个具有个体属性的生理名词,还是一个作为社会载体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身体所体现的文化内蕴是不一样的。通过对身体内涵的探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学叙事是身体言说的主要形式之一,文学家们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将特定时期的身体以及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的各种欲望显现出来。对丁玲小说“身体书写”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周佳《革命感知与创伤书写——丁玲左翼短篇小说里的身体和空间》是从空间维度的身体经验与革命感知角度解读丁玲小说;陈宁《从性别视角看丁玲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则认为丁玲创作对女性主体性的生命观照在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交锋中呈现出一条曲折的演变轨迹;郭冰茹《借助身体、爱欲与革命的书写来认同自我——丁玲早期小说新论》,着重以丁玲早期(1927—1930年)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文本中身体、爱欲、革命与自我认同的关系,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展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本文与以上学术论文一样,意欲从“身体”视角解读丁玲的文学创作,不过切入点不同。本文集中考察丁玲在延安抗战时期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一颗没出膛的子弹》《压碎的心》《入伍》等作品,阐述身体言说意在突显在特定语境下身体的国家性、民族性和工具性,“心”与“国”链接的新形态,分析丁玲抗战时期作品中“抗战”国家叙述与身体言说的冲突。
一、对身体意蕴的不同阐释
关于身体的研究最先是在西方史学界兴起,后来才引入中国。之前身体并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但在后现代主义及新社会文化史的推动下,对身体的研究不断扩大。当代文化研究把身体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在这个视角下,身体不只是物质实体、生物数据或是生理学事实,而是一个作为社会符号的存在。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的身体,往往被打上了伦理、性别、政治的种种烙印,体现着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内涵。身体是抗日战争小说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直接参与了知识分子对个体与民族革命之间关系的历史想象,丁玲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对身体进行了多重阐释。
(一)伦理身体
抗战时期,在封闭落后的村子里,人民深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其落后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从父辈对子女身体的绝对支配权便可以看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通过对贞贞命运的叙述,展现了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与操纵。
贞贞早期与夏大宝暗生情愫,但遭到贞贞父母的强烈反对,只因为夏大宝贫穷的家世。贞贞父母不顾贞贞自己的意念执意要她给一个家道殷实的米铺小老板做填房。从这点来看,贞贞的父母是要贞贞放弃对自己身体支配的权利,让她无条件遵循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可见在当时,伦理对身体的控制是多么强势。但贞贞不满这种伦理对身体的处分,她坚决反抗,宁愿去教堂找神父当修女,也不遵从父母对她身体的判决。但因为这样的一个偶然,贞贞遭遇了日本人的玷污,被迫成了一名日本的随军“慰安妇”。这对于贞贞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美好的青春年华里,竟遭遇了如此悲惨的劫难,其导火索便是父权的控制。如果贞贞的父母不逼迫她,贞贞也不会离家出走,更不会有后面的悲剧发生。贞贞经历的这一切正展现了传统伦理的残酷性。后来当身患重病的贞贞回家治病时,受尽了人们的白眼,连她的家人也看不起她,他们看上去爱她,但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的脸面。此刻,贞贞的父母迫切希望她能嫁出去,不再嫌弃夏大宝的贫穷,只要他能娶贞贞。此时,他们对夏大宝什么要求都不做,反而还感激他。贞贞父母对夏大宝由一开始的轻视、嫌弃到后来的期待、满足,可窥见他们的自私。在传统伦理的影响下,他们丝毫不在乎贞贞的幸福,不在乎贞贞内心真正的需求,他们至始至终在乎的都只是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利益。贞贞父母对待夏大宝态度的转变更加凸显出传统伦理的虚伪性。
在男权社会里,贞贞不能选择自己的爱情,在为国献身后依然遭受到人们的白眼。贞贞的遭遇从侧面体现出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支配所产生的悲剧。这种传统伦理要求子辈必须放弃自己的意志,放弃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力,绝对服从父辈的意志。但贞贞却向这种所谓的遵循父辈意志的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即使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勇敢的抗争也体现了女性独立的一种进步。
(二)性别身体
性别作为一种生理属性的同时,也具有文化的属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性别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之中。但在抗战时期,无论是男性身体还是女性身体,都彰显了其存在的特殊价值意义。
丁玲将中国女性的处境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从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到中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再到晚期的《杜晚香》无不反映了女性身体的命运。
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还是《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都是抗战时期从传统伦理社会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她们以自己真实存在的身体作为抗争的工具,奋力进入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中,憧憬在那里能获得新生。但在这奋斗的过程中,她们的身体却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她们身体的多重身份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丁玲对抗战时期所有女性命运的思考。
在传统礼教中,女性的贞洁高于一切,一旦失去了贞洁,就会成为别人白眼唾弃的对象。很多女性失贞之后,在各种舆论压力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贞贞在离家过程中被日军奸污,陈老太婆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落入日军魔掌。她们作为女性,承受了男性体会不到的痛苦,她们是战争最严重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同情,甚至还受到其他女性的冷眼相待,这是女性的悲哀。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贞贞她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作为一名女性的价值,她们用自己的身体为战争做贡献。贞贞用自己患病的身体获取重要的情报,陈老太婆用自己年老虚弱的身体呼吁、激励更多的民众积极抗日。贞贞的选择虽然没有被霞村的人理解和认可,但她为自己寻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她可以逃离原来那些自私冷漠无知的人们,开始新的生活。陈老太婆虽然一开始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因她至始至终没有放弃,最后新的信念诞生,她成功了!
贞贞和陈老太婆是抗战时期涌现出来的新女性,她们虽然承受了战争给女性带来的种种痛苦,但却用自己的身体向人们、向社会证明了女性的价值。
(三)政治身体
在抗战时期,无论是伦理身体还是性别身体里,都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政治对身体的操控力量。无论是贞贞还是陈老太婆,她们都在政治力量的引导下,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政治对女性的身体有着绝对的控制。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他们要求贞贞传送情报,贞贞不得不遵从,她忍受着病体的剧痛,冒着生命危险也照做不二。当她身患重病时,他们给她治病,而治病的目的也是能让她继续工作,他们此刻不认为失贞后的贞贞就是一个不再贞洁的女性,反而利用这一点,让贞贞的身体为政治服务。在他们看来,贞贞能够继续发挥身体的政治价值,那么,她就是干净的。虽然贞贞为政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凭借自己身体的政治属性找到一条崭新的出路。贞贞被日军无休止的蹂躏强暴,她的身心必定是痛苦不堪的,她自己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想要结束这痛苦的一切。但是革命政治的力量激起了她生的欲望,让她在痛苦的煎熬中寻到了一丝精神上的慰藉。获取的重要情报让她感受到自己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被日军玷污的自己竟有着被认可的价值。最终她在政治力量的牵引下,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去了延安,去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是革命政治力量最集中的地带,但愿她在那里可以真正获得新生。
《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因为政治力量的牵引,凭着最后一口气回到村子里发挥自己身体的政治作用。陈老太婆与贞贞不同,她不像贞贞那样利用自己的身体获取情报展现身体的政治性,她是在经历日军的残暴之后,偷偷逃回来为革命政治贡献力量。在政治力量的牵引下,她没有一蹶不振,没有自我放弃,而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感染身边的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警醒他们,去呼吁他们站起来反抗。她每向人们讲述一次自己的经历,就要再痛苦地揭一次伤疤,没有人愿意将自己曾经遭受的耻辱伤痛再一次次地揭露给别人看,但是她却做了,即使别人还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她也从未放弃,从未停止,可见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一开始她的所作所为不被她的儿子儿媳妇们理解,也只会带给别人恐慌和害怕,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听她的诉说,认可她的观点,支持她的选择,最终一起战斗,陈老太婆终究在获取了同情的同时也唤醒了民众。这样的结局,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轻松,她由此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是政治的力量让她所做的一切没有被辜负,变得有价值有意义。
政治对男性身体的操控更是不言而喻。男性是抗战的主力军,在抗战时期,他们似乎为政治而生。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小红军,才十来岁,但他在面对死亡时流露出来的不是年少理应出现的畏惧,而是一种为国、为政治牺牲的坦然,可见政治的影响力之巨大与深入人心。在《夜》中,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农民又是政治指导员的何华明,为了政治工作却让自己喜爱的田地荒芜,让自己的老妻越来越极端,离自己越来越远。碍于自己是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他放下了自己内心难以控制的生理需求,并且在待产的老牛产仔需要照顾时离开,回到繁忙压抑的工作中去。政治的力量让他别无选择,但他也在等待着在政治力量指引下黎明的出现。
二、人物身体的多重属性
身体具有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身体是个人的,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通俗地说,身体的个人属性便是“小我”,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人。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又是社会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我们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舍弃“小我”去服从集体、民族或国家的意志,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身体的社会属性便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大我”。
说起战争,我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枪械炮弹,殊不知使用这些武器的身体才是战争的首要工具。当国家战争爆发的时候,身体的个人属性会被削弱,被忽视,被隐蔽,而其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则会被放大。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家军事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不管是老人青年还是孩童,其身体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国在家在,国难人悲。丁玲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主人公贞贞的身体成了各种势力交织使用的工具。贞贞是在落后而又封闭的霞村里担任特殊工作的女性,其命运受到了丁玲的关注。贞贞是其身体的拥有者,但其决定权和使用权却不由自己把握。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里,小红军将其身体的决定权交付于连长,体现的是对抗战的绝对奉献。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居然能保持绝对的理智,心系民族,为了国家的统一无谓生死。在《夜》中,具有农民身份和政治指导员双重身份的何华明在面对农活与政治工作的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遇,他克制住自己身体的私欲在无穷的黑暗中等待着未知的黎明。
(一)身体的个人属性
一些原本落后封闭的地区,在抗战时期成为解放区。这里的民众一方面深受传统礼教伦理道德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渴望着身体的自由,精神的独立。由此,人们对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发起抗争,于是身体担起自我精神救赎的重担。
1.贞贞欲掌控自己身体却不能如愿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于1940年创作的,是一部极具时代感和现实感的作品。作品以“我”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我”去霞村治病,刚好结识了一位回来治病的女子贞贞,“我”在了解了贞贞的故事后对她的遭遇给予了充分同情,对贞贞进步思想与愿为国献身的精神满含钦佩。
作品充斥着人们对贞贞的各种议论:“……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他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1]219村子里的人都在言语上辱骂着贞贞,骂她连破鞋都不如,说她不害臊……此时的“我”对贞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充满了好奇。后来才知道早些时候贞贞与家境贫穷的一个村底下磨房里的小伙计夏大宝有情意,但却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并给她另讲了一门亲事,强迫她做西柳村一家年纪快三十了的米铺小老板的填房。她不愿去做别人的填房,不愿遵从父母的意志,即便不能如自己所愿,也绝不把自己的身体就这样交付出去。很明显这时贞贞父母想要占有贞贞的身体所属权,换做别人,在这个必须遵从父母之命的时代,或许便会选择默默忍受。但贞贞没有,她去教堂找神父,要求出家做修女,她在极力争取自己身体的所属权,身体在此时成了她自我精神救赎的唯一工具。然而她并没有如愿,这一次的抗争让她跳入了另一个火坑。正是这时,日本鬼子打到了霞村,在教堂里掳走了贞贞,使其被迫成了日军慰安妇。她在遭受着日本人残忍蹂躏的同时也忍受着全村人的白眼唾弃,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着我们所想象不到的痛苦和折磨,她的身体成了日本军人发泄情欲的工具,她不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1]224-225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境遇下,贞贞依旧没有放弃,她利用自己的身体传递情报,努力寻找着新的道路。
2.陈老太婆失身后的觉悟
小说《新的信念》讲述的也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在一次日军扫荡过程中,陈新汉的母亲陈老太婆与其子走失,在自己遭遇被日军奸污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孙子被日军残忍杀害,孙女银姑在日军的残忍蹂躏中咬舌死去。陈老太婆在经历这一切后,对日军深感痛恨并燃起理智抗争的信念。她失身后,凭借自己的意志拖着被日军残害到奄奄一息的身体,撑着最后一口气艰难地逃回了家。原文中是这样描述陈老太婆回村的,“渐渐这生物移近了村子,认得出是个人形的东西,然而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它便又倒在路旁了。直到要起来驱逐一只围绕着它的狗。它无力地摆动着它的手,挣着佝偻的腰,倾斜的,惊恐的,往一个熟悉的家跑去……然而它却瓦解了似的摊在地上,看见了两只黄的,含着欲望的眼睛在它上面,它没有力量推开它,也没有力量让一边去,只呻吟了一声,便垂下那褶皱了的枯了的眼皮”[1]169-170。她回去之后像变了个人,开始向家里人甚至满村子去演讲日本鬼子施暴的经过,讲她亲眼所见的,亲身经历过的场面。当她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她是痛苦的,“开始,当她看见她的儿子时,她便停住了。她怕儿子们探索的眼光,而且她觉得羞耻,痛苦使她不能说下去”[1]172。但她没有把这种痛苦隐藏于心,她要把她的痛苦告诉全村的人,在痛斥日本人的惨无人性、残忍至极的同时也激起全村人的愤怒。“这不爱饶舌的老太婆,在她说话中感到一丝安慰,在这里她得着同情,同感,觉得她的仇恨也在别人身上生长,因此她忘了畏葸。在起首的时候,还有些唠唠叨叨,跟着便流泪了,她审查那些人的脸色,懂得什么辞句更能激动人心”[1]172-173。
陈老太婆通过自己身体的述说体现的是对日军的积极抗争,是对自我的精神价值的努力追寻。虽然她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的言说会不会有效果,甚至一开始还有些羞愧,但是到后来,她在言说中得到了安慰,逐渐找回了自我,于是便开始研究更有力的说辞。在她三儿子陈立汉回来之后,又将他儿子讲述的抗战的故事作为言说的材料。最后,有千百个声音痛苦地响应她:“我们要活,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1]179她成功了!在她的言说下,人民终于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之前胆小懦弱的他们已逐渐转化成了英勇抗战的英雄!随着村民的抗战意识觉醒,胜利的曙光终将到来!“陈老太婆的成功与社会同仇敌忾进行抗战的大环境有关。陈老太婆加入了社会主流话语言说系统,而且一度引领潮流”[2]。
3.老妻因身体的衰老而被嫌弃
《夜》是丁玲于1941年创作的,这篇小说是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它“所展示的多种内心冲突,也多与身体欲望对政治工作的搅扰有关”[3]。它集中讲述了一个刚被提升为指导员的农民何华明在一夜间从个人情爱的欲动到坚定革命立场的故事。这篇小说提到了三名女性,分别是清子、侯桂英和他的老妻,这三名女性中,唯有他的老妻没有名字。他的老妻没有清子外在的身体美,没有侯桂英的精神层面的慰藉,有的只是苍老的被他厌弃的容颜、无休止的埋怨与争吵。
《夜》中的老妻作为一名女性,她的身体的个人属性的展现方式不似贞贞也不似陈老太婆,老妻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体找到一条自己想要的道路,她从嫁给何华明开始,就意味着自己注定不幸福。何华明作为一名政治指导员,有忙不完的公事,根本无暇顾及家中的农事与老妻,就连家里最重要的母牛产子他也没有时间等待,这便让家中老妻的身体承受了农事的重担。正因为这样,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老妻怪他不顾家,埋怨他责怪他,他怪老妻思想落后,看不起她,嫌弃她。然而即便如此,老妻却始终没有想过要与他分开,离开他,在老妻心里,她的身体归属权仅仅是她丈夫一个人的,即便自己再苦再累,无论多恨自己的丈夫,都因为丈夫的一句“睡吧,牛还没有养仔呢,怕要到明天”[1]260而归于平静。或许这就是她想要的,想要自己的丈夫多放点心思在农事上,多给予自己一点安慰,一丝关心,或许这就够了。她为了自己的这点念想也在一直努力,自己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这繁重的一切,用她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
(二)身体的国家属性
战争要使用的炮弹武器有很多,但终归是人的战争,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抗战时期的身体具有革命的性质,身体的归属权不再是个人,而是集体和社会、民族和国家。此刻,国家的安危与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家国同体,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立使得身体凸显国家属性。
1.小红军勇于为国牺牲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受了伤的小红军因掉了队,被老大娘收留了。此时他身虽不与队伍在一起,但不忘自己是一名红军,为了革命努力着。他将红军的英勇故事,自己的打仗经验,以及之前在小组会上和演讲里面学得的一些话语和那些能够倒背如流的术语讲述给这里的村民听,“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着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我们红军当前的任务,就是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快要灭亡中国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参加红军去打日本……”[1]126他的这一番言说,使得红军的威信增强,在人民群众中打下了坚实的革命基础,增强了全民众统一抗战的信心及在红军的带领下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对重归队伍的渴望。他想为国效力,想去前线打日本鬼子,无畏牺牲,奋勇向前。然而一天夜里,一连的东北军到屋里乱翻一气,发现了那顶军帽,就来抓小红军,要拿枪杀小红军。连长问他怕死不怕,他的回答是“怕死不当红军!”一个十三岁的小红军竟是如此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当连长冷冷地说出要给他一颗枪弹时,他却异常镇定地说:“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连长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他大喊道:“……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他是红军,我们叫他赤匪的。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1]131-132小红军赤手空拳,凭着一颗勇敢和赤诚的爱国之心,征服了一个连的东北兵,“这其实表达了民族主义话语的胜利:民族救亡的期待超越了阶级的矛盾和隔阂”[4]。
为何一个13岁的孩子如此深明大义,因为他从小就在红军的领地里长大,他把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爱刻进了骨子里,自己的血肉之躯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红军,他无畏牺牲,正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无数这样的大小红军,抗日战争才得以胜利,国家民族才会统一。
2.贞贞愿为国献身
抗战时期,霞村的贞贞为了收集情报,忍受着日本人的凌辱和村里人的白眼唾弃,牺牲了小我的幸福,成全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体现了身体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国家性。
在抗战时期,要为国效力并不仅仅只有去扛枪作战,贞贞利用自己的身体获取并传送情报,又何尝不是在为革命贡献?“……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别的不要紧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这不行呐,唉,又怕被鬼子认出来,又怕误了时间,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才又拖着起了身。”[1]225贞贞为了国家,为了挽救战火中的民族,忍着身体的剧痛给游击队传送情报。遭受身体和精神重创的贞贞丝毫没有拒绝这项艰巨的任务,在传送情报的过程中也没有因为自身的困难而选择放弃,她不顾自己的安危,一心为国效力,即使得不到其他人的尊重和理解,也从未后悔。
抗战时期的贞贞,放弃了小我的幸福,自愿为国家为民族献身,她的身体已不是她自己一个人的,而是国家的、民族的。
3.陈老太婆为抗战做宣传
抗战时期的陈老太婆失身后回村积极为抗战做宣传,她化悲痛为力量,呼吁更多的人站起来共同抗战,齐心协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陈老太婆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女性,在被日军玷污之后,本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一生,或许这样她会少承受些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在看到自己的孙女和孙子惨死在日本人刀下的时候,她也可以选择去和日本人决一死战,为自己的孙女孙子报仇,即使可能仅仅是无畏的牺牲,也比忍受亲眼看到却无法抗争的悲痛要强。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克服自身心理和精神上的煎熬和苦痛,把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的悲痛化为抗战的力量,与其让自己更早地结束痛苦、结束生命,倒不如利用这些为国效力。她要把她看到的这一切,经历的这一切告诉自己的亲人,告诉自己村子里的人,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残酷,让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的局面,让大家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只为了给死去的亲人邻里报仇,为了让自己留一条活路,为了救民族于水火,为了保住我们的国家。最后,经过陈老太婆的坚持与努力,她做到了。人们统一抗战的意识已经觉醒,光明在她坚定的信念中显露出来了!
三、“身”与“心”的矛盾
身体是我们处于物质世界的载体,而灵魂则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物质世界存在的客体与精神世界的主体既有趋于一致的时候,也有起冲突的时候。上文中我们提到在抗战的语境下,身体作为各种工具被使用,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属性,有着不同的阐释。那当身体的属性不一致的时候,思想灵魂也将与它呈现不同的状态。
抗战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丁玲的独立的女性意识被唤醒的同时,也激发了她对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历程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反映在文学中。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等这些作品中,无不体现着在抗战背景下的人民承受着肉体与精神所带来的痛楚,创作紧密配合身体国家化、工具化的时代潮流。
(一)“身”与“心”的统一
当身体具有个人属性之时,其与思想灵魂便是一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为了逃避做一个三十多岁的米铺小老板的填房,选择抗争,这时她的身体与她的思想灵魂是一致的,她的身体被自己的灵魂操控着,具有个人的属性。她这时的抗争单从结果来看也是成功的,她没有做填房。而后,贞贞选择做情报工作之时,想必身体与灵魂也是一致的。在国家动荡、民族危亡之时,贞贞愿意牺牲小我,她的思想灵魂指引着她的身体去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当她的身体患病之后,她也强忍着痛楚,保持思想灵魂的一致。最后贞贞决定去延安,也高度体现了身体与思想灵魂的一致。
《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也与贞贞相似,只是为革命、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具体的事不一样。陈老太婆经历了痛彻心扉的一切后,回村宣讲,为的就是能够团结民众一起抗战。她是自发地演讲,自发地努力,没有人直接强迫,一切都是她自发的决定。这也正说明此刻她的身体与思想灵魂也是一致的。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小红军,虽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但愿意为了打日本而直面死亡。他在政治教育的熏陶下长大,自觉地挑起抗战的重担,并言行一致,无畏生死。即便最后东北军连长会开枪打死他或者用刀还是其他方式杀了他,想必小红军也绝不会畏惧,也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此刻,他的身体和他的思想灵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二)“身”与“心”的冲突
当身体处于被动的情态,自身无法掌控身体的决定权之时,身体将会与思想灵魂产生强烈的冲突,个人将遭受灵与肉分离所带来的痛苦。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这三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当时的女性在遭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损害时,有可能得不到民众的丝毫同情与怜悯,有的只是无尽的谩骂与讥笑侮辱。丁玲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站在女性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凸显了觉醒的女性意识,言说着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深沉矛盾。
《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是一个勇于与传统封建礼教抗争的女性,但也是传统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是战争的牺牲品。在面对日本鬼子的强暴蹂躏之时,她的身体承受着致命的伤害,心灵烙下了无法治愈的疤痕。但坚强的贞贞让自己的身体成了传送情报的工具。贞贞患病回村所遭受的那一切是其内心不愿面对与接受的。原文中贞贞是这样表述的:“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倒也是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再说家里几个人吧,还不都一样,谁都偷偷的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没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人在那种地方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是因为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1]224这时贞贞的身体与思想灵魂是冲突的,于是思想灵魂便让步于身体。贞贞对自己的遭遇“实在伤心”,她变得硬心肠“也是因为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虽然表面上贞贞不在意村里人对她的评价和态度,但其实她内心也是充满了恐惧的。“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1]232贞贞也以为自己病了,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这时贞贞的潜意识里还是存有封建传统礼教的影子,并未完完全全的独立出来。而她自己也说人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贞贞的身体与其思想灵魂还是存有很大的冲突的。
《夜》的主人公何华明在革命话语权的控制之下,使得个人的欲望让步于革命的理性。何华明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农民,二是政治指导员,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指导员上,由于政治工作的繁忙,他已经三四天都没有回家了,因为他家唯一的牛就要产仔才被准许回家。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的土地没有时间耕作,不得不荒芜,他想回家耕作田地,却又有着实在离不开的工作,这使得他的内心有着说不出的苦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支配权,作为一个农民,他是多么渴望能够操持好家中的田地。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土地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他却没有这个权利,他的身体归属于政治,一切以指导员的工作为中心,哪怕家中田地荒芜。 “正是在革命后的日常政治实践中,何华明身上逐渐暴露出了个人与革命诉求之间的不同步之处”[3]。
何华明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身材丰满的清子,“长而黑的发辫上绑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条纹花布袖子的肩膀,高高地举着,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1]255这让他有了一个奇异的感觉。当他回到家中,面对脸上爬满皱纹,前脑开始露顶的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婆时,他是满脸的嫌恶。在他去牛栏边看牛生仔了没有时,二十三岁的侯桂英出现了,侯桂英的出现使得何华明心跳加速,甚至萌生出强烈的生理欲望。三个女性使得何华明陷入深深的矛盾纠结之中,尤其是自己的妻子与侯桂英。面对人老珠黄,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甚至还埋怨他的妻子,他看不起她,厌倦她,甚至想与她离婚。当他遇到刚好可以填补这一切的侯桂英的时候,他似乎难以抑制本能的生理欲望,“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了,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以什么都不怕的”[1]260。这都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真真切切的声音,然而,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作为指导员的他,碍于政治身份,不能这样做。他们是干部,是要受批评的。
“充分暴露、展示内心的困惑与矛盾,以期实现对革命更透彻的理解,成为丁玲在延安早期书写中探索个人与革命相互关系的方式之一”[3]。何华明压制住了自身对爱情对生活的欲望,最终选择了维护自己革命者的纯洁形象。在何华明身上深刻地体现了革命的理性与个人的欲望的冲突,最后的结果是革命理性的胜利。
《在医院中》中的陆萍在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便在一家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到后来进入抗大学习,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她不想像之前一样浪费她的时间,付出没有报酬的感情。可是毕业后,为了满足党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她却又被分进了医院做“产婆”。虽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但是在党的引领下,她还是带着一颗热情的心来到这所医院工作。可是,这里的情况远没有期待中那么美好,她与这里的人以及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这是一个肮脏恶劣的、易使人灰心泄气丧失意志的环境,这里人们冷漠、自私自利,医院设备落后,管理松散不科学,工作人员懒惰敷衍……陆萍对这样的环境感到失望,但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堕落,她想改变,她想努力去做好,但到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她唯一能做的、唯一能摆脱的方式是离开。
陆萍的革命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仅有着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而且还接受了政治的学习,有着崇高的道德修养,但她所在的工作环境却是肮脏、保守、落后的。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陆萍对这所医院充满了失望。这所医院可以说是当时延安的缩影。陆萍与医院环境的冲突也代表着先进知识分子与当时保守落后的社会形态的矛盾,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体与思想灵魂也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这也“凸显了身体国家化这一现代化进程对身体存在价值的规训,也说明青年人将革命视为确立自我,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是革命年代个人成长史上的必然”[5]。
丁玲抗战时期文学作品通过性别书写来追寻主体身份,同时赋予了人物身体一定的社会政治内涵,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展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解读权力怎样以国家与民族的名义利用身体这一工具达到政治目的,从而导致国家叙事与身体言说的冲突。
四、结语
我们从哲学层面的唯物史观上看,人具有三种属性:自然属性、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以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身体属性分为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身体又有着不同的阐释。社会在变化,每个时期的事物都不一样,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总不是顺利的,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而此刻人们的身体则会是其最直观的体现。在抗战时期,个人的身体是各种势力的操控工具,身体的个体属性被削弱,社会属性增强,身体必须服从民族国家的意志。个体的政治身体凸显,个体在身体的磨难中,以亲身经历的方式,积极投身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去,但在此过程中,个人的身体也与其思想灵魂有着激烈的冲突。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中,个人的命运与出路通过身体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