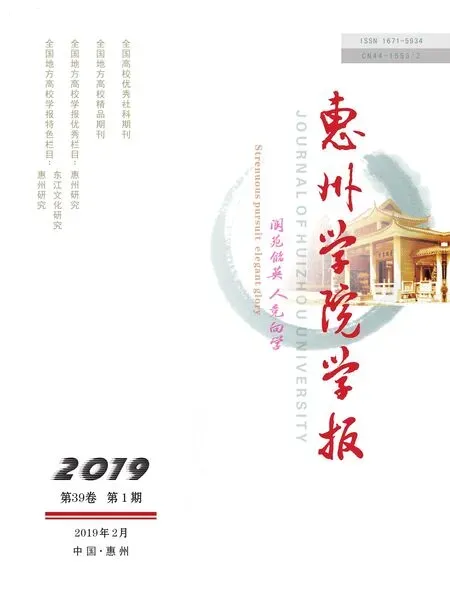林语堂中期汉英翻译的主体间性思考1
——从动机谈起
2019-02-21盛卓立
盛卓立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自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以来,“戴着脚镣跳舞”的译者似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禁锢了译者的创造性,以“忠实”和“等值”作为评判翻译行为的唯一标准,把译者视为“传话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横空出世,操控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译论纷纷竖起解放译者的大旗,译者摇身变成了对翻译拥有无上权力的操纵者,但这种主体性的过度张扬是对前两种范式下译者主体性遮蔽的矫枉过正[1]。翻译研究的走向无疑一直深受哲学思潮的影响,过度强调主体性加深了“唯我主义”产生的可能,于是,人本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来消解危机。受到哲学思潮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也开始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
一、翻译的主体间性
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对“主体间性”的发展各有自己的贡献,尤其是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强调“视界融合”,即蕴涵于文本中作者“初始的视界”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理解者“现今的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了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进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以及新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2]217。然而,哈贝马斯对此却持有异议,主要是批判伽氏对于“前结构”或者说“前理解”的过于倚重。“理解的前判断结构就是所谓事实上已确定的意见一致[3]192”,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合理的交往往往被抑止,人们的社会意识通常是在文化的专制下产生的,这种意见一致难道还能成为有效的、真理的存在吗?如果读者带有这样的“前结构”去理解原作,必然会将自身的偏见融入作者的初始视界中,难免曲解作者的精神、思想和意图。因此,哈贝马斯更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合理的、具有规范性的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一种以语言为符号媒介,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沟通和交流,由此看来,哈贝马斯对于“主体间”这一概念的把握是要高于伽达默尔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早期翻译研究对译者地位的忽视,抑或文化学派对译者的过度追捧,说到底都还是对传统二元论的固守,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相同的狭隘性。而“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恶性循环,从此翻译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认识行为,而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民主对话。
谈到主体间性,则不得不涉及“多主体”的问题。导致二元论缺陷的元凶就是对“主体”和“作为主体的人”这两个概念的误解和混淆。然而在真实的交往行为中,“人”固然具有明显的主动性,但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无时无刻不受到周遭世界的反向影响,因而主体与传统“客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征服。“主体间性”思想将认识论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将对象客体提升为同样自由能动的主体[4]”。而对于翻译中“多主体”的理解,学者们也各持己见,有的认为翻译活动应当包含三个主体(译者、作者和读者);有的认为除以上三者外,文本与语言也可以成为主体;还有的认为翻译主体是译者、作者、读者以及他们所属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应当是三个有生命主体(译者、读者、作者)和五个无生命主体(原文化、译者文化、译文读者文化、原文、译文)的总和①。很明显,第一种观点未能传递出对“主体间性”深刻内涵的理解,而最后一种观点虽然非常全面却比较复杂,在真实的翻译研究中,容易引发误操作。实际上原文化、译者文化和译文读者文化往往并非以相对独立者的姿态存在,它们融于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视界中,可以说在讨论任何两组因素(如作者和译者)的相互作用时,文化因素都不可能被抛开。因此,作者、译者、读者、原文和译文这五个因素已足够扮演翻译的主体角色。
在强调各主体的平等、民主的对话和交流时,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是否存在绝对的平等?从理想的状态而言,在翻译实践中各主体应当是彼此制约、互相影响,谁也不该凌驾于谁之上。然而现实很清楚地说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完全、绝对同等或对等也不可能[4]”。马克思辩证唯物论认为,矛盾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而另一方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当翻译各主体之间产生某种交互关系时,其实也就是产生了一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两者。如再深入思考一下,则会发现有一个因素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甚至在某些因素的对话中(如作者与读者)发挥着桥梁(或中介)作用,这就是译者,可见译者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翻译全过程的核心。这与“主体间性”的精神并不相悖,多主体从未意味着主体间的绝对平等,此种误解只是源于对主体间性的机械理解。
二、林语堂中期汉英翻译的动机分析
承认译者在多主体中的绝对核心地位,是主体间性理论存在的根本要求。译者是“人”或由“人”构成的某个组织,而人一旦涉足某项活动就必然有其缘由,这就是翻译动机的最基本解释。要研究一个翻译实践行为,就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抓一个主要方面,提纲挈领,一网打入。毫无疑问,没有比译者更合适地选择了,而从译者入手则不可不谈动机问题。
动机心理学认为动机问题涉及内在起因、外在诱因和自我调节三大因素,动机就是“在自我调节的作用下,个体使自身的内在要求与行为的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素[5]241”。当一个人产生了动机,便会尽可能地创设条件去实施一个行为,当然动机并不能保证该行为必然能实施或完成,但个体受动机驱使,只要有适合的条件存在,就会努力实现该行为,达到预期目标。在翻译活动中,假如译者动机不足,那么整个翻译行为就无法顺利实施,甚至会土崩瓦解,而本该出现的各个翻译因素(主体)自然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林语堂是中国近代翻译家,中期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半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是其翻译成就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②。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给尚迷茫无知的西方读者下了一剂灵药,是中国文化“西进运动”的先驱。然而,纵观其汉英翻译的整个过程,不免令人疑窦丛生。当中国主流翻译界集体致力于翻译外国进步文学时,林语堂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在浩瀚的中华文学海洋中,他为何独爱老庄哲学和性灵文学?他的翻译手段为何如此灵活多变不可捉摸?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牵扯到各翻译主体间或隐或现的关系。显然,想要解开这些疑惑,必须先解决动机问题。
林语堂生于福建一基督教牧师家庭,从小耳濡目染西方文化,长大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英语语言功底扎实,不过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并未因特殊的成长环境而受到损害。林语堂的童年是在福建漳州的乡间度过的,那里民风淳朴、山景秀美,一派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风情,受此熏陶,林语堂的性情闲淡洒脱。成年后,他因深感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粗陋而博览群书,“详细考察了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特别崇拜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将他们的思想称之为道山的高峰[6]”,而与古人思想的碰撞使林语堂不免愈发珍视自己所推崇的生活理念。成长中所受到的自然熏陶和因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后爆发的热爱正是其后来从事汉英翻译的内在起因。可是当林语堂正摩拳擦掌准备投身“精神欧化”运动之际,一场政治屠杀席卷了北京知识界,邵飘萍等进步文化人被奉系军阀杀害,林语堂举家逃出北京,一番流离辗转磨灭了他本身就不够浓烈的进步意识,骨子里的闲逸气质按捺不住,于是开始闭口不谈政治,只谈“幽默”和“生活的艺术”。他的内在起因受到了这样的外在诱因的刺激后,产生了不同于当时很多翻译家的行为动机。当然,内因与外因的自我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动机的最终成型也经历了相对漫长的一个时间段,动机往往在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减弱或增强,而对于林语堂来说,他的翻译动机显然是愈来愈炽热。林语堂的汉英双语能力扎实、对译语读者的审美心理有颇深的了解,自身又具备良好的翻译学术能力,这些都减少了翻译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他热爱中国传统哲学和性灵学说,具备强大的行为实施意志力;而最初的几部译作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受到了热烈的积极反响。这一过程反映了其自身对内在起因和外在诱因进行调节的行为,并通过这个过程巩固了他的汉英翻译动机:即将豁达、闲适的中国生活哲学译介到西方,从而躲避残酷的政治斗争并传播自己所热爱的中国性灵文化[7]。
三、林语堂中期汉英翻译的主体间性
上文所述,翻译主体包含了有生命和无生命共五个因素,根据马克思辩证法联系普遍性的原则,这五个因素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受篇幅所限无法一一阐明。实际上,当确定译者在翻译各主体中的核心地位后,从译者出发形成一种辐射性的主体间对话已经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因此,此处所说的主体间性主要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文本(原作和译作)三种。
(一)译者与作者的主体间性
译者与作者都属于有生命的“人”,他们的主体间交往是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的。“译者进入他人思想的主体,感受他者的思路,在心灵中与他人交流,译者在这种交流中开拓并提升自己的主体性[8]”。由此可见,译者虽是翻译全过程的核心,但他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他必须在与作者的相互碰撞中才有可能为翻译奠基。
林语堂在中期阶段的英译工作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文学各个方面,尤爱老庄哲学,中国古代文人(如苏东坡、陶渊明等)的诗歌与散文以及一些古典通俗小说。显然林语堂对于自身翻译内容的范畴有着明确的界定,而对此的理解必须回溯到前文对其翻译动机的分析。林氏自幼性情洒脱不羁,成年后生活优越,颇有一种古时士大夫阶层的心态,他对于政治斗争的精神准备与经验都是不充足的,无法进行彻底的抗争,于是退而求其次用幽默的口吻来吐吐闷气,“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9]16”,以至于到了自己开始做翻译时,其心态也未有变化,即要谈性灵便谈个透彻。于是“无为而治”的老庄、“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超脱凡尘的沈三白等等就成了他的精神知音。林氏在《浮生六记》译本的序言中不吝言辞地大加赞美,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全世界一读的书,因为“此书中的二人老实诚恳,于追求美好之中,虽生活清贫困顿……但却一心要抓住时刻的幸福[10]20-21”。林语堂是理解他们的,即使身处不同时空,也丝毫不影响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如果说,林语堂的本性牵引他爱上这些古人,那么后者也在不断地强化着、丰富着林氏的精神世界。
(二)译者与读者的主体间性
如果说译者和作者是一种精神挚友,那么译者与读者间的关系则具有更强的目的性。无论译者怎样推崇自己所选择的作品,其译作能否被接受并不由他所决定,所以译者必须预设读者的存在,了解和接受读者的需求、自身设想与读者所思之间的差距,并努力进行弥合以最终实现译本被读者群成功接受。
林语堂对于读者群的认知显然是非常清晰的,这不仅是由于自身对西方文化的常年浸润,也是由于赛珍珠及其牵头的约翰·戴公司的助力。当时的美国社会,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但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人们常常疲于应付对财富的追求而无暇享受生活,因此急需开启生活乐趣之门的钥匙,正是由于对这一点的深刻了解,林语堂才能大胆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作品进行译介。林语堂秉持“中庸的哲学,善于持中守正,事理通达,心气和平[11]”,在《孔子的智慧》一书的序言中,林语堂如是表达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观点:“西方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12]2”。又比如在林语堂的文学翻译名单中,涨潮、陶渊明、沈复、苏东坡等都赫然在列,这些文人性格豁达、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不仅合林氏自身的口味,也恰恰弥补了西方物质主义下人性中自然一面的缺失,自然大受欢迎。
虽然林氏的翻译动机与读者的所需是大致吻合的,但作者与读者的文化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距,作为两者中介的译者自身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角度来说都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既要迎合读者兴趣又无法完全背弃作者,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都带有一些矛盾性,不过恰恰是这种矛盾性证明了翻译各主体之间存在着交互性的作用。林氏对于作者和译者的复杂情感、对于解决这一难题而设置的种种方案在原、译两种文本中都有明确体现,因而可以说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甚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对话都必定经由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而展开。
(三)译者与原作、译作的主体间性
传统译论通常将译者看作主体,而将文本当成客体,所以产生了“主—客”(我—他)二元对立关系。如今人们认识到人不仅可以与人交流,还可以与“物”交流,世上并没有绝对的“主—客”之分。原作是作者的文化世界的反映而译作则不可避免地带上读者文化世界的某些表现,所以文本是带有意识的,“它的意识与译者主体意识并无差别[8]”,译者要理解作者必须首先进入原作的精神世界,而要满足读者则又必须在译作中表达自己对于读者的尊重。
林语堂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发觉自己身上中国文化的缺失,继而大量阅读中国古典著作,通过原作感受作者的精神世界,从而与身处不同时空的作者建立精神对话,这种行为正是主体间性的一种表现。林语堂似乎舍不得丢掉任何一个自己的精神挚友,他的翻译涉及面极广,既有哲学经典、也有诗词小品,甚至还有通俗小说,林语堂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文本范畴内翻译尽可能多的作品,因此,林语堂对原作的形式做了各种处理:用选集的形式收录更多的内容,如《孔子的智慧》和《古文小品译英》等;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大量翻译,如《生活的艺术》;全译和节译并用,如《浮生六记》属全译、《古文小品译英》中既有全译作品,也有节译作品。同时,林氏又保持着与读者的精神对话,尽量地降低读者进入原作文化世界的门槛,比如采用编译的形式,把自身对原作的理解通俗地加以阐述,用自己为作者与读者搭建交流的桥梁,如《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此外,他还运用了改译法,将一些难以传递的语言形式用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以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如他在《苏东坡传》中所说,“有些诗词我译成英文诗,有些牵扯太多掌故,译起来显得怪诞不诗意,不加长注又怕含义不清,只好改写成英文散文[13]23”。
除此以外,林语堂在翻译中还试图将作者与读者的文化视野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真实和平等的对话。但显然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他不能想出一个完美的办法,始终徘徊犹豫在作者与读者两极之间,因而在文化处理上就表现出了双面性。首先,他本着对作者及其文化世界的尊重,一直努力想将真实的中国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又考虑到需对读者进行文化补偿,便采用了音译、直译、增译等多种方法来进行不同的处理。
(1)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③
I have pulled out the hait’ang and chiching in front of my studio,and have just planted ten or twenty green banana trees there.
(2)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帐悬姻缘簿。(《浮生六记》)
It was a picture of the Old Man holding,in one hand,a red silk thread[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and,in the other,a walking-stick with the Book of Matrimony suspended form it.
例(1)中的海棠、紫荆是颇受中国古时文人垂青的植物,但其本身并不带有过多的文化意象,读者从上下文已然能够判断其大致的属性,因而林氏干脆使用音译法将其异国情调尽情传递。而例(2)中所述形象是中国传说中的月老,他掌管人间婚嫁事宜,用红线将一对男女的双足相连,从而定下姻缘。由于这一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人皆知,因此句中并没有将“红丝”一词的意义说明,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是超出了他们的文化理解范畴,所以林语堂用增译法将缺失信息补足。
其次,受动机影响,林语堂力图使西方读者群接受他所译介的中国古典作品,就不得不更多地迎合读者的欣赏品味,对原作文化世界的背离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文化信息置换和文化信息省译是常用的方法。
(3)夏七月,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不亦快哉》)
It is a hot day in July when the sun hangs still in the sky and there is not a whiff of wind or air,nor a trace of clouds;
(4)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东坡诗文选》)
I was able to collect funds and obtain several thousand bushels of rice for the purpose of feeding orphans.
例3 中的七月是中国农历中的月份,但西方读者并不了解这种中国独有的历法,解释起来也比较复杂,出于读者需要的考虑,此处仅以July 替代。而bushel是专用于称量农作物的计量单位,与汉语中的“石”的应用语境具有相似性,因而被直接予以替代。然而林语堂的这种处理方法虽有简便之效,但却不免误导读者,灌输错误的文化信息。如上例中的“石”作为容量单位,一石约为100升,而1个bushel为36.4升,两者相差之大令人瞠目!这显然背离了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尊互重。
(5)蝉为虫中之夷齐,蜂为虫中之管晏。(《幽梦影》)
The cicada is the retired gentleman among the insects,and the bee is an efficient administrator.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两人因互相谦让王位而双双出逃,后因商亡于周而归隐首阳山,只以采薇(野豌豆)为食,一老妇见状问其原因,两人如实相告,老妇却说:“普天下皆为王土,薇不也是周王的吗?”于是两人连薇也不采了,双双饿死在首阳山。管晏是管仲和晏婴的并称,都是春秋时的齐国名相。蝉以清风露水为生,不受尘世浊物的污染,所以它们与自身清白而坚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样品性高洁。而蜜蜂则是每日辛勤劳碌,采花酿蜜,日夜操劳,与治才良相管仲、晏婴一样。林语堂用retired gentleman 和efficient administrator 来释义,虽言语简明,实则省略了背后的文化蕴义,令人不免遗憾。
四、结语
主体间性打破了主体对客体的奴役樊笼,但各主体间是无法达到绝对的平等的,译者贯穿翻译活动始终,在其他各主体之间搭起桥梁实现对话。翻译动机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驱动力,因而译者的主体间交往也时时受到动机的引导,在处理与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时,会体现出偏向性。林语堂受其汉英翻译动机的影响,虽通过原作与作者进行了精神对话,成为精神挚友,但现实中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读者的所思所想,因而,在对文本的形式处理和对文化信息的传递方面出现了各种矛盾性,这固然是译者的无奈,但却也符合现实的主体间对话。
注释:
①以上观点可参阅论文:张轶哲,文军.主体间性在汉诗英译中的体现[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8(1):70-74;刘军平.再思翻译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从主客二分到视角共享[C]∥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整合与创新—第二届海峡“两岸三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32-148;段成.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的主体间性[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5-99;常晖,黄振定.翻译“主体间性”的辩证理解[J].外语学刊,2011(3):113-116.
②一般认为林语堂的文学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在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半页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页(海外);1966年至1976年(在台湾和香港)。
③本文例子均出自《林语堂中英对照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的《不亦快哉》《幽梦影》《东坡诗文选》以及沈复著林语堂译的《浮生六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