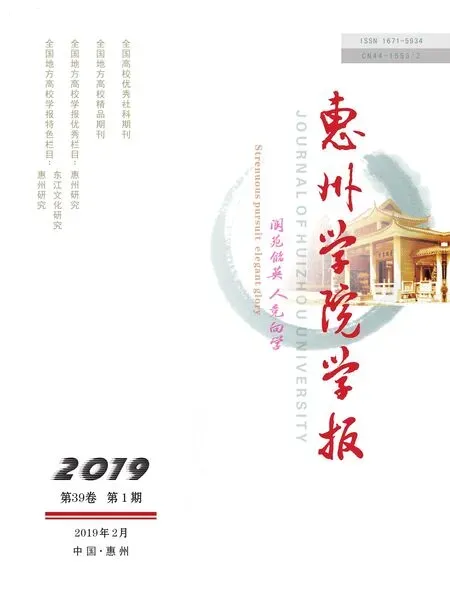修正与批判:明末清初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接受1
——以胡应麟、许学夷、王夫之为例
2019-02-21杨森旺
杨森旺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清人赵执信在总结明人诗学特点时认为“明人之动欲扫弃一切”[1]321,此即郭绍虞所说:“颇带一些‘法西斯’式作风的。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2]513”。因此,能在这种学术风气下较客观公允地认识某人(特别是文派执牛耳者)的文学思想尤为不易。
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重要成员,当他作为艺苑领袖执掌文坛之时,天下文士争趋其门,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对王世贞近乎阿谀谄媚式的虚称浮赞,但其中仍不乏一二能以较客观的学术眼光发明王氏学说而不耽于盲目附和之人;而与之文学观念相左的流派为了标新立异以自立文坛,往往矫枉过正,尤其在王世贞等人去世后,又弃复古文学家如敝屣,但在这种环境下仍可见一二辩证地吸收王世贞文学思想并用之做学术总结之人。清代建立以后,明代文学自然被贴上了“胜国”文学的标签,但在清初,批判任务的承担者却是明朝遗民。正如廖可斌教授所言:“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3]565”。要之,这一类批评家虽不失凌厉激越,但其批评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担当意识远非明代文坛之狺狺詈骂所能比,而他们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观照也会显得更加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
因此,于发明王氏学说之人中选取胡应麟与许学夷作为王世贞汉魏诗学接受的“修正者”,于明朝遗民批评家中选取王夫之作为王世贞汉魏诗学接受的“批判者”,并重点参照诸人诗学专著中有关汉魏诗学的部分,与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相较,找出他们对王氏诗学的继承、发展乃至超越之处。
一、胡应麟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接受
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世贞病笃之时于床榻之上将《弇州山人续稿》托付给胡应麟,嘱咐道:“子为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憾矣[4]305”。“临终托稿”这一行为说明王世贞对胡应麟的器重与期望之深,甚至很可能已将胡应麟视为复古衣钵的继承者。因此,胡应麟的诗学思想自然深受王世贞的影响,但胡氏卓越之处在于通过整合或补充王氏诗学观念以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即汪道昆所言:“抗论醇疵,时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即羽卿、廷礼,不耐不同;以异乎己者正之也,即元美、于鳞,不耐不异[5]1”。这种“抗论醇疵”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学著作《诗薮》中。
(一)明体判格,考源辨流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汉魏诗学的分析展现出以分体论述为经,以辨别格调为纬的撰写模式,但由于“卮言”的文本定性,所以在接受过程中仍给人一种随意性,其中所蕴含的思想需要经过思维加工才能展现出内部的逻辑性。但《诗薮》在王世贞辨体研究的基础上,强化了论述过程的学理性,使演绎更加缜密严谨,这首先便体现在对体制和格调的认识上。先看《诗薮》的编排方式。《诗薮》分为内、外、杂、续四编,内编以体制分论古、近体诗;外编以时代分论周汉、六朝、唐、宋、元各代诗;杂编专论三国、五代、南渡、中州诗之遗佚篇章;续编重点论述明代诗坛情况。在论古体诗中胡应麟将古体分为“杂言”“五言”“七言”,并将“三言”“四言”等纳入“杂言”中依次考察;在论“周汉”诗歌时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论述该时期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风貌与地位,用以勾勒出古体诗演变的内部规律。这种严格的编排方式说明胡应麟对诗歌体制有着自觉的认识。
再看《诗薮》的内容。胡应麟遵循的虽然依旧是“时代格调”的基本价值判断,但并不只是对“格以代降”的简单陈述,而是深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即“时代”与“格调”是相互作用,还是单纯的时代决定论。他说:“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然诗至于律,已属俳优,况小词艳曲乎!宋人不能越唐而汉,而以词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人不能越宋而唐,而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5]23”。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群体思维的变化,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变化在某些方面亦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这就是胡应麟所说的“势”;但另一方面,变化的产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新事物的发展到定型又反作用于“势”,这就是“宋人不能越唐而汉,而以词自名……”的理论要义。通过“时代”与“格调”的双向分析,在辨体研究中格调的内涵就显得更加明确。因此,胡应麟在具体论述时甚至会站在传统格调说的反面,提出“可以世代为限耶?”的质疑。
王世贞在考辨古诗源流的过程中,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许多前人所未及的问题,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但整体上仍显得粗略甚至含混。如关于七言古诗,王世贞仅大致描画了“《柏梁》—《燕歌行》—盛唐七言歌行”这样一个流变过程,而对于“七言古诗与七言歌行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却没有做出任何说明。胡应麟在专卷讨论七言古体时,首段开宗明义,提出“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紧接着对“歌”“行”之名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乐府之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考辨,认为:“《南风》《击壤》,兴于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于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无如骚之《九歌》,皆七言古所自始也。汉则《安世》《房中》《郊祀》《鼓吹》,咸系歌名,并等乐府[5]41”。那么,这种说法会不会与王世贞的古诗体认发生冲突呢?关于这一点胡应麟巧妙地引入“声调”等形式因素,以为“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始之,《燕歌》《白紵》皆此体”[5]41,这就在不脱离王世贞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补苴罅漏,弥偏救弊
王世贞在对汉魏诗歌进行辨体研究时,忽略了对汉魏乐府流变的考察,这显然是乐府体制自身的特点使王氏难以从中发现较明朗的线索,因此王世贞不得不阙之不谈而将焦点集中在乐府创作论上。鉴于此,胡应麟专门解释了这个问题,认为:“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5]12”。就是说由于乐府体制的多样性,以辨体论来研究乐府诗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摆脱古律二分法的限制,从“本色”角度树立乐府中每一种体制各自的典范。他说:“乐府三言,需模仿《郊祀》,裁其峻峭,剂以和平;四言,当拟则《房中》,加以舂容,畅其体制;五言,熟悉《相和》诸篇,愈近愈工,无流艰涩;七言,间效《铙歌》诸作,愈高愈雅,毋堕卑陬……此乐府大法也[5]13”。这就为乐府论由辨体转向创作提供了合理解释。王世贞晚年曾大力挖掘汉魏诗歌“自然”之美学风貌,但何为“自然”,王氏在表述上并未直接道破,而是通过赏析或本事的方式间接地表达出“自然”之“义”与“妙”。这种做法延续了传统诗话的说理模式,但易使文本因缺少提炼而显得要点不够突出。胡应麟则发展了王氏对汉魏诗歌的审美观照,并以古典诗学审美范畴为参照,提出了胡氏“兴象”说以专论汉诗。他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5]100”。这就直接将“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上升到了诗歌本体论的高度。又说:“《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5]25”。则进一步将“兴象”集中到单独的汉代诗歌观照上,并以此解释两汉诗歌的“天工神力,时有独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两汉诗歌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将相对具象化的“自然”论与人的审美创造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王世贞一样,胡应麟作为诗坛复古的代表理论家,其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发展,如果说“前、后七子”时代诗坛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复古,那么到复古运动末期诗坛的核心问题则是要不要复古。胡应麟一方面坚守复古阵地,在强化诗歌辨体的同时引入“兴象”论调作为理论更新;另一方面对诗坛出现的空疏弃古之风展开猛烈批判。其实,空疏弃古不良风气的理论来源,有一部分竟出自复古派内部的“舍筏登岸”之论,这种曲解尤其不能为胡应麟接受。他说:“今人因献吉祖袭杜诗,辄假仲默舍筏之说,动以牛后鸡口为辞。此未睹《何集》者。就仲默言,古诗全法汉魏……今未尝熟读其诗,熟参其语,徒执斯言,师心信手,前人弃去,拾以自珍,一时流辈,互相标鹄,将来有识,渠可尽诬?譬操一壶,以涉溟渤,何岸之能登?[5]349”王世贞晚年虽然强调自得的重要性,但始终认为人的才思需要由苦学(规范)来匡正调剂,即其所谓“抑才以就格,完气以成调”。但复古末流未得王世贞理论之精髓,反而将剿袭剽窃的习气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文坛师心派的崛起一方面为复古末流所激,一方面竟然以复古派“舍筏登岸”之论为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以胡应麟为代表的复古殿军所面临的文坛环境更加混乱不堪,欲维持汉魏盛唐诗学正朔,胡氏就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百篇》出自何典?”的谬论,并沿着王世贞晚年的诗学路线增强汉魏诗歌的包容性与流动性,以期达到古典审美理想的明代复兴。
二、许学夷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接受
根据《诗源辩体》中许学夷自序所言:“是书起于万历癸巳,迄壬子,凡二十年稍成……后二十年,修饰者十之五,增益者十之三[6]2”,可知该书作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至崇祯五年(1632 年)方完稿付刊,前后历时四十年,许氏可谓倾注毕生精力于此。而从万历二十一年至崇祯五年,亦是复古派日衰,公安、竟陵诸派先后崛起于文坛的时代。鉴于复古派之食古不化,“公安三袁”明确提出反对复古、抒写性灵,主张诗歌创作要“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诗歌风貌要“近俚近俳”[7]710。稍后出现的竟陵派吸取了公安派的反面经验,将“性灵”的内涵阉割为一种“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式的内修,以降低狂放对性灵美学的损耗,并重新强调古典法度对人的规范作用。但是,竟陵派的这种调和论只能是一厢情愿,以复古派之保守约束性灵一派之激越,结果却陷入了理论上复古与性灵的互相制约、互相消磨,最终使诗歌的发展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
(一)汉魏诗学价值判断标准的调整
许学夷面对这样的诗学环境,首先认为弊病产生的根源在于“过中”与“离”,即其所言:“后进言诗,上述齐梁,下称晚季,于道为不及;昌穀诸子,首推《郊祀》,次举《铙歌》,于道为过;近袁氏、锺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6]1”。宗六朝晚唐者与宗汉魏盛唐者尚可以“不及”与“过”(“过中”)来评判,而公安、竟陵二派简直就是“趋异厌常”之“离”,遑论“过中”!但不论“过中”还是“离”,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均在于不识“正变”。而晚年主张“调剂”的王世贞与辨体尚不失公允的胡应麟亦纳入了许学夷的批评范畴。他说:“元美、元瑞论诗,于正者虽有所得,于变者则不能知;袁中郎于正者虽不能知,于变者实有所得[6]38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许学夷对王世贞与胡应麟的评价其实代表了他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整体态度,王世贞的不知“变”在这里只是一种观念的集合,即许氏所言:“论诗者以汉魏为至,而以李杜为未极,犹论文者以秦汉为至,而以四子为未极,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识通变之道者也[6]190”。而当具体论及王世贞的作品时,许学夷往往又能深察其变。总体而言,王世贞作为复古巨子,其崇“正”理念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与袁宏道等人的崇“变”一样,皆为一偏之见,皆是“过中”与“离”产生的思想基础。
调整了汉魏诗学价值判断标准之后,许学夷多从探究合理性的角度论述诗歌体制的兴衰正变,对王世贞、胡应麟为代表的传统复古派古诗“唐不及汉魏”“魏不及汉”的论断做出了批判。如关于“唐不及汉魏”,许氏认为:“五言古,自汉魏递变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参始别为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为唐古之壸奥。故或以李杜不及汉魏者,既失之过;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则愈谬也[6]192”。这就从诗歌发展“律”化的必然性看待唐代古体诗,并指出:拿汉魏古诗与唐代古诗作比较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合理且无意义的。王世贞虽然在梳理七言古体诗歌时指出了“创”“畅”“极”的七古发展过程,并把握到了盛唐七古较好地融合了“古”“律”之长,这其实与许学夷的唐古观照有一定的相通性。但对“正变”观念认识的褊狭使王氏仍将唐代古体视为简单的“变”,如此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时代格调”复古集体认同的束缚。
再看“魏不及汉”,王世贞从崇尚古朴的审美偏好出发,对曹植的“流丽”每多贬抑,认为曹植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操与曹丕,而胡应麟承接王世贞的论断,并将其扩展到魏诗与汉诗的比较上,认为“汉诗如炉冶铸成,浑融无迹。魏诗虽极步骤,不免巧匠雕镌耳[5]19”。对此,许学夷特别强调:“元美尝谓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而此谓‘子建才太高、词太华,而实逊父兄’,胡元瑞谓论乐府也。然子建乐府五言,较汉人虽多失体,实足冠冕一代。若孟德《薤露》《蒿里》,是过于质野;子桓《西山》《彭祖》《朝日》《朝游》四篇,虽若合作,然《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6]74”这就仍是从“变”的合理性出发,更正复古派等人的“过中”之论,强调“才能作用”的“理势之自然”,从而跳出价值评判“优劣”二元化的非理性误区。
(二)对汉魏诗歌美学本体的重述
许学夷进一步对汉魏诗歌的美学本体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王世贞晚年将“自然”引入对汉魏诗歌的观照,胡应麟进而又以“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并举,丰富汉魏诗歌的本体内涵,许学夷则在二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兴”与“作用”的汉魏诗歌本体论。何为“情兴”?一方面许学夷继承了传统诗学对“情兴”的解释。所谓“情兴”就是诗人作为审美主体以“情”的产生来回应“物”的召唤,文学作品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由“感官”到“心理”到“文本”再到“接受”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遗漏、不能置换顺序。许学夷认为:“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本乎情,故多托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之宗。”[6]44“汉魏五言,本乎情兴,故其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6]45这就是注重“情兴”在汉魏诗歌产生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样,许氏又认为:“汉魏五言,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颜谢五言,为文而造意,故其语雕刻而意冗[6]47”。这就是说汉魏诗歌符合由“感官”到“接受”的美感生成规律,而颜延之、谢灵运为代表的六朝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于心中预设一种“文本”模式,然后再刻意地去索寻符合这种模式的“意”与“象”,此种创作意识只能使创作主体在修辞与表意上着力,而难以表达主体的真情实感。
另一方面,许学夷又用“作用”补充“情兴”对汉魏诗歌嬗变本质概括的不足。皎然在《诗式》中说:“二子(李陵、苏武)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8]103”。那么对于“作用”该作何解?王世贞认为:“《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9]41”将“作用”指为一种无法琢磨的“法”,却忽略了“法”与“自然”的本质冲突,使后人将“作用”误解为一种“法”,只不过汉魏较隐,后代渐显罢了。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许学夷批判道:“岂以汉人亦有意敛藏耶?善乎赵凡夫云:‘古诗在篇不在句,后人取其句字为法,谓之步武可耳,何尝先自有法!’[6]58”由此,许氏提出了自己对皎然“作用之功”的理解:“‘作用之功’,即所谓完美也……作用之迹,正与‘功’字不同,功则犹为自然,迹则有形可求矣[6]62”。他将“作用”一分为二,即“作用之功”与“作用之迹”,“作用之功”仍属于“自然”的范畴。因此,许氏认为《古诗十九首》“无作用之迹”,而曹植的“五言四句如‘逍遥芙蓉池’‘庆云未时兴’二篇,较之汉人,始见作用之迹[6]82”。可见,许氏标举“作用”目的是为了揭示汉魏诗歌之“变”,以此明确汉末建安诗歌“变不离古”的本质。“作用之功”与“情兴”代表了汉魏古诗之“自然”本色,“作用之迹”与“着意”则表明了古诗由“汉魏”向“六朝”的必然之“变”。
许学夷对王世贞汉魏诗学做了许多修正,因此在《诗源辩体》中屡屡可见他对王氏诗学“过中”之弊的指摘,但更应看到该书对王世贞、胡应麟等人辨体观的继承(如《诗源辩体》就以《艺苑卮言》与《诗薮》为重要参考文献)。胡应麟对王世贞的修正以补充为主,其主导态度在于“扬”;许学夷对王世贞的修正则以指瑕为主,其主导态度在于“持中”,这种指导态度的不同是胡、许二人在接受王世贞汉魏诗学观过程中最大的相异之处。
三、王夫之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接受
王夫之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认识与胡应麟、许学夷等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胡、许二人是“修正者”,其差别体现在修正的态度与程度上;而王夫之则是“批判者”,这种“批判”亦可称之为“负接受”,即以吸取教训的反思意识为主导接受前一历史阶段的反面经验。因此,在王夫之对王世贞诗学思想的观照过程中就难以再见到那种具体而微的解析,而是将王世贞汉魏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诗学思想的代表,置于明代诗学宏观背景下与众多明代文学家一并考察,以便更好地对明代文学整体进行批判。
(一)对明人门户问题的批判
王夫之对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对门户问题的批判上。王夫之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1]14”。“前、后七子”倡导复古而流于剿袭,竟陵派崇尚性灵却流为僻涩,这些诗学流派发展到最后都成为诗坛不得不廓清的贻害,究其根源不在于“偏”,而在于“立门庭”,门庭一立必有“依傍门庭者”,这种思想的依附使立门户者与傍门户者必以门派之是非为是非,这就是“自缚缚人”。王世贞的汉魏诗学观本身就受到“后七子”整体诗学的介入而实质上亦为一种门户之见,虽然晚年有所改变,但如钱谦益所言“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峻坂、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10]437”。
其实,王世贞又何尝不知“门户”之弊,在《艺苑卮言》中他就不无讽刺地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9]425”。然而,“门户”如一把双刃剑,不好的一面如王世贞所言,好的一面却又能使开门立派者激扬文字、坛坫自雄,实现人生“立言”的价值追求。因此,对“门户”充满厌恶的王世贞最终仍同李攀龙等人一起走向了“设坛建墠”的道路。郭绍虞在总结王夫之文论时说:“然而船山却不拈出神韵两字为其诗论主张,则以一经拈出,自有庸人奔来凑附,依旧蹈了建立门庭的覆辙。才破一格,复立一格,这在船山是不为的[11]556”。可见,王夫之吸取教训之深,以至于不轻言自己的诗论主张。
(二)对汉魏诗歌审美本质的新期许
针对汉魏诗歌审美本质,王夫之的理解亦与王世贞有很大的不同。王夫之反对建立门户不仅体现在行动上,更反映在文学理念上;不仅要批判建立门户这一行为,还要摒弃与这一行为相配套的思想基础。
先说王夫之对诗歌创作的认识。王夫之极不赞成明代诗坛所盛行的“格调”一说,认为作诗讲究格调只能使初学者落于字字句句篇篇之形似,而于诗歌之本质一无所得,因此,他对王世贞的诗歌模拟形似给予严厉的批评。王夫之在其明诗选本《明诗评选》上仅选王世贞五绝一首,并评价道:“弇州生平所最短者莫如思致,一切差排只是局面上架过……一套劣应付老明经换府县节下炭金腔料,为宋人所尤诋诃者,以身犯之而不恤。故余不知弇州之以自命者果何等耶?故曰:弇州于诗未有所窥,倘有所窥,即卑即怪,亦自成一致也[12]1554”。在王夫之看来,王世贞等复古派作家毕生追求的“格调”只不过是“一套劣应付老明经换府县节下炭金腔料”,于诗歌创作应有的“思致”却少有所得,而最讽刺的是:王世贞一生于宋多有排斥,诗歌风貌却“即卑即怪”,最终连宋人也不如。
再说王夫之对诗歌审美本质的理解。王夫之否定了“格调”,自然亦不会赞成建立在“格调”基础上的诗美理想。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诗人在论及汉魏诗歌时多以古朴苍凉、梗概多气目之,如王世贞评价汉高祖的《大风歌》“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评价曹操古诗“古直悲凉”;而王夫之则认为《大风歌》“神韵所不待论。三句三意,不须承转,一比一赋,脱然自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岂亦非天授也哉![12]483”评价曹操《短歌行》时又说:“尽古今人废此不得,岂不存乎神理之际哉?以雄快感者,雅士自当不谋。今雅士亦为之心尽,知非雄快也。此篇人人吟得,人人埋没,皆缘摘句索影,谱入孟德心迹。一合全首读之,何尝如此?[12]498”前人每每看到的是《大风歌》的豪气,王夫之却看到了其中的“神韵”“自然”;前人时时称道曹操诗歌的雄劲奋发,王夫之却认为以“雄快”观曹操之诗实未明“孟德心迹”,以至于埋没了诗中蕴含的“神理之际”……所以说王夫之虽未,亦不可能指明何为诗歌之审美本质。然而,仔细查看《古诗评选》《唐诗评选》乃至《明诗评选》,其中的选诗标准、诗歌评语又无不透露出他对诗歌审美本质的理解,即情景交融、韵致无穷。
最后看王夫之对诗歌审美本质实现途径的阐述。王夫之对“格调”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能讲“格调”,而是表明无法通过“格调”理解诗歌的审美本质。他认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1]7”。其中“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从创作主体来说,即是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希求达到的境界;第二层对接受主体来说,即是主体在接受过程中所领略到的韵味。对于是何种境界与韵味,王夫之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可从他对古诗的评选中窥得一二。如他在评鲍照诗歌时说:“空中布意,不堕一解,而往复萦回,兴比宾主,历历不昧[12]530”;评价崔颢《长干行·君家何处住》时说“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1]19”。这种“往复萦回,兴比宾主,历历不昧”大概就是作者追求的境界,而“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则是一首优秀诗歌应展现出的审美观感。何者为“势”?既然对“意”的内涵有了把握,则如王夫之所说“势者,意中之神理也”,“神理”就是规律,即能使在创作中达到理想境界、在鉴赏过程中获得韵味的规律,掌握了这种“势”也就能向上一层达到“意”,达到情景交融、韵致无穷的诗美终极目标。
四、结语
胡应麟与许学夷均为王世贞汉魏诗学的修正接受者。胡氏与许氏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自身所受到的诗学熏陶,决定了他们的期待视野不可能超越明代诗学的总体思维定向与先在结构,二人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对以王世贞诗论为代表的明代中后期复古诗学做出理论上的补充与更正。就汉魏诗学观看,胡应麟由于个人与王世贞的特殊关系,更倾向于维护王世贞汉魏诗学的正统地位。许学夷相较于胡应麟,已与王世贞所处的时代有了一定的距离,其所面临的诗学环境则是公安派与竟陵派对正统诗坛的轮番冲击,这就使许学夷对王世贞汉魏诗学的修正带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即用修正后的汉魏诗学观批判公安派、竟陵派及其末流对诗坛造成的恶劣影响。
而王夫之则是批判的接受者。王夫之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自身的诗学崇尚,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明代诗学的思维定式与先在结构,其期待视野的产生,是建立在对王世贞诗学思想的强力批判上所形成的一种超越明代复古诗学审美本质的诗学新体认。因此,王夫之表达出自己对汉魏诗歌“情景交融、韵致无穷”美学本质的期许,并相应地提出了以“势”达“意”的诗美获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