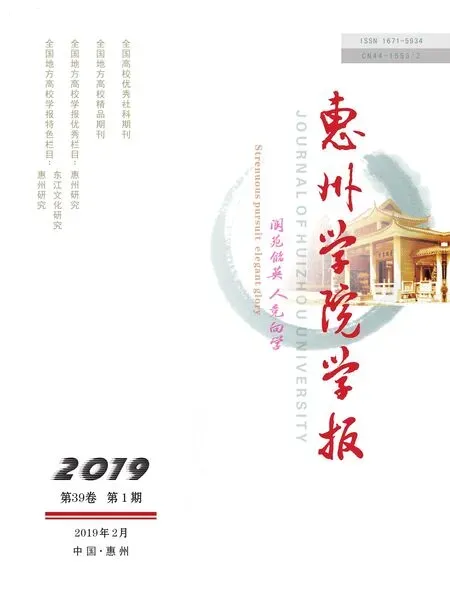苏轼唐庚谪惠作品比较论1
2019-02-21申东城蔡惠珊
申东城,蔡惠珊
(1.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2.揭西北山中学,广东 揭阳 515429)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对唐庚贬谪惠州作品研究仍较少,将苏轼和唐庚谪惠作品比较研究,学界更无人问津。故文章拟比较苏轼和唐庚谪惠作品,分析二人谪惠期间文学创作差异及原因,并阐述谪惠期“东坡精神”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苏轼唐庚受党争所累而遭贬谪惠州的经历相似
苏轼和唐庚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四川老乡,都卓有文学成就,两人仕途之路也同样坎坷,先后受党争所累而贬谪惠州。
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后,十九岁的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新党乘机而起,以宰相章惇为首的新党派向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虞策、来之邵弹劾苏轼所作诰词,认为苏轼任翰林学士时“凡作文字,讥斥先朝”,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59岁的苏轼以左承议郎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未到贬所,政敌们还不罢休,途中诏命几变,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从苏轼十月二日抵达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离开惠州,总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绍圣四年闰二月)。谪惠期间,苏轼创作颇丰,据统计有诗187首、词18首、文(含书信等)363篇。
南宋诗人刘克庄来惠州游西湖时曾写下:“一州两迁客,无地顿奇才。方送端明去,还迎博士来[1]418”。这里端明指苏轼,因苏轼曾任端明殿学士,博士指唐庚,这首诗写的就是苏轼和唐庚先后谪居惠州之事。大观四年(1110 年),唐庚为宗子博士,宰相张商英荐其才,不久即除提举京畿常平。同年九月,也就是苏轼离开惠州之后的第十三年,唐庚即被贬惠州安置。关于唐庚被贬惠州原因,《宋史·张商英传》有云:“何执中、郑居中日夜酝织其(张商英)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客唐庚,窜之惠州[2]8838”。可见唐庚被贬,是为张商英所累,政敌欲除张商英,先以唐庚为打击对象。直到政和五年(1115 年),唐庚才遇赦北归,唐庚在惠州生活五年,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佳作,作诗185 首、文45篇。
二、苏轼唐庚谪惠作品的四个不同
谪惠期间是苏轼和唐庚政治生活低谷期,却是他们创作高峰期之一,这些作品既形象反映了他们谪惠期间生活和当时社会情况,也是他们思想的体现。苏、唐二人谪惠作品有何异同呢?
(一)潇洒处世、乐观旷达与落魄伤感、自省内敛的贬谪心态有差异
年龄上,苏轼贬惠时已59 岁,而唐庚39 岁。苏轼当时已“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长久[3]1043”(《赴英州乞舟行状》)。苏轼已近花甲之年,长期颠沛流离,加上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痔疾,可以说是年老体弱之际。而唐庚却正当青壮年时期,身强力壮。两人遭受贬谪的心态是如何的呢?
北宋中后期党争激烈,从苏、唐二人谪惠作品,都能看到他们贬谪惠州期间忧谗畏讥的心理。苏轼在其给亲友的书信中常常叮嘱亲友“勿示人”“幸读讫,便毁之”“一详览,便付火”“千万密之”等,这些语句可见苏轼的小心谨慎,唯恐再生事端和连累亲朋好友而事事慎言谨行、处处小心戒惧。同样畏祸心理在唐庚诗中也常常能体现出来,如《次勾景山见寄韵》:“此生正坐不知天,岂有豨苓解引年。但觉转喉都是讳,就令摇尾有谁怜。腰金已付儿曹佩,心印还当我辈传。他日乘车来问道,苇间相顾共攀缘[4]206”。这首诗作于政和二年(1112),颔联“但觉转喉都是讳,就令摇尾有谁怜”就写出了唐庚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心理,他虽然已遭贬谪,生活在远离政治斗争核心的蛮荒之地惠州,但其内心对党争之祸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两人面对贬谪都有畏祸心理,但却不尽相同。
首先,苏轼以随处为家的潇洒处世心态面对生活,是一个以惠州为家的主人公形象;而唐庚则落魄伤感,是一个怀念故国的异客形象。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时,惠州父老相携迎迓,立于街道两旁,苏轼当时非常感动,感到惠州这个地方很亲切、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于是写下:“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1]454”(《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初到惠州便觉亲切欣喜写得淋漓尽致。数月后苏轼在《与王巩》的一封长信中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1]550”。他能以贬谪地惠州为家:“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1]479”(《迁居》)。这种随遇而安、视他乡如故乡的人生态度是通脱的,这种对异乡的热爱是从内心奔涌出来的,既非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也非强自排遣的自我慰藉,“四海为家”这个词在别人口中也许带有几分无奈或悲慨,但在苏轼心中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潇洒。苏轼心安即是家的豁达之情让他能在蛮荒之地怡然安居,惠州的一切在苏轼眼中都别有情趣。苏轼用优美的笔触,轻快地写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1]465”(《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488”(《纵笔》),“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480”(《食荔支二首》)。苏轼毫不吝惜地表达出自己对惠州的喜爱之情。
尽管唐庚在惠州生活的时间长于苏轼,但唐庚对惠州似乎没有这种感情。唐庚接到贬谪消息时绝望痛苦,内心政治抱负瞬间化为泡影,十年间难得一次进京为官,未满一年就遭受贬谪,正是“朝持汉使节,暮作楚囚奔[4]203”(《武陵道中》)。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唐庚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庚对突如其来的无辜遭贬感到震惊和痛苦,呈现出一种“逐臣”“愚忠”“愚臣”心态。在他谪惠诗文中,多次用“愚儒”“愚忠”等词来形容自己,如“可是清辉解娱客,能令肠断到愚儒[4]211”(《东麓》),“一出湟关五见梅,愚忠几欲伴黄埃[4]207”(《有感舍弟端儒外甥郭圣俞》)。他诗中也常见贬谪之悲,唐庚不像苏轼那样在贬谪地怡然安居,而是在诗中以“旅人”“逐客”“江南客”“北客”等称呼自己,伤感落魄时时能见,如“残岁无多日,此身犹旅人[4]213”(《次韵强幼安冬日旅舍》),“逐去定知穷不死,向来元以句为生[4]264”(《既以前韵赠勉翁复怀庭玉因次前韵》),诗中唐庚是一个异客形象,他用“南方”“南人”来指代惠州,对自己远方“故国”“故园”怀念深切。
其次,苏轼乐观旷达、超然物外,唐庚则自省内敛。苏轼在惠州经济拮据,加上政府薪俸又没按规定给他,所以苏轼在惠州的生活很艰难,甚至会无米下锅。但他乐观从容地应对,从不怨天尤人,《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云:“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1]485”。说自己要像“千丈松”一样,顽强地生活下去。苏轼乐观旷达精神在他谪惠诗文中随处可见,《记游松风亭》中,把自己比作“挂钩之鱼”“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士兵,在劫难逃,不如实实在在就地歇一会,随缘委命,超然物外。
与苏轼相比,唐庚则显得较自省内敛。其《夜闻蜑户扣船作长江礧,欣然乐之,殊觉有起予之兴。因念涪上所作招渔父词非是,更作此诗反之,示舍弟端儒》展现了诗人反省过程:“当年无奈气何狂,醉檄涪翁弃短蓑。晚落炎州磨岁月,欲从诸蜑丏烟波[4]206”。诗中对自己流落南蛮荒夷之地原因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年自己的“狂”与“傲”在内心进行反省,将贬谪原因归根于自己性格,认为正是这种狂傲性格使自己遭受贬谪,才会在此消磨岁月。谪惠期间,唐庚闭门谢客,他曾感慨“旧物杯中酒,新衔海上翁。百非无一是,显过岂微功[4]208”(《杂诗·其四》),大有借酒浇愁之意。
可见苏轼和唐庚惠州作品反映的贬谪心态虽皆有忧谗畏讥一面,但总体还是不同的,前者旷达乐观,随缘委命,在贬谪地能享受人生,是一个以惠州为家的主人公形象;后者小心谨慎,自省内敛,是一个怀念故国的异客形象。
(二)情景理交融与自然风光再现的岭南风物不同
宋代的惠州,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是封建统治者惩罚“罪臣”的贬谪之地。内地一般人不了解,常闻之色变。可苏轼和唐庚被贬惠州后,都被惠州的美丽自然风光陶醉了。在他们留存的谪惠诗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岭南风物及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但二者不同的是,苏轼笔下的岭南山水、田园风光之作并非为了写景而写景,山川美景往往是议论说理或是触发情志的媒介,多是情、景、理的交融,强化自我感受的抒发;唐庚则是有意识地将岭南风物、山水田园之景作为表现自我心灵意态的背景,再现自然山水。
苏轼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寓情于景、融理于情。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一》:“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1]460”,此诗以白水苍山开篇,意境开阔,秀美的风景触发了诗人对个体生命和人生思考:人生有限,山环水绕的迷人风景却是永恒,我只不过是谪居于此度过短暂的人生罢了。
较之苏轼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多是情、景、理的交融,唐庚对于岭南风物、田园景色的描写则是有意识地再现自然风光,淡化情理的抒发,尤其是以理入诗较少,从而使岭南景物风光无限,别具美感。如《栖禅暮归书所见》二首:“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山深失小寺,湖尽得孤亭。”“春著湖烟腻,晴摇野水光。草青仍过雨,山紫更斜阳”[4]204,描绘了春行晚归所见的娴静优美之景:骤雨斜阳、小寺孤亭、湖烟水光、青草紫山,忽明忽暗之光,绚丽浓艳之色,如同印象派画家的写生之作,把岭南春天特有的风景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唐庚的《杂诗二十首》结合惠州特有的风土人情、田园美景等,将其在惠州生活百态多角度多侧面展示出来。或写蛙鸣鸡叫充溢耳中独特感受“蛤哭明朝雨,鸡鸣暗夜潮[4]208”(《其一》),或写惠州独特物产杨梅“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飞梅[4]208”(《其六》),或写惠州特产白布和黄封酒“竹根收白叠,木杪得黄封[4]208”(《其十》),或写惠州景色“引水江分碧,烹丹井为红[4]208”(《其十二》)等。唐庚将到惠州所见所感的独特景象和体验有意识地用自己的笔描写殆尽,具有独特而浓厚的地方色彩。
(三)多口语化与用典化用的语言之别
苏轼和唐庚谪惠诗文在语言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两者在语言特色上最大不同在于:苏轼多是口语化语言,主张用常言和俗语来写;唐庚则多用典与化用。苏轼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5]2523”。苏轼谪惠诗文多有平淡自然风格,口语化语言使得很多作品都大有“我手写我口”特点。如“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1]485”(《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一)其中“林行婆”“留关”都是通俗直白的方言俗语。苏轼在惠州期间,尤爱陶渊明,用通俗平淡的语言创作了四十七首“和陶诗”。如《和陶贫士七首》:“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1]468”用日常语言把自己和家人艰苦困顿的生活直接书写出来。此外,如《两桥诗》描写了惠州东新桥、西新桥的营造过程:“惠州之东,江溪合流,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之”,对于人民的生活极其不便,人们往往因渡船小水流急而丧生,或因渡河而耽误事情。苏轼对此极其关切,为筑桥“助施犀带”,最终东新桥和西新桥筑成,他感到欢欣鼓舞。苏轼亲自参加桥落成庆典,“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1]481”,用口语化语言道尽眼前之景,把与民同乐的场面写得多么真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当惠州洪水爆发,苏轼《连雨江涨》“床床避雨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1]464”,用通俗语言把当时惠州穷苦百姓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危急场景细致入微描绘出来。
与苏轼口语化语言不同,唐庚诗文则较晦涩难懂,他在诗歌中常借典故来述志传情,如《杂诗·其九》:“多事定何补,寡言聊自温。蟹黄嗔止酒,车白劝加餐。濯足楼船岸,高歌抱朴村。愧无魅可禦,只益负君恩[4]208”。“濯足”出自《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6]170”,“抱朴村”缘于葛洪辞官不就在罗浮山著《抱朴子》的故事。唐庚巧妙地引用两个典故写出自己身遭贬谪后如同古人隐居避世的生活状态。《白小》最后两句“安能蹲会稽,坐待期年钓[4]200”,运用了《庄子·外物》任公子垂钓故事。唐庚善于化用前人诗句,如《泸人何邦直者为安溪把截将有功不赏反得罪来惠州贫甚吾呼与饮为作此诗》:“满饮一杯齐物论,白云苍狗任浮云”[4]204,化用杜诗《可叹》“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7]90”,表达出世事变幻无常。一个“任”字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如《舍弟书约今秋到此》:“从今西望眼,应到见时休[4]204”,化用韩愈《西山》诗“为遮西望眼,终是懒回头”[8]893的诗句。用典与化用是唐庚诗文一大特点,这也是他与苏轼常用口语、通俗自然的语言风格不同处。
(四)自然天成与苦吟推敲的风格特色殊异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云:“他(唐庚)和苏轼算得小同乡,也贬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点相像,而且很佩服苏轼。可是他们两人……一个是欢天喜地,一个是愁眉苦脸。苏轼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唐庚的话恰好相反:‘诗最难事也!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然后成篇……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返复改正……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9]92”钱钟书这段话道出了苏轼和唐庚两人在文学创作风格特色上自然天成与苦吟推敲差异。
苏轼作诗为文从来不刻意,总是漫不经心,“随物赋形”,“冲口而出”,要不得不为文乃为文,无意于工而工,正如他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1418”。苏轼作品行云流水般的风格,达到了自然潇洒、浑然天成的境界。从苏轼贬谪惠州的诗文和与亲友的通信中,都可以看到苏轼这一创作风格特色,如《与陈师锡》“所谓诗文之类,皆不复经心[1]555”。由于其渊深学问,广博知识,使其不刻意之作也能见奇思妙语,如《游博罗香积寺》《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小圃五咏》等。因他善以乐观积极胸怀对待事物,故能从生活平凡细微事物中摄取乐趣,自然而然地化为文章诗篇。苏轼在惠州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很乐观诙谐,他把买羊骨之事写信告诉子由,本来“不敢与仕者争买”就很可怜了,但是苏轼吃着骨间的微肉,竟然说和吃蟹一样,“甚觉有补”。苏轼与表兄程正辅重修旧好,在给程正辅的信中感情真挚,无话不谈,如《与程正辅书》希望表兄能尝到自己酿的酒,这些平凡生活小事,流露出真诚坦率的情感。苏轼惠州作品,无论咏怀遣兴、抒情言志之作,还是悼念朝云的诗、词、文,或是与亲友的诗歌、书信,多是无刻意修饰、自然天成之作。
与苏轼不同,唐庚则重视苦吟推敲。他在惠州诗文以五、七言近体诗为主,他作诗对格律要求非常严格,《遣兴》中说:“酒经自得非多学,诗律伤严近寡恩[4]542”。在诗人看来,作诗是一件需耗费心血的事,是一件“难”事、“苦”事。因为追求格律严谨,他作诗时多有一种苦吟味道,“尚有苦吟三十载,与君同饱蜀山薇[4]206”(《舍弟既到有作》)。唐庚十分注重推敲炼字,谪惠诗作中炼字之处非常多,如其《春归》一诗:“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小市花间合,孤城柳外圆。琴声犯寒食,江色带新年。无计驱愁得,还推到酒边[4]209”。此诗中的字眼“合”“圆”“犯”等字可谓是诗人的精心锤炼,“推”“带”“驱”等动词用得生动活泼,颇有新意,“定”“辄”“还”等虚词意味隽永。又如《野望》:“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4]211”,“裁”“截”两个动词增添了诗歌的意境。除了苦心推敲字句外,唐庚更属对精工。比如《九日怀舍弟》:“重阳陶令节,单阏贾生年。秋色苍梧外,衰颜紫菊前。登高知地尽,引满觉天旋。去岁京城雨,茱萸对惠连[4]203”,前三联精严工对。《杂诗》二十首中也多有对属工整之句,如其十七:“水过渔村湿,沙宽牧地平。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瘴乡人自乐,耕钓各浮生[4]209”。这些精工的属对也是他“悲吟累日”反复修改的结果。
三、苏轼唐庚谪惠作品不同的三个原因
同遭贬谪,为什么苏、唐二人留存的诗文如此不同呢?为什么后人对苏唐二人的印象有别呢?恐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一)社会政治处境有利与不利是外因
苏轼周围的社会政治和人事背景比唐庚宽松、有利。
首先,苏轼得益于表兄程正辅等官场人员之利。苏轼居惠州期间,表兄程正辅到任广南东路提点刑御,并来惠州视察过几次,生活上,苏轼得到程正辅的暗中关照,地方官员也慑于程正辅权势,不敢为难苏轼,反之很关照苏轼。苏轼谪惠无职无权,但他能借助程正辅和惠州知州詹范的力量,在幕后出谋划策,为惠州百姓谋利。苏轼在惠州为百姓所做的很多善事义举都是借助这种关系促成的,比如农民纳粮问题、博罗大火灾后事宜、东新桥和西新桥的建造等都是借助程正辅和其他官吏之力才得以完成。苏轼与官宦的交往很广,除了程正辅,还有惠州两任太守詹范和方子容、广州太守王古、循州太守周彦质,还有博罗令林抃、归善令高令、程乡令侯晋叔、河源令冯祖仁、龙川令翟东玉、兴宁令欧阳叔向等等。在与这些地方官员交往中,苏轼常能得到他们在生活上的大力资助,如詹范和方子容对他曾照顾较多。
其次,苏轼自身人格魅力的影响。在文学上,苏轼是名满天下的文坛泰斗。在政治上,苏轼在贬谪惠州之前已在朝廷做官多年,曾做过哲宗皇帝的老师,担任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也先后在凤翔、密州、徐州、湖州、颍州等州府做过地方官,苏轼在政治上的名声早已遍布天下。苏轼一生光明磊落,具有很高的政治品格,他不凭个人恩怨来处事,不徇私情,一切以国计民生为重,不管居官尊卑,不管在朝在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所到之处尽为百姓做好事,受到百姓的爱戴,众人没有因为苏轼是“罪臣”而减少对他的尊重。所以,有了表兄程正辅的关照和苏轼自身人格魅力的影响,苏轼在惠州期间,才能施展自己“勇于为义”的一点政治理想,同时也使得苏轼的生活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让苏轼即使身处逆境也心有慰藉。
与苏轼的处境相比,唐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北宋徽宗时期,政治环境更加复杂险恶。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唐庚的名气都不如苏轼。唐庚在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考中进士,之后一直在利州、阆中、绵州等州县做官,直到大观四年(1110 年)春,唐庚才入京任宗子博士,随后转任提举京畿常平,同年九月被贬惠州。唐庚在朝廷做官也就仅仅几个月时间,他只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政敌只是拿唐庚当斗争序幕,真正的意图是打击唐庚背后的张商英。正如唐庚在绝句《白鹭》中感慨:“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4]204”,看见门前的白鹭群,便联想到自己此次遭受贬谪正是因为卷入朋党之争。残酷的党争,大起大落的仕途之路,让突然被贬到岭南蛮荒之地的唐庚很难适应。唐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北宋党争使得唐庚的诗文创作逐渐内敛化。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使谪居惠州的唐庚过着“问学兼儒释,交游半士农[4]208”(《杂诗》)的生活,虽然他也有伤时忧民之作,如《蜜果》《采藤曲效王建》,但唐庚始终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个人思想性格通脱旷达和忧伤内敛是内因
首先,谪惠期间,苏轼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北宋自熙宁新法以后新旧党争激烈,常常是旧党上台,新党云散;新党执政,旧党罢黜。官场仕途之人,起伏已是常事。苏轼心中早有准备,故即使一贬再贬也不至于绝望。苏轼少年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儒家入世思想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时期的济世热情虽较之前期已退,但其忧世忧民的本心并没丧失,为国为民的思想支持着苏轼虽遭受贬谪仍顽强地生活下去,只要有可能,他便会利用一切机会去为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百姓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自从一贬再贬,苏轼远大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不可能不痛苦,但苏轼这时常借老庄哲学和佛禅玄理来遣兴排忧,以求获得心灵的安适与自由。
其次,苏轼生性乐观、通脱旷达的个性,使他总是能坦然面对宦海浮沉,以慧眼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性情旷达的苏轼在惠州交往宴游非常频繁,除了与官宦交往,苏轼还与惠州本土人士或邻近州郡高士及众多僧人、道士交往甚密,如潮州吴复古、苏州定慧长老守钦、道士邓守安等等,苏轼与他们诗酒唱和、宴饮游乐,且常有僧人朋友从各地赴惠看望苏轼,抚慰了苏轼远贬岭南而受伤的心灵。与朋友故旧觥筹交错的生活构成了苏轼谪惠期间的重要内容。同时,苏轼又是一个文艺全才,不仅诗、词、文成就斐然,而且书、画也是自成一家,故当身处逆境时,他总从这些方面找到寄托。
与苏轼通脱旷达的性格不同,唐庚生性内敛。最初,唐庚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心,一直坚守儒道,他是怀抱着用世之志走进社会的,但是残酷的党争却把他打倒,面对突如其来的贬谪,唐庚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内心不免凄凉伤感。刚到惠州,唐庚对还朝抱着极大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庚渐渐意识到党争影响的深远性,这使得唐庚出现了畏祸及身思想,造成了他消极避世态度。谪惠期间,虽有文坛故友如郑太玉、强幼安、王观复、任景初等与唐庚诗书往来,但唐庚的交游远远不如苏轼广泛。南居蛮荒,生活艰苦,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他战战兢兢地忍受着恐惧和彷徨、孤独和寂寞。正如其在《杂诗·其二》所说的:“已绝经年笔,仍关尽日门[4]208”,唐庚既害怕自己再次卷入党争,又担心自己作为罪人影响他人,所以“关尽日门”,在惠州生活期间思想比较封闭内敛,自守其身。
(三)家庭环境温暖幸福与孤独凄苦是诱因
自古以来,家庭环境都是每个人生活很关键的一部分,可以说家庭环境的不同是个人性格成就的诱导因素。
苏轼仕途不顺,但幸运的是有个温暖的家,在外面遭受打击时,身后有个安然的避风港,这慰藉了苏轼的心。陪同他来到惠州的有侍妾王朝云,王朝云漂亮、聪颖、能干,最理解苏轼,能从思想感情上关心苏轼。贬谪惠州,在众多侍女姬妾相继离开的情况下,王朝云仍紧随苏轼南迁,长途跋涉,陪伴苏轼过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毫无怨言,最后病死在惠州。与苏轼前两任夫人相比,苏轼与朝云堪称知音,情感较深,谪惠期间,为朝云写下的诗词就有《朝云诗》《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殢人娇》等,在她去世后又写下《雨中花慢》《悼朝云并引》《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西江月·梅花》《惠州荐朝云书》《王朝云墓志铭》等,表达对朝云的深切悼念及其高尚品格的赞美。在惠州期间,苏轼与王朝云的爱情生活故事流传至今,成为历代佳话,堪称是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典范之一。
除了王朝云以外,还有小儿子苏过也一直陪在苏轼身边,特别是在惠州的第二年,王朝云病逝之后,还有苏过陪着苏轼,直至后来苏轼贬谪海南,也是苏过陪伴前往,独自全程侍奉。垂老幽居,地远途穷之际,苏过随侍苏轼,可谓顺逆与共,人物同见,山水同游,诗文同作,父子二人情感深厚,情趣相得,如苏轼在《和陶游斜川》中写道:“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1]475”。苏过受苏轼影响,诗文方面也不断进步,谪惠期间也留下了《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松风亭词》等佳作,这足以让苏轼感到欣慰。除此之外,苏轼与苏辙手足情深,不论身在何处,兄弟二人始终相互扶助,相互牵挂,这给暮年投荒、身处逆境的苏轼极大的温暖。
与苏轼相比,唐庚就没有这么幸福了。贬谪惠州,只有他的外甥郭圣俞陪同他远赴贬所,虽然后来他的弟弟唐庾也来到惠州,陪伴他直到唐庚遇赦北归,但他的妻子儿女都不在身边,不能共享天伦之乐,加上遭遇贬谪的精神压力,所以常常表现出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以及谪居异乡、身不由己的情绪。
四、谪惠期“东坡精神”的价值意义和深远影响
“东坡精神”是苏轼仕途、人生中精神特质的核心,是苏轼一生集民族的真善美于一身的人本主义。苏轼谪居在惠州的两年零七个月,是苏轼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其为诗为文、为人为官处处都体现着“东坡精神”。苏轼谪惠期的思想堪称“东坡精神”的代表之一。
同是贬谪惠州,苏轼来惠时间比唐庚早,可是居留的时间则比唐庚短,论理惠州百姓对唐庚应该更有感情,可并非如此,九百多年来,人们对苏轼和唐庚却有不同的态度。正如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10]6”,“东坡精神”也流芳千古,而唐庚却少为人知。通过前面的比较,可见苏轼和唐庚最大不同,在于唐庚即使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仅仅是在文字上,而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而苏轼则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思想,他平等待民,不分等级,不分愚贤,不分地域,视民如己,爱民如子,更加体现了“东坡精神”惠州外化的价值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东坡精神”最主要特征是巧妙地将传统儒家的“穷”和“达”思想统一起来。尽管苏轼历经仕途坎坷和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使命感。他心胸坦荡,立身处世,自有本末,绝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趋炎附势,不结朋党,不徇私情,一切以利国便民为旨,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为国为民的崇高人格精神。《宋史》称:“(轼)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5]2827”。即使到了环境恶劣的惠州,尽管是毫无职权的闲官,他仍心系苍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力为百姓做实事,为百姓谋利益,其惠民之举,至今惠州人民有口皆碑,苏轼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这是唐庚无法企及的。
其次,“东坡精神”还体现在他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处世智慧。仕途经历了几番辉煌和失落后,不论身处何地,不论何种打击,苏轼面对现实的风浪始终保持安定超然的状态。即便几遭贬谪,来到当时荒蛮偏远的惠州,身处逆境,苏轼依然泰然处之,在思想行动上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他的旷达自适和随遇而安胸怀。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淡功名成败,看破穷达得失的人生智慧,铸就了他特立独行的“东坡精神”,而惠州正是他成就“东坡精神”的主要地方之一,其后历代文人士大夫常把这种精神作为学习楷模,这是东坡之幸,也是惠州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