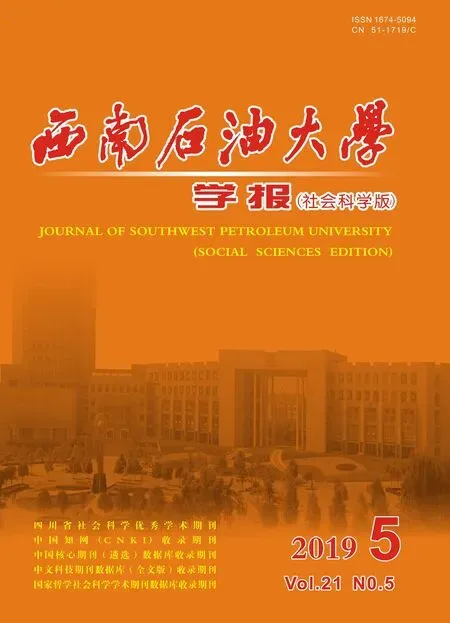刍议文学研究中的概念隐喻
——以《李尔王》为例
2019-02-21冯军
冯 军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引言
随着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学不仅是认知的产物,更是认知的工具,“正如丽萨·詹塞恩(Lisa Zunshine)所提出的那样,文学承担着认知训练的功能(literature affords a cognitive callisthenics)”[1]4。人类认知源于日常生活中身体与外界的互动,但是这种模式下产生的认知是最基础、最原始的认知,高级复杂的认知离不开文学的塑造,因为文学对认知的训练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1]4,这样人类认知才能不断进化发展。著名的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更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2],从而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不但拉开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序幕,也为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最终在人文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认知革命,隐喻成了文学与语言学通向认知的桥梁。
1 隐喻研究概述
1.1 隐喻的含义及流派
人们提起隐喻,往往想到的是比喻修辞,就像转喻、提喻、反讽一样。在比喻中,词语的意义通常是被扭曲的,表达的并不是其字面意思。当人们说“男人是狼”时,其实是对“狼”的常规意义的偏离。隐喻的理解机制是对比和类比,这一思想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另一种同样古老的关于隐喻的理解是心象说,即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是基于心理意象(mental image),比如,“人”具有“狼”的意象。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隐喻使我们以此物理解彼物。据此,索斯凯斯(Soskice)将隐喻定义为“隐喻是一种修辞,通过这种修辞,我们能够使人通过一种事物联想起另外一种事物”[4]。隐喻的定义纷繁复杂,据索斯凯斯的说法,至少存在125 种不同的定义,其中还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定义[4]。可以说,隐喻是一个对话体式(amoebaean)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开放性结构概念。因为它的边界是模糊的,明喻和隐喻、转喻与隐喻是否属于同一类或同种概念,目前也存在争议。
现代隐喻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一是反传统派(iconoclasts)。他们否认隐喻的修辞意义,甚至怀疑隐喻的存在。在他们看来,隐喻只是一种掩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代表人物是分析哲学家、实在论者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他极力捍卫“真值语义论”,即当且仅当我们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句子为真时,我们才能理解这句话。因此,从语义真值论来看,隐喻表达几乎全部是假话。更进一步,戴维森甚至否定隐喻具有传递语义和表达思想的功能。二是互动论(者)派(interactionists)。代表人物有理查德(I A Richards)、布莱克(Max Black)等。互动论者认为隐喻意义源于本体与喻体的互动。三是认知隐喻派,代表人物包括尼采(Nietzsche)、赫尔曼·黑塞(Hesse)、莱考夫(Lakoff)等。他们认为隐喻意义是原始(基本)的意义表述形式,并坚信隐喻弥漫在我们日常生活、思维和认知的方方面面,隐喻是我们思维的方式。
1.2 隐喻研究:从修辞到认知
隐喻研究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长期以来,人们把隐喻只当作是语言修辞手段,并区分了文学隐喻和非文学隐喻,认为文学中的隐喻表达比非文学隐喻表达更富有创造性、更新奇、更复杂、更难以理解。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的特征就是审美性地刻意扭曲作品的语言成分,换句话说,就是有意识地违背语言的标准规范[5]。英美文体学家对文学语言作了进一步的解释[6-8],认为文学运用非常规的语言表达凸显了特定的文本,同时刷新了读者的态度和世界观。根据这一传统,隐喻表达的运用被看作是一种语义层面的特殊偏离,因为隐喻表达从字面上而言是不合逻辑、荒谬和无意义的[8]。文学中的隐喻由于涉及多个隐喻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所在文本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于(或优于)非文学隐喻。诺沃提尼(Nowottny)指出,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诗歌的语言结构性更强,尤其是隐喻表达有助于形成复杂的文本组织结构,从而塑造出诗歌的整体意义和效果[7]。
楚尔(Tsur)的认知诗学运用认知理论系统解释了文本结构与文本效果之间的关系[9]。就隐喻而言,楚尔试图解释某些独立的新奇隐喻如何能够产生独特的效果。他认为隐喻表达涉及逻辑悖论,这一悖论通过去掉与喻体不相关的特征,同时将剩下的特征传递给本体的方式得以消解[9-10]。例如,“smiling hooks”用于指代照片中的笑脸就涉及一个逻辑悖论(喻体是hooks,本体是smiling faces)。要消解这一悖论,首先需要去掉喻体的不相关特征(如hooks 是由金属制成的),然后将剩余特征投射到本体(如hooks 会使两个实体之间产生有力的、痛苦的联系)。楚尔作为认知诗学的创始人,与莱考夫和约翰逊等人处在相同的历史时期,虽然他当时已经开始尝试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文学中的隐喻效果,但是受时代的局限及信息交流的限制,他并没有突破隐喻的传统修辞定义。
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开始,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对大量隐喻进行分析和研究后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隐喻,不但渗透在语言里,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2]。这样的隐喻被莱可夫和约翰逊等称为概念隐喻。根据他们的观点,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如温度、空间、动作等)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概念(如心理感受、社会关系、道德等),从而实现抽象思维的手段。
隐喻的本质是人们利用熟悉、具体的经验去构造陌生、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从概念发展的角度来看,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是主体在具体概念与具体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根据具身认知理论,概念知识是基于主体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身体经验是主体认识世界的起点。毫无疑问,主体同具体的客体进行互动时会获得多重感知体验,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事物的概念化的认识。然而,人的认知并不局限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表达,而是要认知、思考和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思想,人类要探索和认识复杂的抽象概念与思想,就必须借助已知的具体概念,将其映射(mapping)到未知的抽象概念领域,以通过具体事物来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与思想,把握抽象的范畴和关系。
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不仅使日常语言中的隐喻重新受到关注,也促使文学领域的隐喻研究进入了新局面。莱考夫和特勒(Lakoff &Turner)首先提出诗歌中的隐喻表达可以被看做是概念隐喻在文学中的运用,比如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As I walked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this world”就是概念隐喻“LIFE IS A JOURNEY”的实例。他们进一步归纳出诗歌中四种主要的隐喻创造模式:①扩大常规隐喻的使用;②使用特别的,非寻常的例子扩大意象图式;③质疑常规隐喻的局限;④合成多个常规隐喻来构成复杂的隐喻[11]。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诗人创新性地使用了我们日常使用的隐喻工具。与前面的论述相反,这种观点将日常语言中的隐喻看作是基础隐喻,文学中的隐喻被看作是基础隐喻的创新运用。
2 叙事中的隐喻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解释学家之一,马克·特勒(Mark Turner)是文学理论家、认知诗学的国际领军人物之一。他们二人都对故事和隐喻有深入研究,认为隐喻与叙事具有相似性特征。基于此,斯奈法尔(Stefán Snævarr)进一步提出,可能存在一种同时具有叙事与隐喻特征的混合物,并将其命名为“N—Ms”(叙事性隐喻)。笔者认为,隐喻与叙事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叙事作品之中包含了大量的隐喻表达;在宏观层面,隐喻的映射机制和类比逻辑是读者理解叙事作品的基础。
2.1 读者与人物
弗科尼亚(Fauconnier)和马克·特勒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不仅可以作为概念隐喻的补充,解释非常规隐喻,而且可以解释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读者如何能够赋予故事中的人物以意识。根据他们的观点,我们无意识地创建了一个自己与他人的整合空间[12]。在整合空间中,我们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对方身上,从而认为他人也具有相同的意识。根据体验哲学家的观点,人类的思维方式是隐喻。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可以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故事人物行为心理的理解采用的是“以己度人”的方式,即阅读叙事作品时,读者往往将自己当成故事中的某个人物。比如,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可能会将自己比作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种相对有意识的认知活动。另外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是:出于人的本能,我们会将人类的本能属性投射到故事中所有人物角色身上,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对异性的欲望、对食物的需求等。
隐喻是叙事移情和心智阅读的基础机制。如果没有隐喻的映射机制和类比逻辑,读者就无法把握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无法理解人物的行为,也就不会产生移情效应。读者对故事人物的感情色彩和好恶程度是读者心理与人物心理类比映射的结果,匹配度越高,读者对人物的好感就越强,反之,读者对人物的好感就越低。但是,叙事中的这种隐喻机制也有与概念隐喻理论相冲突的地方。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映射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单向映射,而叙事中的读者—人物映射是双向的,即读者将自己的属性映射到人物身上,同时也将人物的某些特征映射到自我。读者将自己与故事人物进行类比,这其实是一种认识、重塑自我的方式,即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认识自我。从这点来看,阅读叙事作品能够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自我修养。
2.2 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
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也是通过隐喻连接起来的,读者通过现实世界来理解故事世界。如果故事中所描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且在内容结构上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叙事作品是不可能被读者理解的。当然,正常情况下作者也写不出这种作品。现实世界与故事世界是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映射一般包括对象和结构两大类型。对象映射是指将现实世界中的各个元素映射到故事世界,包括现实世界的人和物以及人类思想、真理、规律、价值观、景观、场景、自然现象等。结构映射是指将现实世界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映射到故事世界,包括逻辑关系、程序关系、空间关系、时间关系、附属关系、功用关系、数量关系、大小形状关系等。但是这种映射并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通常只是部分对象和关系的映射,尤其是在虚构叙事作品中,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即使时间、地点和故事情节等全部相同,故事人物也不可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同名,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构作品。
叙事作品就像一枚棱镜,透过棱镜,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另一面。路易斯-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小说《暗夜旅程》(Journ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深渊般的别样世界,在那里“反话”是一种生存必备技能,这也是对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隐喻。
2.3 隐喻与寓言
除了读者与人物、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隐喻映射外,故事与故事之间也可以映射或整合。这种故事现象被马克·特勒称为“寓言(parables)”。换言之,“寓言”特指一种故事——该故事往往被投射到另一个故事[13]。此处的“寓言”概念除了包含汉语中狭义的“寓言”体裁外,还包括歇后语、谚语等,其主要特征是故事内容高度概括、涵义固定、适用面广。从概念隐喻的角度来看,寓言故事充当的是源域,其他故事充当的是目标域。将一个故事投射到另一个故事是与人类普遍认知密不可分的一种文学能力。寓言故事的存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认知负荷,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寓言。比如谚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我们可以用这个寓言故事指称另一个关于忠诚的故事:某个皇帝死了,他生前宠爱的某个大臣就出来争夺皇位。这时,寓言故事就是源故事(source-story),“忠诚”的故事就是目标故事(target-story)。读者通过将源故事中的核心要素映射到目标故事,从而理解目标故事。
3 《李尔王》中的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为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路径,特别是在解释语言表达形式与更高层面的文学想象结构之间的同一性方面。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源于身体经验的“平衡”(balance)和“连接”(Links)图式塑造了大量的概念隐喻,贯穿了整个文本,这些概念隐喻对读者理解整部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以莎士比亚《李尔王》的第一幕为例,阐释概念隐喻在文本理解中的作用。
概念隐喻理论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坚持体验认知观。体验主义者认为,隐喻的产生是将源域中的元素和结构投射到目标域的结果。源域是图式化的、间接性的身体经验。用约翰逊(Johnson)的话说,就是隐喻源于人类的体验性知识(embodied human understanding)[14],我们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具有一种最基本的图式化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从大量的身体经验中提炼出相同的抽象结构并找出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莎剧《李尔王》反映了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身体经验进行图式化的过程。例如《李尔王》中的著名台词“我是个所受惩罚超过所犯罪过的人(I am a man,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这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李尔王具有很强的公平观念,他认为在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他所遭受的惩罚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应得的。这种罪与罚之间的平衡是我们对公平最原始的理解,而这种抽象的理解跟我们身体平衡有关。水平面的平衡统辖了所有语言与非语言领域的“公平”。法庭上断案的依据是双方证据的分量轻重,目击者也可能会有偏私,所以古代西方法庭上代表公平的标志是一个盲人妇女手托一个双盘平衡秤。现实生活中这种平衡的图式化意象被投射到看似与之毫无关系的数学等量、视觉艺术等方面,从而产生了关于平衡的概念隐喻。“公平”概念源于现实经验中的“平衡”的观点解释了“我是个所受惩罚超过所犯罪过的人”这句话的认知机制。同时,这种“平衡”图式(Balance Schema)解释了爱德加的话“He childed as I fathered”。这句话体现了两个女儿施加给李尔的痛苦平衡了葛罗斯特施加给爱德加的痛苦(以及主角色与次主角色之间的平衡)。此外,“平衡”图式还解释了李尔对父女关系的错误理解。在第四幕第七场中,李尔醒来后请求考狄利亚说:“如果你有毒药为我预备着,我愿意喝下去。我知道你不爱我;因为我记得你的两个姐姐都虐待我;你虐待我还有几分理由,他们却没有理由虐待我。”李尔自始至终错误地用“平衡”图式来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但是考狄利亚没有用这种图式来理解父女关系,她说道:“谁都没有理由。”子女没有任何理由责怪自己的父母;反过来,父母犯了错,子女不应该为了公平再进行报复。《李尔王》中另一个重要的源域图式是“连结”图式(LINKS Schema)。该图式包含两个实体以及两个实体相互连接的关系。跟平衡图式一样,连结图式也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我们生而与父母具有血缘关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纽带源于生理、血缘上的联系,这种联系被进一步延伸为因果关系。当一件事紧随另一件事发生时,我们本能地认为这两件事具有因果关系。
大多数莎士比亚批评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在一开始的场景中就奠定了整个剧本世界的氛围基调,这两个重要图式正好证明了这一论述。实际上,这种基调是通过主要概念图式奠定的。在《李尔王》开场第一幕中,葛罗斯特对肯特介绍他与爱蒙德的父子关系这段话奠定了两个重要图式:“平衡”图式和“连结”图式。葛罗斯特跟李尔一样,他通过“孩子是财产”的概念隐喻来理解父子关系。葛罗斯特用“charge”一词来喻指对爱蒙德的抚养,而“charge”一词源于房地产行业。爱蒙德是一个私生子,给葛罗斯特的声誉带来损失,因此还算不上财产,只能算是消费品。爱德加虽然不是私生子,但是在葛罗斯特的眼中也没有差别。从剧本一开始,家族亲情关系就被贬低了。在这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剧本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内核则是“爱是投资”这一概念隐喻。因为爱是投资,所以谁给的收益大,李尔就在谁身上多投资,给予更多的爱,而李尔的爱也就是他的国土。反过来,大女儿和二女儿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国家,也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当李尔放弃王位,没有了权力,也就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因此大女儿和二女儿对他的爱也就越来越少了。在剧中另一对父子关系中,一开始就注定了爱蒙德后来对父亲的忤逆,不仅因为父子的联结关系,更因为爱德蒙与爱德加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主管与财务、儿子与女儿、私生子与合法子女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语言和情节都隐含着相同的认知结构:平衡图式和连结图式以及“爱是投资”的概念隐喻。
以往很多研究将《李尔王》的第一幕当作是一场审判或是爱的考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场景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审判的要素,如犯罪行为、法官、辩护人、陪审团、对立双方等。笔者认为,《李尔王》第一幕并不是一场审判,而是基于一个类似审判程序的财务审计场景的语义框架。这一幕的核心人物是李尔王,贯穿整个故事场景的是“子女是财产”“爱是投资”的概念隐喻。李尔将女儿们看作是资本。对投资者来说,投资是要有收益的,因此,在这个语义框架内,“孝心就是收益”,要定期对投资进行审计,看看是否获得应有的利润;还要对各项投资的收益额进行比较,有时还要对投资方案进行调整,对于收益高的项目要追加投资额度,对于收益不好的项目就要降低投资份额甚至放弃投资。李尔的很多关键性语言表达同时可以纳入到财务审计情景中:他想“divest”(“divest”有“出售”的含义)自己的权利、国土利益(interest of territory),于是将女儿们召集在一起,让她们“tell”有多爱他,最爱他的人就会分得最多的财产①财务审计制度是14 世纪才传到英国的,据文献记载,莎士比亚时代大多数审计人员还是文盲,因此当时的财务审计是口头形式,没有账本记录,“audit”一词源于拉丁语“audire”,意思是“听”。。这一语义框架使我们将这一场景理解为资本投资过程,收益高的一方就会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低的一方将得不到投资。在李尔眼里,抚养子女就是投资。现在女儿们长大了,该是计算收益的时候了,每一个女儿都说出自己对父亲的爱,李尔通过听(审计)女儿们的汇报,对第一轮投资进行决算,根据第一轮投资的收益情况决定第二轮投资,即划分国土。因而,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极力夸大自己对父亲的爱,他们遵循了李尔的语义框架,在回答中使用了大量多义词表达,如“dearer”“beyond what can be valued”“makes breath poor”“metal”②根据莎士比亚的使用习惯,metal 一般指金子,等同于gold metal。“prize me at her worth”“comes to short”③源于财务审计的一个习语。。这些表达既有亲情意义,也有金钱方面的意义。
在财务审计情景中,另一个概念是“Balance”。“Balance”也是一个跟审计密切相关的概念,有“收支相抵”“债务抵消”等含义。李尔想通过财产分配来“balance”女儿们对自己的爱,充分暴露出李尔执着于约翰逊(Johnson)所说的“道德数学”(moral mathematics),即抚养子女的心血付出可以用数量来计算,这个数量应该和子女表达出来的爱保持平衡。因此,当考迪利亚回答“nothing”的时候,李尔说道“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李尔对“nothing”的理解是一个数字“0”,所以根据审计中的平衡原则,考迪利亚就应该一无所有。
4 结语
概念隐喻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家之宝,也是认知诗学的重要理论工具。概念隐喻理论为文学文本分析提供了一套具体有效的概念和方法。传统研究虽然也能对《李尔王》中的隐喻表达进行描述,但是只能停留在语言修辞层面,难以与悲剧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理解联系起来。笔者通过对概念隐喻理论本身以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李尔王》中的“平衡”图式和“连结”图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概念隐喻“子女是财产”“爱是投资”,试图说明概念隐喻理论不仅能够对这些表层语言进行描写,还能够更深层次地解释这种语言背后的认知机理,用同一套理论机制解释整个文本不同结构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笔者看来,这种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工具的文本分析比纯粹的印象式批评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