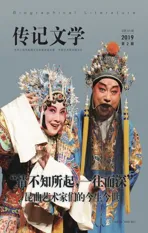“关于小说选材的问题”
——茅盾、鲁迅1934年7月14日联名致伊罗生函
2019-02-21北塔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伊罗生先生:
来信收到了。关于小说集选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
Ⅰ.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Ⅱ.龚冰庐的《炭矿夫》,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好。这一篇,我们已介绍给您。
Ⅲ.由一九三○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近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候姚女士和您的好!
茅盾 鲁迅
七月十四日
再: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载在《二心集》内。又及
一
在茅盾留世的众多信件中,有3封信颇为特殊。因为这3封的落款人都是茅盾和鲁迅联名,收信者是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在中国做记者的伊罗生[原名哈罗德·R.伊罗生(Harold Robert lsaacs)]。
伊罗生之前在上海主持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不时会刊发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译。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伊罗生有个比较大的设想——利用那些已经在《中国论坛》发表的作品,再扩充一些,选编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小说集,主要是中短篇,然后拿到美国去出版。一开始,他给这部书拟的名字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后来,他又从鲁迅的一篇演讲中吸取灵感,将书名改为《草鞋脚》,征得鲁迅同意而确定。”(见黎辛:《我常想起伊罗生》,载《百年潮》2001年第8期)
那么,伊罗生为这本英译中国现代小说集取名“草鞋脚”的灵感,是受了鲁迅哪一篇演讲的激发呢?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讲演,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观众达2000余人,不得不临时改为露天举行,这是鲁迅一生60多场公开演讲中最为轰动的一次。
鲁迅在演讲的开头说:“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前进,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
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所兴起的是文学革命,1930年左右所发起的是革命文学。前者的主体是西装先生,后者的主体是下等人。他高度概括而又无比生动地分别用“皮鞋”和“泥腿”来形象地指称两种不同的主体。
“泥腿”或“泥腿子”指的是农民,因为农民在庄稼地里忙碌时,免不了让泥水弄脏了衣裤和身体尤其是双腿。在所谓城里人和自命高贵的人嘴里,这个称呼带有贬义。有时农民们光着脚,有时穿着鞋子,当然不可能是皮鞋,只能是自己编织的草鞋。伊罗生可能由此得到灵感,用草鞋去对应皮鞋,“草鞋脚”的英文名为“Straw San d a ls”,这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语境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贴切而形象的书名。
为了选编《草鞋脚》集子里的篇目,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不打算当记者了,准备集中精力编译中国现代进步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请注意,这里虽然说是“编译”,但其实伊罗生主要负责编选,而译的工作则是他请别人做的(参见戈宝权:《谈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文献资料刊物《文献》1979年第2辑)。因此,有些人以为伊罗生是《草鞋脚》的译者是错误的。
伊罗生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以及一份关于中国左翼期刊的介绍。为此,伊罗生在上海时还专门去鲁迅府上拜访、讨教。选目初稿由茅盾拟定、鲁迅审定之后,寄给伊罗生。此间顺便提一下,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说,他“拟定的选目包括二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作品”,这个记忆有误,从后来重新发现的他的手写稿复制件上看到,应该是27篇(参见戈宝权:《谈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开创性意义的翻译出版选题,鲁迅和茅盾都认为非常有价值;况且,从当时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把‘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有才华而国外无人知晓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这将有益于推动革命文学力量的发展壮大,并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了解。于是,鲁迅和茅盾开始热心地以实际行动支持此事,“对伊罗生提出的要求,决定尽量予以满足”。
1934年3月底,伊罗生夫妇俩从上海迁居到北京,继续未完成的编译工作。两个月以后,伊罗生给鲁迅写了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封信。从此,双方开始用通信的方式讨论选编工作,主要是来回磋商哪些该选、哪些不该选。对于鲁迅和茅盾给出的选目,伊罗生并没有全部采用,他更倾向于1918年之后发表的、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而非鲁迅和茅盾建议的刚刚进入文坛的“下等人的泥腿”的作品。而其实,鲁迅与茅盾二人建议伊罗生入选的是1930年之后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所谓“新兴普罗文学”作家作品。
伊罗生在1973年4月为英文版《草鞋脚》重写的“引言”中说:“这些短篇小说是在鲁迅和茅盾的指导与商议之下编选出来的:鲁迅就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和主要的创作家之一;茅盾则是他的年轻的朋友和同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作家当中仅次于鲁迅本人的最重要的作家。”但英文版《草鞋脚》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74年推出时,副标题为《中国短篇小说(1918-1933)》,封面上所署编者名只有伊罗生一个人,并没有鲁迅和茅盾,也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80年10月,伊罗生应邀再度访华时,还专门去看望茅盾。1981年,以鲁迅和茅盾二人所定的选目为基础,再加上后来他们跟伊罗生通信中追加推荐的3篇,一共30篇,由蔡清富编定,再由茅盾审定并作序,以《草鞋脚》为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是为中文版《草鞋脚》,封面上编者署名为鲁迅和茅盾。

编者署名伊罗生的英文版《草鞋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述伊罗生的信一般都寄给鲁迅,有的由鲁迅个人直接回复,有的是鲁迅和茅盾商量之后由茅盾执笔然后鲁迅加上签名的方式回复。双方目前留下来的来往书信加起来总共6封,彼此各3封。万树玉在其所编《茅盾年谱》中说:“伊罗生就该小说集的选编问题,和鲁迅、茅盾通过四次信”,数量上是不对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鲁迅、茅盾选编《草鞋脚》,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戈宝权曾对这些书信有过全面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但笔者在拜读他的长文《谈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之后,发现两个问题:1.他的解读是以鲁迅为主角或者说中心,伊罗生和茅盾则为配角。2.他对有些作品,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读者已经陌生的作品缺乏介绍。笔者以为,就双方之间的全部通信或者说鲁迅本人单独写的信而言,以他为中心解读是合理的。但是,就鲁迅和茅盾联名的3封书信来说,则茅盾的比重更多一些,因为这些信都是由茅盾执笔所写,大部分内容表达的也都是茅盾的意思,鲁迅只是签名并提供了少量意见。因此,本文仅以两人联合署名的其中一封作为样本,以茅盾为中心,进行补充性的解读。
二
对于伊罗生来信谈“小说集选材的问题”, 茅盾和鲁迅于7月14日联名复信给出几条建议。首条是,与其选蒋光慈的《短裤党》,不如选蒋的短篇小说,茅盾和鲁迅认为《短裤党》歪曲了“当时的革命人物”,“写得并不好”。
《短裤党》是蒋光慈于1927年4月初完成的中篇小说。以现在的小说分类学来看,这是一部纪实小说。这是最早正面描写中国工人运动的作品,及时反映了上海工人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3次武装起义的情景,塑造了如杨直夫(原型为瞿秋白)、史兆炎(原型为赵世炎)等工人和革命者的形象。
那么,蒋光慈在《短裤党》里歪曲的“当时的革命人物”包括瞿秋白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蒋光慈是将瞿秋白写进文学作品的第一位作家,两人曾经是亲密战友。据马德俊撰写的《蒋光慈佚文考论》,瞿秋白参与构思了《短裤党》,并为本书定名。因此,于情于理于事,蒋光慈都不可能歪曲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革命人物的光辉形象,更不用说是歪曲瞿秋白的清白形象了。
之所以在信中不建议伊罗生选蒋光慈的这篇《短裤党》,或与茅盾对蒋光慈作品的看法有关,在《〈地泉〉读后感》中,茅盾就曾借批评阳翰笙的《地泉》小说三部曲而有所发挥,“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分析、批判蒋光慈的作品”。茅盾认为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文学的通病——在于人物形象刻画上的“脸谱化”和结构艺术上的“程式化”(参见《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115页)。虽然他在与鲁迅联名给伊罗生的书信中,对蒋作品的态度,表达得相对比较委婉和客气,但由两人草拟出来的初选作品共24人27篇,其中并没有蒋光慈的任何一篇,甚至连蒋的“比较好些”的短篇小说都没有入选。
不过,在最终的《草鞋脚》英文版中,伊罗生虽然放弃了《短裤党》,但还是选了蒋的另一短篇小说,英文译名为“H assan”。这篇从内容上看是写上海的一个印度巡捕的。当年在上海滩,人们喜欢把印度巡捕叫做“红头阿三”。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篇是蒋写于1929年的《阿三》。译者把题目“音译”为“Hassan”,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好看的、英俊的”,印度人却很少用它,这种译意跟含有贬义的“阿三”正好相反。
茅盾和鲁迅给伊罗生的小说集选材的第二条建议是,与其选龚冰庐的《碳矿夫》,不如选楼适夷的《盐场》,这其后有什么深意吗?
先说龚冰庐的《碳矿夫》。龚冰庐(1908-1955),江苏崇明(今上海市)人,他原是山东某矿的管理人员,熟悉矿工生活。“早在1927年……龚冰庐就写出短篇小说《炭矿夫》《裁判》《矿山祭》等,成为我国描写煤矿生活小说第一人。”(见庞崇娅:《煤矿是文学的富矿》,载《阳光》2018年第11期)《炭矿夫》是龚冰庐的代表作,以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为线索,父亲是煤矿大罢工的组织者,罢工失败后被枪杀,孩子才8岁就到矿上当童工,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并炸毁了矿区。此篇曾与《裁判》和《矿山祭》两篇一起,以短篇小说集形式出版,书名还是《炭矿夫》,1929年3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龚冰庐本来是创造社成员,曾在《创造月刊》等多种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炭矿夫》最初就发表于1928年2月发行的《创造月刊》第2卷第2期。
是否因为鲁迅和茅盾与创造社曾有过节,而牵连到对龚冰庐及其作品的看法呢?这种推测似乎不能成立。因为,1930年3月2日,龚出席了由鲁迅和茅盾大力支持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成为“左联”发起人(最初的盟员)之一;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密令查禁左翼和进步书籍149种,龚的短篇小说集《炭矿夫》《黎明之前》两书也在列。由此看来,至少在他后来当汉奸以前,他在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上,跟鲁迅和茅盾还是比较靠拢的。
再看他们推荐选入的楼适夷的《盐场》。这是楼适夷以笔名“建南”发表于《拓荒者》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上的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以庵东盐场为原型,深刻反映了当地盐民的生活、苦难与斗争,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楼适夷与茅盾相处甚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香港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盐场》一篇是鲁迅和茅盾在这封信里追加推荐的。在第一批名单里,他们推荐的不是这篇作品,而是楼适夷的另一篇小说《死》。楼适夷的这两篇作品最终都被伊罗生选入英文版的《草鞋脚》。
那么,如何来理解茅盾和鲁迅给伊罗生的小说集选材建议中对于蒋光慈和龚冰庐作品的看法呢?

关于此,两人介绍选入“一九三○年至今”的左翼“新近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的建议,是有力的明证。
何谷天,原名何稻玉(1907—1952),四川荥经县人,幼年丧父,中学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1933年任“左联”执委、组织部部长。在鲁迅的鼓励下,他根据自己在军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雪地》;鲁迅又把这篇作品推荐给茅盾,发表于民国22年9月1日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茅盾在编发这篇作品时,以笔名“惕若”写了编后记《〈雪地〉的尾巴》,其中写道:“在这一期上,我们刊载了何谷天的《雪地》。这位作者,大约二十多岁,可说是一位‘文学青年’,以前他有没有做过小说,我们不知道;他这名字是很生疏的。”
沙汀曾任“左联”小说组组长,1934年已任“左联”执委,与茅盾保持了一生的友谊,直到晚年还与茅盾往来、通信。推荐选入其的《老人》一篇,发表于《文学》第 1 卷 2 期(1933 年 8 月1 日) ,这篇与《航线》《平平常常的故事》等类似,是反映土地改革及劳动人民觉醒的作品。
欧阳山,1932年组织中国“左联”广州分会,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曾任小说研究委员会主任。鲁迅和茅盾推荐的欧阳山的作品是《水棚里的清道夫》。茅盾对欧阳山其人其作的推介是这样写的:“欧阳山,广东人,曾经在广州作文学运动而被官厅注意,不能在广州立足。他的小说曾经收集在一个短篇小说集内,可是这个短篇集现在也被禁了,那时他写小说用的是笔名‘罗西’。这是他最近的作品,背景是广州。此篇曾首发在1933年10月出版的《文艺》创刊号,《文艺》是在上海出版一个左翼的文艺刊物,只出了三期,即被禁止。”从“左翼”和“被禁”等关键词中可以看出茅盾之所以欣赏并推介欧阳山,或是因为其人及其作品的反抗精神与进步意识。正如鲁迅在1934年3月23日为英文版《草鞋脚》所写的序言中所说:“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草明,原名吴绚文,生于广东顺德,在广州读中学时,即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31年开始文学创作。与欧阳山为文坛伉俪,曾参与后者创办的进步刊物《广州文艺》的编辑工作。她因作品揭露旧制度而被通缉,1933年逃往上海,并加入“左联”。茅盾推荐的是她的第一篇小说《倾跌》。这篇作品是她到上海后写的,作品通过描写两个失业女工沦为娼妓的悲惨遭遇,控诉资本家的残酷和贪婪。茅盾给这篇作品所写的推介语说:“草明女士年纪很轻,可是她的作风已经很成熟。”
张天翼,1929年正式开始写作生涯,1931年加入“左联”,与沙汀、艾芜等并称为“左联”新秀。所推荐的是他的《一件寻常事》。这篇小说首发于1933年7月1日刊行的《文学》杂志创刊号。关于《文学》创刊号,朱自清曾撰写专文发表在7月24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0期上,署名“言”。他在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该刊虽貌似名家如林,但作品几乎乏善可陈,“旧《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及常常为该刊撰稿之傅东华诸人,近以‘文学社’名义,编辑一文艺杂志,定名《文学》。其创刊号已于七月一日出版,凡昔与《小说月报》关系较切之作家,几皆见于是册,以是卷帙颇巨。惟内容则未见精彩。就创作小说言:茅盾之《残冬》为《春蚕》《秋收》之续,然用意、布局、描写手腕皆不逮前作。圣陶之《多收了三五斗》及巴金《一个女人》均草率无足道。而郁达夫《迟暮》,王统照《乡谈》二篇结构单纯,直难作小说读。王文艺术尤劣。”不过,对“新手”张天翼的作品,朱自清却在是文中赞赏有加:“是册中惟张天翼之《一件寻常事》状一失业工人之贫困,至鸩其病妻,以减无力医药之苦,最为力作。全文但就工人之稚子目中写出,益显真切。”(转引自孙玉蓉:《朱自清的三篇集外佚文》,《博览群书》(2011年第12期)茅盾曾评说张天翼及其作品:“意识上是前进的作家,形式上它有它新奇的作风。”
然而,遗憾的是,除了何谷天的《雪地》一篇被伊罗生选入英文版《草鞋脚》外,鲁迅和茅盾所推介的沙汀、草明、欧阳山、张天翼的作品均未被伊罗生选入这部小说集。
三
在7月14日的回信末尾,茅盾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因此向伊罗生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其实,茅盾一开始拟定的选目中自己的作品选的是《大泽乡》和《春蚕》两篇,但伊罗生认为,茅盾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仅次于鲁迅,既然鲁迅的作品选了5篇,茅盾的作品至少得有3篇,他向茅盾提出选《春蚕》《秋收》和《喜剧》3篇。那么,伊罗生为何不选茅盾自己建议的《大泽乡》,而以《秋收》和《喜剧》两篇取而代之呢?对此,伊罗生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大泽乡》是茅盾连续创作的3篇历史小说之一(另两篇是《豹子头林冲》和《石碣》),1931年以笔名蒲牢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2卷第1号。“蒲牢”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为龙生的九子之一,善音好吼,洪钟上的龙形兽钮是它的形象。茅盾对取这个笔名的用意作过一番解释:“意在暗示蒋介石的文化围剿虽日益酷烈,但左翼文坛成员仍要大声反抗,无所畏惧,且反抗之声要愈传愈远。”(《我走过的道路》中册)

不过,茅盾一向谦虚,当他得知伊罗生打算选入他的3篇作品时,他却提出将《秋收》去掉,建议只选《春蚕》和《喜剧》两篇即可。《春蚕》和《秋收》是“农村三部曲”里的两篇(另一篇是《残冬》),读者对此较为熟悉,相比之下,《喜剧》则不那么有名了。
茅盾的短篇小说《喜剧》作于1931年,以何典为笔名发表于1931年10月发行的《北斗》第1卷第2期上。故事讲述的是,某青年在大革命期间因为散发传单而被捕,被关在上海的“西牢”——帝国主义租界内的监狱里,度过了5年的铁窗生活。刑满释放以后,他发现“革命”已经成功,“青天白日满地红”,然而却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最后只好决定冒充“共产党”自首,重新回到牢监里去,以便解决“住与食”的问题。很明显,茅盾借鉴了欧·亨利的名篇《警察与赞美诗》的结尾。“喜剧”与“赞美诗”一样,都是反用其意,以跟小说中的事实形成对比,达到某种反讽效果,所谓“悲凉的喜剧”、“带泪的笑”。
不过,伊罗生最终还是坚持己见,把3篇全部收入了英文版《草鞋脚》中。而至于信的末尾“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的提议,伊罗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30年3月2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在演说中告诫“左联”人士,要防止右倾,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鲁迅特别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在演说中也对“左联”工作提出4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的这篇演讲对于“左联”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此,伊罗生提出要将此篇收入《草鞋脚》。根据鲁迅、茅盾、伊罗生三人一开始对这部小说集的预设,他们要编的基本上就是一部与“左联”密切相关的小说集,而收入鲁迅的这篇演讲,作为附录,对读者理解集子里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无疑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所以,鲁迅和茅盾于信中告诉伊罗生这篇演讲稿收在《二心集》里,应该是要他自己根据提供的出版信息去找。但不知为何,伊罗生最终并没有编入鲁迅的这篇演讲稿。
此外,在7月14日的这封回信中还有一条信息,即茅盾和鲁迅问候的“姚女士”。此人是伊罗生的新婚夫人姚白森,原名维奥拉(Viola Robinson),姚白森是她的中文名。伊罗生来中国前,两人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后来,姚白森不远万里独自乘船从美国来到中国,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不久,二人离开上海,择居北京,姚白森在一所中学里教英文,1980年还在宋庆龄邀请下重访中国。鲁迅和茅盾两人当年联名给伊罗生的几封书信,几乎每封最后都会客气地问候她。
行文至此,不由得感慨,中国文坛两位伟大人物联名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封300余字的信文中,隐藏的内涵何其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