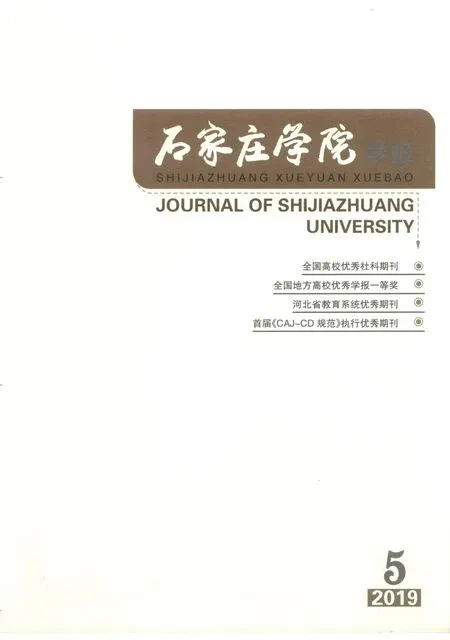论《启蒙辩证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2019-02-20刘光斌
刘光斌,张 翼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按照统治自然模式来设想的话,主要指人与外界自然的统治关系,人与内在自然的统治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作为人性自然的统治关系。维格豪斯(Rolf Wiggerhaus)认为:“《启蒙辩证法》的主旨是:全部文明的合理性的核心就是对自然的统治。”[1]91那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为什么要统治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采用自我持存原则检视人与自然关系,认为《启蒙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反映了人与外界自然、内在自然和人性自然的统治关系。虽然他们过分渲染了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且与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观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启蒙辩证法》中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及其工具理性逻辑,从生态批判、社会批判和历史哲学层面认识和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后续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的自我持存与人对外界自然的统治关系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人类与外界自然的关系。他们用启蒙批判神话,认为从神话向启蒙的转变伴随着作为类的人与外界自然关系的转变,人与自然关系从自然控制人到人统治自然的转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启蒙转变为新的神话的分析中指出,启蒙对外界自然的统治与神话自然中外界自然对人的统治逻辑具有同一性。他们认为:“神话自然与启蒙对自然的统治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2]前言5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解释了神话自然的形成、神话自然转向启蒙统治自然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自我持存原则,从而把历史的文明进程解释为一个人类逐步摆脱自然统治和不断完善人类统治自然的过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释了神话自然的产生以及神话自然统治人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人们用神话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是早期人类无法认识自然现象,并对那些自然现象产生惧怕的心理。虽然自然现象获得了神话的解释,但神话通过幻想使人们失去了自主,强大的自然在早期的人类面前被神秘化,便形成了神话自然。神话实际上只是早期人类解释自然的一种方式而已,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ánes)批判的那样,神是人塑造出来的,是人的复制品,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并把人的性情附加在神身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神话人物都可以还原为人类主体,折射出早期人类看待自然的方式,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2]4,也可以说,“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2]4。不过,在原初意义上人类并没有把握精神实体——神的存在,只是正视了个体面对的自然之物,当人们遇到他们不熟悉的恐怖之物时总是发出惊呼,惊呼之词便成为该物的名称。“它总是在与已知事物的关系里确定未知事物的超验性,继而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化为神圣。”[2]1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了神话自然产生的根源,即人们出于恐怖和无知,用神话解释自然界中的陌生之物,恐惧的表达变成了解释,而实际上人们不可能摆脱恐惧,神话成了自然统治人的替代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清楚地意识到早期人类对自然的神话解释带有泛灵论的色彩,以至于他们认为“唤醒世界就要根除泛灵论”[2]3。具体的做法就是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重视工具理性的作用。多德(Nigel Dodd)指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增长来自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3]81依据多德的观点,人们只有依靠工具理性才能摆脱自然对人的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说:“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2]11
人类只有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对自然的恐惧,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注到了理性的力量。他们引用培根(Francis Bacon)的观点:“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2]2人类能够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把握越来越多的自然规律,运用理性克服迷信,人类用理性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于是自然失去了原来的魔力。人类用知识、理性对神话自然祛魅之后,利用工具理性征服自然,进入到启蒙对自然的统治之中。马儿图切利(Danile Martuccelli)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理性和统治连接在一起的根源就在人统治和支配自然的愿望中”[4]205。随着知识的进步、启蒙工具理性的兴起,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征服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逐渐地改变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做法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即由人臣服自然、畏惧自然转向人统治自然和人统治人,“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2]2。启蒙用知识消除人们对自然的恐惧之后,早期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转化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不过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神话自然对人的统治和启蒙对自然的统治在统治产生的逻辑上取得了一致,只是关系颠倒了而已。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神话自然向启蒙统治自然的转化进程,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转变进程,即从臣服自然到统治自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自我持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我持存“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2]23,他们认为人类恐惧自然并服从于神话迷信的统治,是出于自我持存的需要;启蒙用理性取代了迷信,人类统治自然并工具性地对待自然,同样是出于自我持存的需要。不变的是人的自我持存的目的,变化的是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已经成为人类统治自然的重要工具,从自我持存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变得尤为重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2]23人类出于维护人的自我持存的需要,借助理性反对迷信对人的统治的同时,也用理性去统治自然,所以,自我持存“正是在其培植理性,同时也是罢黜理性的过程中形成的”[2]25。理性把人们从臣服自然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统治自然的泥潭之中,因此,人们只是在臣服自然和统治自然之间进行选择,在神话的迷信与启蒙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从人类自我持存的生存论考察人与外界自然的关系,现代文明的发展可以视为是人类统治自然的过程,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人们必须通过工具理性统治自然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为“外界自然是生存抗争的舞台”[1]87-88。人类必须依靠外界自然才能生存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靠自然界生活。”[5]56启蒙自然解释了人类为了自我持存的目的统治了自然,人与自然的权力关系在形式上颠倒过来。
二、个人的自我持存与人对内在自然的自我规训关系
在《启蒙辩证法》中,个人主体的历史可以视为人与外界自然打交道历史的补充现象,表现为人在改造外界自然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伸张,不断获得自我确认,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看成人与内在自然的关系。在早期人类惧怕自然的背景下,人遭受漠视,人的内在自然受到压抑,而在启蒙工具理性的召唤下,人的地位得到重视,人以工具性的方式控制外界自然。当人们乐观地憧憬一个适合于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到来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指出,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人们将不得不对自己的内在自然进行规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释了祭祀活动中的牺牲和启蒙的自我持存及其关系,并论证了个人出于自我持存的需要而对自己的内在自然进行了规训。
在神话自然中,个人对自然危险采取单纯消极防御并服从自然的方式,反映在祭祀活动中就是人们向神灵供奉牺牲。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最初人们依靠感知和直觉行动,依靠神的启示、仪式和巫术而行动,以抵御自然的危险。他们重点分析了祭祀活动,认为在祭祀活动中人类向神供奉了大量的牺牲,祭祀活动“变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合理交换的巫术模式”[2]41,尽管人和神的交换活动纯粹是象征意义上的,但牺牲“变成了一种人支配神的工具”[2]41,人们为了达到让神服从人的目的而向神供奉牺牲。霍耐特(Axel Honneth)把祭祀和巫术看成是集体导演的一种模仿,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危险的单纯的消极防御。他说:“巫术是集体导演的一种模仿。这种人为地使群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做法,履行了这样的功能,即通过虚构来减轻实际上不可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危险的影响。”[6]37启蒙取代神话后,人采取了积极统治自然的方式应对自然危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祭祀供奉的牺牲与人的自我持存的合理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神话世界中的神灵鬼怪、仪式、巫术逐渐被启蒙的科学知识和理性等取代,导致“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2]42。人们借助于技术性的知识从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开始进行重复性的、有规律的依据计算和权衡而采取的行动,并发挥统治自然的作用。
随着神话自然向启蒙对自然统治的转变,理性得到高扬,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提升,当人类以控制自然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人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人最初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对外界自然产生恐惧,现在由于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们把自己看作主体,自然则被看成是主体作用的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尽管自我从盲目的自然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但自然的支配权还依然在牺牲中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2]44为什么会这样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我持存虽然取代了牺牲,但仍然像牺牲一样,不过是一种交换而已,不过这一次是以人自己否定内在自然为代价。他们指出:“由于人的自然被否定了,因此,不仅控制外部自然的目的,而且人类自身生命的目的,也都遭到了歪曲。”[2]44意思是人不仅畏惧外界自然而且也畏惧内在自然,人们为了自我持存就需要自我束缚,这种自我束缚就类似于祭祀活动中人把自己作为牺牲,只是人们是用理性对自己的内在自然进行束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2]44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旦人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就变得毫无意义。“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自我持存所支配、压迫和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2]45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了人对自然危险的单纯消极防御和积极统治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说:“启蒙摧毁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2]8也就是说,在神话中,人们用仪式、巫术反复强化了对自然臣服和对人的统治,现代人们通过运用理性掌握自然规律来统治外界自然,此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内在自然受到控制的过程。因为一方面,人们依靠内在性原则,通过作用于自然,从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概括出事物的规律并自认为掌握了统治自然的规律,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必须按照规律采取行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们把规律看成他获取自己生计的手段,这其实就是“把自我持存当作适应手段”[2]8-9。神话转变为启蒙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人与外界自然的关系,即人类从臣服自然到统治自然,也改变了个人与他的内在自然的关系,人们依据经验直觉行动到依据理性行动,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个人的自我规训过程,人们通过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也要求主体依照规律行动。可见,神话的内在原则成为启蒙的内在原则,只是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把神的启示和仪式强化的主体意识认同的形式转变为主体自觉接受规律约束并依据规律行事,这产生了颇为吊诡的现象,人确立主体地位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自由受到约束的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的现象?这是个人出于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采用理性对自己进行了自我规训的结果。维格豪斯指出:“只有懂得自我规训的人才能生存下来。”[1]88个人为了自我持存的需要应该遵从自然规律活动,人们控制自然、感知和体验世界,意味着自我控制的主体的确立,人们因为成功的自我控制而把自己视为主体。出于人的自我持存需要,只有摆脱自然界中为生存需要进行的斗争,人的主体地位才能确定下来,自我规训的人才能依靠理性或科学知识去统治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辩证法》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公式是“靠控制内在自然的主体来控制外界自然”[1]88。因此,神话自然对人类的统治和启蒙对自然的统治都是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规训来实现的。
三、社会的自我持存与人对人的人性自然的统治关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了人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看成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作为人性自然的关系,把社会看成是非人的自然过程,他们认为:“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2]前言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基于社会统治的历史哲学的考察,分析了社会分工及其强化的自我持存,指出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人统治人和社会统治自然的现象。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社会分工出发分析了早期社会维护自然对人的统治以及社会对人的统治关系。他们分析了早期的社会分工及其产生的权力关系,表现为人臣服自然和世俗权力对人的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祭祀和巫师成了解释神话的大师,为了维护神话权威而与世俗权力结合起来。他们指出:“谁要是损害了符号,谁就要以超自然权力的名义,将其置于它的世俗权力的支配下,而经过筛选的社会机构正是这种世俗权力的体现。”[2]15在早期的社会分工中,祭祀、巫师们、各种社会机构以及违反符号的人各自在神学世界中代表不同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神圣存在把它的本性移植给它‘私交甚密’的巫师”[2]16,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认为祭祀和巫师们“被视为神灵之物和道德义务的共同体规范的唯一诠释者”[7]175。祭祀和巫师们使用神话语言,象征着神对人们的命令,由于社会机构是为了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因此,遵从祭祀和巫师们的仪式和神话语言既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臣服,也反映了人们对特权者代表的普遍社会权力的惧怕,谁若违反了宗教禁忌就会受到来自神灵的惩罚,实际上就是遭受世俗权力的制裁。
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反映出社会统治自然和社会统治人现象的出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了在游牧生活的早期基于性别分工男女所从事的劳动,“男人狩猎,女人则从事无需严格管制的劳作”[2]16。部落成员以个体方式影响自然的进程,自然的演化过程被视为必须服从的规范。在游牧生活的后期,统治正以社会结构的方式呈现出来,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为统治者和被征服者,被统治者总是在压迫下进行劳动。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反复出现、永远相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2]1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由统治发展而成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2]16,被统治者要生存下去必须服从权力的统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决定了文明进程,并进一步加深了权力与服从的分化。“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由此形成了对自然的工具性关系的诸多方面,随后产生了施令者和听令者,即预先确定目标的人、脑力劳动者,与执行者、体力劳动者。”[1]89这种社会分工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反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社会统治外界自然的方式和社会统治人的方式作了类比,“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2]6,人们用科学对待万物就是为了统治自然,统治者只有了解人才能更好地去统治人。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发展到极致,“以统治关系和财产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机制变成物化的虚假自然关系”[8]125。社会一方面强化了对自然的统治,“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前言4,另一方面财产关系强化了人对人的统治,“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2]前言4。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影响了社会自我持存,对资本家而言,劳动能够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2]23;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已,“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2]23。于是,我们能够看到资产阶级不再把生存当作基础,已经完全成为施令者,他们习惯于组织和管理,而与具体生产劳动越来越远,也就是远离了自然。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要谋求生存,自我持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无产阶级作为劳动者非常接近自然,但是不能享受劳动的快乐,只是统治自然的工具,这是因为“他的标准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2]22。就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维系而言,商品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追求都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必然导致对自然的统治和破坏。正如库克(Deborah Cook)所说:“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生存,我们把自我持存的任务交给了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继续通过征服外界自然和内在的、本能的自然来保护自己。”[9]437
霍耐特指出:“在社会劳动中,人类把对自然过程的实际控制作为尺度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生活,而批判的活动却恰恰对社会的这种自我持存过程的既有组织方式提出质疑。”[6]13因此,从自我持存的历史哲学层面分析,社会分化为少数拥有特权的精英和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大众,从人无力统治自然的这一阶段看,这种社会不平等是无可替代的进步力量,为全社会在以后挣脱自然的桎梏及其对人类生存的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随着人们统治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条件也得到改善,但并没有改善社会统治的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自然统治程度的提高,并不是摆脱社会统治的必要条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统治自然是为了人的解放,实际上他们只是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人被统治的原因,人们用统治自然的同样方式控制了自身和他人。人们看到对外界自然的控制越来越高效,自我规训的主体就越远离自然,主体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化自然,社会统治就越来越严密,主体就越发与主体针锋相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垄断了一切经济决策权和政治决策权,个体的自主性遭到更大程度上的约束。霍耐特指出:“人如今作为他自己理性的牺牲品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这种无主体的对策性和技术性思维的系统。”[6]33可见社会自我持存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解脱,而是社会结构的持久稳定,社会自我持存产生的结果是使每一个人成为统治对象,社会统治结构变得更加稳定。
四、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及其后续影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采用自我持存原则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霍耐特那里得到印证。他说:“《启蒙辩证法》勾勒的不是人类支配自然的那种解放过程,而是理性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论证依据的是这样的信念,即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为主体的自我持存服务的。”[6]33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解释为三种统治形式;作为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在人类自我持存的要求下把其自然环境抽象为可支配的事物;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在个人自我持存的要求下规训了人的内在自然,个人只有进行自我控制才能顺应生存的需要;社会与自然和人的关系表明在社会自我持存的要求下,不仅自然环境被客体化,而且人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权力的控制。所有三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都被解释为统治关系,这与《启蒙辩证法》的总体悲观论调保持一致。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对此也作出了评论:“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人受到的不断强化统治的根源,最终说来就在人和自然最初发生的分裂中,在这种分裂导致的统治愿望中。”[4]206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的解释与现代人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范大相径庭,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自我持存原则解释人与自然统治关系的观点及其后续理论影响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解释为遵循工具理性的统治关系。斯通(Alison Stone)认为阿多诺主张“所有的理性和认知都是工具性的,它们的作用是研究人类如何能够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即满足其自我持存的兴趣”[10]237。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确实是从工具理性角度讨论人的自我持存,认为工具理性的应用使人摆脱对自然的恐惧,从而人统治自然变得可能。为了使统治自然变得可能,人们必须从内心接受理性的思维方式,使自己的行为按照规律办事并进行自我约束。“对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征服就会成为人类生活的绝对目的。”[2]2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为了自我持存或生存的需要必须使自己符合职业的需要、满足生产车间的生产需要,人们越来越受制于他们的对象化,也就是受到作为人化自然的社会的统治。正如霍耐特所说:“人类借助于工具思维的原初历史冲动而学会对付自然,而这种工具性思维的原初历史冲动被逐步移植到规训人的本能、弱化感知能力以及构造社会统治关系的过程之中。”[11]32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三种统治形式的模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工具理性原本作为人类支配自然和控制自己的理性工具,已经转变为大工业的自我维护的工具。霍耐特认为人统治自然的三种形式都遵循了工具理性逻辑:“《启蒙辩证法》描写的是从对自然过程的那种工具性支配的人类历史步伐中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6]95
第二,人与自然统治关系的后续理论影响。《启蒙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统治关系的后续理论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予人们理解当代生态问题的理论意义。《启蒙辩证法》对人与外界自然关系的论述很好地预见了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预示了从生态角度反思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动机”[8]126,人类无节制地控制自然、消耗自然资源,破坏了人们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因此,必须改变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强调对人与第二自然关系的社会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自我持存不仅体现在物质世界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而且体现在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语言符号交往中。库克认为哈贝马斯“重新定义了自我持存,使交往行为成为今天个人自我持存的主要手段”[9]432。哈贝马斯进一步重新理解了人与自然关系,他认为在人与外界自然的关系上,人借助于工具理性征服和统治了自然;在人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上,则需要主体间借助交往行为进行相互合作和尊重;在人与内在自然的关系上,个人的社会化是在生活世界的层面实现的,因此也并非完全出于工具目的的需要。三是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哲学批判。霍耐特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忽视了社会性,“由于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把文明史解释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社会的阶级统治以及对个体本能的控制的那种必然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得不得出这样一种理论上无视社会行为的中间领域的存在的结论”[6]52。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霍耐特强调了社会主体间的斗争关系,以解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依赖关系,当被统治者感受到蔑视的经验时,他们能够起来反抗并重新获得个体的尊重。《启蒙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引起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视,不过,包括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不是主要从生态意义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集中研究人与内在自然以及人与第二自然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研究。“与社会生态学相反,当代理论家们认为除了间接地把他们的思想应用到环境研究中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并没有给予环境足够的重视。”[1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