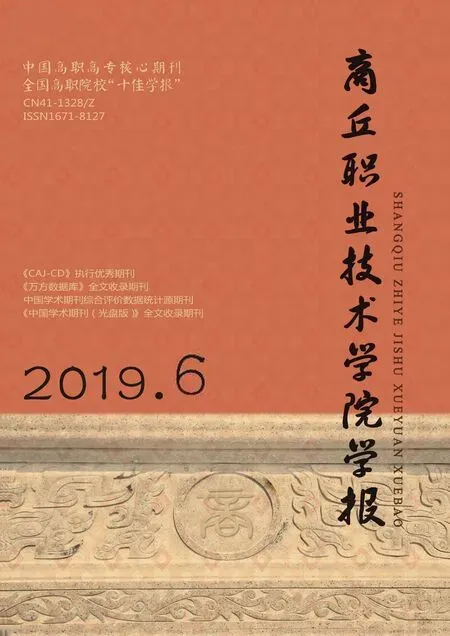名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来自语言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
2019-02-20吴铭
吴 铭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四川 重庆 400031)
名词和动词使用频率较高,二者的异同不仅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也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界、神经病学以及临床上关注的焦点。然而,名动关系又由于其复杂性而极富争议。
印欧语系(如英语等)的形态变化与汉藏语系(如汉语等)相比,更为丰富。因此,理论语言学中对于该语系中词类的划分大多基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观点,认为词类的本质是句法,是在句法使用中体现出来的,句法是词类分类的标准。这与黎锦熙[1]在1924年提出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相契合。
认知神经科学界对于名动关系的探讨也尚未形成定论,主要存在“名动分离”与“名动不分”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名词和动词的神经加工机制相互独立,故名词和动词属于两大不同的词类;后者认为大脑在加工名词和动词时,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加工的,并不存在特异性脑区,因此,二者的神经表征相同或存在大部分相似的交叉性脑区以及小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异性脑区。尽管汉语学界对词类的划分标准以及名动关系存在纷争,如沈家煊[2-4]认为汉语“名动包含”,刘丹青[5]支持“名动分离”,但就现有文献而言,通过电生理学技术探讨名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支持“名动分离”的占多数[6-8]。不过,通过各类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名动关系(“名动分离”或“名动不分”)因素的研究也存在分歧。因此,本文拟从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出发,探讨名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提供启发。
一、理论语言学界
(一)词的分类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构成成分,若产出和习得过程出现障碍,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句子的理解和加工,从而影响诸如会话、沟通等的社交能力[9]。词汇指的是能被独立使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有的词能被划分为称作“词素(morpheme)”的最小的语义单位。
一般而言,词汇具有不同的词类属性。如“蓝天”属于名词,表示具体的事物;“奔跑”属于动词,表示具体的动作。不过,有的词语可能同时属于多个词类范畴,如英语中的“research”、汉语中的“研究”,既可指代动作,亦能指称事件。这是多义(polysemy)的一种特殊现象,是词典中的概括词或词目词在整个社群语言系统中兼属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的语法多功能现象。如果一个词既属于名词又属于动词且各义项相近,那么诸如此类的词就被称为动名兼类词。动名兼类词在现代英语、现代汉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分析语中数量庞大。王仁强等人[10]借助语料库的方法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为例,调查了现代英语兼类的现状,发现兼属两个词类属性的词条共4 431个,其中动名兼类词占59.65%。
(二)汉语词类划分
与英语等印欧语相比,汉语的屈折变化相对较少。因此,印欧语等的词类分类方式是否也适用于现代汉语,引起了巨大争议。陈道望、朱德熙等人认为,汉语词类本质同英语等印欧语相同,也是一种分布类。郭锐、陆俭明等人认为,汉语缺乏形态,因此,汉语词类是以陈述、指称、修饰、辅助这4种基本类型的表述功能为内在依据进行的分类,是具有表述功能的语法意义的类。傅东华认为,汉语中的词类无法简单地与句法成分对应起来,“词语只有在句中才能进行分类”,因而汉语词类无法划分。高名凯[11]认为,词的句法功能属于句法范畴,词类则属于词法范畴,句法范畴不等同于词法范畴,因此,词的句法功能不能作为词类分类的标准。徐通锵认为,汉语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与其采取极为复杂的分类标准,倒不如不分类[12]15。郭锐认为,句法功能虽并非词类本身,但反映了词类差别,尚能作为词类分类的标准[12]60。
陆俭明[13]认为,词类的划分只存在于概括词中,个体词不存在词类的划分。但是,王仁强[14]认为,词类的划分同时存在于个体词和概括词这两个范畴中,词类划分应基于双层词类范畴理论,同时考虑“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言语层面中的个体词和社群语言中的概括词两个层面发生范畴化的情况。言语层面的个体词经过规约化后,被词典学家收录入词典,成为概括词;而概括词也正是由个体词在某一社群语言体系中经过相变抽象得来的,与词汇的使用频率密切相关。量子力学中认为光既有波的特性,又具备粒子的属性,即具有波粒二象性;人文科学界中对于词类的划分也应当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王仁强提出的双层词类范畴理论[14]正是摒弃了牛顿经典力学的二值逻辑思想,遵循了量子力学理论中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多重不确定性等的模糊逻辑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现代汉语词类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词汇假设
强词汇主义假设认为派生和屈折变化独立于句法;而弱词汇主义假设认为派生变化发生在词库内部,属于词,屈折变化发生在句法,独立于词库。因此,无论是强词汇主义假设还是弱词汇主义假设,词类形成于词库,自然也就属于词库。词类的划分是由词汇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名词和动词在句法之前就得到明确的区分,词类是先验存在的[15]。
二、认知神经科学界
认知神经科学界的研究者们虽通过大量的实验就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并在原有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改进,如将语言研究的对象扩大至失语症、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语言障碍的患者;使用诸如ERP技术、FMRI技术、PET技术等较为先进的实验手段;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增加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实验变量,考虑多种因素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理论语言学界中对词类(尤其是现代汉语)的划分标准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因此,基于不同语言学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相应地存在矛盾。换言之,影响汉语名动加工的因素到底是语义、语法还是其他非语言因素尚不明;这些因素对名动加工的影响程度也尚不清楚。未来的研究有望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名动加工各因素的权重比,从而更好地认清名动关系,搞清词类的本质。
(一)来自正常被试的证据
1. ERP技术
与诸如FMRI、MEG、PET等的脑功能成像技术相比,ERP技术具有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记录认知过程中实时的电生理学指标,因此,将ERP技术用于探讨语言的加工和理解过程有着其他方法难以企及的优势。借助该手段来对比英、汉心理词库中名词、动词的认知加工机制,不仅可以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揭示词类的本质;也能通过名词、动词两种不同词类间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处于二者连接处的动名兼类词的属性。目前,运用ERP技术探讨名词、动词加工的神经机制,发现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会对名动分离产生影响。
一是语义因素。大脑在加工名词和动词时表现出的脑电波差异主要是由于二者的语义概念差异所导致的[16-17]。词类在大脑中存在特定性脑区,这是由于词汇所具有的语义差异而非语法差异造成的,即便是隶属同一词类的词语,只要语义上存在差异(如物体名词和行为名词),也会激活不同的脑区[18]。
孤立词条件下,动名兼类词的多重激活过程受到意义相对频率的影响。从语法功能角度出发对汉语名动加工的ERP技术的研究表明,尽管语法可作为名动划界的依据,但语义也可能在名动分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7]。
二是语法因素。认知语法认为语法是名动分类的标准和依据,只有依据语法划分出的类才是语法的类[6][19]。孙崇飞[19]认为,汉语的名动分离是由语法性质决定的,与英语等语言的动词一样,汉语动词也不能直接用作修饰语,只能经过一定的句法加工才能修饰名词,英汉形态差异仅存在于语音层面,即汉语形态无语音实现形式。
三是其他因素。在语言理解过程中,语境可导致词类效应的产生。只要靶词的词类属性与先前出现的语境一致,即使它与语境存在语义冲突,被试的词汇判断速度仍会得以加快。在歧义词加工的早期阶段,语境可以抑制不合适意义的激活,促进合适词类信息的选取以达到消除词类歧义的目的。此外,前导词能为后续语料提供强烈而清晰的句法期望。因此,语境是造成汉语名动分离的原因[20]。
汉语习得年龄、水平、学习环境等对词类判断的反应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除语言学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可能造成汉语名动分离[6][21]。此外,具体性(concreteness)与词性也存在着交互作用[22]。
由于英汉双语名词和动词是分离的,因此,英汉心理词典的多词素单词中存在词性效应。其中语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名词比动词诱发更大的P200和P600,不过在N400和P600成分上,因词性与熟悉度的交互效应显著,从而推断熟悉度和词频也可能影响名动分离[23]。
2. 其他实验证据
梁丹丹等[21]运用FMRI技术考察了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充当名词修饰语时的加工过程,发现三者的加工机制均不相同,继而证明了汉语中存在名动分离。
英语中,名词和动词在语法上存在差异:名词具有性、数、格;动词具有时、体、态。因此,动词具有更为丰富的形态变化,而这一特征导致其在形态——句法整合的加工的实验中,比名词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动词和名词加工的MEG差异来源于语法因素[24]。
杨亦鸣等[6]、刘涛等[7]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名词和动词在大脑中的神经机制时,发现引起汉语“名动分离”的因素是语法因素,从而得出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是语法而非语义。
(二)来自语言障碍患者的证据
帕金森病人的语法障碍主要来源于动词产出能力受损,此外,与动词表征相关的语义概念的延迟也可能是造成其语法障碍的原因之一。动词产出障碍作为执行功能障碍的一种,是由于大脑皮质受损而引起的在词汇产出过程中出现词汇的选择性受损。由于动词涉及的形态屈折变化难于名词,因此,帕金森病患者对动词的加工难于名词。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25]。不过,无论是动词的加工难于名词还是名词的加工难于动词,都表明名词的加工与动词的加工是相互分离的,具有不同的神经表征,形态——句法因素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5]。
目前,对于影响名动分离的因素主要有语义和语法两类。不同的实验得出的不同结论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实验技术的差异所造成的[26]。Alyahya等人[26]使用数据驱动型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研究慢性脑中风失语症患者的名词和动词的产出与理解过程是如何与基本的语言要素(如语音、音系、语义、形态、句法等)相结合的。研究发现,只要控制好名词与动词的可想象度(imageability),名词和动词的加工就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将失语症病人作为被试,探讨其在进行动词、名词加工时激活的脑区差异,发现大脑左半球颞叶以及顶叶区域存在与动词和名词加工相重叠的神经关联物。在单个词汇的加工阶段,大脑各皮质区域共同参与其中[27]。运用PCA研究失语症病人语言加工和认知过程主要涉及以下五个基本模块:音系产出、识别、语义、流畅度和执行功能。名词和动词的加工均涉及音系产出和语义理解这两个过程,名动加工可能存在部分交叉脑区,这与使用FMRI等技术所得到的结果相吻合。
三、结语
探讨名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词类本质,从而理解语言的本质。名动关系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而实证研究大多是以相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实施的。理论语言学界中对于名动关系尚未达成一致,自然也会使得实证研究中对于名动关系的探讨存在纷争。就名动关系而言,理论语言学界主要存在“名动不分”“名动包含”及“名动分离”三种观点;而认知神经科学界则只存在“名动不分”与“名动分离”两种观点,且后者占优势。那么理论语言学界中所存在的“名动包含”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需后续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就影响名动关系的因素而言,主要存在语法和语义两派之争,谁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尚未得知。但已明确的一点是,语法和语义均会对名词与动词的加工产生影响。
将动名兼类词作为研究中介,考察名词和动词的加工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一方面,该类词在语文词典中大量存在,借助该类词来研究名动关系可能会带来新的启发;另一方面,从心理词库的视角,运用神经电生理学技术探讨双语心理词库中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的加工差异仍处于缺失地位。后续研究可通过两种或多种语言词汇加工的对比研究来揭示不同的母语经验对二语学习者的影响因素及原因,为提高二语学习的效率提供新的启发,以期更为科学地指导外语教学。
此外,还可通过将正常人产出的词类与语言障碍患者进行对比,发现语言障碍的词类特点,以便更好地为这类特殊群体的语言治疗提供有力的语言康复理论支撑,实现“产、学、研”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