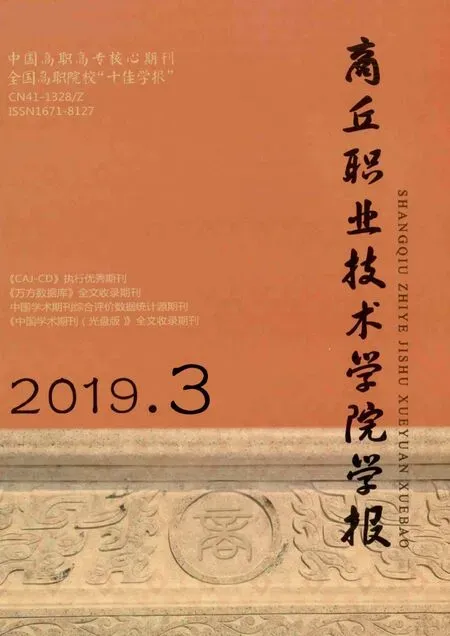妻子行为能力制度的历史考察
2019-02-20胡政
胡 政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行为能力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人只有具备了行为能力,方可“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不仅仅通过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构建其法律关系”[1]。因此,行为能力于民事主体私法生活的开展关涉甚巨。在行为能力的划分标准层面,当今各国民法普遍摒除性别,而以成年且精神正常为标准,赋予自然人完全的行为能力①。我国《民法总则》亦概莫能外。由此可见,男女平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文明法则,可是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长久以来两性的家庭地位是不平等的,具体体现为夫与妻行为能力的不平等。对此,我国《婚姻法》第13条和第15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且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前述条文所强调的平等与自由深具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必须结合历史背景才能深刻认识。可是,各国民法何以摒除性别而以年龄、精神状况划定行为能力,夫妻行为能力之发展在历史上究有何种之演进,此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行为能力制度并非生来就具有自由主义的浪漫气质,在人类历史中,行为能力长久以来一直是父亲、丈夫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男子的特权。而女性在出嫁之前往往受制于父亲,出嫁之后更是落入夫权之桎梏,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志殊难保障。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剖析妻子行为能力的发展过程,就难以真正理解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原则重在保护何方,有何社会基础。何况,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实现仍是进行时,绝非完成时。在偏远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广泛存在。因此,在两性家庭地位平等层面,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综上所述,本文以妻子行为能力表述的历史演进为视角,考察从罗马法到近现代民法妻子行为能力表达的发展过程,旨在助益当代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原则的贯彻和行为能力制度的完善。
一、罗马法中妻子的行为能力
(一)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前510年)
王政时期的罗马尚无法律编纂,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罗马人仅从事耕种、饲养家畜等简单的生产活动,家庭成员之间联系密切。其中,家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拥有家庭的全部财产,并能够决定家庭的一切事务,而家属却没有任何私产,也无法决定任何事务。同时,依古代罗马习惯,家属如从事法律行为,“只能使家长增加利益,而不能使家长负担义务或蒙受损失,不得以家长的名义为承担义务的行为,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做市民法上的债务人”。而且,“如果家属因订立契约而负有债务,这种债务只能是自然债务,不受法律保护”[2]163。因为罗马的家庭由家长、妻子、子女等成员构成,所以妻子作为家属之一自然是要遵循上述习惯法的。因此,王政时期的妻子是无行为能力人,不具有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资格。
(二)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前27年)
共和国时期的已婚妇女通常处于夫权的支配之下。可是,夫权的享有者必须是自权男子②。已婚的他权男子,由于自身处于家长权之下,他享有的夫权即为家长权吸收而由其家长行使。因此,妻子亦有可能受夫家家长权的支配。但是,夫权之下妻子的地位等同于其所生子女的地位,所以夫权对妻子行为能力的限制与家长权对子女行为能力的限制并无不同。故此,妻子与第三人订立契约须经家长(丈夫)的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若丈夫或家长死亡,妻子成为自权人,关于其法律地位《十二铜表法》第五表监护法的第1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祖先认为,甚至成年女子,因其生性轻佻,也应予以监护。”[3]由此可知,共和国时期的已婚妇女即使成为自权人,也要终身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但是,罗马法中的女子监护方式主要是能力补充,也就是被监护人为法律行为时,须经监护人同意以补充其行为能力的不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法律行为均要得到监护人的同意,乌尔披亚努斯在《法学规范》中列举,只有为法律诉讼当事人、有损于本人利益的行为、出让要式移转物、缔结“有夫权婚姻”、订立遗嘱才需要监护人的同意[2]293-294。其余的法律行为,女子皆可独立为之。因此,共和国时期妻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相较于王政时期,其法律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三)帝政时期(公元前27—公元565年)
不同于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女子终身处于监护权之下,帝政初年《尤里亚法》(Lex Julia)即规定,凡女子为生来自由人者,有子女三人以上时,可取得自由之权利,而免处于监护之下,“解放自由人”而有子女四人以上者亦同[4]。此法虽旨在奖励生育,但客观上拓展了妻子的行为能力。及至公元410年,特奥多西乌斯二世和霍诺里乌斯帝复将此自由之权利扩大适用于所有适婚女子,而不论其有无子女,女子监护制度遂告废止[2]295。同时,帝政时期无夫权婚姻盛行,已婚女子不像有夫权婚姻③那样处于夫家的家长权之下,而是仍处于其生父的家长权之下,形同未结婚。因此,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也和未婚时一样,丈夫既不能并吞妻子的财产,也不能干涉妻子与第三方实施法律行为,且夫妻双方可以互为法律行为。故此,帝政时期妻子的行为能力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虽终不能与男子等量齐观,但法律施加给妻子行为能力的枷锁已大为宽松。此时,妻子近乎完全行为能力人,诚如美国学者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B. Morris)所言:“在帝政时期,妻子事实上成为自己的主人。她几近独立于家父,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丈夫,她能够提起诉讼,自由地持有和处置财产。”[5]128
(四)罗马时代妻子行为能力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二、中世纪妻子的行为能力
(一)中世纪妻子行为能力概况
中世纪的欧洲法制“承袭了希腊罗马的欧罗巴文化遗产,接受日耳曼民族传统风俗,发扬了基督教精神”[7]188。具体到家庭法层面,妻子的家庭地位在日耳曼习惯法的基础上,受到了教会法强有力的形塑。与罗马法一样,日耳曼习惯法中女性亦无完全的行为能力,其终身服从于男性近亲属的监护,但不同于罗马法中家长权或夫权之下的妇女没有独立的财产,日耳曼习惯法肯定了妻子对聘金、晨礼④、嫁资⑤以及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因继承所得财产的所有。但由于受制于夫权,妻子非经丈夫的许可不得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丈夫却可以对妻子的全部财产进行管理收益,并且可以处分妻子所有的动产,但对于妻子的不动产,则须经妻子同意后方能处分[8]。但是,对于妆奁或者私房物品,妻子是可以单独使用并处分的[9]217。既然妻子可以处分自己的私房用品,也就意味着妻子可以订立买卖、赠予等合同。既然妻子可以有法律行为,也就意味着妻子至少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后来,由于“日耳曼各个部落逐步开始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并成为各个君主国的国教”[7]240,教会法因之不断渗透中世纪法制,并在婚姻家庭领域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记。本诸《圣经》中人类的原罪是男人和女人共同造成的,中世纪法学著作《萨克森明镜》即以上帝的视角将男女视为平等之人[9]210。但这种平等仅仅是神学或者灵魂意义上的,具体在男女两性家庭地位上的差异,《明镜》依然不能等而视之。《圣经》新约以弗所书亦有言“做妻子的,当服从你们的丈夫,如同服从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脑,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脑”。据此教会法普遍规定,丈夫是一家之主,可以选择住所地,要求妻子履行与她社会地位相符合的家庭义务,并有惩戒妻子的权利;而妻子相对于丈夫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她没有权利独立订立契约、参与各种各样的法律行为,往往被视为无行为能力人[10]209。总之,中世纪妻子近乎无行为能力人,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从事少数极其简单的交易活动。
(二)中世纪妻子行为能力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中世纪虽然在妻子行为能力的发展方面无可称道之处,甚至相较帝政时期的罗马有所退步,但妻子的社会境遇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中世纪妻子行为能力制度是契合中世纪社会经济背景的。在经济层面上,建立在罗马废址之上的日耳曼王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实行封建庄园制度,人们普遍被束缚于封建庄园之中,频繁的商品交易难以维系,无法刺激行为能力制度的生长。全然不同于罗马的经济形态,使得扩张妻子行为能力的社会必要性大大降低,导致了中世纪行为能力制度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同时,中世纪法制深受基督教有关妇女脆弱的神学理论的影响,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因之普遍对妇女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在他们看来,妇女的心智和体力的低劣使她们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无须赋予妻子行为能力,一切由丈夫代劳即可,同时丈夫必须爱自己的妻子,履行保护妻子的职责。为了实现对妻子的保护,在限制妻子行为能力的同时,教会法还确立了婚姻自主、禁止离婚、司法分居制度,以确保女性能够找到令其满意的配偶,避免被丈夫抛弃而陷入贫困。因此,除了经济上的根源外,中世纪对妻子行为能力的限制也是当时法学家在保护妇女意图下的有意为之,并且的确改善了妇女在乱世中本就十分凄惨的社会境遇。虽然这种观念在现代看来是荒谬的,但在中世纪的情境下则是合理且符合需要的。
三、近现代民法中妻子的行为能力
(一)大陆法系妻子行为能力的发展
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尽管其民法典堪为一项革命的创作,但深入考察之不难发现,“这部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在保守主义和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11]164。在《法国民法典》颁布之前,以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为界,北部地区由日耳曼习惯法管辖,南部地区则主要受罗马法影响,但就妻子的法律地位问题,两大地区的观点是一致的,皆认为妻子应从属于丈夫。当时的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妻子是存在精神和生理缺陷的,或者说,至少是缺乏经验的。因此,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妻子无行为能力是社会的常态,即使丈夫离家很久、精神错乱,或者被剥夺法定权利,妻子仍不能恢复她的行为能力,也不能从事任何法律行为,除非得到法院的授权[12]1067。
及至《法国民法典》颁布,平等、自由原则得以确立,但在家庭关系方面仍有大量的封建遗存,身份观念和不平等色彩依旧浓厚。法典第213条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顺从夫。”第217条规定:“即使妻不在共有财产制下或采用分别财产制,未得其夫之参与行为或书面同意,不得为赠予、依有偿名义或无偿名义转让、抵押以及取得行为。”第222条则重申了民法典颁布前的既有规则:“如果夫系禁治产人或缺席,当该事实满足时,法官可授权其妻进行诉讼或订立契约。”由此可见,在妻子行为能力制度方面,《法国民法典》仍延续着旧的历史传统,并没有改进之处。虽然在民法典第一部草案中有建议“夫妻在其财产管理时享有并行使一项平等的权利。就一方或他方财产而设定买卖、契约、债务及抵押的一切行为,如无夫妻双方的合意,均不能成立”,但这仅为灵光一现,于第三部草案中即遭废弃,法律规定又回复到了由丈夫享有财产管理权的立场。因为,人们认为,虽然全部社会关系受制于平等原则仍是正确的,然而在婚姻领域内丈夫的优先地位是适应自然秩序的,否则只会在配偶间导致破坏家庭生活情调的琐碎争吵[11]165。
1938年法国废除了《民法典》第213条,但这并没有消除丈夫对妻子的优越地位。比如,丈夫有权拒绝妻子从事职业活动,只有在此项拒绝于家庭成员或者家庭利益层面非属正当,妻子才可以请求法院授权而不顾丈夫的拒绝。此外,虽然民法赋予了妻子行为能力,但是此规定对于商法却不能适用。立法者认为商事活动过于危险,妻子的社会经验尚不足以应付,故而《法国商法典》第4条“未经丈夫同意,妻子不能成为商人”的规定得以继续沿用。由此可以看出,妻子的行为能力依然严重受限。1942年法国修改了部分法律条文的措辞以扩大妻子的行为自由,如将民法典第223条修改为“妻子可以拥有与丈夫不同的职业,除非丈夫拒绝”,将商法典第4条修改为“妻子可以成为商人,除非丈夫拒绝”[12]1071。但是,如此轻微的改动对于妻子行为能力的扩张是微不足道的。虽然1938年和1942年《法国民法典》的修改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夫妻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但它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尽管丈夫仍然是家庭的头脑,但妻子已不再是罗马人和拿破仑眼中的劣等生物,她既能同丈夫一起管理着家庭,也可以成为丈夫的代理人[12]1070。而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平等在1985年才得以实现,这时夫妻任一方都有权单独管理和处置其个人财产,能单独管理和处置共同财产,只有就共同财产作出最重要的决定时才需要夫妻双方的同意。
作为大陆法系另一代表国家的德国,其民法典的颁布较《法国民法典》晚了将近100年。《德国民法典》所确立的妇女法律地位的确高于法国,如妻子享有诉讼权、享有特有财产的处分权,但夫妻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平等的。民法典贯彻了以丈夫为中心的“夫妻一体主义”,妻在家庭事务中有代夫管理之权,但实施的法律行为必须以丈夫姓名出现,此外,妻虽可单独订立契约,但若契约所担负的义务和因婚姻关系对丈夫所担负的义务相冲突时,丈夫可请求解除契约。这样,就实际剥夺了妻子的行为能力[10]259。直至二战后,德国相继颁布《男女平等权利法》《关于改革婚姻法和亲属法的第一次法律》等专项立法文件,夫妻在行为能力上的不平等才得以消除。
(二)英美法系妻子行为能力的发展
英国法长期奉行“夫妻一体主义”。女子结婚以后,便进入了一种受丈夫保护和管制的法律地位,这种法律地位可以称之为“民事权利的死亡(civil death)”,因为在婚姻共同体的信条之下,婚姻带来的法律后果之一就是使妇女和她们的丈夫成为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就是丈夫[13]。因此,英国的已婚女子几乎毫无权利,遑论拥有行为能力。她不能缔结合同,也无权拥有财产,更不能单独以妻子的身份起诉或应诉。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市场经济日趋活跃,妇女接触社会日益广泛,丈夫再也无法像中世纪那样把妻子束缚在家庭中了。变革的先声最早出现在妻子财产权利领域,1882年英国颁布了《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凡1883年1月1日以后结婚的妇女,有权以其婚前所有或婚后所得的动产及不动产作为分别财产,单独行使所有权及处分权[10]395。该法承认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认为妻子也有权拥有财产并处分之,这在实质上突破了“夫妻一体主义”的理论,认可了妻子的人格,对妻子行为能力的现代化而言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是,该法并未确认妻子完全独立的人格,仅规定妻子在特有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直到1935年的法律改革法才实现夫妻在私法领域的完全平等。该法明确“已婚妇女有取得、占有和处分任何财产的能力,有对任何侵权行为、契约、债务、义务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责任的能力”[10]395。此时夫妻各方拥有同等的行为能力,可独立地从事法律行为,并可独立地承担责任。
与英国法对待妻子行为能力的保守态度不同,美国法显然更开明、更具进步性。早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殖民地时代,美洲大陆受新教革命的影响,使得婚姻的概念以及庆典仪式更趋近于欧洲大陆改革者和民法的态度,而不类于英国国教的观念[5]126。他们认为,婚姻是基于双方合意而订立的民事合同,其法律效力并非来自教会的圣礼。该种社会观念肯定了妻子的意志自由,改善了妻子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形成了一种对妇女权利改善持开放态度的舆论氛围。加之殖民地活跃的商品经济,妻子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可以代表丈夫从事商业活动、监督管理不动产,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总之,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殖民地,妻子行为能力的深度和广度远远地超过了其母国英国,而且“夫妻一体主义”也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5]129。但是,同英国一样,殖民地时期以及美国独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妻子依旧不享有充分的财产权。在19世纪,美国发生了三次改善已婚妇女权利的立法浪潮:第一次发端于1835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这时的立法主要是为了使妻子的财产从丈夫的债务中解放出来;第二次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结束于南北战争,这一时期主要建立了夫妻之间的分别财产制;第三次出现在南北战争之后,目的在于保护妻子的收入[13]。19世纪美国妻子财产权的保护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民主制度的危机、国内经济的困顿、废奴运动的斗争,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各种社会运动之中,并担任了领导角色。同时,南北战争使许多家庭失去了父亲和丈夫,并使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13]。种种的一切导致了旧的家庭模式开始瓦解,逐渐被更灵活的、更个性化的家庭所取代。此后,在私法领域美国基本实现夫妻之间的平等。
(三)近现代民法妻子行为能力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兴盛,欧美国家相继步入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决定了妻子行为能力发展的走向。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已婚妇女社会劳动的参与上,以美国为例,1800年仅有4.4%的女性从事社会劳动,及至1940年这一比例高达25.4%[14]441。二战后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进程明显加快,及至20世纪末,世界主要国家均有50%以上的女性从事社会劳动,如美国70.5%、英国66.2%、德国61.8%、法国59.6%[14]346。这时,法律对妻子行为能力的限制无疑构成对已婚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的极大障碍。与之对应,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的趋势也倒逼着行为能力制度的改革。同时,社会劳动的参与使已婚妇女拥有了独立的收入,扩充了妻子的财产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助推了妻子人格的独立。其次是家庭结构的变革,主妇型婚姻日益被双职工婚姻所取代,由此家庭结构从以丈夫为首的等级模式转向了联合的和对称的模式,等级色彩弱化了,平等色彩增加了。基于旧家庭模式设置的法律制度再也无法适应新的家庭模式,对妻子行为能力的限制即为其适例。最后是意识形态层面,一种与婚姻共同体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思想日益流行,这种思想认为婚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配偶双方的个人价值,并且仅在它能够满足配偶双方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功能时婚姻才应该存续。而法律对妻子行为能力的束缚无疑限制了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并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四、结论与启示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欧洲,妻子行为能力的历史演进根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15]经济基础是导致古代及近代夫妻行为能力存在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差别化制度安排的动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女性,因为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劣等生物,体力上无法自我保护,心智上亦不够成熟稳重,所以必须限缩其行为能力,使其处于父亲或者丈夫的保护之下。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观念,但在蛮荒的古代、动乱的近世,这样的制度安排仍具有合理性。而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家庭由生产消费职能向单纯的消费职能转变,随之带来的是妻子社会角色的变化和外出活动频率的增加,这样的社会需求迫使行为能力制度向男女平等的方向演进。当前,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普遍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夫妻具有同等的行为能力更是其应有之义。通过梳理妻子行为能力的历史,不难发现千百年来妻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法所强调的男女平等,其实质是要求女性能够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法律地位,侧重点在于维护女性权益。这也是我国《婚姻法》特地强调两性家庭地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男女平等的立法方面,我国一向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民国时期,我国民法便确立了男女在各方面平等的原则,在立法理念上,远远地将一些“文明”国家抛在后面。但男女平等的落实仅有法律的宣示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为了贯彻法律所要求的男女平等,必须确保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经济机会,能够平等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在职业活动中要杜绝对女性的歧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男女平等的法律信条。此外,我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监护问题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成年监护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吸取妻子行为能力制度变革的经验教训是有必要的,通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财产权的完全独立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是妻子不致成为丈夫附庸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一是要尊重成年人自己的意愿,细化和完善意定监护规则,避免其独立人格遭到抹杀;二是要保障被监护人的财产权,规定监护监督机构,避免监护人侵吞挪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三是对尚未达到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但存在心智缺陷或者精神障碍的成年人,建议实行保护性照管,以保障其社会参与和人格尊严。
注释:
①《法国民法典》第488条规定:“年满18岁为成年,达此年龄者,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瑞士民法典》第13条规定:“成年且有判断能力的人有行为能力。”《意大利民法典》第2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为成年。成年后,取得从事一切活动的行为能力。”《德国民法典》未正面规定何者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可从第104条(无行为能力之规定)、第106条(限制行为能力之规定)反推出完全行为能力者须以成年为要。
②自权人是指不受家长权、夫权和买主权支配的人。
③有夫权婚姻是市民法上的结婚方式,最初只有有夫权婚姻才能发生婚姻的效力,无夫权婚姻则视为姘合。此种婚姻中,妻子脱离生父的家长权而成为夫方之家子,其财产亦归夫之所有,妻子在家庭中仅处于丈夫女儿之地位,如同本人所生子女的姐姐一样。
④依日耳曼习惯法,丈夫于新婚第二天清晨,须赠送妻子动产或不动产,故谓之晨礼。
⑤嫁资是指妻子出嫁时,其父或监护人所给付的一定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