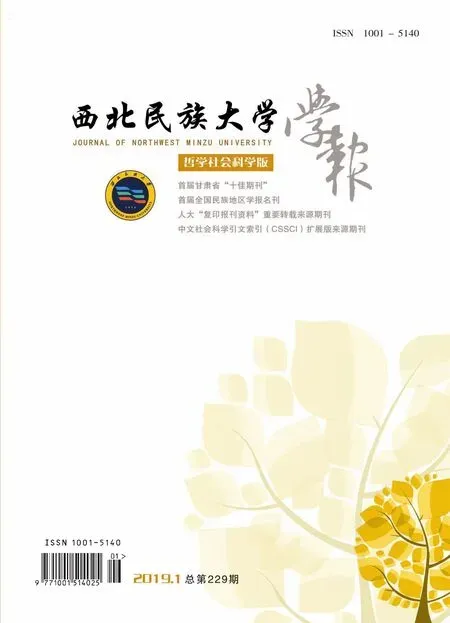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2019-02-20唐婷
唐 婷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0世纪以来关于白居易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围绕其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最初胡适先生提出白居易诗歌是“写实主义”,随之以刘大杰先生、马茂元先生等为代表主张白居易诗歌是“现实主义宣言”,但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裴斐先生认为白居易诗歌理论过于狭隘,违背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以白居易的新乐府、讽谕诗为对象,围绕诗歌反映政治,还是诗歌是艺术等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形成了白居易研究的一个热潮。关于“讽谕诗”,据白居易自述,是指从元和三年(808年)拾遗而来,“关于美刺比兴者”,及从武德到元和期间所作的因事立题的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称之为“讽谕诗”。白居易强调其“讽谕诗”继承了《诗经》“美刺比兴”的传统,其创作理念直接取道于《诗经》。而我们仔细比对《诗经》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就会发现二者在政教指向上并不一致,这实际上与白居易对“讽谕”的独特理解直接相关。
一、《策林》中的“讽教”观
《策林》是白居易为应试而专门编纂的一组对策集。据徐松《登科记考》载,白居易前后共三次科考及第[1]531,第一次在贞元十六年(800年),时二十九岁;第二次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当年知贡举者为礼部侍郎权德舆;第三次在元和元年(806年),与元稹一道考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林》就是作于这次登第之前。《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2]287《策林》对于研究科举考试的形势、举子备考的状态以及探讨白居易在政治、经济、兵防、文化等方面的观念,皆是不可多得的史料。除此,《策林》中所透露的白居易对于“讽谕”的认知直接影响了其“讽谕诗”的创作。
白居易认为,《诗经》的精神内核即“讽谕教化”,阐释《诗经》要把握鸟兽虫鱼的喻义,才能充分理解“比兴”的深刻内涵。《策林》第六十目“救学者之失”,针对《诗》《书》、礼、乐的教习重点,云:
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於章句训诂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袭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之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宗庙。是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远之训,畅于中而发于外矣。[2]1360
针对《诗》,白居易指出“六义风赋”是宗旨,说《诗》者不能专讲鸟兽草木之名。古时说《诗》,于鸟兽之名多有留意,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179夏含夷先生指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并不是指动物学或者植物学的知识,而是说通过《诗》,我们可以认识鸟兽草木的象征性质,可以理解山陵为什么危险,鸿雁为什么和婚姻问题有关系”[4]8。诚如斯言,《诗》中的鸟兽草木都具有喻示意义,都关涉着一定的人伦道德,因此《毛传》《郑笺》要以“兴喻”来阐释,这便正是“六义”中“比”“兴”的奥义微旨。白居易言下之意也是要探寻鸟兽草木的喻义,领会《诗》的“美刺比兴”,不能专做博物学研究。白居易谈到历代诗歌创作时指出:“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2]961他认为《诗》中的鸟兽草木都具有“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讽谏意义,故倡导说《诗》者要领会了这层意思才算得其宗旨。
对策中,白居易通过《礼记》来理解《诗》的方式,早在贞元十九年(803年)权德舆的《明经策问·毛诗问》中已出现。科举策问是《经学研究》的导向之一,参考其他经典来把握《诗》义应该说是当时说《诗》的一大趋势。对策中的“温柔敦厚”,出自《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郑注》云:“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5]1690《孔疏》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5]1690白居易点明《诗》有温柔敦厚之教,是为了强调“《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讽谕精神;主张说《诗》者把握“六义风赋”之宗旨,同样是为了强调“讽谕”。总之,白居易认为《诗经》的精神内核就是“讽谕教化”。
白居易虽无直接阐述《诗经》的研究文字,但《策林》中凡关涉政治思想与文学主张的阐述,大多都渗透了白居易重视“讽谕教化”的《诗》学观念。在政治思想方面,如《策林》“议守险”论政、教关系,云:
以道德为藩,以仁义为屏,以忠信为甲胄,以礼法为干橹者,教之险,政之守也。以城池为固,以金革为备,以江河为襟带,以丘陵为咽喉者,地之险,人之守也。王者之兴,必兼而用之。[2]1347
白居易认为教化是国家政治的一道屏障。教化施于人,从道德礼义上移风易俗,则国家政治安定、民心和顺;反之,则国家礼义凌迟,政衰民困。《策林》“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谈君臣间教化不兴,云:
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君好则臣为,上行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2]1314
君臣之间是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关系,即《诗序》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6]269,《孔疏》云:“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谕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霑。”[6]269白居易用此《诗》学观念来说明,上不行勤俭之教,下不效节约之风,君若好奢,则臣易贪冒;反之,君若节用,则臣多清廉。“利用厚生,教之本也”[2]526,故白居易认为民之困穷的根本是由君王的奢欲造成,其政治思想受《诗》学观念影响之可见一斑。
在文学主张上,白居易强调诗歌反映政教也印证了其《诗》学观。《策林》“採诗”云:
圣人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採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採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2]1370
白居易认为“政教”紧系民生,民风是“政教”得失最直接的反映,《诗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6]270国君通过诗歌知一时之风俗民情、政治得失。白居易反复强调诗歌与王政之间的关系,这段备考时所作的对策,在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做府试官时,原封不动地变为了考题。《进士策问五道》第三道,云: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诗歌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2]1001
白居易强调诗歌反映政教的观点,在之后的《与元九书》中,更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962的主张,提倡文章、诗歌要围绕时政而作,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这种创作理念其实就是孔颖达疏解《毛传》《郑笺》所提出的“诗缘政作”的诗学理论。白居易主张诗歌反映政教,是其文学思想受《诗》学影响的直接表现。
以上,《策林》中关于白居易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显示出《诗经》重视“讽谕教化”的观念对白居易的影响之深。然而,白居易的诗学理论并非完全照搬传统《诗》学,白居易的诗歌实践,或为颂美,或为讽谕,其所关涉的对象都是民众。白居易引《诗》也有专注于“生民病”的取向,如《蓼萧》言王泽遍及四海则民知礼义;《禾黍》言时和岁丰则民无饥馁;《北风》言威虐及人则民不堪其苦;《硕鼠》言重敛于下则民生凋敝等,从创作实践到用诗取向,恰是源于白居易对《诗经》“讽谕教化”的独特理解。
二、白居易对“讽教”的独特诠释
关于“讽谕教化”,《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269这段文字在隋唐《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陆德明《毛诗音义》引众家之言,云:
“风,风也”,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凤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风,托音曰讽。”崔云:“用风感物,则谓之讽。”沈云:“上‘风’是《国风》,即《诗》之六义也。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今从沈说。‘风以动之’如字。沈福凤反,云谓自下刺上,感动之,名变风也。今不用。[5]269
按陆德明所引,唐以前学者对“风”已有各种诠释,或认为“风,讽也,教也”;或认为“风,风也,教也”,陆德明取后者,认为“风”是君王施行教化,如风动万物。《孔疏》则云:
风,训讽也,教也。讽谓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谕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霑。[5]270
与陆德明不同,孔颖达取前者,“风,讽也,教也”,君王施行教化之初,先要讽谕触动,尔后民乃开悟。陆氏、孔氏虽有不同理解,但皆认为“风”乃自上而下,唐代其他学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颜师古《匡谬正俗》云:
《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今人读“风”为讽天下,案《序》释云“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此当言“所以风天下”,不宜读为讽。又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今人读云“风以动之”,不作“讽”音。案此盖《序》释“风”者,训讽,训教,讽刺谓自下而上,教化谓自上而下,今当读云“讽以动之”,不宜直作“风”也。[6]477
所引“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今本《诗经》作“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颜师古用“讽”字,他认为“风”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则“训讽”,指“讽刺谓自下而上”;二则“训教”,指“教化谓自上而下”,两层含义有上、下之别。
白居易与颜师古对于“讽教”的理解是一致的,就上文所论,白居易在阐述政治思想时偏重于“教化”,而在诗学主张中则偏重于“讽谕”,前者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自上而下;后者是站在民众的立场,自下而上,正是出于这样的诗学观念,故白居易引《诗》多围绕“生民病”。因此,白居易对于《诗经》的理解其实与传统《诗》学并不相同。传统《诗》学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诗序》云:“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6]270《关雎传》云:“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有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6]264郑玄云:“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6]271《孔疏》释《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云:“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6]302传统《诗》学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认为诗是君王用于移风易俗、施行教化的渠道,故《孔疏》每谈到“谏君”,之后总补充到“君又用之教化”,强调《诗》中那些讽谏君王的诗,同时又被作为教化的素材“用之邦国”“用之乡人”。而白居易偏重于自下而上的讽谕规谏,认为诗是臣民下情上达、规讽君王的渠道,故在将《诗》作为诗学典范时,白居易只提到用于讽谕箴刺的诗。在其实际的诗歌创作中,白居易也是将“讽谕”作为《诗》的精神内核。于是,在白居易这里,《诗》学观念由经学研究的“重政教”转向了诗学创作的“重讽谕”。
三、“讽教”与“讽谕诗”的创作
白居易偏重“讽谕”的《诗》学观念,直接指导着其诗歌创作实践。《策林》“议文章”,云: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覈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2]369
白居易认为诗人要稽政覈实,才能最终实现补察时政、惩恶劝善的政治作用,这显然是来自“讽谕”思想。而究竟如何稽政覈实?白居易在实际创作中有所诠释,《新乐府序》云:“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2]52《采诗官》云:“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2]90一则下至诗人,主要是为民、为君而作;二则上至君王,要广开言路,泄导人情。如罗宗强先生所说,此时(元和四年前后)白居易对于讽谏的内容还并未局限于“生民病”[7]183,在《寄唐生》中,则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15;又《伤唐衢二首》之二云:“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2]16即明确地将稽政覈实限定在“生民病”上。
“惟歌生民病”是白居易将“讽谕”观念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实践,故其将这部分诗命名为“讽谕诗”,白居易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2]964世所共知,“讽谕诗”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但又别于《诗经》传统的诗歌主张:一是“讽谕诗”是源于白居易对《诗经》“讽教”精神中“讽”的单方面继承;二是,因白居易对“讽谕”的独特理解,“讽谕诗”是以“生民病”为主要题材,与《诗经》并不相同;三是“讽谕诗”反映了白居易对“六义”中“赋”的关注,而非“比”“兴”。
白居易的“讽谕”观念是强调自下而上的讽刺规箴,以“生民病”为描写对象,向统治者反映政治民情。在一百五十首“讽谕诗”中,以《秦中吟》最为典型,白居易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2]30这组诗涉及到婚娶、赋税、致仕、时风等多方面,皆以平民穷困的日常生活为素材,平铺直叙地展现出来。如关于贫富悬殊而天壤有别的论述:
《议婚》云:“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颜色非相远,贫富则有殊。贫为时所弃,富为时作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闻君欲娶妇,娶妇意何如?”[2]30
《轻肥》云:“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罇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麟。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2]33
《买花》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戔戔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2]34
又如,关于赋税太重,民不堪其苦。《重赋》云: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2]31
在这些以“生民病”为叙述主角的诗歌中,充斥着平白切直、自下而上的“讽谕”,白居易充分表达了其“兼济天下”的儒家道义与兼爱情怀。元稹云:“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9]54皮日休云:“立身百行足,为文六义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10]106邓元锡云:“白太傅《秦中吟》、《新乐府》之作,风时赋事,美刺兴比,欲尽备六诗之义,大哉洋洋乎!”[11]230诗论中,多将白居易的这类诗比作“风”,因《秦中吟》篇篇写民事、句句刺权贵,有“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之余韵,故以“风”称之。然而,《国风》的描述对象多是权利阶层,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不同。
《国风》多以“比兴”的方式,借鸟兽草木之事劝谏君王。如刺淫乱,《雄雉》诗云:“雄雉于飞,泄泄其羽。”《传》云:“兴也。雄雉见雌雉,飞而鼓其翼,泄泄然。”[6]302《笺》云:“兴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奋讯其形貌,志在妇人而已,不恤国之政事。”[6]302又刺俭啬,《园有桃》诗云:“园有桃,其实之肴。”《传》云:“兴也。园有桃,其实之食。国有民,得其力。”[6]357《笺》云:“魏君薄公税,省国用,不取于民,食园桃而已。不施德教,民无以战,其侵削之由由是也。”[6]357又刺无礼,《蒹葭》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传》云:“兴也。蒹,薕。葭,芦也。苍苍,盛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6]372《笺》云:“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盛,指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6]372这些诗都是直接讽刺君王,虽讽刺内容各异,但总体上都关涉着人伦道德、礼义教化,是站在权力阶层的角度谈治国之道德大厦、精神大厦的构筑。也就是上文所论,《诗经》对于“讽谕教化”,实质上更侧重于“政治教化”;而白居易以“生民病”为主的叙述视角,落笔处多是民众生活的困苦,直接刻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受到苛政剥削的艰辛,这是站在民众之中,以诗为谏的“讽谕”精神,《国风》中虽也有少数描写民众困苦的篇章,如《君子于役》《硕鼠》《北风》等,但诗中的民众往往充满着反抗的力量和大胆批评的魄力,《硕鼠》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直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并发誓“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北风》将虐政比作肃杀的北风,言“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也是要“适彼乐土”,这与白居易笔下“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重赋》)、“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纳粟》),“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等形象相比较,前者是“德政谴责”,后者乃是“生活控诉”,两者有泾渭分明的区别。
白居易的“讽谕诗”将笔触深入贫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艰辛的血泪控诉,这样的叙述视角和情感铺设是《诗经》里所没有的。因此,白居易的“讽谕”观源于《诗》又有别于《诗》。“讽喻诗”纯粹是下情上达、讽刺规谏,与强调“政治教化”的《国风》有所不同。
四、“讽谕”走向理论成熟
讽谕诗的创作源于《诗经》传统,也有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则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则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则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
白居易有“兼济”之志,在与元稹的书信中提道:“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2]964白居易奉守儒家道义,影响了其诗歌创作的发生并渗透在创作实践中。所谓“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12]700,正因为白居易具有“兼济”情怀,故心系之处、触目所得,多是百姓困苦,进而才有“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2]24也因这份“兼济”之志,故白居易常在写尽百姓艰难之后,自责:“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观刈麦》);又“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纳粟》)等,促使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内在原因,是其“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念。
再者,白居易以民为贵的政治思想也影响着“讽谕诗”的创作。白居易“贵民”,《策林》“不劳而理”,云:
三皇之为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2]1293
白居易祖述“三皇五帝”,认为君王要与天下百姓同心同德,出令设教要考虑到百姓的所欲所求,才能天下大和、垂拱而治。君王“知人安之至难也,则念去烦扰之吏。爱人命之至重也,则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罢也,则念省修葺之劳。忧人财之易匮也,则念减服御之费。惧人之有馁也,则念薄麦禾之税。畏人之有寒也,则念轻布帛之征。虑人之有愁苦也,则念节声乐之娱。恐之人有怨旷也,则念损嫔嫱之数。故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则天下和平矣。”[2]1296白居易认为,君王制定方针政策要以百姓为中心,要考虑到百姓安生立命的实际需求。在其观念中,国家兴亡在于得失人心,人心得失在于君政善恶,故“民”才是政治的核心,云:
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也。何则?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2]1300
王政成败关键是人心所向,白居易以此说明百姓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作用。显然,白居易秉持着以民为贵的政治思想,故客居长安时,每见民生凋敝则痛心疾首,一定要情感愤激地直接倾泻出来,才能明“兼济”之志。而白居易之所以能生动刻画百姓生活的细节,这与其自身遭际有关。
白居易在《论和糴状》中,云:“臣久处乡闾,曾为和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覩。臣顷者常欲疏此人病,闻于天聪;疏远贱微,无由上达。今幸擢居禁职,列在谏官,苟有他闻,犹合陈献;况备谙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缄默,隐而不言,不唯上辜圣恩,实亦内负夙愿。[2]1235如其言,这段仕宦经历应该也为“讽谕诗”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正因为“久处乡闾”,白居易才能将百姓生活的艰难刻画得如此细致;也因为曾“亲自鞭挞”,所以对官吏的行事做派格外了解;最后又恰逢“列在谏官”,有了下情上达的渠道,这些都是“讽谕诗”创作的条件。总之,“讽谕诗”继承《诗经》“讽谕规谏”的精神,又渗透着白居易“以民为重”的道德观念、政治思想及其自身的仕宦经历。综上,“讽谕”作为一种诗学观念在白居易这里走向成熟,不是没有原因的。
“讽谕诗”反映出白居易更热衷于“赋”,而非“比”“兴”。罗宗强先生认为:“在那些诗里,他的讽谕不是讬讽,不是兴寄,而是直谏。……它是直叙其事,说明意之所在。”[9]180众所周知,白居易倡导文章诗歌平易直白、村妇老妪可解,故其“讽谕诗”浅切直接。但有一点,白居易在为诗命名时,云“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谓之“讽谕诗”。而“讽谕诗”多是直陈其事,并非关于“比”“兴”,这如何理解?白居易的“比兴”是指与美刺、讽谕相近的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创作方法。在实际的诗歌创作方法上,他更强调“赋”。《策林》云:“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2]1293“六义”之中,白居易独标“风赋”,凸显出对“风赋”的特别关注,而“讽谕诗”直陈生民病的特征秉承了“风赋”传统,这与《诗经》以“比兴”讽劝君王实乃异曲同工。至此,“讽谕诗”的叙述模式由《诗经》的“道君王之事”转换为白居易的“直陈生民病”,且后者成为了唐朝诗人用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白居易论当朝诗人也反映出“直陈生民病”的主张。白居易认为杜甫最有风雅遗韵,杜诗中又以“《新安》《石壕》《潼关》《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13]345最善,这些篇章都是直接描述征伐无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杜甫描写百姓生活困苦的诗并不多,至白居易正式提出“惟歌生民病”的讽谕主张,将这种创作风格作为一种自觉追求,并躬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此时“讽谕”理论走向成熟,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乃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可以说,“直陈生民病”的讽谕方式始于杜甫,而成于白居易。在与白居易时代相近的诗人中,得其称颂者又有韦应物、张籍、元稹,这三位有关讽谕的诗中均有“直陈生民病”的特征。白居易云:“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2]2韦应物的歌行多借古讽今、借物抒怀,也有“直陈生民病”者,如《鼙鼓行》写服役之士,家有鳏孤独妇之苦;《采玉行》写采玉之丁,身处绝岭之险,但这样的篇章毕竟是少数,较多“歌生民病”的是张籍。白居易论张籍,云:“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2]2张籍的乐府诗多“直陈生民病”,除白居易所引四首外,又如《野老歌》《牧童词》《贾客乐》写百姓不堪赋税之重;《征妇怨》《寄衣曲》《关山月》写征战戍役之苦;《筑城词》写壮丁筑城之劳,《山头鹿》写战争连年、民生凋敝等。张籍“以同情之心写实,作品本身就往往自然流出讽谕之义”[8]174,是“讽谕诗”直陈生民病的推波助澜者。而元稹,在诗学思想上与白居易相合,如白居易将诗名为“讽谕诗”,元稹也将诗分作“乐讽”“古讽”“律讽”,同样强调诗歌“讽刺规谏”的政治作用,元稹诗中也以“生民病”为题材,如《旱灾自咎贻七县宰》《代曲江老人百韵》《田家词》等,总体上元稹的讽谕诗更偏重于“即事名篇”,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略不同。
以上,通过分析《策林》中有关白居易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的资料,反映出白居易对《诗经》“讽谕教化”的独特理解。与传统《诗》学相比,白居易偏重于自下而上的“讽谕”,此观念直接影响了“讽谕诗”的产生与创作。“讽谕诗”正是秉承自下而上的观念,用“直陈生民病”的方式来规谏君王,这种方式又发展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