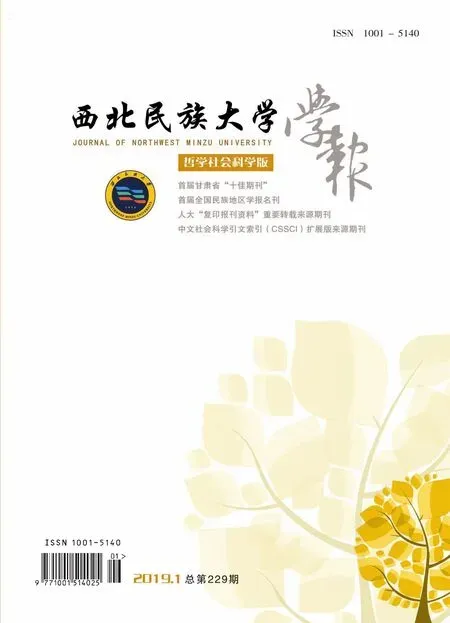故国新知: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019-02-20苏永前
苏永前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界来说,人类学的输入无疑是一件大事。经由早期学者的译介与传播,这一学科不仅很快在国内落地生根,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从已有研究来看,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不乏其人,其中较重要的如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注]① 前一著作主要围绕中国人类学早期重镇中山大学展开;后一著作系高等学校教材。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上述论著受视角、体例所限,在资料上尚有补充的必要。
一、人类学的初步译介
19世纪末,汉语“人类学”一词已在日本率先出现。1898年,《东亚报》(艺学卷四)发表《歇兹开路氏人种说》一文中有“于是人类学者相踵辈出”之语。此文章在日本刊出,因而在国内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中国学者中,较早使用“人类学”一词的是梁启超。在发表于1902年的《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写道:“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1]可以推断,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接触到在当时尚属新兴学科——人类学。不过《新史学》一文中,人类学只作为与史学相关的学科而被顺便提及。
1903年,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并于次年初颁布,其中《大学堂章程》之“文学科大学”的“中外地理学门”主课中有“人种及人类学”,“万国史学门科目”“英国文学门”选修课中均有“人种及人类学”。与此同时,王国维1904年秋执教江苏师范学堂时,讲义第二篇即为“教育人类学”,其中谈道“教育者不可不就所教之儿童而精密究之,此种研究即教育的人类学也。人有身体及心意二部,故教育的人类学自分而为二。其研究其有形的身体者,谓之教育的人体学;其研究无形的心意者,谓之教育的心理学”[2]。这里已显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端倪。
在此前后,对于国外人类学知识的译介不断见诸报刊。1903年,罗大维将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一书译成中文,该书中曾多次引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抑野蛮人自由之状态,于前世纪虽为思想之倾向,今日社会学发达,已决明野蛮人之状态之非自由。英国人类学者兰博克氏之《文明起原论》曰:‘野蛮人无往而能自由,其于世界中到处、日日复杂之生活,为最不便。何也?以其习惯往往不能为法律所特许。’”[3]39-40“人类学者威尔确乌、加罗利诸氏,谓头骨广与头骨长者属于高等,而现在人种中之最下等者,为亚乌斯特利亚人。”[3]741904年,《江苏》杂志发表坪井正五郎的《人类学讲话》一文,其中说到:“古昔言人类学者,虽亦有之,然皆不过就人生人性二者言之,而未尝及于吾人之人类全体。今言人类学,当分二种:一言身,一言心。究其一而不究其二,不得谓之人类学。譬之有精神,有肉体。研究人类学者,不可遗肉体而单言精神,亦不可遗精神而单言肉体。”[4]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结束部分建言,“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5]39,其中第三科“史学科科目”下,第十项为“人类学”[5]40。
国内较早对人类学作专门介绍,是1904年《大陆》杂志第2卷第12期发表的未署名文章《人类学之目的及研究人类学之材料》,作者首先指出:“人类亦自然产物之一,若研求其性质,亦须用理学的方法,始能知悉人性之正鹄。”[6]1这里所谓“理学的方法”,亦即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在人类学诞生之前,已有动物学涉及人的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弊端:“又动物学者以人类为动物,动物学书中时论及人类,然关乎人类可研究之事甚多,往往有于他动物不必视为重要,而于人类则必须详细讲求者。使人类与他动物一概相提并论,未免失其权衡。故动物学书中之论人类,吾人嫌其过略。”[6]1-2动物学之外,其他涉及人的学科也各有局限:“夫人体则详之于解剖学,人心则详之于心理学,人语则详之于言语学,众人相集而成之社会则详之于社会学,人事之经历则详之于历史学。又有考古学以探明人类之遗物。然则人类性情行为之各部,皆各有其科学以研求之矣。虽然,是等为人类一局部之学,而非真能解释人类者也。例如解剖学,以明人体构造为目的,然人类之研究不第身体,故斯学之目的不可谓之知人类。观于心理学乃至考古学亦同。”[6]2与上述学科的“局部研究”不同,人类学则注重对人的“整体研究”,“非体非心,离脱局部之研究以论人类,是即人类学也。”[6]2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明人之所以为人,即明人类之本质、现状及由来”[6]3。为达此目的,“则体也,心也,言语也,古物也,皆可用以为研究人类学之材料”[6]3。
此后,致力于介绍西方人类学的学者还有孙学悟。1916年,孙学悟在《科学》杂志发表《人类学之概略》一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此文资料更为翔实,还对人类学的几个主要分支作了详细说明。文章首先追溯了人类学的来源:
人类学者,专为研究人之为类之科学也,其起源与它科学相仿,首以好奇之性久深于人己所不达之问题,每立种种假设以解释之。其学说初或列于信仰之范围而无证明之事实,或传述前人之记录而流于杳渺无真理之境。以是之故,人类学至十九世纪后始含有科学性质。自后欧美学士探险旅行者渐多,大城巨市博物馆陈设日富,同时动植学逐渐进步,事实标本,广集博征。人类学研究之方法与其立论之基础遂渐趋于科学之地位。然人类学之成立与其范围之划定,实始于1859年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刊行、法兰西中央石器之发现,故1859年,不啻近世人类学之新纪元也。[7]429
孙学悟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略作讨论后,重点介绍了人类学的主要分支:一是人体学,主要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为何物之问题”;二是人性学,重点研究“地势、气候及周围状态对于人种上文化之影响”;三是人种学,主要是对人类文化的比较研究;四是古物学,旨在研究“历史以前之人种及人性”[7]431-442。上述各个分支中,尤以“人种学”的论述最为详细。在“人种学”的论述中,孙学悟首先分辨了“人种学”与“人性学”的差异:前者“以文化为标准而区别种族”,后者则“仅为一比较文化之研究”;然后介绍了人种学的目的及研究资料:“人种学家首先采集‘原人’之标本以为研究之资”,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人类进步之阶级,贯通文野人之历史,以观察进化史之梗概”;最后对人种学的主要学说及研究方法作了扼要说明[7]436-437。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进化论”学说风靡国内,孙学悟却对该学说有所警惕:“人种学上学说,多基于天演进化之理论。然以解说一切,则未免失之于陋。浅学者徒随声附和,以致失科学之价值。”[7]437最后,对人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逐一作了说明。在“古物学”的介绍中,相对于博物馆而言,他更加强调墓葬发掘现场的重要性,由这种思想,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现代考古学意识的萌芽。
当然,孙学悟这篇文章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人类学的几个分支中,“人性学”与“人种学”可以合并为一类(即归入今天所谓“文化人类学”名下)。此外,“人种”这一名词自晚清起已被频繁使用,其涵义主要指某个人类群体的体质、遗传特征。朱铭三在《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曾谈道:“在称呼体质人类学为人种学的国中,所谓体质人类学,却是指的生体人类学而说。……我们研究人类,若是从人类的精神生活以至于文化方面加以研究,那么这种科学叫做民族学。”[8]而在孙学悟笔下,“人种学”却仅强调文化的比较研究(相当于今天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在术语的翻译上也欠斟酌。不过,在西方人类学“东渐”的当时,这篇文章的“启蒙”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二、人类学论著的涌现
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旨在于“本进化之原理,论人类之变迁”[9]封底。在当时,这本书“著作界所绝无仅有”[9]封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人类学专著。该书面世数年之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曾有评介:“陈君以科学之方法,叙论人类学,诚杰作也。”[10]在“绪言”中,陈映璜首先对人类学的发展态势作了介绍,最近六十年间,其发达之状况“尤足令人惊愕者,则人类学是也。或携罗针历海上以探险,或执锹锄入地下以凿幽。凡古来之隔于瘴烟疠雨,蔽于土壤沙砾,史乘弗载、口碑弗传之杂物碎片、人畜化石,纷纷以发现见告矣。即书契以前之人类,世所谓原人者,亦能扩充范围,广罗证据。吾人一观察书契以前之遗物,获知人类之知识,如何由单一简易,蕲进于巧緻复杂。其生存竞争之结果,实不难积渐演进递嬗递新”[9]1。与前述孙学悟等人观点不同的是,陈映璜在书中不仅突出了人类学的学科特性,而且强调这门新兴学科的反思性品格。他认为,18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地原住民的陆续被发现,“种族优越论”在欧洲甚嚣尘上:
世有骄傲人种,见有与己貌不同之人种,肆意轻蔑。辄谓有色人种,未吸文明之空气,未浴开化之雨露,彼构成野蛮五体之元素。较吾人之组织物质,遥为劣等。其心思材力不能善逮吾人之敏锐精明,更勿论矣。加以奴隶贩卖,残忍无智之恶习,又足以助长其口实,遂判定世界人种,有优劣贵贱之别。甚至虚造学说,谓先天的主治者,特造此等奴隶,以供优等人种驱使,故非洲黑人,不应享有人种。此种妄自尊大之见,几固结不可解矣。[9]2
在陈映璜看来,人类学的价值,在于研究者所具有的“世界的眼光”与“世界的观念”。有此“眼光”与“观念”,才会对“他者”产生某种宽容与理解:“要之各国人民,社交上之风俗习惯,皆因其社会组织异同之结果,原不足异。如以某民信偶像,某民无夫妇之别,或噉生肉,或焚杀魔巫,或牺牲子女,似此蒙昧之习惯,恒不恤诽谤而骂詈之,徒以自尊自大之偏见,侮蔑他人种,适自形其浅陋,且与研究人类学之本旨,相剌谬也实甚。”[9]3“绪言”之外,该书分“总论”与“本论”两部分。“总论”部分主要对人类学的范围、定义、分类进行了界说;“本论”部分又分十一项专题逐一展开论述,内容涉及人类的分布与起源、人类体质、人类心理、人类社会等领域。此书出版后,人类学“始引起学人之注意”[11]6。当然,此书也有不足之处,正如徐益棠所论:陈映璜“仅从生物的体质的观点,种族的或优生的方面加以说明而已”,因而“大都可供自然科学者之参考,社会科学者尚未加以注意也”[11]6。
梅思平1927年在《教育杂志》发表的长文《文化人类学之三大派》,重点对文化人类学中“进化论派”“批评派”和“传播学派”分别作了介绍。这是笔者所见国内第一篇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专论,其在西方人类学“东渐”过程中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梅思平在文章开篇即指出:“现代科学中,与中国人关系最切而最不为中国人所注意的恐怕就是人类学(anthropology)。”[12]1考虑到此文发表时,中国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尚停留在零星介绍阶段,相关的学术组织尚未建立,因而这里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在梅思平看来,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主要由于国内学界的两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把人类学的范围看得过小,以为人类学不过是研究各人种之肤色、骨骼、毛发等体质特征的差别及分类,所以都看作一种干燥无味的科学,引不起研究的兴趣。第二种误解是把人类学的范围看得过大,以为人类学除研究肤色、骨骼、毛发等之外,还要研究人类的心理、言语、宗教、以及一切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那么,则人类学的范围除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还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古物学、言语学、比较宗教学等一切重大的科学。[12]1
梅思平则将人类学划分为两大类别:研究人类肤色、骨骼和毛发等体质现象的为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言语、宗教、艺术、物质生活和社会组织等各种文化现象的为文化人类学。后者进一步可分为物质文化、社会组织、艺术及宗教3个部分。他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原始民族”的范围之内:“依‘人类学’三个字论理的范围而言,当然要包括世界上一切现存的及业经灭亡的各种民族之研究。但是事实上也并不如此。所谓‘文化人类学’实际上不过是‘原始民族学’,其研究的范围并不涉及高等文化的民族。”[12]2文化人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呈现出由异文化回归本土、由部落组织回归文明社会的趋势,不过,在写作此文的当时,人类学依然以欧洲之外的“原始民族”为主要对象,因而这里的判断当今看来似乎有些陈旧,在当时却是切中了人类学发展的主脉。梅思平认为,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深浅两个层面的意义:较浅的一面,是引起人们对于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兴趣;更深的一层,则是“这种科学在现时中国学术界上也是有很急切的需要”[12]2。对于后一层意义,他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当时论战正酣的“东西文化问题”——既然论争对象为文化,自然需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二是“古史问题”:“二千余年来在中国思想界上操有最高威权的经籍到这几年已经渐渐地为人所不信了,但是这种怀疑经籍的态度还是消极的入手的办法。要积极地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究竟怎样,非将全世界的文化来仔细比较一番是不可的。”[12]3这里所针对的是顾颉刚等发起的“疑古辨伪”运动。顾氏在推倒“伪古史”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由于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因而不断受到学界的非议。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学界即出现“古史重建”的趋势,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郑振铎《汤祷篇》和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即是这种趋势的代表。梅思平早在郭沫若等人之前,已经预见到文化人类学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其目光之超前应当肯定。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梅思平在文章中“用极通俗的材料和极浅显的学说,叙述文化人类学沿革的史略及最近各派的趋势,一面是想引起一般人研究此学的兴趣,一面是想作治文化史者或治经学者一种最简单的途径”[12]3。不出所料,此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沿着上述两种趋势发展:一方面是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与田野调查的开展,一方面是文史学者以之作为阐释上古文化的理论资源——后者正是早期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实践领域之一。
在孙学悟、陈映璜、梅思平等学人向国内介绍人类学知识的同时,许多刊物也开始发表与人类学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1915年,《进步》杂志第7卷第6期发表了《最近人类学遗传性之研究》。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马君武的《赫克尔之一元哲学》一文,第一章标题即为“人类学”。1918年,《教育杂志》第10卷第8~9期连载天民的《儿童游戏与人类学之意义》。1922年,《学生》杂志发表程小青的《人类学上的新发现》一文,介绍了在罗得西亚(Rhodesia)一座山洞中发现的几具人类头骨,从而验证人类学界关于从猿到直立人中间过渡阶段的预言,文中还附有几幅人类头骨演化的图片。同一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元始民族底妆饰》一文,作者署名“鸿”,文章根据格罗塞(Grosse)《艺术的起源》一书写成。就笔者目力所及,这篇文章是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最早译介。
此外,国内学界对国际领域的人类学动向也极为关注。1906年,“第六届世界刑事人类学会”在意大利召开,日本派代表参加。创办于日本的《法政杂志》对此作了报道。锺赓言将日本学者安达峰一郎的《第六次万国刑事人类学会报告》译成中文,在《新译界》杂志1906年第一至第三期连载。192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设立人类学科,《教育杂志》对此作了报道:“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向设十学科,现已决定从1928年4月起,将人类学独立成科,招收专攻的学生。主任教授尚未定人,惟该学部助教授理学博士松村瞭氏已内定为该学科助教授;此外当再物色讲师二名。”[13]
在当下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中,周作人、茅盾等学者往往被忽略。其实,早在民国初年(1911年),周作人已受英国人类学兼神话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的影响,采用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古籍中所载的民间故事(童话)进行阐释。在其之后,茅盾也对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作了介绍。诚然,他们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关系不大,但从人类学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来看,其意义不可小觑。
三、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起步
随着人类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中央研究院为开端,人类学学科建设得以启动。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该研究所下设四组,其中第一组为民族学组,由蔡元培兼任组长。早期研究人员除蔡员培外,还有凌纯声、颜复礼(F.Jaeger)、商承祖、林惠祥4人,后来又聘史图特为特约研究员。民族学组最初在南京办公,1929年三四月间迁往上海。1934年,中央研究院增设体质人类学,成立人类学组。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划归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成为“研究生物统计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惟一之国立机关”[14]。此年秋,因凌纯声、陶云逵等应云南省政府邀请赴滇从事田野考察,又聘请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吴定良主持组内事务。吴氏上任后,便着手建成生物统计学与人类学两个实验室。抗日战争中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主编《人类学集刊》,年出一卷,每卷两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继中央研究院之后,较早建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或院系的还有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1927年七八月间,中山大学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为筹备主任,聘傅斯年、顾颉刚及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为教授。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8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和民俗4个学会。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和民俗3个方面,尤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为重心。1927年暑期,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设有人类学、民族文化、民俗学等十余组[15]109。
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成立于1928年秋,最初课程体系不够完善,自1930年起开始增聘教授,并将基本课程逐渐开班。当时的3名教授中,傅尚林讲授“社会学原理”“家庭问题”“城市与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史禄国讲授“普通人类学”“初民社会”和“史前记”,陈达兼任系主任,讲授“社会机关参观”(兼社会调查方法)“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吴文藻当时任讲师,仅担任“社会思想史”一门课程。除上述课程之外,还向已修过“普通人类学”的学生增设“民族分类学”选修课,主要内容为世界若干民族的分类、分类的原理与方法、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与变迁原理等[16]。课程设置上,该系将现有课程分为人类学、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三组,“学生可就性之所近,择一组的功课选习,以资造就”[17]20。其中人类学组基本课程有:“普通人类学”“社会学原理”“社会机关参观”“初民社会”“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实习”“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17]20。1930年,清华大学还成立社会人类学会,吴文藻、傅尚霖、史禄国等教授出席,史禄国发表了题为“关于世界人类学发展及现状”的演讲。该会规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由各会员轮流作研究报告。会上还就出版刊物及邀请专家演讲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定[18]。
中国人类学界在积极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1930年9月,中国科学社选派刘咸为代表,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第十五次国际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会议”。刘咸于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为巴黎国际人类学会会员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此次会议有19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会,与会者200余人。刘咸虽然因委派太迟而未能提交论文,但在会议期间受邀用英语发表演说,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向国际学界作了介绍。由其演说,我们对人类学在当时国内大学的设置情况也可略窥一斑:
采用近代科学方法之人类学教学,在中国可谓甚新颖。现在中国各著名大学课程中,多有人类学一科,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三大纲,复分细目,与欧美各国大学相同。而民族学一科,尤为中国学者所喜研,除各大学先后设立人类学系外,广东中山大学并成立民俗学会,发行专刊,作始虽简,将终必钜,学生之习斯学者实繁有徒,将来定有不少学人,可以蔚成专家。此外政府并资送程度优秀之学生,分赴欧美各国分门作高深研究,俾学成之后,共同作大规模之探研,预料在将来,人类学一科,在中国必有长足之进步。[19]
1931年9月,国际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会与巴黎国际人类学院按照1930年葡萄牙会议议决案,在法国巴黎继续举行“第十五届会议暨国际人类学院第五次大会”讨论1930年会议未决事宜。会议有12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刘咸受教育部委派再次代表中国出席,在会议第五组(民族学组)宣读了《猡猡经典文稿之研究》和《苗族芦笙之研究》两篇论文。此外,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如北平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将有关人类学、考古学的多种学术著作邮寄到伦敦驻英使馆,由使馆转交大会以供展览。这些著作“颇得世界学者之重视”。尤其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杨锺健、裴文中二人关于“北京人”的著作,更是受到国外学者的赞许[20]。
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又多有交叉之处,因而当时许多大学新设的社会学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整合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力量。比如,吴文藻、林耀华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徐益棠、马长寿曾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吴泽霖、岑家梧、陈国钧曾在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外,从课程设置来看,当时国内大学的社会学系大都开设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如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课程纲要中,就列有社会基础、社会变迁、社会起源、社会进化、人类起源、民俗学等与人类学有关的课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由吴文藻讲授社会人类学[15]196。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部又在上海暨南大学创设人类学系,由理学院院长刘咸兼任系主任一职。教职人员中,吴士华任体质人类学教授,薛仲董任人类遗传学教授,卢于道任心理学教授,应成一任社会学教授。创办之初学生人数并不多,至第二年,两个年级的学生总数仅为19人。教学资料中,比较重要的是700多件民俗学标本,其中包括台湾高山族的日用器具和艺术品400余件,海南岛黎族器具和用品300余件,都是很珍稀的文化资料,连前来参观的外国学者都表示惊奇和赞赏。除一般教学活动外,学生中还成立了人类学会,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学术演讲,聘请著名学者讲述有关的议题。受邀前来作过演讲的有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副代表、民族学家费子智(C.P.Fitzgerald)、海关民船研究专家伍士德(G.R.Worcester)和同济大学史图博(A.Stubel)教授。由于暨南大学在当时担负华侨教育的使命,而南洋又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圣地,南洋侨胞来自各地,对于当地原住民族多有接触,因而在该校创办人类学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1]。
在人类学学科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许多人类学重要著作也不断被翻译到国内。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竟在《晨报副镌》译登至一年之久,而不为阅者所厌恶”[22]。该书译者为何作霖、欧宗佑,从1921年12月开始刊登,直到1923年才连载结束。1928年夏,李安宅完成了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一书的翻译初稿,经修改后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原著相比,译作在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地方加了按语和译注,在国内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除此之外,译介到国内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还有摩尔根《古代社会》、梅因《古代法》、陆维《初民社会》、马烈特《人类学》、穆拉利耶《社会进化史》、魏士拉《社会人类学序论》、素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编《人类学方法指南》、般尼《民俗学问题格》等[23]。正是在上述学者、高校、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之下,人类学在经历最初的介绍与传播之后,很快在国内生根发芽,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