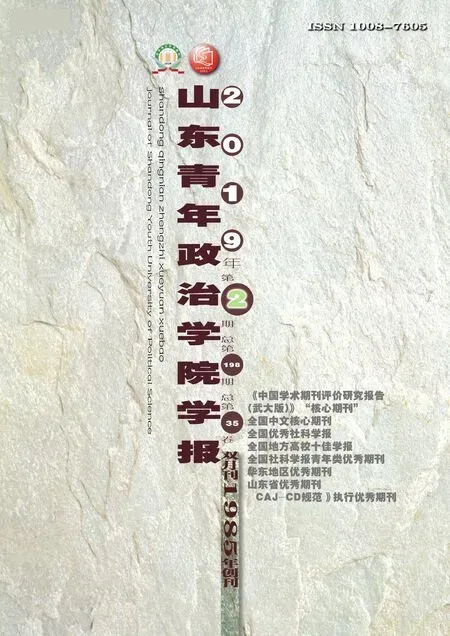略论近代以来中国儿童观的政治因素及嬗变历程
2019-02-19原琳琳何茜曦
原琳琳,何茜曦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所谓儿童观,乃是外界对儿童最基本的看法、态度、主张。不同的学科、领域会有不同的儿童观。当前对儿童观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从政治角度去探讨儿童观的则相对少见。事实上,儿童观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教育、心理的角度去探讨儿童观,往往将儿童作为自变量,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儿童更主要的是作为因变量存在。
就本体性存在而言,儿童是离不开政治的,儿童必然身处于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主体必然依据相应的政治价值、目的为儿童提供成长的环境,也塑造、安排着其成长过程。每一个政治体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其培养儿童的方式与内容的不同,既而所塑造出的儿童亦是有差异的。政治体系的存续必然依赖于政治制度的维持、机构的运作、人员的执行,必须实现相应的政治事业,而这也赋予了儿童不同的政治角色和政治任务。这种关系在近代以来的儿童观变迁中有着清晰的脉络。
一、新文化运动与儿童本位观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空前严重。救国,成为最迫切的任务。改制,成为必须的选择。清王朝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进行改革。而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看来,政治改革以图救国固然没错,但未及根本。中国的危机在于国民素质,只有通过改造国民才能从根源上解除危机。早在1895年春,严复从社会进化的角度首次提出改造国民以振兴中国,从根本上着力,提升民力、民智、民德。
此后,梁启超的《新民说》系统阐明了国民改造的思想,明确将“新民”作为当今第一急务。他认为,“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1]。制度的革新不能简单地依靠统治者一人之力,需要整个国民的合力,因此政制革新,就必须要有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而作新民,自然也就要有新儿童。《少年中国说》便是其儿童改造的思想宣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必须要养成智、富、独立、自由、进步的品质,才能让国家永葆青春富强。从器物模仿到国民改造,思想家不断深入去思索中国落后的根源。从少年强,到国民新,再到国家强,这是一条新的救国道路。但是这种以国家为目的的儿童观,仍旧没有走出国家主义的藩篱,而儿童观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中。
当政制变革以后,国家仍旧没能被拯救,政治生活也江河日下。而不断上演的复辟和复古闹剧,让人惊觉到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国家,而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新文化运动一反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传统,将个人放置于第一位。不是为了国家富强去改造国民,而是要用国家来实现个人的发展。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3]易卜生也认为:“须使个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工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4]因而,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发现”人的运动,而对儿童的“发现”亦是其璀璨的一面。
从改造到发现,便是转向以人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这是一次彻底的转变,而其矛头则指向传统的伦理政治。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乃是伦理政治的核心。辛亥革命虽然改变了君为臣纲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在家庭和社会中依旧没能改变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文化心理。而正是后两者为前者提供了死灰复燃的土壤。也正因如此,儿童和妇女始终没能从父权的牢笼里解放出来。 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三纲统治的传统社会是人的荒原,是儿童的荒原,亦是中华民族贫弱的根源。因此,我们今天不得不重新思考怎样“做人”,怎样“做父亲”。 周作人曾说:“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其来者远,未可骤详,然考虑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如何,要亦一重因也。”[5]鲁迅则明确提出,“一切设施都以儿童为本位”[6]。儿童本位观旨在将儿童从父权伦理和家庭礼教中解救出来,以人道主义和个体主义重构家庭、社会和政治秩序,实现中华民族在人伦、文化、政治上的彻底更新,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儿童就是儿童;儿童属于自己;父子间纯粹的爱。
儿童就是儿童,并不是同义反复,而是以儿童为本位去“发现”儿童。传统社会中,儿童是被放置于宗法伦理中看待,孩子行为的判断皆依照成人的规则。因此,儿童自然而然地被当作缩小的成人对待。越是懂得礼教规范的儿童越深得大人喜欢,而孩子活泼好动、无所顾忌的天性则是需要被管教、被约束的。在《风筝》中,作为哥哥的鲁迅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行为,而弟弟却恰好喜欢风筝,每次都望着空中的风筝欢呼雀跃。当发现弟弟躲在杂物间里偷偷做风筝时,鲁迅便把风筝的翅骨折坏,又将风轮踏扁。直到多年后鲁迅才明白自己对弟弟幼小心灵的伤害。大人的中心主义将儿童变成了小大人,儿童的世界不被理解,儿童本身没有得到承认。“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这样想!),用他们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7]周作人用顽童手中的小鸟形容了儿童被忽视、被抹杀的境况。而为了开辟“人荒”,“发现”儿童,就必须将小鸟当作儿童。除了攻击传统礼教,新文化运用儿童文学打开了儿童的世界,如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俞平伯的《忆》等,赵景深、郑振铎、沈雁冰亦将大量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带入中国儿童的世界。
儿童属于自己。以儿童为本位,不仅要求摆脱成人中心主义,更要打碎父权的桎梏。传统社会中,父亲对于儿子的权威,不仅体现在言行上的模范,更体现在父亲以“私产”方式对待儿童。儿童依附于父亲,没有人格和权利上的独立性。对此,他们以西方的生物进化思想发起了革命。任何生物的本能都是要保存、延续、进化自身。个体的生命必然会终结,因此才重视后代的繁衍。食欲是保存现在的生命,性欲是保存永久的生命。所以,孩子的产生乃是父亲生命自我保存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恩情。鲁迅说:“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8]因此,父权并不具有伦理正当性,孩子也不是父亲的“私产”。儿童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儿童理应和成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具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权利的保护而为礼教所戕害的生命悲剧,时常出现在鲁迅的笔下,如《明天》《药》《风波》《狂人日记》,等等。权利成为“救救孩子”的武器,只有儿童具有了权利才能真正属于自己。
既然,儿童属于自己,父子之间并不是“恩”,那么父亲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待孩子呢?消除了成人中心主义的思想和父权伦理的父子关系,就只有纯粹的父子之爱了。这种以孩子为本位的爱,便是纯粹的爱,也是完满的爱,天性的爱。用“爱”代替“恩”,是对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的一种重塑。父亲需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去理解、教育孩子,教给他自立的能力,帮他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9]。所以,养儿也不是为了防老,而是要尽父母之责帮他实现独立而全面的发展。在这种无私奉献的父母之爱中,实现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与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等人主张将这场运动限制在文化领域,还提出“二十年不问政治”。事实表明,这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时空想。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分化,不仅是文化主张的不同,更是政治道路的分野。从政治体系和政治事业来看,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属性依旧属于旧民主主义。而这条道路却难以解决中国政治的困境。“娜拉”出走以后,面临的却是一个堕落和残忍的世界。面对回身与向前的两难之境,不得不另寻他路。
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与革命儿童观
五四以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根本上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而这一新的政治体系需要与此相适应的人、事、物来支撑维系,也必然会生成相应的政治内容。这个体系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共产主义,其生成的政治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项政治事业。而阶级斗争与革命乃是体系建设与维持、事业实现与完成的基本形式。因此,新的政治体系塑造出新的儿童,新的政治事业产生新的政治角色,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是新儿童塑造与实现的方式。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改革的方式完成,但从社会性质来讲这依旧是一场革命,而此后开展的各项运动同样是以革命斗争的形式出现,直至文化大革命将革命的逻辑发展到顶峰。革命,乃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属性,而身在其中的儿童自然成为革命儿童,革命儿童观亦就此诞生。
总的看来,革命儿童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儿童是革命的儿童;儿童属于国家;阶级关系优先。所谓革命的儿童,便是将儿童卷入革命运动,塑造成革命的战士,肩负革命的使命。革命儿童又称为“红色儿童”。革命儿童的出现,让儿童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从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始,革命教育成为儿童教育的重点,从小就要播下革命的观念,阶级关系、敌我关系在儿童心中有清楚的划分。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就规定,“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10]。学校教育之外,通过大量革命的儿歌、童谣、宣讲等给儿童灌输相应的政治认识,以唤起儿童的革命热情。而塑造出来的典型革命儿童也成为孩子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如小三子、王二小、刘胡兰、小喜根、刘文学、雷锋等。与革命教育相应,儿童同样有自己的革命组织,比如劳动童子团、共产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红小兵组织等。儿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松散的团体,组织内有着严格的纪律。这也塑造了革命儿童守纪律、听指挥、顾大局的行为特征。而随着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革命事业和革命对象的变化,革命儿童所肩负的使命和承受的任务也一起改变,革命儿童以不同的身份和形象呈现出来。土地革命时期是集革命与劳动生产一体的“劳动童子”、“共产儿童”,抗日战争时期是集抗战与劳动生产于一体的“小八路”,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继续阶级斗争并反蒋拥共的“小解放军”,在建国后是参与国家建设和政治运动的“少年先锋”,是五年计划中的“小主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小兵”,等等。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革命事业逐渐走上了巅峰,革命儿童的特性也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
儿童属于国家,是针对儿童归属于家庭而言。革命儿童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儿童必然走出家庭,为了国家和革命而行动,甚至儿童反过来动员大人参与革命。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劳动生产中,儿童们还充当着“小先生”的角色,每天在放学以后,他们会进入冬学的课堂,教大人们识字,认识政治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区分阶级敌人,号召大家参加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胶东50万儿童团员中,就有35600多名“小先生”。[11]儿童的革命组织则直接将儿童从家庭剥离出来,以更高、更大的组织作为认同和归属对象,从分清阶级、敌我关系开始,直至为革命、国家献身。过早脱离家庭的襁褓促使儿童在政治上早熟,不断突破生理上的局限参与到革命的各个环节,从站岗放哨到持枪上阵,从普通儿童团到少年铁血队,从少年先锋到大公无私的红卫兵。而在革命思想不断催化,革命运动不断焙炼,革命组织不断卷入的过程中,儿童对家庭的归宿感不断被冲淡,对革命、国家、领袖的依附感不断增强。家庭只是儿童生活供养的场所,逐渐失去了伦理教化和身心归属的功能。而作为国家的儿童,组织与领袖的鼓励、嘉奖也让他们有了获得感和成就感,组织从小对儿童的培养也让政治体系和政治事业有了“接班人”。而不断深入和高涨的革命运动也逐步将儿童带离家庭、父母,参与到对敌人的斗争中,直至文革中家庭也成为革命的场所,父母成为批斗的对象。最终,革命儿童发展为儿童革命。国家的儿童从生活的弱者转变为“强者”,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同成人一样进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一样去解放他人,解放自己。
国家是阶级的国家,革命是阶级的革命。革命对儿童的教育也就是阶级教育,国家的儿童亦必然是阶级的儿童。因而,阶级关系优先自然成为革命儿童的典型特征。缺乏生活经验的儿童难以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全面的认识,简单明了的阶级划分对于他们来讲则容易把握,因而阶级的分立成为儿童构建、处理世界关系的基本图式。阶级关系成为儿童在革命中进行敌友、亲疏关系判定的依据,要么是阶级敌人,要么是亲如一家的“同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地主、日军、国民党的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儿童的行为都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明确的阶级斗争对象,而投身革命、为国奉献,也就成为儿童阶级意识和立场的外在表现。在全面革命化、政治化的生活中,阶级关系不仅成为儿童处理社会关系的标尺,亦随着革命的深化逐渐取代了家庭的伦理关系。当革命发展到极端时期,以阶级的名义背弃伦理便成为“大义灭亲”的表现。革命、国家、阶级共同形塑、安排着儿童,也是这一时期儿童观的关键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多元儿童观
文革的结束意味着20世纪中国革命的退潮,而改革开放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了一条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总的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是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断激活传统智慧的结果。而儿童观也伴随着这一历史性巨变,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状态。
首先,坚持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放弃了阶级革命,儿童已不再是革命的儿童,但是依旧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持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依旧需要青少年的进一步继承、开拓。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文中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陈云也谈到:“少先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接班人,是共产主义事业上的接班人。”[13]儿童从小要学习做“四有新人”,要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要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遵守法纪。虽已无需儿童革命,但儿童需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品质,这是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保障。199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规定:“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直到今天,“接班人”教育也是少年儿童教育的重点。儿童的“接班人”定位乃是由中国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决定了“接班人”新的时代内涵。
除了做“接班人”,儿童开始向自身回归。中国的现代化本身也就是不断融入世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掀起了对人的反思,异化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社会亦开始对革命儿童观的过失进行反省,主张重新看待孩子,新文化运动中的“儿童本位观”重新发展开来。儿童重新被当作儿童对待。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在同年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所具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具有庄严的历史意义。以儿童为本位,尊重儿童的价值,维护儿童的权利,提升儿童的素质,实现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新时期的社会共识。与此相应,儿童文学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西方的经典儿童读物《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重新进入儿童的视野,新的儿童文学也被大量译介进来,如林格伦的《小飞人》、罗琳的《哈利·波特》等。本土的儿童文学也打破了革命单一的题材模式,关注儿童的真实世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郑渊洁的《童话大王》、曹文轩的《古堡》、陈丹燕的《中国少女》、刘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岁》、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苏曼华的《猪屁股带来的烦恼》,等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儿童已不再是英勇无畏革命的小战士,而是个性鲜明、可爱活泼的真实少儿形象。
再者,儿童开始回归家庭,回归伦理。自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家庭礼教,到革命运动对家庭关系的异化,这大半个世纪中我们都没有对如何构建家庭关系进行过积极的思考。一味地模仿西方,到最后发现不但西方文化学不好,自身所固有的特色也丢失了。伴随着文化大繁荣的却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上演了邯郸学步的悲剧。中国传统造就了中国人,中国人没必要也变不成西方人。因此,文化自觉也逐渐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而经历了新陈代谢后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兴盛起来。父母与学校开始向儿童教授传统的家庭伦理、礼仪规范,从小学做一个中国人。儿童是家庭的儿童,是伦理的儿童,亦是文化的儿童。这种回归不仅关乎儿童将来如何做人、成人,关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关乎中国政治的改革与发展。
四、结语
政治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业,儿童亦不例外。儿童问题亦是政治问题,儿童观也是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综观近代以来儿童观的嬗变历程,正好走出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而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体现。从对传统的否定而全面学习西方,到对西方政治道路的否定转向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革命实践,再到中、西、马的全面融合发展。与此相应,逐步形成了一元主导,多元共融的儿童观。不可否认,这种融合依旧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多元文化和多种政治取向不断磨合、调适的过程。然而无论怎样变化,信仰、自由、道德都是作为人必不可少的要件,儿童亦是如此。在未来的道路上,儿童的发展必须要树立坚定的信仰,要过自由的生活,要养成道德的行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儿童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政治发展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