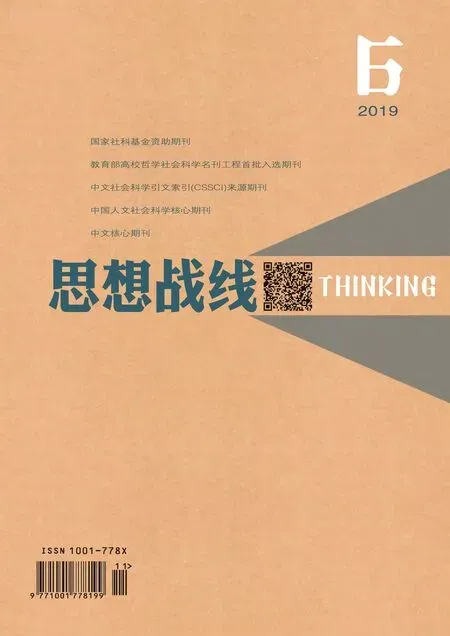范氏义庄“敬宗收族”意义再阐释
2019-02-18马秋菊
马秋菊
自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关系变迁、阶层沉浮不定,官僚家庭想要长保富贵变得更加不易;同时,随着门阀世族的崩溃,宗法下移,“敬宗收族”的观念逐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使得官僚阶层得以以聚族为契机,重建自己的根基。在此过程中,苏州范氏宗族凭借范氏义庄得以重新聚拢和崛起最为后人所称道,学界对此也有颇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单就范氏义庄立论,主要探讨义庄的发展历程或经济措施;①如 [日] 近藤秀树《范氏义庄变迁》,《东洋史研究》1963年第4辑;[日] 伊原弘介《范氏义庄租册の研究》,《史学研究》1965年第94期;陈荣照《论范氏义庄》,《宋史研究集》第17辑,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8年;王卫平《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二是将范氏义庄与范氏宗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从义庄的创立、发展和对范氏家族的作用两方面,论述创置和经营义庄对范氏一族世家大族地位长久维持的作用。②如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学术月刊》1991年10月;王善军《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范氏义庄对于范氏宗族的作用自是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是范仲淹开此风气之先?范仲淹支系又是如何利用义庄完成宗族再造?“敬宗收族”的意义在其中又是被如何阐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范仲淹创置范氏义庄的动机和范氏义庄管理的科层设计两方面为中心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并结合此后义庄的发展,进一步论述义庄创建背后的意义。
一、范氏义庄创建与“敬宗”之目标
(一)敬宗与恤宗
《礼记·大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③郑 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三四《大传第十六》,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7页。把尊祖—敬宗—收族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宗是祖在现实生活的投影,人间的化身,由尊祖而敬宗,由同敬一宗而同属一族,由宗而族,完成了宗族的构建。在宋代,无门阀世族传统的平民,无可溯之祖,无固有之宗,虽同样是倡导“敬宗收族”,但如何阐释却是另一种样貌。在宋代,践行“敬宗收族”活动最为人称道的是范氏义庄。范仲淹在创置义庄时自述: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①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告子弟书》,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2页。
虽未言及确定之“祖宗”,却以祖宗的视角,以“祖宗之意无亲疏”来说明“饥寒者吾安得不恤”,所呈现的是由祖宗认同到宗族认同,由敬宗到恤宗的直接联系。敬宗是恤宗的缘由,而恤宗又把敬宗思想落实到实处。
范仲淹在初拟的十三条《义庄规矩》中就明确以恤养的方式惠泽每一个族人。“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冬衣每口一疋,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疋。”②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1~798页。以口以房计,无论贫富,惠及全族,即以祖宗的视角等而视之,以物质保障的形式体现祖宗对子孙的兼爱。又在物质保障基础上,“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先尊□后卑□”,③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9页。以伦理秩序规范分配额度,用经济手段来实现伦理道德的推广,反过来强化族人的宗法伦理观念,强化族人的敬宗思想。
范仲淹之后,其诸子不断扩充《义庄规矩》,在规范细化之上,添设义学。教养结合,教养子弟行之以礼的同时,培养优秀子弟,借科举之途光大门楣,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壮大宗族。时人常赞:“先文正置义田,非谓以斗粟疋缣始能饱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④钱公辅:《义田记》,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0页。其“深意”就在于此。
(二)敬宗与统宗
范仲淹创义庄自述,前半段从祖宗视角强调恤宗即敬宗,后半段则一再强调范仲淹是祖宗“积德百馀年”的始发一人,因而不敢独享富贵,以期今日有颜入家庙,异日无愧见祖宗。且不说苏州范氏一族世代官宦,范仲淹胞兄仲温官至太子中舍(正五品上),与当时范仲淹所任的户部侍郎(正四品下)并无太大差别,“始发于吾”无从谈起。享富贵也非范仲淹一人,为何还要特别强调他个人富贵与“见祖宗于地下”的关系?这就要从“敬宗”的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敬宗是宗族重建的起点,只有敬宗,以祖宗为核心创建自己的伦理关系才能得到宗族的承认,才能把自己融于宗族之中。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⑤欧阳修:《居士集》卷二〇《范仲淹神道碑》,载《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44页。范仲淹也随之改名朱说。后范仲淹艰苦自励,“祥符八年,年二十七岁,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广德军司理,后迎侍母夫人”。自此,范仲淹仍以朱说之名为官一方。后范仲淹“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⑥楼 钥:《范文正公年谱》;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附录2《年谱》,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2~863页。范仲淹归宗之途并非顺畅。但自范氏义庄创建之后,“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⑦刘 宰:《漫塘集》卷二一《希墟张氏义庄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6~577页。以范公之后统称范氏一族,视范仲淹为苏州范氏绵延永续的源头。前后差别,判若云泥。
再看范仲淹以“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人家庙”来说明不敢“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其敬宗之情就别有一番深意了。范仲淹以祖宗“积德百余年”的始发者自任,以此为责创建惠泽全族的义庄。这实际暗含了他与祖宗同心同德、相通相连,成了代祖宗行事的宗子,这是原有的宗法体系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范仲淹在《告子弟书》中明确自己与祖宗关系的同时,也在祖宗的载体上进一步把“敬宗”落实到具体。
所谓“神依于主,体魄藏于墓”,①宋 荦:《西陂类稿》卷二五《祖茔祭田碑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9页。已无明确之“宗”和可载之木主时,祖坟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以“本家松楸实在其侧,常令此寺照管”,②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一《乞赐白云寺额箚子》,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7页。把苏州吴县西部的天平山白云寺改作坟寺,以祀范仲淹曾祖徐国公、祖唐国公、考周国公。此时的坟寺仅作为对范仲淹个人或其家庭恩赐的私产而存在,是对范仲淹先祖的追赐。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白云寺不仅成为了先公祠堂,把《义庄规矩》编类刻石于其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范仲淹子纯仁更是在天平山置田千亩,并入义庄。至此,天平山白云寺已俨然成为宗族依托之所在。《义庄规矩》明令:“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为子孙者所当相与扶持,不废香火。”天平山白云寺是“敬宗”的实体,是子子孙孙所当敬奉扶持的具体对象,是范氏一族宗法精神的外在表征。然而,在《义庄规矩》中,白云寺却一直作为“文正公曾祖徐国公、祖唐国公、父周国公坟茔”③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9页、第1164页、第1165页。之所在来表述,所强调的仍是范仲淹个人的支系传承。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更是于此“更作新庙,揭忠烈之榜于庙门”,④范端信:《范氏家乘》《重修忠烈庙记》,光绪三十二年。建范文正公忠烈庙于坟寺之侧,与宗族祠堂同列同尊,成为范氏一族同须敬奉扶持的对象。与祖宗同心同德、相通相连之意,具象地成为与祖宗同列同尊的祠庙,使范仲淹本身融于“敬宗”的体系之中,借由敬奉,获得了宗法观念上的统宗之实。
范仲淹以敬宗之名,代祖宗行事,明确了自己与祖宗之间的直接关系,借此融入宗族的同时,以祖宗之名重建以自己主导的宗族伦理体系。其子孙也正是沿着这一条路径最终成为义庄管理体系中不可撼动的“文正位”,成了以苏州范氏宗族的实际领导人。
范仲淹创范氏义庄所为“敬宗”之目标实则有二:大处为宗族发展,以恤宗的形式团结教育族人,达宗族长久不坠的目标。小处为支系利益,以敬宗为名,从强调范仲淹与祖宗的直接联系中,明确范仲淹本身的伦理地位,把他的支系领导融于宗族再造的过程之中。
二、 范氏义庄管理的科层设计与“收族”之效果
(一)范氏义庄管理的科层设计
随着范氏义庄的发展,经由范仲淹支系几代人的努力,义庄的管理日益规范,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层设计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级:文正位—掌管人—诸房(位)。⑤范氏义庄科层设计的史料皆出苏州范氏《义庄规矩》,按制定人的世代可分为三类:一是范仲淹于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定的十三条《义庄规矩》;二是范仲淹三个儿子(纯仁、纯礼、纯粹)于熙宁六年(1073年)至政和五年(1115年)间续定的二十八条《续定义庄规矩》;三是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续定的十二条《清宪公续定规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7~799页,第1159~1168页。)
1. 文正位
“文正位”第一次出现是在元丰六年(1083年)范纯仁《续定义庄规矩》中,此后成为义庄的常规设置。从“文正位勘会先文正公於平江府兴置义庄”“申文正位”“文正位指挥与支”“虽已申而未得文正位报,不得止凭诸位文字施行”等语可知,“文正位”是范仲淹后人中,代表范仲淹支系统管义庄事物的执行人。“文正位”不参与义庄具体事物的管理和执行,但规则方针,如普济的原则、婚丧嫁娶的份额和次序、义学规矩等,都出自于“文正文”;遇到奖励、惩罚或是有争议时,也都由“文正位”裁决。
2. 掌管人
“掌管人”是范氏义庄具体事物的执行总管,“义庄事惟听掌管人依规处置,其族人虽是尊长,不得侵扰干预”。“掌管人”是“于诸房选择子弟一名管勾”,并不限定出自某房。具体职责有二:
一是清查人口,按房分米。“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处批请。”“掌管人亦置簿拘辖,簿头录诸房口数为额”。
二是纠察违规,维护义庄财产。“诸位子弟纵人采取近坟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断。”“拆移舍屋者禁之,违者掌管人申官理断。”“诸位子弟在外不检生子,冒请月米,掌管人及诸位觉察,勿给。”“义庄遇有人赎田,其价钱不得支费,限当月内以元钱典买田土。辄将他用,勒掌管人偿纳”。
3. 诸房(位)
诸房、诸位的名称变化与范氏宗族组织体系的发展相伴,总体而言经历了由“诸房”到“诸位”,再到“诸房”“诸位”合一的过程。诸房(位)的职责主要是协助掌管人管理义庄、监督掌管人和纠查引导本支系子弟的行为。
协助掌管人管理义庄主要有三:一是登记本支系人口,掌请米历子并“签字圆备”;二是动员本支系族人,量力出钱,以助束修等费用;三是临时情况,共同商议。
监督掌管人主要是经济违规,如“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赔填”。“掌管人有欺弊者,听诸位具实状同申文正位”“掌庄子弟如有违犯,许诸房觉察”等。
纠察引导本支系子弟行为有三:一是子弟违规录名,冒请月米,诸位觉察勿给;二是子弟违规侵占义庄财产,诸位觉察,合房受罚;三是引导子弟向学,“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二)科层设计制度下的权威体系
北宋时,范仲淹支系并不居于苏州,义庄经历了两次破坏,但也借由破坏后的重整,《义庄规矩》更趋严格,形成了科层设计制度下的权威体系。
先是范仲淹在时,仅拟《义庄规矩》十三条,掌管人“置簿拘辖”,“仰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靠的是掌管人和诸房(位)的自觉遵守。“五七年间,渐至废坏”,范仲淹诸子出面续定《义庄规矩》,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在科层设计中添加了“文正位”这一层级,文正位居于掌管人和诸房(位)之上,诸事难决则“申文正位”。并请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在表面上看是请求苏州地方官府协助管理义庄事物,但从“许诸位经申文正位公议,移文平江府理断”“即不伏,掌管人及诸位申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断”等条款来看,报官受理之前是“文正位”的允许,就从侧面保证了范仲淹支系“文正位”对义庄享有绝对决策权。“南渡之后,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蠢弊百出,尽失初意。”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以承文正公之志,再次“增固旧规”,不仅子弟诸事违规皆须“申文正位”,而且不见《续定义庄规矩》“诸位不得于规矩外妄乞特支。虽得文正位指挥与支,亦仰诸位及掌管人执守勿给”一条。在强化“文正位”决策权的同时,不再对“文正位”有所限制。随着义庄事务扩及范氏一族衣食住行、教育礼仪方方面面,范仲淹支系也间接获得了范氏宗族的最高执掌权,成了无名的族长,弥补了无宗子核心之弊。
范仲淹支系通过制定《义庄规矩》建立起宗族核心支柱体系。在“文正位”之下,掌管人和诸房(位)也从经济管理着手,由义庄稳固宗族体系。
从管理科层来看,文正位之下是掌管人。掌管人是义庄的执行总管,但无决策权,更似职业经理,也以经济的方式奖励和惩罚。如“掌管子弟若年终当年诸位月给米不阙,支糙米二十石。虽阙而能支及半年以上无侵隐者,给一半”;“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赔填”;“义庄勾当人催租米不足,随所欠分数克除请受”;“义庄辄令墓客充他役者,罚掌庄子弟本名月米一季”等。这是用经济利益敦促掌管人维护好义庄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稳固义庄的基底。
掌管人之下是诸房(位),诸房(位)对子弟的经济分配和经济纠察都是在掌管人管理之下执行,除非掌管人有所违犯,否则诸房(位)都无超越掌管人的经济权力。但事有例外,诸房(位)合议以决断时,诸房(位)就成了超越掌管人的宗族集体。如“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只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方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等,在触及宗族利益更为核心的发展和伦理道德方面,诸房(位)就以宗族集体代表的形象支配义庄财产,救亲戚乡里于急难、助子弟以学行,体现了宗族以伦理道德和集体发展为指向的思想观念。
诸房(位)本身也借由经济的分配和纠察逐渐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体。从《义庄规矩》“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处批请”,无特定之人管理房内事物,到《续定义庄规矩》“诸位请米历子,各令诸位签字圆备”,由特定之“诸位”管理本房事物,族下支系建成一个有领导的集体。又从《续定义庄规矩》“掌管人侵欺,及诸位辄假贷义庄钱斛之类,并申官理断偿纳,不得以月给米折除”,只需自行承担违规行为,到《清宪公续定规矩》“有违犯之人,诸房觉察,申文正位,罚全房月米一年”;“掌庄子弟如有违犯,许诸房觉察,申文正位,委请公当子弟对众点算,取见实侵数目,以全房月米填还,足日起支”;“岁寒堂除科举年分,诸位子弟暂请肄业,余时不得於内饮宴安泊。如违,罚全房月米一月”等,子弟犯错全房受罚,以经济利益引导子弟明晓宗族是一个同生共荣的集体,诸房(位)与诸房(位)子弟合为一体,“房”的组织性不断强化,范氏宗族也由生活化走向了组织化。
总之,通过范氏义庄“文正位—掌管人—诸房(位)”三级科层管理,范仲淹支系借由最终决策权,成为范氏一族实际上的族长,占据了伦理的核心地位;范氏一族也在享受义庄物资配给和赋予其上的管控之中,由一个生活化的分散族群聚拢成一个组织化的宗族集体,实现了族聚于一体、合力发展的“收族”目的。在聚族之上,以中间层掌管人对义庄经济的维护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义庄土地长久之利,再以仪礼教养相引导,使“子弟知读书之美”,由义庄长存到宗族永聚,由子弟发展到宗族长久,以期实现宗族绵延永续的目的。
三、范氏义庄的影响
(一)示范效应下义庄的发展
宋人赞范仲淹义庄之举曰:“先文正置义田,非谓以斗粟疋缣始能饱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其“深意”为何?钱公辅释之曰:
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今观文正公之义,其与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义垂於身后,其规模远举又疑其过之。①钱公辅:《义田记》,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0页。
范仲淹以“亲亲”之意为引导,借“敬宗”之名,建义庄来恤宗、统宗,使族聚于一处;再由义庄科层管理的逐渐完善,把思想观念落到实处,“仁有等级,而言有次序”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使宗统于一体。思想观念与组织形态的相互结合,最终完成了苏州范氏的宗族再造。在此之上,是土地为基础建立的教养结合的宗族发展保障体系。
土地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建立在其上的保障体系可以长久地施行,保证了组织的延续性,使宗族由分散的个体开始凝聚成有组织的集体。在宗族经济保障之上,是以养育德、以养寓教,在使子弟明伦理道德,为一方表率的同时,辅之以义学等“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的措施,借读书应举之途,巩固和增强本族的综合竞争力,使得范氏一族在社会流动加快,世家大族骤盛骤衰的浪潮中维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自公作始,吴中士大夫多放而为之”,①刘 宰:《漫塘集》卷二一《希墟张氏义庄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6~577页。直至南宋,士大夫或“遵文正公旧规”,②胡 寅:《斐然集》卷二一《成都施氏义田记》,尹文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08页。或“仿佛范文正公义庄之意”,③咸淳《玉峰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5页。仍以范氏义庄为表率,以义庄之形,行敬宗收族之实。
自范仲淹创范氏义庄,在苏州的周边地区及范仲淹的亲友群体纷纷仿效创建义庄。这些义庄基本上都延续范氏义庄凭个人之力,以土地为基、以养聚族的特性,如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④《宋史》卷三三一《韩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67页。黄振妻刘氏“斥嫁资以规义田,均给娴族”;⑤万历《绍兴府志》卷四五《人物志十一·孝义》,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曾巩“置义田于临川郡城之后湖、与属邑金谿之南原,立为规约以惠利其族”;⑥虞 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五《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0页。丁思妻谢氏“割己田二千亩、宅一区为义庄义宅,以供祠祭,以赡族人子孙”;⑦嘉靖《江阴县志》卷一八《列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韩维“其居家,俸赐悉以均给宗族及故人子弟,周恤之甚厚。方闲退时,聚族数百口,置田数十顷,以为义庄,抚孤幼尤力”;⑧韩 维:《南阳集》附录《韩维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5页。张恪“择良田数顷为义庄,宗族诸事取给焉”;⑨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五八《孝义》,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2579页。王汉之“买田乡里,䟽宗群从均济若一”;⑩程 俱:《北山小集》卷三四《赠正奉大夫王公行状》,《四部丛刊续编》第398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魏宪“增广义宅、义庄,以衣食疎族”⑪⑪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二《故显谟阁直学士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3页。⑫万历《绍兴府志》卷四五《人物志十一·孝义》,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⑬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九《孙君墓表》,载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75页。等。这些义庄延续了范仲淹“祖宗之意无亲疏”的观念,从祖宗视角的关怀恤宗,非单给衣食,而是关乎宗族礼法的丧葬祭祀等事都有涉及,并制定相应的规约来规范族人。以土地为基却不以生产为务,讲求分配、消费,以分配、消费的指向来表达对族人的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大夫或其家人创建义庄远非单纯的扶贫济困,而是带有强烈宗法意识的宗族再造。
同时,以个人之力创宗族义庄,又与前代共建族产大相径庭,创建者成了族产分配和宗族规范的核心,也借由族产的分配和制定规约,宗族的伦理核心也出现相应的位移,形成以创建者或创建者支系为核心的伦理秩序。诸暨黄氏宗族即为一例。诸暨黄氏本是地方小族,后黄振妻刘氏“斥嫁资”建黄氏义庄,并立规矩以约族人,族众日聚,黄氏渐大,后诸暨黄氏便以黄振所建望烟楼为宗祠堂号,以此为宗,且随着诸暨黄氏族人的迁徙,“望烟堂”也成为了江浙一带许多黄氏族人通用堂号。⑫⑪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二《故显谟阁直学士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3页。⑫万历《绍兴府志》卷四五《人物志十一·孝义》,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⑬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九《孙君墓表》,载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75页。
随着义庄的普遍建立,南宋时,创建者的身份出现相对下移,由京官为主变为地方官和平民为主;在财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义庄的职能也发生转变,开始由聚族保族转向更为实际的济族助族,救济性超越了保障性,呈现出宗族救济的特征。但虽言救济,关乎宗族礼法的婚丧嫁娶祭祀等事仍是义庄支出的重点,救济的对象也仍然按照宗法伦理,“长幼亲疏,咸有伦序”。⑬⑪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二《故显谟阁直学士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3页。⑫万历《绍兴府志》卷四五《人物志十一·孝义》,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⑬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九《孙君墓表》,载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75页。而且只要力所能及,义庄皆沿袭土地为基础的教养结合的宗族发展保障体系。上犹钟氏、乐平王氏、海盐鲁氏、休宁汪氏、崇安江氏、苏州叶氏、莆田方氏、仙游郑氏、永丰俞氏、镇江汤氏等族的义庄①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九《输石卫乡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4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3页;孙 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八《宋故资政殿大学士王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6页;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七《鲁文谧》,《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9页;《新安旌城汪氏家录》,载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徽学》2003年第1期;魏了翁:《鹤山集》卷八三《知南平军朝请江君埙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2页;陈 起:《江湖小集》卷四一《喜义庄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1页;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一二《莆田方氏义庄规矩序》,《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84页;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六《提管郑中实先生鼎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6页;嘉靖《永丰县志》卷四《人物·孝行》,载《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至顺《镇江志》卷一九《人材》,杨积庆,贾秀英等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莫不如此。这些义庄的创建者或起于微寒,或历经宗族兴衰,更知聚族合力和读书上进的重要性,正如叶茵在《喜义庄成》所言:“以义名庄遗后昆,隐然文正典刑存。当知疏远诸亲族,同是高曾下子孙。先世家风传不坠,废祠香烬喜重温。更能培植诗书种,忠孝他年萃一门。”②陈 起:《江湖小集》卷四一《喜义庄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1页。义庄之于宗族,不仅是聚族保族的依托,还是宗族能够培育子弟向上发展的支撑。以范氏义庄为范,时人所期待的是“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③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载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1页。
(二)义庄与国家基层治理
“先文正置义田”深意的一面是为族,另一面则是为国。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源,仁民爱物是流,若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矣。范仲淹正是沿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古训,以宗亲之爱为仁爱万物之根本。以义庄为起点,教养结合,在宗族内部实现家给人足的同时,通过义学等教育形式,使子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④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载朱明勋《中国古代家训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40页。形成由家及国,时和岁丰的局面,希翼达到兼济的目的。后人常赞之曰:“本朝文正范公置义庄于姑苏,最为缙绅所矜式,自家而国,则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知已。”⑤胡 寅:《斐然集》卷二一《成都施氏义田记》,尹文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08页。
这是范仲淹通过范氏义庄所表达的天下之思,也体现了士大夫群体的家国之情。中国古代士大夫皆有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并思在合一地形成了以家喻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这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展开,家就成了规范秩序的起点,由家而国,形成层层递进的圈层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士大夫观念所指的“家”并非分散的个体小家庭,散沙一般的个体小家庭和简单的家庭关系无法承载和诠释复杂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仪礼秩序,因而士大夫常在更大的范围——宗族内实践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秩序。
范氏义庄的创建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修齐治平的范本。通过创建义庄,不仅把“敬宗收族”的理念落到实处,完成了宗法秩序的重建和建立宗族长久发展的根基,而且把宗族的伦理道德和仪礼秩序进一步往外延伸,在更大的社会实践中施展他们的抱负,这在南宋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义庄救济日益成为地方救济的重要方面,有关乡亲常赖义庄而活的记载日益增多。王诏“有田数顷,置庄,名曰布施,专济族党里闾之贫者,邑人德之”;⑥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四《摭遗》,载李先勇,王会豪,周 斌等校点《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6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1页。陶士达“为义廪,几以赒族姻,为义薪,几以平市估”;⑦周 南:《山房集》卷五《陶宣义墓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页。舒邦佐“尝买田二千亩为义庄,以赡亲故之不给,其乡邻之无告者人食其德,至于今”;①吴 澄:《吴文正集》卷七七《故平山舒府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4页。季逢昌“有疾辞归,惟义是尚,立义庄赒孤贫婚丧,仰给者无算,咸称为长者云”;②嘉靖《常熟县志》卷九《列传》,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第1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毛拱巳妻董氏,以“虽贵贱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实同体也;古者比闾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捐金市田,岁储其入,而昏嫁而丧葬而疾病而贫不能自赡者,于我乎给”。③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四《毛氏慈惠庄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5页。借由义庄的稳定性,为地方救济注入一股较为稳定的经济力量,成为地方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同样地,以有针对性的救助把地方社会也逐渐引导到伦理规范和仪礼秩序之中。
其次,部分士人将义庄教养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始推及乡里。林国钧“建红泉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赡四方从学之士”;④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二《人物》,载刘兆祐《中国史学丛书》第3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3982页。钟鼎“偕姪日新,置义庄、建书院,延师以教乡族子弟”⑤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九《输石卫乡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4册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3页。等,教之养之,维持地方经济根基的同时推动地方文化教育,把宗族的教养体系推广到地方,使地方也形成长效的稳定发展体系。
更有甚者,借由国家权力的部分下移之势,一改融乡亲于宗族的救助方式,开始超越宗族的职责范围,借由义庄参与到基层的救助体系。武宁田氏宗族主导的希贤庄,仿效义仓,以宗族资产作为贷本,春散秋敛,在政府主导的义仓频频出现挪作他用、莫名侵占的情况下,武宁田氏以“民自为之而官夺之,谁敢哉”⑥姚 勉:《雪坡舍人集》卷三五《武宁田氏希贤庄记》,《宋集珍本丛刊》第8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37页。的气概,主持乡里赈济事务,利用宗族亲缘优势,子弟协从合作,变临时帮扶为长效管理,也借由制度化的管理,使宗族管理部分地融入基层社会的治理当中。台州赵氏宗族,在赵处温、赵亥兄弟的主导下,“出义庄田三百亩,以供义役,岁储粟千石以助乡之贫而无敛,及婚丧无力者”。⑦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八《台州府》,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7,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242页。以义庄为后盾,在常规的扶弱济贫、婚丧嫁娶之外,直接参与政府基层治理最重要的职役之中。这种以宗族之名参与基层治理的形式,为宗族与地方的融合开启了新的篇章,掀开了族权地方化的一角。
总之,士大夫建立义庄的出发点是为了实践“敬宗收族”的观念,但家国一体的宗族观念和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使得士大夫终会将族推向乡,融义庄实践于国家基层治理。在此后的发展中,也的确出现诸多跨宗族的通过义庄管理地方的事例,如四明乡曲义庄、衢州乡曲义庄等。这些以“理义淑士心”的乡曲义庄,把伦理教化与经济救助结合到一起,由族而乡,积极地维护着基层社会秩序。
此外还应注意到,虽然士大夫是在修齐治平理想的指导下参与国家社会基层的救济和管理,但其活动本身却并不完全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产物,而是儒家伦理道德与社会发展、地方需求互动的产物,所以不能完全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去解释义庄实践的过程。而应该反过来,从以义庄为核心的社会实践中,去理解和解释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观念、宗族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
儒学本身就无特定的含义,所呈现的更多是社会治理的技术,儒家伦理道德所呈现的“敬宗收族”也好,修齐治平也罢,并非无用的说教,而是士大夫借由种种实践对社会关系的调理。通过义庄的实践,士大夫完成宗族身份认同的构建和强化,并将其与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相连接,进而实现了宗族身份认同、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小 结
义庄是伴随宗族复兴运动而出现的新型宗族经济组织,肇始于范仲淹所创建的范氏义庄。范仲淹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在范氏义庄创建之初就带有了强烈的伦理诉求,并通过恤宗教养子弟和统宗统族于一体的方式,表达了其“敬宗”之目标。此后,范仲淹及其支系,通过义庄“文正位—掌管人—诸房(位)”三级科层管理的设立,实际有效的管理运作,使范氏一族由生活化的分散族群聚拢成一个组织化教养咸备的宗族组织,达“收族”之效果。原为宗法伦理意义上“敬宗收族”在范氏义庄的实践中已转变为更具实践意义的道德行为和组织体系。
但有先忧后乐人生格局的范仲淹并不止步于此,“先文正置义田”之深意除了有为族的一面,还有为国的一面。他以范氏义庄为起点,教养结合,在实现宗族内部家给人足、团结有序的同时,也通过族人知理明义的形象把家国之思展现给世人。范仲淹以宗亲之爱为仁爱万物的根本,自家而国,层层递进,把散沙一般的个体小家庭和简单的家庭关系无法承载和诠释的复杂儒家伦理道德和仪礼秩序,以宗族组织的形态呈现给世人,使儒家伦理道德和仪礼秩序成为真正可看、可触、可行的实体。
在范仲淹之后,无数怀着绵延永续希望和修齐治平理想的士人,他们群起而仿之,以义庄为手段重建宗族体系,并在理想和信念的感召下,突破宗族的界限,以义庄式的组织体系参与地方救济和基层治理,在扩大宗族的社会影响力之上,以经济的手段践行着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义庄成为士人们把理想落实到实际的途径之一。
义庄作为宗族最具生命力的经济组织之一,延续近千年,直至现代土地制度改革才彻底消亡。在面临社会价值观重构的今天,家风建设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从具有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意识的宋代士人身上,找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从伦理认同角度,发挥宗族社会认同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