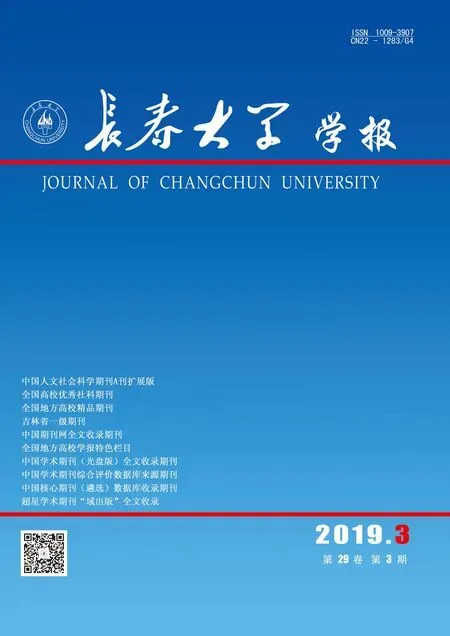徽墨装饰艺术中的文化和审美来源
2019-02-16江保锋
闻 婧,江保锋
(1.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书写工具,制墨工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统制墨工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就是其装饰图式的艺术呈现力十分丰富,使墨锭兼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特质。在我国制墨工艺中,徽州制墨(徽墨)最具代表性,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是徽墨的装饰图式,蕴含着中华经典传统文化及新安理学和徽州区域审美的多重文化属性。徽墨装饰图式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和延承有着很高的视觉价值,体现着鲜明的本土文化和审美特色,已成为徽文化代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来源于传统经典文化
徽墨装饰在题材和内容上均受到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呈现出经典传统文化底蕴下的美学本质和价值取向。徽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以新安程朱理学为核心代表与道德准则,尤其是新安程朱理学中的礼仪规范是徽墨装饰范式的宗元。新安理学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为实践原则并逐渐形成徽州文化的基础特质。徽州文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新安理学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等社会伦理与纲常作为徽州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这与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中“崇儒尚礼”的道德观念一致。新安程朱理学把崇尚儒家文化作为内核融入到各类艺术创作观念之中并始终指导着艺术的实践环节[1]。因而,在这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徽墨装饰中的艺术图式所呈现出的文化和审美内涵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1.1 教育为先
与徽州文化中的其他艺术形态一样,徽墨装饰艺术图式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性”两种显著文化特色。与装饰艺术特质相比,其呈现出的教化作用更加突出,徽墨装饰艺术表达出的内涵更加明显,为其艺术性和审美性积累了丰富的视觉语言。这种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性”的文化表达是建立在具体形象的再现之上的,通过概念的相近性与通俗化,逐渐引申为某种文化底蕴下的思想或情感表达,这种表达的方式往往具有文化共识性,对世人或后人有直接的教育作用。徽墨装饰艺术呈现出的题材和图式内容,都是传统文化共识体系下的不自觉流露,有明显的儒文化烙印,是中华优秀文化母体下的子体。
1.2 助力人伦
徽墨装饰艺术体系中,以“成教化,助人伦”为表达手段的图式十分常见,尤其是明清时期以后的徽墨装饰,受徽州传统宗法观念和徽州商业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逐渐在政治仕途和经济地位方面确立了具有血缘和人脉关系下的“仁孝”观念。当然,这种“仁孝”观念跳不出儒家文化的“孝道”基础,但徽文化中更注重反映的是生殖和繁衍这一通俗主题,我们可以将这一主题概括为传统的继嗣观念,这种观念以血缘宗亲或者说是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为维系核心,全面强化了子女对父母及长辈的尽孝理论,在适应传统文化脉络的宗法观和商业观念下,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形成习俗,甚至逐渐形成了绵延家族生息命脉意识的子孙观[2]。明代徽州的制墨大家程君房在其著名的墨谱《程氏墨苑》中,就将子孙观念文化背景下的装饰图式《百子图》作为对应性体现图式。此图在表现形式上将民间装饰艺术中的各种儿童形象用罗列的手法融会于一幅画面之中,直接表达了徽州宗族观念下人丁兴旺的朴实观念,在继承性和宗族延绵观念上寄予了强烈的愿望。
1.3 朴素观念
在徽墨装饰艺术图式中,诸如以葡萄、石榴、瓜瓞等为代表的具有旺盛繁衍能力的植物纹饰较为常见,也反映着某种文化的期望与寄予,体现出《诗经》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朴素繁衍观,同时也是承袭着中国本土哲学体系的文化原型。这种具有强烈繁衍和生命承袭性质的徽墨装饰图式成为了重要的文化题材和表达内容,较为著名的《石榴百子》墨就是其中的代表。
1.4 植根经典
在明代徽州出版的重要墨谱图式中,《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都反映和记载了大量有关儒家题材的图式作品。这些图式的文化来源大多出自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和《易经》,尤其是将《易经》中的“太极图”以及“伏羲六十四卦”图式作为具有文化象征性的徽墨装饰图案来源,使实用性的墨锭成为具有富含哲理和深厚传统文化与历史底蕴的文化性商品。受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徽文化将儒家“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徽州人在“崇儒尚文”方面的思想根深蒂固,例如在著名的徽墨装饰作品中就有“送子赶考图”墨、“折桂有望”墨和“十八学士”墨,反映出徽州文化在中华优秀文化体系下对“入仕”的强烈愿望和向往。因此,徽墨装饰图式俨然成为了儒家文化体系下教化后辈的“教科书”,这与传统文化的积淀有着直接关联。
2 来源于徽州区域性创作主题
徽墨装饰艺术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归根结底还是与域内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有着密切的关联,受徽州区域文化影响,徽州区域内的独特自然地貌加上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儒家道德观,为其在题材选择上创造了生动而具体的形象蓝本,展现了徽州区域内的丰富社会生活和人文思想情感,不仅在审美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更包含着特定社会感情下的意识形态,从一个较为特殊的艺术视角鲜明地映射出本土文化的面貌特征。徽墨装饰艺术在内涵上源于传统文化与徽州区域文化,借助徽墨的视觉表现形式传达古徽州区域内特有的社会生活审美意识,通过徽墨的使用传播,将这种人文式审美规则在潜意识的视觉感受中影响着文化受用者。
2.1 田园主题
徽墨装饰艺术的创作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主体审美,图式的主题内容是由区域内主体的艺术创作者完成的,所以创作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创作者所处环境和对社会认知的影响。徽州历来重视教育,域内民众长期积累了较好的学识和素养,创作者对包括景观在内的审美认知都能从文化的视角中加以理解和审视。徽墨装饰图式的创作者在“崇儒尚文”的传统文化和本土民俗文化的熏陶下,融入自己对乡土生活、人生感悟以及对社会情感、图式趣味的认知作为图式创作的源泉,加之对自己内心的审美感悟,把常见的视觉图式化作内在的创作主题,往往容易获得视觉呈现方式和审美感受上的亲切感[3]。这种广泛表现徽州区域内世俗生活和民间情趣的徽墨装饰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人文性装饰艺术气息。在徽墨装饰中,“耕织图”套图就是以描绘徽州本土民俗为主题的图式,画面采用系列作品的形式展现,运用纪实性的描绘手法把徽州人们生活中的春耕秋播、浇灌采摘、纺纱印染等全部的劳作过程呈现在徽墨的装饰之中,将徽州人家的劳作场景和民俗情趣与自然山水有机地整合在方寸画面之内,视觉效果生动而自然,运用了较为直观的图式叙述手法来反映本土人民的勤劳,富含极其浓厚的乡土气息。
2.2 山水主题
徽墨装饰艺术中的曹素功墨是知名的徽墨品牌,在其“紫玉光”墨的装饰图式中,“黄山图”就是依托徽州境内知名的黄山风光而创作的徽州集锦墨。“黄山图”将黄山的气韵通过著名的三十六峰整合为一幅套图,以中国传统书画白描的手法,展现了黄山的气势磅礴。这些对徽州区域内景观的视觉传达,在反映着徽州区域内文化和艺术风貌的同时,也体现着徽州人对故土热爱的内在感情。其视觉表达通过徽墨的传播也为其他地区的徽商以及使用者提供了一种艺术范式,使观看者产生一种对文化的亲近感和对故乡的思恋之情。
3 来源于徽州区域性审美
徽墨装饰艺术的审美特质受徽州其他艺术门类的审美影响。从地域文化的特性上看,在人类漫长的文化历史进程中,自然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不同区域内的文化和审美有着不同的表现态势,每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又必然会产生与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相对应的群体性审美心理,并逐渐演变为有着显著艺术特征和艺术符号的伴有一定艺术精神特质和审美共性的艺术遗产,一旦形成区域内的审美共性,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化的结构,产生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共塑作用。
3.1 本土画派
在徽州文化艺术体系中,“新安画派”是徽州所有艺术领域中的突出代表。新安画派的视觉表现以徽州地缘和地貌为蓝本,在强调师法自然的同时,也注重创作者的情感抒发,将新安画派审美特质中的孤傲、倔强和冷逸之情凝聚于墨笔之端,在画家“立于儒”“修于禅”的文化情感下,将新安山水的“荒寒自然”塑造于“渴笔润墨”的粉本之上,用空灵超脱的主体精神烘托画境,通过人格化的艺术手段将高洁的气节和精神传达于作为视觉载体的画纸之端,以独特的画风来体现画家的精神面貌和时代审美。“新安画派”所形成的独特艺术体系,以鲜明的区域艺术特性为徽墨装饰艺术中经典的图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视觉素材,可以说,以“新安画派”为代表的徽州艺术门类直接影响了徽墨的装饰范式的发展。徽墨装饰中关于图式的构图法则、视觉布局都直接来源于“新安画派”的视觉语言模式,徽墨装饰的主题内容可以直接将徽州的自然风土人情变为画面的主要表达对象,在呈现出的语言格调上也与“新安画派”相通。在徽墨装饰工艺的图式设计环节中,“新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丁云鹏等都直接参与了绘制工作,使徽墨的装饰在内涵上始终与画派特色保持一致,呈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3.2 广纳群艺
除了徽墨装饰艺术在绘制环节中融合于“新安画派”的艺术形式以外,在墨模的雕刻工艺环节中与徽州版画相互影响和补充。《徽派版画史论集》的作者周芜在陈述徽州版画时说,徽派版画技术的高度发展,从传统的墨模制作中得到了启发,看来是不会有异议的[4]。包括徽州著名的“黄氏刻工”在其技艺发展中都受到“墨模”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启发,再加以融会贯通。可见,徽州版画与徽州制墨工艺在技术和图式资源上融会贯通,相互提升区域内艺术门类的审美价值。
4 来源于消费群体的精神需求
作为徽墨消费群体,个人精神需求也直接影响着徽墨装饰图式的文化取向。徽墨的消费者都是有一定审美情趣和精神取向的文人,其价值行为准则是由内化了的精神需求所决定的。
4.1 迎合文人
由于传统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封建意识形态之上的附属品,经济服从于上层建筑和上层文化,文人阶层正是控制封建社会话语权的群体,可以说,整个封建社会就是围绕文人思想运转的社会。人在商品艺术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主导性,恰恰徽墨的消费群体又直接是文人群体,更加深了制作工艺的文化关联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徽墨工艺尤其是徽墨的装饰图案必须要迎合文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万历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徽州制墨行业竞争逐渐激烈。制墨作坊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在制墨材料上下足功夫以外,更加看重的是装饰设计所呈现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内涵,以便迎合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文人在无法满足主观化和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时,往往定制自己喜爱的徽墨产品,甚至直接参与制作,这些署上自己名号的自制墨将文人自己独特的感受寄托在装饰图式上,用以传达理想境界或表露闲情逸致或以图言志、以图怀咏,再加上精美的题款点缀,显得异常雅致。自制墨为文人社交和突显自己的独特审美创造了传播渠道。
4.2 挖掘内涵
在明代制墨名家方于鲁和程大约的墨谱图式中,著名文人的书法作品十分常见,与墨谱中的其他图式一样,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式,为徽墨装饰增添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价值。另一种和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装饰图式就是与文人生活中的闲情逸趣相伴的物件,例如“屏风”。“屏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居住环境中是一种常设构件。在传统绘画中,屏风有着构建诗意空间和视觉想象的作用。在著名墨谱《程氏墨苑》中有一幅记载“何修学海”的图式,其视觉空间中设置着与文人生活关联密切的书架、太湖石和竹木、屏风等物件。屏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分割画面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又能突显其文化象征。屏风和太湖石以及竹木景观在中国文化中都能突显文人理想化的生活,再配以适当的人物活动,将文化和自然并置于具有人文气氛的场景之中,传达文人理想化的远离尘烟的处事生活方式。
4.3 体现形式
徽墨装饰中对于与文人相关的视觉符号往往采用一种隐喻的表现手法,包含着具有直接意义的视觉形象,是一种诉诸于语言表达之上的意向性视觉表达。在中国哲学体系中,这种传统的文化符号具有儒学“泛爱论”属性和“比德”属性,往往具有以物言志的思维传达特点。比如在清代汪节庵的“唤卿呼子谓多事”墨中,图式中以童叟对坐为视觉主题,但在墨的四周辅以兰花与荷花等代表文人和君子含义的特殊植物,这些生生不息的植物图式为文人的“儒气”提供了启示,为徽州人把教育融入生活化模式以及人与自然的朴实关系创造了一种文化空间,起到教育和勉励后人在做人和做事上的普适性原则,传达着美好的生活理想。对于这种具有文人象征含义的物件在视觉上的运用不仅是通过平面图式来表现的,还有一种手法就是在轮廓造型中直接运用,在墨模的雕刻环节直接将徽墨的轮廓进行形式仿生,压制出丰富的墨锭造型。比如《方氏墨谱》和《程式墨苑》中都有与“竹”式造型有关的墨锭,方于鲁的“玄池竹”墨锭就是将“竹子”的视觉形象用来直接表现的代表。此外,其他形制不一的徽墨诸如圆饼形的“龙蟠墨”和“琴式墨”都具有外观造型上的直接美感,在传达文人精神与节操层面的含义上表现得自然而圆融,和谐而统一[5]。
5 结语
徽墨在发展之初以实用性为目标,注重材料考究层面,随着流通范围和影响的扩大,徽墨逐渐提高了装饰方面的艺术性。影响其装饰形式的最主要因素首先是处于文化层面的传统人文,其次是在徽墨流通过程中使用者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再有是制作者为迎合消费者而采取的图式设计策略,均可体现徽墨在制作和流通中的精神和文化需求。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能够全面地映射出徽州文化背景下的民俗、教育和生活的状态,挖掘和研究徽墨装饰的文化影响、题材来源和审美情趣以及文人的情感需求,有利于提升本土审美取向和延展徽州文化的传承脉络,为徽墨装饰艺术在视觉图式方面融入新时代的视觉洪流提供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加上徽墨在实用性和审美性上的共生关系,使徽墨成为我国封建时期文化传承的标杆,其装饰特色在视觉呈现发展史上具有时空穿越和文化浸润的特点,并逐渐散发出独有的芬芳,体现着区域价值观下独特的心灵密码,阐释着中华文明下的美学价值和人文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