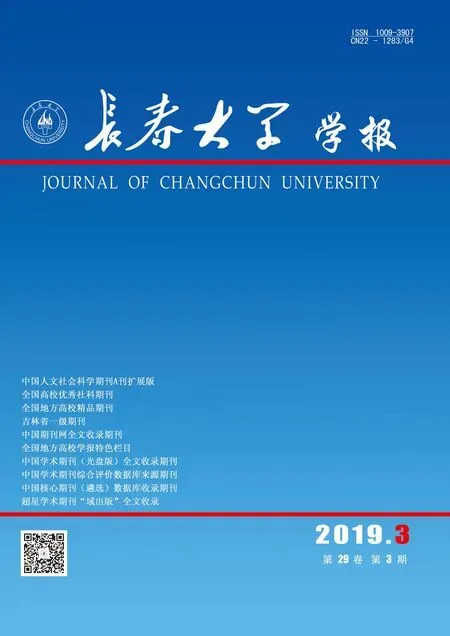词汇修辞偏离视角下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2019-02-16刘春娴杨劲松
刘春娴,杨劲松
(广东医学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1 马尔克斯的爱情情结与疾病书写
爱情、疾病、死亡、孤独等主题,始终贯穿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涯。其中,疾病话题不仅一次地出现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早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就精心刻画过马孔多小镇的人们患上了“失眠症”和“健忘症”等“会传染的”疾病情景。这些疾病的症状是:病人身体永远不会感到疲惫,他们会忘记现实,甚至忘掉一切。从隐喻意义层面分析,“失眠”和“健忘”可以被看作是拉美地区人民在被殖民和被外来文明“异化”之后对自身文化根基的遗忘。一般而言,疾病属于本质性的事实范畴(自然生理现象),但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并不单一地指向医学领域,通常是跨领域地映射指涉性的意义范畴(文学、道德、文化、政治意义)。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继其扛鼎之作《百年孤独》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主人公阿里萨和费尔米娜从懵懂少年到垂暮之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阿里萨对费尔米娜的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爱情可以超越阶级,超越年龄,超越一切界限。书中关于爱情的描写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刻骨铭心,直击灵魂,道尽了爱情的种种可能:爱情可以是年轻的、衰老的、精神的、肉体的、忠贞的、神秘的、粗暴的、简单的、放荡的、柏拉图式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这一部大部头小说展现了马尔克斯对爱情主题和疾病书写的偏爱,书中对疾病“霍乱”的描写可见一斑。爱情、战争、苦难、死亡,或秩序的失衡,或环境的破坏等,既是拉美地区罹患的苦难史,也是对“疾病”常规意义上的偏离。从词汇修辞偏离角度出发,通过分析“霍乱”的词汇偏离操作过程与意义,有助于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对大时代背景所作的现实主义描绘,以及马尔克斯借疾病、爱情、历史和政治叙事展现的关乎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文关怀。
2 词汇偏离与意义
说到“偏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保留部分常规的偏离形式具有致奇的修辞效果。”[1]从语言层面指出了偏离产生修辞效果的可观性。现代语言学派代表沙尔·巴依认为,偏离就是被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词汇表征,并且“同一个词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具有纯粹的智慧意义,或者具有主观意义或情感意义”[2]。杰弗里·利奇在其《语义学》一书中,把最广义的词义(意义)划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3]。词汇的偏离表征具体表现为“意义位”上的多种表达方式。利奇将意义研究置于各种语境之中,强调了具体语境对意义的影响。“实际上,每个单词在一次新的语境中,意义都会与语境互动而发生偏离。”[4]文章试以《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核心词汇“霍乱”为分析对象,探索了当词汇置于不同的语境时,其作为语言符号如何与具体语境产生互动而形成偏离致奇的修辞效果。
所谓“疾病”,从表面上看,是医学范畴的事实现象;从修辞层面上看,疾病运用偏向于指涉性的意义范畴;在美学价值层面,“疾病”一词在内涵上指向医学,在外延上承载着道德评价、价值判断、社会状况、政治表现和意识形态等种种想象,被赋予了许多隐喻含义。小说中的关键词“霍乱”为管窥疾病研究提供一个豁口。医学上,“霍乱”是指因摄入受到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或水源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疾病,临床表现为剧烈性泻吐、米泔水状大便,肌肉阵痛性痉挛等。“瘟疫”,并不是某种具体疾病的名称,而通指大规模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小说中“霍乱”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直接指代具体的医学疾病名称,也可表现为具有“瘟疫”性质的种种抽象概念。当“霍乱”一词指向医学术语和临床病症时,映射的是词汇的概念意义,或称为本义,即语言符号所载附的最基本的意义。当“霍乱”表现为具有瘟疫性质的抽象概念时,该词汇偏离产生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反映意义和内涵意义等则与具体语境产生互动,展示了丰富的偏离表征。换言之,这种偏离于“疾病”本义的语义表征,是基于疾病现象的疾病想象。从修辞学角度来说,突破词汇的本义,偏离于常规之外,是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意义建构。
3 “霍乱”的偏离表征与意义
3.1 爱情语境下的情感意义
利奇认为,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感情或态度的,通常可借助于词语的褒贬义获得。情感意义的探讨始于心理学研究,因而其产生有明显的心理动因。而在情感的表达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外化为形式各样的生理表现。显而易见,从小说的题名《霍乱时期的爱情》上来看,“霍乱”和“爱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类似于霍乱病症的乌托邦爱情故事,是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态度的书写。“霍乱”的词汇偏离具体表现为受到爱情语境的制约,临时违背词语常规的概念意义,使词语获得新的意义,形成新奇的意境。主人公阿里萨的母亲特兰西多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5]250在母亲看来,儿子因爱而生的相思病等同于感染了霍乱,染上爱情如同罹患“霍乱”一般,具备种种瘟疫的症候,备受煎熬。少年时代的阿里萨在初见费尔米娜以后,“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晕厥……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5]69。而在其皓首之年,当阿里萨乘坐的士车再见费尔米娜时,同样表现出类似于霍乱的症状,“他的腹部突然涨起来,像要爆炸一般,充满了疼痛的气泡……肠子像螺旋似的绞动着……”[5]349。情感疾病借助了生理疾病“霍乱”的词语褒义而折射情感意义,具体表征为“紧张、恐惧”的心理诱因和“腹泻、呕吐、晕厥、盗汗”等生理反应。爱情是一种情感疾病,既具情感意义也有疾病意义。在阿里萨乌托邦式的爱恋里,爱情的症候与霍乱的症状如出一辙,无法治愈。因此,即便他备受煎熬,也甘之如饴。疾病般的爱情和爱情般的疾病融为一体。
根据利奇的观点,情感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理性、内涵和语体等内容重叠,常常依附于概念意义、内涵意义和社会意义而进行表达。爱情语境下的词汇“霍乱”体现为爱的萌发和生长,也偏离为情的消亡和重生。这是情感意义对内涵意义的依附。在男女主人公迟暮之年享受河上旅行时,船只主桅杆上标志着“霍乱”的一面黄旗迎风飘扬,他们以此方式标志爱的永生,标志隔离,拒绝回到现代生活中,就如罹患霍乱拒绝医治一样,从最初的被迫隔离到最后的主动隔离,宣示了世俗意义上的“死亡”,从而实现了情感意义上的“重生”,再次展现了疾病与爱情的相生相长。
“霍乱”的词汇表征还受爱情语境的影响,借助词语的贬义从而偏离至其他维度。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多受阻扰,源于蛰居在民族文化里陈腐、落后、保守的观念和制度。这正如致病的细菌或病毒,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在跨越半个世纪的重逢后,费尔米娜感叹道:“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5]372年轻时,费尔米娜的爱情受到其势利、专断的父亲强烈阻挠,婚姻由家长操控;年老时,爱情又受到了儿女的指责,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进一步说,拉丁美洲民族精神里贫穷落后、愚昧野蛮、因循守旧、与世隔绝的做派和态度,不仅仅阻挠了爱情,更是成为阻碍民族发展、国家进步的绊脚石。而这种民族意识中的蒙昧状态何尝不是一种民族疾病呢?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纠葛暗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民族振兴的征途上,驱除民族意识里具有传染性和瘟疫性的蒙昧主义、愚昧主义、野蛮主义和守旧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3.2 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意义
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主要指关于语言运用的社会环境的意义。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传递社会信息和时代信息。换言之,使用词汇的社会环境不同,词的社会意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语言的运用是一个运动过程,词义也在运动。伴随着词义运动,“霍乱”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意义。故事设定在1880至1930年之间,彼时哥伦比亚地处热带地区加勒比海沿岸,遍野蔓延的霍乱显然是一段疾病灾难史,从侧面描绘了一个多灾多难、多病多患的国度。小说中,当瘟疫性的“霍乱”被置于殖民时期、内战等不同历史语境下,折射不同的社会意义。
殖民时期,霍乱是民族式“疾患”具体而微的表现。霍乱可以被引申为一种带有传染病性质的民族疾病,其细节描写比比皆是。例如:费尔米娜的丈夫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留学归来,他“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街上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5]130。这里所指的“不幸”,并非词汇本身最基本的概念意义“不好的事情”,而是偏离为时代背景下肆虐而生的医学范畴内的生理性疾病——霍乱。殖民历史语境下,词义运动也使其进一步偏离为指代拉美地区和民族满目疮痍的“思想瘟疫”。在乌苏比诺医生看来,“殖民地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入体内”[5]123。在这一历史时期,简陋的卫生条件和肮脏的卫生状况、带有致命隐患的环境设施,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导致了肆意流行的疾病。这是拉美文化中的落后、愚昧、穷困的一面。而要治愈蔓延拉美地区的霍乱,就是要治理和改造根深蒂固的、落伍不堪的“民族陋疾”。无论是囿于“生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霍乱”,都映射了词汇偏离的社会意义,即:要治疗疾病,就需努力学习现代精湛的西式医学技术以及西方文明新观念,才能根除民族顽疾,进一步履行社会使命和从事社会革新事业。毋庸置疑,对接受现代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乌尔比诺医生来说,西式医学技术和西方文明新观念,是预防和治疗霍乱,解救和援助落后民族并战胜顽疾的一剂良药。
如果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给拉美地区的人民带来了难以治愈的生理折磨,那么断断续续近百年的内战则给这个沧桑的民族以无法抚平的心理创伤。小说中反映了自由党和共和党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自由党人信奉人文主义精神,立志革命;保守党人“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致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源源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动乱、灾难和死亡。权力之争背后的目的是掌握大权进而实行独裁统治,结果仍然是鱼肉人民,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阿里萨在乘坐着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船时,曾经遇到了一艘高挂着标志瘟疫黄旗的船只,亲眼目睹了百年内战带来的苦痛:“……河上漂过三具肿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兀鹭……他们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5]162这一历史语境下,“霍乱”的词义偏离为“内战”,折射的社会意义是:相争相斗的党派、无休无止的内战就是一场疾病风暴,如同泛着“恶臭”的霍乱一样,为拉美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投射了巨大的阴影。
3.3 政治语境下的反映意义
反映意义(Reflected Meaning),是通过同一词语的另一意义的联想而产生的意义。词语能够引起读者联想到其他事物的特征,而联想的产生与具体环境紧密相连。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对疾病是如何在政治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被隐喻化的进行了细致考察,深入剖析疾病如何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逐渐沦为“一种道德评判或政治态度”[6]3。政治语境下的“霍乱”,常常运用疾病隐喻、疾病联想或疾病想象等手段把其他事物比作疾病,以获得某种修辞意义、道德意义或政治意义。换言之,当“霍乱”被置于政治语境时,能够通过联想、想象、隐喻等偏离修辞手段而产生反映意义。
首先,疾病是社会问题或状况的反映。桑塔格指出:“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6]68在女主人公费尔米娜与丈夫乌苏比诺经历气球旅行时,他们俯瞰着曾经的家园,飞过了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当乌苏比诺医生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家园一片狼藉,发现目之所及尸横遍野时,他说道:“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都挨了仁慈的一枪”[5]260。政府军队对香蕉厂工人进行了大屠杀,使得曾经美好的家园处处蔓延着极权笼罩和死亡绝望,更是一场人为的“霍乱”,带有强烈的军事和政治隐喻色彩。此处通过隐喻,“霍乱”偏离为时下混乱的政治状况和张狂的军事活动。
此外,现代的极权主义运动,就是赤裸裸地把疾病化的想象运用到政治活动中。政治语境下的疾病隐喻在于煽动暴力,并且使暴力正当化。费尔米娜恼于丈夫外遇而重回故乡时,她看到了又一番悲惨的景象:“从火车站一直到墓地的路上,日光暴晒下的肿胀尸体随处可见。”要塞长官对她说:“是霍乱。”她注意到了“那些晒焦的尸体嘴里都泛着白沫……没有一具尸体像她乘坐气球时看见的那些那样,脑后挨了仁慈的一枪”,而长官回应道:“上帝也在改善自己的方法。”[5]289这番描写揭示了“霍乱”不仅仅出于不可抗拒的“天灾”,更是缘于蓄意为之的“人祸”。从一开始明目张胆的屠杀,到后面小心谨慎的暗杀,“霍乱”成了政府进行残暴军事统治和血腥镇压的借口,疾病想象成为政治暴力的幌子,成为施暴者冠冕堂皇地实行暴力的理由。政治语境下的“霍乱”词义偏离的操作过程就是通过该词进行词义联想,通过疾病想象而产生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反映意义:失衡的秩序、残酷的统治,无情的剥削,这些均是社会的不治之症,是殖民时代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笼罩在拉美大地的政治状况,也是一种比疾病意义上更为恐怖的人为的“瘟疫”。政府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种反面乌托邦,而带有隐喻腔调的疾病偏离操作正是“马尔克斯”们对传播着瘟疫似的政治军事活动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表达了拉美人民的共同心声。
3.4 生态语境下的主题意义
相对于文学批评中的社会语言和历史语言而言,生态批评主要以“环境”为文本构建语境,重点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与马尔克斯始终遵循着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写作路数不谋而合。当“霍乱”指涉生态语境下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或精神生态时,会发生相对于固定概念意义的词义偏离。利奇对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的解释是,说话人借助组织信息的方式,如调整语序、强调手段、逻辑重音等来传递的突出的意义。一般而言,通过改变词汇在句子中的“语序”或进行“强调”可以实现不同的主题意义。以小说结尾处为例,显性的自然生态环境文本描述被放置在故事结点正是一种特殊的“提醒”,这种信息的“强调”方式展现了马尔克斯对尘喧日上的生态危机的审视、反思和批判。
20世纪初叶,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技术革命一日千里,商业意识无孔不入,西方现代文明浸染了拉丁美洲政治、经济、文学等方方面面。欧洲先进的现代科技文明和印第安部落古老传统文化杂陈一处,相互碰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产生了“阵痛性”的疾病反应,呼应了小说的主题。50年前,“两岸的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见证了自然环境的良好,“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5]161证明了物种的平衡和谐。50年后,男女主人公乘坐着“新忠诚号”通往爱情的永生永世时,他们发现轮船的锅炉已将茂密的雨林消耗殆尽,看到动物被赶尽杀绝,目睹河道变得越来越窄、河水越来越浑浊:“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杀光了在河岸峭壁上一连几小时张着大口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短吻鳄;随着枝繁叶茂的森林的消亡,叽里呱啦叫个不停的鹦鹉和像疯子一般吵嚷着的长尾猴也逐渐销声匿迹;而用硕大的乳房在河滩上给幼畜喂奶、像悲伤的女人一样哭泣的海牛,也被寻开心的猎人用穿甲子弹灭绝了。”[5]381前后两处关于“雨林、大树、鹦鹉、长尾猴、短吻鳄”等自然生态现象的对照性描写,彰显了马尔克斯对生态主题的深刻关注。
马格达莱纳大河两岸风光的剧变,反映了拉美大陆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掠夺、西方经济的浪潮式影响、国家的专制独裁统治、社会的种族性别压迫,加剧了社会生态的失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和隔阂,催化了精神生态的迷失。如此种种,构成了拉美地区在通往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生态危机。在生态语境中,“现代化、全球化”等词是对“霍乱”词义的偏离。在词汇的言内维度特征的基础上表达生态话语实践中的言外生态人文意义。把这些信息放在小说结尾处进行处理,调整了顺序结构,是一种显性的“强调”手段,更加突出生态主题意义。在马尔克斯看来,商业化、现代化乃至全球化之于拉美地区,恰如一场文化霸权上的“瘟疫”,极具传染性和毁灭性。当放置在全新的生态语言环境中,词语呈现了新面目,传递了词汇偏离的主题信息。弥漫着瘟疫性的现代科技文化对原始生态的破坏和毁灭,反映了马尔克斯作为典型的本土主义代表人物对尘喧日上的全球化战略的深刻反思和忧虑,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生态主义意识,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
4 结语
作为“魔幻现实主义”先行者,马尔克斯可谓匠心独运,驻足拉美一方故土,一边撰写颇具“魔幻性”的爱情乌托邦,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一边书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美历史和现实,再现了贫穷国度的百年沧桑。从词汇偏离的角度解读“霍乱”,通过分析该词汇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词汇偏离意义,我们看到了马尔克斯试图唤醒沉睡的大众意识,感受到了他所展现的关乎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文关怀,认识了他对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乃至世界命运的深刻思考。不可否认,基于词汇“霍乱”的修辞偏离表征与意义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思考历史事件,反思现实社会,关注生态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