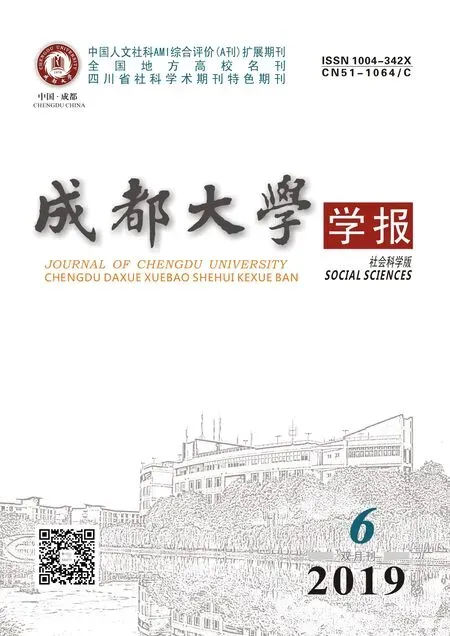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之王超篇*
2019-02-16李轼华
李轼华 万 平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2.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45)
王超,男,1970年11月4日出生,四川射洪县人。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1992年进入成都市川剧院工作至今。拜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蓝光临为师,并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晓艇、王世泽、李家敏、余开源等老师的悉心指教。工文武生,扮相俊美、嗓音圆润高亢、表演细腻。在从艺的三十多年里,饰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充分展示了其艺术才华。代表作品有《尘埃落定》《欲海狂潮》《装盒盘宫》《越王回国》《托国入吴》《访友》《放裴》《刘氏四娘》《春江月》《聂小倩》《白蛇传》《望娘滩》《红梅记》《燕燕》《黎明十二桥》《岁岁重阳》《逼侄赴科》《归舟》《阖宫欢庆》等。从艺三十多年来多次获奖,主要荣誉称号有:
1993年,在《刘氏四娘》中饰演傅罗卜获全国地方戏曲交流评比展演“优秀表演奖”,第四届“文华新剧目奖”。1998年,在《越王回国》中饰演越王勾践,荣获了四川省中青年川剧(豫剧、京剧)生、净角比赛表演“一等奖”。2002—2003年,在《装盒盘宫》中饰演陈琳,先后荣获成都市专业艺术院团中青年比赛演出“金奖”“四川省中青年戏曲表演大奖赛一等奖”。2006年在川剧《欲海狂潮》中饰演白三郎,荣获第三届中国川剧节“优秀表演奖”。2008年,在新编传统戏《红梅记》中,担任男主角“裴禹”。该剧参加法国巴黎演出获“塞纳大奖”。2013年,获得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16年,主演《尘埃落定》,获26届上海白玉兰奖。
采写时间:2018年9月13日
采写地点: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采 写:李轼华 万 平
摄 录:彭 鑫 陈佳慧
李轼华(以下简称李):王老师您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您。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四川省的社科规划项目——“川剧艺术家口述史”,入选的传主都是曾经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项——梅花奖的得主,您是第26届梅花奖得主。
王超(以下简称王):对。
李:今天能够采访到您,我们非常荣幸。王老师,您和川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当初您是怎样走上这条艺术道路的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从艺经历呢?
王:说是艺术家我觉得有点过奖了,我觉得我就是一般的演员恰当些。说起我的成长经历,我觉得还是有点丰富。我的家庭是农村的,射洪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我是1987年进入四川省川剧学校,现在已经改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当时考这个学校是1987年,真的是百里挑一,全省有300多人报考,结果只招收了我们5名演员。那时候,这个招生卡得很严,因为我们所有的到学校学习的费用,都是由国家全部管完,所以那时候招生是非常严格的。我报考的时候,我们那个年级我是插班生。因为当初我们学校我们班是学制7年,那批娃娃学7年。
他们最初考入学校的时候,一般都是十三四岁,(连)12岁的都有,就是说男女都处于变声期前就进来了,他们进入学校两三年后,就15、16、17岁,这时候变声期就过了,很多学员换声期一过嗓子就没啦。所以为了保证这个班各方面行当比较整齐,又有唱的,又有做的,所以在全省补招10名演员,(当时)有300多人报名,结果经过层层筛选,就只招了5名演员,还有5名没招到。那时候对川剧演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加上我们是定向,定向成都市川剧院,所以要求就更严格。当时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说我们这次招生以嗓音条件为主,为主选,就是嗓音条件比较好的,那么我们首招。所以招人年龄有所放宽,就是变声期过后的学员——一般来说是16岁以下,14岁到16岁,因为这个期间属于变声期,男娃娃这个期间一般就处于变声期。当时我的年龄已经17岁,已经超了一岁,但是那时候我的嗓音已经发展到变声期以后,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嗓音,当然也不是完全成型了,所以当时就把我招进来了。
李:您还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具体情况吗?
王:我是在射洪一个很偏远的中学读书,当时交通又不发达,很多老师招生是不愿意到我们学校来的。我记得,当初来招我们的那个老师,是四川省川剧学校的钟开志老师,这个老师他舍得跑,舍得下乡,下到地方镇上去,他不辞辛劳,坐公交车,灰尘都扑满了他一身。我们当时那个路是土路,有一点(柏)油,但是很差,基本上都翻沙了,公交车又差。从射洪县城到我们那个学校有四十多公里,他就这样坐车到我们学校来把我招过去了。到射洪县城,又进行了一次复试。复试来了很多老师,(大概)有10多个老师。因为我们当时进这种考试的场合经历得比较少,所以这种场面就很紧张。第二天,我们全县有20多人参加复试,(当时)第一个就把我叫进去复试。复试的时候(老师)就对我说,你要大胆地考,你要放开,我说我从来就很少唱。偶尔唱下歌,其他唱戏剧,因为小时候接触过,我的父亲是一个石匠,平时喜欢喊号子,嗓子比较好,平常喜欢川剧,也要哼两句,我从小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再加上我们村里要演一些川剧,可能那个时候看了一些,在广播里听了一些,有点印象,你说很喜欢也算不上,(只是)有那么点嗓子可以唱。所以当时那个老师对我说你要大胆放开地考,你只要放开认真考的话,你就有可能考得起。我就问我能考得上吗?(他说)我们现在不敢跟你说考得上不,但是现在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你就有可能考得上。因为他知道我的条件,所以我就第一个进入了复试。(当时)有十多个老师,有的拿着手风琴试一下音准,也有我们川剧表演艺术家老师吊嗓,叫我跟着他唱。复试顺利结束。最后还有一关“超龄",17岁,超了一岁,就需要破格录取。我到学校,还和当时校长赵培镛谈了一下,他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把我通知到川剧学校去,就看了一下我,最后才决定喊我回去等通知。我还是不放心,我问考得上吗?他说你回去等通知吧,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考得上不。实际上他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按照规定他又不能说我录取了,就只给我说回去等通知。我当时等通知的心情是很痛苦的,很紧张,很矛盾。最后当然是录取了。
李:您进入省川剧学校学习后还是经历了很多磨炼吧?
王:录取了进来之后有很多困难。因为那些同学是13岁、14岁甚至12岁就进来了,他们从小就开始摸爬滚打,练压腿、下腰各种基本功。他们很小,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年龄小痛苦就少。而且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了三年了。进来之后这些课程他们已经开完了,在我身上就不会再开这些课程了。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刻苦,自己去找老师补,自己私下去找老师补。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排戏,按照我们这个七年的课时规定,前两三年是练基本功、练基础。后四年就开始排戏,直接就排戏,就开始演戏了。那么我进来什么基础都没有,要自己去补,最后学校想了一个办法就把我安排到其他的新生班,去练基本功。但是练基本功要练压腿,骨头啊什么的都硬了,腰也硬了,腿也硬了,已经趋于成熟,很恼火,所以那会儿吃了很多苦,也排除了很多困难,说实话,就跟着那些新生一起练。新生他们年龄都偏小,应该说一般都是14、15岁,我比他们大两岁。所以这种困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必须要赶上去。当时我是农村的,说实际一点就是想跳出农门,出来之后工作也解决了、户口也解决了,还可以吃国家粮,这不是很好嘛,所以(当时)心里面有一个无形的动力在里面。最后呢,一方面我跟着那些年轻的小娃娃练基本功,另一方面,又要跟着这个班上的进度排戏。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啊,出手出脚唱什么都不懂,很恼火。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下死功夫。所以自己私底下去找老师,就这个样子。
李:您从省川剧学校毕业后就分到了成都市川剧院?
王:毕业了之后就到了成都市川剧院,现在是叫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成都市川剧院有两个团,一二联合团和第三团,我当时到的是一二联合团。我们的演出场地就是锦江剧场,当时我们一二联合团有很多的老艺术家,三团是叫青年团。联合团就有很多老艺术家,可喜的是那个时间跟着老艺术家确实学了不少东西。学了演戏呀,包括做人呀,在很多方面学了不少的东西,最后跟着他们排了戏。排的第一个戏叫《刘氏四娘》,我是1992年到的团,1993年就开始排这个戏,年底就拿了奖,这就是我的人生中排的第一个,也是艺术道路上排的第一个大戏,也是我的艺术道路上拿的第一个奖。就是文化部艺术局的一个奖,叫“全国地方戏曲交流演出南方片优秀配角奖”。在这个戏中,我是一个配角。第一主角是二度梅花奖获得者刘芸老师,她也是凭借这个戏1994年在北京演出获二度梅。我呢就是凭借这个戏,拿了全国地方戏曲表演的优秀奖,所以这是我人生艺术上一个转折点。可以说这个戏演出以后获得了很多好评,包括文化部的专家,包括很多老师,以及我们当地的戏迷,都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对我印象就很深刻,对我的评价比较高。这个戏(演的)是母亲和儿子的故事——目连和母亲的故事,比较感人,当时我也演得比较淳朴。演得比较小,也没有过多城市繁华的那种困扰。所以当时演得很淳朴,也很感人,也很打动人。我们当地的观众、戏迷,以及我们当时的主管领导,还有北京的专家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所以这部戏给我奠定了基础,也给了我信心。接下来,到了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很多年后,就(开始)有一点迷茫了,大家都下海经商去了。社会上的人去挣钱了,我们那个剧团那几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演出。不只是我们成都川剧院(这样),这是整个社团的一种现象。包括陈巧茹他们都去卖过化妆品,我去开过两年的出租车,也没有办法,要生存。(当时)整个剧院都没有演出,即使演出也没有什么人去看,大家都去挣钱了,那时候心里都是慌的,都想到挣钱。(但是)自己又觉得从开始学这个,对舞台还是有一种眷恋,对舞台恋恋不舍,离不开这里。所以最后一旦这个剧院各方面有所好转,形势有好转,我就要去学它。后来我就又去演了戏,进入21世纪,就演了成都市川剧院很多的大戏,基本上都是我的男主演,像什么《红梅记》《欲海狂潮》《岁岁重阳》《白蛇传》,最近的《尘埃落定》,反正戏比较多。中间还有一年,到省川剧院去了,就演《望娘滩》和那个《白蛇传》,又参加北京的表演。所以说我觉得,中间有些过程是比较困惑,好在现在我觉得形势还是比较好,所以我又重新走回来了。
李:王老师,刚才您说到您在四川省川剧学校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好老师。那么后来,您在从艺的道路上应该是遇到了更多的良师益友,比如说蓝光临老师、晓艇老师等,那么这些老师在您从艺的道路上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王: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会儿是打基础,那些老师在基础方面,包括唱做念打基本功方面,私下给我补课,我觉得受益匪浅。确实在基础方面我觉得得到了锻炼。进了川剧院以后,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了。作为一个正式演员,很多情况下就是必须要靠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体会、去演出、去琢磨。到了川剧院之后就是到了另一个天地,因为这是演出单位,有很多老师是专业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演出,而学校的老师主要从事的是教学,上舞台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到了剧院过后,我遇到了蓝光临老师、晓艇老师,还有更多的老师,这些小生行老师。因为我是唱小生的,那么我就特别关注我们小生行的老师,这些老艺术家。看他们的戏非常感叹,非常崇拜他们,觉得这些老师技术确实相当精湛,相当好,各个老师各有所长。从每个老师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光环和优点,很多确实让我们惊讶。后来综合我自己(各方面情况),最终拜师蓝光临老师。蓝光临老师对我来说是师父,对我关怀无微不至,特别是艺术上,(我)耳目染地看他演出,他也给我排戏,一手一脚给我排,从他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还有晓艇老师这些,包括王世泽老师,他们每个身上都有他们每个人非常亮丽闪光的地方。我们老师的表演、唱腔这些非常棒,比如说给我排《越王回国》这部戏,还有《装盒盘宫》《石怀玉惊梦》这些非常棒的戏。所以(后来)我在做专场的时候,就分别请了我师父蓝老师给我排戏,让晓艇老师也给我排《逼侄赴科》这个戏。我的专场是三个戏,就是《装盒盘宫》《逼侄赴科》《越王回国》。所以这三个老师对我来说,从我对艺术的那种理解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多的提拔,(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他们的艺术(营养),学到了他们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最终拿梅花奖,还有我演了那么多大戏,都是因为平常从他们那里,从舞台上他们的演出中,观摩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一手一脚教我,潜移默化转移到我塑造的人物和大戏当中。
李:在您从艺的经历过程当中,您获了很多奖,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也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我看到您这儿有这样的一幅字画,就是观众送给您的。在您的获奖当中,其中分量最重的,也是在您从艺道路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您获得了梅花奖。我们都知道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要赢得这个梅花奖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能不能讲一下您当时的获奖情况呢?
王: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几个老师的教导下,也演了那么多的戏。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有自己的追求,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也是给自己一种信心和一种目标。在2010年的时候,央视来采访我,当时我在后台,央视来随机采访拍摄我,我在化妆,他就在边上问:“请问你的新年心愿是什么?”我随口一答:“拿梅花奖!”这个视频在央视播了,我们北京中国剧协的领导也看了。中国戏剧界梅花奖,在每个演员心中那个分量(很重)。这些年,我在老师的教导下演了很多折子戏,也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观众平时也非常喜欢我演这些戏。平常呢,大大小小的全国的比赛、我们省内的中青年川剧演员比赛比较多,我也参加了不少(奖项)。其实我去参加比赛,一方面我就是想拿奖,拿奖不为给我自己带来什么,我就是想证明自己。二是检验自己,就是我检验自己学到的东西,我在舞台上,这么多年我刻苦学习,我锻炼的成果,让观众检验、让专家检验。如果得到他们的认可,我觉得非常高兴,对我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同时我又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起点,朝另外一个目标走。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一个戏剧演员,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必须朝我们的目标走,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说实话,我在这方面确实拿了不少的奖。比如说,四川省中青年戏剧演员比赛,这个就是检验我们整个戏剧界不同年龄层次演员(的一个比赛),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都是内行,你演出来的戏,大家都在一个台上(比),我觉得这次演戏基本上达到了我要求的效果。只要我去参加比赛,我拿的奖不是金奖就是一等奖,我从来没有拿过银奖。所以说,就我拿的这个梅花奖,我就是作为一个川剧小生演员向全国戏剧演员的最高奖冲刺,检验我这么多年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2013年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比赛),当时我演了几个折子戏。本来是该2011年就去的,因为当时自己家庭各方面的原因,延后了两年,但这个我觉得不影响我的这种追求,时间早迟,我都会去争取的。所以在2013年我就(排了)一台折子戏,就是刚才我说的《装盘盒宫》《逼侄赴科》《越王回国》,都是我们老师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三个戏应该说是我们老师的代表作,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当时这三个戏他们演得确实比较多,但是毕竟是在全国的一个平台上展示,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剧种和全国的专家以及参赛选手来观摩。我们川剧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特别是小生,有很多技巧,全国其他小生都竞相来学习。所以我对这次这个专场非常重视,非常认真对待,最后在这个地方呈现。我们那个剧场只能坐600多人,当时好像到处站满了人,大概有800多人,就是不能再放人进去了。我觉得当时那个呈现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从各方面来说我都必须把它完成好,我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那个专场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当时为了准备这个专场,我前后演出了一年,天天坚持跑步,锻炼体力。一个折子戏几十分钟,三个戏就一百多分钟,需要你一个人完成,而且最主要的是一次性完成,所以折子戏比大戏累,大戏两个多小时,它有很多的角色,很多的情节,其他的角色可以给你分担,但折子戏主要是你自己主演,它要消耗的精力和体力都特别多。所以我当时最主要的是锻炼体力,各方面去做准备。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基本上令我满意的,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拿了第26届梅花奖。过了几年,正好我又到上海,当时我们是演这个《尘埃落定》,就在上海无意中拿了个白玉兰奖。《尘埃落定》我是主演,是演傻子,在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他们就喊顺便报一个(奖),这个也不是刻意的,因为你在这儿演出,在上海参加一个展演,你都可以报这个(奖),主角奖、配角奖都有。当时我们没有刻意为奖去做准备,反正我们当时都要去演,就顺便去报了白玉兰奖。当时报了就报了,结果第二年就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就让我去领奖,我说领什么奖?他说:白玉兰奖,你入围啦!入围了?我说那是什么奖啊,那边说最先就是入围白玉兰主角提名奖。然后再从提名奖中产生主角奖。最终我就去了。有点遗憾最后获得的是第26届上海白玉兰主角提名奖。这个奖,全国只有10多个,所以也算很幸运的事。也是无意之中的一个事情。
李:除了您获得梅花奖的这几个作品和获得白玉兰奖的《尘埃落定》之外,您还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欲海狂潮》啊、《红梅记》啊等等,您在舞台上也塑造了很多角色,在这些剧目和角色当中,您比较满意的有哪些呢?
王:其实这么多年,很多角色我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对我来说我最满意的,我觉得还是《尘埃落定》。《尘埃落定》这个戏,就是阿来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戏我是主角。我这么多年除了这个作品是一号,还有个戏叫《黎明十二桥》,我也是主角,它是一个现代戏,是军人戏,这个戏我也比较喜欢。当然还有折子戏《装盒盘宫》这些代表作,《装盒盘宫》《访友》这些戏都是我们川剧文生的戏,我都是比较喜欢的。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个角色。我觉得傻子这个剧中人物有一种超前的意识,他形傻但人不傻,是一种非常善良的(形象)。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空灵的感觉,有时演员可以从中去发掘,去找你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给一个演员的创造和发挥留着空间,所以我喜欢这个角色。我不太喜欢那种直来直去的角色,就是那种非常单一非常单纯的、很儒雅的那种角色,一种小生,一种舞台上的古装的形状,他非常单一,人物性格等各方面都非常单一,我就不太喜欢这种(角色)。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就是给我们演员留下一些创造性空间发挥的这种角色。《尘埃落定》傻子这个形象(就是这样),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傻子的形象,但是每个演员表演呈现出来的形象又不一样,你有怎样的理解就有怎样的形象展现,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嘛!所以说我喜欢这种有创造性有挑战性的角色。
李:王老师您能不能总结一下,您在川剧表演艺术上的一些特点,您在塑造角色当中有哪些特点?
王: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自己演出这么多戏,这么多角色,别人说我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在声腔这方面,在我们当今这个小生行里(有自己的优势)。前面老艺术家我们不去评论,现在这些学生辈还没有起来,那么在当今我们这个阶段,我觉得观众比较认可的就是我的声腔,我的演唱方面。我的很多戏,应该都是以唱为主,而且特别是很多大幕戏,我的唱都是一个亮点。我会把我的特点,我的唱融入到人物中去,融入到剧情中去,让它更好地为人物和剧情服务,而这个剧这个人物通过我的演唱,通过我的表演,它也会得到一些提升,这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特点。另外我喜欢表演那种比较有阳刚气那种(角色)。他们说小生是半个小旦,半个女角,但是我觉得小生毕竟是个男人,我不希望演得脂粉气太浓重,我觉得那样子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我自己在这方面,演出了我自己的一种书生的味道。但是在塑造其他人物的时候,演现代剧的时候我喜欢去塑造那些具有阳刚美阳刚气的角色。但如果说确实有些角色需要那种书生气、书卷气,我也可以去演。所以在我这么多年演的角色当中很多角色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都有鲜明的特色,比如《尘埃落定》傻子的形象、《黎明十二桥》肖飞军人的形象。《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就是书生形象,还有《红梅戏》中的裴禹,他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书生形象,他嫉恶如仇。(我)还演了一些农民,比如《岁岁重阳》,就是以前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改编的)那个戏。这个角色就是农民,两兄弟,一人演了两个角色——豹子和虎子。豹子就是没有文化,完全是一个使蛮力气的人,在农村里天天饿饭,跟着娃娃鬼混,他的哥哥虎子是当过兵的,非常有文化,这两个角色性格就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对这种角色,我就觉得有个性,整个人又有特点又有挑战性,我就非常喜欢,我就喜欢演这种人物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演了这么多的戏,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演唱和声腔。通过这些来塑造人物,为这个人物、这个剧情、这个剧目增添人物色彩,这些(就是)这么多年我总结出来我自己的特点。
李:我们注意到,成都市川剧院,最近十几年除了整理复排一些传统的大幕戏、折子戏之外,另外还演出了许多现代戏,比如说,您就有几个代表作品,您能不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王:作为一个演员,就要多去塑造人物,多去演戏,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作为一个剧院就要与时俱进,不能老演传统戏,传统戏我们需要传承,但是我们要传承,我们还要发展创新,现代戏它与时俱进,它是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现象,反映事实,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创作了很多现代戏,比如刚才说的《黎明十二桥》《岁岁重阳》,还有我们最近的《尘埃落定》这些戏,我觉得这些戏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还获得了很多大奖。比如说我们的《欲海狂潮》这部戏,其实《欲海狂潮》这部戏我很喜欢,我也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它是一个新编的古装戏,这个戏也获得了很多奖,也获得了我们的“文华奖”。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戏,既是反映时事,同时也是锻炼了演员,也为剧院增添了剧目,也为剧院剧目留下了丰富的资料。那么今后,我们这代演了这些戏之后,今后再一代一代传下去,今天的这些现代戏,到了今后经过很多年后,也许它就叫传统戏了,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方面我们整个成都川剧院也做得非常好,应该说也是走在了我们川剧院团的前列。我们演出了那么多的戏,而且每个戏我们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有的戏甚至在中国戏曲界都是叫得响的。
李:现在成都市川剧院正在排演一出新的戏——《天衣无缝》?
王:对,今年这一阶段我们正在排《天衣无缝》,这个戏就是我们剧院的一个作家、编剧张勇的作品。她以前写了两个电视剧,现在是第三个电视剧,马上就要播出了,我们也想借着一种影视的传播,和我们川剧舞台上的传播,形成一种效应,舞台和电视效应,来把它川剧排出来。这是一部红色的谍战剧,我们把地点放在成都,这个戏剧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戏,我在协助也在负责这个戏,同时也是这个戏的男主演,这个戏有男主演和女主演,男主演和女主演两个戏份差不多,女主演是一个正面人物,男主演相当于是一个反面人物,是个特务,但是按照我们有个规矩,就是不能把反面人物作为一号角色,不能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就只能做配角。
李:这部戏是您和王玉梅老师演的?
王:对,王玉梅。
李:是拍成电视剧吗?
王:这个戏它是《天衣无缝》,这个有电视剧今年播放,应该是在浙江卫视,但是我们川剧现在没有排成,所以它就是舞台剧,不会拍电视。
李:是即将要演出了吗?
王:11月6号在锦城艺术宫演出。
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个通知——《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就是我们所说的52号文件,那么您觉得这个文件对我们的川剧艺术传承振兴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王:我觉得这是一个“及时雨”,这个52号文件对我们中国戏曲来说,是来得非常及时的。
确实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习主席说的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那我们川剧它就是四川人民的根和四川人民的魂,应该说它是四川人长期生活的结晶。因为(以前)我们没有电视,我们四川人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川剧,看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它非常接地气。只不过现在的娱乐方式太多了,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了,他没有时间静下来去欣赏。而且川剧作为一个舞台剧,它毕竟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它不像电视剧,坐在家里面随时都可以看,电视不播放川剧,大家必须要进剧院看,这就是它的一个限制。现在大家生活节奏也加快了,没有时间进剧场,所以观众慢慢减少,我们这些剧团也从以前几百个剧团减少为几十个,剧团垮的垮、撤的撤,所以对我们川剧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应该说现在的情况是很窘迫。所以(保护川剧)也是对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然要保护了,就说明已经是很危险了,就濒临危险了。那么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确实观众变少,因为观众可以看的东西太多。另一方面,确实这么多年,我们这个从业人员待遇低,待遇低之后,从业人员就减少。没有很多人愿意做,没有很多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更别说买房子置业,这些更谈不上了。好在现在,我们国家大力扶持和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当然它不光是川剧,涉及到整个中国戏曲界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春风吹得好!我们现在有些又采取了具体的措施,首先解决观众。一个剧目演出,这个文艺作品拿出来没观众,随便你怎么,没观众就很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培养我们的观众,我们现在就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送戏,把戏送到学校,送到社区,送到高校去。送到甚至比较大的企业单位去,去讲课,给他们送到学校去,就是为了送上门去,给他们有机会去看,只有他先看了,有兴趣了,(才会喜欢),他看都没看到,怎么能够说喜欢呢?就谈不上(喜欢)。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既然你没时间进去(看戏),我们就把它送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觉得送到这个地方来了,也没耽误你更多时间,你就等于把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看了,就领悟了,慢慢地就喜欢了。现在很多人说我不喜欢(川剧),实际上他说这种话之前他根本就没看过(川剧),他只是听人家说不好看。给他送到学校、社区去了,他看了,诶,他觉得好看,这个唱得好又好听,这个扮相又好看,服饰又美,他就觉得好看,就改变了他这种印象。这样的话,他就喜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这些,我们观众断层了,我们的演员也断层了,所以我们最近也招了30多个年轻新演员,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川剧接班人。另一方面在学校开设这种特色教育课,我们对中小学也有一对一的教育辅导,就是以这些措施培养更多的观众,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希望这些孩子今后从事这个专业行业,但是就是说不准在他们当中就会出现专业的从业者,甚至大艺术家,我们的角儿,说不定无意之中就产生了。所以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对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是积极配合。
李:这个送戏进校园让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川剧、接受川剧、热爱川剧,这是对我们川剧艺术的一种传承和保护。那么您对川剧的传承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听说您的儿子现在也从事专业的川剧的学习,而且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他的情况呢?
王:我儿子现在在我们川剧院,是通过正规的学习,还比较优秀的成绩考入成都市川剧院的。他应该是受了我的直接影响,我经常要演戏,经常要练,他就在旁边看,看了以后,他就喜欢上了,所以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变脸,六七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变脸,最后进入了四川省川剧学校去学习,系统地学习,学了四年以后,读本科,拿到本科文凭,然后参加戏曲小梅花的比赛,还获得了金奖,因为他从小就看得多,有我潜移默化对他的影响。最后毕业后通过公招的形式进了成都市川剧院。他的行当也是小生,他在其他行当,小丑啊等行当他都在演,全面发展嘛。不光是演戏,而且他现在在文学这一方面也非常不错,写点东西也像模像样的,也有很多文章被转载,我们给他转载,或者微博上去转载,评价还不错,非常高。而且他自己私下还写了一两个剧本,就是大型剧本。我希望今后他不光是在演出方面,而且要在编和导方面发展,因为戏剧舞台这个空间很大,我觉得全面发展对他也有利,对我们这个事业也有利。我是这样想的。
李:您的儿子子承父业,这也是您对川剧事业另外一种传承和保护的形式。
王:一种贡献吧。
李:对,是对川剧事业的一种贡献。
王:嗯,但是呢,他现在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也经常在敲打他。他自己很好学,很有天赋,很喜欢钻研。各种都去尝试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现在的阅历和经历都非常欠缺,需要的是更多的舞台实践和锻炼机会,需要更多的平台去学习,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
李:祝您的儿子在川剧艺术的舞台上越走越好,也祝愿我们的川剧事业能够更加繁荣。谢谢王老师今天接受我们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