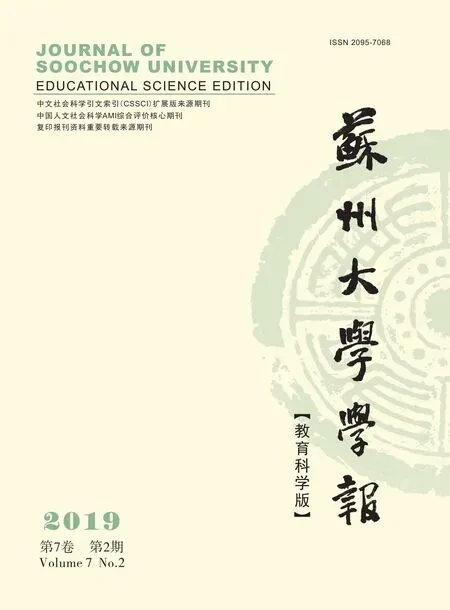一个教育家成长的人文环境:舒新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2019-02-11陆秀清
肖 朗 陆秀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一、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堪称近代中国思想比较解放和活跃的历史时期,从而为近代中国新思潮、新文化的崛起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人文环境。这一时期湖南不仅掀起了学校教育改革的热潮,而且报刊发展迅速,出现勃兴之势,对此有学者指出,“从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6年中,湖南先后出版的报刊有100余种,在种类和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进而有专家分析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无论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还是诸如长沙这样的省会城市,都呈现出“大量新书刊方便可得、投稿渠道增多、独立办报便捷”[2]的态势。 更有学人断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湖南这个特有的历史文化平台上,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政治和军事诸方面的灿若星河的湘籍人才群体”[3]。舒新城即为这一时期湖南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有学者把舒新城与吴虞、钱玄同、张菘年、陈望道、王统照等并列为当时曾投稿《新青年》“通讯栏”的代表人物,并概括道:舒新城“时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学生,致信《新青年》,建议该刊在青年界提倡社会服务,希望能养成风气。毕业后,他在长沙等地中学执教,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4]。学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人文环境对舒新城个人成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课题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有鉴于此,本文拟突出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具体考察舒新城在长沙和上海两地的活动业绩,以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勾勒他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著名教育家的历史轨迹。
二、初入长沙报刊出版界: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时值舒新城就读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之际,他利用暑假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与同学周调阳、刘范猷等在《湖南民报》做编辑,该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创办的新型报刊之一,“以发挥民治精神,注重民生主义,监督执政,指导国民为宗旨”,其内容则分为社论、中央新闻、各省新闻、本省新闻、世界新闻、时评、文苑、小说等项。[5]在此期间,舒新城结识了同在报馆工作的陶菊隐和时任副刊编辑的许彦飞等人,据陶菊隐称:“我在《湖南民报》认识了舒新城先生。他是来自溆浦县的穷学生……他半工半读,暑假到城内担任新闻记者或在中学任教……我们在《湖南民报》仅仅打了个照面,就各自西东。”[6]此举可视为舒新城步入新闻出版界的肇始,他也曾言:“我的新闻与出版的学习,要以此时为嚆矢。”[7]尽管舒新城在报社工作只有短短两个月,但也收获了不少新闻与出版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更增强了其借助新闻媒体参与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自觉意识。从1916年起舒新城已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新颖的言论所吸引,遂写信给主编陈独秀,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信中首先称赞道:“迭读嘉言傥论,心焉向往,振聋发聩,贵杂志不啻为吾国青年界之晨钟。”[8]接着,舒新城在信中写道:“惟我国社会素以家庭为主,于人类相互之关系未明……一般人民于家庭外不知有社会,甚者且于一人外不知有家庭,长此以往,不至人尽相食不止。……新城不敏,愿提倡社会服务于青年界,冀成风尚,以改良社会。”[8]最后,舒新城建议:“足下何以教之,能于贵杂志辟一栏为通信地乎?希赐裁答。”[8]陈独秀在回信中赞扬和鼓励舒新城道:“热忱高见,钦佩良深。……呜呼!三户少年,诚非余子所及。”[8]同时委婉地表示“倘同志来函较多,自当别设一栏为诸君通信地。惟青年社会,如此销沉,深恐曲高和寡耳”[8]。尽管如此,陈独秀仍采纳了舒新城的建议,在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增辟“通信”栏目并刊载了舒新城的信和陈自己的回信,遂开创了近代中国期刊设置读者“通信”栏目的先河。作为这一创举的首倡者,舒新城的功绩固然不可埋没,而他在《湖南民报》的工作实践经历也可以说为其日后创办人生第一份教育杂志《湖南教育月刊》积累了相关经验与知识。
舒新城曾坦言自己“在私塾与学校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但没有一个地方使我满足!”,所以“不一定期望于毕业后以教育为职业——当时唯一的希望为新闻记者,教育只视为不得已的职业”。[9]但理想与现实是有距离的。1917年夏,舒新城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兑泽中学任音乐和英语教员,一年后他离开该中学,开始研究教育问题。他始而倾资购读中文教育书籍,但不能满意;继而借阅桑戴克《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英文节本和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英文本,“读之如获至宝,始知教育要社会化、生活化等论据,及刺激与反应之原理,及其在教育上之应用等等。……更知教育学之外尚有教育哲学,于是从事教育著述之志愿益坚,而夜以继日地读书”[7]。当年暑假期间,舒新城在长沙雅礼大学开办的暑期讲习班讲授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并兼任教会学校——福湘女学的教育学教师。1919年初,舒新城专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兼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适逢该校图书室,有杜威、桑戴克、詹姆斯、孟禄、贺尔(Stanley Hall)等的各种教育及心理学的著作,以及其他英美文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于是我有如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当时精神上愉快自不可言,而求知的欲望则发展至于极点……而詹姆斯的小心理学,桑戴克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简本,贺尔的青年心理,孟禄的中等教育读之尤多;就是詹氏的大心理学、桑氏的大教育心理学、孟氏的教育辞典也常为翻阅”[7]。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及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舒新城不仅阅读了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等本省杂志,“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7]。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这一时期舒新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的重要思想资源。
1919年11月,舒新城被迫辞去福湘女学的教职后即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杨国础、宋焕达、方扩军等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杂志,并于创刊号《本刊宣言》中明确提出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办刊方针,设置评论、专论、世界教育、世界大事、讲演、调查、通讯、附录等栏目,其中“专论栏以湖南教育问题为主题,调查栏专发表私立学校实况”。[7]舒新城被推举为总编,宋、杨任编辑,方任经理。作为教育刊物,《湖南教育月刊》重点探讨湖南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批判湖南教育界的流弊,改造时下的湖南教育。署名作者除创刊的四人外,还有毛泽东、杨树达、张效敏、蒋作宾等湖南籍人士,而出自舒新城手笔的文章最多,包括《桑戴克的教育学说》《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悼杨怀中先生》《无教育的教育》《感情教育》《什么是湖南人的文化运动》《痛苦的解除——快乐》《〈湖南教育月刊〉停刊宣言》,此外转载了姜琦《新文化运动和教育》等文章。
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舒新城曾向胡适、陈独秀、张东荪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及名人约稿。如1919年11月4日他寄赠一册《湖南教育月刊》给胡适并附信道:“一、请先生批评指教。二、请先生在各报纸杂志上介绍。三、请先生做文章给本月刊。”[8]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胡适是否作出回应不得而知,但《湖南教育月刊》确实未发表过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不过张东荪寄回了《我的教育观》一文,舒新城将它作为开篇文章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刊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在《什么是湖南人的文化运动》一文中舒新城谈及湖南的出版业,指出全省的出版物较少,且销量甚差,他估计只有外省的十分之二三,影响全靠对外宣传和做广告;在教科书编译方面,湖南的成绩亦岌岌可危。[10]但《湖南教育月刊》在教育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长沙《大公报》曾发文宣称:“自从杜威博士到了我国,我国思想界如得了一种保障,人人都知道现在世界有个杜威,杜威在现在世界是个什么人了。但是还有一个同杜威齐名的,也是个大教育家。列位如果即欲知道,《湖南教育月刊》有篇《桑戴克的教育学说》,载得清清楚楚。”[11]但该刊于1920年4月出至第5期时,却因时任湖南总督的军阀张敬尧的胁迫而停刊。
主办《湖南教育月刊》之余,舒新城还向长沙的本地杂志《体育周报》投稿。该刊主办人黄醒将办刊宗旨归结为“体育是为着人生的幸福,凡人皆须取得体育的权利”[12],因而该刊定位为教育学术刊物,而非一般报道体育运动信息的大众刊物。《新青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还专门介绍过《体育周报》并给予主办人客观的评价:“楚怡小学校有一个体操教员黄醒君,他的文学和思想,不仅在体操教员中间算出色的,就是一般小学教员及得他的也少。他看见新潮来了,体育上的见解、进步,也是不可不随世界潮流变迁的;并且当这欧战终了时候,体育上到底应该如何设施、进行,都是很要紧;他就组织了一个《体育周报》。同时他又把那杂志社做了一个代派处,专门代买海内‘新思潮’的杂志,借此介绍新思潮到湖南。”[13]能得到《新青年》的肯定,足见该刊在当时的湖南及全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当代有学者认为:“《体育周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选择了一个大众化话题,提倡‘体育革命’,约请国内外一流作者撰写稿件,代售处遍及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成都、武昌、吉林、安庆、云南等省市,从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它虽然不是全国创办最早的体育类期刊,但出版期数却最多。凭借这份期刊,使湖南在中国体育期刊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12]舒新城在该刊上发表了两篇以儿童为主题的文章,前一篇为连载长文《儿童学》,后一篇《儿童研究大意》发表于1920年特刊第1号。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向上海的报刊投稿,以期寻觅新的平台和机遇。
三、舒新城的“双城记”:往返于长沙和上海的教育足迹
1918年3月4日,《学灯》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在上海创刊,它由原先的“教育界消息”栏目改版而来,改版前专门登载教育领域的各种新闻和信息,改版后依旧围绕教育而展开启蒙宣传,其首任主编张东荪[注]张东荪担任《学灯》主编的时间为1918年3月至1919年2月。在《学灯宣言》中道出了该刊的首要目标为“促进教育,灌输文化”[14],关于该刊的宗旨及内容,他又表述道:“内载关于学术及社会问题之提倡,评论思潮,研究论坛,丛谭名著,译述新文艺,学术界消息及讨论通讯诸门,藉以革新思想,促进文化。其大旨:(一)对于原有文化,主张以科学解剖之;(二)对于西方文化,主张以哲学与科学调和而一并输入之,排斥抄袭盲从之说、皮相之论;(三)对于新派所持之主义,加以研究,不作无价值之调和论;(四)对于教育,主张顺应世界潮流,提倡德谟克拉西之教育,以发展人格为主旨,不以职业教育之实用主义为满足;(五)对于教育制度,反对抄袭的与固执不化之制度;(六)对于教育事情,揭载各种教育上之流弊;(七)对于学风,主张改造成活泼朴实之学风,排除现在萎靡不振之积习。”[14]当代有学者称《学灯》在近代中国“为报纸有学术性副刊的创始”[15]。随着《学灯》逐步扩版,该刊新设“学校指南”“教育小言”“学校记事”等与教育有关的栏目,较之以往其内容和思想的学术性有所提高。舒新城抓住了这一机遇,行使自己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如1919年8、9月间,他在阅读发表于《学灯》的反思与批判教会学校的文章后,便撰写了长文《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投给《学灯》,随即以“畅吾”的笔名连载于同年10月13—18日间出版的《学灯》。该文发表后,福湘女学校方强烈不满,最终迫使舒新城辞职。
如前所述,1919年11月舒新城离开福湘女校后主要致力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但同时也积极向上海的《学灯》《解放与改造》等杂志投稿。特别是当《学灯》增辟了教育类栏目后,它逐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包括舒新城在内的教育界人士讨论国内教育改革问题、介绍与推广国外教育思想和经验的新的公共舆论平台。借助这一平台,舒新城反思与论述国内的教育现实问题,如《阶级的教育与人之教育》(1920年10月)、《中国公学风潮问题》(1921年11月)等;发布当时的教育信息,如《长沙学校之现状》(1919年11月)、《北游杂记》(1921年11月)等;介绍国外新兴的教学法,如《介绍推士先生的科学教学法》(1921年7月)、《道尔顿制的讨论——复沈宗璜先生兼质张东荪先生》(1923年2月)、《道尔顿制的心理》(1923年7月)等;围绕教育及文化改造问题与当时的知名学者交换意见,如《舒新城致俞颂华》(1920年5月)、《舒新城致张冀成》(1920年8月)、《舒新城致朱经农》(1923年10月)等。总的来说,《学灯》使得诸如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获得了较为自主的话语权,这也体现了《学灯宣言》中所谓“屏门户之见,广商友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的办刊宗旨和精神。[14]再如,该刊“青年俱乐部”栏目还未正式与读者见面前,其征稿原则便先行宣布“专备各校教员及学生诸君之投稿,凡有益青年身心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登出者酌具赠品)”[16]。与1918年第1期《新青年》开始发展成为仅限同人发表言论的平台不同[注]该期《新青年》发布的“本报编辑部启事”中写道:“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学灯》则为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及青年学子开辟了开放的公共舆论平台,遂使其广为流传,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点可借用时人的评论来佐证,如著名学者张静庐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②[注]②宗白华于1919年11月至1920年4月期间担任《学灯》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17]另有专家指出:“自陈独秀、胡适之借《新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化运动后,全国青年的思想,为之一新。1918年初,《时事新报》创副刊《学灯》,接受新思潮。《学灯》自宗白华、郭绍虞以至郑振铎诸编辑,均一贯地保持其独立发展的精神。”[18]当代有学者也认为:“《学灯》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讨论环境,实际上是传达和灌输一种平等交流的观念和自由探讨的精神。”[19]以宗白华为首的《学灯》编辑部一贯秉持的理念为“我们是一张白纸,没有成见,没有偏见;希望大家来刻下他的心灵创造”[20]。因此,社会各界人士均可在这个公共舆论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而舒新城也正是借助这一平台所发挥的传播效力,在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的同时联络了诸多教育界人士,从而将自己学术的人脉圈子进一步拓宽。尤其是《学灯》创办之初即继承了《新青年》的传统,通过设置“通讯”栏目为作者、读者和编者提供了相互交流信息的渠道,这类沟通方式广泛地存在于作者、读者和编者群体的内外部,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和畅通的传播系统。
张东荪担任《时事新报》主编期间又在上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并宣称该刊的宗旨为“研究世界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学说,用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种种问题的参考材料,再尽我们的能力把这种学说传播出去,使全国的人都添无数参考印证的材料,使中华民国的思想有一些革新的动机,使中华民国的新生命有一个坚固的基础”[21]。舒新城也向该刊积极投稿,并先后于1920年1月1日和4月15日分别在第二卷第一期及第八期的“思潮”栏目中发表了《自我(The Self)的研究》 和《怎样改造武人思想》两文。前文主要介绍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及皮尔斯伯里(Walter B.Pillsbury)的《心理学》 (Psychology)和 《心理学概要》(The Essentials of Psychology)两书中涉及“自我”(the self)的理论;后文则用心理学来分析武人(军人)与学生的不同之处,提出利用出版物通过自下而上的启蒙教育来改造武人思想的观点。
如前所述,《湖南教育月刊》于1920年4月因张敬尧的胁迫而停刊,此时张东荪向舒新城伸出了援手。舒新城日后回忆道:“因为一年来在上海投稿较多,且与《时事新报》的主笔张东荪先生常有通讯,在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只有打算投奔到他那里去。”[7]他于6月下旬赴沪,并住在张君安排好的姚主教路松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舒新城与张东荪及《时事新报》的另一位主编俞颂华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并联名在《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还协助张东荪承担《时事新报》的部分编辑工作,并在上面发表诸篇文章。因此,两人交流增多,关系日趋密切。
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走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易培基主持,舒新城受邀于9月回湘教书。关于此事的经纬,舒新城记载道:“我到沪未及两月,因易寅村(培基)先生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而派遣其教务主任熊仁安君赴沪聘请教员,我也以长沙教育家之头衔而被聘为第一师范的教育科专任教员了。”[7]“八月间熊仁安君亲去上海聘请教员。当时被聘者有曾在浙江一师教书有成绩之夏丏尊、沈仲九——沈系后去——及武昌三杰之余家菊、陈启天——又一杰为已逝之恽代英,均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我呢?大概是因为一年来写过一些文章,那年五月,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部实用教育学,承蒙他采及葑菲,亲至松社……勉以敬恭桑梓之义。我于是于九月初与熊君同行返乡——湘人之同返者尚有孙俍工。”[7]另据专家介绍,舒新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教师,同时期与他共事的有教务主任匡互生,担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王鲁彦、田汉、孙俍工、李抱良、吴芳吉、汪馥泉、周方、谢觉哉等,担任英语教员的周谷城,担任社会学教员的黄士衡,担任地理教员的吴晦华,担任博物教员的廖先任,担任化学教员的吉光勋、欧阳刚中,担任生物教员的辛树帜,以及文犊员朱芳圃,其中14人为湖南籍。[22]据舒新城个人回忆,“那时我与夏丏尊、沈仲九、孙俍工、余家菊、陈启天诸君虽然都是初次相识,但因为大家都是‘新文化’——新文化最简单的标志,是弃文言而写语体文——中人,思想相同,而大家又都肯努力学文,没有染上一般教员放下课本即行聚赌的习气,所以感情上都很好。平常无事,很容易集在一起清谈”[7],而请夏、沈两人到家便饭,“我们之间,也觉得这种无拘无束有如家人的生活很为有趣,每次见面总是无挂无碍地畅谈。如吃晚饭,则非到学校要关门的时候不散。在罢教的时候夏丏尊、沈仲九寄居我家,我们三人促局斗室之中,话匣子总是不关,有时夜以继日地睡在床上通夜谈话。那种诚恳坦白的同事生活,也是我教师生活中所绝无仅有的。”[7]交流带来的是学术思想的碰撞和进步,“因为常与夏、沈、余、陈诸君过从,而他们所习的又各不同,余与我虽同教教育科目,但平日的学历也不一样,于是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也都与我的知识交织,而将我的学问范围扩大,学术眼界提高……我的新知识却日新月异地换来不少”[7]。
这一时期为了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办成湖南文化的中心,学校主持者提倡学生自治,并鼓励他们参加校内各种活动团体乃至校外的政治社团。据陈启天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笔者注)夏,长沙第一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笔者注)教务主任匡务逊(匡互生——笔者注)出外聘请教员,有余家菊、沈仲九、舒新城、夏丏尊及我应约前去。我们这几个人,在当时被称为新人物,而一时集中在第一师范教书,自易招徕学生。加之原来的教职员,如匡务逊、熊梦飞(熊仁安——笔者注)等,亦曾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民国九年前后,长沙第一师范,可说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办教育,在当时最受青年学生欢迎。所以我们在第一师范教书,也多受学生欢迎。学生亦有不少有志上进的,使我们觉得值得用力教导他们”[23]。当时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余家菊也回忆道:“校中同事者有匡务逊、熊梦飞、舒新城、沈定九(沈仲九——笔者注)、夏丏尊、崔载扬(崔载阳——笔者注)、毛泽东,皆俊彦之士,卓然有所建树。”[24]在此期间,舒新城做了若干教育改革的大胆尝试,尤其在训育方面主张推行“顾问制”,对此他日后曾解释道:“由学生择其平日所信仰之教师请为顾问,为顾问者对于学生日常生活上的事情都负指导之责。”他还认为“顾问制的精神有几分与英国大学的导师制(Tutor system)相似,是我四五年的理想,在湖南第一师范曾经施行一次”。[8]该制推行以后,舒新城竭诚指导每一位来问学校功课、社会问题乃至个人私事的学生,于是来者络绎不绝,竟有百余名学生选他做顾问。[7]可见该制在当时的学校训育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施行后也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如“因当时教师指导的人数没有规定,逐至多者指导百余人,少者无一人,教师之间很有问题”[8]。此外,舒新城还与其他教师一起废除年级制,开始试行学科制,包括(1)选科制——“允许学生于必修科目之外,可以就其性之所近选修若干种科目”;(2)能力分组制——“将各年级同一科目排在同一时间上课,听学生依其程度随班上课,依其能力随时升级。如二年级上学期的某生,其国文程度只能及二年上学期,而算学则可达三年上学期,则国文在二上,算学在三上受课。倘其算学能力特优,或于假期自行补习而能跳级,则下一学期可听其升至四上受课。”[7]为此他还重新编写讲义。
1920年秋,杜威、罗素、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张东荪等中外教育家、学者应邀到长沙演讲[25],舒新城、夏丏尊等人都参与了接待与记录工作。[26]。据有的学者介绍,张东荪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做了三次讲演[2]在湖南期间,张东荪还在发表于《时事新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舒新城君常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27]由此可见,此时两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这也为日后张东荪邀请舒新城出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改名为吴淞中学)主任埋下了伏笔。
四、吴淞中学与中华书局:在上海的教学改革及其成果出版
舒新城曾回忆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在教育学术之研究上甚有兴趣,在一师与同事学生相处也甚相得,自然不想有别的活动。但因为怀了许多教育上的主张,下意识中也未尝不有择机实行主张的倾向。这机会果然于十年春来临了”[7]。1921年春,张东荪推荐舒新城担任上海吴淞中学主任,为此舒新城于7月5日抵达上海吴淞中学。参观校园后,舒新城“决心要把这庄严的殿堂,变为理想的学府,而准备接受中学主任的聘约,努力于实现我的教育主张”[7]。他首先做的工作是整顿教师队伍,即“约请教员——教员之以‘声应气求’而来者,有叶圣陶、朱自清、陈兼善、常乃惪、刘延陵、刘建阳、吴有训、许敦谷诸人”[7]。另据丰子恺的幼女丰一吟记载,这一时期丰子恺除了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外,还在吴淞中学兼课,其同事有“舒新城(该校主任)、沈仲九、孙俍工、陈兼善、匡互生、周为群、陶载良、常乃德、张作人、朱光潜、朱自清”[28]等。舒新城进一步介绍道:“从十一年(1922年——笔者注)起,旧教员已完全退出,剩下我们所谓志同道合的十余人。我们都很年轻,也都很‘前进’,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问题,都有一些意见,对于教育则因为我们多数是习教育的——常(常乃悳——笔者注)、陈(陈兼善——笔者注)、周(周为群——笔者注)、陶(陶载良——笔者注)、孙(孙俍工——笔者注)、刘(刘建阳——笔者注)、吴(吴有训——笔者注)都是北京高师毕业的——故意见特多,而主张也特多。因为吴淞与上海隔得相当远,而我们又都是外路人,且都有努力学业的习惯,所以每逢假日或上课之余非有要事不去上海,总是大家集在一起清谈。因为各人所习的科目不同,所谈的范围也漫无限制,真所谓‘天下之大,苍蝇之微’,都是我们谈话的资料。我们除去好谈能谈而外,且好写能写。某种问题谈得有结果,或有很相反的意见,每每笔之于书向报纸杂志发表。”[7]
舒新城在上海吴淞中学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其中既有借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的学科制、导师制等,也有结合吴淞中学实际情况而新创的工作制、分科教学制等。工作制是指以工作代体操,舒新城曾言:“在体育方面,我们以为其目的不仅在增进健康,应于筋肉活动之中同时增加生产。”[7]为此他与部分教师 “曾将校外空地划分若干小块,由俍工(孙俍工——笔者注)、仲九(沈仲九——笔者注)领导着自愿的学生工作;不参加生产工作的仍上体操”[7]。分科教学制是指设立国文、史地、生物等分科教室,将各科应用的书籍和标本仪器集中在一起,以便师生分科研究参考致用,没有课的时候也是开放着,任由学生自由出入;同时“在教学方面,我们反对注入式,采用自学辅导,特别重视学生的自动”,为此规定各组的功课每周最多不过三十小时,使学生多有自习的时间,并规定教师在课外指导的责任。之所以能在吴淞中学开展上述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舒新城曾坦言:“我们把当时的学校,当作实验理想的自由园地而自由试验。……在十一年一年之间,我们因为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既不顾旧的拘束,政府的政令又每每不出都门……所以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只本着我们所见而努力地天天改进。”[7]上述改革都为日后在吴淞中学开展道尔顿制试验做了铺垫。
在上述一系列教学改革试验中,学科制可谓最基本的、影响最大的改革。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科制的弊端频现,据舒新城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编制课表费时费力,造成了学生功课相冲突的局面;(2)学生各科所能达到的学力程度不同,导致毕业期限难以统一,如英语达到了毕业要求,数学却还停留在低年级水平;(3)各科成绩优越的学生不能升级,只得按部就班按学程规定升级。[29]另外,舒新城也指出了学科制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1)学理上缺乏根据。改行学科制,旨在改变原来年级制不适宜学生个性发展,学生可以进行各科单独学习,某科不及格,只要复习某科,不用重习及格科目,不致耗费时光。之前学生因各科平均分不及格,按规定需要降级重学一年,现在某科不及格,只需一个学期重习某科即可,较之年级制,学科制省时省力,又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但从根本上讲,学科制还是存在重复学习的弊端,因为某科不及格,依旧要从头开始重习某科,学生固然没能达到某科学业要求,不能否认其在一学期中掌握了某科学程要求的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五,现在又要求他重习已掌握的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五。(2)有碍学生个性发展。学科制着眼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却又以一学期为某一学程的期限,这仍会阻碍学生的个性发展,因为每个学生的身心发育状况有所不同,所以就不能要求他们按部就班,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教学,否则个性难以真正得到发展。关于这一点,舒新城曾分析道:“现在实行学科制的中等学校,大概都是分科制,少数行选科制,但对于选课开班的人数最少亦有十人以上的限制。假定某校有近于美术的学生五人,无论如何,学校决不能单独为他们五人开班,这五生势不得不改学其所不愿学的学科。这样,又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吗?这些问题,我们主张选科的学科制的人,能有完满的答复吗?”[30]面对教学改革中遭遇的困境,再联系自己接受过的教育经历,舒新城指出:“因注重发展学生个性而采用学科制,发生的困难特多,有若干竟至无法解决,常常使我回想到旧时私塾与书院个别修学的便利与愉快,但受环境与时代的限制,又绝不能恢复私塾或书院的教学方法。适逢十一年六月,美国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道尔顿制介绍到中国,我们以为这方法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困难,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决定于十月起,先将国语及社会常识两科,试行道尔顿制了。”[7]
事实上,诚如舒新城所言:“道尔顿制的试行,在中国以我们为最早,而介绍以我为最力。我们曾于十一年在《教育杂志》中出一道尔顿制专号,说明我们决定采用此方法的原因,也就是学科制的困难的告白。”[7]舒新城介绍道:“道尔顿(Dalton)是美国麻沙朱色州(Massachusetts)的一城,有一公立中学名道尔顿中学;这地方本为纺织业中心点,学生毕业后大多要进纺织界,但学校却采苏格兰的经院制,以致与社会需要不相应,而高年生逐渐减少。校长乔克敏(Jackman)于一九一九年二月采用柏克赫司特(Miss Helen Parkhurst)女士的作业室教学计划。未一年,成绩卓著,柏女士以其方法在道尔顿中学试验成功,故名道尔顿制(Dalton Plan)以纪念之。”[7]他又把道尔顿制的原则及其精神较为准确地归结为“自由、合作,即不用旧日的班级制及钟点制,而使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与同学共同研究,自由学习”[7]。吴淞中学试行道尔顿制后,“全国轰动,各省教育界之来吴淞参观者络绎于途,每致我们应接不暇”[7]。尽管因试行道尔顿制而与学校当局意见分歧,舒新城于1923年1月离开吴淞中学,“但道尔顿制在十二年以后之数年间却风靡一时。试行此制之学校几遍全国——尤以奉天为盛”[7]。就舒新城个人而言,1923年2月他应东南大学附中主任廖世承之邀,到南京出任该校研究股主任,配合廖世承继续试行道尔顿制,并专门在东南大学开办的暑期学校讲授道尔顿制,还多次在上海、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做关于道尔顿制和教学法的演讲。舒新城日后回忆这一段经历时称“道尔顿制”四字使他成名,并跻身于“教育家”的行列,使其在中国教育方法史上占一席之地。[7]
从1922年舒新城撰写的第一篇介绍道尔顿制的论文《关于道尔顿制的著作》发表于当年第一期的《教育杂志》上算起,至1925年11月《中华教育界》第十五卷第五期刊载他撰写最后一篇展望道尔顿制未来命运的文章——《今后中国的道尔顿制》,期间他在以上两个教育期刊各发表了7篇研究道尔顿制的论文,此外还各有2篇文章发表于《学灯》《教育与人生》《中等教育》三种刊物,总计舒新城写了20篇以道尔顿制为主题的文章。在此基础上,1922—1924年间舒新城完成了四部有关道尔顿制的著作,按其出版顺序分别为《道尔顿制概观》(1923年5月)、《道尔顿制讨论集》(1924年3月)、《道尔顿制研究集》(1924年6月)、《道尔顿制浅说》(1924年6月)。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绝非机缘巧合,而是与书局掌门人陆费逵有着紧密的关联。
1922年9月29日,在吴淞中学宴请来校讲演嘉宾陆费逵的晚宴上,舒新城以该校主任的身份,第一次与之见面,前者年长后者7岁,但相晤甚欢,在饭桌上就开始畅谈,饭毕仍未结束,并致使陆费逵返程车期延迟,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事实上,此前两人对对方均有所了解,舒新城在校念书时就曾读过陆费逵发表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上的诸篇文章,而陆费逵除阅览过舒新城在上述两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外,还曾看过他《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纲要》两书。一面之缘后,陆费逵便致函约舒新城去沪长谈,据舒新城回忆称:“自此而后,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多,畅谈的时间更长,有时甚至谈了终日。”[7]两人的交谊更进一步。据载,1923年1月陆费逵“约舒新城入中华书局主持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因舒不愿管理事务,未果。……8月和舒新城合编的《新小学初级公民课本》第一册出版”; 1924年11月陆费逵“和舒新城合编的《新中学教科书人生哲学》全一册出版”。[31]自从与陆费逵结识后,中华书局便成为舒新城出版个人著述的首选之地,应该说这也为他日后应陆费逵之聘主持编纂大型辞书《辞海》,进而主持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创造了条件。
五、结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特定的人文环境中,舒新城往返于长沙与上海两地,穿梭于教育教学与报刊出版两界,“尽量利用既有的条件和业已获得的新思想资源,向正在勃兴的新文化运动靠拢,主动接受和参与了这个新事业,通过从事有关的活动,不断为自己在地方社会和中心地区积累人望与社会资本”[2]。具体而言,在主观上他通过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而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并接受当时先进的思想观念;在客观上他既积极争取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声援,又努力获得张东荪、陆费逵等文化出版界名流的提携,更广交夏丏尊、常乃惪等同行及同辈朋友,在学问和思想上相互学习与切磋,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及人脉关系。一方面,舒新城任教于长沙和上海的各所学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并把在改革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学说,再回到实践中对这些理论学说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的双向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舒新城通过撰写论著并利用报刊和出版平台,宣传自身和他人的教育观点、学说和理论,使之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出版推广的双向良性互动,对当时中国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推进作用。所有这些活动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文环境的产物,又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文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氛围及其特色。正是在此过程中,舒新城从一个普通教师逐渐成长为著名教育家,并为他最终成为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教育出版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