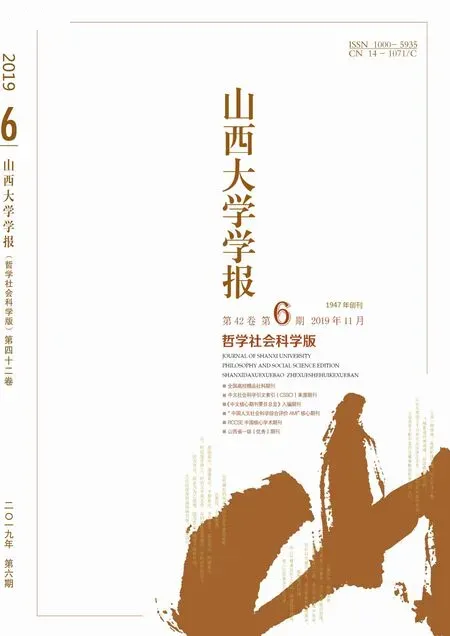《吕氏乡约》:北宋乡村社会礼教推行的理想与实践
2019-02-11王美华
王美华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吕氏乡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首部乡约,因其对元明清时期的乡约推行影响甚大,后世对吕氏首创“乡约”之举赞誉有加。近年以来,对北宋乡约的研究渐多,不再只是将其作为明清乡约的起源简单追溯。从《吕氏乡约》的撰制到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内容的变化,宋代乡约的实际推行及其与明清乡约的比较等方面皆有一定的探究和分析。但需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往往重视就乡约本身而论,缺乏从扩展的视域中考察宋代乡约的问题,尤其是从士大夫群体关注乡村社会礼教推行的视角,阐释和探究《吕氏乡约》修撰及推行等问题。也正由此,有关宋代乡约的论述虽渐增多,但对其修撰背因、体系设计、推行实践等问题的深入挖掘仍有不足。本文将结合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推行礼仪教化民俗的意识倾向及官方礼制下移的趋势特征,进一步分析《吕氏乡约》的修撰缘起、体系设计以及实际推行,阐释北宋士大夫群体乡村社会礼仪教化的理想与实践。
一 《吕氏乡约》的修撰与张载礼学的“致用”观念
“乡约”一词,首创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闲居于蓝田家中的吕大钧撰成《乡约》(1)关于《吕氏乡约》的修撰者,经南宋朱熹考究确定为吕大钧,后世基本因之不变。据《宋史·吕大防传附弟吕大钧传》记载,吕大钧曾“丁外艰,家居讲道”数年。根据吕大钧的人生轨迹,乡约正是其在熙宁九年(1076)于蓝田“家居”时完成并尽力推行的。(《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附弟吕大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47页。),关于《吕氏乡约》的修撰者,经南宋朱熹考究确定为吕大钧,后世基本因之不变。据《宋史·吕大防传附弟吕大钧传》记载,吕大钧曾“丁外艰,家居讲道”数年。根据吕大钧的人生轨迹,乡约正是其在熙宁九年(1076)于蓝田“家居”时完成并尽力推行的,并推行于乡里之间。关于《吕氏乡约》的修撰缘起,学界各有说法,其中杨开道提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在《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指出:乡约的修撰乃是吕大钧受张载所提倡的礼学观念的影响而进行的以礼教化乡民理想的一种实践。[1]27-42这一观点获得了多数认可。至21世纪之初,胡庆钧提出“乡约制度的产生却是保甲制的一个反动”的观点[2];杨建宏则在《<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一文中明确认为:乡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王安石的保甲法的不满;吕氏兄弟创立乡约组织以加强地方自治,回应王安石的保甲法。[3]此种将乡约缘起与王安石的保甲制直接联系起来的说法,也在一定范围内被接受。然因《吕氏乡约》修撰和推行的时间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在无更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便推断乡约是与保甲法的“对立”,未免有些牵强(2)事实上,考究关于乡约修撰和推行的各种文献记载之后,并没有看到其明确针对保甲法的主旨迹象,更未见到其他人士论及其针对“新法”的问题,亦无来自“新法”派的有关乡约的意见。。事实上,杨文中也曾论及,蓝田吕氏兄弟之所以创立了“乡约”来与保甲法“对立”,“这与张载创立的关学的致用务实的特点以及吕氏兄弟师从并服膺关学有着密切的联系”[3]。换言之,其亦承认张载关学一派的礼学“致用”观对吕氏修撰乡约的影响。吕大钧为张载弟子,其撰制《乡约》,受张氏礼学观念影响,亦是情理之中。
张载曾讲学于关中,世称为横渠先生[4]12724,其学派于后世亦被称为关学。“躬行礼教为本”[5]11恰是关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与同时期的其他礼学思想不同,张载尤其强调礼学“致用”实行,从实践层面复古行礼:起于自家,外延至乡里之间;任职于地方则教化一方,闲居之际则行礼于自家。史载:“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4]12724张载自家婚丧葬皆用古仪并傅今礼,效仿遵行礼仪者甚众,“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6]383。此外,张载亦将复行古礼、教民化俗作为施政一方的职责,认为“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6]264在任云岩县令时,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6]382明确推行乡饮之礼仪以教民化俗。
需要指出的是,张载躬行礼教以化民俗,并非只限于上面两点,其还曾有过建构乡村社会治理“自治”组织体系的设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张载“移疾屏居南山下”[4]12724,退居家乡专注于讲学之际,将复行古礼、教民化俗的理念加以进一步的探索和讨论,更趋明确“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意向。[6]384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云:张载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6]384张载所议之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的理想体系,涉及井田、赋役、经界、宅里、敛法、储蓄、兴学、礼俗、救灾等诸方面,力图实现先王之古礼遗法、教化当今之乡民。其还曾明确表露出士人可“自行”此法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意向,所谓:“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6]384。尽管这种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设计,就张载而言“有志未就”,其被再次征召入朝后,于熙宁十年(1077)冬十二月病卒于临潼馆舍。但犹可试验之于一乡的主张,却显然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学生。
吕大钧出身于关中蓝田吕氏家族[4]10839,与其兄弟吕大忠、吕大临三人皆曾从张载学,明确承袭了关学重视礼教的精神。史载:吕氏兄弟“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4]10844。其中,吕大钧被称誉为尤其“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4]10844。吕氏五子登科,为当地名族,于关中地区甚有威望,所谓“关中化之”,或许过誉,但因遵行古礼于自家,引起周围士人重视家族礼法甚至出现一些效仿行事者,大概是无疑的。吕大钧秉承张载礼学“致用”、躬行礼教的理念,于熙宁九年(1076)闲居于蓝田家中之际,撰成《乡约》并实际推行开来,终将对乡村社会治理之理想设计“自行”“验之”于乡里之间了(3)朱鸿林认为:“蓝田吕氏乡约的性质是私人和自愿性的”。事实上,此约是“从不预期在政府的监管下运作的”。(参见氏著《中国近世乡约的性质、有效性及其现代意义略论》,收入《孔庙从祀与乡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23—241页。)。
《吕氏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罚式、聚会、主事等共计七部分。[7]563-567此外,吕大钧还另撰《乡仪》以为辅助,其内容包括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共计四部分,详细规范了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吕大钧创制了“乡约”的概念,设计了乡约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杨开道曾指出:陕西蓝田乃“关学根本之地”,吕氏兄弟即“所谓礼学实践之家”[1]28。吕大钧修撰《乡约》,源于张载的礼学“致用”观念,秉承其躬行礼仪教化的理念和主张。关于这一点,显然是无疑的了。然仔细考究吕大钧的“乡约”体系内容,却不难看出,其秉承的不仅是师门的传承,还有那个时代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共识”。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乡约》的内容与张载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设计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二 《吕氏乡约》的设计与士大夫群体乡村社会教化的理想
吕大钧撰制《乡约》明显是受张载的礼学“致用”观念的影响,然其体系内容却并非完全源自张载的复行古礼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设计。前文论及,张载退居乡间讲学之际,与学者议古之法,设计了理想的乡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内容包括井田、赋役、经界、宅里、敛法、储蓄、兴学、礼俗、救灾等诸方面,表露“自行”先王之古礼遗法于乡村的主张。对比而言,《吕氏乡约》的体系内容设计则有明显差异,其更偏重于礼仪教化、道德规范,而不包括井田、赋役、经界、宅里,甚至敛法、储蓄、兴学等方面也未有明确关注,惟有礼俗、救恤两方面的主要内容而已。由此而言,对《吕氏乡约》体系内容的认知,若只是探论到纵向“师门传承”层面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扩展考察视域则可发现,《吕氏乡约》的设计,其实与北宋中期以来官僚士大夫群体关注和倡导的推行礼仪下移于民间以教民化俗的倾向是同步的。
首先,《吕氏乡约》之中明确秉承的乡饮酒礼传统,正是北宋中期以来被官僚士大夫群体不断强调的乡村社会礼教推行的重点之一。北宋中期以来,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下移于民间、教化民俗的关注不断加强,突出表现就是奏请推动有关乡饮酒的礼文仪制的修订。例如,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中,田锡就曾“以白衣上书阙下”“请复乡饮礼”。[8]2在《请复乡饮礼书》文中指出:“颁乡饮之礼,修乡饮之仪”,使乡民百姓观祭献之严,阅揖让拜起之式,见升降进退之容,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乡邑化之。[8]29此后,奏请制定颁行乡饮酒礼之事不断。宋真宗时,孙何曾献五议,其四即是“请行乡饮酒礼”[4]10098;及至宋仁宗时,王琪上时务十二事,其中即亦有“行乡饮”之事[4]10245。有志于乡村社会礼教推行的官僚士大夫们积极敦促朝廷撰制和复行乡饮酒礼,除了奏请修礼之外,还有于任职之地方实际力行乡饮酒礼者。例如前文提及,张载任职云岩令时,每月具酒食,召集高年长者,举行仿效乡饮酒的宴饮聚会[4]12723,意在敦促将礼仪教化之谕传达于乡里之民。[6]382再如,张戬知金堂县时,“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4]12725月吉设酒食召老者宴饮,其子孙旁侍,劝以孝悌礼仪,亦正是履行乡饮之用意;且张戬还通过设簿“籍记”乡民之善行的方式,来劝善戒恶,督促乡民遵行礼教。总之,北宋中期以来,对于有志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官僚士大夫而言,推行乡饮酒礼以教民化俗,进而形成乡村民众礼让之风,在一定意义上已是一种“共识”了。
乡饮酒实质就是一种定期举行的尊老尚齿、明长幼之序的宴饮聚会。《吕氏乡约》体系设计中的“聚会”,正是秉承了乡饮酒之模式。“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7]567此外,《乡仪》之中列有“齿位”等条,强调凡聚会之乡人,坐序以年齿,以及聚会宴饮之相关程式等。按此规条,乡约成员需要定期聚会,每月一次小聚,略简;每季一次大聚会,较隆重。聚会之际,按年齿排序,尊老尚齿,劝以孝悌;论及善恶行径、书之于籍册,行赏罚之事。显然是效仿乡饮酒礼而制定的乡约成员的聚会体例,通过定期宴饮聚会,宣示礼仪教化之意图。
其次,《吕氏乡约》以遵行礼仪为主、以互助救济为辅的格局,与北宋中期以来的有志于推行礼仪教化的一些地方官的“劝谕”规条,有直接关联。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中期以来基层地方官推行礼教、导民化俗的事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一些地方官僚设计并颁布了针对乡村民众的礼教范式。例如,宋仁宗皇祐中,陈襄知仙居县,撰制颁布《劝谕文》[9]655以教化乡里,其劝谕规条涉及乡村民众生活诸方面,劝诫“吾乡”之民: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莫作盗贼、赌博、争讼、侵凌等。以期“吾乡”之民,家内和睦、子弟有学、乡闾有礼、亲戚救济、婚丧相助、按时耕作、无违法度。陈襄仙居《劝谕文》被认为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10]。既有对家内伦理秩序、子弟培养的重视,对乡民按时耕种、无违法度之强调,又有对乡闾之间礼义往来、亲戚邻里救恤及患难相助的敦劝,还涉及道路相遇避让之礼节,燕饮往来坐立拜起之程式,等等。意在构建起乡村社会生活的礼教道德规范,以期乡闾之间呈现“礼义之俗”的局面,“吾民”皆知“礼义”也。[9]655
与陈襄对地方乡里之民的礼教规范类似,蔡襄知福州时,着意于推行礼教,针对乡里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条其事作《五戒》以训敕之”[11]4516,其中涉及父母慈、人子孝、兄弟友爱、重视婚姻、和善乡闾等五个方面,以期居于“乡党”之民能尊礼教为良善。[12]1503-1504蔡襄福州劝诫之规条,虽不如陈襄仙居劝谕文那样的明细,但涉及方面、礼教用意相差无几。至于宋哲宗时,郑至道为天台令(4)郑至道为天台令时,当在宋哲宗元祐二年左右,时间略晚于吕大钧撰制《乡约》。,以为民俗鄙陋皆由礼教导化未至之故,遂宣布“谕俗七篇”,戒谕乡闾百姓孝父母、爱兄弟、睦宗族、恤邻里、重婚姻、正丧服、重本业,以期乡里百姓“各以此更相训教,率而行之”,则礼义之风“必从此始”。[13]927-932郑至道颁谕俗文,直接将孝爱于家、和睦于族、乡闾救济、重婚礼丧服等诸项礼教规范广布于乡党之间。细观这些劝谕或戒谕所宣示的大体相同的规范内容亦可知,在建构乡村社会礼教规范体系方面,北宋中期以来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中已是有一定“共识”的。而吕氏的“乡约”体系设计与这些劝谕或戒谕体系亦是基本相同的。
《吕氏乡约》的体系设计中,凸显礼教导向和具体规范的主要是前四部分内容。(1)“德业相劝”为首篇,要求乡约成员能够修身以善、齐家睦族、各治本业[7]563;(2)“过失相规”为次篇,列述犯义、犯约、不修之过三种类型,主旨意在戒谕乡约成员不可酗博斗讼、行止逾礼、行不恭逊以及交非其人、游戏怠惰等[7]564;(3)“礼俗相交”为第三篇,明确乡约成员各自家庭生活中的婚姻丧葬祭祀之礼,以及成员之间相互交往中的诸项礼仪规范[7]565;(4)“患难相恤”为第四篇,主旨在于强调乡约成员的患难(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互相救助的保障体制。[7]566上述四篇是《吕氏乡约》的主体,从修身齐家、任职置业、交朋处事的道德规范到言行举止遵循仪规的过失训诫,从冠婚丧祭、人际交往的礼俗规范到患难之际的互助相恤,诸条之中将推行礼仪、教化乡民的理想设计明确地阐述出来。而这种乡村社会礼教体系与陈襄等人的劝谕体系设计无疑是十分相似的。简言之,谕俗也好,乡约也好,涉及内容基本相同:家内—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妇有恩,宗族—少长有序、和睦相处、治产营家,乡邻—互助救济、往来有礼、各重本业,由个体之家到家族、宗族,再到邻里乡党,建构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礼教规范秩序。这一礼教规范体系的建构,正是北宋中期以来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对乡村社会礼教推行的理想设计。只是《吕氏乡约》的礼教理想设计是建立在“自行”试验于一乡的基础上,而陈襄等人的劝谕则是建立在官方督责推行的基础上的。
又次,《吕氏乡约》清楚规范了乡约成员冠婚丧祭以及人际交往诸方面的具体礼仪,正与北宋中期以来一些官僚士大夫积极倡导的礼制下移的倾向相对应。北宋中期以来,关于庶民百姓层面的礼仪规范的讨论一直存在,针对“士庶”“民家”或“民庶”的仪制诏令不断出现,制订并推行庶民礼仪的意识倾向也越来越明显。[14]60-61熙宁中,朝廷一度诏令太常礼官议定复行冠婚丧祭诸礼之事,但因如何具体制订礼文仪制仍尚未有明确方针,礼官多懈怠于其事。[6]384其后,随着推行礼仪下移的意识倾向更趋增强,具体礼文修定的方针和原则才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了。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正月,知秦州吕大防就正式进呈奏疏《请定婚嫁丧祭之礼》[15]1033,明确提出当推行婚嫁丧祭之礼文仪制,使“黎庶”“小人”视之“足以成化”。其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朱光庭进奏《乞详议五礼以教民》[15]1034、太常博士颜复亦上奏《乞详议五礼以教民》[15]1035,并明确提出:应修定“民庶所守”之仪规礼文,然后“就其便安”,引导黎庶百姓知晓礼文。正是由于讨论不断推进,修定庶民礼仪的方针方法逐渐明确,至宋徽宗朝制定《政和五礼新仪》时,最终明确列出了专门针对庶民礼仪的仪制条目。从时间进程来看,《吕氏乡约》的撰制正处于制定和推行庶民礼仪的讨论不断的熙宁时期,亦是制定庶民礼仪的方针和原则尚未明确、仍处于含混模糊状态的时间节点上,乡约的礼仪规定也恰恰反映了这一点。
《吕氏乡约》之“礼俗相交”篇,明确乡约成员社会生活、相互交往中的礼仪规范,此篇共计五条,包括自家婚姻丧葬祭祀、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庆弔行事、婚嫁庆贺遗物、丧葬灾患遗物以及婚嫁丧葬助事等。[7]565出于敦行礼仪的用意,吕大钧还特别撰修《乡仪》以为具体行礼之参照。以往学者在探究吕氏乡约的构想时,往往会忽视其后辅加的《乡仪》内容,若将“礼俗相交”篇与“乡仪”二者的内容结合起来考量,会愈加凸显吕大钧推行礼仪于乡村社会之中的理念。《乡仪》有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四部分,共二十三条。宾仪内容最多,具体包括相见之节、长少之名、往还之数、衣冠、刺字、往见进退之节、宾至迎送之节、拜揖、请召、齿位、献酢、道途相遇、献遗、迎劳、饯送等十五条;吉仪包括祭先、祭旁亲、祭五祀、祷水旱等四条;嘉礼包括昏、冠二条;凶礼包括弔哭、居丧二条。上述这些礼仪,包括了迎送交往、集会宴饮、家祭群祷、严婚加冠、吊哭居丧等各个方面,不仅涉及乡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还关注到家内冠婚丧祭的行事准则,明确表露出对乡村民众公私生活的约束和规范意图。当然,这种礼仪规范正与朝廷层面中的礼仪下移的进程同步,当时臣僚奏议中尚未辨明如何修定符合庶民百姓实际生活的礼文仪制,只是屡屡含糊提出“复行古礼”的主张,而此也表露在《吕氏乡约》的礼仪中了。其“礼俗相交”篇之开篇即云:“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7]565显然,吕大钧在撰制《乡约》及《乡仪》之时,亦无专门针对乡村民众的冠婚丧祭及交往诸礼的仪制规范,所依据者仍是《仪礼》这样的古代礼文经典(5)杨开道甚至认为:“礼俗相交”部分,其实是吕氏乡约“内容最空、布置最劣的部分”。(参见氏著《中国乡约制度》第四章“吕氏乡约的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8-87页。),此举与其一贯的复行古礼的主张是一致的。
所以,《吕氏乡约》的体系设计,虽与张载关学的礼学“致用”观以及“躬行礼教”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理念有直接关联,但其无疑亦体现着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群体推动礼教下移于民间、建构乡村礼教秩序的理想。
三 《吕氏乡约》的推行与士大夫群体“自行”礼仪教化的实践
北宋中期以来,官僚士大夫群体对礼教推行于庶民百姓层面的关注,并非只是敦促礼文修定、地方官劝俗行礼,亦有一些官僚士大夫“自行”于家外延及宗族邻里乡党的实践尝试。《吕氏乡约》的撰制和推行,与这些“自行”礼仪教化实践之间,亦有着重要的联系。
出于遵行礼仪、教民化俗的目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自行”尝试制定和推行家礼仪规,尝试以家族(宗族)为核心和基础,敦促邻里乡党遵行礼教之风俗。上文论及的张载、吕氏兄弟各于其家遵行古礼、撰制家族礼仪并教化关中地区,其实还有司马光、韩琦等人亦曾致力于家族礼仪的撰修和遵行。尤其司马光亲撰《书仪》《家范》等,并非只是针对自家,明显意欲构建一套体系完整的家族礼仪规范体系并力图扩展推行开来,此举未尝不是一种推行礼教于士民之间的努力尝试。司马光的《书仪》是北宋最精详的家礼文本,明确规定了家族冠婚丧祭诸仪,[16]尽管其中冠婚丧祭诸礼的主体步骤仍是多按循《仪礼》而来,但具体仪节叙述中顺应世俗民情、考虑“贫家”庶民生活的倾向清晰可见,明显表露出其欲将此家族之礼推行于普通士庶民众层面的意愿。
在官僚士大夫们力行礼仪教化的实践举措中,值得尤为注意的是范仲淹的义庄建制。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家居节俭“而好施予”,曾“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4]10276。宋仁宗皇祐年间,范仲淹花费巨资置田地十余顷,在苏州吴县创立了义庄,并制定《义庄规矩》十三条。以置田所得,“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17]917。《义庄规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诸房计口给米及冬衣;(2)婚丧支钱;(3)乡里、外姻亲戚相助救济[17]918-919。由此规矩可知,作为一种宗族共济之规范,义庄意在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衣食,有救助宗族贫寒者之主旨;规范族人的生活,通过婚嫁丧葬支助钱财,保证族人能够遵行婚丧之礼,避免因贫失礼、违礼;在保障规范同宗诸房之人生活的基础上,对贫窘患难不能度日之乡里、外姻亲戚,量行济助。《义庄规矩》中明确宣示“吉凶给之费”[18]579,强调遵行礼仪规范,不仅使宗族贫者婚丧嫁娶可“自举”;此外,还通过遇凶荒之际支钱先支丧葬而后及嫁娶、凶事同时则先尊后卑等规定,彰显宗族内部的伦理尊卑秩序。整体而言,这是一个以维系范氏宗族内部稳定延续为基础,外延兼顾乡里邻党、外姻亲戚的救恤互助体系,明确推动礼教法令遵行于乡村社会民众之间的实践尝试。义庄成员是居于本乡的范氏族人,义庄周济族人兼及乡邻亲戚,其实质正是以宗族为基础建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一种方式。
将范氏《义庄规矩》与《吕氏乡约》二者进行对比,(1)前者以宗族成员为主体,外延及乡里乡邻,后者主要针对自愿加入乡约的乡里之人;(2)前者设立经济基础,以经济保障和互助帮扶为主,而以礼仪引导为辅,后者则是礼教引导和规范为基础,互助帮扶救恤为辅;(3)前者发起者出资并订立约束机制,后者发起者订立约束机制,由众人出资维护体系运行。二者之间差异虽然明显,但建构乡村社会礼教秩序的用意是相同的;且二者都是以家族(宗族)作为基础和依托的。《吕氏乡约》的实际推行正是以蓝田吕氏家族(宗族)为根基的。吕氏家族于吕通、吕蕡时并未著名,至吕蕡六子“其五登科”后,声名迭起而为关中著族。造就蓝田吕氏家族声名在外的,当然还在于吕氏兄弟的治学有道。[4]10844乡约推行的重要前提就是基于吕氏家族在当地的威望和影响。今可见《吕氏乡约》诸篇之末,所附吕氏长兄亦为族长的吕大忠的一段陈述,明言吕氏家族推行乡约的实际意图,其云:“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推行乡约即愿与乡邻乡党共行“礼教”,“成吾里仁之美”[7]567。在这一段话中,吕大忠指明,吕氏家族倡导并推行乡约,欲促成乡党邻里之间的礼仪教化。显然,从实际推行的角度来看,乡约是为吕氏家族的乡约,而非吕大钧个人的乡约。换言之,乡约体系也就是以吕氏家族为基础,向外延及邻里、乡党等的乡村社会的礼教规范体系。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关注乡村社会治理,积极展开了对乡村社会礼仪教化的讨论和实践尝试,《吕氏乡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撰制并实际推行的,“礼教主张便是乡约制度的根本”[1]32。《吕氏乡约》为宋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乡约”范式,尽管这种新范式在实际推行之际遭遇各种阻力[19],实际推行的时间大概只有五年多(6)胡庆钧在《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文中提出:从熙宁九年(1076)到元丰五年(1082)吕大钧逝世,“吕氏乡约只在本乡推行了5年半”。这短短5年半当中吕氏乡约也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3期,第41-45页。),最终不了了之。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无法低估的。时至今日,扩展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吕氏乡约》,可见其不仅反映了是张载关学一派礼学“致用”的理念,更是镌刻着那个时代官僚士大夫群体积极推动礼制下移、建构乡村社会礼教规范体系的趋向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