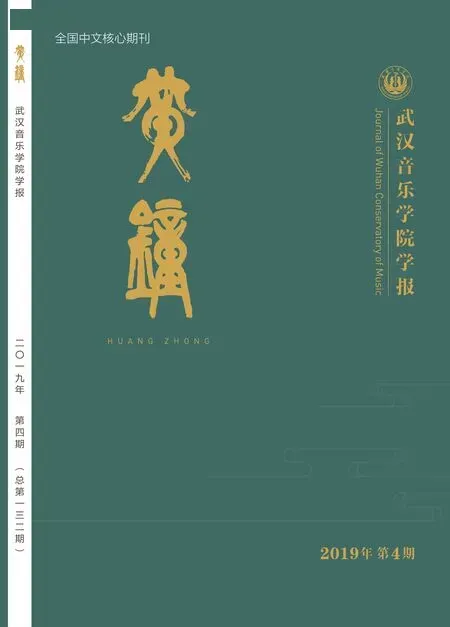变奏究竟意味着什么
——视听普瑞斯纳为电影《蓝》的配乐
2019-02-07刘夜
刘 夜
一种变化的重复,形形色色的重复,千姿百态的重复,万变不离其宗的重复……在基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1941—1996)和普瑞斯纳(Preisner,1955—)著名的“三色”之《蓝》(Blue)中,变奏纷呈,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变奏,在作业本上是一个手法,作曲家的手段技法之一。音色、音区、音值、节奏、速度、装饰音、对位、复调、句法等等都可寻求远近不一、弹性鬼魅的变奏元素。可那个“变奏源”——去向千山万水的主题如若真能确切指向什么的话,当这个主题如若又同时纳入了现代文明及现代哲学诸多敏感而困惑的根本性主题后,那飘逸的音符又是何以堪负与拖拽的呢?
一、朱莉叶的“波兰眼神”:肖邦—基斯洛夫斯基—普瑞斯纳
(一)何谓“神性”
有一类“简单”却异常神奇的音乐,异常久远异常撼人心魄,异常地动听着、诱惑着世界各地的耳朵——即古老的“土著人音乐”。比如非洲的黑人音乐,美洲的印第安人音乐,南太平洋诸岛的原住民音乐,亚洲的青藏高原民间音乐、阿拉伯音乐……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其语言、手法、风格各异,却共有着一种源头的音乐“基因”,一种生命之上亦根亦泥、亦凡亦灵的“宗教性”。
从文化和审美上看待“宗教性”,它再不单单是“宗教”了,我姑且称之为人文心灵的“神性”。何谓神性?此我理解的“神性”,即:生命特有的完备的独立系统和生命无尚的尊严(此因篇幅,不作展开)。人类正据此建立起开放的精神视野,进而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它是人文建构的归宿。所以生命的神性也是一个真实的创造态,并由此炫目纷呈地展现出生命的神圣和生命的无限动人。
还有一类是由有姓名的人所谱写的音乐,却因其极富人性且同样撼人心魄而被听者将之特别区分开来,因其极富异彩则必将被时间继续珍藏起来。比如肖邦、雅纳契克,比如普瑞斯纳……
(二)这两个波兰人
我一直信奉“神性”,而不能接受任何“宗教”。因为:我源源不断地被世间无限神奇的万象深深打动着,宇宙自然的妙合之处随处可见,逻辑的美韵分毫不偏,而终极的元点与终点却无以知晓,且“我”自身即是如此一份存在;因为:凡“教”,就意味着“人”所为,而凡“人”,就意味着大自然之一“局部”域或“有限”体——拿局部界定整体,以有限言说无限,至此,你是关闭还是开放?我当然选择逻辑。且再因为:尽管我深明Ta们(创始者及其教源)有爱与善的初衷,但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千万年它不流向万千可能的——“面目全非”之境。①作者注:“在神的本质的观点中肯定的东西仅仅是人的东西”,此为“神性”在“人性”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注42: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另参易中天:《艺术人类学》之“人类学与艺术本质的还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由此,我在阅读生活中一直追踪敬阅一位从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归来的刘小枫先生的思语。在看了由他以现代神学理论学术背景下所主编的《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不可言说的言说》《神学美学导论》等“学术研究文库”及“当代欧陆宗教思想系列”②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刘小枫主编:“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丛书,北京:三联书店1995-1997年出版;刘小枫主编:“当代欧陆宗教思想系列”丛书;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等宏篇之论后,偶从(又是这质地坚硬的“偶在”)《读书》(1997年2月)杂志上翻到他一篇《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这是为他称之“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而写的一篇祭文。文章开篇即蘸满思想者的深沉之爱:“听到基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③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电影?这可是在表达上最为“通俗”的一门语言啊!“大思想家”?我甚为好奇。随之,我便在现有资讯条件下“链接”上“基斯洛夫斯基”,又进而“链接”起“普瑞斯纳”。
基斯洛夫斯基被誉为“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最有才华、最无所顾及的电影大师”。④由中国中央电视台10频道“人物专栏·基斯洛夫斯基(上、中、下)”大型专题片片头语引自西欧众媒体。他自幼生长于波兰华沙,毕业于波兰洛兹电影学校。基斯洛夫斯基总是自编自导,并信守忠实于真实生活。他说:“摄影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摄影机只能讲述真实的东西。”对于生活,“我只能描述它,我不能编造它。”⑤[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其早年拍摄的《工人的七一年》(Workers’71)、《履历》(Curriculum Vitae,1975)、《宁静》(The Calm,1976)、《生命的烙印》(The Scar,1976)、《守夜者的观点》(From a Night Porter’s Point of View,1978)等就都以记录片体裁来真切关注城市居民、工人、士兵的日常生活,在当时波兰独树一帜。后以《偶然之生》(Blind Chance,1981)、《永无休止》(No End,1984)等多部视角独特、表达新颖的作品享誉欧洲影坛。并不断推出《十诫》(The Decalogue,1988)、《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1991)等力作跻身于20世纪世界最为锋芒耀眼的电影大师之列。更以涤荡现代人类深沉困境的封镜之作“三 色 系 列”《 蓝 》(Blue,1993)、《白 》(White,1994)、《红》(Red,1994)举世公认而横亘影史,成为人类艺术哲学相关教案的典范之作。
正因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主题之深沉、蕴涵之丰富、表达之奇异、镜像之细腻一向无人所及,影片的音乐就再不只是传统的电影配乐所要求和完成的渲染、烘托了。尤其在“三色”之《蓝》中,剧情主要围绕“当代欧洲最具才华的作曲家”及主人公的一部举世绝响为线来多重展开,音乐——就更上升为直接的主题和命题,并直接参与陈述、诠释、伸引、叩问、对答……等完整情节的灵魂共铸、血肉共熔无可分割的内容了。那么,一个非凡大师非同寻常之作中的非凡之任,也一定要由一个绝对非凡的作曲家站出来了!他,正是——普瑞斯纳!
普瑞斯纳,毕业于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先后曾与众多著名导演合作电影配乐,倍受青睐。如:与法国最为知名的新浪潮元老路易·马勒(Louis Malle)合作的《爱情重伤》(Damage,1992);与波兰著名导演霍兰德(Holland)合作的《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1993,其主题曲即为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所演唱风靡全球的Winter Light);与路易·曼多奇(Luis Mandoki)合作的《当男人爱上女人》(When a Man Loves a Woman,1994)等等。普瑞斯纳自言钟情于浪漫乐曲,他强调音乐的旋律是一首乐曲中最重要的元素,缺乏和谐与过于人工化的音乐都“不是他的那杯茶”。⑥罗展风:《电影x音乐》“哲理音符:蓝、白、红的三色人生”,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他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合作始于1984年,直至1996年基氏去世,12年中他们共同以光影声色编织了《无休无止》《十诫》系列、《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等17部为世人推崇的杰作。基氏一直高度赞扬普列斯纳的音乐,当观众影评人对其电影大加赞赏时,基氏往往把赞赏归功于普列斯纳,认为是普氏的音乐把自己拍不到的东西呈现出来:“他(普列斯纳)想要配乐的地方让我感到惊奇……”⑦[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181页。“我们两人好像有某种无法形容的心灵共通,拍摄《蓝》时,普列斯纳的音乐一直不停地影响我的思路……最后当我完成最后剪接,看到影片时,我才了解若没有他的音乐,我将无法把故事说到这个程度,好像他才是影响影片最深的创作者。”⑧[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228页。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因病去世,普列斯纳在痛苦中为亡友写下了《给友人的安魂弥撒曲》(Requiem For My Friend)。普列斯纳曾说,基氏的去世,就像他心里的某一部份也随着他死去一样。⑨普瑞斯纳官方网站,http://www.preisner.com。2005年香港的《号外》曾派员远赴波兰,访问了这位作曲家。岁月流逝,情谊都尽在普列斯纳的一番话里:“当你遇上一个人时,你总要知道,有一天,你或他将会有分离的一天。与K最开心的,是我们合作了17部电影,但我们的成功,不单是因为我们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俩对生命有共同的看法,这是一段美好创作期的完结,尤其是对我的音乐。”⑩《深圳商报》,2006年7月7日。
看过这些影片的人,“大抵不难察觉普列斯纳的乐音早为电影注入了一种听觉上的灵气——是形而上的、洗涤心灵的、具自省生命的灵魂乐章,也是鲜有在其它电影中所能接触的哲思乐音,像来自造物主的天外诗篇:纯粹、洁净、包容,叫人宁静与释然。”[11]吴冠平主编:《20世纪的电影——世界电影经典》,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页。
(三)母性的眼神
音乐未启前,我们先光顾一下影片《蓝》的梗概:故事从高贵、美满、幸福并具有作曲才华的女主人公朱莉叶自丈夫和女儿突然意外双双身亡切入。她在深深的痛楚中无以自拔而又自杀未遂。无以面对现实的朱莉叶决定匆匆抛却财产、房屋、感情、记忆、身份等一切,以漂泊新所寻求精神避难以期解脱。途中一路却发现世界充满无尽的可悲可悯的无奈之景。并意外地偶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富有才华的作曲家丈夫,生前竟另有婚外新欢,这给自以为与丈夫间始终恩爱忠贞的朱莉叶本已死灰般失魄中撞击来莫大的震惊和嘲讽,且丈夫的情人还怀拽温情和责任地怀孕着丈夫所不知的遗腹子。情感受虐,精神遭到新一轮冲击后,朱莉叶重新审视生命,如何安置自己?她再次投向丈夫应约而未完成的《欧洲联盟统一颂歌》。
笔者是一个较晚才听到肖邦音乐的人。不过,相比幼年就能听或弹奏他音乐的幸运者,我又很庆幸自己是在近“人到中年”时才碰触到肖邦的音乐。最初一听他音乐,心里就断定,他是个人间的精灵。后来读到刘小枫先生的那篇祭文,看了《蓝》《白》《红》,知道了基斯洛夫斯基也是个波兰人,顿然觉得那似乎盛产丰饶而脆弱、多情而哀伤的“眼神”。当进一步了解并敬仰于他编剧导演的《十诫》《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蓝》《白》《红》等非凡之作,尤其痴迷于这些艺术创造里的音乐及它们都出自于斯瑞普纳之手,又是一个波兰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又都曾安身(流亡)、创作于法国(巴黎),这时我更愿相信,那一路离神很近——那里存有更多男人的灵魂并具有女人的处境——母性的哀伤与无奈的自理……
我们在《蓝》的女主人公朱莉叶眼里,处处可见到这种巴黎街头的“波兰眼神”;我们从普瑞斯纳更多的音乐中,也时时可听到这种暗暗承受的真切的“母性”的眼神。
二、精神救赎的逻辑元点
一串串机遇或命定,经处处设埋下桩桩隐喻,流着淌着就溃不及防地抵向了宿命。这样的宿命一直是基氏电影陈述和叩问的母题。“基氏作品构成一个隐喻的织体,生活是在偶在的网络之中,一个个体的命运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永恒的依持。即使是爱,也在偶然中成为碎片。但这又都不是黑白分明的,是蔚蓝色的。”[12]刘小枫:《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读书》,1997年第2期。《蓝》《白》《红》三部曲是他们继拍摄完一系列“现代版”的《十诫》后,将《十诫》中的信条和自由、平等、博爱完全以人性、隐私及个体层面置入真切的现代社会,以期得到更广义的观照、打量、审视和理解。它们成为了基氏的“天鹅之歌”。基氏以“三色”来对应到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又互有交织与洇染。比如《蓝》取了“自由”,是关于爱与不爱、恨与不恨、赐予与剥夺……的自由,且无论怎样的自由和选择又都最终落入到囚笼深重的陷井之中。普瑞斯纳创作三部电影音乐也分别对应有宿命、反讽、伤痛三种人生体验。
(一)引子:无奈的沉痛
《蓝》的第一组镜头用了7分05秒钟,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一个偶然的车祸打碎了幸福(车祸是在高速行驰中美满的一家人正分享着有关一个病人的笑话时发生的):女主人公朱莉叶苏醒时得知丈夫和女儿都已丧生。幸福美满的生活骤间荡然无存,静默中的朱莉叶悲痛欲绝无以自拔,但她自杀未遂(护士及时发现)。
这一段画面滑过,耳朵里几乎只有车祸发生时的一声巨响,和朱莉叶夜间偷药自杀时砸碎医院窗玻璃的碎响萦回于耳畔,大段大段几乎没有响动没有对白的画面上也没有音乐。唯一一处音乐的“痕迹”、为音乐留下伏笔的是最初车祸发生时,画面里有一个彩球和一页(谁都不会经意的)乐谱从车窗飞出——又慢慢翻卷——随风飘去——那页轻飞的乐谱除了“真实”,除了“伏笔”,还有“宿命”的隐喻。
直至积淀下8分31秒的“静默画面”后,才在已故的丈夫、杰出的作曲家帕特里斯的出殡仪式上,缓缓奏起挽歌,出现了音乐。音乐在慢板上以单音小号“面无表情”般地滑出,冰凉、凝重。
音乐为b和声小调,音域在一个八度内,却以下行级进、下行小跳、上行小跳和一个上行大跳等“平稳”而“广阔”地铺来,竟在44秒时间里囊有明确清晰的“哀泣”“应答”“回忆”“惊叹”“疑问”“渴求”“抚慰”“虚弱”“安息”……等情态信息。取6/4拍,共6小节。每小节后两拍留作休止,气息长哽,悲风痛彻。画面上是女主人公在医院病床上从电视现场直播里收看出殡的情景。这段短小的音乐正是从作曲家帕特里斯应约尚未完成的《欧洲联盟统一颂歌》的主题抽拧出的一个哀叹式变奏,是为洗练的“引子”。音乐在第一次出现时,即有“自由”而又“宿命”的内核,隐喻“严酷现实”之音的同时也自然赋予了生命曾灿烂一时的丈夫“帕特里斯”的表征性。故而也几次作插入部(reprise)运用于后。
“严酷现实”果然卷土又来,影片在第10分40秒钟,躺在阳台上昏懵中的朱莉叶脸上拂过一道蔚蓝色的光,顷刻被冲天而出、迎头喷泼的管弦强奏所惊醒。1小节后则突转轻若游丝的双簧管答接,这里管弦乐配器具有强大的张力,强放强收仅6小节便陈述了人物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撞。命运面对偶发,美满面对坍塌,情感皈依荡然无存……她在慢慢苏醒之中步步逼近着真正的惊恐:如何咀嚼一个女人空前的、釜底抽薪的灵魂丧失与孤零零的无助无奈……
(二)主题:蔚蓝色的花瓣
基斯洛夫斯基自称“我知道我的电影想要什么样的气氛,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能帮我达到这个目的,也不知道怎么写那音乐。”[13][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181页。多年合作中,基氏总是从讨论剧本一开始就将普瑞斯纳邀入其中,直接参与选场、布景、拍外景、剪片、编辑等工作全程。基氏十分赞赏普瑞斯纳独立的创作见地,他曾对记者说普瑞斯纳是真正能与他一起创作的人,“而不仅仅是叫他找出一些已有的效果。我经常想要把音乐放入一个他认为听起来很荒唐的地方,而有些我没想过要有音乐的场景他却认为应该插入音乐,于是我们就把音乐插进去了,在这个领域他绝对比我敏感。我的想法比较传统,而他的思维则更现代,充满了惊奇。也就是说,他想要配乐的地方让我感到惊奇。”[14][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228页。
主题音乐Blue的第一次出现,是以钢琴缓慢奏出,与音乐同步的画面是以大特写镜头缓慢移对着“手稿乐谱”上的音符,又是一脸蔚蓝掠过,基氏“仿佛要把无形的音乐也要拍下来”。[15]罗展风:《电影x音乐》,“哲理音符:蓝、白、红的三色人生”。从朱莉叶来到钢琴大厅拿起乐谱稿的18分32秒至19分42秒时砸下琴盖,音乐未落她已承负不起。这也正是举世期待、她丈夫应欧洲议会委托所写《欧洲统一颂歌》的音乐主题。(见谱例)
这主题一吟一叹,规整乐句的每一小节都起伏滑动,弧线如同一瓣瓣花瓣在绽放、蜷缩,艳丽而清冷。在宗教性的抚慰感中又强大地潜流着丰富的变奏空间。
悲伤的朱莉叶无以面对附着有先前生活的一切,房屋、家具、存款、身份、友情、照片、乐谱……她一件一件清除或匆匆交给代理人处理。她上路了,选择去向一个精神避难的陌生之所。
离开之前,她还决绝地叫来了一直暗恋着自己的奥利维亚(丈夫生前的助理)同床一夜——誓作决裂过去。朱莉叶麻木地与奥利维亚拥吻时,蔚蓝的光普照着她坚毅的脸庞——主题变奏为小提琴铿锵的顿弓撕扯着……

谱 电影《蓝》的音乐主题
影片至36分58秒,画面为朱莉叶深夜被困于公寓走廊,意外看见邻房妓女在接客,关灯后嬉笑声传出时,Blue主题出现完整的第三次变奏,以较弱的人声哼鸣合唱和弦乐拨奏。
此后主题的每一次再现,都换了一件个性十足的乐器主奏和相应配器的变奏。既连缀呼应着各个蒙太奇散镜,又透射出当下人物内心动荡的丰富隐喻。
其间穿插了一个又一个的蒙太奇镜像,单独看似乎与剧中“主线情节”都并不相干,诸如:夜间于空旷的游泳池独自游泳;街头惨遭群殴的流浪人;街边老太太强撑着颤颤兢兢的身子艰难地将空瓶扔进垃圾桶;养老院半植物化的老母亲在看电视里颤抖的老头被搀扶着从高空跳蹦极;一无所知地只提醒女儿“要有钱”;街边哀伤的吹笛人及音乐;借邻居的猫来杀自己不敢杀的房内刚出生的幼鼠;意外打碎了花盆;雨滴声的蓝色风铃被撤碎;透视镜下子宫里婴儿胚胎的蠕动;跳脱衣舞的妓女正欲上台却发现台下第一排观众里有自己的亲生父亲;瘫倒在路边的人被唤醒后嘀咕出一句“人都有放不下的东西”……
都是不知姓不知名、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人与事,可是显然,一路处处都是普通着的触目惊心,这日常化的“偶然”世像也正是音乐或无声的空白所要延展和所要叩问的一个个血泪个体——都放不下什么呢?天下真有出路吗?真能有伤痛与苦难的逃避之所吗?!看似影像的“画面复调”跳出了“主调情节”……自由诉求的事件变了,但事件的本质不会改变,依然去向宿命。一个个姓名都不同,时间也不同,一桩桩事件不一样——主题是可换不同乐器演奏的,浮生世象是可“变奏”的——可“放不下”的依然是那个“主题”,比如苦难,比如爱,比如伤害最亲的人,比如摆不脱的天涯沦落。
编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是一位善于捕捉浮动在生活中看得见的表征层面与浸透在生命里看不见的隐喻层面的“思想叙事家”,而普瑞斯纳的音乐极具驾驭“看不见的一面——生活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驾驭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223页。
(三)合唱:痛惜地救赎
《蓝》的音乐在充满浓郁的电影叙事感中,不时以句法的回旋和画面音效时淡时强,不时地唤起听者油然关照起自我生存与情态和对生命的反思,且始终引领剧内和剧外人紧迫地期待、追寻的出路和更为深远的安置之所。
朱莉叶偶然从电视节目里意外看到了丈夫生前竟有外遇,丈夫与美貌的情人亲昵的画面令她极为震惊。当朱莉叶怒冲冲找到这个情人,知道他们也深深相爱,并发现她正怀孕着丈夫生前所遗的孩子时,她又不知所措。对于深爱、愤恨的这个丈夫,他已经不在这个人间,面前尚为学生的女人已在品尝母亲的滋味了……朱莉叶又经挣扎,试图平息自己,寻求新的打理情感的途径。她将丈夫的情人叫来,把即将卖出的别墅收回并将这钥匙交给她手里,还叮嘱让孩子出生后就随丈夫的姓来取名……
朱莉叶正神奇“化蝶”,化炼出又一种爱的能力。
向以打捞“哲理音符”著称的普瑞斯纳在《蓝》中的主题与变奏,整个音乐都要面对的是:天罗地网,都将因爱而驰入陷进;解脱出路,又只能以爱来救赎余生。
接着,朱莉叶找到丈夫的前助理,他们共同为帕特里斯未完成的作品续写起来。这里出现了音乐Oliver and Julie-Trial Composition一段。画面又是特写乐谱手稿上的音符,与音乐同步滑进。钢琴和中提琴轻柔地前奏,紧接声势潮涌般的管弦乐队大线条地掀起。此处朱莉叶改为“去掉打击乐”,更加突出小号在高音区的傲然迎风。再由钢琴弱收过渡传递给饱含哀鸣、超然、抚慰的长笛乐句。
创作者和剧中人同熔在生命之爱与精神焦虑的深渊里,艰难地层层穿越着“个体偶在性”、自我愚弄般的“个体自由”、咽喉中粘液般咳嗽不出的既空洞又充实的“双重无奈”……,可仍固执地要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来——珍惜这残缺破损的爱的碎片。是的,只有爱,一切化为爱,才是真正抵挡伤害、救赎苦难的唯一出路,方能倍加无防无备地来承受命运的作弄。著名思想家刘小枫先生把这种特有的“痛惜”称作“蔚蓝色的信念”。[1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255-256页。
影片至1小时25分38秒,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颂唱乐段出现,前为合唱,后为女高音独唱,这也是《欧洲统一颂歌》的结尾段。歌词借《圣经·保罗》第13章关于“爱”的赞词。气势高亢、声线干净,以爱的信念颂唱出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庄严而神圣。画面再次以特写乐谱手稿上的音符切入……后又大胆转入足足3分钟的完全黑屏中,只闻其声的慰咏“长镜”,直至影片结束。
“音乐导演”普瑞斯纳在这里特选用古希腊文来演唱:
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
我即使有先知讲道之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念,哪怕就能移山倒海,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
我若倾其所有周济穷人,又舍我身叫人焚烧,可如果没有爱,仍然算不了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羞耻之事、不求己利、不怒、不恶,只求真理;凡事包容,凡是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恩赐的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18]《保罗:科林多前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版,第194页。
(四)余音:精神皈依
“惟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时时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即头上闪烁着繁星的天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以此集结了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精神交汇,随之一个启蒙理想冉冉呈现:敬畏秩序与良知,精神律令源自人心自立。[19][波]基斯洛夫斯基、皮斯维茨:《十诫——Dekalog十个电影故事》“序”,陈希米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
时代,譬如大街上的交通,我看得见,那秩序是由红绿灯加持以法律、规则的警察在维系。那精神秩序呢?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有个观念:“文化必须维系秩序”。他说,有史以来,如果文化不能成功地处理基本的问题,就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文化必须激发成员持续生存下去并参加持续生存所必须的各种活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要保持适应,它必须能够变化。”[20][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之“文化的功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据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第10版),第49页。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我们的一切精神创造,必须建立和维系我们的精神秩序。那么“生存”“秩序”“适应”无疑是大地上“母性主题”的支撑基域。
其实,宇宙即秩序!春夏秋冬是秩序,星系轨迹是秩序,星球大小、能量多少、倾斜角度、运行速度……无不是秩序,那么是谁在维系呢?谁是那个贯彻宇宙力大无穷的“警察”呢?又比如,你如何理解生灵里不可思议的,那真正彻底——无私——的母爱呢?
是的,爱——具有这个力量,宇宙的“母性意志”是这个“警察”,它持有的法律或者法则就叫“爱”。康德所敬畏的“星空”正是宇宙母性意志的壮阔秩序。
现代困境的突围依据与途道,也必依旧在“根本”处得以凛然昭示。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虽刨掘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已是一份安分的回归,但其着眼之主体,比起康德之怀来,还是孤立了多,局部了些。
艺术哲学领域一路追问的“何为诗性”?譬如,肖邦以“钢琴诗人”定居于人类音乐史。文献和浩如烟海的唱片还提出一个“肖邦音乐中最难驾驭的是玛祖卡”的命题。肖邦稍嫌过激地也曾自言“我的钢琴只熟悉玛祖卡”,且他的“天鹅之歌”也确是“玛祖卡”。肖邦永不厌倦地挥洒那些奇妙多变的重音、非平稳节奏、骤喧又静骤热又冷,且舞亦歌亦诉的“玛祖卡”里究竟承载着什么样的景致呢?其实,那恰恰不正是最为简练而又无穷丰富的“变奏元素”蕴涵其间么?
笔者再次领认到:真正的诗性绝不是浮躁,绝不是虚妄。诗性的实质正在于:揭穿一切欺骗,直抵真相。而要揭穿山重水复天落地网层层胶膜般的一切欺骗(包括自欺!),那灵魂中的深刻内省,浸入骨髓的别无旁杂,是定要一番可贵、可靠、且更为敏锐而丰饶的“真切”去抵达的。
那么,爱——的抵达,就要求必须有这样一个品质。
结 语
普瑞斯纳为电影《蓝》的配乐结合电影隐喻性叙事与现代精神所探求的主题展开观照和评述,从音乐主题随着影片各发展情节丰富而巧妙的变奏,由“灵性”音乐切入现实境遇的情感归宿而追问“神性”力量,由艺术形态向艺术美学审视,在艺术哲学层面提出“母性精神”的人性皈依,并作了一定的阐释,认为普瑞斯纳以音乐如何探求、陈述、传达现代人的精神皈依具有启示意义和价值。
上世纪在创作上推出一部部经典之作,激情而冷峻地专注于现代人伦去向的伟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说《蓝》:“是一部表现音乐的电影。”[21][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228页。这是指的制作过程,而《蓝》事实上是一部用音乐探密康德代表人类无限敬畏的那个“法则”——爱——的皈依的注码。
基氏曾言在他的电影中,事情很少是直接说出来的。“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幕后,你看不见它。它可能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也可能在音乐中,灯光中。”基斯洛夫斯基是幸运的,上帝赐予了他一个普列斯纳。基氏异常要求电影配乐里的“音”外之音,他激赏普瑞斯纳:“你如何才能描述音乐:非常美?庄严?绕梁三日?神秘?你大可把这些形容词全写下来,但是你还是必须等作曲家去发现那些音符,并演奏出来。而这些音乐必须能够与你前先写下的文字彼此呼应。这些全让齐毕尼夫·普瑞斯纳给出神入化地办到了!”[22][英]达纽西亚·斯多克编:《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第181页。
这个以音乐出神入化的穿越者,普瑞斯纳却不是音乐学院出身的,他的本行是法律和历史学,他从未跟谁学过作曲,音乐完全自学而就。他天然地只知道、只需要忠实地捕捉在他心尖上的脉流,心灵在哪里,心音便流向哪里,且又敏锐地富有哲思地品尝……甚至“凡是已经确立的形式我都试图尽量避免”。[23]刘索拉:《行走的刘索拉——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禁想起很多如马友友那般,大学生涯从朱莉亚音乐学院退学转而去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直至博士学业的音乐家来。这样,也许他们正是为让那些音乐学院和作曲系走出的人才们,甚至让音乐大师们的门徒们再次躬身自问音乐的“心灵到底在哪里?”的启示。
是的,音乐具有若干独特的属性,是人类“既崇尚秩序,又表达自由;既体现万物共存,又尊重个体差异;既协调人与自然,又沟通神人世界;既拓展人类智慧,又捍卫美善法則的文化范式。这种能体现某种宇宙法则的文明范式,为人类精神世界提供了神奇的人性守护和社会形塑力量”。[24]臧艺兵:《论音乐法则与人类生活秩序》,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1卷,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