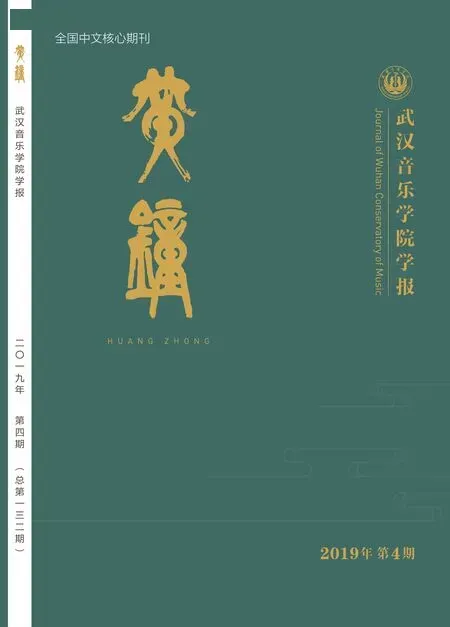拥有六十年经验与经验用了六十年
——李文如纪事点滴
2019-02-07张振涛
张振涛
一、崇本重旧的手艺
1994年,我到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孤庄头采访,看到音乐会老师傅刘万福残破不堪的谱本——一小捆勉强连在一起、已经端不起来的谱纸。然而,其中的抄写式样,却是唐宋俗写字体。不知道乐谱还能不能修复,抱着一试的态度,带回中国音乐研究所,交给李文如师傅(我们习惯于叫他“李师傅”)。他看了一眼说:“放在那里吧,过几天来拿”。说实话,我心里直打鼓,这么破的谱本也能修复?过了两天,我到他那间位于图书馆顶头的小作坊,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本装订整齐的谱本。封面用现代硬纸装订,端口线锁。内里用新纸在旧纸下重新托衬,即在新的宣纸上刷浆,把老谱面贴在上面。经过垫衬,残破谱页不但连接起来,而且硬整挺脱,不易撕裂。剩下半面或三分之一的老谱页,粘连的平平整整,与两天前的模样判若天壤。我揉揉眼,搓搓手,轻轻托起谱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两天前拿回来的“碎片”。待我把“新书”拿给孤庄头的刘万福老人时,他像我一样,揉揉眼,搓搓手,轻轻托起谱本,同样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碎梦”。起死回生,就是李文如在京城古籍修复界久享大名的本事——令旧籍、残卷甚至碎片,旧貌变新颜的美容术。这自然也是他在中国音乐学界鼎鼎大名的原因。
这样的事,可不止发生过一次。我把天津市静海县东滩头乡南元蒙口村音乐会的谱本拿回来修补的事也是一样,那也是一堆残破凌乱的散页。数日后,经他过手,端严若经,挺挺脱脱,焕然一新。后来,我们把冀中音乐会较好的谱本都拿回中国音乐研究所,交给李文如复印。他把前后加上封面封底,我把乐社情况打成一张“说明”,放在前面,装订一册,成为资料。这种收集方式,是中国音乐研究所老一代学者和资料人员沿袭下来的规矩。
1999年,《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及成寿寺旧谱》获得影印出版的经费,但须把线状的老谱本全部拆开,逐页扫描。他跟书到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待扫描之后,把谱面用木板压紧,手拿针线,重新装禙。一双巧手,平如权衡;一双睁目,明如水境。针脚距离,像测量的一样均匀。既成,不更一针。
以旧书成新本,以新版从旧籍,就是这个行业崇本重旧、翻旧如新的规矩。最后,乐谱恢复如初。我之所以想到这些细节,就是因为若没有这些细节就无法再现现场感中像母亲为孩子洗澡一样的笃定形象。
二、不可替代的角色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他仅仅是个图书管理员,我们这批从地方考进京城的外地学生,有一阵子开始大量采购古代典籍。哪里有便宜的旧书店,哪里有版本较好的重印本,他都门清。我们常要先去请教他,再按图索骥。至于许多基本的版本学知识,都得益于他手把手的指教。他把图书馆收藏的数种陈旸《乐书》(元刻明递修本、光绪二年广东方氏刊本等)、朱载堉《乐律全书》以及《律吕正义》等不同版本的优劣,拿出来一页页翻着告诉我们。现场教学比起读版本学的知识更易理解。他还教给我如何通过纸张鉴别年代,让我能够大致鉴别民间谱本的抄写时间。
1954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成立,自那时开始,他便在这座享誉音乐学界的专业图书馆里负责采购、装订,一待就是一辈子。不忍旧书散市井、委泥沙、饱虫鼠,明珠暗投,惟愿把不同渠道和旧书摊上捡到的包括《义轩琴经》等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古籍、乐谱、刊物,一一捡拾,汇总一堂,成为他一生恪守的才业操行。
自我进入中国音乐研究所后,就见他每天上午在图书馆干些杂务,然后骑上自行车,钻进北京的大热天或大雪天,到各家书店和旧物商店,购买书籍并予记录。凌冒雨雪,不避寒暑,马不舍鞍,身不释甲。回来时,车筐里总是装得颤巍巍的一堆书。
20世纪的天幕,喷射出一簇簇炫目的礼花,但新时代的炫目礼花往往以牺牲旧时代已经黯然失色的珍宝为代价,所以,自那之后,他便开始检拾天花乱坠后被丢掉的珍宝。旧时刊物,经过战乱,多有残缺,难以齐全。20、30年代出版的《乐风》《音乐杂志》《音乐季刊》《音乐小杂志》(共两期)等,均属稀有刊物。1949年前的刊物,多不定期,也没有常设机构,旋生旋灭,难以蓄聚。要想配齐,谈何容易。汇集1949年前所有出版的总计133种音乐期刊,是时代断裂和社会转型后才能感受到的可贵举动,让人懂得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及时动手的预见有多么超前。
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收集的刊物,不但包括学术类,还包括《民族音乐》《歌曲月刊》等创作类期刊。为了凑齐全1949年后出版过的140余种、总数4440期的刊物,他的操心程度,比其他人更甚。“日知其所不足,月无忘其所缺”。心里永远装着哪类期刊还未凑齐的名称。最后,20世纪的所有音乐刊物,一本不缺,全部汇集一堂。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赢得了刊物收集最全的荣耀,这项荣誉中既有像杨荫浏、李元庆等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也有像李文如等执行者不懈努力、常年不辍的行为,他们的名字,是20世纪期刊汇总行动中无法绕开的存在。
中央音乐学院专门从事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汪毓和教授评价道:“一本刊物若是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找不到了,大概就不存在了”。上海音乐学院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的戴鹏海教授也说:“一个课题的可行性如何,要先看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后再定”。编辑《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的孙继南教授说:“我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史料,不是研究人员提供的,是音乐研究所的资料人员提供的”。他们的赞誉,都是亲身感受。这些常出现于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的受惠学者,都对李文如报以充分的尊敬。
李文如深信,所有的资料都精彩,到了有用之人手里,都是宝贝。从他随口说出的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来找到了什么资料并印证了什么事实的故事就可见一斑。那些故事和见识,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谈起为某位外地音乐家找到心仪已久的资料而高兴时,他甚至比人家还高兴。花一生精力,给音乐家查找资料、获得论据、提供保障,是他觉得自己没白忙活的最大安慰。以团体为依托,因机构的影响力而有了自己的影响力,就是他认为的最好回报。其实,一座图书馆名声是要看吸引了什么读者。音乐学界几乎没有不到过这里的,我们开玩笑说:“若没进过这座图书馆,还不能称为音乐学家”。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人知道,找不到书,就去问他。他走进藏书室,准确走到书架前,第几排,第几栏,一把抽出来,准确无误。那种速度,就是用心程度的见证。
Study on Risk Perception of Chinese Tourists Traveling to the Philippines——A Case Study of Xiamen Tourist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ENG Yu 18
李文如资性淳笃,做人低调,谦谦君子,不计声名。收集图书,摩挲期刊,变废为宝,借以自娱。他的安静目光,就是苍天赐予。晚年闲居,不交宾客,嗜酒自奉,凡数十年。当21世纪电子书的灿烂阳光冉冉升起时,因摆弄线装书而成就满满的李文如在终身不离的北京度过了最后时光,享年91岁。
三、第一部期刊篇目工具书
无间断收藏,留下了20世纪未断档的全部期刊,成为一笔惊天财富。李文如的不凡之处或令人叹为观止的举动,就在于琢磨到了把这份财富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工具书的创意。那代人的历史意识是天生的,这种似乎只是研究人员才有的整合意识,产生于他身上,一点不让人吃惊。没有转化,价值便得不到提升。重布山河,成为他后半生矢志不渝的目标。
1949年前的期刊杂志,曾在资料室主任文彦带领下,编为《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1906—1949)》,198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薄薄的小书,促使了李文如的更大计划。把1949年后所有期刊的篇目,重编一书。于是,他逐渐把期刊目录,全部复印出来,订为一本本单册。《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音乐艺术》等,先单刊复印,后汇为一体。图书馆阅览室左侧,一直放着蓝色封面装订成册的各类刊物目录的合订本。它们都出自李师傅之手。然而,没有经费,壮志难酬。乔建中与我正巧在台北讲学,于是联系了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由其资助,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版《华文音乐期刊篇目资料汇编1950—2000》。
虽然在台湾出版了,一是价格昂贵,二是运输不畅,内陆根本见不到,起不到传播作用。这项由“施合郑民俗基金会”资助的非卖品,印数只有300套。所以我们决定再出简体版。我找到文化艺术出版社王红,由“杨荫浏基金”资助,2005年出版简体版《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
两大本380万字的大部头工具书,成为李文如人生的顶峰之作。十年一剑,心织手耕,累摞一编,平生雪鸿。不起眼的资料员,被厚厚两大册工具书抬至到学术史的高位。“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荣也!”①[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90页。这项荣誉超过职称分量,补偿了他未能获得专业职称的遗憾。人人都想做“惊天动地的事”,不愿意做“默默无闻的事”。而有心人开始做“默默无闻的事”,最后必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人之差距,就在小事上。他没有追求永恒,不问名声,却因此而永恒。从延续的意义上讲,这部反映20世纪音乐期刊全貌的工具书,历史价值绝不逊于任何学术专著。

图 李文如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
计算机时代来了,查阅方式变了,但人们依然用得上工具书。翻读纸质和油印的工具书,让人感到温暖——没有冰冷的荧光屏闪动的温暖。人类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关键书目,因辐射力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工具书就是其中的“钤键”。因其存在,使后人有了扶手与台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研究20世纪期刊发展史的硕博论文,每每看到引用这部书,都让我们益加敬重编者。
四、小事见不凡
我老家在山东济南,父亲在山东省音协工作。每次回家,他总是叮嘱我找几本缺失的《山东歌声》《齐鲁艺苑》《齐鲁乐苑》。这类地方性刊物,不但不定期,而且常未公开发行,印数不大,书店也买不到,所以难找。但只要有一本未凑齐,他就放心不下,定要通过各种关系补全。没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人逼他这样做,更没人监督他这样做。自觉行动,习以为常。“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于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②[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如果那样,图书馆就没有了连续不断的期刊,就没有了20世纪所有期刊篇目目录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他之所以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就是为了这份连续不断的学术史百分之百地不打折扣!这是多么高远的意识。有这等意识的人,仅仅是图书管理员吗?他像“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文人一样。这就是职业操守与境界!
编辑《杨荫浏全集》时,查到他汇为一编的资料集——杨荫浏参与“六公圣会”编辑《普天颂赞》时在教会刊物《真理与生命》专栏《圣歌与圣乐》发表的16篇文章。手持此编,不禁大惊。默默做事的李文如做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事!只有当后人用到这类资料时才发现,他已经准备好了。唾手可得的“伏笔”,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埋下的。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常年从事一个行当,会产生一种超越时代的敏感性,甚至想到了后人可能会用到什么资料而为你准备就绪的超前意念。这如同学者发现关键的问题意识一样,一目通灵,烛照万里。
许多人失去了职业操守,那意味着失去了在纷乱世界上划定用武之地的自信与自足,意味着失去了面对困境时必须获得“手艺足以用世、才干足以当难”的应对技能。比起平凡岗位上没有大起大落的李文如来,无职业操守者没有故事,因为没有体现其生存能力的技术支撑。大家之所以能深刻地记住他,不但因为他那一手令人称奇的绝活以及一捆捆装订成册的书刊,还因为一份处处体现职业操守的超前意念。他把生命,定位一业,左右逢源,出手不凡。他找到了施展抱负、释放才能的灼点。李文如一代人比之我们遇到过更多翻天覆地的社会动乱和内心冲突,有过比之我们的生活平均点更低的起点以及更难适应的环境和土壤,但这些都被他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找对位置,应对从容,不吝私力,方便众人,平和状态,美风美仪。面对这类能工巧匠,我们方能沉思,一生定位,多么重要。
21世纪初,伍国栋告诉我,他回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期刊,发现出现了断档,期刊缺期了。不能不说,导致如此的原因一是全国音乐类期刊数量暴增,二是因为没有了李文如这样的员工。他退休了,那个位置,无人能补。只有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一个人的重要性。他的离任,就是断裂的开始。下一代人谁还能像他一样为了缺一期刊物像丢了魂儿似的、非要补回来才能睡个安稳觉的劲儿?
五、众家评价
为资料员歌功颂德的不多,乔建中、梁茂春,英国学者钟思第,都为他写了专文。台湾繁体版《华文音乐期刊篇目资料汇编1950—2000》出版之际,我请乔建中做“跋”,题为《文如其人》。我把此文也附于《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之后。钟思第用英文记录了李文如给他留下的印象。三篇短文,各自描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也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梁茂春教授的评价独特而新鲜:
李文如勤勤恳恳地在音乐史料的收集和建设方面工作了一辈子,他使我联想到金庸在《天龙八部》里描写的那位“扫地僧”,扫地僧隐匿在藏经阁沉默寡言地打扫卫生,凡四十年,而他却是身怀神功的武林高僧。
什么是“扫地僧”,就是深藏功力而不出来折腾的人。面子上的事,他不掺合。等到玩不下去了,他出来,一扫定乾坤。作为研究所最早的老人之一,他做事规矩,不越本分,却常于关键时刻,解决问题,是位名副其实的扫地僧。
他的朴素外表与身怀绝技,好像很不相称,擦肩而过,会觉得太普通。一次与一位朋友出门,正遇上他推车从外面回来,春天大风,虽然戴着帽子,依然灰尘满面(自行车后座的书刊却被捂得严严实实)。朋友听说过李文如的神话,却在初见时嘀咕了一句:“这就是古籍修复专家?”
21世纪初,中国音乐研究所在香港大学举办音乐文化展,为了给他一次去香港的机会,也给他了一份邀请函,那意味着由对方出资、让一生疏食粗衣、寡于外游的老先生奢侈一把。到了签证处,公安人员问他身体健康情况如何,本可以用一句“健康”的话挡回去。他却当真,说身体不好,这病那病。结果,公安局没给他签证。唯一一次机会泡了汤。我们都说他太实诚了。然而这就是李文如——集和善、认真、糊涂于一身的“李师傅”。这或许就是福楼拜笔下“淳朴的心”的样子。
我为李石根《西安鼓乐全书》写书评时套用了作曲家王梓的话“一辈子唱一首歌,一首歌唱一辈子”,题目定为《一辈子干一件事,一件事干一辈子》。2019年上映的纪录片叫《尺八·一声一世》,萧梅也总结学者都是“一生一事”。这些概括都适合李文如。他的确是一辈子干一件事而一件事干一辈子的人。大部分人被庸常琐事羁绊,一辈子像个金钟埋在土里,升不得空,发不得响。踏踏实实把一件事干一辈子的人,就能像猫玩老鼠似的,碾压所有竞争者,在一个领域尽显王者风范。李文如是在图书馆界拥有六十年经验并把这种经验用了六十年的人,或者说找到了与世界相处方式并做出非凡成就的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过去的60年间,不但在理论上建构了中国音乐学的整体框架,而且在音响、乐器、书谱收藏方面独树一帜。这些成就皆因图书馆有几位令人提神的人。大名鼎鼎的明清家具收藏家王世襄,他的太太、工文善画的袁荃猷,孔子世家的嫡系传人孔德墉,尽心事事、知无不为的文彦,甘于寂寞、服务周到的王秋萍、张家仙、华蔚芳、李久玲等……他们安静的无声无息,像只听得见翻书声的图书馆。50年代,他们白天泡在馆里,晚上也泡在馆里,简直当成自个的家。全心谋事,早去晚归,身累心甘,不思酬报。图书馆之所以声望日隆,就在于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是大人物,但参与了机构建设,与研究人员携手同心,开创局面,在近乎殉道者的职位上,完成了人生追求!他们的身份难以界定,说是音乐家也不是音乐家,说不是音乐家也是音乐家。王世襄编出《中国音乐书谱志》、李文如编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袁荃猷编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这些成果,仅是资料吗?“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学者站在前列,天下共知,图书馆员,藏在背后,无名无姓。但李文如不同,内有全力汇刊网罗之誉,外有修复古籍骇耳之声,鼎鼎大名,无人不晓。中国音乐研究所第一代人远非大家常谈论的几位学者,还有一批资质极高的资料员,每个人都参与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重大项目的资料汇集工作。对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建设、对教科书的成编、成书、成功,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资料为中心”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核心理念。如此说来,机构成功,一半在资料。像李文如这样的资料员,应该被学术史记录,而切勿以百工之技而轻视之。中国音乐研究所不仅有杨荫浏、李元庆等杰出学者和领导人,还有王世襄、孔德墉、李文如等堪称豪华的“绿叶”阵营。他们同样令人高山仰止。
回忆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做馆长的时光,我常在读者渐渐离去、馆员们三三俩俩下班之后,把一个个房间的开关关上。独坐角落,看着由一排排书架构成、承载着学科史的库府,享受被黄昏和书香沐浴的时光。那一刻,我觉得离老先生们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