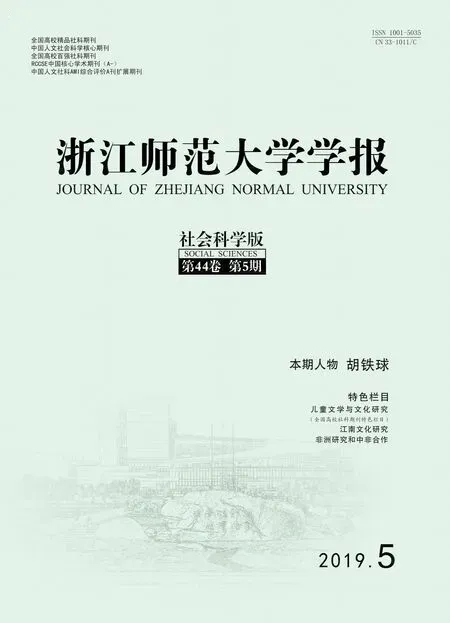论英国政府的南海政策(1920—1975)
——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为中心
2019-01-30刘玉山
刘玉山
(温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5)*
近代以来的南海问题涉及方有很多,如中国(包括台湾当局)、法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学界的研究也非常繁多,①但目前学界还没有英国曾经有意对南海进行主权声索的研究。事实上,英国近代以来多次来到南海进行踏查,这就为其提供了历史溯源上的“联系”,也正因此,英国虽不像上述国家或地区对南海主权提出明确而针锋相对的声索,但它又的确“皮里阳秋”地进行了暗战,成为南海涉事方中并不显眼的一方,这的确非常值得学界玩味,对于英国作为涉事方的关注,有助于拓展南海问题研究的宽度,进而增进对南海问题研究的深度。
一、20世纪20—30年代:牵制法国,力求战略平衡,服膺《九国公约》
相较于英国,法国对南海诸岛的殖民野心要强烈得多。1898年,法国殖民部在与法国驻海口领事馆的交流中得知了西沙群岛的存在,立刻意识到了重要性。同年,法国殖民部转交给印度支那总督一则信息,即一个新闻记者夏布里埃(Mr N.Chabrier)希望在西沙群岛为渔民提供一个商店,但时任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Paul Doumer)立刻泼了冷水,认为夏布里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过杜梅却认为:“鉴于西沙群岛的特殊地理位置,他建议建立一座灯塔,为接下来的主权声索提供依据。”[1]183-194
1909年5月4日,法国驻广州总领事博韦(Beauvais)致电法国外交部,他首先介绍了两广总督张人骏1907年收复东沙群岛及1909年李准将军收复西沙群岛概况,他充分肯定了西沙群岛的战略要冲地位,对于法国政府因为经费问题而搁浅修建灯塔感到非常遗憾。但博韦对于法国在西沙群岛的政策的建议仍然“首鼠两端”,首先他建议为了法国的利益,要阻止中国占据这些岛屿,法国政府可以做一些调查,找到一些“清楚的”“无可争辩的”有利于法国的证据。但话锋一转,博韦又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他用了“the game not be worth the candle”来形容,因为任何一桩介入都将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感情的新浪潮,这对法国的伤害要远大于占领西沙。[1]183-194时任法国驻华使馆的副官布瓦索纳(Boissonnas)甚至提出为了与中国政府就云南铁路获取更大补偿,对于西沙群岛“所有权”的放弃是个好的转圜。
不管怎么说,20世纪20年代之前,就连法国政府自己也承认无论政治和土著事务部、印度支那总督府或者海军司令部都没有任何关于西沙群岛的信息。[1]183-1941921年初,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咨询法国海军上尉雷米(Remy),法国是否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雷米作了否定的回答,这件事情被披露在1921年2月2日出版的《新欧洲》(EuropeNouvelle)报刊,连该报也发出感叹:“作出回答的法国政府官员没有意识到在西沙群岛的潜艇基地将有效地控制印度支那海岸线?”[1]183-194通过这一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西沙群岛并非印度支那领土,法国官员甚至连统属的意识都没有。所以当1921年中国南方军政府再次重申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法国政府就担心是否中国官员得知了这次对话抑或看了这篇报道。
1921年3月,印度支那总督莫里斯·隆(Maurice Long)在一封信中透露,如果要取代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这看起来是不过分的,即法国政府必须在西沙有军事或海军基地的存在。[1]1871927年11月26日,印度支那执行总督帕斯奎尔(Pasquier)给殖民部的电文中说道:“似乎法国从来没有对这些群岛进行过主权声索,从逻辑上来说,它们更像印度尼西亚群岛而不是印度支那半岛。”[1]1881928年11月17日印度支那执行总督罗宾(R.Robin)致电法国殖民部,透露他密切关注到中国海南领导人黄强已经计划开发西沙群岛,基于“持续高涨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作为法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历史文件和地理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主权声索。[1]1931929年2月18日,法国海军部给外交部的信函中透露,鉴于罗宾坚持基于历史文件视角进行主权声索,但目前海军部还没有找到相关文件,特别是1921年的时候,在“某种安全和非割让状态下”我们承认中国拥有主权。[1]180-196很显然,海军部意指雷米(Remy)上尉对答日本株式会社事宜。海军部给罗宾的建议是“等等看”。
1929年1月22日顺化的安南驻扎官乐福(Le Fol)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帕斯奎尔(Pasquier)的电文中透露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直到上个世纪西沙群岛似乎一直是个“无主地”,乐福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个叫做塔博德(Jean Louis Taberd)的法国传教士1837年所写的文章《交趾支那地理考释》(TheGeographyofCochinChina),里面记载了安南嘉隆皇帝曾在1816年在西沙升起了旗帜。中国宣称西沙主权是在1909年。但他又承认,西沙群岛是中国海南岛的自然地理延伸。[1]180-196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乐福没有继续顺着西沙是海南岛“自然延伸说”的思路说下去,因为乐福“严重”意识到,如果在西沙建立一个基地,则无异于在西贡和香港之间装上一双眼。[1]180-196
对西沙群岛这块“蛋糕”做了更详细的全盘考虑的要数帕斯奎尔。1930年4月30日帕斯奎尔给法国殖民部长的电文中提出了他的三点看法:首先,得益于具有官方背景的位于芽庄的克拉姆博士(Dr.Krempf),其领导的海洋研究所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的地质和海洋资源调查,得出了西沙群岛经济价值正在与日俱增的结论。其次,1920年一个日本公司没有经过允许去开采鸟粪,敲响了警钟。最后,同时也是帕斯奎尔最看重的一点:使印度支那成为这些岛屿霸主的需要。因为船只从西贡到香港,为了避免这些暗礁林立的水域,需要绕一个大弯。他为前总督保罗·杜梅做过实际的技术调查,只是因经费考虑没有在西沙建立灯塔而“耿耿于怀”。[1]167-168帕斯奎尔并且具有战略性的“深思熟悉”:“我们要权衡利弊,在更有利的环境下,当我们对中国必须放弃某种优势和利益时,西沙群岛将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1]167-168
帕斯奎尔也的确是在“认真”做这件事情,乐福(Le Fol)已经在顺化宫廷找到了四封信和四幅地图,这让帕斯奎尔很“自信”地认为:这将无可争辩地建立安南在1909年之前有效占据西沙群岛的充分证据链。[1]201并且他反复强调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它将是打赢与中国“外交战”的关键。但法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用了“难以确认”一词给帕斯奎尔为整理上述证据所做努力以当头棒击。[1]204
总体上来说,法国政府对西沙群岛的认识是个逐渐深入和逐渐由承认西沙不属于法国,转而寻求主权声索这样一个过程。究其原因,与20世纪30年代水上飞机(Hydravion)实现跨洲航行,国际客货运输获得巨大成功有关,西沙群岛作为水上飞机中转站的前景似乎也对帕斯奎尔本人有所触动。[2]1930年4月12日,法国“玛丽修斯号”进占南威岛,鸣炮竖旗。1933年4月7日至12日,法舰“亚斯特洛赛”和“亚拉亚特”号继续进占安波沙洲、太平岛、北子岛、南子岛、南钥岛、鸿庥岛、中业岛、杨信沙洲等其余八岛。7月25日,法国在其公报中宣布占领南海九岛,这就是“南海九小岛事件”。
19世纪末,在机缘巧合下,英国媒体大力呼吁英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立一座灯塔,为了航行安全。[1]192事实上,在西沙海域,1891年德国船“马里亚纳号(Mariana)”、1895年德国船“贝罗娜号(Bellona)”、1896年日本船“Imegu Maru”都触礁沉没,其中后两艘是运铜船,在英国公司上了保险。后来沉船上的铜被海南地方当局打捞,还因此与英国政府产生交涉,西沙群岛逐渐吸引了英国的注意。[1]192
1920年,英国外交部关注到了日本新闻媒体报道称西沙群岛已经被日本兼并,当时英国外交部建议中国应当鼓起勇气来捍卫其主权,在这些岩礁上建立灯塔。[3]时任中国海军总长萨镇冰提及会运送舰船去西沙群岛,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当时英国驻华代办克莱夫(R.H.Clive)建议英国外交部着手让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去建立灯塔。1922年,海关总税务司已经同意派遣海关税务船去西沙群岛做勘探调查,并且舰长被要求要被日本船只看见他们的行踪。[3]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是考虑中的海关税务船是“一艘破船”,且西沙群岛是“脱离常规节拍的”。[3]
英国驻北京总领事埃夫林(Aveling)在1931年6月2日致电驻华公使兰普森(Lampson)时仍然对近十年前是谁阻止了海关总税务司不要派遣舰船去西沙“耿耿于怀”,因为克莱夫与海关总税务司的谈话并没有上报外交部。[3]不过海关总税务司没有去的原因在1931年6月23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透露出来:“因为他们考虑建立灯塔会吸引船只靠近,导致更多沉船事故,而目前却给予了船只更宽阔的泊位。”[3]6月5日,兰普森致电埃夫林,让他通知上海总领事馆对海关总税务司做独立的调查,并且广州总领事馆“应当被告诉秘密地完成任何可能的信息”,[3]同时兰普森自己也将与中国海军总长陈绍宽取得联系。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赫尔伯特·菲利普斯(Herbert Phillips)着手进行西沙动态相关资料的分析,1932年5月19日他将当日《民国日报》一则有关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文章翻译后致电兰普森,该文认为,从地理上,这些岛屿位于中国领土水域;历史上看,清政府让水师提督李准率兵来到这些岛屿鸣枪、升旗,宣示了中国主权;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会议上,印度支那天文台和法国天文台的领导认可中国在这些岛屿所建立的天文台。文章尤其提到,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不可能在它宗主国的领土上建立宝塔和纪念碑。可以说这篇文章的说理有理有节。随后,菲利普斯将10月11日的《华北日报》、10月17日的《广州公报》、11月18日的《广州日报》、11月26日的《市民日报》有关广东政府开发西沙群岛的报道再次致电兰普森。
英国驻巴黎大使特里尔(Tyrrell)1931年6月10日也收到了兰普森的急电,特里尔为法国政府辩解,认为法国政府欲占据西沙群岛“没有任何的真实”,安南皇帝在1806或1815年就兼并了这些岛屿,法国政府注意到了1909年中国的国旗在Duncan岛升起来。特里尔公允地评价道:“我理解他们在那个时候进入,并没有遭到抗议。最近对这个群岛所采取的行动是因为海军部担心这个群岛有朝一日会被中国或其他国家建成水上飞机或潜艇基地。如果外交部法律顾问总结出安南国王兼并这些岛屿在19世纪早期是有效的,法国政府,很显然,会致电中国政府,声称他们拥有主权,这个事件是有争议的,仲裁将被建议。法国政府认为对这些岛屿的兼并没有问题产生,可英国外交部完全担心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第1款将完全禁止任何扩张行为。对于这件事,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的主权声索是否优于法方。一旦法方占优,则《九国公约》不适用,如果中国占优,则法国政府将完全接受,不可越雷池半步(make no further move)。”[3]
1932年8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致电英国驻法大使特里尔,用“深入调查”来形容外交部对中法西沙事件的看法有绝对把握。它认为:“中国当局近来已经发布了投标开发西沙海鸟粪邀请,法国政府致电中国驻法大使馆,表明法方的观点即法方拥有西沙主权,并且对岛屿的未来进行了勾画,法方的官方表达用的是友好的语言,它意图表明法国政府希冀用外交对话来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府并没有任何重视海鸟粪,他们不相信有足够的数量来证明其商业价值,但是对中国当局采取的行动是他们被迫的行为,为了先发制人保持法国的势头,法国官方强调友谊的属性,并无意做司法仲裁。”[4]
1932年9月26日,英国海军部致电外交部明确指出:“这个新月型的西沙群岛被证明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对海军有很大的重要性,既不是法国,也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中国应当对这个群岛拥有声索权。”[5]海军部认识到了西沙群岛的战略地位,更是认为西沙群岛属于中国,显示出英国军方对法国的不满与对中国领土主权利益的同情。英国外交部的态度则是遵循《九国公约》第一条“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质上则是牵制法国过于膨胀的殖民野心。在《九国公约》签订前一年,美、英、法、日四国在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在英国看来,两大公约对法国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但综观上世纪20—30年代,总体上英国政府对南海的关注并不多,即使是1933年发生“南海九小岛事件”,英国政府仅仅要求法国作出说明,并没有更深入地纠诘,更像是例行公事的外交程式,对法国的主权声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抵制(the French claim was neither recognized nor resisted by us),[6]直到二战期间西南沙群岛为日本非法侵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缘政治上的颉颃。英国1786年控制了槟城,1819年控制新加坡,1824年占领马六甲,一战前,英国已经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的缅甸也在19世纪80年代为英国所控制。与此同时,19世纪末,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成立“印度支那联邦”,这一时期英法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矛盾处于一个“衡平状态”。基于此,英国政府更希望用国际法来限制法国势力在南海的扩张,而不是介入进来与法国发生直接的矛盾冲突。其次,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英国深陷其中。1929—1931年,英国对外贸易额从8.39亿英镑减少到6.58亿至4.55亿。国际收支也出现巨额逆差,从1929年收入1.03亿英镑下降到1930年的0.28亿英镑,1931年则亏空1.04亿英镑。[7]因此,英国自顾不暇,无意与法国南海争锋。[8]最后,英国虽然近代对南海进行了多次踏查,但与法国相比,殖民意愿比较模糊,法国则视西南沙群岛为其“禁脔”,两国对南海的欲望值是不太一样的。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则不同,南北越分治,法国势力逐步从印度支那退出,此时,英国政府提出“主权声索”已然没有障碍,只是“世易则时移”,英国面对的南海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二、20世纪50年代:反复论证,终未公开提出主权声索
与二战前英国略显暧昧的态度不同,50年代英国政府内部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开始增多,表现也积极得多。英国外交部认为,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诉求最早的是英国,1864年“来福门号(Rifleman)”曾到达这里,1877年英国的国旗在这里升起。[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范围其实在“外交部档案”中用的是“Spratley and Amboina Cay”,“Spratley”就是南沙最大的岛屿之一南威岛(即斯巴特列岛),“Amboina Cay”是离南威岛并不太远的一个沙洲,叫安波沙洲。在英方看来,南沙的许多“岛屿”都是暗礁和浅滩,一些是在潮汐状态下被覆盖,不适宜居住,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安排和占领。[6]一言以蔽之,英方眼中的南沙群岛就是南威岛和安波沙洲,而并非整个南沙群岛所覆盖的所有区域,我们一般用“Spratly”指代整个南沙群岛,而英方所认为的南沙就是南威岛及安波沙洲。
事实上,英国近代以来对南海的踏查始于1802年英舰“马克雷司号”对隐遁暗沙进行的测量,其他英舰1826、1844、1851、1862年都曾窜入南海进行过调查。[9]但最显眼的要数“来福门号”,该舰在1864、1865、1866、1867和1868年连续闯入南沙群岛一些岛礁活动,正因为有着如此“显赫”的经历,英国外交部不由自主地将1864年定为英国南海主权声索的起始年。
1956年3月1日,一个叫克洛马(Cloma)的菲律宾海事学校教师带领他的学生40人来到南沙群岛,给这些岛屿改名、树立占领牌。5月11日,正式宣布占有,克洛马自任“总统”。5月15日,克洛马发表《告世界宣言》,宣告占领南沙群岛33个岛礁,命名为“自由地”,这就是所谓的“克洛马事件”。5月27日,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才注意到此一事件,其反应速度明显偏慢。在给外交部东南亚司的电文中,驻马尼拉大使馆提出以下四点疑问:
1.是否斯巴特列岛现在还为克洛马一伙人占据?
2.其他被占领岛屿的位置和名称?
3.“自由地”的地理范围是菲律宾政府还是系个人行为?
4.菲律宾政府是否声索主权还是这个声索仅仅系个人行为?[6]
应该说大使馆的疑问都问到了关键之处,但英国外交部对“克洛马事件”并不重视,对马尼拉大使馆的相关讯息和疑问也并未及时作出回应。5月30日,外交部官员罗杰(Lodge)致电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提出英国应如何阻止这些岛屿(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落入敌对者之手的对策。罗杰认为仅仅提出政治上的主权诉求而没有实际的行动支持,只会是空虚和无用的行为。因为战略上的原因,英国对新加坡牢牢掌握,如果允许它自由行是,则不知其可?[6]可能是罗杰觉得电文写得还不够具体和直接,在电文的底端,他又附加了一些语言,这就将他的观点彻底阐述清楚。罗杰说:“我们可以叫北婆罗洲(按:时婆罗洲北部的沙巴和沙捞越为英国殖民地)派遣一些警察,带着便携式的电台,到达每一个岛进行看管,这些警察闲着无事的时候可以钓鱼,并且轮流来驻守,一旦遇到麻烦,电台则可以作为一个破坏者存在。”[6]
联想到北婆罗洲应发挥作用的还大有人在,1956年6月1日,驻在新加坡的英国东南亚事务专员致电英国外交部研究部指出,1951年英国“丹皮尔号”到达南沙群岛时,发现岛上有一些渔民来自婆罗洲,这显示出南沙群岛与英属婆罗洲之间有着存在已久的联系,为英国的主权诉求提供了支撑。[6]英国外交部官员西蒙(Symon)立刻就泼了冷水:“我不认为婆罗洲的渔民到南沙群岛会有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证据到国际法庭,那么中国也可以给出类似的证据即中国渔民到过南沙群岛。”[6]但英国东南亚事务专员似乎对此抱有热情,随即致电英国殖民部,告知他已找到“泛马来亚渔业主任”,如果外交部研究部认为婆罗洲渔民与英国主权声索有关系,他建议找到这个渔业主任“顺藤摸瓜”。[6]
1956年6月4日,英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致电外交部,在谈到南沙涉事国时,大使馆认为虽然《旧金山和约》只说日本放弃西沙和南沙群岛,《开罗宣言》也仅提及台湾和满洲作为领土归还给中国。但南沙群岛(按:这里的措辞是Spratly,而非Spratley)却被认为是日本所窃取的领土之一。该大使还否定了越南的主权声索,原因是:“法国宣称西沙群岛是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但没有证据延伸到南沙群岛。”谈到英国政府的南沙立场时提出应用“法律方式”来评估南沙的战略意义。[6]
1956年8月8日,英国外交部在拖延了两个月后就6月4日菲大使馆谈论之事由远东司进行了系统的回答,“我们对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的主权声索是如此微弱,以致于在国际法院是没有胜算的,一些岛屿仅潮汐时露出水面,是不适合居住的,因此是不能够被占领的。这些岛屿从战略上说,对我们也没有可视的战略价值,我们所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使它成为我们的潜在敌人,在西方控制南海的状态下,它也不应该形成严重的战略威胁,外交部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商量,但上述原则不会发生改变。”[6]
新加坡英国东南亚事务专员1956年6月5日致电外交部,谈到婆罗洲壳牌公司(Shell Company of Borneo)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来开发海床石油,该公司要求英国远东基地总司令派遣一些地质学家去斯巴特列岛。该总司令建议派遣“皇家丹皮尔号(Dampier)”考察船前往,该司令并且要求东南亚事务专员指导“皇家丹皮尔号”的指挥官是否升起英国的国旗并且占据这个岛屿。
在1956年6月8日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一份署名“Spratley Island”的“FC1082∕C”文档,该文档针对近期中国(包括台湾当局)、越南、菲律宾等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诉求,认为:
英国政府是否应该重新评估自身的主权诉求,海军和殖民部认为,斯巴特列岛对英国政府来说没有战略和经济价值。如果被认为是一个有战略或经济价值的评估,那么(中国)台湾当局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占领了该岛。当法国当局1930年宣称对斯巴特列岛的吞并时,我们首次表达了我们的主权诉求。后来,我们并没有承认法国的诉求,我们并没有施加我们的压力,缘于我们在1932年接受了大法官的建议即“在常设国际法院仲裁拥有一个非常暗淡的胜利前景”,由于我们的诉求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至今20多年时间,我们没有施加我们的主权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其他涉事国家的利益展示,看起来是不合适的,如“皇家丹皮尔号”在斯巴特列岛升旗或进行占领。英国的船只运送地质学家来斯巴特列岛,为了一个英国公司开采海床的目的,这看上去也不是合适时机。我们都知道,斯巴特列岛在菲律宾或(中国)台湾当局占领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6]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档有很多人签字,由于较为潦草和模糊,尚无法辨识,但其中一个签字很长的有如下笔迹:“派遣船只运送地质学家去一个争议地区是不合适的。”[6]显而易见,英国政府内部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上世纪30年代英国对于法国侵占“南海九小岛”事件表现暧昧,随着时间的推移,20多年过去了,英方认识到其在南海的影响力更加式微。再从现实的角度看,英方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公司而介入本就纷扰的南海“泥淖”。吊诡的是,这份文档的页边缘却被用钢笔打上了大大的“×”号,这至少表明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份文档展示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或者说这未必代表官方观点,但从英国政府的后续动作来看,又完全按照这份文档所体现的精神在执行。
1956年6月12日,英国外交部就6月5日驻新加坡的英国东南亚事务专员所议之事有了回电,回电内容杂糅了6月8日的外交部文档“FC1082∕C”与文档批示内容。回电称:我们对斯巴特列岛的主权声索从来没有被放弃,但也从未施加压力,它被认为是乏力的,由于缺乏有效的主权实施,在国际法院也不可能赢。我们不希望卷入中国(包括台湾当局)、菲律宾和越南的南沙争端,“皇家丹皮尔号”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升旗或做占领状。有消息称台湾当局已经到达这个岛屿,我们的船只输送地质学家去是不明智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6]最终这一计划被取消。
6月6日,英国驻南越大使馆就中国大陆关于西南沙问题的声明发表声明,而南越也发表声明,信誓旦旦认为其主权源于1952年(按:应为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并致电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官员西蒙(Symon)作出这样的批示:“日本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中放弃南沙群岛,但并没有任何接收方(but no one received them)。”[6]6月9日,英国驻南越大使馆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再次对南越当局的南沙主权声索提出异议,认为:尽管南越一直以法国的继承者自居,但法国政府认为这些岛屿(南沙群岛)在1933年特别地被法国进行了主权声索,但他们并不构成法属印度支那的拥有。从法律视角看,这些岛屿“属于”法国。[6]很明显,英国外交人员认可的法方立场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印度支那政府行为分离说”,在法方看来,隶属于法国的印度支那当局20世纪30年代对南沙群岛的占领行为是法国政府的行为,与脱离法国独立的越南(不管是北越还是南越)的行为是两回事,越南不能混淆法律概念,将法国政府的行为“据为己有”,二者政府行为效力不同。当然,此时的法国政府已断了南海念想,但对南越当局的“混淆视听”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没有发现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南沙群岛问题的直接谈话内容,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丹尼斯·艾伦(Denis Allen)在1956年6月15日外交部的一份电文中作出的批示引用了首相的观点:“首相简短的回答如下:南沙群岛岛礁底下是否有石油还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贸然)提出我们的主权声索,则(前景)非常暗淡。”[6]在首相定调的基础上,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罗(Crowe)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一地区发现了石油,我们就很希望进行主权声索,我们就应该搜集很多必要的证据来卷入这场纠纷。”[6]英国驻北京大使将195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邵循正)、《奇怪的“发现”》(崔奇)致电英国外交部,8月16日,英国外交部在回电中称:“任何对争议岛屿的主权声索,将取决于持续占领和行政管理,英国对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的主权声索严重式微就是因为没有持续占领它们。”[6]同时,英国外交部认为,这两篇文章为中国的主权声索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6]
到了1957年,英国海军部经过深入研究后确认:“我们在这些岛屿没有利益,所有涉事的主权声索方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A storm in a Teacup)。”[10]“茶杯里的风暴”典故源自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名言,某次,他听说欧洲袖珍国圣马力诺发生了政治动乱,就用“茶杯里的风暴”来评论,比喻那里的动乱对欧洲局势无关痛痒。同年4月11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在给驻北京大使的电文中还对海军部对南海不再感兴趣而“耿耿于怀”。[10]可见南海的经济与战略价值并不能“吸引”海军部的目光,海军部坚持作壁上观的政策,认为南海问题与己无关。
至此,英国政府内部对于他们存在“可能性”主权声索的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的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即限于19世纪60年代的“发现”已经年代久远,且并没有持续地施加影响,因此英国的主权声索是微弱的。更由于南海并没有发现石油,又有诸多涉事方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并不愿“趟这潭浑水”。总体来说,外交部的积极性要更高一些,不断对南沙群岛问题提出论证,但海军部的“消极”态度又会影响到外交部的决策,在没有海军的实际支持下,外交部所做出的一系列“理论论证”不过是竹篮打水而已。同时,通观上世纪50年代“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政府似对中国(包括台湾当局)的南沙群岛主权声索并没有持太多异议,相反,对菲律宾和越南,尤其是越南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学界应该注意的现象。为什么英国政府对越南的行为如此“反感”?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中方无论是外交声明还是报刊舆论文章,对南海主权的论证鞭辟入里、有理有据,英国外交部也折服,这从其内部人员的交流中不止一次流露出来。其次,南越当局以所谓法国继承者自居,既对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又对南沙群岛志在必得,英国政府对这种得陇望蜀的行为自然是“反感”的。
三、20世纪60—70年代:“主权声索”彻底死心,变身旁观者
1971年11月2日,针对南越政府的申明,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是:英国政府从不接受南越政府关于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的任何观点,英国政府保留对上述二岛主权声索的权利。[11]同年11月24日,英国外交部东南亚司斯马特(Smart)与南越驻英国大使通电话时称:“英国政府从来不承认1877年以来各个国家的主权声索。”[11]
对南海是否进行主权声索,在英国外交部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很多官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又纷纭歧异,迄无定论,主要表现为三派即“两个极端,一个中间”:一派是较为积极的“主权声索派”,如远东司官员欧威廉(William Geoffrey Ehrman)认为,鉴于南海区域存在石油储量的可能性,英国政府应当持续增加对南海的主权声索。[11]另一派则持消极的论点(实际上又是最客观的)即“放弃声索派”,如皮特·布莱克(Peter Blaker)认为英国的主权声索实质上已经消失,进行声索会导致与中国的关系恶化。[11]东南亚司斯奎尔(Squire)的观点与皮特·布莱克类似。[12]远东司戴维斯(Davies)认为在中越西沙争端中,英方应避免发表评论,截止目前为止是成功的。[12]第三派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观点略显模糊,比如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些岛屿,而是赢得一些利益。[11]外交部研究部法律顾问丹扎女士(Denza)也就南海形势提出“两个事实,五种选择”,“两个事实”是:(1)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地对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提出主权诉求;(2)针对中国政府和南越的声明,英国政府并没有特别的表示。“五种选择”是:(1)正式对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提出主权诉求;(2)保留对上述二岛主权诉求的权利;(3)保留对整个南沙群岛(而不仅仅是上述二岛)主权诉求的权利;(4)什么都不做,以致于在无所作为中消磨掉我们的诉求;(5)放弃我们的诉求。[11]
英国国防和海外政策委员会则态度非常明确,即英国的主权声索已经消散。司法部长也认为英国再进行主权声索已经没有实质意义。[12]
最终,1974年1月,英国国务院提出让英国国防和海外政策委员会接受外交部法律顾问的建议,系统拟出英国政府对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的具体意见。[12]随后,英国国防和海外政策委员会从法律和政治的视角草拟了英国政府对待南沙群岛的备忘录,具体如下:
法律思考:
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得到了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似乎是有一定证据的,但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则主权声索减弱,因为没有有效行使管辖或开发上述该岛礁资源。
1932年政府法律官员认为,这种主权声索在国际常设法院面前有极其微弱的胜算。当1930年代法国声称占据这些岛屿时我们没有反抗,就已经失掉了胜算。1939年日本占据了这些岛屿,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会”中,它是建立在这些岛屿属于法国的假设下的。1971年针对南越声明南沙主权,我们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我们仍旧占有南沙群岛主权。
具有强大法律声索的国家是中国和法国,我们私下里认为法国的主权声索已经在消逝。
政治考虑:
下面这几点因素是我们正式对南沙进行主权声索的梗概:
1.它将给英国增加新的责任(包括一个潜在的防卫信用),而不是我们的承诺即减少在东亚地区的存在。
2.在很多年的沉默后去公开进行一个很微弱的声索,将被其他的声索者尤其是中国视为挑衅。
3.很可能中国将继续追索南沙,并且在将来某个时间占领它们,我们不反对中国的占领。因此,我们应当认为英国的主权声索已经消散。[12]
与上世纪50年代对自身南沙群岛“主权声索”类似,都是认为其自身的“声索”是非常微弱的,此时的措辞更是用了“消散”来形容。与50年代稍有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主权声索则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即“不反对”。与此同时,英国的司法部长也同意外交部法律顾问所做出的“在国际法上英国没有胜算”这样的论断。[12]但是英国外交部却“心有不甘”,做了“主权声索”预案,预案回顾了1864年英国皇家海军“来福门”号即在斯巴特列岛和安波沙洲出现。1877年英国政府颁发许可证,并且一个采集海鸟粪的美国公民在这些岛礁上升起了英国国旗。这种权利1889年被赋予中央婆罗洲公司(The Central Borneo Company),直到1932年这些岛礁还被英国殖民署列为殖民地。同时,预案一再强调两个事实,即涉事方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声索证明其是有争议的,英国与南沙有“历史的联系(historical connection)”,但这种“联系”已经很多年没有被维护了。[12]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特勋爵(Lord Goronwy Roberts)提出英国政府是否需要针对西沙提出政府声明,外交部东南亚司则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发表声明是为了获得利益,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会因英国的“放弃”而有一丝补偿。[12]
事实上,美国政府在197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认为英国1864年“来福门”号造访南沙群岛是“西方有记录的第一次”,但也实事求是地认为:“英国政府并没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来展示它的主权。”[13]连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都不认可英国在南沙群岛有事实上的“主权存在”,这也是英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介入南沙争端进而进行主权声索的原因。至此,英国政府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彻底死心,包括中越西沙海战等重要事件,英国外交部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政策上的分析和观察,“主权声索”却不再被提及以至今天。
结 论
纵观20世纪20到70年代英国政府的南海政策,由最初不愿直面咄咄逼人的法国到50—60年代开始反复论证,但意见较为不一致,虽也有如新加坡英国东南亚事务专员一样对声索抱有希望和热情者,但总体的观点还是认为年代久远,声索已成泡影,所以终未公开提出主权声索。70年代的情况与50—60年代类似,各种声音都存在,但英国政府综合权衡后还是“识时务”地彻底放弃了主权声索,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所谓主权证据难以自圆其说,自己都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政府较为务实的一面。
注释:
①褚静涛《克洛马事件与台湾当局的应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栗广《1950s:中国台湾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基于台湾、美国档案的解读》(《南海学刊》2016年第1期)、黄俊凌《20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张明亮《南中国海争端与中菲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郭渊《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刘洲《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南海诸岛研究》(武汉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何维保《再论〈旧金山对日和约〉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规定及影响》(《美国研究》2014年第4期)、王潞《国际局势下的“九小岛事件”》(《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