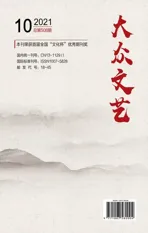《金陵十三钗》的女性意识辨析
2019-01-28江南大学人文学院214122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女性意识”是严歌苓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论者在论述小说《金陵十三钗》时,多认为其展现了“女性的伟力”,表达了对历史、人性的深度思考等。然而笔者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时却感到其背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涵,不禁怀疑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否确如论者所言:是女性的“生命宣言”?
学者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指出:所谓叙事伦理,就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并通过这种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以此来营构不以社会道德观念为准则的具体的伦理诉求1。叙事伦理的教化在于抱慰、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那么其必定倾听女性的生命呢喃。然而《金陵十三钗》中女性的生命感觉和伦理诉求是被抑遏甚至异化的。
一、女性身体经验的斥离
女性意识又称女性主体意识,其首先是指“女性对自身有明确的性别自认,即女性的自觉”。女性主体意识包含“人”和“女人”两种价值取向。而“人”的存在,首先是身体的存在。现代之后,伦理主体发现或者说重新恢复了自己的身体,如何认识和处置自己的身体由此成为一个伦理问题。生命感觉以自然的身体为载体,因此叙事伦理能够发现和认同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性别认同是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基础的基础”,就女性而言,对自己身体的认同是其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赋权的基础。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了书写女性身体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女性应该用自己的肉体来表达思想。小说《金陵十三钗》可以说是一场女性身体的狂欢,小说开篇就写了女性特有的生理体验。“孟书娟一下子坐起来;她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她的初潮来了”,这是“我”十三岁的姨妈孟书娟的初潮。那么书娟如何看待“初潮”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生理现象呢?“书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秘密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色液体……”书娟对突然到来的人生“转折”事件是充满好奇和嫌恶的,少女对初潮的迷惘好奇可以理解,可为何会对一件一无所知的事物感到嫌恶呢?不仅如此,十三岁的孟书娟认为这雌性经血是一种极致的耻辱,因为“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在书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灵”与“肉”的分离,她不仅不了解自己的身体,身体与意识之间甚至形成一种对峙关系:书娟厌恶且仇视自己的身体。
然而有意思的是,妓女们的身体却对她形成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以玉墨为首的十三个妓女进入教堂后,书娟等女学生多次偷窥她们,书娟对这群妓女在嫌恶之余有着更为复杂的微妙情愫。书娟在借着地下室仓库的透气孔偷窥玉墨跳舞时,看见玉墨把身体“扭成八段,扭成虫”,不禁对着透气孔大骂:“骚婊子!不要脸!”可同时书娟又看得着了迷:“书娟发现自己两腿盘了个莲坐,屁股搁在潮湿冰冷的石板地面上,身子向右边大腿靠,”她顾不得地面的潮湿,已经完全沉醉于玉墨美妙的身体和舞姿中了。在书娟眼中玉墨“一贯貌似淑女,含蓄大方且知书达理,只在这样的刹那放出耀眼的光芒”,因此书娟对玉墨感到羞耻、厌恶的同时内心深处还有几分嫉妒甚至向往。在妓女这一群体的身上,特别是在“挂头牌”的赵玉墨身上,少女书娟似乎找到了对自己身体认知中缺失的那一部分。在嫉妒与厌恶的矛盾情绪中体现出来的是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对自己身体的疏离以及对性别身份的厌恶。身体是自我价值的承载者,也是自我观照外界的起点。然而,书娟是缺乏对女性身体的认知的,或者说她并不认同自己的性别身份,笔者认为这是解构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起点。这样看来,作家的确在小说中书写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性别经验,但是在这种书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性别自认的缺失。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捐弃
西方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发展了波伏娃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以区分“自然性别”。女性的自然性别是先天的,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建构起来的,它是带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概念。女性在自觉认同自己的身体后,还必须独立地从女性立场出发来审视自我价值和外部世界,对其进行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体认。
如果说书娟是不认同自己身体的女性,那么以自己的身体为傲并以此“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中的妓女们是否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代表呢?恐怕仍然是有名无实。小说中,书娟骂玉墨是“骚婊子,不要脸”后,玉墨进行了反击:“玉墨一边搂着少校蠕动,一边不断朝透气孔转过脸,她知道书娟还没走,”玉墨借此向书娟示威:“在你的骂声中,我赵玉墨又征服了一具灵肉。”少校身上的伤被玉墨挤得剧痛,但也痛得心甘情愿。“她的胯骨撞到戴少校身上时,少校给她撞得忘了老家,撞出一个老八丘的笑来”,玉墨知道骂她的女孩仍然在看她,于是“她就浪给她看,她的浪是有人买账的,天下男人都买账……”玉墨由此获得了报复的快感和满足感。然而在这场女性之间的交锋中,玉墨的胜利是以征服戴少校这个男性为标志的。此时玉墨和书娟都以是否得到男性的认可来评判输赢,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可无形中变成了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同样地,玉墨等妓女之所以能勾引少校甚至神甫这些男性,让男人为之神魂颠倒,看似是女性在征服男性,实际上是男性变相地在给女性赋权,而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
这种虚构的女性“胜利”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在男权社会统治下被异化的女性。在传统男权主义社会中,女性被定义为第二性,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不具有自主性的附属品,男性根据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来塑造和规范女性。在这种男性权威和女性卑微对立关系的诱导与规训下,女性会不自觉地接受这种异化的性别想象,认同自身作为“他者”的地位与形象,采用男性的立场、标准和视角来观照自己。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书娟看到窑姐在阿顾怀里敞开前襟时脸上一阵臊热,想到她们“靠两腿间那绝密部位谋生”就要脸红地“啊哟”一声……因为男性对女性的理想就是:“娼妓其内淑女其表,”而妓女失了淑女的外表和贞洁,因此书娟对窑姐们的羞耻、厌恶其实是来自于男性的理想取向;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书娟认为男人的堕落全是因为女人的勾引,对这些寄生在男人弱点上的女人有火一样的仇恨:“她们连英雄少校也不放过,也去开发他的弱点”,因为在男性权力话语中女性形象是被歪曲、贬低的,其把一切罪恶都归诸于女性,认为女人的性之罪是导致男性精神堕落的始作俑者。“话语即权力”,福柯认为权力通过话语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温和而隐秘地完成对个体精神的规训2。男性掌握着权力,也就控制着绝对的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女性不仅是失语者,甚至可能无意识地成为男性的代言人,所以被男性思维同化的书娟是有足够的动力去污蔑和仇恨妓女的。不管是玉墨还是书娟,她们身上并不具备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的话语权力。
三、男权伦理道德的规训
学者谢有顺认为,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和生命感觉的多维复杂性,它不在善恶的伦理道德中挣扎,而是以生命的宽广与仁慈来倾听个体的灵魂絮语3。也就是说,叙事伦理依据的道德与人类社会道德是不一致的,其关注的是作为普遍的“人”的生命感觉,具有一种“无差别善意”的宽广胸怀,强调生命感觉的“自然”而非“应然”。
以玉墨为首的十三个妓女挺身而出,代替了女学生们慷慨赴死。《金陵十三钗》因此被标榜为女性自强、妓女救国的故事,常被认为其歌颂了妓女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然而这些赞美是妓女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试想妓女为何需要牺牲才能为自己换来尊严呢?就连最接近神性的英格曼神甫也产生了让妓女代替学生去送死的念头,因为妓女“是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玉墨更是毫不留情地自轻自贱:“我们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而她们要拯救的却是清白的处女,而且是学生,是孩子。在这种干净与肮脏、纯洁与风骚的对比中,妓女的牺牲似乎显得越来越具有其合理性。不仅如此,玉墨是主动并且自愿提出要代替女学生去送死的,这样就进一步放大了妓女的崇高行为。如此,妓女们的赴死就显得悲壮而且绚烂:“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妓女赴死这一行为虽然悲壮,但同时也体现了道德观念的“应然”,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是与叙事伦理中的平等、仁慈、尊严等“自然”内涵相悖的。
进一步说,这种“应然”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来源于男权主义社会。人们对妓女的价值、行为等早已有所预设,而设想的依据就是男性视角中坚韧、自强、崇高的女性理想形象,她们能够自觉地消解所有凌辱和不幸,而女性显然是不自觉地接受和消解了这些苦难。
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女性是缺乏自觉的性别自认以及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在女性“生命宣言”的背后运作的仍然是男权话语机制和伦理道德体系。书娟是排斥自己身体、被男权社会异化的女性,而靠牺牲生命换取尊严的玉墨则是男权社会中心甘情愿的殉道者,她们身上都没有呈现出伸展和抱慰女性生命感觉的叙事伦理形态,也就不具有真正的女性意识,这也反映出现代的女性意识是以一种更具有遮蔽性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女性的处境也许就是这样:像严歌苓这样一位自由又自主的大家,却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男性压制下的他者地位世界中。要彻底走出男权社会的藩篱,对女作家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注释: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谢有顺.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