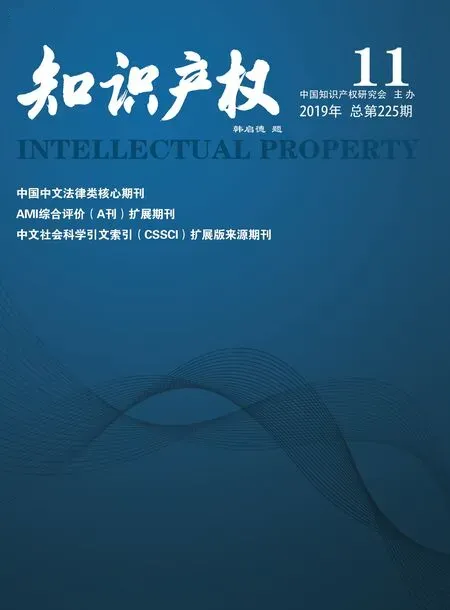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伦理探究
2019-01-27曹新明杨绪东
曹新明 杨绪东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自动生成作品的能力逐渐增强,对以自然人作为创作者为伦理基础而构建的著作权制度构成挑战,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著作权保护价值的伦理冲突。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依靠自己的大脑创作的作品在表达形式上并无差异,两者的功能、用途基本一致。基于著作权制度是以自然人为本旨而构建的伦理规则体系,实难接纳人工智能作为作者而给予保护,否则会造成整个制度伦理及功用的倾覆。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质上属于人类的投资行为,将其归属于以激励投资者为原则的著作权制度,在法律伦理上是十分契合的。而且,从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而言,将著作权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投资者更为恰当,这不仅可以保持既有制度伦理基础的稳固,而且可以激励人工智能生成产业的投资。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与应用,使其效能越来越强势,导致在众多领域对人类产生了挑战。因此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①《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载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31日。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挑战,在著作权法领域,现今主要表现在作品的生成能力上,并且其生成速度差不多已经超越了人类作者。②日本人工智能创作的《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等四部作品,于日本第三届“星新一奖”赛事中通过初审,毫无破绽。但是,基于当今著作权伦理基础可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只能是自然人创作的作品,进而限制了人工智能成为作者的可能性。这种以自然人为创作者的伦理规则,使得既有著作权立法范式不可能将人工智能作为其生成物的作者给予有效保护③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 民初23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该案为我国首例AI 生成内容著作权案。,由此可能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实施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著作权法律规范,妥当地处理好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保护所遇到的伦理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借助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适用著作权或者邻接权等规则暗合的体系性解释。然而,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模糊了传统法律社会中人与物的界限,呈现出非“人”亦非“物”的新情势④虽然人工智能不是“人”,但也不是“物”。不能因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不是自然人,就否定其可版权性。引自易继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 期,第137-147 页。,使得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如果建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规则,就需要正本清源,严格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再者,因为“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⑤[美]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52 页。,所以对新技术引发的重大变革作出新的规制,当然应当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本原则。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汉斯教授曾指明,此研究的最终功用确是为寻求一种可达致“技术手段与人类需求及目的”之间的平衡。⑥[德]汉斯·约纳斯著:《技术、医学与伦理学》,张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 页。
一、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现实性
众所周知,人类进行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开发的最元初动力就是弥补自然人肌能、体能、技能、艺能等综合能力的欠缺,以提升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最终达到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目的。人类进行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技术、产品或工具设备等,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包括人工智能也不例外。人们研究人工智能的本因就是将人类从简单、机械、重复、繁杂、琐碎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让人类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仍然是辅助人劳动的工具,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然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不仅超越人的体能,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人的智能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蓝机器人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初显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智能超越了人类;2016年的ALphaGo 战胜人类围棋超一流棋手李世石、2017年Master 打败围棋棋手柯洁以及 2018年初围棋机器人以 60:0 的不败战绩碾压人类围棋棋手,已经肯定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超越人类的智力。,对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主宰者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尊严。⑧“劳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参见百度词条:劳动,载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976265?fr=aladdin#7_5,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7日。面对已然来临的智能社会,人们正陷入一个伦理困境:人工智能以其卓越的体能和智能为人类服务的同时,有可能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上的“主宰者”,甚至主宰人类。然而,不管未来的人工智能是否真的能够与人类称兄道弟,平起平坐,或者主宰人类,至少这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会变成现实。⑨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理由确认AI 机器人不可能超越人类:1.哥德尔不完备定律;2.钱德拉塞卡极限;3.思维的量子本源: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其结论是,人类的量子思维模式,AI 是不可能做到的;4.生物细胞生长原理。因此,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至少在未来300年内不可能超越超越人类。为什么是 300年?只有估计,没有论证。人工智能的先驱马文明斯基说过:情感、直觉和情绪是人类独有的,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学会。他在人与AI 之间画了一条线:机器的事由机器做,人类的事由人类做。尽管如此,为了防患于未然,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战略”⑩我国已于2017年7月20日正式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目前已发布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丹麦数字技术增长战略》《欧盟人工智能通讯》《法国国家AI 计划》《印度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日本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新加坡人工智能战略》《英国人工智能行业新政》,美国正在加紧制定《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美国人工智能未来法案》等。实施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伦理规范⑪2016年日本制定人工智能研究伦理指针草案,提出合理利用人工智能。为了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仍然具有伦理和社会意识,2017年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宣布了三项新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2018年英国上议院发布人工智能报告,指出在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必须把伦理道德置于核心位置,以确保这项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欧盟委员会2019年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以提升人们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信任。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阶段,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就专门提出有关我国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提案。,以确保人工智能永远处于辅助人类工具地位的前提下,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挑战。现实已经肯定人工智能能够根据操作指令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也发布报告指明,未来15年90%的新闻稿件将由人工智能完成,大量的音乐、文学及摄影作品也将由人工智能创作。⑫参见杨延超:《机器人来了,法律准备好了吗?》,载《检察时报》2016年6月17日第005 版。
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不仅正在逐步降低自然人的主流劳动身份,同时也在加速塑造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正是因为自然人劳动者身份才确立了对其通过劳动而创造的财产享有财产权⑬参见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 期,第122-133 页。,罗马法就是赋予劳动者以财产权利之制度建构的肇始者。著作权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然人对其创作作品的权利保护,开创了智力劳动者的产权身份。基于这种格局,自然人所从事的劳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通常意义下,智力劳动只能由人类即自然人自己完成或者是某种工具、机器、设备等在人类即自然人的支配、主导或指示下完成。体力劳动既可以由人类自己进行,也可以由人类即自然人支配、主导或指示某种工具、机器或设备进行。然而,发展到今天,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在人类(即自然人)的支配、主导或指示下完成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能够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算法、软件、模块、数据等独立进行智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例如,具有文学艺术表达生成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具有按照人类即自然人事先发出的指令或者事先设计好的功能,独立生成诗歌、小说、新闻稿件、拍摄照片、设计图片、语言会话等。虽然当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场景设计、指令安置、功能设计可以生成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并且在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两个方面并不必然比人类差。但是,因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规范或者著作权法还没有给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以民事主体资格,所以,从法律上讲,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如果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条件,⑭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可知,一种表达形式能否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形式条件,包括该种表达形式蕴含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属于《著作权法》第3 条所规定的作品类型;二是实质条件,包括独创性、可复制性、合法性,不属于排除对象;三是本质条件,即该种表达形式的创作者是自然人,而不是动物、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应当特别注意:这三项条件就是某种表达形式是否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可以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该作品的作者和著作权人都不是生成该作品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只能是自然人。⑮[美]吴军著:《智能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14-315 页。事实上,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生成物——的生成行为实现了由信息到知识再到表达的人类路径的超越,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人机协作。
2016年3月,日本“人工智能(AI)小说创作”的研究人员在东京发布会上首次介绍了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创作的四篇小说。⑯宗仁:《不敢想象!日本AI 人工智能系统能写出完整小说》,载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603/Tz4N9YkA6KHggIwK.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7日。概言之,该四篇小说的创作中,依然存在人的智力参与。这种人机协作模式即可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自然人创作的助手,更进一步地表明人工智能在该创作模式下仍不能完全脱离于人类,只是增强了自然人的创作能力,代替人类完成了创作过程中繁琐的创作要素编排任务。然而,事实上人机协作创作模式依然对既有创作范式作出了许多改变。质言之,在文本生成过程中,人工智能实现了思想与表达的分离,自然人只是向人工智能系统贡献了的创作思路、创作思想或素材,人工智能算法则是独立地对自然人提供的创作思路、思想或素材进行了具象化表达。然而,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的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⑰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 页。,在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的生成行为则是在自然人指导下运行算法的一种机械过程,打破了传统创作思想与表达的一元主体体系,使人工智能算法本身逐渐有了独立的创作地位。
随着技术的迭代,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实际上就是算法自主的结果,其中包括设计算法、内置数据、功能安排的人类智慧。2017年5月,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创作”(实际上应当是生成)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⑱参见百度百科:《阳光失了玻璃窗》,载https://baike.baidu.co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7日。该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创作”诗集的事实肯定了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创作”能力。严格地讲,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所进行的“创作”,就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独立于自然人完成的行为。基于此,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不再需要自然人给予其指导,更不需要人类经验素材上的训练。至此,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实现了由人机协作模式向算法自主模式的跨越,自然人不再能够参与到具体表达形式的生成过程,因此,自然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关系发生变化——人类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关系弱化到单纯地依靠投资行为来维持。
二、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伦理挑战
当今时代,除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具有“创作”诗集的能力,其他种类的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生成能力。基于这种客观现实,人们已经开始高度关注是否应当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视为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⑲参见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 期,第3-8 页;梁志文:《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 期,第156-165 页;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 期,第128-136 页;等等。单纯就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成的结果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比较简单,作为“作品”对待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技术有变,然法理有常,评估技术对法律的影响,切不可脱离其体系化的思维”。⑳参见李琛:《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方法——以著作权为例》,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7 期,第14-22 页。继言之,从著作权赖以存在的劳动理论、人格理论或者功利理论角度分析,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对待,就存在着伦理障碍。㉑参见彭立静:《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载《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 期,第18-21 页。因为著作权并非一个单纯的立法技术上的概念,还是一个维持公平正义价值的伦理概念,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何以可准据著作权保护,首先必须经由制度基础伦理的重新检验。
(一)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对著作权劳动理论的伦理挑战
关于财产权的本源,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劳动理论甚为经典。据而言之,人类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财产权,既不是君主的恩赐,也不是社会契约,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勤勉劳动而产生。㉒[英]洛克著:《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 页。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相较于传统的财产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其仍然以劳动理论作为重要的权利基础。㉓参见冯晓青:《试论构建知识产权理论基础的增加价值理论》,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第2 期,第76-80 页。概其缘由,该理论与知识产权存有渊源上的同构性,其对知识产权中所蕴涵的劳动创新价值的增加给予了财产权上的肯定。㉔参见刘晓霞、蔡永刚:《知识产权保护之法理学检视——基于洛克劳动财产权理论视域的研究》,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9 期,第113-115 页。概言之,劳动理论可以论证著作权的合理性在于,人类利用其智慧和知识进行的创作就是一种在社会公共元素之上增加新的价值的劳动,劳动成果就是作品;国家法律明确承认人类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就是保护其劳动成果的权利,保护社会公平价值。深入探究劳动理论的要义,不仅使著作权在名义上摆脱了封建特权的恶名,还将其上升为人人得以追求的自然权利,而且使著作权在制度上摒弃了封建社会王权赏赐的个例方式,转变为公民社会劳动财产的普遍分配机制。因此,现行著作权的产权分配正义的基础多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公民)是作者。㉕参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9 条、第11 条规定。
如果从人工智能输出的并不是原样输入的信息,而是经过计算机使用人的加工而形成的新作品,那么这时的输出信号就构成了创作。㉖郑成思著:《计算机、软件与数据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4 页。然而,随着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广泛应用,其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能力对著作权制度构建所依据的劳动理论产生冲击。概因著作权领域的劳动具象化为创作,其不仅决定着著作权保护的宏观正义,而且决定着著作权授予的微观正义。所以论述人工智能生成物对劳动理论的冲击,可以归纳为以下两项:第一,在宏观正义上,著作权的保护源于创作,其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该智力活动在质的定义上应归属于人的劳动,在量的定义上应达到劳动的谨慎勤勉。由于人工智能生成在形式上仅具备作品的外观,其在质上实应归属于一种脱离了人的劳动范畴的算法生成物,与人的创作作品的智力活动相去甚远;在量上应归属于一种依赖指令的被动执行过程,并未渗入任何人的谨慎勤勉的劳动。㉗参见黄玉烨、司马航:《孳息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4 期,第 23-29 页。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归属于著作权体系而得以授权。第二,在微观上,著作权的授予也源于创作,即依据创作贡献决定著作权利益的分配模式,仅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服务的,均不视为创作,不能参与创作的利益分享。当今人工智能所为的生成,无论在人机协作模式中由人提供思想再由人工智能生成相应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还是在算法自主模式中由人工智能完全自主地生成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人工智能所谓的这种生成物就没有人的直接参与。这种情形下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就需要认真研究,而不能简单确定其分配模式。如果这种生成物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构成条件,则可以作为普通作品产生著作权,归属于相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否则,该人工智能生成物就不能作为普通作品受著作权保护。至于这种生成物能否作为其他创作成果受保护,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决定。
(二)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对著作权人格理论的伦理挑战
较之英美法系采纳以财产权激励为中心的版权体系,我国则移植了大陆法系以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元并重的作者权体系。㉘参见刘宇琼:《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历史和体系之思》,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9 期,第49-54 页。因此,我国在法律中将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划分为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两类,并规定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保护路径。著作人格权在理论渊源上,与著作财产权的劳动理论完全相异,其可溯源于欧洲近代人格理论的兴起与人权保护的兴盛。㉙参见吴雨辉:《著作人格权的历史与命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 期,第149-157 页。论及人格理论在法哲学中的思想资料,康德与黑格尔可谓贡献丰厚,给我们思考人格之本质提供了两种范式。首先,开创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的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其不仅指人类认识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㉚[德]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00 页。其次,黑格尔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意志或自由精神,意志以人格为外化,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该财产并不限于有体物,只要在人的自由意志的支配下,精神产品的外部定在亦可成为财产权的客体。㉛[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 页、第203 页。不管是理性中心的康德,还是精神中心的黑格尔,两者都将人定性为“绝对价值”,享有“绝对权利”。质言之,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拥有理性的人,只能作为目的,不能作为手段,即人的“尊严”必须被尊重。
人是伦理学上的基本概念,后被移植到私法领域,并以意志或理性来源为标准,对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义务的履行者和责任的承担者进行着合理配置。㉜[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8 页。在此意义上,人格理论不仅为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了正当的伦理基础,更为著作人格权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可靠的伦理支撑。以著作人格权中的署名权为例,因作品中渗透着创作者的人格,其表征着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与意志抉择,在作品完成后赋予其表明身份的权利并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署名权中也暗含着“理性认知,自主决策,自主负责”的理性人逻辑,即创作者基于理性认知,在创作新作品的同时,承担着应尊重他人作品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因此,在上述意义上,著作人格权事实上是基于人格标准,对相关权利、义务与责任进行协调分配的伦理架构。然而,在新兴的智能社会中,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所践行的“机械推理”却在不断超越着“人的理性”,甚至出现了“机械推理”完全取代“人的理性”的自主生成,以致对著作权构建的以自由意志为基础预设的理性人架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概此冲击,首先因人工智能生成中人的理性不再能够渗入到所生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上,使得人的人格无法体现,由此标榜作者创作的署名权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次更因人对人工智能生成的表达缺乏参与,无法对最终成果获得理性的认知,法律原预设的“理性人”便难以再继续承担著作人格权所赋予的相应义务与责任。
(三)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对著作权功利理论的伦理挑战
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功利理论成为著作权制度论辩的又一伦理范式。功利理论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即著作权制度为作品创作者提供产权激励,鼓励其持续进行作品创作,努力为社会增加新的知识价值,最终促进社会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知识产权法的激励机制以公平、公正为标准,主要体现于公平竞争和分配机制上,如果知识产权法不能体现公平(尤其分配公平)原则,势必会大大挫伤创造者的积极性。㉝参见申来津:《知识产权法的激励功能及其发生机制》,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 期,第152-155 页。因为在传统的作品生产过程中,人是创作作品的绝对中心,是故现行的著作权制度激励机制是以激励创作为标准。具言之,为践行分配的公平价值,在私权的归属上,著作权制度采取了以创造为中心的分配原则,将作品的著作权授予作者。然而,当人工智能生成诸种文学艺术表达形式成为广泛存在的事实,这种以作者创作为中心的著作权激励机制便陷入激励上的失灵。具其表现,首先在激励的对象上发生异化。因为传统的著作权制度是以激励创作为中心,但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的便捷性、高效化,实现了文化市场由“创作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若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同等的著作权保护,则其实际上并非在激励人的创作而是在激励着人的投资。其次在激励的目的上发生背离。传统的著作权制度通过赋予作者以产权实现其创作的回报,可激励更多的创作行为,但由于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具备着远超于人的优势,若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同等的著作权保护,则会使得人的创作成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挫伤人的创作激情,最终造成著作权制度原有的激励目的无法实现。
(四)小结
综上之述,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迭代,文化产业正面临着由以人为主的创作密集型产业向以技术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换,概此源于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逐渐实现了由人机协作的扶持向自主生成的自立的变革及国家对该变革在战略上的推进。应此情势的变化,从著作权制度的伦理范式考察,无论是以创作为基础的劳动理论,抑或是以人格为基础的人格理论,还是以激励创作为基础的功利理论,在指导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分配时,其制度体系均无法有效的践行与规范分配的公平正义价值。鉴于此,若因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类作品性,就断然固守人工智能创作应授予著作权保护的伦理范式范式,不仅不会有效地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的分配问题,而且还会使原本协调运行的著作权体系陷入失灵,实为不明智之举。
三、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伦理新释
早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既已对计算机创作作品的版权问题作出倾向性的回应,即“采用计算机系统创作出可以受版权法保护的新作品,主要应当用现有的版权国际公约中关于版权保护的一般原则去调节”。㉞同注释㉖,第72 页。然而,由于人工智能生成虽在形式上表征着作品的独创性,但本质上却为依赖机械推理的算法生成物,其中蕴含的人类贡献率却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㉟参见陶乾:《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载《法学》2018年第4 期,第3-15 页。鉴于此,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不仅需要考察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身的问题,更需要考察人们为使人工智能获得强劲的生成能力所进行的巨额投资。事实上,为了人工智能获得足够的生成能力人们必须进行投资,而且投资的数额还十分巨大。在当今著作权体系下,作品的创作者只能是自然人,作品的著作权人虽然可以是拟制人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人工智能机器人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其在成的文学艺术表达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著作权人。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投入,有必要在现行著作权体系内寻找合适保护路径,为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提供更加符合投资规律的保护。
本文第一作者于2012年发表在《中国法学》的文章《合作作品法律规定的完善》就作品著作权归属原则进行了探讨,其中提出了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原则。以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原则来决定人工智能生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权利归属,不仅能够妥切地解决其著作权归属问题,更能符合伦理原则。从伦理角度看,著作权法律制度是以自然人为基础设计构建的,即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是著作权(尤其大陆法系著作权制度)的依归。此后,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制度造成的冲击与挑战,法律扩张了著作权主体,使之由单纯的自然人主体扩张至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直到今天,法律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这种制度扩张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著作权领域的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因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创设目的仍然是为了自然人的权利和利益,并没有违反基本伦理规则。将著作权主体扩张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制度设计,为什么没有违反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呢?其实质要义就是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创作者或者作者就是自然人,而不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换言之,当今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所确立的作者或者创作者就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只是该项原则即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的补充。
第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不是作者,而且不可能成为创作者,而只能被视为作者。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对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的补充,以弥补特殊情况下自然人作为作者或者创作者有违公平原则。单纯从法律位阶角度看,公平原则在法律上的位阶高于著作权中的自然人中心主义原则。因此,为了彰显著作权制度是符合并贯穿公平原则的法旨,就需要对自然人中心主义进行补充。例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了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的条件。㊱《著作权法》第11 条第3 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由此规定可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需要符合四个条件:(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主持者身份,即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例如,由各个大学发布的招生简章或者学校宣传资料,肯定是有该学校的某个自然人或者某些自然人创作编写的,但必须是由学校主持的。这样的招生简章或者宣传资料,如果是编写者个人自己主动编写的,就不能作为学校的招生简章或者宣传资料使用,只能作为该撰写者个人作品。(2)意志宣示,即:某个自然人或者某些自然人创作过程中所进行表达形式必须“代表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这是一个看似抽象但却非常具体的条件,例如,学校发布招生简章或者宣传资料,必须能够代表学校意志,不能只是代表撰写者个人意志。此处所讲的“学校意志”,就是学校集体领导决定的意志。(3)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发布。以学校名义发布招生简章或者宣传资料,才能够具有公信力,还可能产生宣传学校,吸引生源的效果。(4)法律责任承担者,即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仍然属于自然人的结合体或者自然人利益集合体,为了人类即自然人的财产利益或者人身利益而设立的。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充其量只能是服务于人类的辅助工具,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与自然人平行的物种,更不可能是超越人类的新兴物种。㊲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得知,人工智能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超越人类,究其原因包括人工智能是“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在于人;人类大脑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其生物机理是人工智能不能模仿的;人类智能是一个需要亿万细胞协作,产生化学反应,电流刺激的自然产物。人工智能是一个程序、软件、芯片“设计”的“纯”电流反应。即使是1 岁大的婴儿的吃饭能力,学习认识世界的能力,也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模拟的。引自灵盾者文化:《我为什么说人工智能不能超越人类,原因有四个》,载http://www.sohu.com/a/196526218_479097,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7日。截至目前,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慧动物,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规范秩序都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㊳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表达,包括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引自百度百科词条:《人类中心主义》,载https://baike.baidu.com/ite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7日。其他动物不可能与人类并列,更不用说由人类研究制造出来的器物,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其他机器人等。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原则,人工智能机器人只能作为人类的辅助工具,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可能远超人类个体,但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整体。在这种伦理原则指导下,我们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的新制度就是以自然人为中心,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划归为普通作品之列,具体规则如下:第一,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构成条件进行判断:(1)如果符合作品构成要件,则可以确认该行成文学艺术表达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否则就不属于作品。(2)当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作品条件被认定为作品之后,紧接着需要对该作品进行类型分析:第一种类型分析就是看其是否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作品类型;第二种类型分析就是看是否属于合作作品、翻译作品、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等;第三种类型分析就是是否属于其他种类的作品。因为不同类型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是不同的。(3)权利归属分析。首先,对参与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等相关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分析确认;其次,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成过程中付出了实质性劳动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分析确认;最后,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其著作权归属。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约定,或者由若干合同约定但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则根据智力贡献者、投资者、物力支持者、人工智能操作者、指令发布者或者其他相关者的具体情形进行协商确定。无法进行协商或者协商无法达成协议的,可以请求版权管理机关调解、申请仲裁或者起诉解决。
结语
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未来将会发展得更快,所具有的生成能力将更加强劲,其生成物的保护将更加复杂。因此,关于人工智能生成能力或者生成物所涉及到的基本伦理规则也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截至到现在,人们对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成能力或者生成物所关涉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是刚刚开始,现在给出的答案只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需要人们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的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人也许还不能成为人类的竞争者,无法挑战人类这唯一高智慧动物地位。尽管现在有学者从技术角度、伦理角度、研发角度或者其他视角研究,得出了人工智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超越人类的结论。㊴同注释㊲ 。根据该结论,界定人工智能生成能力或者生成物所涉及的伦理规则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或者过于强劲的冲击。但是,现在的学者还不可能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或者更长远的未来作出绝对的结论,不可能完全排除人工智能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人类的终结者。到那时,现在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生成能力伦理或者生成物伦理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至于那样的时代是否真的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谁也不知道。希望学界同仁继续关注,为人类的未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