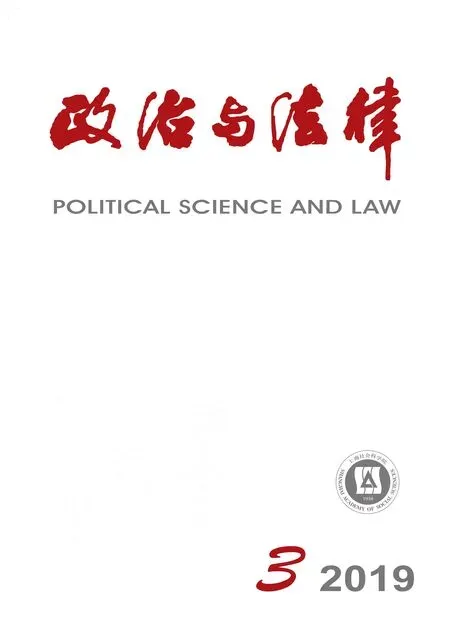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研究*
2019-01-26侯艳芳
侯艳芳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237)
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是在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为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对法益刑事保护方式进行的调整。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对环境资源犯罪具体罪名的修改和解释,既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回应,也是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立法体现。对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在现阶段是否具有必要性,我国刑法学界已出现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进行研究,厘清学术争议的焦点所在、探究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实质,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刑事治理理念的更新,而且有利于促进环境刑事治理实践的发展。
一、关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学术之争
(一)对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支持与质疑
刑法的惩罚性功能与预防性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域的制度及其实践中此消彼长。“预防刑法是刑法开放发展、适应社会变迁的产物,它表现出与传统刑法的结构性差异。”①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是刑法强调发挥预防性功能以更为周全地保护社会安全的立法体现,是刑法从惩罚实害向预防风险的立法倾斜,属于以报应指向到目的指向的刑事立法选择。
现阶段我国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主要任务是社会风险防控和环境风险防控。当前,社会风险表现得较为多元,主要包括来自恐怖行为的风险、来自危险物质的风险和来自网络的风险。环境风险包括生态破坏风险和资源枯竭风险。尽管环境风险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阶段,但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骤增,环境风险尤其是生态破坏风险空前加大。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通过刑法对犯罪完成标准的调整(处罚实害犯向处罚危险犯的转变和处罚具体危险犯向处罚抽象危险犯的转变)、对共犯进行正犯化处罚(教唆犯的正犯化和帮助犯的正犯化)和行为阶段处罚的提前化(预备行为的单独犯罪化和实行行为的提前犯罪化)等方式实现。“一种特别令人感叹的发展是,把保护相当严密地划定范围的法益特别是私人法益的刑法通过这种法益范围的延伸引向抽象的危险犯。”②[德]格吕恩特·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为刑法由重点惩治实害犯向惩治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转向,其本质是危险犯的扩张。
“在刑法观念逐步转向功能主义、刑法与政策考虑紧密关联的今天,刑法的谦抑性并不反对及时增设一定数量的新罪。”③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刑法的谦抑性并非绝对否定犯罪化。当前,在社会风险防控和环境风险防控领域,国家公权力发挥作用不足而非过度,刑事制裁整体适用缺位而非过严。“在环境、公共健康、市场和有组织犯罪等领域,刑法的扩张亦即新型犯罪的创设,非常明显地表明犯罪化的刑事政策比去罪化的刑事政策用得更多。”④Mariela Machado,La Protección Penal de los Bienes Juridicos Collectivos y su Relacion con los Delitos de Peligro 01 Pensamiento penal 9(2010).转引自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作为一种理念与制度的革新,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在本质上是刑法理论对实践需求的理性回应。“德国刑法并非在谦抑,而是在不断向外扩展,其中包含了远远处于‘古典’刑法理论之外的领域”。⑤[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新型犯罪对法益的侵害呈现出空前的危害性,而传统刑法面对犯罪治理需求难以有所作为。为回应国家和公众对安全与秩序的强烈诉求,刑法理论不断自我更新,对同一法益的刑法保护在立法上就会体现为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
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主要理论依据为风险刑法理论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其体现出由结果无价值理论向行为无价值理论的转变。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引起人们对权力过度干预自由的担忧。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质疑者反对象征刑法,并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提出了担忧。质疑者认为,刑法保护实质上体现着国家公权力介入公众权利领域的程度与范围,而权力与权利的合理界限一直是人权理论关注的焦点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行使的审慎性、刑事手段的最后性应被强调。
(二)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未解决课题
“‘风险刑法’所具有的反法治属性、对积极一般预防的过度依赖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的脱离现实,决定了以之为据的环境犯罪治理的早期化欠缺合理性。”⑥刘艳红:《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面对上述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担忧,有学者的回应是:“法益保护早期化并非建构于风险刑法理论之上,能够有效治理污染环境犯罪;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为依据,不存在消解法益概念的问题。”⑦黄旭巍:《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之展开》,《法学》2016年第7期。关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理论风险与实践选择,有论者主张:“尽管预防性刑法采取的干预环境犯罪措施有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但国家基于生态环境和百姓的身体健康等重要民生问题的考量,做出以影响经济发展的较大风险换取国家‘青山绿水’和人民百姓健康安全的价值抉择。……立法模式必须向民生刑法与安全刑法转向,相较之过去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民生与安全。”⑧李梁:《环境犯罪刑法治理早期化之理论与实践》,《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
对于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前者才是实现环境法益良善保护的首选路径,在实践不需要刑事司法的介入时强行介入,是研究者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另一担忧。如果环境行政执法能够有效防治环境侵害,则无需刑事司法介入,即要考量刑事司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问题,此时即使刑事司法介入,如果已有的刑事立法能够应对惩治环境侵害的实践需要,则亦无需刑法保护的提前化。还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要求应当尽可能地依据民事法、行政法对法律权益进行保护。因此,如果实证数据表明,采用征收过期费等行政处罚方式,已经足以有效地抑制了环境污染的危险源,那么就不需要进入到刑法的视野。”⑨姚贝、王拓:《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期。对于上述担忧,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与回应。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担忧与回应,主要集中在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合理与否、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评价依据应注重理论合理性还是现实必要性、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的取舍三个方面。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是将环境法益脱离于传统法益而进行保护的基础理念,在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要实现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对实践需求精准且理性的回应,就要根据集合法益的特点建构二元防范体系。环境法益保护中刑事司法手段的必要性是对质疑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有力回应。笔者于本文中将对这些争议较大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展开分析与论证。
二、法益的中心主义之辨: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基础探寻
(一)刑法明确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规范实质
法益的中心主义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发展具有引领意义。生态中心主义在改变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对刑法根深蒂固之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法益中心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其是否脱离现实、消解法益方面,相关的回应需要对《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的规范进行深度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成立要件,污染环境罪则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成立要件。《2016年解释》第1条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规定为入罪条件,即无论是否对人类法益造成侵害,只要严重侵害了环境法益中的自然法益,就要按照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责任。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将保护的法益由体现为“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人类法益扩大到体现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环境法益。
“不仅是人的生命健康应当通过环境得到保护,使之免受危险的威胁,而且保护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护一个完整的自然,也都是属于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内容的。”⑩[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进步,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方式的不断调整,环境刑法保护法益呈现出纵向前移的趋势。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由人类法益向自然法益的拓展,其本源动力和修法实质,则在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在行为人已经侵害到自然法益而尚未侵害到或者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侵害到人类法益时,即可将有关行为认定为犯罪。侵害环境行为对人类法益的侵害是通过具有中介性质的自然法益实现的。侵害环境行为可直接作用于自然法益,进而可间接作用于人类法益。
“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观,意味着环境本身就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将环境本身作为保护法益无疑会使犯罪提前成立。”⑪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环境资源犯罪中的污染环境罪,将严重侵害自然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必等待已经出现了对人类法益的明显侵害,属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纵向前移。刑法保护的法益由体现为“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人类法益扩大到体现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环境法益,而“严重污染环境”实质上是行为通过侵害环境法益中的自然法益进而侵害或者威胁到人类法益。因此,就对人类法益的保护而言,我国刑事立法将惩治对人类法益产生实际侵害后果的行为转向惩治对人类法益产生侵害危险的行为,此种由惩罚实害转向预防风险的立法追求体现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
(二)集合法益之提倡:自然法益纯粹论的批判
随着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成为国家治理方略,刑法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的立场已逐步为立法机关采纳。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在法益内涵的进阶上表现为由人类法益扩大到人类法益与作为自然法益的环境法益的集合。自然法益受侵害是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背景下犯罪成立的核心标准,而传统刑法保护的生命健康、财产法益等人类法益是环境资源犯罪行为侵害自然法益的或然性产物。刑事立法对自然法益进行独立保护,对侵害自然法益行为的惩治不要求已然侵害人类法益。现阶段我国环境法益刑事保护与《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相比,对自然的非工具性价值予以认可,体现出对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与人类法益不可分割之客观事实的尊重。
环境资源犯罪行为对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的侵害应当具有“公害”的特征。“从社会活动之立场观之,导致公害现象之社会因素,无非为产业之生产活动,国民之消费活动,与介乎此二者之运销活动三者。”⑫邱聪智:《公害法原理》,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7年版,第415-416页。进行具有社会性质的产业活动,对自然法益的侵害行为可以成立环境资源犯罪;个人或者家庭丢弃垃圾(包含建筑垃圾)、排放废水等正常消费活动造成危害的行为,由于其是难以避免的生存性需求且污染程度较低,一般不作为环境资源犯罪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对自然法益的侵害行为具有“公害”特征,有利于区分环境资源犯罪与一般的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如果行为人由于消费活动(不具有公害特征)侵害了环境法益中的自然法益,进而对人类法益产生侵害危险或者实害后果,一般就应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刑事立法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不宜理解为刑法对与人类法益完全无涉的自然法益进行保护。无论在环境伦理上是否承认脱离人类法益之自然的存在,作为环境整体组成要素的人与自然都关系密切、难以分割,且刑事立法始终难以脱离人本主义的价值诉求。随着人类探索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与人类法益无涉的自然法益变得凤毛麟角。就具体刑事案件而言,一般较易判断行为是否已经通过侵害自然要素侵害到人类法益,却难以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的界限进行严格的划分。例如,对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条件“严重污染环境”,在相应司法解释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否单纯侵害了自然法益进而需要适用刑法的问题通常不予考量。
环境资源犯罪惩治既要摒弃《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绝对人类法益保护的指向,也要警惕割裂地强调与人类法益完全无涉的自然法益纯粹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背景下,环境资源犯罪对自然法益的保护具有独立性,但该独立性是相对的,其应当服从于环境法益的整体性特征。在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长久影响下,刑事立法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既是应对严峻环境保护态势的必然路径,也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主选择。刑事立法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人类意志的烙印。“环境法益一方面为典型的非个体法益,另一方面又指向具备一定的抽象性的生态环境整体,因此被视为集合法益的典型代表。”⑬李川:《二元集合法益与累积犯形态研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环境领域刑法扩张的着力点在于突破人类法益的局限,将自然法益相对独立化,形成具有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是刑法保护由个人法益向集合法益的转向。
三、二元防范体系的构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划定
(一)实践而非理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主要依据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支持者以风险刑法理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为基础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质疑者则通过对上述两种理论实践效果的考量进行反驳。例如,有学者提出,环境资源犯罪惩处应在传统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双管齐下地解决,而非诉求于风险刑法:在刑法之内层面,应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核心是谨守刑法的谦抑性;在刑法之外层面,动用刑法之前的其他部门法防线的薄弱是主要原因。针对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极低的刑事责任追究率几乎消解了对“刑罚的必定性”的确信。⑭参见前注⑥,刘艳红文。面对质疑,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支持者认为,法益保护的提前化能够有效治理污染环境犯罪。⑮参见前注⑦,黄旭巍文。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提出本身是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需求的理性回应。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本质是基于实践需求的理论创设,其生命力在于良好的实践效果。
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实质是国家刑罚权力附条件的扩张,因此科学划定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是确保刑罚权合理扩张的关键。具体到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界限划定的关键因素在于行为侵害环境法益的具体样态,即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形态。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是对行为侵害环境法益具体样态的动态评价。该具体样态表现为行为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和具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危险两种方式。对上述具体样态的动态评价亦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把“将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前为“将具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即环境刑法由实害结果防范调整至危险防范;二是虽仍然要求行为造成实际损害的后果,但是将行为造成实际损害后果之因果过程中的时间点提前,即对环境刑法做出环境实害结果防范范围内的调整。
在刑事立法对自然法益进行独立保护的背景下,若刑法对环境的保护由实害结果防范直接调整至危险防范,将对自然法益造成侵害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则虽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环境资源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认定的难题,但亦会不合理地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若刑法对环境的保护在环境实害结果防范范围内进行调整,则虽有利于克服刑法调整范围严重扩大化倾向,便于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环境资源犯罪认定标准的确定,但对环境法益侵害危险存在困难的情形却难以应对。《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对行为侵害环境法益具体样态的动态评价调整属于由实害结果防范调整至危险防范,还是在环境实害结果防范范围内的调整,抑或是以上述两种方式之一为主体而进行的兼容性微调,直接决定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划定是否合理。
(二)二元防范体系:集合法益保护的具体界限
刑事立法罪状中“严重污染环境”属于客观要素中的危险防范抑或实害结果防范,决定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划定。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体现了刑法针对环境损害的危险防范,“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构成犯罪,而无需有严重结果的存在,相应的犯罪则由结果犯转化为危险犯”。⑯王勇:《环境犯罪立法:理念转换与趋势前瞻》,《当代法学》2014年第3期。将结果犯降格为危险犯的适例是,《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结果构成要件,使得只要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即构成污染环境罪;⑰参见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运用实害的构成要件保护法益,可能遭遇举证的困难,如运用危险构成要件则可避免该困难。⑱参见郑昆山:《环境刑法之基础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233页。有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具有情节犯属性,应当将“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要件的情形多样化,不再限于造成人身法益、财产法益实害后果的情形。⑲参见喻海松:《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法律适用》2017年第23期。另有观点提出“严重污染环境”认定标准已突破实害犯的规定,使污染环境罪变成兼具危险犯与实害犯性质的双重犯。⑳参见高峰:《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困境之破解》,《人民检察》2014年第7期。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划定应以环境法益的本质为依据。环境法益是集合法益,是包含人类法益和自然法益的超个人法益,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具体样态因此具有二元性。《2016年解释》第1条对“严重污染环境”这一抽象立法表述详细列举了十七种具体情形,强调刑法对环境法益中的人类法益和自然法益进行二元一体化保护。从该条对行为所侵害法益的内容分类角度看,除去该条第18项的兜底性规定,前七项和第10项是关于行为造成自然法益实际损害的规定;第8项和第9项是从减少的支出、违法所得以及财产损失的角度判断环境法益侵害程度,其与第11项至第17项都是关于行为造成人类法益实际损害的规定。环境刑法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进行二元一体化保护的具体方式表现如下。其一,环境刑法对人类法益的保护。《2016年解释》第1条第8项、第9项与第11项至第17项都是关于行为造成环境法益中人类法益实际损害的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因果关系的发展具有复杂性、证据采集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此对污染环境罪刑事责任的有效追究要求司法者必须具备专业的环保知识。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开启了环境法律责任追究的专业化进程,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提升需要较长时间,同时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罪的法律规定出台时间较晚,相关司法实践经验尚处于积累阶段,如果将“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行为对环境法益中人类法益产生的危险,由司法者具体判断该危险是否存在,在高度强调司法责任制的现阶段,只会降低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可能性,进而会造成相关罪名的虚置。其二,环境刑法对自然法益的保护。自然法益主要是指自然的自洁性利益,即法所保护的自然在其自我代谢能力范围内保持其清洁性的利益。“只有在对环境的‘消费’不突破环境的‘供给’时,在对实质上是环境使用的环境损害实施了有效的防治,在对具体的环境消费者实施了有效的限制时,表现为自然状态的环境利益才能真正得以实现。”㉑徐祥民、朱雯:《环境利益的本质特征》,《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根据《2016年解释》第1条前四项的规定,只要行为发生“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达到“三吨以上”或者分别达到“三倍以上”、“十倍以上”的标准之一,就已经实际侵害到自然的自洁性利益。该条第10项“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是独立保护自然法益的直接体现,基于该条前七项是对行为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具体表述,第10项应当理解为对侵害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行为的兜底性规定。该条第5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第6项“两年内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以及第7项“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是对行为情节的描述。司法解释针对自然法益规定情节犯,源于对自然法益侵害行为判断的渐进性和复杂性,该判断还高度依赖于及时且科学的取证。针对自然法益规定情节犯是在严峻的环境污染治理态势下从“严”治理的阶段性措施,其对遏制当下环境资源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的高发态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上述对行为情节描述的司法解释规定,模糊了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界限,压缩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权运行的合理范围,不利于环境的长远保护。
刑法对环境法益保护的界限划定因环境法益的集合法益性质体现出二元化特征。刑法对环境法益中人类法益的保护界限是行为造成对人类法益的实害结果,对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的保护界限是行为造成对自然法益的实害结果和拟制的实害结果(以行为具备特定情节为标准)。事实上,行为对人类法益造成实害结果的判断,运用传统法益损害判断方式即可实现;行为对自然法益造成实害结果的判断尤其是对自然法益造成实害结果之临界点的判断,则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因此,司法解释在规定对自然法益造成实害结果的同时,规定行为对自然法益造成拟制的实害结果。其虽短期内具有实用性,却明显逾越了刑事司法权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环境资源犯罪因果关系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确定侵害行为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之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表达规则在立法技术上困难重重。现有法律与司法解释体现出的环境法益保护二元防范体系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保护的分立式特征明显,而一体化特征不足,在应对上述困难时,在一定程度上越过了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界限。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运用累积犯理论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的临界点进行认定。
只有明确了某具体犯罪设置所要最终保护的法益内涵,才能进一步明确其设置形态。在刑法明确对自然法益进行独立保护的背景下,运用累积犯理论完善环境法益保护的防范体系就有了依据。“在环境污染物质长时期积累可能造成健康损害或者可能造成破坏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场合,刑法便予以介入。”㉒同前注⑨,姚贝、王拓文。德、日刑法为了保护环境介质提出的累积犯是指某种行为样态虽然原本确实不能侵害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不能侵害到成为问题之程度,但是能够诱发居于同一方向的其他行为样态之共同作业侵害的犯罪类型。㉓See Wolfgang Wohlers.Rechtsgutstheorie und Deliktsstruktur.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GA)2002:19-20;Wolfgang Wohlers.Deliktstypen des Präventionsstrafrechts-zur Dogmatik“moderner“Gefährdungsdelikte.Berlin:Duncker&Humblot,2000:318-320.转引自李晓龙:《刑法保护前置化趋势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9页。累积犯理论的提出是由环境侵害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环境资源犯罪的行政犯特征共同决定的。累积犯立法肇始于环境资源犯罪的治理,由于对环境法益的侵害并不具有瞬时性,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没有明显的节点,在环境法益侵害危险认定存在困难的情形下,便根据累积犯理论对其进行刑事追责。环境保护领域的累积犯对人类法益的实害结果具有诱发性,对自然法益则已经造成了实害结果,仅因为单一行为造成的自然法益实际损害较小需累积到一定程度,或者需要其他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在量上达到刑法予以规制的程度。
综上所述,构建环境法益保护的二元防范体系,要根据环境法益的集合法益特征,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进行一体化保护,同时要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点充分运用累积犯理论以解决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之临界点认定的难题,并合理划定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
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实践需求
(一)环境刑事司法权扩张之实践效果的检视
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的取舍是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争议焦点之一。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质疑者认为,在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者之中,前者才是实现环境法益良善保护的首选路径。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实质上是刑事权力作用领域的扩张,其挤压了原有环境保护行政权力调整的范围。事实上,行政违法行为不仅违反秩序,而且也侵害法益。对某一侵害法益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抑或刑事责任,从特定立法阶段看属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问题,该界限的理性调整受到犯罪形势和刑事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治理严重法益侵害行为的实践效果是衡量刑事司法权扩张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通过行政制裁即可取得良善效果,则无需刑事司法权的扩张;反之,刑事司法权的扩张就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受重视经济发展指标、漠视环境保护效果的传统观念影响,环境保护权力受制于功利性政绩观,可作为领域非常有限。在环境侵害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例数量很少,该罪名一度被虚置。作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主要表现,刑法新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出台后,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涉嫌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同比分别增长25.5%和22.4%。㉔参见霍桃:《最高检挂牌督办33起破坏环境资源案》,《中国环境报》2015年10月28日,第8版。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督促移送涉嫌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852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040件,起诉27101人。㉕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http://www.spp.gov.cn/spp/gzbg/201603/t20160321_114723.shtml,2018年11月14日访问。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专项立案监督,建议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16件,挂牌督办张百锋等人偷排废酸案等22起重大案件,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9173人。㉖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7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http://www.spp.gov.cn/spp/gzbg/201703/t20170320_185861.shtml,2018年11月14日访问。全国检察机关连续4年开展专项立案监督,坚决惩治污染大气、水源、土壤以及进口“洋垃圾”、非法占用耕地、破坏性采矿、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起诉13.7万人,较前五年上升59.3%。㉗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年3月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http://www.spp.gov.cn/spp/gzbg/201803/t20180325_372171.shtml,2018年11月14日访问。与此同时,全国法院2014年新收污染环境罪案件1188件,比2013年增长7.9倍,案件数量超过近10年污染环境案件的总和;㉘参见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 守护国家法治生态》,《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7日,第5版。2015年审结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9万件,同比上升18.8%。㉙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6ce239a82c31348f8856a986e9eb45.html,2018年11月14日访问。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0394件,审结18874件,生效判决涉及23727人。㉚参见郑学林:《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的新发展》,《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7日,第8版。原有刑事立法惩治环境侵害不力的局面在2014年后迅速得到扭转,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在环境法益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环境刑事司法权在现阶段的扩张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环境刑事司法权的扩张是相对的,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则是绝对的。环境行政执法是环境刑事司法得以展开的重要线索来源,环境刑事司法是环境行政执法高效运行的最终强力保障。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就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对行刑衔接节点进行了实质性改变,有必要对节点标准和取证方式进行适时明确和调整。
(二)行刑衔接之节点标准的明确
环境法治可以归结为建设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严格执行环境法律的规定和严格追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人的责任。㉛参见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年6月)指出,“注重依法监管”具体表现为“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方式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并受到高度重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让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标准改变为“严重污染环境”,环境领域行政法调整和刑法调整的界限,已由是否对传统人类法益造成严重侵害,转变为是否对环境法益造成严重侵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节点,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会移送刑事司法,转变为虽然尚未发生人类法益严重侵害后果但也可能会移送刑事司法。
环境行政执法中发现的环境问题是查处环境犯罪的重要线索来源,因此确立环境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刑事司法的具体标准就十分必要。环境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行为构成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差异。两者行为构成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违法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不同。以污染环境行为为例,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对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并无明确要求,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认定则要求主体的主观方面必须为故意。两者行为构成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刑法将具有加重后果或者特殊情节的环境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㉜参见侯艳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24日,第5版。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需判断行为人故意造成人类法益严重损害的程度即可决定是否移送刑事司法,改变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侵害行为虽然尚未造成人类法益严重损害,但仍需进一步对是否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和是否符合《2016年解释》的规定进行考察后才能决定是否移送刑事司法。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是对环境资源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成立标准的实质性改变,因此环境法益遭到严重侵害而应受到刑事追责的具体标准需要重新明确。《2016年解释》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在予以列举式规定的同时,规定了“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这一兜底性条款。该兜底性条款的适用应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在侵害对象的判断方面,环境资源犯罪是行为通过侵害环境法益中的自然法益进而侵害了人类法益,或者是行为仅侵害了环境法益中的自然法益而尚未侵害人类法益,因此行为对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的侵害是最为直接的且具有必然性。这决定了进行环境资源犯罪追责的底线即兜底条款的适用,首先应当以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作为对象来判断“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其二,在侵害程度的判断方面,兜底条款的适用还要与列举式规定中污染环境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相当。刑法对环境法益中自然法益的保护包括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两个方面。刑法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受污染、保障自然资源不会枯竭,因此,兜底条款中行为侵害程度的判断,除了考察行为发生地、行为对象数量、污染物质含量、具体行为方式和防治污染成本外,还应当考察生态恢复可能性(包括恢复技术、恢复成本、恢复时间等)和资源再生能力(包括资源再生可能性和行为人为资源再生可能做出的劳务与财产支出)。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之取证方式的调整
环境侵害取证具有明显的时效性,若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过程中获得的证据不符合刑事追责的要求,则再次取得形式上合法、实质上有效的证据就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取证方式进行调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依据保护人类法益的刑法追责,有关人身与财产的损害性证据搜集是追责的关键,裁判者的审查重点是环境侵害行为和损害性证据事实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依据保护环境法益的刑法追责,环境数据的测定将成为追责的关键,司法者审查的重点应当是环境数据的取样检测和条件分析过程。
环境数据的取样检测是环境数据测定的前提和基础。进行环境数据的取样检测,需要设置合理的取样时间和取样地点。设置合理的取样时间存在两个难点,即取样的时间段和持续时间段。污染环境行为发生的时间段一般是在非正常工作时间,因此环境数据的取样必须相应地具有机动性;在需要证明污染环境行为具有持续性的场合,行为的事前推定存在困难,因此需要等待排污行为的持续而难以予以及时制止。取样地点的合理性设置,直接决定着污染环境行为是否能够被依法追责。取样地点要尽可能接近污染源,同时进行对比性取样,保证对比性取样与污染源取样空间距离为最短,进而将其他污染物质的可能影响降到最低。
环境数据的条件分析是通过对环境数据取样检测获得的数据进行环境条件的分析,判断污染环境行为与检测数据之间关系的直接性和排他性。环境本身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证明检测数据中的污染物质并非来自其他污染源存在困难。检测数据中的污染物质并非只能由一个污染源产生,只有当污染物质是只能由指控污染源才能排放的特殊物质时,才能排除其他污染源存在的可能而确定唯一性。污染环境行为与检测数据之间关系具有直接性与排他性的判断,可以依据环境介质的不同进行分类处理。环境数据的条件分析是运用环境与法律专业知识确定污染环境行为与检测数据之间关联紧密度的过程,是环境法益刑法保护提前化后追责程序面临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