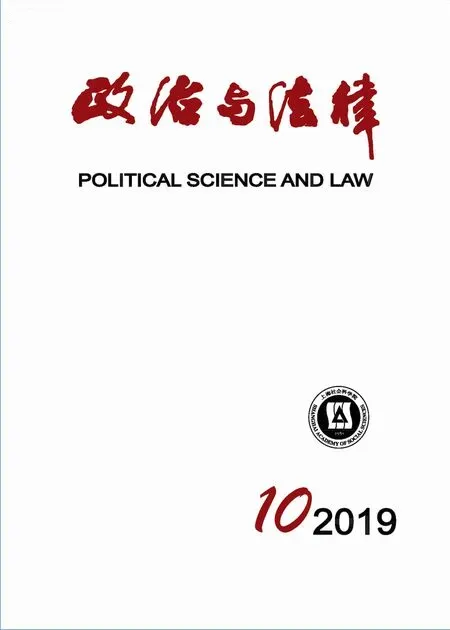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
——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
2019-01-26虞婷婷
虞婷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Web2.0时代,任何个体只要接入互联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因此用户利用网络之便利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层出不穷,单独追究用户的侵权责任在经济上几乎无效。基于诉讼成本的考量,权利人一般会将网络服务商一并作为被告或者仅仅起诉网络服务商。在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时,过错的有无是一个核心问题。其中衡量网络服务商是否有过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是否履行了网络传播内容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所谓知识产权审查义务,是指网络服务商应当主动对用户上传信息的知识产权合法性进行审查,并采取合理的措施移除侵权内容的义务。为了贯彻技术中立原则的法律精神,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借鉴了美国法上的避风港规则,网络服务商只需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或者应知侵权明显的事实后采取必要措施,无需主动对知识产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①笔者于本文并无意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服务商”等概念进行区分,其指向的均是与内容服务提供者相对的服务商,出于用语统一之考量,除必要引用之外,笔者于本文正文中均采“网络服务商”之术语。即便相关规范已明确将网络服务商是否主动审查排除于过错的考量因素之外,司法实务中仍未形成一致意见,有的法院认为“网络服务商不负主动审查义务”,②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终199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提出其有义务“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③参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终2735号民事判决书。或应设分类频道等模式而对授权进行审查。④参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终2038号民事判决书。在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网络服务商只承担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不需要对用户上传的信息进行合法性审查。⑤参见孔祥俊:《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57页;梅术文:《著作权法上的传播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27页。不过,近年来有部分学者主张网络服务商应负担事前的内容过滤或人工审核等义务。⑥参见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宋亚辉:《竞价排名服务中的网络关键词审查义务研究》,《法学家》2013年第4期。司法实务、学说的混乱以及与法律规范的不一致,需要人们对网络服务商不负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基本论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问题之所在:避风港规则引发的利益失衡
我国在规制网络服务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尤其是著作权侵权)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以下简称:DMCA)确立的避风港规则。DMCA第512条(c)项对网络服务商免责的主观条件有如下要求:其对于用户的侵权行为既不存在实际知情(actual knowledge),也不存在明显知情(apparent knowledge),前者一般以权利人的通知予以证明,后者指的是意识到侵权明显的事实或情境。为了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意识到侵权明显的事实或者情境,美国国会创设了“红旗测试”(red flag test)。⑦Liliana Chang,The Red Flag Test For Apparent Knowledge Under The DMCA§512(C)Safe Harbor.28 Cardozo Arts&Ent.L.J.197(2010).然而,无论是“实际知情”还是“明显知情”,其指向的都是具体特定的侵权事实(specific infringement),仅仅对侵权行为的存在有着概括性的知情不会妨碍其驶入“避风港”。与此相应,DMCA第512条(m)项也将查找、监控侵权行为的负担施加给了权利人,⑧See DMCA512(m),Protection of privacy.--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ndit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subsections(a)through(d)on--(1)a service provider monitoring its service or affirmatively seeking facts indicating infringing activity,except to the extent consistent with a standard technical measure complying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i);or(2)a service provider gaining access to,removing,or disabling access to material in cases in which such conduct is prohibited by law.如果一项侵权行为还需要网络服务商进行调查才能确定,那就不属于显而易见的“红旗”,因此,DMCA实际上免除了网络服务商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在这样的前提下,认定网络服务商是否存在过错只能依靠权利人的通知以及网络用户如同“红旗”般明显的侵权行为,此种规制模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引入避风港规则的中国都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
(一)理论障碍: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的过错形态被狭隘地解读
美国法院在解释“实际知情”和“明显知情”时都将其限定于对具体侵权事实的知情,即“具体知情”(specific knowledge)。一方面,“具体知情”要求与普通法的一般理念不符。根据普通法上的辅助侵权理论,如果网络服务商对第三方侵权行为有着概括性的知情,以至于它可以“合理预期”(reason-ably anticipate)侵权行为在未来会发生,那么它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⑨David H.Bernstein,Michael R.Potenza,Why The Reasonable Anticipation Standard Is The Reasonable Way To Assess Contributory Trademark Liability In The Online Marketplace.2011 Stan.Tech.L.Rev.4(2011).另一方面,在“具体知情”理念下,实际知情或者明显知情指向的都是网络服务商故意的过错形态,并不包含过失因素。例如,在Corbis Corp.v.Amazon.com案中,法院就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理性人可能从既有事实中推出侵权的存在,“明显知情”的实质在于网络服务商是否在其已经意识到的公然侵权的事实面前故意继续其行为,对明显侵权的“红旗”视而不见。⑩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have deduced from the circumstances.Instead,the question under§512(c)(1)(A)(ii)is“whether the service provider deliberately proceeded in the face of blatant factors of which it was aware or whether it turned a blind eye to red flags of obvious infringement”.See Corbis Corp.v.Amazon.com,Inc.,351 F.Supp.2d at 1107-1108.由此可知,“红旗标准”适用的前提是“意识”到具体侵权行为的存在,所认定的主观心态至少为“间接故意”。在我国,不少学者也以“红旗标准”来解释我国法上的“应知”,主张其为蕴含故意内容的“推定知道”(有理由知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0日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9条也指出,被告实施教唆、帮助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上应当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主观过错。“明知”指实际知道侵权行为存在;“应知”指因存在着明显侵权行为的事实,应当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存在。其对“应知”的理解亦是对红旗标准的借鉴。与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规则相比,“应知”的内容被大幅限缩,降低了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的要求(甚至对网络服务商没有注意义务的要求)。此种狭义的解读将使传统侵权法上的过失归责原则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领域面临形同虚设的窘境。
(二)实践难题:避风港规则使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之间利益失衡严重
由于对“实际知情”和“明显知情”的要求如此之高,美国法院实际上确立了这样的判定标准:网络服务商只有在收到符合要求的通知时才构成“知情”。迄今为止,美国尚无一例判决认定“明显知情”的“红旗”成立,即便其意识到侵权普遍存在且从侵权活动中获得利益也能驶入避风港。因此有学者开始提出质疑,对于公然承载了大量侵权内容的服务,严格适用具体知情要求,可能不符合法律的利益平衡价值。Mary Rasenberger,Christine Pepe,Copyright Enforcement and Online File Hosting Services:Have Courts Struck the Proper Balance?59 J.Copyright Soc’y U.S.A.p669(2012).如果认为网络服务商的过错形态仅限于故意,那么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靠权利人积极主动的监控以及通知,对于时间敏感性较强的权利客体而言,通知后的删除很有可能于事无补。一般来说,版权内容在刚刚上传的即时是最有价值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容的价值会逐渐降低。因此,当侵权性的内容最终被删除时,它可能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了。不仅如此,我国在引进避风港规则时还存在移植上的疏漏,并未将惩戒重复侵权用户和容纳标准技术措施作为避风港的准入门槛。网络服务商只要公开联系信息并履行通知后的删除义务即可免除赔偿责任,客观上促使其在打击侵权方面完全持消极等待立场。以“红旗原则”和“通知—删除”义务为核心的避风港规则是对互联网产业的一种保护以及对作品传播的鼓励。然而,从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的价值追求来看,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产业的发展为代价。我国在互联网产业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处理方面与美国相比有一定的目标差异,互联网产业要健康有序发展,必须以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化为前提。
二、问题之症结:技术中立原则与最小防范成本理论
DMCA设立避风港规则旨在为网络服务商和版权所有者提供更强大的激励,使其合作监测和处理发生在数字网络环境的版权侵权,在政策导向上偏向于网络服务商利益之维护,但这种立法导向在今天却导致了新的利益失衡,其根源在于避风港规则制定时所依赖的技术中立原则和最小防范成本理论被人为僵化了,因此也就成为网络服务商用以主张其不承担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一把利剑。
(一)技术中立原则
中立往往意味着禁止歧视与干预,网络环境下的技术中立要求网络服务商应扮演的“纯粹传输者”的角色,作为一种媒介,其主要功能在于传递信息而不是改变信息的形式或内容。技术中立原则在版权侵权领域的适用最早确立于美国的“索尼案”。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借鉴了美国专利法中的“普通商品原则”,认为如果产品可能被广泛用于合法的、不受争议的非侵权用途(实质性非侵权用途),那么即使制造商和销售商知道其设备可能被用于侵权,也不能推定其构成共同侵权。Sony Crop.of America V.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464 U.S.417.(1984).按技术中立原则,网络仅为一种纯粹的信息传播工具,不应承载任何价值判断。只要网络服务商保持“公共承运人”的中立性就享有责任豁免,无需承担监管网络的职责和义务。参见高薇:《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承运人规制》,《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就技术中立与审查义务的关系而言,立法决策者需要在“完全的技术中立+豁免平台义务”与“有限的技术中立+科以平台更重的义务”之间作出理性的选择。现实是,即便网络服务商技术不中立的运营模式越来越普遍,却仍然凭借“技术中立”来为其服务披上圣洁的道德外衣,以求最大程度地获得“信息中介”意义上的责任豁免。以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为例,其经营的淘宝网表面上并不从双方的交易中直接获益而仅提供交易平台,但其收益却主要来源于广告及检索排名等增值服务。淘宝网站有着海量的商品和卖家,而真正得以集中曝光的商品却集中在少数卖家手中,这往往是因为其通过在淘宝上购买广告摊位、检索的优先排名等方式让自己的产品能够优先展示在消费者面前。对于此类经过竞价排名的用户侵犯知识产权,淘宝网仍然以其中介地位为由主张不负审查义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成为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潮流。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网络平台更加积极地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广泛用于对用户个人行为预测和干预,逐渐偏离避风港规则下的中立被动的服务定位。参见魏露露:《网络平台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对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因此,在新技术环境下,随着平台自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不断深化,此种免责主张并非当然具有正当性。
(二)最小防范成本原则
DMCA之所以让版权所有人承担查找和监控侵权的义务,除了技术中立原则的考量,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将版权所有人视为监控义务的最小成本负担者。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不负审查义务”之规定,国家版权局也曾召开“著作权法修改媒体互动会”作出说明:“对于网络服务商来说,在技术上目前还无法实现对内容是否经过著作权授权的甄别,因此不具备可操作性,不能要求网站承担这样的义务。”杨理光:《版权局:现有技术不足让网络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http://tech.sina.com.cn/i/2012-04-25/17387019216.shtml,2019年7月23日访问。质言之,囿于技术等客观条件,网络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的成本过于高昂,相反,版权所有者处于一种独特的特权地位,能够最好地评估侵权的成本与网络效应和互补性带来的经济收益。Anna Katz,Copyright In Cyberspace:Why Owners Should Bear The Burden Of Identifying Infringing Material Under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18 B.U.J.Sci.&Tech.L.372(2012).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权利人了解自己的权属状况,由于网络服务商不会授予权利人访问其专有代码的特权,致使权利人难以定位和识别网络上所有的侵权内容,只能在每个站点上分别监控。在网络环境下,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是潜在的“侵权人”,而识别网络空间中的侵权人身份需要极高的成本。随着侵权的泛滥,权利人进行监控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是逐渐递增的,重复执行既浪费资源也不能有效预防侵权。从网络环境的现实运作来看,权利人监控网络与防范侵权并不存在内核的一致性。以著作权为例,一旦未经权利人授权的作品被上传到网络,侵权就已经发生,并且,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损害也会增加。权利人独立于网络平台或者搜索引擎服务商,即便其对网络上的信息进行了积极主动的监控也不能阻止侵权信息的上传,权利人发现侵权信息之后再向网络服务商发送通知,也不属于预防侵权的范畴,而是仅仅一种止损手段。可见,一律将权利人视为最小防范成本的负担人,确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三、修正的前提: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关系之厘清
(一)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之证成
只有反映行为人过失的注意义务本身得到证成,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网络服务商是否需要承担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直以来,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界对于网络服务商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这一基本理念并不存在分歧。然而,在过错责任下,网络服务商具体的过错形态如何却未形成一致意见。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在规定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的过错时经历了“明知”⇀“知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知道”的变迁。笼统的“知道”二字应当如何解读,在学界也一直争执不休,其中不乏有学者认为“知道”规则属于故意侵权范畴,即仅指实际知道(明知)和其证据法上的衍生类型“很可能知道”(有理由知道),不包括过失意义上的“应知”。参见胡晶晶:《论“知道规则”之“应知”— —以故意/过失区分为视角》,《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第6期。具体到知识产权领域,《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既采用了“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的表述(第22条),又规定了“明知或者应知”(第23条);《最高人民的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则仅规定了“明知或者应知”(第8条)。“明知”为故意的主观过错形态争议不大,但如何解释“应知”却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和“应知”应适用推定规则,参见徐伟:《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基础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2页。推定规则下的“应知”与“明知”一样均含有故意的主观状态。参见王光文:《论我国视频网站版权侵权案件频发的原因与应对》,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9页。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主观判定必须以对特定侵权行为的知晓为条件,仅仅概括知晓存在侵权行为一般不宜认定构成侵权。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是一种故意而非过失责任。参见曹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主要对象》,《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著作权还是商标权领域,在规则层面,“应知”或“知道”都指向故意,但在实践层面,法院却或多或少地给网络服务商设置了注意义务,“应知”也就包含过失。参见冯术杰:《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对“知道”、“应知”的不同认识,反映了我国研究者对于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过错形态的认知差异。将“知道”、“应知”限定为故意,并通过推定的法律技术予以确认,这在操作层面确实是可行的,但却使传统侵权法上的过失归责原则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形同虚设,而将过失纳入“知道”、“应知”的范畴则可以维系过错内涵的完整性。
如果像直接侵权人那样对网络服务商实行严格的责任,这将为权利人提供最为周密的保护,对网络产业的发展则是致命的打击。相反,如果过错仅限于网络服务商的故意行为,这将明显缩小可能成立的侵权范围。如果过错也涵括网络服务商的疏忽行为,这将得到一个合理的中间保护范围(intermediate scope)。David H.Bernstein,Michael R.Potenza,Why The Reasonable Anticipation Standard Is The Reasonable Way To Assess Contributory Trademark Liability In The Online Marketplace.2011 Stan.Tech.L.Rev.40-41(2011).DMCA制定时的信息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网络服务商越来越多地对网站内容进行有意识、有控制力的引导;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新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严重性、网络服务商履行注意义务的成本和权利人预防侵权的难度等关键因素发生了变化。在诉讼中要证明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侵权存在故意帮助行为无疑困难重重,如果认为网络服务商仅为其故意行为买单,那么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将毫无保障。为实现新的利益平衡,对“知道”和“应知”的解读也应当符合当下网络技术发展的现实,网络服务商应为其过失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而过失客观化的表现就是行为人对其应履行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二)审查义务属于较高层级的注意义务
DMCA出台之前,美国法院要求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上传的内容履行审查义务,与这种审查义务对应的是严格责任。如在1993年的Frena案中,网络用户未经许可而将原告享有版权的170张照片上传至被告运营的BBS中。法院认为,无论被告是否实施上传行为,只要其网站中出现侵权作品的复制件,就足以认定被告未履行主动审查义务而构成侵权。See Playboy Enterprises,Inc.v.Frena,839 F.Supp.1552(1993).由此可知,在美国早期的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商往往被视为电子出版者(electronic publisher),与内容提供者一样在运营过程中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查义务,并对此承担严格责任。DMCA网络服务商的审查义务免除,对于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由严格责任走向过错责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上述变迁历程来看,审查义务对应的是严格责任,与其相对,注意义务则指向过错责任,因此,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当属并列关系。
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在讨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关系时存在并列、等同于包含三种不同的观点。持并列论的学者以王迁为代表,其认为审查义务意味着网络服务商必须积极采取合理措施对用户上传的内容主动加以逐个审视,并查验上传者是否有合法、完整的授权文件;注意义务则意味着网络服务商在其能够和应当发现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的情况下及时制止侵权行为,至于其是否能够和应当发现侵权事实,取决于服务性质、职业要求、同行业中的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参见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6页。持等同论的学者以谢雪凯为代表,其认为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均以行为人对侵权事实尽其所能去发现并制止为落脚点,两者无论内容抑或法律效果均并无二致。参见谢雪凯:《审查义务:在线服务商主观过错之轴心——立法与判例的启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持包含论的学者以吕炳斌为代表,其认为从法律逻辑上而言,审查义务实为一种加强版的注意义务,仍可从合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推导而出。参见吕炳斌:《网络版权避风港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出版》2015年23期。相比较而言,笔者比较赞同最后一种观点。我国司法实践从未经历过像美国法院那样的归责原则之变迁。一直以来,我国法院奉行的都是间接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事实上,审查义务与严格责任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后者是一种结果责任,即无论是否具有审查义务只要存在侵权行为,网络服务商都要承担侵权责任。要使审查义务发挥实质意义的功效,就应当使其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联系起来,在四个构成要件中最佳连接点只有不法行为和过错。不法行为往往指向积极地作为,但审查义务之违反却是一种不作为,因此只能将审查义务与过错联系起来,审查义务的履行与否也是衡量网络服务商是否存在过错的客观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具有功能和效果上的一致性,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两者是完全等同的。注意义务要求网络服务商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须尽到必要的谨慎和注意,审查义务要求其还须积极地作为,事先主动审查用户上传信息的知识产权合法性,如事前采用过滤技术或者人工审查以排除侵权信息,这并不以侵权明显为前提。不过,就其本质而言,审查义务属于注意义务涵摄的范畴,审查义务的确立,要求网络服务商积极采取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预防措施,弥补了既有的注意义务体系整体被动之不足,换言之,审查义务本质上属于较高层级的注意义务。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较高的注意义务”,其实质内容就是审查用户上传内容的知识产权合法性。如在中文在线诉苹果系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苹果公司对涉案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负有较高注意义务,但其未要求涉案应用程序开发商提供相关的权属证明文件(未履行审查义务),因此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802号民事裁定书。在十九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潇湘书院(天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十九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有签约作者提供的原创作品(也有用户上传的他人作品),对网络用户上传的涉案作品是否获得作者授权,是否涉嫌侵权,应当负有一定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二审法院指出,十九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其经营模式等负有较高注意义务,应积极与上传者取得联系,对相关作品是否原创或者是否具有合法授权进行核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侵权行为发生或持续。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6209号民事判决书。质言之,在以“较高的注意义务”认定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的过错时,法院一方面认为义务的性质仍然是注意义务,另一方面又将审查知识产权的合法性作为该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
我国主流观点认为,网络服务商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但不承担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参见马一德:《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过错认定》,《现代法学》2018年第1期;姚志伟、慎凯:《关键词推广中的商标侵权问题研究——以关键词推广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为中心》,《知识产权》2015年第11期;李欲晓、李忠妹:《视频分享网站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这将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进行了人为地割裂和对立。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从法律逻辑上而言,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注意义务的设定并非一成不变,在特定的情形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进行知识产权审查亦是其合理注意义务的应有内容。换言之,注意义务包含审查义务,但一般注意义务并不必然引发审查义务,因此,在注意义务得到证成的前提下,需要分析一般注意义务上升为审查义务的合理性。
四、修正的方向:一般注意义务上升为审查义务之合理性
(一)从技术中立原则到私权力理论
传播学原理认为,网络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方面,网络媒介作为实现自然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手段、方法和活动,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网络媒介作为被社会的人所创造和应用,服务于一定社会目的并满足其需要的手段、方法和活动,又具有社会属性。参见燕道成:《“网络中立”:干预性的中立》,《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技术中立原则主要从网络媒介的自然属性来理解其价值,忽视其社会属性。以竞价排名为例,算法本身仅指在一个有效的输入后,通过有限的计算步骤得出结果,从而解决某一问题或者得到结论,从这个角度看,其属于一项自动的科学技术。然而,究其本质而言,搜索算法仅是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人类决策而已,网页排名的算法实际上被赋予了设计者或经营者的意识因素,算法本身的自动性不等于算法运用的中立性。尽管DMCA为网络服务商塑造的避风港规则也要求其仅仅作为侵权信息通过的被动渠道(passive conduits),但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商背离了设立避风港的宗旨,网络服务商通过对内容、访问以及终端用户进行控制也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融合,这与网络的中立性背道而驰。Georgios I.Zekos,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In Cyberspace: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15 Chi.-Kent J.Intell.Prop.335-336(2016).剥开技术中立的外衣,网络服务商已经超越“单纯通道”的消极角色,不仅具备了影响网络行为的动机(意志),还具有影响网络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质上属于网络空间私权力的运行。权力的本质在于“哪怕遇到反对也能彻底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郭道晖:《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资源优势的运用则是权力产生、作用的基础。运用这种资源优势的主体如果是国家或社会公共组织,对应的就是公权力,如果是普通私人主体,对应的则是私权力(private power)。参见张小强:《互联网的网络化治理:用户权利的契约化与网络中介私权力依赖》,《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7期。网络服务商的私权力建立在其具有的技术资源、平台资源、信息资源及其支撑的市场资源优势基础之上。在私权力作用下,网络服务商的角色由市场规则的服从者转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并渐渐成为网络社会空间及其内生秩序的主要承担者和建构者,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了网络世界的新型权威。参见邹晓玫:《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角色构造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以淘宝网为例,其平台运营者在该网络空间实际上享有相应的“准立法权”(制定大量有约束性的平台规则)、“准行政权”(对用户进行内部管理)以及“准司法权”(对用户之间的纠纷争议进行裁决处理)。
从网络空间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网络社会也是国家主权所及之地。然而,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去中心化和信息碎片化特征,使得国家治理手段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网络服务商由此演化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参见裴炜:《针对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执法义务边界》,《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因此,网络服务商享有的私权力具有极强的行政执法属性,与私权力对应的义务主要是行政义务(公法义务),但私权力的运作同时也可以产生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私法义务)。日益受到重视的网络审查就是一个例证,目前网络服务商的信息过滤义务并非完全以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出发点,而是同时包含私权保护的客观要求,出现了公私权益同质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此类协助执法义务,关注对象涉及个人隐私、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以及色情、暴力、仇恨、危害国家安全等广泛事项。参见张新宝、许可:《网络空间主权的治理模式及其制度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知识产权既是一种私权利,也代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财产秩序,代表了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参见于波:《网络中介服务商知识产权法律义务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3页。因此,网络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对私权的保护,也是对网络空间公共秩序的维护,网络服务商基于私权力的行使而主动进行知识产权合法性审查,着眼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此种秩序维护恰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权。私权力所具有的支配优势、所拥有的资源,意味着网络服务商在网络生态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符合“有权必有责”的一般原理。换言之,私权力就是网络服务商承担他人责任的基础。在其监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的背景下,再以技术中立原则作为豁免其审查义务的理由实在难以成立。
(二)网络服务商是最小防范成本的负担人
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初始权利的分配并不影响社会的福利,即防范措施的采取与谁是最小防范成本人无关。然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真实世界里,这种交易无法进行,初始权利的分配就影响了经济效率。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应将权利界定给防范成本较大的一方,Daniel H.Cole,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to Property.Indiana Legal Studies Research.32(March).267-277(2014).防范成本较小的一方则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因此,决策者需要在网络服务商和权利人之间确定谁是最小防范成本负担人。最小防范成本理论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比较各方当事人负担的防范成本,选择成本负担最小的一方,这是讨论的前提,因为其揭示了网络服务商比权利人更适合承担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经济合理性;其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即便网络服务商比权利人更适合作为审查义务的成本负担人,还需进一步判断网络服务商的预防成本是否小于预防产生的收益。
首先,确定最小防范成本负担人(the least-cost avoider)。随着过滤技术的进步以及成本的降低,网络经营者可以凭借内容识别技术和智能算法进行信息检查,其能力大大提高。与权利人相比,让网络服务商承担监控过滤义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果。通过运行相同的技术系统实现多个权利人的利益,过滤的边际成本也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降低,Lital Helman,Gideon Parchomovsky,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Standard.111 Colum.L.Rev.1213(2011).在上传阶段就将侵权内容过滤掉,也是防范侵权的题中之义。平台因承担主动审查义务而承担的激励损失不仅绝对值降低了,而且在与权利人激励损失的比较中,其相对值也下降了。除过滤技术之外,人工审查的成本也并非绝对居高不下,对于特定的网络服务商如视频分享网站而言,其为了满足行政管理部门的内容监管要求,必须对于网站内提供在线播放的每一个视频文件进行内容审查,所需的相关人力成本已经支出。虽然该审查本身不是为了防止侵犯著作权目的,但在进行内容审查时附加进行著作权合法性的审查,对视频分享网站而言不会增加不合理的负担。即便进行监控或审查确实会产生额外的人工成本,但其内部的人力资源等也可以进行重新分配,“通知—删除”环节中的人力资源很大一部分将转移到事前的监督环节上,因此,相对而言,其负担的成本总量并不会明显增加。Ashley Bumatay,A Look At TradeKey:Shifting Policing Burdens From Trademark Owners To Online Marketplaces.11 Hastings Bus.L.J.355(2015).质言之,网络服务商进行人工审查的成本中,有一部分属于其本应承担的行政审查义务的加强版,还有一部分则是其“通知—删除”义务的转嫁,这样一来,真正增加的成本就可以控制在网络服务商的承受范围之内。唯需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这决定了其不能像有形财产一样通过对实物的占有而彰显权利,从而使得权利的确认和侵权的判定都格外困难。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网络服务商难以判断哪些内容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也不能确定上传者是否经过了授权或者属合理使用。相反,权利人最适合处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让网络服务商负担审查义务的同时还需进行成本的合理分担而不是完全转移。
其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小防范成本理论所包含的另一个含义是,被告的防范成本应当小于预期损失,即所谓的“汉德公式”。汉德公式由美国第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在United States v.Carroll Towing Co.案中创设。该案中被告的驳船船员离开了他的驳船长达21小时,在这段时间里驳船离开了停泊处并在随风漂流的过程中恰巧与一艘油轮发生了碰撞。当时港口很繁忙,危险也很明显,因此事故损失的边际减少量很大,而船员的离开缺乏令人满意的解释暗示了注意的边际成本很低,法庭据此认定了被告存在过失。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王强、杨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汉德公式鼓励以合理的成本预防意外事故损失,因此需要就审查成本与预期损失(或因审查而产生的预期收益)进行衡量。就审查成本而言,无论是人工审查还是过滤技术都意味着网络服务商需要额外负担一定的金钱成本(包括过滤系统开发与维护、人力资源支出等等),但如前所述,此类成本可以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源重新分配而得到控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网络服务商承担的与审查直接相关的成本,还有整个社会可能为之负担的成本,审查机制的运行可能会导致合法信息被错误删除,进而威胁到用户的言论自由与个人隐私,这是对公共利益的挑战。对于此类间接成本,需要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本身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实上,言论自由并非知识产权审查独有的难题,目前正在构建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也会对言论自由造成威胁,甚至威胁更大,但以网络安全审查为代表的私人执法并不能因此而废止,参见孙禹:《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规规则— —以德国〈网络执行法〉为借鉴》,《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如果认为网络审查有其必要性,那就不能以言论自由为借口阻止知识产权审查。第二,技术的成熟和程序的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被错误删除并为信息被错误删除的用户提供事后救济。事前,无论是过滤技术还是人工审查都应当将合理使用等情形考虑在内,以比例原则对网络服务商的私权力进行适当限制。事后,可以设定类似于反通知的补救程序恢复用户的合法信息。第三,即便合法信息被错误删除,以经济分析的视角来看,同时阻止合法使用(lawful uses)和侵权使用(infringing uses)也可能会产生净福利收益(net welfare gain),尤其在以下三种情形中更是如此:其一,侵权使用造成的损害高于合法使用带来的收益;其二,侵权使用造成的损害与合法使用带来的利益相当,但侵权使用对价格更敏感;其三,创作新作品带来的激励大于阻碍合法使用所带来的损害。Douglas Lichtman,William Landes,In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An Economic Perspective.16 Harv.J.L.&Tech.404-405(2003).
就预期损失而言,如果网络服务商不主动对用户上传的信息进行审查,那就只有通过设置侵权提示、投诉举报通道等方式来预防侵权发生,但声明、提示完全靠网络用户自觉自愿配合,并没有强制约束力。用户不会因网络服务商的警示就放弃销售假货等侵权行为,由于权利人逐个维权的效率低下也使得用户存有侥幸心理甚至有恃无恐。对于权利人而言,侵权因网络传播的扩散性造成的损失往往并非微小,网络盗版盛行将导致知识产权的投资者不能收回其投入成本。当投资与报酬之间呈现显著不相当的状况时就会产生“价值差”(Value Gap),知识产权的创新激励将因此大打折扣,更有甚者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威胁。例如,在商标权领域,网络假冒产品的泛滥除了对商标权人利益造成损害之外,无疑会增加消费者筛选信息的搜寻成本,既扭曲正常的竞争秩序,实际上也损害了公共利益。在著作权领域,以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为例,其使用的ID Content系统耗费了其母公司谷歌公司5000万美元。截至2016年,版权人就其作品通过该系统获得的广告收益分成超过10亿美元。Chris Sprigman&Mark A.Lemley,Why Notice-and-Takedown Is a Bit of Copyright Law Worth Saving,Los Angeles Times,June21,2016.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sprigman-lemley-notice-and-takedown-dmca-20160621-snap-story.html.visited 20 Dec 2018.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履行审查义务带来的创新激励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往往会超过审查的成本,从而产生一个有效率的结果。然而,需要明确的是,YouTube平台上的过滤系统是其与权利人合作自愿应用的,实践中大部分网络服务商并未与权利人达成这样的协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权利人、网络用户和平台自然会通过谈判,确定平台应当承担一定主动审查义务的新秩序。不过,由于三方之间以及各方内部的交易成本都异常高昂,如果法律不干预,很难指望所有平台都会承担一定的主动审查义务。因此,以法律规则层面确立网络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仍然十分必要。
五、余 论
从国内外立法和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确立网络服务商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亦非全属纸上谈兵。尽管美国DMCA对服务商监控义务持否定态度,但就其代表性案例观察,似有“由严谨至宽松,再回归于严谨”之趋势,且相关业者于此实务发展下,亦未有因侵权责任加重,及课予监控并采取过滤机制的责任,导致其创新受阻、发展停滞不前之情形。参见蔡硕庭:《网路服务提供者侵害著作权之民事责任》,《智慧财产评论》(台北)2018年第1期。《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5条仅规定服务商“不承担监督的一般性义务”,但是此规定不涉及特殊情况下的监督义务,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完全排除网络服务商审查义务还是有所区别的。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议会于2019年3月26日通过的《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s Market)进一步限制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豁免条件。该指令第17条规定的豁免条件之一是在权利人已经提供了相关且必要信息的作品和其他内容之后,网络服务商应履行较高行业标准的专业注意义务(high industr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diligence),尽最大努力确保未经授权内容不被获取。Directive(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Text with EEA relevance).OJ L 130,17.5.2019,pp.120.这样的豁免条件将倒逼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上传的内容采取事先过滤的措施,尽管该规定是否完全合理还颇具争议,See Giancarlo Frosio,To Filter,Or Not To Filter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EU Copyright Reform.36 Cardozo Arts&Ent.L.J.331-363(2018).See T.Randolph Bearda,George S.Forda,Michael Sterna:Safe Harb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Online Platform Markets:An Economic Analysis.36 Cardozo Arts&Ent.L.J.317(2018).但也反映了强化网络服务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趋向。在德国,规定网络服务商责任的《电信媒介法》(TMG)仍然以DMCA为蓝本,但在司法实务中却通过延伸适用交往安全义务而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定位于“妨害人责任”,为其创设了“面向未来的审查义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3年的GEMA v.Rapidshare案中就指出,身为资讯储存服务中介者的Rapidshare应承担“部分主动监控义务”,有必要采取合理措施以识别特定类型非法活动,例如通过采取词汇过滤的方式来针对特定情况进行监控。Urteil des BGH vom 15.August 2013(Az.I ZR 79/12).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法院对于审查义务的态度也不像立法机关或者司法解释的起草者那样绝对地否定,如前述乐视诉视畅以及乐视诉迈奔灵动案等案件中,法院均认为网络服务商应当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因设分类频道等模式对授权进行审查,既有判例对审查义务的适度肯定也使网络服务商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
审查义务的正当性得以证成之后,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在制度层面确立审查义务的适用条件和履行规则,从而实现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在我国法律制度下的本土构建(具体规则的完善有待笔者另行撰文研究)。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分地让所有服务商对其网络上的任何信息一一审查,即所谓的“普遍审查”。事实上,任何个案中的义务都必须结合特定的主体和具体的情形加以确定,并不存在一项先验的义务。因此,有必要厘清适用审查义务的具体情形,即哪一类服务商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负担积极主动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如是否需要区分网络服务商主体类型、行为类型以及权利客体类型,这有赖于以一定标准为基础的类型化研究。另一方面,审查义务的履行需要充分考量成本和收益,即无论是审查方式的选择(人工审查还是技术过滤)、审查程度的确立(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成本分担(如权利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过滤系统的购买与维护),还是相关配套措施的采取(如为保障合理使用而为涉嫌侵权用户提供的程序救济)都应以此为衡量标准,至于具体规则的建构,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