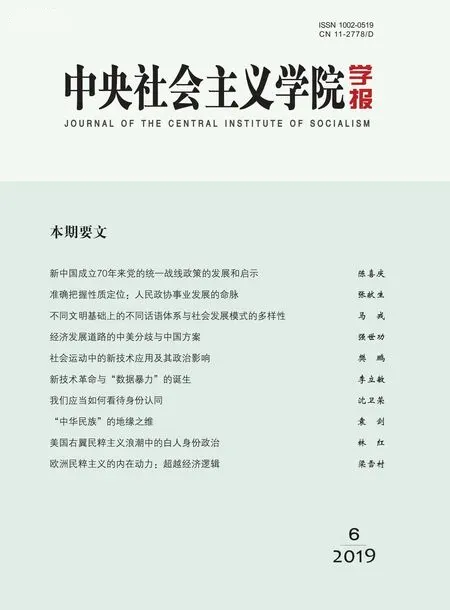不同文明基础上的不同话语体系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2019-01-26马戎
马 戎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是多元和不同步的,先后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征,包括不同的语言体系、不同的宗教和社会伦理体系、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在人类古文明体系当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延续几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在语言文字、文化伦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它与在基督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美现代文明体系、在伊斯兰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亚和北非文明以及在印度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亚文明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中华文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这与具有一神教性质并强烈排斥异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①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第151-161页。几千年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核心地区,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儒学体系始终是中华文明社会伦理的主脉。儒学体系既不排斥无神论,也不排斥其他不威胁中华文化生存、愿意接受中国社会秩序并能够与中华文明和平共存的任何外来宗教。在与其他文明体系的交往进程中,那些受到中华文明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的外来宗教群体(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逐步减弱了其排他性,并得以与中华文明主流群体和平共处、彼此融汇。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以中华文明为主脉而建立的中国各个朝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为中国留下一部未曾中断的朝代延续史。中华文明和中国各朝代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中长期发挥着引领作用,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
一、在中华文明基础上生长出的中华话语体系
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社会统治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对于生活在边缘地区或境外那些在体质、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原人群存在差异的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内部各类人际关系……中华文明都发展出自身一套基本理念与逻辑思路,产生了一套相应的概念与话语体系,如“天人合一”“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等①[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3页。,研究中国儒学、道教、佛学的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大量阐述②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68页。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71-283页。。总体而言,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一神教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征服自然界、排斥异教徒的处世理念,中华文明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社会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和谐共处。中国人信奉的是“天道”和“大一统”理念,与其他文明体之间的交往遵循的是“和而不同”原则,在对外交往中对外藩的赏赐通常超过外藩的“贡物”。中国东临大海,北面是荒原冻土,南面是热带丛林,西面是高原雪山,这片土地已足够辽阔,治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几千万乃至上亿民众,防御外敌、维护治安和组织赈灾等始终是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如果不是外敌逼迫太甚,中原王朝很少对外开拓疆土③隋朝、唐朝征服朝鲜半岛失败后,后面的朝代时常以此为戒。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列为“不征之国”。。相比之下,由边疆“蛮夷”部落“入主中原”所建立的中央王朝(如元朝、清朝)对开拓疆土还具有更多的动力。
二、西方文明进入中国
在16世纪欧洲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后,西欧各国出现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社会伦理体系和经济结构,“民族国家”成为新政治实体单元并出现了一整套新的国际秩序准则,“主权”(sovereignty)、“领土”(territory)、“外交”(foreign a ff airs)、“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y)等一套新概念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的规则。在废除了世袭封建等级制度后,欧洲社会中下层民众的聪明才智与经济活动得到发展的空间,随后的科技革命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整套各学科知识体系和相应教育制度的创建,并使欧洲发展成为经济和军事霸权国家。
西方国家来到亚洲后,用坚船利炮逼迫亚洲各国签订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通过战争手段强行打破了东亚地区的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失去了对周边各国的传统文化感召力,被迫承认中华文化传统无法抵御西方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交涉过程中完全丧失话语权和对自身传统文明的自信心,被迫放弃中华传统的“天下”理念和“华夷”秩序,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欧洲外交规则这套外来话语,从而开启了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两套思维模式和两套概念话语之间的艰难对话。
在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并开放国门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转而以全新的态度来认识西方工业文明。可以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被迫全面引进和学习在欧洲文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和一整套西方观念逻辑、表述话语、行为规则,呈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提出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的口号。
三、西方话语体系经过翻译进入中国现代话语体系
自1905年正式“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欧美国家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概念(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及专用术语)经过系统的翻译,在新开办的西式学校里被系统地介绍给中国民众。在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概念的传播过程中,明治维新后西方知识体系的日文译本成为中国人接受这一体系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在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新式的现代学校与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共同成为欧洲新知识的传播体系,欧洲各学科的经典与文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推动了中国汉字改革并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晚清时期,一些中国精英曾把英美宪政体制视为中国新生政体的效仿榜样,但随着曹锟贿选和宋教仁遇刺,推行宪政的尝试屡遇挫折。来自俄国和苏联的另一种欧洲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政治实践(十月革命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先后对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国共两党分别建立的政党体制、军队和社会组织都带有苏俄模式的深刻印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的政治理论、行政体制、社会组织和教育制度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榜样。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基本路线上发生论战,中国与苏联发展模式逐渐拉开距离。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大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或在美国大学进修,其中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回国任教。1991年苏联解体,欧美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被中国知识界视为“普世性的”科学体系并开始全面主导中国各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国的经济体制借鉴欧美的市场机制,城乡公有制经济组织逐步转型以适合市场竞争机制,中国努力融入世界经济与市场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体制改革借鉴美国大学聘任制度、教师绩效评估以美国学术期刊作为最高标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中国大学的追赶目标。
四、外来的西方话语体系能否扎根于中国本地的“水土”
但这套根植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基础的所谓“现代”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与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理念毕竟存在许多本质性的差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革命成功并建立政权,就是因为既没有走西方议会选举的政治道路,也没有走俄国十月革命“城市工人起义”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绩,也是因为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也不同于美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学和知识体系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照抄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体制。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面对的是有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西方国家的许多核心概念是很难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社会的。例如,西方话语中的party、nation、nation-state、democracy、freedom、justice、equality、right等被译为中文的“政党”“民族”“民族国家”“民主”“自由”“公正”“平等”“权利”等词汇,但中国人却很难理解这些词汇后面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文化内涵与中国社会历史传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如果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是很难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的。
五、西方的“民族”(nation)和中国的“民族”
以nation为例,汉语中通常译为“民族”。自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和媒体称呼中国具有族源、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传统的各类群体时,把这些群体都称为nation,如Manchu nation,Mongolian nation, Tibetan Nation,译成汉文就是“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等,又把中原的汉人(清朝叫“民人”)称为Chinese nation,后演变为“汉民族”。孙隆基指出:“满汉矛盾固然存在,但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甚至连‘满族’、‘汉族’这类名词也是很现代的。”①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晚清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自称“皇汉民族”(见邹容《革命军》),这就把中国传统中的群体称谓完全搞乱了。此时,梁启超只好提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区分,希望以清朝全国民众聚合为“中华民族”,以此实现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郑重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同时也称为“中华国族”。United Nations被译为“联合国”。因此,从其本意来看,“国族”应当是nation概念应用于中国的最合适的译法。
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提出中华民族内部的满蒙回藏等群体应被称为“宗族”③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回民是“有特殊生活习惯之国民”。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④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3-785页。顾先生希望以此凝聚全国各族民众共同抗日。而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后,参照苏联模式,把中国境内在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与汉人有差异的都称为“民族”。1949年后通过“民族识别”认定了56个“民族”,为每个国民确定的身份中有“民族身份”,并为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自治地方”,制定并实施了多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集体性优惠政策。这一整套概念与思维逻辑与几千年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有教无类”理念和划分群体时所遵循的“华夷之辨”逻辑全然不同,强化了各族群之间的人口边界、身份差异和政治意识。中华文明传统中本来没有西方nationalism(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但近代西方概念体系特别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并产生或引发了民族领域的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面对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的与nationalism相关的社会动荡,中国学者必须深刻探讨西方的nation话语体系及相关概念的来源与内涵,分析这一话语体系被“移植”到非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后引发的社会效果。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对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本土的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西方基础概念和分析逻辑的系统性反思,提出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各群体和谐相处并共同繁荣的相关理论和社会发展模式。
六、西方知识话语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适用于中国土壤
除了nation(民族)问题之外,中国学术界需要对鸦片战争后系统引入中国的一整套源自西方文明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意愿,那么,个人意愿与群体和社会的意愿冲突了怎么办?“民主”强调的是决策的投票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多数人的判断是错误的怎么办?“平等”强调的是个人所获机会与报酬的平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中国古代贤哲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权利”强调的是每个个体通过法律如何捍卫个人权利,那么,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有哪些应尽的义务?我们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和先进之处,但是决不能简单地照搬和“依样画葫芦”。
在我们开展这一反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与中国社会发展史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其成功之处并独具特色的。我们看到其他古代文明都先后中断,群体之间的互相征伐和宗教战争多次造成人类文明的浩劫,但是,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二十五史几千年延续至今。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知识宝库。中国历代典籍中关于天道、秩序、人伦、信仰、征战、法律等论述中有许多精髓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发掘和思考,思考为什么中原群体可以逐步吸收融汇周边各个人群,最终形成一个几亿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实体。“汉族”绝对不是西方词汇中的nation, 虽然我主张把56个“民族”这个层面改称“族群”,但是我们也无法把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融汇了周边许多群体、规模达到13亿的汉人群体视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群体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简单地把目前讲汉语的庞大人群称为“汉族”,在结构上与赫哲族、布朗族等并列为56个“民族”之一,这近乎玩笑。1949年后,中国参照苏联马恩列斯编辑局的英文译法,曾长期把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译成nationalities。而国际通常的用法,nationality 被理解为国籍,这在今天各国护照上都有清楚的显示。如美国护照上的nationality一栏必须填写“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国护照上的nationality一栏必须填写“CHINA中国”。换言之,无论是西方的nation(民族或国族)、ethnic group(族群),还是nationality,都不能清楚地表明中国14亿国民的内部结构。那么,长期以来我们采用西方(欧美、苏联)的“民族”话语并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建立的制度与政策,难道不需要对之进行反思吗?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源自西方并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占据权威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概念话语进行系统的反思:每一个关键的西方概念的原意及其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当前的译法是否得当?这些概念和分析逻辑在被运用到分析和理解中国社会时,都出现了哪些问题?西方国家在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方面,在现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创建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我们无疑需要充分尊重西方知识体系和这一知识体系在西方社会实践中带来的成果与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进行上述理论反思时,同样需要坚持从中国现实社会矛盾和各种客观现象出发,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努力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重新思考和借鉴中国历史上用以表述政治体制、群际关系、人际关系时使用的那些带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深刻理解这一知识体系中蕴涵的中华文明体系的传统智慧,以此作为我们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参照系。
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西方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的比较研究中整理归纳出既能继承中华文明传统精华、又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一套新世纪的中国话语,用它来讲述历史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人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故事”才能真正讲好。西方人在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建设他们的未来,中国人在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建设我们的未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加和谐,和平才有可能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才有可能真正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