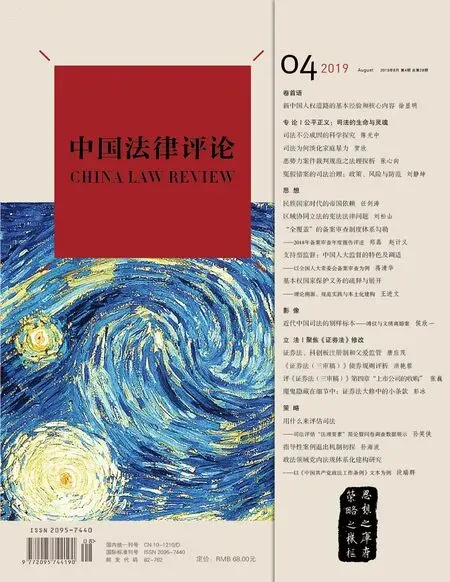评《证券法(三审稿)》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
2019-01-25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张 巍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一、大额持股信息披露
《证券法(三审稿)》第71条涉及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这一稿可谓迄今最严格的披露规则。自“宝万之争”激起中国资本市场上敌意收购的千层浪之后,如何监管敌意收购也是这几年的一个热点话题,笔者曾发表过一些拙见。1张巍:《美国的上市公司收购防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黄红元、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第十九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153页。应当认识到敌意收购可以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在设计可能阻碍敌意收购的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时须特加谨慎。
大额持股信息披露制度发源于美国,故此,在制定中国的相关规则时借鉴美国的经验,十分必要。笔者曾撰文介绍美国因何建立,又如何执行此项制度。2张巍:《资本的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三十五、三十六节。概括而言,美国对于大额持股信息披露的态度大体可以用三个词概括,那就是“例外”、“中立”和“轻罚”。
“例外”者,大额持股信息披露乃是要求外部投资人向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人披露信息,实为证券法披露原则之例外。 “中立”者,立法在敌意收购人与目标公司管理层之间居中而立,不采取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故此,在规则设计之初,美国就放开了口子,在达到5%的披露触发点之后,并不要求立即披露,相反给予外部投资人十天继续增持的机会。“轻罚”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于违反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者通常只是命令禁止再犯并外加罚款,且数目不大。3比如SEC近年的处罚案例In the Matter of Shuipin Lin,被处罚人未按规定披露持股长达数年,且有其他违规行为,SEC仅合并处罚3万美元,见https://www.sec.gov/litigation/admin/2015/34-74497.pdf。美国法院对违反此项信息披露要求者处以比较严厉的吐出获利(disgorgement)的仅有一例——SEC v. First City Fin. Corp., Ltd., 890 F. 2d 1215 (D.C. Cir. 1989)。此外,对于漏报一致行动人集体持股,或者不当采用要求较低的13G披露的情况,SEC也大多不作严惩,甚至不作任何处罚。4Stephen Bainbridg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3rd ed.), Foundation Press (2012); Kristin Giglia, A Little Letter, a Big Difference: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o Possible Misuse of Schedule 13G/13D Filings, 116 Columbia Law Review 105 (2016).如第71条新增的36个月剥夺投票权这种极刑,SEC和美国的法院几乎不取。有鉴于这种平衡的政策考虑,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授权SEC修改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包括缩短披露期限,然而将近十年过去,SEC却迟迟没有动手。
虽然美国也要求跨越5%界限的大额持股者对此后每1%的持股变动及时作出披露,但是,中国原来继受自英国及香港的5%“急刹车”,原地立定三天不许买卖,本就较美国制度苛严,倘若再加上剥夺表决权三年的制裁,恐怕制度本身已经可数全世界最严。如果对比分析英美制度,英国虽然对敌意收购人课以较为严格的持股信息披露义务,而其同时也禁止目标方管理层采用抵御措施,可谓一个两头皆严的制度;反之,美国则是两边都宽,既放松对敌意收购人的持股信息披露,也放宽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抵御限制。因此,无论英制还是美制皆有其内在的平衡。而中国的制度则是对敌意收购者甚严,却对目标公司抵御未加足够限制,由此恐令制度失衡。
此外,第71条的严格披露制度既然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这一章中,那么,需要如此进行披露的就应当是“有意”收购上市公司——或者至少影响上市公司经营决策——的投资人。换言之,对于没有这种意图的投资人,也没有理由对其适用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第71条规定的持股5%就要披露,接下来每1%变动要报告,每5%变动要再停三天的规则,对以投资上市公司股票为日常业务而无意影响上市公司经营决策的消极投资人,无疑增加了巨大负担。这一点对指数基金等公募基金影响尤为明显。同一管理人旗下的各只基金若是被视为一致行动人,那么几乎管理人层面在每个上市公司的持股都能达到大额持股披露的标准,因此,只要有任何基金合计的持股变动超过1%就得报告,超过5%则所有基金要停三天。即便不考虑合并计算问题,单只基金在某些上市公司中持股超越5%也非罕见,于是也得忙于申报披露。
或许有人认为可以借助证监会的行政规章直接豁免公募基金的大额持股披露义务。然而,事情也许并不这么简单。一方面,上面提到的披露负担并非公募基金独有,只要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多只基金可能被视为一致行动人,而这些基金的常规业务就是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那么,无论公募、私募,都会陷入第71条规定的繁重的信息披露负担。另一方面,假如立法者希望增强上市公司持股信息的透明性,那么,简单豁免这些基金的披露义务也会削弱这种立法目的,尤其是当这些基金大比例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之时。
对此,美国的多层次持股披露制度很值得参考。美国的证券监管规则根据持股的数量、目的,对持股人的义务区别对待,分别作出13D、13G和13F披露。不同种类的披露在披露时机和披露内容上有很大差别,基本满足了各类基金等机构投资人的实际需求,也为市场提供了适当的持股信息。择要而言,13D披露需在持股达到5%后10日内作出,且披露内容较多,特别是持股者的目的以及今后的计划,甚至包括与取得股票及其相应权利相关的各种协议、安排。13G披露通常只需在每个自然年结束后的45日内作出,5倘若持股增至10%以上,则需于10日内更新披露。并且13G的披露内容比13D简单得多,主要关于持股者的身份、持股种类及数量。13F则是基金等机构投资人每季度定期披露的多头持股信息,披露时间为每季度结束后的45日内,披露内容与13G类似。有关各类披露的具体要求,可以参考SEC的详细说明。6参见SEC官方网站:https://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guidance/reg13d-interp.htm; https://www.sec.gov/divisions/inv estment/13ffaq.htm,2019年6月20日访问。当然,美国人的经验也是随着岁月累积而来,从13D到13F用了7年,713F披露要求始于1975年。而到目前的13G,整整花了30年813G披露要求始于1977年,目前的规则确立于1998年。——别人花这样长的时间凝聚起来的经验正好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综上所述,建议删除第71条第4款,同时将第71条的披露义务人范围限于有收购或影响公司经营活动之意图者。至于无此意图者的持股披露,可以授权证监会另行制定低于第71条要求的规则。
二、要约收购义务人
《证券法(三审稿)》第73条规定要约收购义务人为持有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30%的股东,其中“有表决权”几个字为新增。这一修正的意图或许在于和科创板同股不同权制度相配套,不过,科创板规则并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发行没有表决权的股票,因此,此四字新增的实际意义不明。
然而,第73条并没有填补现行强制要约规则的一个漏洞。现行的要约触发条件只看收购人取得的“股份”比例,第73条继承了这一态度。可是,在实践中时有出现股东通过表决权委托协议将表决权转让给他人,9参见蒋学跃:《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问题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5期。这种情况下,虽然“股份”并未易手,而这些股份代表的对公司的控制权实际已经易手。既然强制要约制度的目的是让非控股股东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时,有机会分享控制权溢价或者选择退出,10马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制度解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那么,其触发条件自然应当以作为控制权之基础的表决权比例为准,而非名义上的股份持有比例。实际上,将拥有的表决权比例作为确定强制要约义务人的标准也是此项制度发源地英联邦(Common Wealth)各国的通例。11例如新加坡《收购法典》(Takeover Code)第14.1条。据说,实务中已经有将“股份”当作“表决权”的做法,倘若如此,则此次修法更应予以明确,以消除法律与实务的鸿沟。
在科创板允许双重股权架构公司上市之后,强制要约的义务人或许出现了新问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票虽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却可以其他方式转让,而一经转让,特别表决权即转化为普通表决权。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假如有第三方希望取得同股不同权公司的控制权,必定要与特别表决权股东协商取得其股份,即便转让之后特别表决权消失也是如此,否则不可能取得控制权。此时,纵然转让之后特别表决权股会变成普通表决权股,但相信特别表决权股东不会愿意以普通表决权股的价格出让其股票,而会索取控制权溢价。
那么,这种溢价是不是需要与其他股东分享?如不分享,则根本违反强制要约的初衷。举轻以明重,既然没有特别表决权的控股股东在转让控股权时,中小股东尚且可以分享控制权溢价,那么,有特别表决权的控股股东出让控制权的,又为何不许其他股东分享溢价?如果要求分享,则需要将“强制要约义务人”规定为“取得股份转让之前上市公司30%表决权”的投资人。可是,倘使真作此规定,则协商购得特殊表决权股的买家不免会觉得冤枉——明明自己购得的股份表决权可能远远不到30%,还需要大量购进其他股东的股票方可取得控制权,却被视同已经获得控制权者同样对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从前双重股权架构盛行的美国并无强制要约制度,而移植到有此制度的法域后,两种制度如何衔接恐怕尚待思虑。
为此,建议将第73条的强制要约义务人改为取得代表已发行股份30%“表决权”者,至于具有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如何适用强制要约义务,可留待日后证监会另行决定。换言之,就是暂缓将强制要约用于双重股权架构公司。实际上,在上市早期,特别表决权股东主动退出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此,暂缓适用以便继续研究也是可行的方案。
三、要约公告事项
《证券法(三审稿)》第74条没有对收购要约的公告事项作出改变,原有规则基本可行。不过,笔者建议增加披露与要约相关的协议、安排之全文的要求,以便市场投资人更好地判断要约完成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安排包括触发强制要约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融资协议,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附属协议。实践中曾有出现因为触发要约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履行而终止要约的情况,如熔盛重工放弃收购全柴集团、天元锰业中止收购英力特等,给公众投资人造成一定损失。披露这些与要约相关的协议、安排,有助于市场认清要约涉及的风险,做好应对措施。
四、修改要约条件
《证券法(三审稿)》第76条限制了要约人对要约条件的修改权,特别禁止反向修改原有条件。这种限制或许对保护公众投资人有一定帮助,不过,也可以预期要约人因此采取预防性措施,相应降低初始要约价格、减少初始要约数量、缩短初始要约期限。另外,本条并未包括对要约成就条件的修改,因此,收购人仍有机会通过改变成就条件,一定程度实现对原要约条件的反向修改。比如通过提高要约成就所需达到的接受要约的比例,12举例而言,要约人收购40%股票,原先约定只要出售股票的比例超过20%,要约人就需要接受全部出售的股票(以40%为限),后修改要约成就条件为出售股票的比例超过30%。假如最终出售股票的比例是25%,根据修改后的条件,要约人可以不收购任何股票,而依据原来的条件则需要买下这25%的股票。可以起到类似于减少初始要约数量的作用。笔者认为,这种修改要约成就条件的做法,至少和强制全面要约给予中小股东分享溢价和退出机会的意图不符,在强制全面要约中应予禁止。至于在部分要约中是否要禁止,则要看立法者有多大意愿杜绝反向修改要约条件的情况。
有关修改要约条件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敌意收购中,当目标方采取抵御措施时,要约方可否突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现行要求,在要约的最后15日内提高收购价格,或者增加其他有利的收购条件?这个问题在中国首起成功完成的敌意要约收购——浙民投收购ST生化——过程中被凸显出来。
ST生化的大股东在要约期限的最后几天提出转让自己的股份,实际上是想利用看上去超过要约价格的转让价格来打压要约成功的可能性,而其转让的对象当然是与大股东友善的“白衣骑士”。根据现行的收购规则,由于未出现竞争要约,收购方无法以修改要约、优化收购条件来应对。站在保护中小投资者以及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的立场上,似乎没有理由禁止收购方作出这种改变。换言之,应当将目标方采取抵御措施与出现竞争要约并列,作为允许要约方在要约期满前15日内优化要约条件的情形。当然,这一点可以借助修改收购管理办法来实现。
对于本条,建议明确依法发起全面要约者不得对要约成就设定条件。同时,有必要考虑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40条,扩大允许在最后15日内正向修改要约条件的范围。
五、不同种类股份的收购条件
《证券法(三审稿)》第77条新增一款,规定上市公司发行的不同种类股份可以适用不同的收购条件。此款乍看似乎是为科创板的双重股权架构公司所设,可细思量也许不是那么回事。首先,上交所的科创板规则已经明确特别表决权股不得在二级市场交易,由此,特别表决权股实际上也不太可能上市——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13在200多家同股不同权公司中,超级表决权股上市的只有15家(Andrew William Winden, Sunrise, Sunse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ssessment of Dual-Class Stock Structures, 2018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852 (2018))。何况,美国还没有超级表决权股不得在二级市场交易,且一经转让即转变为普通表决权股的规定。于是,第77条讲的要约收购不能适用于主动要约收购特别表决权股的情况。
其次,如果在强制要约情况下,对未上市流通的股票也可以发出要约,并且这些股票的持有人也可以接受要约,那么,此新增的一款似乎可以适用于如下情形,即收购人先收购到了30%的普通表决权股,由此触发强制要约义务,于是其同时向特别表决权股股东以及剩余的普通表决权股股东发出要约,而针对这两类股票的要约条件有所不同——照常理应当是给特别表决权股的条件更优。可是,实践中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十分可疑。意图取得双重股权架构公司控制权的人,假如不事先与特别表决权股东达成协议,实际上很难取得控制权。而倘若已经与特别表决权股东达成了协议,恐怕也就不会再如此迂回激发强制要约。
不过,即便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立法上应当如何处理,仍旧需要考虑。根据目前第77条第2款的思路,要约人以高溢价收购到的特别表决权股在收购完成之后几乎没可能保留控制权,而真正帮助收购人取得控制权的普通表决权股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溢价,等于让特别表决权股东独占控制权溢价。14当然,普通表决权股东预计到收购人无从单靠收购超级表决权股实现控制权移转,也会因此趁机提高要价。对此,需要借助博弈论模型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其最终结果也有可能是收购方必须按同等条件收购各类股票方才可以获得控制权。这个有趣的问题留待继续研究。如此结果是否有悖强制要约制度的初衷?总之,如前文所言,有关双重股权架构与强制要约规则如何结合的问题尚有待思虑,不宜轻易作出规定。
再次,如果第2款讲的是通过协议收购特别表决权股,那么,目前的规则下协议收购与要约收购原本就可以有不同条件。比如协议收购到20%的股份,再发部分要约收购10%的股份,此前后两项收购的条件就可以不同。反过来,如果先要约收购10%,再协议收购20%,两者的条件依然可以不同。当然,现行规则下,要约收购在后的,其价格通常不能低于在先的协议收购价格(除非两者间隔超过6个月)。假如新增这一款是专为针对协议收购特殊表决权股在先、要约收购普通表决权股在后的情况下,放宽后者价格不得低于前者的限制,那么,第77条第2款目前的文字完全不能体现这种意图。
最后,倘若此款与同股不同权无关,而专为同时发行A股与B股的公司而设,那么,一则目前尚未出现过同时要约收购A股与B股的事例;二则从同时吸收合并A、B股的实际操作看,赎买A股和B股的对价——包括溢价比例——原本就不相同。
为此,建议删除第77条第2款。假如此款专门为明确同时要约收购A股与B股的要求而设,则只需在第1款后半分句添上适用于被收购公司“同类股票”的所有股东即可。
六、上市公司分立、合并之事前行政许可
《证券法(三审稿)》第85条为新增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在分立、合并之前先取得行政许可。笔者认为,对于上市公司的合并许可没有太大意义,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如果A公司收购上市公司B的全部股票,使B成为A的全资子公司,却不将B吸收合并,实际效果和A吸收合并B一样。而根据第85条,让B成为全资子公司无需许可,而吸收合并却要许可。不难想象,此种情况下,只会有更多的收购者选择全资控股,而非直接合并上市公司。
再退一步说,如果上述A公司不收购上市公司B的全部股票,而只是收购其控制权,根据第85条仍旧不需要事前行政许可。然而,从交易实质看,大股东部分控股比完全私有化更可能危害中小股东利益。留着中小股东正好剥削宰割,而私有化了一切都归自己,也宰割不到别人。所以说,假如第85条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恐怕反成南辕北辙。类似地,假如合并交易中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还是要靠许可之外的其他制度加以限制,那么,分立交易中的这种侵害同样也可以依赖类似制度解决,依然不需要额外附加事先行政许可。
对于这一条,立法者或有必要先明确立法目的,随后再分别考察,为实现此等目的,上市公司分立与合并有无事先审查之必要。如果只是为保护中小投资者,那么,笔者建议删除此条。
总体而言,除大额持股信息披露之外,本章对现有制度并未有太多改变,而大额持股信息披露制度的改变方向不无疑问。此外,要约收购制度如何与双重股权架构相衔接,尚无成熟经验可以参考,值得立法者仔细考虑,在得出妥善结论之前,暂且不宜将强制要约适用于同股不同权的公司。最后,中国的上市公司收购制度本身或许还待通盘考虑,尤其在注册制全面推行之后,仍有必要对收购制度作出全面变革。鉴于此,建议此次证券法修正尽可能对上市公司收购规则少作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