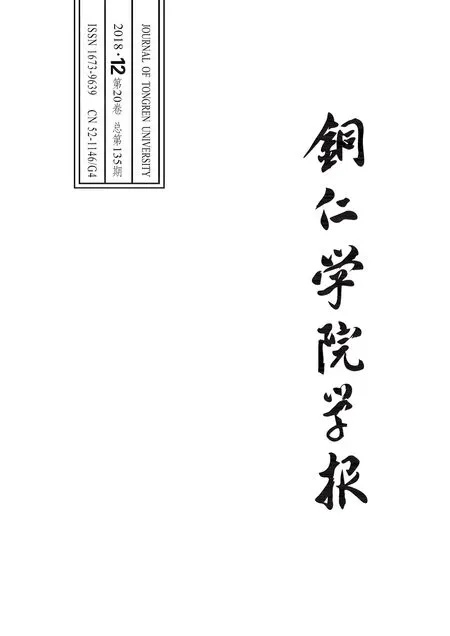中古开合到今音四呼不规则变异探析
2019-01-21曹利华
曹利华
中古开合到今音四呼不规则变异探析
曹利华
(攀枝花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开合”是描写汉语韵部发音状况的一组对称系统,是语音性质的重要区别性特征。以《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所收例字为对象,从历时角度纵向分析中古开合至今音四呼的流变情况及一般规律,重点探析不合一般规律但仍有据可循的语音演变情况。
中古音; 开合; 四等; 四呼
开合是描写汉语韵部发音状况的一组对称系统,是语音性质的重要区别性特征。我们从历时角度纵向分析中古开合至今音四呼的演变情况及其条件、规律,重点分析不规则演变及成因。这里把比较的重点放在中古汉语与现代标准语上,而跳过近代汉语时期。因为近代音是中古音的简化结果,是现代音的早期形式,明白了中古到现代的情况,近古的情况就不期而然地提到了;另外,《广韵》承袭《切韵》又“务求赅广”,语音囊括“古今南北”,现代音的来源差不多都可以从《广韵》找到根据,二者具有可比性。
一、“开合”“四等”相关概念
(一)“开合”名称及由来
“开口”、“合口”之称已被《广韵》末所附《辨十四声例法》采用。所谓的“十四声”指:开口声、合口声、蹴口声、撮唇声、开唇声、随鼻声、舌根声、蹴舌下卷声、垂舌声、齿声、牙声、腭声、喉声、牙齿齐呼开口送等诸声。或指声母,或指韵母,或指韵尾,非皆音呼之法。单看“开口声、合口声”也标准不一:“开口声,阿哥河等并开口声,合口声,庵甘堪谙等并是合口声”[1],前者指以[ɑ]为主要元音的韵,后者则指收[m]尾的“闭口韵”。
一般认为陆法言《切韵》已将一些韵按开合分立,孙愐《唐韵》又进一步分别开合,到《广韵》已有十三处分立,等韵图中则贯彻开合分图的原则。并且中古韵书之反切对开合之别也作了严格区分,高本汉(1926)考察“三千多个反切之开合都是正确的。”[2]总之,中古时期对汉语韵部发音状况的区分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那就是当时等韵图①所体现出的“两呼四等”。正如戴震《声韵考》所云:“郑樵本《七音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音声洪细,别之为一、二、三、四等列,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依次审定部分。”[3]
不过古人主要是凭听感作出的直觉判断,未把[u]介音离析出来。即使是明清时期的音韵学家也只是根据唇形和听感体验来区别两类韵母。如王国琚《读等韵及反切门法合解》曰:“开口呼者,口开呼气,而字即出也。”吕维祺《同文铎》云:“七音虽同,而有开口合口之不同,开口者其声单而朗,合口者其声骈而浑。”江永《音学辨微·七辨开合口》云:“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
“若以今语释之,则介音或主要元音有[u]者谓之合口,反之,则谓之开口;实即圆唇与不圆唇之异而已”[4]。对“开合”的认识各家观点基本一致。即开合的区别在于介音或主要元音是否圆唇,介音或主要元音是[u]者为合口。
另外,对开合的认识也有人持“介音说”或“声母唇化说”,不过二者都有疏漏之处。前者,以是否有[u]介音作为区别开合的唯一标准,对无介音的一等韵则不能区分;后者则认为开合之分在于声母是否唇化,这又很难解释韵书中开合同韵的事实。
(二)“四等”“洪细”
谈“呼”必涉“等”。“等”是与“呼”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音韵学术语。
旧来论“等”者,以清代江永、陈澧之说最精。江永《音学辨微·八辨等列》是这样解释“等”的:“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他所谓的“洪细”是就韵母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而言的,具体讲“洪”指一、二等韵,“细”指三、四等韵。“洪细”与开合相配便有了“开合洪细”之称。
现代语音学解释,就是把韵母中的元音及介音按发音差异分为四个等列,纳入汉语所有韵母。一等韵、二等韵,无[i]介音,主要元音发音时前者开口度最大舌位较后,后者开口度次大舌位较前;三等韵、四等韵,韵母中有[i]介音,主要元音发音时前者开口度较小舌位在前,后者开口度最小舌位最前。简言之,“等”指介音[i]的有无及元音之翕侈。
宋元等韵学所反映的中古音之等呼格局是“开合四等”。至明清,语音实际已经明显的发生了变化,开口四等、合口四等不复能辨,于是并等立呼。
二、中古开合到今音四呼之流变
对开合至四呼的演变,我们以开合为纲,共分八类,分别探讨中古开口一、二、三、四等,合口一、二、三、四等,与现代汉语四呼的对应关系及背离演变规律的特殊现象。
具体做法是以《汉语方言调查字表》[5]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6]为依据,以《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所列全部例字为调查对象,比较它们的中古音与现代音,考察中古开合四等到现代四呼之流变。中古音的声韵地位及声韵拼合关系以《汉语方言调查字表》为基准,将中古声母分为四系十二组,即帮系,帮滂并明、非敷奉微两组;端系,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邪三组;知系,知彻澄娘、庄出崇生、章昌船书禅、日四组;见系,见溪群疑、晓匣、影喻三组。韵摄则按无韵尾、元音韵尾、鼻音韵尾顺序排列,囊括全部16摄、206韵。一般举平以赅上去,入声韵单列。
(一)中古开口一、二、三、四等的语音流变
中古开口一等字,分属果、蟹、效、流、咸、山、臻、宕、曾9摄的歌、咍、泰、豪、侯、覃、谈、寒、痕、唐、登11韵(举平以赅上去入,下同)。中古开口一等韵只能与帮、端、见三系中的帮、端、泥、精、见、晓、影七组声母相拼,而不与知系、非组声母相拼。就所与相拼的声母系组而言,只有果摄歌韵端组、泥组、见组字和宕摄铎韵端系(端组、泥组、精组)字今读合口[uo]韵,如“多、挪、我,托、诺、作”,其余可拼合者一律读开口呼,如“贝、刀、楼、高、杂、喝、恩”等。可见,中古开口一等演变为现代开口呼这一规律是很明显的。
中古开口二等字,分属于假、蟹、效、咸、山、江、梗七摄,麻、皆、佳、夬、肴、咸、衔、山、删、江、庚、耕12韵。中古开口二等韵可以和帮、端、知、见四个声系中的帮、泥、知、庄、见、晓、影七组声母相拼。就调查情况看,中古开口二等字今多开口呼,只有见系字今多读齐齿个别读撮口,江摄知系字今读合口。具体为:
(1)帮系。今多读以[a]为主要元音的开口呼,如“巴[pA]、排[pʻai]”。只有江摄入声今读[o][u]韵,如“剥[o]、驳[po]、檏[pʻu]、朴[pʻu]”。
(2)端系。只有泥组字,今全读开口呼。如“拿[nA]、攮[nɑŋ],冷[lǝŋ]、棚[pʻǝŋ]”。
(3)知系。今多读开口呼。如:“钗[tʂʻai]、橙[tʂʻǝŋ]、泽[ʦɤ]”。只有江摄今读合口,如“桩[tʂuɑŋ]、窗[tʂʻuɑŋ]、桌[tʂuo]、捉[tʂuo]”。
(4)见系。中古开口二等字的今音读法较复杂。多读齐齿呼,如“家[ʨia]、交[ʨiɑu]、谐[ɕiɛ]、鞋[ɕiɛ]”。一部分读与之相应的开口呼,如“搞[kau]、扛[kʻɑŋ]、格[kɤ]、更[kǝŋ]”。而部分觉韵字读撮口或合口,如“觉[ʨyɛ]、学[ɕyɛ]、握[uo]、桌[tʂuo]”。
中古开口三等韵遍及十六摄中的十三摄,只有仅具合口的“通”、“遇”两摄和仅具二等的“江”摄没有开口三等字,再具体点说,只有“东、冬、钟、江、鱼、虞、模”七韵没有开口三等字。开口三等和声母有着广泛的拼合关系。开口三等可以和帮、端、知、见四系中,非、端两组以外的十组声母相拼。以所与拼合的声母系组而言,中古开口三等字有如下演变:
(1)帮系。帮组,今多读齐齿呼,如“蔽[pi]、彪[piɑu]、别[piɛ]、禀[piŋ]”。只有止摄支、脂二韵和流摄尤韵有读开口呼或合口呼的情况,如“碑[pei]、悲[pei]、矛[mɑu]、浮[fu]”。
(2)端系。今多读齐齿呼,如泥组的“例[li]、燎[liɑu]”,如精组的“尖[ʨiɑn]、接[ʨiɛ]”。而止摄今读开口呼,舌尖前音[ʦ] [ʦʻ][s]后读[ɿ],舌尖后音[tʂ][tʂʻ][ʂ]后读[ʅ],如“资”[ʦɿ]、知[tʂʅ]”。山摄入声薛韵的“薛 [ɕyɛ]”字,臻摄真韵的“讯”[ɕyn]字今读撮口呼,算是例外。
(3)知系。今一律读开口呼,如庄组的“筛[ʂɑi]、衬[tʂʻən]”,章组的“毡[tʂɑn]、折[tʂɤ]”,日组的惹[ʐɤ]、柔[ʐou]”。而流摄尤韵“漱”[ʂu],宕摄阳韵“庄”[tʂuɑŋ],宕摄阳韵“饷”[ɕiɑŋ],入声药韵“酌”[tʂuo],假摄麻韵“爹”[tiɛ]等字例外。
(4)见系。今多读齐齿呼。如“洁[ʨiɛ]、脚[ʨiɑu]、牺[ɕi]、枵[ɕiɑu]、耶[iɛ]、移[i]”,宕摄入声药韵“酌”[tʂuo],山摄元韵“轩”[ɕyɑn],宕摄入声药韵“约”[yɛ]等字例外。
可见,除宕摄和极个别例字,中古开口三等韵,帮、端、见三系今音韵母读齐齿呼,这合乎“中古开口三等→今音齐齿呼”的演变规律;中古开口三等知系今韵母读开口呼。总之,《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收录1218个开口三等字,演变为今音韵母的情况是:713字今读齐齿呼,占总数的三分之二;29字今读合口呼,14字今读撮口呼,齐撮两呼字数很少可以忽略不计。463字读开口呼,其中有422字为知系字。故可以笼统地说,中古开口三等知系声母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读开口呼,其余各声系都读齐齿呼。
中古开口四等韵,只有蟹、效、咸、山、梗五摄的齐、萧、添、先、青五韵,可与帮、端、见三系的声母相拼。中古齐、萧、添、先、青五韵今全读齐齿呼,各举两例如“蓖[pi]、低[ti],刁[tiɑu]、聊[liɑu],谦[ʨʻiɑn]、嫌[ɕiɑn],边[piɑn]、肩[ʨiɑn],姘[pʻin]、瓶[piŋ]”。“壻[ɕy]”“吃”[tʂʻʅ]两字例外。可见,开口四等字的语音演变基本上是遵循“中古开口四等→今齐齿呼”之规律的。现代基本可以按中古开口四等各韵目的今音读法,去读所有的中古开口四等字。
(二)中古合口一、二、三、四等的语音流变
中古合口一等字,分属果、遇、蟹、山、臻、宕、曾、通八摄中的戈、模、灰、桓、魂、唐、登、东、冬九韵。中古合口一等韵与声母的拼合关系,与开口一等韵完全相同。即只能与帮、端、见三系中的帮、端、泥、精、见、晓、影七组声母相拼,而不与知系和非组声母相拼。中古合口一等韵就所与相拼的声母系组而言端系、见系今多读合口呼,“徒[tʻu]、朵[tuo],过[kuo]、姑[ku]”,戈韵极个别读[ɤ],如“科[kʻɤ]、和[xɤ]”。帮系只有帮组字,且古今演变规律复杂,部分今开口,如“杯[pei]、般[pan]、奔[pǝn]”;部分读合口[u],如“铺[pʻu]、不[pu]”;部分读齐齿,如“拼、坯”。
可见,中古合口一等字,在现代普通话中绝大多数读合口呼。《字表》所收519个合口一等字中,有414个今读合口呼,占80%。只有帮组和个别泥组字今读开口呼。没有读齐、撮二呼的(坯、拼二字例外)。可见,中古合口一等到今音的演变还是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的。
中古合口二等字,《字表》所列仅72个,它们分属假、蟹、山、梗四摄的麻、皆、佳、山、删、庚、耕七韵。依《字表》所列,中古合口二等韵只与知系庄组和见系相拼。今音几乎全读合口呼,且绝大多数是[a]为主要元音。(“傻、横”两字例外)具体为假摄,今读合口[ua],如“耍[ʂua]、夸[kʻua]”。蟹摄,今读合口[uai]和[ua],如“乖[kuai]、怀[xuai]、挂[kua]、画[xua]”。山摄,舒声今读合口[uan],如“鳏[kuan]、关[kuan]”;入声,今读合口[ua],如“滑[xua]、挖[ua]”。梗摄,舒声,今读合口[uɑŋ][uŋ],如“矿[kʻuɑŋ]、轰[xuŋ]”(“横[xəŋ]”例外),入声,今读合口[uo][ua],如“虢[kuo]、划[xua]”。
合口三等韵与开口三等相比多通、遇两摄,少效、流、深三摄,共遍及过、遇、蟹、止、咸、山、臻、宕、曾、梗、通11摄。就所与相拼的声母讲,合口三等与开口三等基本一致,都能和帮、端、知、见四系中的十组声母帮、泥、精、知、庄、章、日、见、晓、影相拼。只是开口三等与帮系的帮组相拼,合口三等与帮系的非组相拼。演变规律如下:
(1)知系。今毫无例外全读合口呼,如“初[tʂʻu]、所[suo]”。
(2)见系。今多读撮口呼,如“迂[y]、悦[yɛ]”。止摄止、脂、微三韵今读合口[uei],如“龟[kuei]、麾[xuei]”。山摄仙韵,梗摄清、昔两韵,通摄东韵的个别字今读齐齿呼,如“沿[iɑn]、倾、疫、嗅[ɕiu]”。
(3)端系。今多都齐齿、撮口二呼。如泥组“恋[liɑn]、隆[luŋ]”,精组“嘴[ʦui]、全[ʨʻyɑn]”。止摄止、脂二韵今读开口[ei],如“累[lei]、垒[lei]”,属例外。
(4)帮系。合口三等韵只与帮系的帮组声母相拼,今多读主要元音为[ɑ][ə]的开口呼,如“凡[fɑn]、分[fən]”。语音演变比较复杂最不合规律。
中古合口四等只有蟹、山、梗三摄中的齐、先、青三韵,《字表》仅收21字。合口四等韵只与见系声母相拼,故合口四等字的音节较少,《广韵》仅收录290字,占总字数的1.14%。中古合口四等今读作合口或齐齿。具体为齐韵,或读合口[uei],或读齐齿[iɛ][i],如“圭[kuei]、携[ɕiɛ]、畦[ʨʻi]”;先韵,舒声今读撮口[yɑn],入声读[yɛ],如“犬[ʨʻyɑn]、穴[ɕyɛ]”;青韵,舒声《字表》仅收见系“萤[iŋ]、迥[ʨyŋ]”两字,分别读齐齿呼、撮口呼,入声则无合口四等字。
以上我们对中古开合与现代四呼之流变关系做了详细描述。最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就是:中古的开口一二等今读开口呼,开口三四等今读齐齿呼,合口一二等今读合口呼,合口三四等今读撮口呼,尽管尚有许多变通之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今音开齐合撮四呼上溯中古开合四等。
(三)今音四呼上溯中古开合及对应关系
以下列表展示从今音四呼上溯中古音开合的情况,用“+”号表示符合一般规律的情况。对不符合一般规律的,分两种情况处理:属于一类现象的附今韵母,属个别现象的列例字1个。
以上,我们对“中古开合——今音四呼”,分别从古至今、从今溯古互求,可见语音演变的规律是很明显的,即开口一、二等今为开,合口一、二等今为合,开口三、四等为齐,合口三、四等为撮。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韵类都是如此演变,还有一些韵类演变方向不合一般规律,以下分论之。
三、中古开合到今音四呼之不规则演变探析
中古开合到今音四呼,“不规则”的演变也并非无缘无故的。任何“不规则”的变化都有其具体原因,都是受特殊因素的影响才发生的。对一般规律来说它属不规则变化,然而它却另有一套规则;从另一套规则的角度看,它就成了有规律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语音发展过程中,如果这种在同一原因下具有同种性质的例外现象出现的频率增多,就会成为一条规律。同时,这些演变的规律也很严整。这种严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音是按照音类(一类一类)变化的;另一方面语音变化是按不同条件进行的。同一类语音由于受到不同条件的影响,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一般来讲,声母的变化受韵母及声调的影响,韵母的变化受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声调的变化受声母清浊的影响。所以,本文所列韵母的变化也多以声母为演变条件。
以下逐条列出不合一般规律但仍有规律可循的语音演变情况。也可以说是不合规律的规律现象。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情况比较复杂。有些可以明确说明,有的一时还难以解释清楚,我们参酌时仁前贤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口一等“歌、铎”两韵,部分字今读合口[uo]韵。例如:
歌韵 铎韵
多ta→tuo 托tʻak→tʻuo
挪na→nuo 诺nak→nuo
罗la→luo 洛lak→luo
据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先秦“歌[ɑi]”部在中古时期分化为“歌、麻”两部,一等为[ɑ],二、三等属“麻[a]”部。确实“歌”到了宋代已由[ɑ]转变为[ɔ],元明清一直都是[o],直到近代才变为[uo]。中古入声“铎[ɑŋ]”韵,到后来失去了辅音韵尾,主要元音发生了与“歌[ɑ]”同样的变化。
并且王先生分析了“为什么其它的开口字没有变为合口,唯独‘歌、铎’两韵字变了合口的原因”[7]。因为“‘歌、铎’两韵字的开口呼在没有变[uo]之前是经过了一个[o]的阶段的。”而由[ɑ]变[o],则可用后低元音的高化来解释。现代北京话中,唇音声母后的[uo]不很明显,所以还可认为是单纯的[o],汉语拼音只写成bo、po、mo;舌齿音声母后的[uo]就很明显,所以写成duo、tuo、zhuo等。
目前,想要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内部治理方面,完善股权结构,依据上市公司的性质进行股权的流动,促进股权的多元化。在法律上保证监事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出监督职能。要保证经营管理层的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一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外部控制上,要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加强控制权市场,完善市场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力度,保证其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我国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尚处于起步时期,会计信息披露的完善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有关会计信息披露的各种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表1 从今音四呼上溯中古音开合的情况简表
(二)开口二等见系字,今大多读齐齿呼。如:
街kai→ʨiɛ 奸kan→ʨian 家ka→ʨia
开口二等字本没有韵头,在发展过程中插入了韵头[i],因此出现了开口二等字变细音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只见于喉音字(即影、晓、匣、见、溪、疑六母)二等字。就是说“舌根音和喉音在元音[a]前面的时候,[a]和辅音之间逐渐产生一个短弱的[i](半元音性质的)。”这个韵头[i]产生之后,声母[k][kʻ][x]受它的影响便鄂化为舌面音[ʨ][ ʨʻ][ɕ]。这便是开口二等见系字,今读齐齿呼的原因。
(三)开口二等江韵、三等阳韵的知、庄组字,今读合口呼韵母。例如:
江韵 阳韵
椿tʃəŋ→tʂuaŋ 庄ʃiaŋ→tʂuaŋ
窗tʃʻɔŋ→tʂʻuaŋ 疮ʃiaŋ→tʂʻuaŋ
双tʃɔŋ→ʂuaŋ 床ʤiaŋ→tʂʻuaŋ
江韵的演化,由开口变合口时经过了一个齐齿的阶段,如双ʃɔŋ→ʃaŋ→ʃiaŋ→ʂʻuaŋ是如此演化的,所以它与阳韵的庄系字都是齐齿变合口。
元朝时三等阳韵的合口字与一等唐韵字已经合流,如“匡、筐”(阳韵)与“广”(唐韵)音同调不同,“枉”(阳韵)与“汪”(唐韵)也读为同音,等等。《蒙古字韵》对音都作[uaŋ],所以说[iuaŋ]在元代就已经消失了。因此,现代就没有与[aŋ]相对的[yaŋ]韵母。
江、阳韵的入声字也产生了相应的[u]介音,如桌、捉、酌、若等。另外,部分见溪字现代都读撮口呼。例如:
觉韵 药韵
觉kɔk→ʨyɛ 却kiak→ʨʻyɛ
确kʻɔk→ʨʻyɛ 约iak→yɛ
学kʻɔk→ɕyɛ 爵ʦiak→ʨyɛ
这些觉、药韵字在《蒙古字韵》中念[iau]和[iɛu]。可是,在《中原音韵》中它们却产生了另一种读音[io]。念[iau]和[iɛu]的音在元末明初已同样归并为[iau],念[io]的音在后代则变为[yɛ]。因为[io]中的介音受后面的圆唇元音影响变成了圆唇的[y-],而介音后的[o]则又受到前面前高元音的影响而而舌位前移,变为前元音[ɛ]。这样相互影响便促成了[io]到[yɛ]的演化。念[yɛ]的字主要是从原入声字变来的,所以现代汉语[yɛ]韵基本上没有原来的阴声韵字。
(四)开口三等知系字,今多读开口呼;合口三等知系字,今多读合口。例如:
知tie → tʂʻʅ 朝diɛu→tʂʻau 沾 tiɛm→ tʂʻan
追tʂiei→ tʂuei 传tʂʻ ian→tʂʻuan 率ʂʻ1ai→ʂʻuai
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发音部位的不调和引起的。知系声母字即后来的卷舌声母[tʂ tʂʻʂʐ]等,它们发音时舌尖抵住硬颚的后部,而[i]是舌面前部的高元音,两者的发音部位极不兼容,所以在发音过程中便发生了[i]韵头的失落。因此中古的开口三等知系字,发展到现代绝大多数消失了[i]介音,而读为开口呼了。
类此,合口三等中的[i]也会失落,仅留下[u],故合口三等知系字,今多读合口呼,而不读撮口呼。爹、漱二字例外,尚不知如何解释。
(五)开口三等止、蟹两摄今音全为开口[ɿ][ʅ]韵或齐齿[i]韵。例如:
止摄 蟹摄
资ʦi→ʦɿ 制tiɛi→tʂʅ
支 tie→tʂʅ 祭ʦiɛi→ʨi
离lie→li 例liɛi→li
《广韵》微韵和蟹摄的韵头、韵尾均为[i],后来它们便吞没了主要元音,而使整个韵母变成了[i]。之[iə]韵的主要元音是央元音[ə],而[ə]可前可后、可高可低。这里它受前面高元音[i]的影响,而向前发展,促使支、脂合流。最后,它们的主要元音被[i]吞没,韵母也变为[i]。而韵母[i]与[ts][tʂ]两组韵母的发音部位极不协调,于是韵母[i]便受声母的同化变为[ɿ][ʅ]。“悲”(脂韵帮母)“厕”(之韵庄母)二字例外。
(六)合口一等帮系字今音部分读开口,合口三等字今全读开口或单韵母[u]。
合口一等各摄唇音声母后[u]介音失落,韵母便由合而开,灰韵泥、来两母字和魂韵的泥母字也有[u]介音失落的现象。例如:
灰韵 魂韵
杯 puɒi → pei 本puən → pen
内 nuɒi → nei 门muən→ men
雷 luɒi → lei 嫩nuən → nen
简言之,中古合口唇音字今读开口,是由语音上的异化作用造成的。唇音声母与合口[u]发音相似,便发生异化作用把[u]介音排挤掉了,从而形成开口字。正由于此,合口二等与四等即使在中古时期也没有唇音字。
合口韵的唇音声母首先促成了[u]介音的失落,[n]、[l]声母字则较为缓慢或不起变化。至明末清初的《字母切韵要法》[n]、[l]声母字“馁、内、雷、累”等仍与[uei]韵字“魁、堆、推”等同列,而不与[ei]韵字“悲、裴”等同列,可见这些字失掉[u]介音当在清初之后。有两个字例外,即“坯”(蟹摄灰韵)“拼”(山摄桓韵)。
语音的变化不仅是严整的,有一般规律或特殊规律可循的。正如中古开合四等到今音四呼之演变,一般规律是开口一二等今音读开口,开口三四等今音读齐齿,合口一二等今音读合口,合口三四等今音读撮口;还有“开口一等歌、铎两韵部分字今读合口[uo]韵”等特殊规律。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音的演变也是复杂的。规律之外,常常有极个别的例外现象存在。或许这些个别现象仅从语音系统内部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而要从社会、人文各方面综合考虑,以求答案。这种例外只能说明语音演变的复杂性,而不能否定语音演变的规律性。
以中古止摄支韵心母“死”字为例,在《广韵》它单独占一个小韵,没有一个同音字。现代支、脂、之三韵合流,三韵平声今读阴平或去声的[sɿ],上声今读上声的[sɿ]或[ɕi]。“死”在现代仍独占一个音节。这是由避凶造成的。又如“入”字,中古属开口三等入声缉韵字,所有中古属开口三等入声缉韵字今音韵母均为[i],唯独日母“入”字今音韵母为[u],这是由避秽造成的。
以上只是从避忌方面说明了某些特殊变化的原因。特殊变化的原因很多,情况也很复杂。至今还有一些语音演变现象我们无法解释。如中古开口二等肴韵的“抓”字、咸韵的“赚”字读合口,而合口二等只有“傻”(麻韵庄母)一字读开口。这些特殊的变化是结果的体现,任何一种结果,不论它多么微不足道都有一定的原因,语音的变化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宁愿相信这些例外现象也是有原因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原因会逐渐被揭示出来。
注释:
①等韵图,音韵学家翻译佛经过程中受梵文拼音原理启发,发明的一种用图表说明反切、分析语音的方法,把三十六字母和二百零六韵的拼合关系在图表中展示,并列出代表字,类似现代汉语的《声韵拼合总表》。
[1] 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551.
[2]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1.
[3] 戴震.戴震全书:3[M].合肥:黄山书社,2010:300.
[4]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6.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Z].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汉语方言调查字表[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王力.汉语语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8]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
Analysis on the Irregular Variation of Four-tone Pronunciation in Today from Opening and Closing in Ancient China
CAO Lihua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Sichuan, China )
"Opening and closing" is a set of symmetrical systems describ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rhymes, and also the importa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e phonetic nature. Taking the example characters collected in theofas the object, we analyze the changes and general rules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in ancient China to the four-tone pronunciation in today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focus on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that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ules but still has evidence to follow.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opening and closing, four classes, four-tone pronunciation
2018-10-27
四川省高水平研究团队资助项目“传统文化背景下攀西地区特色文化应用研究”(川社联〔2017〕43号)。
曹利华(1981-),女,河南濮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音韵,汉语语法。
H123
A
1673-9639 (2018) 12-0052-07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印有家)(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