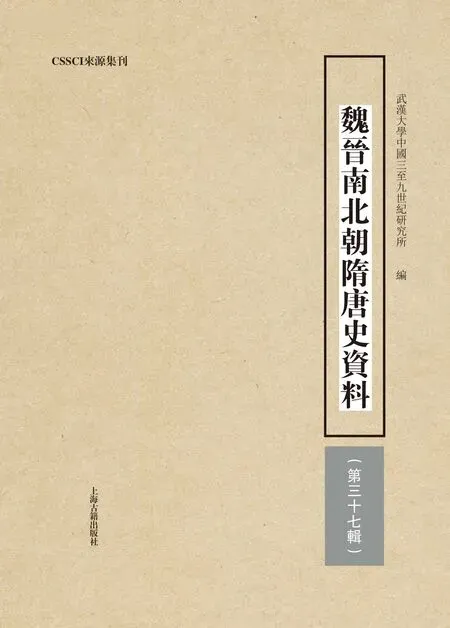日藏古寫本《毛詩正義·小戎》《蒹葭》校議
——北宋官校《五經正義》管窺之二*
2019-01-21李霖
李 霖
傳世唐抄本與刊本文本往往存在較大差别。宋初國子監校刻四部群籍時,對唐抄本典籍所作校勘工作,是我們認識唐抄本與宋刊本差别的關鍵。本系列研究以《五經正義》爲對象,通過以宋刊單疏本爲主的刊本,校勘傳世唐抄本系統《五經正義》,以期窺見北宋國子監對唐抄本主體做了哪些校勘工作,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唐抄本的面貌。






本研究采用的底本符號如下:
攸: 底本此“攸”字與校本不同。


連: 底本此“連”字缺損,據校本擬補。能勉强辨認者不加框。幾乎無法辨認者不取。
校語符號如下:

(無): 刊本無此字。
繼敦煌本《周易正義·賁卦》之後,[注]李霖: 《敦煌本〈周易·賁卦〉正義校議——北宋官校〈五經正義〉管窺之一》,《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8輯,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7年。本文以日藏《毛詩正義·小戎》《蒹葭》寫本殘卷爲底本,以南宋紹興九年刊《毛詩正義》單疏覆刻本爲校本,通過分析二者的異文,認識北宋勘官對唐抄《毛詩正義》所作校勘工作。
一、 底 本 簡 介
日藏《毛詩正義·小戎》《蒹葭》殘卷,起《秦風·小戎》首章傳“游環至續靷”疏“脅驅當服馬脅也”之“服”字,終《蒹葭》次章傳“坻小渚”疏“故繫渚言之”之“故”字。中有斷損,存103行,行24字左右(20至27字)。
殘卷分藏三處,一爲富岡謙藏(君撝)舊藏67行,圖版收録於1921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第一集》,後有1913年羅振玉手書跋,[注]1918年刊《雪堂校刊群書叙録》收録此跋,題《日本古寫本毛詩單疏殘卷跋》,文字略有出入。謂其“字迹疏秀,唐寫本之佳者”。此影印本圖版共5葉,每葉右下標漢字序號一至五,當係原卷紙張數。1981年大阪市立美術館所編《唐鈔本》,記録其縱長爲27.5 cm×50.4 cm、27.4 cm×25.8 cm、27.4 cm×25.4 cm、25.5 cm×24.5 cm,[注]大阪市立美術館編: 《唐鈔本》,臺北: 明文書局,1981年,第155頁。蓋一、二兩紙粘連未分。1936年大阪府立圖書館編纂《富岡文庫善本書影》,原大影印此卷第一紙首11行、第四紙首5行及第四紙末之紙背寫經4行,[注]背面寫經前空一行,正是第四紙末行文字(當“文本校録”行80),由此可以確定寫經在此卷的位置。圖版最爲清晰。書影所附文字標題云“斷簡四枚”,亦以一、二兩紙算作一枚。原件今歸京都市政府所有。下稱“富岡本”。
二爲小島佑馬舊藏23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1938年拍攝的照片。小島氏舊藏書,今歸日本高知大學,1987年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出版《小島文庫目録》,卷首有此殘卷的彩色圖版。下稱“小島本”。
三爲天理圖書館所藏殘片13行,圖版收録於該館在1968年編印的《善本寫真集》31《古册殘葉》。《善本寫真集》解題謂其“紙高27.1釐米,寬24.2釐米;墨界高21.8釐米,行寬1.9釐米”。下稱“天理本”。
此三件寫本同出一筆,用紙也相同,原爲一卷無疑。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首次將全卷合璧影印出版。
關於殘卷的書寫時代,1933年長澤規矩也等編《佚存書目》著録富岡本,斷爲“奈良朝鈔本”,認爲是日人所寫,約當唐睿宗至德宗時期,並提及小島本。[注]服部宇之吉: 《佚存書目》,東京: 文求堂書店、松雲堂書店,1933年,第71頁。1968年《善本寫真集》天理本解題云:“此殘片與舊制指定‘國寶’之富岡本同出一筆。富岡本避唐太宗諱‘民’字,明顯是唐人抄本。本殘片背面有草寫佛經,似乎出於日本奈良末、平安初期手筆。這一點,可以作爲推測這部抄本傳入日本時間的參考。”認爲是唐人所書,傳入日本後,日人在其紙背草寫佛經。
此卷究竟是唐人所書,抑或日人轉寫,實難斷言。我們主要關注其抄寫時間和文本來源。前人每遇避“民”字諱之抄本,即視爲唐抄,並非確論。日人或宋人轉寫,都可能保留底本的避諱習慣,[注]某一朝代的諱字可能成爲後代的俗字。諱字只能判斷成書時間之上限。全卷“民”字或闕末筆,“葉”字寫作“”,是高宗顯慶二年以後的避諱習慣,[注]據《舊唐書》本紀,顯慶二年十二月,高宗詔“改‘昬’‘葉’字”。可作爲此卷抄寫時間的上限。至於其下限,仍須探討。筆者未見卷背佛經全貌,《正義》與佛經之先後關係,尚待考實。然《佚存書目》既著録爲奈良朝抄本,量非無據,《正義》應在天理本解題所謂奈良末、平安初之寫經以前抄録,因而我們傾向於長澤富岡本解題所謂奈良朝抄本的鑒定。今比勘其文本,全卷與宋刊單疏本差别較大,絶非從宋刊本出,必源於唐抄。依本研究的慣例,逕稱爲唐抄本。
爲便叙述,校録將三件唐抄底本按《正義》内容次序統編行號,不計闕行,各本序號如下:
《小戎》正義13行(小島本),行1至13。
《小戎》正義13行(天理本),行14至26。
《小戎》正義27行、《蒹葭》正義40行(富岡本),行27至93。
《蒹葭》正義10行(小島本),行94至103。
其中的富岡本,近有王曉平先生已作校勘研究,[注]王曉平: 《京都市藏唐鈔本〈毛詩正義秦風殘卷〉》,見氏著《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第49—61頁。校本主要采用阮刻本。由於我們的關注點有所不同,今采用南宋紹興九年覆刻單疏本《毛詩正義》,重校包括富岡本在内的全卷文本。 底本全卷“曰”多寫作“日”,逕改不出校。
二、 文 本 校 録
(以下小島本)
1 服馬脅也隂 儺也横側車前所以儺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

案此段皆劉熙《釋名》文(參《正義》上文),今本《釋名》作“笭”字。[注]見《釋名》卷七《釋車》第二十四,據《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嘉靖覆宋末書棚本,下同。“荃”與車無涉,宋刊單疏本誤。
2 也治白金以沃灌靷也續續靷端也 箋游環至之環

案《正義》上文云“銷此白金”,此當作“冶”。今本《釋名》亦作“冶”,宋刊本是。
抄本行5兩處皆作“環”字,此處作“ 毞 ”,當係筆誤。《釋名》亦作“環”。
3 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
4 禁止驂馬也輈在軓前横木暎軓故知垂輈上謂隂板輈上也靷言

5 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傳文茵至曰
6 馵 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 文綵故知

7 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 文綵是也暢訓爲

8 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里者名爲綦馬名爲

9 騏知其色作 綦文也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馵樊光云後右

案“後右足白,驤;左白,馵”,宋本《爾雅》如此。作“左馵”亦通。“白”字究係唐抄所遺,抑宋刊所加,今已不得而知,因“白”字省之亦通,姑以爲宋刊所加。
10 足白驤左足白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


12 同也 箋言我至五德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
13 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礼

(中闕約30行,以下天理本)
14 皮之轁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壊交暢

案“轁”“韜”通。
刊本“韔”字,全卷皆作“暢”。經文“虎韔鏤膺”,《釋文》出“韔”字云:“本亦作‘暢’”。若《正義》唐抄本主體作“韔”,則“暢”爲此卷假借;若唐抄本主體即作“暢”,則“韔”字爲宋刊所改。然全卷“暢”字甚多,無一作“韔”,因疑《正義》唐抄本主體乃至《正義》原本作“暢”,宋刊本改作“韔”。


案抄本涉兩“暢”字而奪文。

16 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
17 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
18 静之善人秩秩然有哲智其德音逺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

19 役故閔念之 傳俴駟至文貌 正義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


案“爲”與“以爲”義同。箋釋傳文云“以薄金爲介之札”,亦不著“以”字。此疏“以”字,疑爲《正義》刊本所增。


22予三隅予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礼曰進戈者前其鐏後

23 其刃進予戰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當有錞也彼注云鋭底曰


案“錞”“鐓”義同。詩及毛傳用“錞”字;今本《禮記·曲禮》用“鐓”字(明拓本唐石經亦然),《禮記釋文》出“鐓”字,云“本又作‘錞’”。此卷疏文皆用“錞”,同詩及毛傳;單疏刊本《毛詩正義》皆作“鐓”,同今本《禮記·曲禮》。蓋撰疏人所據《禮記》作“錞”,同《釋文》又本,宋刊本另據《禮記》版本改之。
24 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錞取其錞地則錞異物言錞鐏者取類相非


案敦煌寫本“ 棳 ”爲“盡”之俗字,[注]參見黄征: 《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1頁。在宋刊本中“盡”字也常省“灬”旁。此卷“畫”字寫作“ 棳 ”,當視爲錯别字。全卷“畫”字屢見,皆作“ 棳 ”,當非底本“畫”字模糊不清,而又屬於抄手个人風格。

案今本《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抄本“常”字左闕,細辨之下,似爲“常”字,而非“掌”字。抄本有“五兵”二字,同今本《周禮》,宋刊本無。抄本無“各”字,刊本有“各”字,同今本《周禮》。抄本此行以下脱,刊本作“其等以待軍事”,無今本《周禮》“其物與”三字。抄本與刊本皆與《周禮》原文不同,抄本與《周禮》不同之處,省“各”字猶可通,“掌”作“常”則顯然訛誤;刊本與《周禮》原文之不同,乃省“五兵”及“其物”,讀《正義》下文,並不涉及“五兵”及“其物”,因知刊本與《周禮》原文所以不同,蓋非漏略,而爲有意調整。
又,从抄本“辨”字殘存部分觀察,似“辯”字,姑從刊本補爲“辨”。
(中闕3行,以下富岡本)
27 文貌 箋俴至淺尨伐 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外馬之意以馬



案此章“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又首章“小戎俴收”傳云“俴,淺”。故此詩《正義》“俴”“淺”並用。乍看此卷“淺駟”似爲詩文“俴駟”之误,然“淺”字照應疏文前後之“深淺”“淺薄”,似較“俴”字爲優。單疏刊本作“俴”,蓋以“淺”爲誤字而改從詩文。



宋刊本於“苦”上多“則”字,蓋以照應上文“金厚則重”及下文“物不和則不得羣聚”。然彼處兩“則”字前後主語皆一致,此處添“則”字,文氣似不暢。《正義》原本當無“則”字。

30 不和則不得群聚故以和爲群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蒙茸皆尨


31 蒙同音周礼用牲用玉言尨者皆謂雜色故轉尨爲蒙明尨是

案此言“轉”者,即《正義》下文所謂“以義言之,無正訓”之意。此疏“轉蒙爲尨”,釋箋“蒙,尨也”;下文疏“轉討爲尨”,釋箋“討,雜也”。此卷作“轉尨爲蒙”,似誤導,此段疏文“蒙”“尨”反復出現,易生訛奪,今以刊本爲是。羅振玉跋云:“疏誼謂《詩》轉《周禮》之‘尨’爲‘蒙’”,恐怕是誤解了“轉”字的含義。


案“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乃引箋文,“傳以蒙爲討”乃述毛傳“蒙,討羽”,刊本文意通順,抄本皆涉上文而訛,非别有據。
33 之無正訓也 傳底之虎至縢約 正義曰下句云交暢二弓則

案毛傳作“虎,虎皮也”云云,抄本“底之”二字不知從何而來,或爲“虎”字之形訛。
34 虎暢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暢爲弓室也弟子識曰執

案羅振玉跋云:“識,職古通,《周禮》‘職方氏’,漢《華山廟碑》作‘識方氏’。”


37 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大帶者彼謂在腹

案今本《周禮》鄭注作“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抄本省“今馬”亦通,又改“也”爲“者”,“者”字可作爲引出下文正義的提示語,甚通。上行《正義》述《春官·巾車》大意,即非《周禮》原文,此處亦不必引鄭注原文。刊本引鄭注原文,蓋宋初勘官校改。
38 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謂暢中謂顛到安置之既夕記説明

案“到”“倒”古今字。






43 也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謂以繩約弓然後内

44 之暢中也 箋鏤膺有刻金飾 正義曰釋器説治器之名

45 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飾之巾車云金路樊纓九

46 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説丘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礼

案“説”“謂”同義,“謂”字當係宋刊本所改。
47 玉路金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之諸未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

案《周禮·巾车》玉路、金路注皆謂以金或以玉“飾諸末”,則此疏當作“以金玉飾車之末”,或“以金玉飾諸末”。抄本上行有“車之飾”三字,此行或涉彼文而衍“車之”,原當作“以金玉飾諸末”。宋刊單疏本删“之諸未(末)”三字,雖通,却失“末”義。
48 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 五采罽飾

49 之革路樊纓 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

案“條”“絛”通。
50 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鐡皆
51 是不用必要黄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釣膺不作鏤膺知此

52 鏤膺非金路也 傳厭厭至有知 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
53 秩秩智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

(中闕3行)
54 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
55 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 教必得周礼

案“得”“待”義微有别,究竟孰是,當就前後語境辨析。本章箋云“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下文疏述鄭意亦云“若得周禮以教”,均作“得”。此“得”字之依據。然《正義》此處乃述毛意,毛傳云“國家待禮然後興”,上文疏述毛意亦云“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均作“待”。是毛以爲“待周禮”,[注]又“待”字與序之疏相協。《蒹葭》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其疏云“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須禮”即釋“用周禮”,“須”同“需”,“需”有“待”義。鄭以爲“得周禮”,二家已稍有不同,疏述毛、鄭,理當各仍其舊。《正義》此處述毛,筆者以爲“待”字爲優,然“得”字亦非無據。抄本作“得”,唐抄本主體或如此。另一方面,“得”“待”形近易訛,抄本作“得”字,不能完全排除涉前後文“歲事得成”“國乃得興”訛爲“得”字的可能。今姑以爲唐抄本主體作“得”,宋初勘官改爲“待”字。
56 以教之然後服 從上金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礼其國未得

57 興也由未能周礼故得未人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逺在大水一

58 邊大水喻礼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礼樂之樂邊既以水喻礼樂礼樂

案抄本此行末尾“礼”“樂”二字下均標重文符號。


案“阻”“險”義近,“阻險”即“險阻”,而後者更爲常用。《詩》云“道阻且長”,《正義》此處以“長遠”釋“長”,不云“遠長”,以“阻險”訓“阻”則可與之相諧。設若《正義》原本作“險阻且長遠”,“阻”“且”二字形近而相連,抄手似不當誤爲“阻險且”,因疑《正義》原本當作“阻險”。《邶風·泉水》疏云“道路以阻險爲難”與此處義近,[注]單疏刊本闕,《毛詩要義》無文,此據宋刊十行本卷二之三葉七右行二。可作旁證。然則“險阻”當爲宋刊本所改。《商頌·殷武》“罙入其阻”箋云“冒入其險阻”,鄭玄以“險阻”訓“阻”。《毛詩正義》勘官當熟悉鄭箋,《殷武》箋蓋此疏改作“險阻”的依據之一。


案此卷“逆礼以治國,則得人之道,終不可至”,與全篇毛傳所討論的“得人之道”呼應,甚通,《正義》原本當如此。刊本似誤解其意,添“無”字,删“之”字,作“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解釋上文“道阻險且長遠,不可得至”,看似通順,實與全段不協。
61 游而往從之 則菀然在於水中央言順礼治國則得人之道 自來

案“在於水中央”無“之”字亦可,此述經文“宛在水中央”大意,有“之”字則文氣更暢。下文行69—70述經文作“在水中央”而無“之”字,然亦無“於”字,則下文不具“之”字更爲妥帖。此處有“之”字更佳,疑抄本誤脱。
《釋文》出《蒹葭》經文“宛在”二字,云“本亦作苑”,“苑”“菀”通。《正義》撰人所見《蒹葭》當作“菀”字,《正義》原本亦當用“菀”字。(反之,若《正義》原本爲“宛”,抄手不必改作較爲生僻的“菀”字。)《蒹葭》唐石經拓本作“宛”,與今詩同。至宋初校刻《正義》時,《蒹葭》詩“宛”字當更通行,《正義》因改從詩文作“宛”。
62卬己正近在礼樂之内然則非礼必不得人心不能固國君何以不

案此卷行94、96(小島本)用“迎”字皆同於宋刊本,此處作“卬”,當係“迎”字之訛。
抄本作“非礼必不得人心,不能固國”,看似欠通;刊本作“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重複“得人”二字,將“心”改爲形近之“必”字,看似合理,其實二者意義已有分歧。抄本文句有三層涵義: 第一,禮是得人心的必要條件;第二,禮是固國的必要條件;第三,突出禮對固國的重要意義,得人心只是二者間的過渡。二、三兩點符合詩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刊本文句也有三層涵義: 第一,禮是得人的必要條件;第二,得人是固國的充分條件;第三,强調得人對於固國的重要意義。僅第二點,即知刊本文句與詩序不合,不如抄本妥帖。抄本文句當接近《正義》原本,刊本所改反失之。此條可與行83第二條校語並觀。
63 求用周礼乎 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强盛雖

64 似不可淍傷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黄矣以興衆民之

案此卷“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黄”與今本鄭箋文字全同,《正義》原本或即如此。宋刊單疏本增“下”“爲”二字,用意何在?《正義》此處乃述鄭箋之意,下文又解毛傳“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云:“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己任用矣。”[注]此據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録文,當此卷行78—80,行80以後闕。是《正義》下文以節令及《豳風·七月》證八月白露初降時草已可用,而毛傳概言“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成”(鄭箋亦然),二者時間有所不合,《正義》調和兩説,以爲傳意“白露凝戾爲霜”指九月中霜降之時節草乃成(《正義》應以爲箋意亦然)。而宋刊本於《正義》此處添“下”“爲”二字,作“白露下,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黄矣”(所添“爲”字似無實義),玩其文意,乃指從八月白露降下之後(白露節)至九月中霜降節期間之事,則已與《七月》之“八月萑葦”相協,卻又與《正義》下文謂“(九月中)霜降草乃成”有所不同,顧此失彼,已失《正義》原義。
65强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礼以教則衆民

66 自然服矣故欲求周礼當得知周礼之人所謂是周礼之人在

案抄本“故”字,似爲引出鄭玄對詩句“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解釋,即“所謂是〔知〕周礼之人”云云,[注]“〔知〕”表示底本誤脱“知”字,爲便叙述,暫時補入,下同。《正義》原本或如此。僅就疏文“欲求周礼,當得知周礼之人”而言,與上文並無因果關係,刊本删“故”字,或出於此。
67 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喻以假言逺既言此人在一邊因以水


案抄本作“阻長”亦通,不必盡依詩文“道阻且長”。然“阻”“且”二字形近,不能排除“且”字爲抄手遺漏的可能。姑以唐抄本主體作“阻長”,宋初勘官據詩文添“且”字。


案無“往”字亦通,行70、71“(不)以敬順求之”,刊本即未添“往”字。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此處《正義》述鄭意,不必照録原文。刊本有“往”字,蓋宋初勘官所加。行70“以敬順求之”,刊本未加“往”字者,蓋以彼疏對應之箋文“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並無“往”字。

70 水中央易可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

案“易”“可”連用則不詞,抄本“可”字或涉下文“則不可得”而衍。
71 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
72礼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傳蒹葭至後興 正義曰蒹蒹葭


此卷疏文引毛傳誤作“蒹蒹”,二字直書而下,不用重文符號,與全卷書寫習慣相違,知後一“蒹”字當爲抄手誤書。誤書不必始於此卷,底本或已如此。知者,此卷行87脱“一方”二字的重文符號,則此卷底本或更早的底本已有使用重文符號的習慣;設若底本作“蒹”加重文符號,則此卷不會寫作“蒹蒹”,知底本或已誤作“蒹蒹”。


74薕水草也賢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人謂之薕兖州

75人謂之樖C通語也祭義説飬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


案此卷“露”字數見,他處皆寫作“露”,惟此處寫作“ 賳 ”,當係形訛。

78 以爲説也八月白 露莭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白露凝戾

案抄本此行兩“節”字,一作“莭”,當係抄手隨手書寫。
此卷承前省“八月”“九月”,《正義》原本當如此。宋陳祥道《禮書·月令二十四氣》引劉歆《三統曆》、唐賈公彦《周禮·春官·大史》疏皆如此。然《三統曆》與《周禮疏》皆歷數一年二十四節氣,省去每月第二節氣前所重複之月份,層次更爲清晰。《毛詩正義》取八月、九月四氣,只云“秋分中”“霜降中”,似嫌不妥。宋初《正義》勘官補“八月”“九月”,乃使文意清楚明白。
79 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 曲薄充歲事也七

案“薄”“簿”通。

(中闕4行)
81 能用周礼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能從國未能固故易傳興用周礼教

案此係箋之疏,箋云“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抄本作“民未能從”,亦通。此卷“能”字旁補入“從國未能”四字,且書體相同,知抄手涉兩“能”字而誤,則其所據底本即作“能從”,不作“服從”。刊本作“服從”者,蓋照應箋文之“服”字。
抄本“故易傳,興用周礼教民則服也”者,毛傳以“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鄭箋改易毛傳之義,以“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至白露疑戾爲霜則成而黄”,興“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與此類似,《鄭風·山有扶蘇》疏曰“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者於下位”,[注]此據單疏本録文,宋十行本“美德”下無“者”字。“喻”字之後爲箋義。這種表述方式,在《毛詩正義》中並不常見,他處述毛、鄭异義,多以“故易傳也”結束,或以“故易傳以爲”云云總結前述箋義。抄本當係《正義》原本,宋初勘官蓋不明其意而删去“興”字。既删“興”字,本應補入“以爲”二字引領箋義,今作“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若不重讀傳、箋,實不知“用周禮教民則服”是傳義還是箋義。




案此處疏文引詩序“未能用周禮”。《蒹葭》疏多云“周禮”,亦有單言“禮”者,例如上文行71—72“求知礼之賢人”。此處抄本作“未能用礼”亦通,不必悉依詩序。姑認爲“周”字爲宋刊本所增,但不能排除抄本脱“周”字的可能。
“〔詩刺〕未能用礼,未得人心”者,據詩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知《蒹葭》所刺是襄公未能用周禮之事,宋刊單疏本所多“則”字,看似使“未得人心”緊承前文,更加通順,其實也將“刺”之重心轉移至“未得人心”,此與詩序所言詩旨並不符合。且下句又有一“則”字,更與此句“則”字重複。故刊本所多“則”字並不妥當,《正義》原本當無“則”字。抄本行62“非礼必不得人心,不能固國”,亦突出“禮”的作用,彼處刊本作“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似突出“得人”,與此行所加“則”字意義相似,皆與詩序不能盡合。
“則所謂維人,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者,傳既訓“伊”作“維”,詩句“所謂伊人”即“所謂維人”,《正義》結合上文“〔詩刺〕未能用禮,未得人心”,進一步解釋“所謂維人”的涵義,乃是“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首“則”字,順承上文之“未得人心”,引出下文“所謂維人”的内涵。宋刊單疏本無“所謂維人”句,使文意不通,當非有意調整,而係涉兩“所謂維”而脱文。


案抄本有“則以水喻礼”五字,刊本全句皆無,當係有意删去。然而首章疏述毛意,亦有“大水喻礼樂”“以水喻礼樂”(行58)的表述。且綜觀全卷異文,刊本有意更改唐抄本之處,變動並無如此之巨者。刊本緣何删去此句,着實令人費解,不能完全排除刊本誤脱的可能。
行末所殘文字,刊本的相應文字是“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9字。並本行所存18字,凡27字。而全卷整行文字最多的行3,即爲27字。本行闕文是否悉與刊本符合,今已不得而知。


86 句言從水内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礼以求得人之道故



案抄本脱重文符號。


案抄本出文“云”字係衍文,説詳下文“異文分析”部分。
抄本此行所闕文字,所對應的刊本文字是“則民服此經當是”7字,並所存20字及1空格計之,凡28字之位置,已超出全卷行字範圍(20至27字)。就殘損的位置與其他各行比對,所闕當只4至6字,似與刊本文字有所不同。


90 在水一邊假喻以言逺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

案無“大”字亦通。疏文此處乃引述鄭箋“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逺”,“大”字當係宋初勘官據鄭箋原文所補。然而單疏刊本亦未引箋文“乃”字(《正義》撰人所據箋文應有“乃”字),[注]首章疏述毛意云“乃遠在大水一邊”,毛傳無文,實據鄭箋,因知《正義》撰人所見箋文有“乃”字,與今本《毛詩》相同。知《正義》引述注文本來不必與原文一一相符。


案抄本出文“曰”字當衍,説詳“異文分析”。今毛傳作“逆流而上曰遡洄”,出文標起始當爲“逆流”二字,“洷”字與抄本“流”字(右上無點)形近,或涉此而訛。説又見下行校語。


案抄本此行所闕文字,以鄰行87至90相應位置推之,當有8字,刊本作“正義曰釋水云逆流”8字,與抄本闕文情况相符,可以佐證撰疏人所見毛傳亦作“逆流而上曰”云云,無此卷上行“洷”字。
此卷“度”字左側闕損,就所占位置看來,左側不應有水旁,當是“度”字。“渡”、“度”通。南宋刊《爾雅疏》此處元修葉引孫炎曰俱作“渡”。抄本下行“度水”之“度”字,殘存末劃之鋒芒處頓筆頗重,再參考該行其他殘字位置,彼文亦當係“度”而非“渡”字。行94(小島本)所存“未度”字亦闕左邊,據其位置推測,亦爲“度”字無水旁。知此寫卷用“度”字,宋刊本用“渡”字。但此卷“度”字在唐抄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尚不得而知。

(以下小島本,中闕3行)



案抄本此行“箋”字寫作“牋”,全卷僅此一例,當係抄手隨手書寫。
96 傳順礼未道來迎之 正義曰定本



案今本《小雅·湛露》用“匪”字,抄本用“非”,同。


案上行闕文所對應的刊本文字作“言見日乾,故知晞爲乾”,本行“彼言露晞,謂露盡物乾”者,順承《正義》上文,乃針對《小雅·湛露》首章“匪陽不晞”傳“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彼《湛露》傳僅謂“晞”爲“露”乾,並未明言“物”乾。然彼箋又云“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明言“物”。且彼傳之疏已云“此在物而湛湛然是盛也”,又云“以陽爲乾物”,[注]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卷十七首葉左面。雜采箋義。《湛露》疏既以“晞”兼指“露”及“物乾”,此處指斥其義,亦當有“物”字。《正義》原本當如此。無“物”字亦通,姑以爲無者乃宋刊本所删。




案《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湄”,同宋刊《毛詩正義》。抄本重“水”字,又不用重文符號,當係抄手之誤。


案“坻”“坘”通。
三、 異 文 分 析
(一) 唐抄本的特徵
1. 文本特徵
了解寫卷的抄寫特點,有助於推測此卷文本在唐抄本中的典型性,從而幫助我們判斷此卷與宋刊單疏本異文的性質。甚至有些時候,成爲異文分類的前提。
此卷避諱不嚴,“虎”字數見,皆不闕末筆。“葉”字一見,改作“”。“紲”字在行40至43頻繁出現,皆未改形或闕筆。“民”字行64、65兩字闕筆,行55、81、82、88四字不闕筆。

此外,行88出文“箋云”衍“云”字,行91出文“傳曰”衍“曰”字,衍文皆與《正義》内容相關。説明抄手對《正義》内容尚有一定了解。
2. 行款特徵
分析寫卷行款在《正義》唐抄本中的典型性,是我們認識唐抄本主體與宋刊單疏本行款關係的前提。
全卷每紙13或14行、行24字左右。具體的用紙和行數(闕行按照對應的刊本字數换算爲抄本行數)如下:
小島本第一紙13行,後闕約30行。
天理本一紙13行,後闕3行。
富岡本第一紙14行(首行闕右半);
第二紙13行,後闕3行;
第三紙14行;
第四紙13行,後闕4行;
第五紙13行(末行左部大半殘損),下闕3行。
小島本第二紙10行。
若忽略首、末兩紙,將其他每兩紙之間所闕行數還原,恰好可以凑成每紙15行,[注]此卷用紙情况究竟如何,還需要考察卷背寫經的情况。與南宋刊單疏本及北宋刊《孝經》的行數吻合。又,全卷皆有墨界,行字多在22至25字之間,偶少至20字,多至27字,亦與單疏刊本每行25至30字接近。然而在討論宋刊本與此卷行款的關係之前,應先明確此卷行款在《正義》唐抄本中是否典型。
實際上,此卷用紙在現存唐抄《五經正義》中並不具有代表性。至於其行字及一行起訖,是否遵循了某種規範,需要具體分析。
行75首“人謂之”三字涉上行而衍,假設衍文乃此卷新生之誤,則其底本“人謂之”三字必在行中,不在行首,可證此卷與底本一行起訖文字不同。若底本已誤,則上溯其未誤之祖本,亦當與此本一行起訖不同。此其一。
行81“未能”旁同筆補入“從國未能”4字,此行原有24字,並補入的4字共計28字,超出全卷行字範圍。可以推知底本每行起訖似與此卷不同。此其二。
由此二證,可知此卷每行起訖並不嚴格依據某一種相對精善的底本(即不衍“人謂之”三字的祖本),而主要取決於紙幅和抄手的個人因素。
全卷各行字數(含空格)緩慢波動,行33以前多在24字以上,行34至53多爲22或23字,行54至62多爲25字上下,行63至81多爲23、24字。行82以後無完行,本來行字不得而知。我們推測這種波動的態勢,當非遵循某一精善底本已有的規範,而似乎主要取决於抄手的個人因素。
(二) 宋刊本的調整
唐抄本《正義》引述群經經、注,未必照録原文,宋刊單疏本則多原文引用。
行9“馬後右足白驤左馵”,不誤,刊本據《爾雅》於“左”後補“白”字。
行28“淺駟”,刊本依《小戎》經文作“俴駟”。其實鄭箋訓“俴”爲“淺”,《正義》此處疏釋箋文,此卷作“淺”字較優。然《小戎》傳、箋、疏“俴”“淺”並見,我們猜測宋初勘官所見唐抄本,此處作“俴駟”者亦當不在少數。宋初勘官取“俴駟”,蓋因與詩句原文相同。
行37引《周禮》注“謂大帶者”,甚通,刊本依鄭注原文改爲“謂今馬大帶也”,並虚詞“者”字亦改之。然行36對應的刊本《正義》引述《周禮》亦非原文。
行39引《儀禮》注“縛之於裏備頃傷”,“頃”字文意較優,刊本依鄭注原文改“裏”爲“弓裏”,改“頃”爲“損”。
行68—69抄本“阻長”“不以敬順求之”,刊本分别依詩句及鄭箋原文改爲“阻且長”“不以敬順往求之”。然行70、71對應的刊本《正義》述箋意亦不添“往”字。
行90引述鄭箋“在水一邊”,刊本依箋文改作“在大水一邊”。然箋文句首有“乃”字,《正義》刊本未引,亦不盡與原文相符。
以上七條抄本文字,誠然未必皆爲宋初勘官所見。然而這些抄本與刊本間的異文具有共同的指向,足證引用群經經注原文,是宋初《毛詩正義》勘官的一項校勘原則。
其中行37、42、68—69、90四條,刊本該處疏文或前後疏文所引亦未盡與原本符合。究其原因,唐抄本輾轉傳抄,其中當有抄手不以底本爲然,妄據所引典籍原文更改該書文字者。宋初文臣薈萃諸抄,若一本與引文原本相符,一本有異,勘官當以相符者爲是。我們推測,勘官不必一遇引文即翻檢原書,而應優先校勘《正義》抄本,遇有引文互歧之處,始核對原書。反之,若將《正義》引文一皆以原本更改,則文本變化太大,尤其是和“定本”相關的《正義》所據經注文本與宋刊經注本的諸多不同,[注]參本文末尾。亦將不復存在。我們認爲“引用原文”作爲宋初《正義》勘官的一項校勘原則,僅適用於局部細節,並不要求《正義》全部引文與原書符合,也不對具體文本作大幅改動。
引用原文作爲北宋國子監的校勘原則之一,並非絶對優先的原則。《小戎》末章傳“俴駟至文貌”疏引《周禮·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今本《周禮》“五盾”前有“五兵”,“其等”前有“其物與”。此卷行26猶可辨“五兵”二字,下殘。刊本未引的“五兵”及“其物”,下文疏亦不涉及,似爲刊本有意删去。
宋刊本對《正義》文句的調整,可能對疏文含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改變。
抄本行29“知宜薄也”,刊本作“知其薄也”。“宜”字或可誤爲“其”,然“其”字不易誤爲“宜”,知抄本當有所本,蓋唐抄本主體乃至《正義》原本如此。然細味文意,刊本“其”字似較“宜”字爲優。
行47“以金玉飾車之諸未”,“車之”二字或涉上行而衍,“未”字當從《周禮》注作“末”。此卷雖誤,必有不誤之唐抄本,而刊本迳作“以金玉飾車”,不及“末”義,蓋仿下文疏“以五采罽飾之”“以絛絲飾之”之例。檢今本《周禮》注,“以五采罽飾之”“以絛絲飾之”原文如此,此亦不當删“飾諸末”三字,宋刊本失之。
行55疏述毛意作“必得周礼”,唐抄本主體或如此。考《蒹葭》“得”字乃鄭箋用字,毛傳用“待”,刊本改作“待”,較抄本爲優。
行64“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黄”與今本箋文全同,唐抄本主體乃至《正義》原本當如此。刊本於“白露”後添“下”字,在“黄”前添“爲”字,乃宋人有意調整。刊本作“白露下”得以調和《蒹葭》注“白露凝戾爲霜”與《七月》詩“八月萑葦”可能存在的矛盾,却與下文行78—80略有不合。
行78“八月白露莭,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與劉歆《三統曆》、賈公彦《周禮疏》相符,當爲《正義》原本。單疏刊本各添“八月”“九月”於兩“中”字之上,文意没有變化,而更易於理解。
行84“則以水喻礼”一句紧承上文,當來自《正義》原本,刊本不知何故删之。

行59疏訓“阻”爲“阻險”,易令人疑爲“險阻”之誤。刊本改作“險阻”,表意其實不如“阻險”妥帖。
行60“則得人之道,終不可至”,看似費解,其實不誤。刊本改作“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看似照應上文,實與全段不合。
行62“非礼必不得人心,不能固國”,看似欠通。刊本改作“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看似合理,深究其義,遠不如抄本恰當。
行81—82“故易傳興用周礼教民則服也”,“興”字似衍,其實絶不可少。刊本删之,看似平順,反令文意不通。
行98釋“晞”字引述《湛露》“露盡物乾”之意,“物”字似衍,而實與《湛露》箋文、疏文相符。刊本删“物”字,未盡妥當。
上述凡十一條異文,我們認爲刊本優於抄本的僅有行29、78、55三條。實際上,諸條異文未必都是北宋勘官校勘之資。然而宋刊本改動唐抄《正義》之迹及其得失,由此得以概見。
抄本中的虚詞,有時較爲隨意,尤以句末語助爲甚,不宜深入推求。聊舉此卷與刊本虚詞的異文中,可能源自《正義》原本者三條,略窺刊本更改虚詞之迹。

行66“故”字前後兩句不具因果關係,刊本删之。然若著眼於全段,有“故”字更佳。
行83“未能用礼,未得人心”,刊本於後一“未”字前添“則”字,看似更通,而實與詩序不合。

刊本《小戎》疏文“韔”字,全卷皆作“暢”,與詩文之《釋文》或本符合,當係《正義》原本。刊本“韔”字與宋刊經注本一致。[注]參見行14校語。
刊本《蒹葭》疏文“宛”字,抄本兩處皆作“菀”,與詩文之《釋文》或本符合,當係《正義》原本。刊本“宛”字蓋據通行經注本改之。[注]參見行61校語。
全卷“知”“智”並見,“智”字皆爲名詞或形容詞,“知”皆爲動詞,無一相混,蓋《正義》原本如此。刊本統一作“知”,或有意將今字“智”還原爲古字“知”。

(三) 唐抄本與宋刊本的共通之處
除了宋初勘官之調整,由此卷還可推知《毛詩正義》唐抄本主體與宋刊單疏本可能具有的如下共通特徵。意即宋刊單疏本的這些特徵,當係承襲唐抄本,而非宋人新設。
1. 出文
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出文體例統一,每舉首尾二字(偶或三字,尾字往往删去句末語助),以“某某至某某”的形式引出疏文。注之出文以“傳”“箋”字領首,作“傳某某至某某”或“箋某某至某某”。若所釋文句較短,則引録原文,如《蒹葭》次章出文“傳晞乾”。序之出文以篇題章句領首,接詩序尾二字(含句末語助),或只具篇題章句、不加詩序,作“某詩幾章章幾句至某也”或“某詩幾章章幾句”,例如“《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或“《出車》六章章八句”。
這種出文格式,究係唐抄《毛詩正義》舊式,還是一如《周易正義》是北宋勘官始確立的規範,需要校勘各件唐抄《毛詩正義》殘卷。[注]傳世唐抄本《毛詩正義》尚有俄藏敦煌出土《毛詩正義·思齊》抄本殘片Дx.09328、英藏敦煌出土《毛詩正義·民勞》抄本殘卷S.498、日藏《毛詩·韓奕》《江漢》經注及正義古抄本。除此卷外,敦煌本《民勞》正義的出文也具有研究價值。此卷涵蓋15處出文,多與單疏刊本一致。行27、33、72出文有異,皆抄本之訛誤。行96則係異體字。惟行88箋之出文“箋”後多“云”字、行91傳之出文“傳”後多“曰”字,不免惹人懷疑《正義》原本出文偶有“云”“曰”等字,並不如單疏刊本整齊。
今檢宋刊十行本出文,箋之出文多“云”字者往往而有,如《魏風·陟岵》序之出文“箋云役乎至徵發”,《小雅·出車》三章出文“箋云往築至軍壘”,《南陔》等三篇出文“箋云三篇至之舊”,《南有嘉魚》末章出文“箋云壹宿至遲之”,《四月》首章出文“箋云徂猶至一夕”“箋云我先至亂世”,《瓠葉》序出文“箋云牛羊豕至賔客”等等。然單疏刊本箋之出文皆無“云”字。十行本疏文當以單疏刊本爲底本,而出文仍不同如此,知箋之出文或涉《毛詩》經注本箋文領首之標識“笺云”而增“云”字。彼雖後來南宋中期注疏合編本時妄作,移以視唐抄本,出文“云”字或亦出於類似原因而誤衍。此卷“傳曰”乃是緊接“箋云”的下一條出文,疑亦出於類似原因而誤衍。
排除抄本訛誤之後,可以推知與《周易正義》出文不同,《毛詩正義》唐抄本主體乃至《正義》原本《小戎》《蒹葭》二疏出文,原應與單疏刊本高度接近。宋刊單疏本出文,應主要承襲自唐抄本。
2. 空格
全卷出文前後皆留空格,以醒眼目,宋刊單疏本與此體例相同。至宋刊十行本以下,空格或改爲圓圈。
疏述一章大意,若毛、鄭異義,則以“毛以爲”“鄭以爲”别之,單疏刊本於“鄭以爲”之前空格。此卷行63“鄭以爲”前即留有空格,説明唐抄《毛詩正義》本來具備在“鄭以爲”前空格的體例,宋刊單疏本乃是承襲唐抄本。
3. 篇首
此卷殘存内容包括《小戎》疏尾至《蒹葭》疏首過渡之處,尤可寶貴。抄本於兩篇之間,並不提行,中間僅以空格區别。空格之下,《蒹葭》疏乃以包含篇題、章句的出文“《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領首。《蒹葭》疏首的空格體例和出文内容,單疏刊本皆與之吻合,至後來注疏合刻本始發生較大變化。而單疏刊本各篇之首,多與《蒹葭》疏相近(或不標詩序尾字)。由此可以推知,宋刊單疏本《毛詩》各篇疏文領首處,主要因襲唐抄本之舊。
4. 引《定本》
《五經正義》所引《定本》問題複雜,目前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存世唐抄《正義》涉及《定本》者,據筆者所知僅有兩件。一爲日本安倍氏舊藏《大雅·韓奕》《江漢》正義,一爲此卷。彼本是《毛詩正義》的節録本,删去了其所對應刊本全部8處《定本》内容,不免讓人懷疑《定本》内容是否有可能爲宋人新添。此本行94至96正涉及《定本》内容,雖不能使《定本》問題獲得突破,至少能够提供一個最基本的討論前提: 唐人《正義》原本已引《定本》。
四、 總 結
北宋國子監面對《五經正義》唐抄本歧異,校勘形成標準的“定本”梓行,這一工作勢必在糾正抄本舛訛的同時,也泯滅了文本的個性和活力,甚至可能改變《正義》撰人的原意。本研究試圖通過重校唐抄《正義》,窺知當時校勘工作的具體情況,勘官對唐抄本做了何種程度的改訂。
繼敦煌本《周易正義·賁卦》之後,本文此次以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校勘唐抄《秦風·小戎》《蒹葭》正義。通過分析各類異文,可以推知北宋校勘官對唐抄《毛詩正義》作了一系列核對引文、調整文句、更改用字的工作。宋人的這些校勘工作,對唐抄本主體乃至《毛詩正義》原本的更動,得失互見。同時,我們還可推知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關於出文、空格、篇首的一些體例和引用《定本》内容,當主要源自唐抄本,而非北宋勘官新設。對於北宋官校《五經正義》更全面的認識,尚待校勘其他唐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