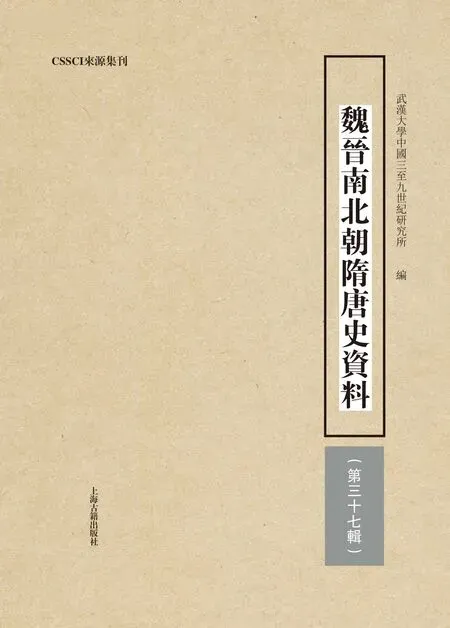唐肅宗改元寶應事發微
2019-01-19豆興法
豆興法
年號作爲皇權的符號,其選擇與使用具有豐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如果説國號是某姓政權的象徵,具有“公”的性質;那麽年號則是皇帝個人的象徵,凸顯“私”的性質。上到國家行政,下到百姓日常,皇帝個人的權威可以通過年號的廣泛使用,滲透到帝國的各個角落。因此,自漢武帝創立年號紀年以來,歷代皇帝基本行用不廢。[注]有關漢武帝創立年號紀年的研究,參見辛德勇: 《重談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的啓用時間》,《文史》2009年第1期,第43—90頁;收入氏著《建元與改元: 西漢新莽年號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第1—101頁。辛先生在此書自序中提出年號是年代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用“年號學”來界定與年號研究相關的問題。漢武帝之後,仍有少數皇帝和政權並未采用年號紀年。參見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65—76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1—399頁。至明清兩朝,年號更發展成爲皇帝的代稱。然而上元二年(761)九月,唐肅宗卻下詔去年號、改正朔。[注]《唐大詔令集》卷四《去上元年號赦》,北京: 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3頁。這在唐史上是僅有的一例,其中深意,孫英剛先生已有很好的解讀。[注]參見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65—76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71—399頁。本文關注的是僅僅半年後,病危之際的肅宗又下詔令太子李豫監國,並以楚州獻寶爲由,重新啓用年號紀年——改元寶應。[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263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762),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7242—7243頁。
肅、代二帝權力交接之際,正處於安史之亂即將平定,藩鎮割據也幾成定局之時。此時唐廷面臨的情況複雜多變,對於這一時期的政治局勢,學界早有注意。[注]黄永年: 《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中國唐史研究會編: 《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4—249頁;收入氏著《文史存稿》,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26—251頁;林偉洲: 《安史之亂與肅代二朝新政權結構的開展》,新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但對於肅宗改元寶應,學界關注不多。[注]一些研究雖未直接涉及寶應年號問題,但其研究思路和觀察角度給予我們很大啓發。參見黄永年: 《唐元和後期黨争與憲宗之死》,《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2年,第197—213頁;收入氏著《文史探微》,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第450—467頁。凍國棟: 《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僞號”行用及吏民心態——附説“僞號”的模仿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2003年,第 176—186 頁;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9—277頁。辛德勇: 《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文史》2012年第3輯,第81—161頁;收入氏著《建元與改元: 西漢新莽年號研究》,第119—240頁。孫英剛先生在討論肅宗去年號、改正朔問題時,論及改元寶應之事,但由於孫先生文章重點並不在此,所以未展開討論。[注]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76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98頁。肅宗下詔令太子李豫監國、改元寶應等一系列舉動包含以往學界所忽視的肅、代皇位交接之際的諸多細節,還關涉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唐代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問題。[注]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36、246頁。如果着眼這些細節進行深入闡發,透析年號産生背後複雜的政治背景,可以進一步深入認識肅、代之際的政局及皇位繼承問題。本文擬對唐肅宗改元寶應及相關問題做一梳理,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楚州獻寶始末
要討論改元寶應問題,必須從改元的直接原因——楚州進獻符瑞開始,而這又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密切相關,故簡要論述之。
(元年建巳月)壬子,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 (依次爲玄黄天符、玉雞、穀璧、西王母白環、碧色寶、如意寶珠、紅靺鞨、琅玕珠、玉玦、玉印、皇后采桑鈎、雷公石斧、闕名)十三寶置於日中,皆白氣連天。侁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升,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曰:‘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寅,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崩於西内神龍殿。上自仲春不豫,聞上皇登遐,不勝哀悸,因兹大漸。乙丑,詔皇太子監國。[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62—263頁。按《舊唐書·肅宗本紀》云“十三枚”卻只列舉了十二件寶物名稱。《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在列舉寶物時云“十三缺”,可知第十三寶闕名。(第1374頁)
《新唐書》卷六《代宗本紀》載:
元年建巳月,肅宗寢疾,乃詔皇太子監國。而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建元。”乃以元年爲寶應元年。[注]《新唐書》卷六《代宗本紀》,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66—167頁。
自宋代以來,不少學者都已指出上帝賜寶之事乃是人爲製造,批評肅宗父子迷信鬼神,爲妖人所惑。[注](宋) 范祖禹: 《唐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161頁。(元) 鄭元祐: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李修生主編: 《全元文》卷一二九,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638頁。清代喬萊並没有止步於此,他認爲:“崔圓者,太子少師也。真如獲寶時,圓出爲節度使。意者,圓授意崔侁,侁假手真如詐爲瑞應,安太子也。”[注](清) 劉寶楠: 《寶應圖經》卷首上,臺北: 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9頁。日本學者中村裕一認爲:“楚州距長安約二千五百唐里,如果楚州刺史的報告是接到中央具有政治意圖的授意後作出的,那麽恐怕皇太子監國一事必須很早就已在中央策劃好了。”[注](日) 中村裕一: 《關於唐代的制書式》,收入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7頁。王永平先生則認爲:“令肅宗感到不安的是,安史叛軍尚未完全消滅殆盡,李唐皇統能否傳之‘萬代’尚未可知,所以他憂心忡忡。四月,就在他病入膏肓、傳命太子監國之際,還導演了上帝賜十三寶的故事。”[注]王永平: 《道教與唐代社會》,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9頁。以上三位在符瑞製造者身份問題上有所分歧,但對於製造者的目的卻有大致相同的結論——都認爲是爲了穩固太子李豫的地位。那麽楚州獻寶的製造者是誰?此次獻寶事件果真是爲了太子李豫而策劃的嗎?在討論改元寶應事之前,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回答。
喬萊提出淮南節度使崔圓主導了此次獻寶事件,其主要依據應是《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載: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爲尼,號曰真如……(上帝賜寶後)翼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恒……翼日(崔)侁至,恒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圓爲録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爲若何。”圓懼而止。侁乃遺盧恒隨真如上獻。[注](唐) 蘇鶚: 《杜陽雜編》,《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北京: 中華書局,1961年,第3254—3256頁。需要説明的是,今傳本《杜陽雜編》並無此條,可能是曾有收録但此後散佚了。(宋)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引楚州刺史鄭輅《得寶記》所載與此條高度相似,兩者應有同一史源。唯一不同是案驗寶物的環節,《得寶記》用“真如具以聞官”一句帶過,並未涉王滔之、盧恒、崔圓等人。(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2464頁)鄭輅應是唐人,但生卒年不詳,兩《唐書》無傳。(宋) 王象之: 《輿地碑記目》卷二《楚州碑記》云:“唐《得寶記》,楚州刺史鄭輅撰。舊有碑,今在寶應縣。”(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39頁)郁賢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編》將其記入卷一二四《楚州·待考録》,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03頁。
由材料可知,除正史中提到的尼姑真如與楚州刺史崔侁,此次獻寶還涉及安宜縣攝縣令王滔之、楚州刺史從事盧恒、淮南節度使崔圓三人。但由於史料缺乏,我們無法獲得關於真如、崔侁、王滔之、盧恒等人更多的信息。所幸崔圓是肅宗朝重臣,相關史料較多,可以延展我們的討論。
王滔之、盧恒、崔侁、崔圓等地方官員案驗寶物之事,雖僅見於《杜陽雜編》,但筆者認爲應當存在這一過程。理由有三: 其一,《杜陽雜編》雖是成書於晚唐的筆記小説,但其所敍史事頗有被《新唐書》《資治通鑑》所取者。[注]黄永年: 《唐史史料學》,北京: 中華書局,2015年,第158頁。其二,上奏和進獻符瑞是唐代地方官的基本職責,也屬於地方官員的考課内容。[注]《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第1919頁;(日)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 《唐令拾遺》考課令第十四,長春出版社,1989年,第261頁。按唐代《儀制令》規定,地方官員發現符瑞後,首先需要對其進行案驗,確定無誤才能上報。[注]《唐會要》卷二八《祥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新1版,第618頁。其三,《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載:“其楚州刺史並出寶縣官及進寶官等,量與進改。隨進寶官典傔等,各量與一官。”[注]《唐大詔令集》卷三《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第113頁。楚州刺史、出寶縣官、進寶官正對應了崔侁、王滔之、盧恒三人。詔書中雖未提及崔圓,但彼時崔圓確爲淮南節度使。[注]《舊唐書》卷一八《崔圓傳》,第3279—3280頁。其治下官員預謀向中央進獻符瑞,崔圓不可能不參與其中。那麽,果如喬萊所言,符瑞是崔圓爲鞏固太子地位而造?筆者認爲這種可能性很小。崔圓確曾在乾元元年(758)五月,任太子少師。上元二年(761)二月出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時仍兼任太子詹事。[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52、260頁。但唐玄宗爲控制太子勢力,已將東宫體制非實體化,太子與東宫官的政治關係日趨疏遠。[注]任士英: 《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98—199頁。唐肅宗很可能也繼承了此種政策,而且肅宗本人即在朔方軍的支持下擅自登基,對於太子結交地方軍政大員之事,應當十分敏感。所以崔圓是不可能自作主張爲太子李豫製造符瑞的。
那麽是否如中村裕一先生所説,中央早就有令太子監國的計畫;或者像王永平先生所説,肅宗憂心李唐皇統的延續,所以指使地方官員製造象徵太子天命的符瑞呢?筆者認爲崔圓等地方官員製造符瑞,有可能是中央授意,但製造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太子李豫。首先太子李豫能否順利繼承皇位,除了安史叛軍的威脅以外,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唐肅宗的張皇后。[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一,肅宗上元元年(760),第7212頁。張后在肅宗朝干預政事,權勢頗盛。肅宗雖有不滿,卻無可奈何。[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張皇后傳》,第2185—2186頁。乾元二年(759)正月肅宗加尊號,張后暗示百官請肅宗給她加尊號曰:“翊聖”,顯然是想要模仿唐中宗韋后。[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載:“百官請加皇后張氏尊號曰:‘翊聖’”(第254頁)。神龍三年(707)九月庚子,中宗加尊號“應天神龍”,同時韋后也加尊號“順天翊聖”。見《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第145頁。張后也一直希望肅宗立其子興王李佋爲太子。[注]《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第3560頁。更重要的是,前文已指出楚州所獻寶物中有一寶名爲“皇后采桑鈎”。乾元二年(759)三月,張皇后曾“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内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張皇后傳》,第2186頁;《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55頁。其聲勢儼然與武后祭祀先蠶相媲美。[注]武后曾多次舉行祭祀先蠶的典禮。見《舊唐書》卷四、卷五《高宗本紀》第75、98、100頁。如果肅宗想要利用符瑞宣示李豫的天命,又怎麽會容忍製造出來的符瑞中有“皇后采桑鈎”這一明顯對應張后符命的寶物?[注]象徵天命的符瑞中出現了“皇后采桑鈎”,也從側面反映出張皇后在肅宗朝的影響力。此外,元年建巳月壬子(762年四月初三)肅宗接到楚州獻寶,群臣表賀。[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762),第7241頁。需説明的是《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記載寶物達京的具體時間爲“建巳月十三日”(四月十三日)。但《杜陽雜編》所載爲孤證,《舊唐書·肅宗本紀》《新唐書·肅宗本紀》《册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均記爲“建巳月壬子”(四月初三)。所以《杜陽雜編》所載應是“建巳月三日”之誤。即使所記爲確,十三日接到獻寶後,肅宗的答詔也能證明楚州符瑞並非爲太子李豫所製造。肅宗答詔曰:“太寶禎符,時膺昌運,皇天不秘,紫府降靈。……股肱奉上,宗廟福予,豈唯朕躬,致此嘉瑞,卿咸有一德。……所請宣示中外、編入史册者依。”[注]《册府元龜》卷二五《帝王部·符瑞四》,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第266頁。這裏肅宗顯然認爲楚州所獻寶物是自己的符命,並没有提到太子李豫。綜上所述,楚州所獻符瑞並非特地爲太子李豫而製造。崔圓、崔侁等淮南地方官員製造符瑞的動機,須結合楚州地方與中央的政治局勢方能理解。
出寶地安宜縣,位於江蘇省中部,唐代屬淮南道楚州治下。[注]參見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册,北京: 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54頁。唐代因尼姑獻寶,更名寶應縣,沿用至今。[注]《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三》,第1573頁。明嘉靖年間,知縣岳東升建有八寶亭。此亭后損毁,清代重修。見(明) 岳東升: 《得寶河記》、(清) 葉維庚: 《重建八寶亭記》,見道光《重修寶應縣志》卷二四,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063—1065,1124—1125頁。“八寶亭”之名當是岳東升等以爲唐時天帝只賜真如八寶,忽視了有關前五寶的記載。如《杜陽雜編》載天帝對真如説,“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見《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第3255頁。安史之亂爆發後,楚州所在的江淮地區成爲唐朝最重要的財賦來源之地,是國家命脉之所在。因爲中央政策失誤,上元元年(760)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叛亂。[注]相關研究參見李碧妍: 《從“劉展之亂”看唐肅宗的江淮政策》,《學術月刊》2010年10月,第130—137頁;收入氏著《危機與重構: 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42—456頁。直到上元二年(761)正月,才由田神功、李藏用等人平定。“劉展之亂”使江淮地區遭受嚴重破壞。史稱:“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上元二年(761),第7223頁。二月,肅宗任命崔圓爲淮南節度使,處理亂後江淮地區事務,足見對他的信任。[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60頁。九月,江淮發生饑荒,人相食。十月,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旋即李藏用竟也因“謀反”被殺。[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上元二年(761),第7235頁。此事縱然是由李藏用和高幹的私人恩怨引起的,但畢竟是在其治下發生了動亂,淮南節度使崔圓難辭其咎。肅宗元年(762)建辰月(三月),發生了預示災異的天象。史稱:“建辰月,肅宗病。是月丙戌,月上有黄白冠連成暈,東井、五諸侯、南北河、輿鬼皆在中。”[注]《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下》,第1325頁。緊接着,建巳月壬子(四月初三),楚州刺史崔侁就進獻有鎮災功能的定國寶玉十三枚。爲更直觀的展現天象與楚州所獻寶物的關係,兹列表如下:

表一 天象、災異與楚州寶物對照表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楚州所獻寶物功能與天象災異之間有明顯的對應關係。肅宗元年(762)建辰月(三月)出現天文異象,建巳月(四月)楚州所獻定國寶玉就有相應的禳災功用,這應該不會是巧合。
唐肅宗對天文星占一直非常重視。乾元元年(758),肅宗特地對天文機構進行改革。[注]相關研究參見趙貞: 《乾元元年(758)肅宗的天文機構改革》,《人文雜誌》2007年第6期,第155—161頁;收入氏著《唐宋天文星占與帝王政治》,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1—52頁。乾元三年(760)閏四月,還曾因星文變異,改年號爲上元。[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59頁。關於上元年號的含義,參見孫英剛: 《“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 曆法、讖緯與隋唐政治》,《唐研究》第十八卷,2012年,第21—48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13—343頁。此次月暈所圍東井、輿鬼等其分野在秦,屬古雍州之地。[注]《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下》,第1313頁。預示着唐朝統治的核心區域長安等地會發生兵災、水旱和饑荒。如何應對此種天象,應該是肅宗十分關心的問題。筆者認爲崔圓有可能得到了不利天象的消息,於是製造了可以鎮災的符瑞來迎合肅宗。首先,崔圓此人政治嗅覺十分敏鋭。其任劍南節度使時,在玄宗入蜀之前就已派人打探到消息,提前準備接駕事宜,大受玄宗褒獎。[注]《舊唐書》卷一八《崔圓傳》,第3279頁在肅宗朝又與李輔國交往密切,得到肅宗的寵任。[注]《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琯傳》,第3322頁。崔圓想必十分了解肅宗喜好陰陽鬼神之説。[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上元二年(761),第7234頁;《資治通鑑》卷二二六,代宗大曆十四年(779),第7390頁。其次,新任楚州刺史崔侁上任不過半年就進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不得不讓人懷疑此事是崔圓爲了彌補過失,用獻寶的形式向中央表忠心。第三,楚州所獻十三寶都爲稀世珍寶。楚州曾爲大量胡商活動之地,具備收集寶物的條件。[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一,肅宗上元元年(760),第7221頁。參見蘇保華,王椰林: 《從〈太平廣記〉看唐代揚州的胡人活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69—73頁。第四,崔侁在表中特别强調天帝指示:“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63頁。第二寶名爲“玉雞”,按《宋書·符瑞志》云“玉雞,王者至孝則至。”[注]《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850頁。《舊唐書·五行志》也説:“玉雞,毛白玉也,以孝理天下則見。”[注]《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第1374頁。唐肅宗自立於靈武,本身就面臨着巨大的道德壓力。於是提倡“孝道”就成爲肅宗構建其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他在即位制書中説:“今群工卿士僉曰:‘孝莫大於繼德,功莫盛於中興。’朕所以治兵朔方,將殄寇逆,務以大者,本其孝乎。”[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42頁。關於肅宗孝道問題,參見齊子通: 《孝道與悖逆之間: 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第205—222頁。强調他自立的動機在於“盡孝”。肅宗登基後改年號爲“至德”。《孝經》開篇就講:“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經注疏》卷一《開宗明義章第一》,(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第2545頁。“至德”一詞含義甚明。收復長安後,肅宗遠迎玄宗至望賢宫、下馬趨進、蹈舞稱慶、親自進食、牽馬導行等行爲,在萬民的注目下親自示範了“孝”。[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49頁。據《杜陽雜編》和《得寶記》記載,天帝賜寶的時間在建子月十八日,此日正是肅宗朝見唐玄宗的日子。[注]《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第3254頁;《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引《得寶記》,第2464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上元二年(761)建子月條載:“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内。”(第7236頁)從這種時間上的巧合可以看出楚州符瑞是爲迎合肅宗而製造的。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崔圓、崔侁等淮南地方官員所製造的楚州獻寶活動,是爲了迎合肅宗及其應對異常天象的需求而精心策劃的,此次符瑞事件在製造之初是爲了彰顯唐肅宗而不是太子李豫的“天命”。
二、 肅宗改元寶應諸疑點
然而楚州符瑞的歸屬在肅宗病危之際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四月十六日,肅宗突然下詔稱寶物象徵太子李豫的天命,令太子監國並改元。[注]《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云:“四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即建巳月甲子,這應該是制書起草的日期。《舊唐書》等記建巳月乙丑(四月十六日)應當是詔書發布的日期。參見 中村裕一: 《關於唐代的制書式》,收入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第306頁。《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載:
皇太子豫……宜令權監國。又以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告歷數之符,金璧定祅災之氣。總集瑞命,祗承鴻休。因以體元,叶于五紀。其元年宜改爲寶應元年,建巳月改爲四月,其餘月並依常數,仍舊以正月一日爲歲首。受兹福應,佇以升平。……其楚州刺史并出寶縣官及進寶官等,量與進改。隨進寶官典傔等,各量與一官。宣示中外,咸知朕意,主者施行。[注]《唐大詔令集》卷三《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第112—113頁。
制書明言天賜寶物乃是神明昭告天下“歷數”之所在,且此十三寶有鎮災的作用。所謂“歷數”是指帝王繼承的次序。[注]《論語注疏》卷第二《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十三經注疏》,第2535頁。)(漢) 蔡邕《光武濟陽宫碑》云:“歷數在帝,踐祚允宜。”見(唐)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卷一二《帝王部二·後漢光武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237頁。制書稱太子李豫集祥瑞符命於一身,理應繼承大統。於是據此改元寶應,仍以正月一日爲歲首,並表示有了寶物的福應,升平之世就要到來,最後對獻寶官員等進行獎賞。《唐大詔令集》所載此制書後附有宰相裴遵慶等人的覆奏曰:
伏惟皇太子,承累聖之資……況神告其符,天不秘寶。克昌景命,必静祅氛。豈謝金縢啓翌日之期,玄符告彝倫之敍……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注]《唐大詔令集》卷三《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第113頁。
門下省的覆奏指出神明降寶,應太子李豫之德,彰顯了太子的天命。他一定能光大祖宗基業,平定叛亂。“玄符告彝倫之敍”意爲玄符指明了皇位繼承的順序。至此,楚州所獻寶物,經歷了從獻寶之初(四月初三)對應肅宗之德到太子監國時(四月十六)對應太子李豫之德的轉變。
那麽爲何肅宗要在接受楚州獻寶十三天之後,突然宣稱寶物昭示了太子李豫的天命,將十三寶授予太子呢?此外,四月初三肅宗就收到了地方進獻的寶物,但只是編入史册、宣示中外。爲什麽要到命太子監國時才對相關獻寶人員進行賞賜?這裏提出一個猜想,即肅宗一開始將楚州所獻寶物當做自己的符命,他病危之際,對於太子李豫能否順利繼位充滿擔憂。於是,藉口楚州曾是太子李豫的封地,改稱此次天降寶物乃是昭示李豫的天命,將楚州所獻定國寶玉作爲政治遺産留給李豫。此時才對相關獻寶人員進行賞賜,是爲了替李豫進行宣傳並收攏人心。
但我們知道,上元二年(761)九月肅宗實行了去尊號、去年號、改正朔等一系列較爲極端的措施。[注]《唐大詔令集》卷四《去上元年號赦》,第23頁。孫英剛先生指出肅宗的這些做法並無謙遜之意,反而是含有“復舊維新”的“革命”意味,是充滿深意的政治手段。[注]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74—75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94—396頁。因此,肅宗在命太子監國之際(元年四月十六日)放棄了自己曾非常重視的政策,顯得很突然。緊接着發生張后政變,十八日,肅宗駕崩。二十日,太子李豫繼位。短短五天,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使得改立年號事件顯得撲朔迷離。
孫英剛先生認爲:“改元年爲寶應元年的事情就發生在肅宗駕崩的前一天。很難相信對此事肅宗仍然有行動能力或者決策能力。廢黜肅宗的‘革命’措施,重新定立年號等舉動,很大可能是出自後來的追加或者李輔國等人的操弄。”但由於没有確鑿的證據,孫先生又説:“我們難以接受肅宗毫無徵兆地廢除了自己一手打造的意識形態。不過也有可能,在玄宗死後,肅宗頓感無須再行‘革命’之事,突然想向舊傳統復歸。”[注]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76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98頁。
所謂“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注]《通典》卷五五《禮·告禮》,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1542頁。新君繼位、國家改元之類的大事在民間墓誌中經常有所體現。[注]如《劉感義墓誌》記肅宗去年號、《劉暹墓誌》記代宗改元大曆、《常無名墓誌》記玄宗改元天寶、《江師武墓誌》記懿宗改元咸通等。以上墓誌見胡戟,榮新江主編: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01、605、629、955頁。肅宗改元寶應之事也有可能體現在這一時期的墓誌中。但據《大唐故永王第二男新婦河東郡夫人宇文氏墓誌銘并序》載:“(宇文氏)以元年建卯月(二月)卅日夭於内宅,時春秋廿四矣。即以其年建巳月廿一日(四月二十一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滋水鄉原,禮也。”[注]景亞鸝: 《西安碑林藏唐〈宇文氏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第93—97頁。墓主宇文氏爲永王李璘的兒媳,墓誌作者吴通微時任校書郎,書者李倩爲肅宗之侄。肅宗下詔改元這樣的大事,在長安爲官的吴通微等人必能很快獲知,但此方墓誌中並未體現改元之事。常見的原因是在改元之前墓誌就已刻好,下葬時並未進行改動。但需要注意宇文氏作爲肅宗的侄媳,其喪事由禮部、鴻臚寺負責辦理。[注]《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載:“皇親三等以上喪,舉哀,有司帳具給食”。(第1194頁)《唐六典》卷一八《大理寺鴻臚寺》,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504—505頁。四月十六日肅宗下詔改元,二十日代宗已即位,二十一日宇文氏下葬。墓誌刻畢後進行改動是常有的現象,[注]參見徐沖: 《從“異刻”現象看北魏後期墓誌的“生産過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102—113頁;彭國忠: 《從紙上到石上: 墓誌銘的生産過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34—49頁。修改年號並不複雜。我們知道,永王璘因與肅宗對抗而被殺并廢爲庶人。[注]《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永王璘傳》,第3612頁。墓誌在敍述宇文氏事迹時並未提及永王璘,對其夫也語焉不詳,顯示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禮部、鴻臚寺官員熟知禮典,怎會没注意到墓誌中没有使用寶應年號?所以可能的解釋是直至四月二十一日,唐朝仍未改元寶應。换言之,四月十六日的改元詔書很可能如孫先生所説,是後來追加的。
三、 太子李豫的困境
史書中所載唐肅宗在病危之際賜寶、改元之事,無論真實與否,楚州所獻寶物和寶應年號都在事實上成爲肅宗留給太子李豫的政治遺産。楚州符瑞雖非如喬萊等人所説,專爲太子而製造,但他們認爲此次符瑞事件有利於太子繼位和政局穩定,卻是正確的。鑒於以上提到的諸多疑點,筆者認爲推動此次改元的正是此事的最大受益者——太子李豫即唐代宗。
衆所周知,作爲“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的符瑞,其主要作用是彰顯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但符瑞中含有“有德者當王”的政治邏輯,所以也有潛在的政治風險。[注]魏斌: 《孫吴年號與符瑞問題》,《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第31—55頁。一般只有在面臨重大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才會使用。如貞觀十七年(643)秋八月,涼州出現瑞石五塊,銘文稱太宗新立太子李治爲“千年太子”。其政治背景是這一年太子李承乾政變失敗,唐太宗放棄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另立李治爲太子。但李治太過仁弱,於是太宗采用涼州瑞石來穩固李治的太子地位。[注]相關研究參見孫英剛: 《“太平天子”與“千年太子”: 6—7世紀政治文化史的一種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42—50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101—133頁。太宗的此種做法與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燾利用瑞石來鞏固太子拓跋晃的皇位繼承人地位非常相似。[注]拓跋燾利用符瑞之事參見何德章: 《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2000年,第46—59頁。
唐代宗李豫生於開元十四年(726),他既是唐肅宗的長子,又是唐玄宗的長孫。[注]《新唐書》卷六《代宗本紀》,第166頁。肅宗北奔靈武時,李豫典兵扈從。至德二載(757),其作爲天下兵馬元帥統軍先後收復兩京。在叛軍尚未平定,政局動蕩之際,身爲長子又立下大功的李豫應當是太子的最佳人選。肅宗在乾元元年(758)五月,立李豫爲太子。[注]《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第252頁。此時李豫已32歲,太子之位似乎比較穩固,爲何需要用符瑞來鞏固其地位?更甚者,李豫直接佔用了肅宗已宣示中外的符瑞,並且違背肅宗去年號的政策,設立寶應年號。
這就要從李豫的特殊身份説起。所謂“立嫡以長”,李豫雖爲長子,卻不是嫡子。開元十三年(725),唐肅宗李亨被封爲忠王時,納韋氏爲孺人。[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韋妃傳》,第2186頁。按唐制,孺人視正五品。[注]《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第1821頁。同年,李豫生母吴氏被玄宗賜予李亨。吴氏爲掖庭宫人,身份低微,雖生下長子李豫,卻一直没有位份。[注]代宗繼位後追謚吴氏爲章敬皇后。《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章敬皇后吴氏傳》,第2188頁。開元二十六年(738),李亨被立爲皇太子,韋氏被册爲太子妃。[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韋妃傳》,第2186頁。韋氏之子李僴,雖爲李亨第六子,身份卻是嫡子。[注]吕思勉先生已指出:“若論正適,則肅宗第六子兗王僴,爲韋妃所生。”見氏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3頁。直至天寶五載(746),李亨與韋氏離婚。此後,續娶張氏爲良娣。張氏先後生下李佋、李侗。乾元元年(758)四月,肅宗立張氏爲皇后,李佋自然成爲嫡子。[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張皇后傳》,第2185頁。上元元年(760),李佋去世,李侗則爲嫡子。[注]《舊唐書》卷一一六《肅宗代宗諸子·恭懿太子佋傳》,第3388頁。
肅宗長子李豫的身份與唐高宗長子李忠類似,兩人雖是長子,生母身份卻很低微。[注]《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燕王忠傳》,第2824頁。永徽三年(652),李忠被立爲太子。永徽六年(655),武則天被立爲皇后。隨後許敬宗上疏請改立武則天長子李弘爲太子,主要理由即是現任太子李忠並非皇后所生之嫡子。[注]同上。也正是基於這個理由,肅宗在立太子問題上,曾猶豫不決。史言:“張后生興王佋,才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注]《資治通鑑》卷二二,肅宗乾元元年(758),第7172頁;《舊唐書》卷一一六《肅宗代宗諸子傳·恭懿太子佋傳》載:“佋,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锺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第3388頁)李佋年紀雖小,卻是嫡子又深爲肅宗喜愛,具備被立爲太子的資格。但是肅宗考慮到李豫年長又有大功,最終選擇立李豫爲太子。但即使李豫被立爲太子之後,張后之子李佋、李侗,韋妃之子李僴,曾爲天下兵馬元帥的肅宗第二子李係[注]《舊唐書》卷一一六《肅宗代宗諸子·越王係傳》,第3382頁。都是皇位的潛在競争者。雖然《舊唐書》云:“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注]《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肅宗張皇后傳》,第2186頁。但从此後張后等人發動政變來看,李豫的儲位只是暫時穩固,其太子身份並不足以保證他順利繼位。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指出,唐代“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及新舊君主接續之交,輒有政變發生,遂爲唐代政治史之一大問題也。”[注]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46頁。在李豫之前,唐代尚未有長子成功繼位,也未有首任太子繼位的先例。就在肅宗病危之際發生了張后政變,關於她發動政變的目的,史書中有兩種説法。一説是爲了除掉李輔國。如《肅宗實録》云:“張后因太子監國,謀誅輔國。”[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762)《考異》引《肅宗實録》,第7243頁。《舊唐書·越王係傳》也載:“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宫。”[注]《舊唐書》卷一一六《肅宗代宗諸子·越王係傳》,第3383頁。另一説則是爲了除掉太子李豫。《舊唐書·代宗本紀》云:“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后懼上功高難制,陰引越王係於宫中,將圖廢立。”[注]《舊唐書》卷一一《代宗本紀》,第268頁。《舊唐書·程元振傳》也云:“寶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係入宫,欲令監國。”[注]《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程元振傳》,第4761頁。黄永年先生已指出《肅宗實録》爲了隱諱代宗爲李輔國擁立之事而歪曲真相。[注]黄永年: 《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唐史研究會論文集》,第224—249頁;收入氏著《文史存稿》,第226—251頁。筆者贊同黄先生的觀點,同時認爲《肅宗實録》將政變爆發原因歸結爲張后與李輔國的矛盾,也有爲代宗開脱“弑母”嫌疑的考慮。可見張后一黨的目的是廢掉太子李豫,另立越王係。據《代宗實録》載,政變之後,群臣討論係、僴之罪,云:“二王同惡,共扇奸謀。”[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762)《考異》引《代宗實録》,第7243頁。可見兗王李僴也參與了政變。
關於政變當日的情形《肅宗實録》云:
景(丙)寅,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越王及同謀内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繫之,移皇后於别殿。其夜,六宫内人、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肃宗寶應元年(762)《考異》引《肅宗實録》,第7243頁。
《資治通鑑》的記載更令人震驚,云:
係乃命内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别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宫,宦官宫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僴。[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肃宗寶應元年(762),第7242—7243頁。
肅宗所在的長生殿是雙方人員廝殺的主戰場,病危之際的肅宗若還有神智,定會被此番景象所驚嚇。在平定政變的過程中,張后、李係、李僴以及張后幼子李侗均被殺。[注]《舊唐書》卷一一六《肅宗代宗諸子傳》,第3383、3387—3388、3390頁。太子李豫不僅有“弒母殺弟”的嫌疑,其清除張后黨羽的舉動也加速了肅宗的死亡。换言之,李豫虽得以繼承皇位,但實際上也背負着一定的道德倫理壓力。
對於經過激烈政變才奪得政權的李豫來説,如何凝聚人心迅速渡過政治危機,如何向宫廷内外甚至天下臣民展示自己繼位的合法性就成爲最急迫的問題。既然傳統儒家政治文化中的長子、太子等符號已不足以充分證明李豫繼位的合法性,象徵天命的符瑞自然會進入他的視野。不久前發生的楚州符瑞事件,提供了一個絶好的機會。寶物出自楚州,給曾經爲楚王的李豫提供了天然的借口。[注]鑒於代宗本人十分迷信,筆者傾向於認爲此時代宗有可能確實相信他能贏得政變登上皇位乃是天命所歸。《舊唐書》卷一一八《王縉傳》云“代宗喜祠祀”,第3417頁。《資治通鑑》卷二二六,代宗大曆十四年(779)云“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第7390頁。李豫不顧忌肅宗已宣明符瑞應己之德,也不顧忌十三寶中有象徵政敵張后符命的“皇后采桑鈎”而將符瑞據爲己有,也反映出他對證明其繼位的合法性有着極爲迫切的需求。
四、 寶應年號的政治意義
使用符瑞年號的實質是符瑞崇信,符瑞年號背後體現的是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取向。[注]魏斌: 《孫吴年號與符瑞問題》,《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第33頁。設立寶應年號的政治意義也應結合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來理解。池田温先生認爲建立年號:“就如同給年代取名字一樣,爲祈盼將要到來的時代的昌盛而加以命名。”[注]池田温撰,羅莉等譯: 《日本和中國年號制度的比較》,劉俊文、池田温主編: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250頁。首創《符瑞志》的沈約云:“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注]《宋書》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59頁。統治者選擇符瑞作爲年號看中的是符瑞對政權的維護作用,這也是沈約説“符瑞之義大矣”的原因。符瑞作爲政治合法性和天命的代表,在重大的政治時刻總會見到符瑞的出現,用符瑞作爲年號是其表現形式之一。隋末群雄並起,各自宣稱其爲天命所在。從各個割據政權所選擇的年號就可見一斑,如林士弘的太平、劉武周的天興、竇建德的五鳳、劉黑闥的天造、蕭銑的鳴鳳、宇文化及的天壽等等。以上年號都體現了諸割據政權對天命的争奪,竇建德和蕭銑更是直接將符瑞作爲年號。李唐建國之初雖然也利用符瑞進行政治宣傳,但並没有達到使用符瑞年號的程度,這也反映出李唐的政治自信。但此後李唐統治者在面臨政治危機時也開始使用符瑞年號來彰顯其權力的合法性,如高宗的龍朔、麟德、[注]參見孫英剛: 《“辛酉革命”説與龍朔改革: 7—9世紀的緯學思想與東亞政治》,《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第31—41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44—370頁。儀鳳,[注]參見韓昇: 《上元年間的政局與武則天逼宫》,《史林》2003年第6期,第40—52頁。睿宗的景雲[注]參見余欣: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 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4期,第325—378頁。等。
設立寶應年號也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從國家層面看,安史之亂爆發後,李唐王朝的統治合法性受到嚴重威脅,政治權威遭受巨大打擊。叛軍建元稱帝與李唐分庭抗禮,還大肆宣揚金土相代,李唐喪失天命。[注]参見仇鹿鳴: 《五星會聚與安史起兵的政治宣傳——新發現燕〈嚴復墓誌〉考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114—123頁。燕政權所采用諸如“天成”“應天”“順天”“顯聖”等年號明顯含有承天應命、順天應道的意味。[注]有關安史政權年號問題,參見凍國棟: 《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僞號”行用及吏民心態——附説“僞號”的模仿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2003年,第 176—186 頁;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第259—277頁。甚至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謀反,也自稱梁王,改元黄龍。[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761),第7232頁。對於李唐政權來説,元年(762)建巳月(四月)“四十年太平天子”唐玄宗與“中興唐室”的肅宗相繼去世,朝野上下對於新君代宗能否掌控政局可能還存有疑慮。從宫廷政治層面看,在太子年長、有功的情況下,張后、越王等人仍預謀奪取皇位。可見唐代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此時仍在延續。在太子名號不能打消覬覦者野心的情況下,代宗急需通過符瑞的方式來彰顯其繼位的合法性。
使用符瑞年號可以利用年號廣泛適用的特性將符瑞藴含的政治意義傳達到帝國的各個角落。但肅宗上元二年(761)施行的去年號措施成爲了代宗使用符瑞年號的阻礙。《論語》有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論語注疏》卷一《學而第一》,《十三經注疏》,第2458頁。雖然肅宗的舉措充滿了鼎故革新與復古宗周之意,[注]孫英剛: 《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第73—75頁;收入氏著《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第391—397頁。但是對於經過激烈政變才得以繼承皇位的代宗來説,不使用年號只稱元年,會喪失掉一次在全國範圍内展示其皇權的重要機會。[注]例如北周世宗即位,依照《周禮》稱天王,不建年號但稱元年。御正中大夫崔猷就認爲:“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周書》卷三五《崔猷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1年,第616—617頁。)然而,剛繼位的代宗就擅改先帝之道,於理不合。於是在《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中代宗借肅宗的名義取消了去年號、改正朔的措施,以楚州獻寶昭示太子天命爲由,重新采用年號紀年,改元寶應仍以正月爲歲首。這是對“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注]《漢書》卷一上《敍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9頁。的最好詮釋,也是對妄圖篡奪政權的亂臣賊子的最好回應。
代宗繼位伊始就非常注重利用符瑞來增强其政治合法性,比如代宗登基當天慶雲、紫雲、白鶴、喜鵲、黄氣抱日等大量祥瑞同時出現。[注]《册府元龜》卷二五《帝王部·符瑞第四》,第266頁。我們知道,四月初三楚州地方官就將寶物進獻到朝廷。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太子監國時才對他們進行賞賜。[注]《唐大詔令集》卷三《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第113頁。《杜陽雜編》則明言代宗登基之後才對獻寶官員和尼姑真如進行賞賜:“上既登位,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注]《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第3256頁。足見代宗對於楚州所獻定國寶玉的重視程度要高於肅宗。
代宗對於寶應年號特别重視,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寶應年號是在代宗的影響下設立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將寶應年號加入到其尊號内。繼取消去年號、改正朔之後,代宗又取消了肅宗去尊號的做法,繼位第二年就采用“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的尊號。唐代將年號放入皇帝尊號中的做法源自中宗。神龍三年(707),中宗上尊號“應天神龍”。[注]《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第145頁。此後,玄宗、肅宗的尊號中都有各自的年號。[注]《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載:“(天寶元年)二月丁亥,上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第215頁)《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載:“(乾元二年肅宗)受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第254頁)玄宗因“天降寶符”改元天寶,又將“天寶”年號加入其尊號。代宗在位期間唯一的尊號是“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這個尊號應是對玄宗尊號的模仿。在唐人的文學作品中,代宗也曾被直接稱爲“寶應皇帝”。[注](唐) 圓照: 《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録》卷中載“我今寶應皇帝,再造乾坤,禮樂惟新”。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五卷《目録部》,台北: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第758頁。(唐) 王佑: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營田使清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并序》載“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全唐文》卷四四,第4484頁。
關於代宗尊號的含義,《資治通鑑》載:“(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胡注曰: 以楚州所獻十三寶爲上登極之符應也。”[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763),第7264頁。郭子儀等群臣的《上尊號表》對於此尊號的含義進行了細緻的説明:
若乃神告聖運,天呈寶符,陛下登極之辰,泗水見其五璧……降天休,呈地寶,有夏禹玄珪之感焉。經天緯地之謂文,立極中興之謂武,變化無方之謂聖,精誠上通之謂孝,降天和、騰地氣、生無期、出有爲之謂寶。文以昭之,武以定之,聖以成之,孝以通之,寶以應之,夫然後可以充天地之洪名,崇帝王之大號。故臣等犯冒萬死,奉上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尊號。[注]《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第185—186頁。
“陛下登極之辰,泗水見其五璧”明確指出了代宗登基與楚州符瑞的關係。[注]楚州即在泗水流域。見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册,第54頁。所謂“五璧”指的就是楚州所獻十三寶中的前五寶。[注]楚州所獻十三寶有五寶、八寶之分。見《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第3255頁。這裏只提五寶,有可能是爲了避諱八寶中的“皇后采桑鈎”。奏表中郭子儀刻意將楚州獻寶時間與代宗繼位時間並列在一起,認爲楚州符瑞乃是神明昭告代宗天命的明證,並將楚州所獻諸寶與傳説中的上帝授大禹玄珪作比。“寶應”意爲“寶以應之”,强調的是楚州所獻寶物對應代宗的天命與德行。直至代宗駕崩之後,德宗的《上睿文孝武皇帝册文》還特别强調代宗繼位之時“符瑞并臻”的景象:
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洊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注]唐德宗: 《上睿文孝武皇帝册文》,《全唐文》卷五四,第585頁。
楚州符瑞對於代宗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
其次是代宗一朝,經常將“寶應”年號作爲賜名。如賜作縣名,將獻寶地楚州安宜縣賜名爲寶應縣,一直沿用至今。[注]《太平廣記》卷四四“肅宗朝八寶”條引《杜陽雜編》,第3256頁。賜作寺名。唐代由官方建立並賜名的寺院衆多。在天下諸州建立官寺,始於高宗乾封元年(666)。[注]《册府元龜》卷五一《帝王部·崇釋氏一》,第574頁。載初元年(689)七月,僧人獻上《大雲經》爲武則天登基作輿論宣傳。[注]《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第121頁。武則天革唐爲周後,下令全國諸州建大雲寺。[注]《唐會要》卷四八《寺》,第996頁。武則天下令全國諸州建大雲寺的具體時間應爲天授元年(690)十月。具體考證見參見聶順新: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47—49頁。神龍元年(705)二月,中宗下詔,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佛寺、道觀。神龍三年(707)二月,改寺、觀名爲“龍興”。[注]《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第137、143頁。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下詔天下諸州大雲寺改爲開元寺。[注]《唐會要》卷四八《寺》,第996頁。天寶三載(744)三月,又詔:“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元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注]《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第926頁。這些寺、觀的設立均以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爲契機,如高宗封禪泰山、武后登基、中宗復辟、玄宗立太子等。[注]聶順新: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09頁。官寺是國家政治宣傳的窗口,在佛教徒數量日益膨脹的唐朝意義重大。從安史叛軍對開元寺的破壞就可以看出官寺的象徵意義。乾元二年(759)六月,史思明曾在開元寺内造塔,並將寺名改成其年號“順天”。[注]《資治通鑑》卷二二一,肅宗乾元二年(759),第7194頁。安史叛軍還大肆毁壞開元寺内的玄宗真容。[注]《舊唐書》卷一四二《李寶臣傳》載“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毁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户。”(第3866頁)代宗繼位後,也廣立寶應寺,用以宣揚其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十分明顯。《佛祖統紀》云:“寶應元年……敕長安立寶應金輪寺。”[注](宋)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 《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57頁。據《長安志》卷二《縣十·三原縣》載,寶應金輪寺在三原縣東北。(宋敏求撰,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潔點校: 《長安志·長安志圖》,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93頁。)除此寶應金輪寺外,長安還有寶應寺。[注]《舊唐書》卷一一八《王縉傳》云:“妻李氏卒,(王縉)舍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第3417頁)全國其他州縣也建有寶應寺,如洛陽寶應寺、[注](宋)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 《宋高僧傳》卷八《唐洛京菏澤寺神會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5頁。撫州寶應寺、[注]撫州寶應寺是大曆四年(769)地方官員爲代宗慶祝誕辰而建,奏請代宗賜名寶應寺。見(唐) 顔真卿: 《顔魯公文集》卷一三《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頁。滁州寶應寺[注]《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二載:“(大曆)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琊山建佛剎。’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游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第962頁)等等。
又如賜作功臣號和軍名。史稱“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注]《新唐書》卷五《兵志》,第1332頁。相關研究參見黄樓: 《唐代射生軍考》,《史林》2014年第1期,第61—67頁。實際上據《舊唐書·程元振傳》載:“(程元振)充寶應軍使。”[注]《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程元振傳》,第4762頁。又代宗《廣德二年南郊赦》也明言:“寶應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軍等”。[注]《唐大詔令集》卷六九《廣德二年南郊赦》,第385頁。可見“寶應軍”不是俗稱,射生軍也確被賜名“寶應”。
直到代宗統治末期的大曆十二年(777),“寶應”仍被用來賜名,如賜坊名、[注]“寶應經坊”見《長安志》卷一《唐京城四》,《長安志·長安志圖》,第330頁。賜瑞鹽池名。[注]“寶應靈慶池”見《舊唐書》卷一一《代宗本紀》,第313頁;《舊唐書》卷一二七《蔣鎮傳》,第3578頁。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以“寶應”年號賜名的情況,從代宗登基之初的寶應元年(762)一直持續到大曆十二年(777),足見“寶應”年號在代宗心中的地位。其臣下也投其所好,多次奏請代宗賜名寶應。
五、 結 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肅宗元年建巳月(762年四月)發生的楚州進獻符瑞事件并非淮南地方官員或肅宗爲鞏固太子李豫皇位繼承人地位而製造。這次符瑞事件是崔圓等爲了迎合肅宗及其應對異常天象的需求而精心策劃的。目的是爲了彰顯唐肅宗而不是太子李豫的“天命”。史書中關於肅宗改元寶應的記載存在諸多疑點,因此筆者認爲平定張后政變之後,代宗爲了增强其繼位的合法性,製造了肅宗改元寶應的詔書,取消了肅宗去年號、改正朔的政策。
符瑞之事本爲虚妄,乃是統治者神道設教的政治手段之一。但符瑞的真僞不應成爲關注的焦點,而是需要仔細分析符瑞的内容和制造過程,具體探析其所反映出的政治文化内涵以及制造者和利用者的思想動機。安史之亂帶來的不僅是國家的動亂,還嚴重動摇了李唐王朝一百多年來精心維護的政治合法性。同時,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唐代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問題,在肅、代權力交接之際也有明顯體現。玄宗、肅宗在同一月内先後去世,太子李豫繼位的合法性又受到了張后一黨的嚴重威脅。兩重合法性問題的重壓下,唐王朝顯得風雨飄摇,岌岌可危。寶應年號的使用,旨在以時人觀念中認同的符瑞形式,證明李唐皇權上符天命,太子李豫也是天意所屬的皇位繼承者。符瑞年號與以傳統政治理念爲基礎而形成的年號不同,它没有深奥的政治理論,相反,它具有簡潔的表達方式和易於理解的基本内容,因而能在日常使用中被帝國的普通百姓所感知。[注]國家公文、民間契約文書、墓誌、買地券等均會使用到年號紀年。
以往的研究都將注意力放在中央與地方在符瑞問題上的互動,地方進獻符瑞,中央接受並宣揚符瑞。其實,我們還應注意到將符瑞作爲年號是有别於宣示中外、付諸史館等慣用的宣揚符瑞方法,是一種中央與民衆互動的方式。中央頒布年號,民衆使用年號。年號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其與時間和日常生活的緊密關係。普通民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寶應年號,自然會聯想到它的由來,這就達到了代宗宣傳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寶應年號的使用會滲透到唐王朝的各個角落,會使天下百姓認識到楚州進獻的定國寶玉昭示着新任皇帝乃是天命所歸,在他的治理下太平之世即將到來。無論對於普通百姓還是代宗本人,在經歷過長達七年的戰亂之後,這一絲精神慰藉也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