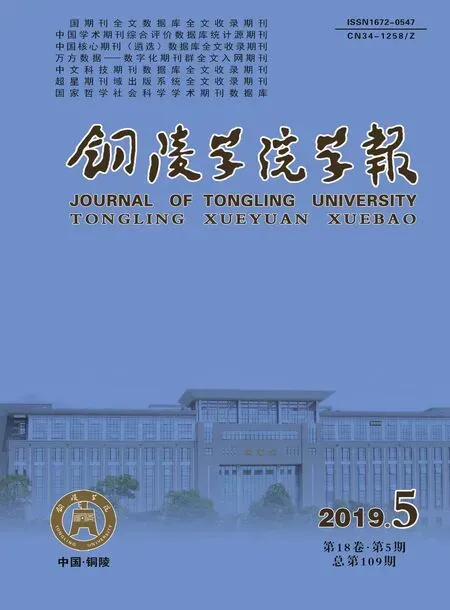浮沉于欲望之间
——论《屋顶上空的爱情》的城市书写
2019-01-21张文斌
张文斌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迅猛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城市化进程与当代文学实践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城市作为一种物质形态,意味着“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正在深刻影响乃至改变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城市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1]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成为一种欲望化的象征。对物质的占有、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城市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故而,城市欲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许春樵的长篇小说《屋顶上空的爱情》即为其中典型代表。
一、生存的焦虑
焦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詹姆斯·布根塔尔将“存在焦虑”定义为由人的生存境况决定的,它产生在人的本体论的被给予性(指人最根本的生活状况和条件)基础之上,是人在面对自身与世界的被给予性及其关系时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主观状态[2]。可见,人的生存焦虑无非是本体遭到来自物质或精神世界的威胁。
具体到《屋顶上空的爱情》中,郑凡出身于皖西农家,年轻、有理想、有才华,是上海东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渴望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所学知识赢得一种独立生活。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可不知从哪一天起,‘知识分子’一词说起来有点拗口了”,广告宣传、推荐材料上只提经济学家、销售总监、职业CEO,再没有人以知识分子自居,“一个没钱没房还没工作的文学硕士是战胜不快一枚茶叶蛋的。”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郑凡,却在网络聊天室里幸运地结识了网名为“难民收容所”的韦丽。韦丽打赌说,只要郑凡放弃大上海,到自己工作地庐阳来,第二天就嫁给他。工作无着的郑凡,最终决定赌一把,并且成功应聘到庐阳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工作。韦丽信守诺言,毅然决然与郑凡登记结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郑凡,经济贫困,只能租住在都是些“收破烂的、做卤菜的、卖豆腐的、炼地沟油的、偷情私奔的等各色社会闲杂人员”的“城中村”,研究生毕业的郑凡沦落成社会底层中的一员。面对城中村的出租屋和赌来的妻子,郑凡郑重承诺:“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买上自己的房子。”因此,购房成为郑凡生活的中心目标,也是实现真正跻身庐阳、跻身城市的标志与象征。然而,高额的房价是郑凡与整个家庭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地里刨不出钱来,我只有靠自己才能住上房子。”每月两千一百六十的工资,除掉租房等,只能存下一千二。作为知识分子的郑凡,既不会巧取豪夺,也不能坑蒙拐骗,只能出卖自己的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依靠兼职筹措购房首付成为郑凡的唯一选择。或给“维也纳森林”地产公司定期编写会刊,一期八百块;或给江淮文化传播公司撰写各种虚假广告;再就是做家教,给学生补课,“每个学生每次辅导三小时,报酬三十块钱,双休日两天可挣一百二十块钱”。会刊编写、广告策划、家教补课等,每个月能挣一千二百块,加上工资的余存,郑凡一年能存接近三万,而庐阳的房价平均不过四千多一点,八十平米的房子,首付百分之二十,“看看缩在被窝里冻得瑟瑟发抖的韦丽,郑凡越想越美好,越想越激动,想象的生活在寒夜里像海洛因一样美妙而虚幻。”然而,“一个小知识分子在巨大的物质浪潮面前,注定了被摔得粉身碎骨。”郑凡再怎么殚精力竭也赶不上一路飙升的房价,只能感慨:“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挣得越多,离买房的梦想就越远”。与此同时,在熟练游走于各个兼职之间时,郑凡陷入深深的精神焦虑之中。一方面,郑凡想守住读书人的矜持与自尊,不屑与雇主们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自己的劳务所得却也是牺牲自己的矜持和清高换来的。此外,郑凡撰写的“古秘方心康宁”广告传单严重失实,遭到稽查大队追责。其实,郑凡在刚接江淮文化传播公司的兼职时,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杜撰得太多了,慢慢地,他就由一开始的抵触抗拒到如今的应用自如麻木不仁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自游国恩、陆侃如之后中国现当代楚辞研究的专家张伯驹教授的学生,尽管为生活情势所迫,毕业后的郑凡没能传承老师的衣钵,但三年的研究学习使他无法忘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屈原。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上,郑凡先是以屈原助楚怀王改革自勉,在会上“大放厥词”“犯上作乱”,因此差点丢了工作。事后,郑凡又以“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自我安慰。吃过一次亏后,在黄梅戏改编研究会上,郑凡“结结巴巴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背负着知识分子名分的郑凡,从农村走向城市,却又挣扎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为了如愿购房,他只能一次次出让自己的自尊和清高,原先坚守的精神世界一步步崩溃解体。在对知识缺乏认可的现代城市,郑凡堕入“灵”与“肉”的分离错位之中,灵魂承受着刀割一样的疼痛[3],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焦虑之中。
二、人性的异化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消费主义文化以强劲之势迅速扩张和渗透到城市社会的各阶层和利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摒弃理想主义、放逐精神价值的实用主义的世俗哲学,便以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完成了物欲对心灵的全面扫荡”[4]。在生存的压迫下,个人生活不得不向物质生活妥协和献媚,物实现对人的绝对统治,人便异化成非人的存在。
为了早日买上房子,郑凡不分日夜地拼命兼职,把每个夜晚、礼拜天、节假日全都拿出去,在结束家教夜课回到出租屋时,“他才发觉自己的身子像是被拆散了的一堆零件,根本拼不出一个活人来。”购房成为郑凡生活的全部和生命意义,“异化的事实就是,人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身力量及其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而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依赖自身以外力量的无能之 “物”,他把自己的生活意义投射到这个“物”之上。”正如韦丽所说,郑凡纠结于买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 “想证明一个知识分子的实力和体面”。此外,明知“天龙虎骨酒”广告宣传的“舒筋活血、防止脑血栓、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等疗效是夸大其词,但在高额的报酬面前,郑凡还是“绞尽了脑汁捏造了一个个瞒天过海的传奇和神话”。给强奸犯龙飞编写传记,给和曹操毫无谱系关系的曹氏家族编写假家谱,给庐春老窖酒策划假广告,给“维也纳森林”房地产虚假宣传等,明知“造假”,郑凡还是说服了自己,“这里不是楚国,我也不是屈原”。“当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追逐着权力和金钱,人性中的恶就肆无忌惮,人人被他人践踏着撕咬着,人人也都践踏着撕咬着他人。”[5]郑凡放弃坚守的过程就是异化为金钱的奴隶的历程。并且,“在消费时代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身体也成了消费社会的一道景观”[6]。文本中,郑凡的大学同学黄杉和野模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因女友母亲要求黄杉必须要有一套房,剑走偏锋的黄杉用一套子虚乌有的假房产欺骗女友,最后被无情戳穿,女友拂袖而去。黄杉发出“我想找一个富婆,把自己的身体和青春搭一起卖了”的吁叹。令人唏嘘的是,就在野模女友嫁给有钱的老头的同时,黄杉真的将自己的身体和青春搭一起卖给了一个全身披金挂银的老富婆,摇身变成了有钱人,出入于各色高档酒店,享受着上流社会的富足、豪华与风光。来自偏远小镇的悦悦,父亲去世多年,病重的母亲在老家靠捡垃圾为生,虽然聪明能干,但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不管如何努力,就是无法获在职场上获得成功。最终,悦悦投入房地产开发商郝老板的怀抱,成功地将自己当作商品推销了出去。读书时代常常写诗弄文的才子黄杉,在物欲的引诱中也没能抵住诱惑;工作兢兢业业聪明能干的悦悦,在生活的重担下出卖身体与青春。于黄杉、悦悦而言,身体异化成商品,成为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产品。确切地说,衣锦还乡的黄杉、名利双收的悦悦,在满足物质欲望的时候,却也失去了人格和灵魂。“由于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灼与困惑只是心灵在物化世界里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则是当一时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心灵的空虚与失落。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并不会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恰恰相反,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却丢掉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与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7]在物欲的城市中,郑凡、黄杉、悦悦等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体,只能依赖于外在,从而丧失自我,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三、批判与救赎
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宽阔的物质世界,但过度的欲望膨胀,致使生存经受危机、人性遭遇异化,对人性的叩问和理想的追寻处于迷惘状态,许春樵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面对欲望沉浮的现实,作家深刻揭露了生存的焦虑、批判了人性的异化,但仍然保留着对生命充满美好的期待,执着于欲望的救赎。
作为自游国恩、陆侃如之后中国现当代楚辞研究的专家张伯驹,并没有对郑凡、老豹、小凯等没有一个继续研究楚辞而抱怨,反而告诫他们不可忘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之良知、心之向善、道之担当。退休后,张伯驹在国学训导中心义务教授《离骚》《论语》,并强调“国学中心如果收学员费用,我就不来教;如果给我薪酬,我也不来教”。在他的坚持下,国学训导中心成为义务教育机构。张伯驹的行为像是孔孟,在礼崩乐坏的物欲世界中固守着“天下归仁焉”的社会理想。
悦悦、莉莉的世故和庸俗彰显出韦丽的善良和纯真。虽了解不深,但在郑凡来到庐阳后,韦丽履行约定、登记结婚。在郑凡郑重许下三年内买上房子的承诺时,韦丽却毫不在乎地说:“没房子挺好,想住哪就住哪,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当郑凡得知维也纳森林的房价打折之后还要六千一百六时,韦丽安慰道:“谁要你买房子了?我不稀罕!”面对购房问题,韦丽不焦躁、不奢望,安贫乐道、纯净朴素,将物质诱惑屏蔽于人性之外。韦丽这一人物设定,似乎就是为了抱慰深陷生存泥淖中的郑凡。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信念,物质并不是人性尊严和安宁生活的唯一基础;更为我们演绎了一种美好,平凡生活的温情和安宁。
郑凡深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焦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垮掉、毫无道德底线。虽然急需攒钱买房,但当曾是夜总会小姐的莉莉先后两次表示可以支援他五十万元且不用偿还的时候,郑凡委婉地谢绝了。而面对突发情况,郑凡身上表现出了急公好义的人性良知。首先,是对周天保的慷慨解囊。在得知手术花费需要二万五千快钱,而周氏父子只有五千块钱时,郑凡还是去银行取钱替他们交了手术费,尽管他清楚 “这些钱极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其次,是对“小偷”小夏的慈心仁厚,不仅为他垫付了三千余元的医药费,还主动在公安局掩饰小夏的盗窃未遂。无论是旧时邻居周天保,还是素不相识的小夏,郑凡所有的举动,都充分说明他的善良天性,证明着他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对知识分子精神道德底线的坚守。在经历买房失败和韦丽的大争吵之后,郑凡放下执念,辞掉所有兼职,决定“做一个宠辱不惊安贫乐道的书生,把学问做好,把副高拿到手,这才是正道”,“这才符合作为一个读书人属性的”。对郑凡觉醒的安排,似乎略显突兀,这显然是作者急于将强烈的主观意绪嵌入小说人物的行为活动的结果,从而凸现出的某些人性深处的亮点,这与许春樵怀有的“救世理想”的立场有关。海德格尔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真正诗人。”[8]优秀的作家、优秀的创作,总是尽可能地向接受者传递丰富的内容与内涵。除却揭示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表象之外,文学创作理应指向有关生存和人性的本质,进而形成形而上的思考。韦丽的纯粹、张伯驹的坚守,还有被承载着许春樵主观意绪、被醒悟的郑凡,虽然缺乏深厚的现实根基,但不妨碍由他们出发的长久的艺术感动。
四、结语
《屋顶上空的爱情》以现实主义叙述立场烛照欲望都市,物欲的刺激促使更多的人们逐步沦为物的奴隶。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他们的在当下时代的生存际遇进行了真切而又细腻的艺术再现,对他们的沦丧堕落进行了深入而冷峻的反思追问,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如许春樵在访谈中所说:“小说的基本价值就在于揭示出了被遮蔽起来的生活真相。作家要写人,但作家不是人贩子,而是精神的引领者,引领读者质疑现实、弃恶向善、发现真相。”[9]这或许就是《屋顶上空的爱情》的城市欲望书写呈示出的警示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