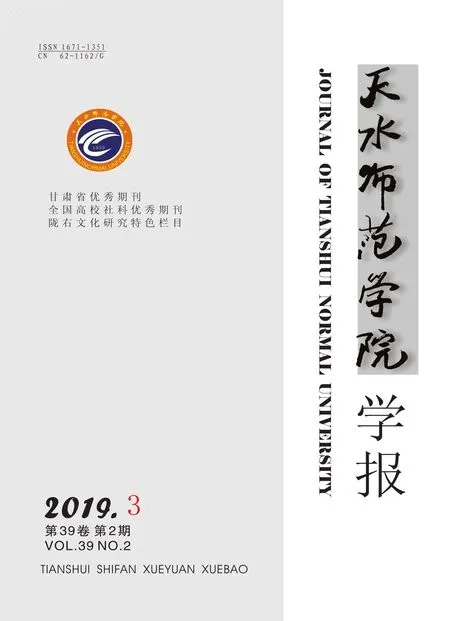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学文化精神对美国20世纪文学的影响
——以“言不尽意”为例
2019-01-21马哈力麦
马哈力麦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举足轻重,上至四书五经,下至唐诗、宋词、元曲,皆是当时文人志士抒情“言志”的主流阵地,纵观中国各朝历代的主流文化,虽然诗歌文化在诗体形式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但其所承载的诗学精神始终贯穿于儒释道等各流派为主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并不断衍生出新的诗学命题。“言不尽意”便是中国诗学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言”与“意”,“象”与“道”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们关注、思考、探究的焦点。在诗歌中,“言”辞本为表“意”,立“象”以尽“意”,但仍有“辞不达意”、“言不尽情”之处,诗歌言说本是达意或得“道”的途径和着力点,但又往往变成桎梏,化为语言的囚牢,使人容易陷入一叶障目或者盲人摸象的处境,得片而忘全,得“象”而忘“意”,断章取义,也就难达大“道”之境。
对此,中国诗学研究者叶维廉曾说:“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1]此处的“机心”所指的大概就是中国诗性思维内在的统一和谐,一种于万象之中求索其宗的依据,一种基于只言片语之上的整体性的直觉感悟,从而以有限之文字达无穷之意境。可见,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境界自古便是一种永恒的中国诗学理想,如果进一步思考其存在方式,“就能从中发现‘言不尽意’的精神之迹,可以看到‘言说’对‘意义’的无限追求与接近,也正是在这种充满希望而又求之不得的寻觅过程中中国之思与诗都诞生了。”[2]这种诗性思维对英美文学尤其是20世纪美国文学产生了影响。
一、中国古典诗学典籍中“言不尽意”之说
很多中国传统诗学著作里都提到“言不尽意”之说。诗歌之语远不止于文字表象,往往以“象”求“意”,得“意”而忘“言”,以“意”取胜。“言不尽意”的直接提出可见于《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3]不管是人志,天意,还是自然万物之理皆是难尽于“言”,遂诉诸于自然万“象”才得以显现,以象悟道,以物观物的表意思维在此处尽显无疑。在此之前,老子亦曾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53“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4]124“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4]53《庄子·秋水》篇中也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5]572一语道破“意”之精妙尽在“言”外。
《庄子·外物》篇亦是有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5]944至魏晋时期,庾阐在《蓍龟论》中提到以“象”求“妙”,“妙”得而忘“象”的论点,之后嵇康作《言不尽意论》,殷融作《象不尽意论》,[6]进一步发展了“言不尽意”说,此后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这一诗学命题。可以发现此命题自出现后经历了从“言不尽意”遂“立象尽意”至“象不尽意”继而“得妙忘象”以求意于“无”的发展历程。“无”,即诗“意”栖居于言语潜层,其本身往往是“不在场”(Absence)。
综上所述,中国诗学精神的“言不尽意”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从第一个层面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文意远不止于文字,不必妄图穷言而尽意,点到为止、存而不论足矣,适当的留白,颇有美学意义上的模糊之美,朦胧之感,这点与西方的某些诗学创作理论是相契合的,如意象派推崇的“诗情画意”,新批评强调的诗歌语言的“含混”(Ambiguity)与张力(Tension),以及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在这一层面上,“言不尽意”往往是创作者为达到留白效果而有意为之,创设出言毕而“意犹未尽”的氛围。“言不尽意”的第二个层面,即中国诗学精神讲求万物之理,天道人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如庄子在《天道》篇所言“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5]488言语不可能倾尽意义的所有层面,“大道无言”,“意”越是精深越是如此,所求的终极意义并不可得,所以解读可能是创造性的多样性的,即布鲁姆的创造性“误读”。
二、“言不尽意”与创作诗学
中国诗学传统对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理念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20世纪早期英美文坛兴起的意象派运动便是典例,此外还有T.S.艾略特及其“客观对应物”理念为代表的新批评流派、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为代表的白描式的“言不尽意”文风,尽管不同流派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都显露出“言不尽意”的思想倾向。
(一)“言不尽意”与意象派
有大量研究显示20世纪早期以庞德等人为首的美国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颇有渊源。中国著名学者赵毅衡在《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文中阐明,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在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上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如“全意象”、“意象并置”、“意象叠加”[7]4等。带有中国风格的意象应用手法实际上为意象派诗歌创设出了立体的结构。“言不尽意”,进而立“象”以致多重“言外意”,实现了意蕴的复调和审美的延异。其他的研究如《论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8]《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9]《英美意象派诗歌的中国情结——从庞德诗歌看英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10]《从“得意忘言”看意象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11]《庞德对中国诗歌与思想的借鉴》[12]等。中国古典诗歌“言不尽意”诗学思想启发了庞德等英美意象派诗人,继而也对美国现代诗人T.S.艾略特、美国作家海明威等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庞德是英美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对中国诗歌文化颇有研究,翻译了许多中国古诗,著有《华章》(Cantos),他在《读书入门》(The A.B.C.of Reading)一书中提出以汉字构造法建立一种新的诗格“形诗”(Phanopoeia)[13],寻求诗中“意”与“象”的相应相合,将意象浇铸融合在视觉想象上。如《在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原文为: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一反英美诗歌历来的史诗般鸿篇巨著式的崇高,此诗以短短两句诗行书写了中国短小精悍式诗歌的优美。庞德领会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言不尽意”思想,遂而以“象”立“意”,意象的并置和叠加使得诗中有画。毫不例外,和很多其他的诗一样,他的这首诗也是以汉字字形的构造选择了意象,《在地铁站》实际上就是由“脸”字的字形联想出的一首“形诗”。反观汉字“脸”,左边“月”字使人联想到幽暗的光,右边“人”字头置于“二”字和横置于“二”字中间的三点“水”之上,几乎可以联想到幽暗的光下,人面如雨后花瓣在疏影横斜的枝头摇曳的画面。“apparition”一词除了表示“离奇出现的东西”,还有“幻影”、“幽灵”之意。可以发现第一句是个隐喻,“幽灵”意象作为喻体暗示了本体——人群中的面孔,若影若现、飘忽不定的特性,这也说明了地铁站光影交错,一张张面孔从昏暗的地铁站往外移动时,借着出口的光突然如幽灵般闪现,紧接着下一句中,人群中面庞“幽灵”般闪现的一瞬又被比作一幅“雨后花瓣压枝头”的图景。
诗中具体的意象的叠加,如“幽灵”、“花瓣”和“枝头”,形成错落有致的立体空间式的诗歌结构,可以不断地拆解合并,衍生出新的意象和理解,如赵毅衡先生所说,“意象派诗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把一个寻常比喻变成含不尽意与言外的‘视觉和弦’技巧,并给予更醒目、更生动、也更富于诗意的形式”。[7]8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Red Wheelbarrow)亦是诗画相通,凝练生动却意蕴无穷。因此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将“言不尽意”诗学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二)“言不尽意”与“客观对应物”
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中的“客观对应物”主张或许部分也源于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歌里汲取的“言不尽意”思想。艾略特与庞德交往密切,深受其影响,不仅撰写了《庞德:节奏和诗歌》一文(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还在他自己的代表作《荒原》的扉页上将庞德与但丁相媲美,称之为“最卓越的匠人”,“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艾略特更是提出了与意象派诗歌相呼应的文艺观“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即写作时不直接表露感情,而是寻找一组物体,一个场景、一连串事件”,[14]7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使得读者感知经验的外部物象一旦出现,便能够立刻唤起那种郁积已久的情感。诗人弱化个人主体性的过度干预让事物客观呈现,使读者可以凭经验性直觉自行体悟,这与“言不尽意”进而寻象观意,以物观物的中国诗学思想相一致。
比起浪漫派诗歌的直抒胸臆,艾略特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思想和意识通过外部事物表现出来,可以说“客观对应物”是浸透了诗人情与思而提炼、凝结、集中起来的带有艺术情感的“意象”。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认为“艺术情感近似于一种真实旁观者的情感”,[15]在他看来,诗意的“表达”意味着“客观化”,由一个(组)意象去刻画另一个(组)意象,而非诗人个人情感的直接释放、喷发或宣泄。如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诗中,“黄色的烟雾”被呈现为“在窗玻璃上蹭着背”、“蜷缩在夜之角落里舔着舌头”的某种动物,将独白者的情绪以对应物——“黄色烟雾”、“蹭背添舌的猫”表达出来,渲染出一种慵懒、无力、怯弱、忐忑却又渴望的情绪,这种“不尽意”更是增添了几分由读者填补“灵魂篇章”的余地和新奇的视觉审美体验。20世纪中期盛行的英美新批评流派早期所持的“情感谬误”和“意图谬误”承袭了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念的部分观点,强调诗歌创作中“言不尽意”式的表达,如诗意的“含混”、“张力”甚至“悖论性”,通过意象的立体化呈现传达出来,读者则通过文本“细读”进行直觉性的体悟。
(三)“言不尽意”与“冰山理论”
美国作家海明威提出的“冰山”论点,与中国诗学思维“言不尽意”的第一个层面,在文学创作上所追求的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倡导简洁自然的文字表达与后者点到为止、存而不论的特点相契合,皆留足了空间任直觉性的体悟驰骋,而这种契合未必是巧合。在他的老师舍伍德·安德森的引荐下,海明威在创作之初就结识了斯泰因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女作家,曾为改革文学语言不断进行试验,反对华丽的文字,主张语言的声音和节奏,在写作中提倡电影片段式的画面呈现。、庞德、艾略特等人,经常参与他们举办的文艺沙龙。期间,海明威得到了当时已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斯泰因、庞德、安德森等人的帮助提点,对于他的手稿,斯泰因就“大的方面提出了意见”,庞德则是“划去他作品中大部分形容词”,[14]4在安德森的帮助下,其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于1925年出版。此后,他的作品陆续发表。由此可见,海明威早期的文学创作极有可能从庞德等意象派那里受到过“言不尽意”诗学思想间接的影响。
海明威在庞德和艾略特等人“言不尽意”思想倾向的启发下,提出了“冰山理论”这一诗学论点,主张文学作品的语言应该简约有效,含蓄凝练,显现八分之一的面貌即可,余下的部分犹如沉在水面以下的冰山一样需要读者自己探索。他在《午后之死》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部分,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16]海明威擅长于不露声色、轻描淡写之中刻画人物内心情绪的惊涛骇浪,这也是他塑造“硬汉”形象最常用的手法。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手法表明海明威从庞德、艾略特等意象派诗人那里受到中国诗学精神特质的影响不是没有可能的。
苏光文在《抗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一文中这样说到:“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的作品在1943-1944年间的中国读者界‘是最出风头的’。”[17]海明威的作品广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事实或许也可以说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微妙的中国诗学思维特质,否则也难以在自古就推崇言外意、弦外音的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流行起来。不仅如此,海明威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的白描式“言不尽意”风格对当时的英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英国作家赫·欧·贝茨的评论所说,海明威“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他“一锤子捣烂了按照花哨图案描绘的所有作品,随着亨利·詹姆斯复杂曲折的作品而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被他剥下了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而海明威在其创作中不懈追求的,正是如贝茨提到的,“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18]他的作品,如《杀手》和《白象似的群山》所体现的简约精炼的语言风格正是中国诗学文化精神“言不尽意”第一个层面所求的,并非所有的文“意”都要以“言”说全然无遗地呈于眼前。相比之下,基于想象、联想、比拟而有所保留的呈现实际上为体悟主体建构起了迷宫式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因而“产生了那种超越语言文字外壳局限的整体性审美功效”,有“如在目前”却“见于言外”的“内视美”。[19]寓“意”于不言中,由读者自己通过观察、思考、体悟之旅所得恐怕要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有乐趣,因为这种“开放性”体悟给读者带来的,是罗兰·巴特所谓的“狂喜”,而非一般的愉悦。
庞德、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有“言不尽意”诗学思想的倾向,但是他们各有侧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其中,庞德身上是最明显的,“言不尽意”在他这里俨然成了“象不尽意”,所以用并置、叠加、脱节的手法来表意,以简洁、精确的意象表达含蓄的意蕴;而艾略特“言不尽意”的侧重点则是带有艺术情感的意象的“客观化”呈现,强调“非个人化”;到了海明威这里则重在以平淡无奇的言语表达实则“深藏不漏”的思想。
三、“言不尽意”与“寒山诗的误读”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中国诗学精神“言不尽意”颇具现代性。从庄子“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而来的“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一语道破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可见对语言本身的质疑古已有之,遂“立象以尽意”而“不尽信书(言)”,“象不尽意”故常以赋比兴言此意彼,而致多重“言外意”、“弦外音”,因此诗歌语言所含之意有时远非文字符号所能及,且汝所达之意又非彼所指之意,即“诗无达诂”①“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诗学命题,最早可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诗无达诂”大意是说,读者对同一诗歌文本意义的理解不可能是恒定不变的、统一的或者唯一性的。。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其十三被认为是最富内涵的一首: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有评论认为“一士常独醉”,看似是“醉”,实则是“貌醉而实醒”,[20]醉只是众人看到的表象,醉者借酒倾吐的“真言”,往往被视作荒唐言而失去瓦解权威的威胁性,自然为似醉实醒者提供了保护,醉翁之意也并不在酒,只是“以酒寄言”;“一夫终年醒”,“醒者似醒”却是真正的醉酒者,他们醉心于表层的假象,从未清醒地去审视周围的世界,此处未见一“酒”字,“酒”字之神却贯穿其中,化作一种“潜意象”融为“醉”与“醒”,“愚”和“颖”之间的张力支点。另一方面,“独醉”也是陶氏不拘小节、感性洒脱的田园生活的写照,而“常醒”则是儒士终日的理性克制,前者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情怀和杯酒人生,后者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矜持冷静和审时度势的权衡。这种“不尽意”就与欧美后现代诗学精神“不确定性”不谋而合。正是言不尽意、诗无达诂的这种诗学不确定性为创造性的“误读”提供了可能。
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说:“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开始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21]由此,如果说影响是“诗无达诂”,即诗的创造性误读的源动力,那么诗学艺术符号本身,意象(能指)与寓意(所指)之间的任意组合关系则是一切误读的基础,这种关系导致了意义的差异(或者说延异)和不确定,造成指意出轨(不在场),为创造性误读留下无限可能。
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曾一度掀起过一阵模仿、翻译、研究唐代寒山诗的“寒山热”,有些模仿者甚至自称为“寒山派”,这大抵与寒山诗所含的“言不尽意”而“诗无达诂”的诗学精神有关,寒山诗多寄情山水自然,有世事无常、大“道”难通之感。有寒山诗研究者曾评价寒山诗,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如这句,“人问寒山道,寒山道不通”,[22]第一句中“道”这一意象既是实指普通的道路,当然也可能指“世道”、“仁道”、“佛道”“天道”,乃至“大道”。第二句中“道”自然是动词,有“言说”之意,看似普普通通一句诗,实则颇有“大道”难以言破,说不清也道不明之妙境,诗学“言不尽意”精神在此诗中显露无疑。寒山诗中“言不尽意”式的玄妙精深的禅理哲思为后世学者奠定了创造性误读的基础。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就是对寒山诗进行创造性“误读”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文体表现形式加以消化与改造,同时加入一些禅宗文化的流行元素,从而将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地融入本民族的诗学思想和文化土壤中,也悄然融入自己自由诗体的创作和翻译之中”,[23]以适应本土诗学文化,吸引美国读者大众。对此,赵毅衡教授曾评论道:“美国现代诗从庞德起,到斯奈德,走过了一个中国影响的大循环。作为当代诗坛的领袖之一,斯奈德撑起了‘中国风格’的大旗。”[24]依寒山诗在美国文坛经久不衰的文学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来看,此言非虚。斯奈德就以巧妙的创造性“误读”,省去了原诗韵脚,将其改译为自由体新诗,还在译文中加上了“If”和“I”等词,令“垮掉的一代”深感自己与寒山同病相怜,身临其“境”,实现了一种“共情”,如第17首译诗:
一自遯寒山, 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
养命餐山果。 Living off mountain plants and berries-
平生何所忧, All my lifetime,why worry?
此世随缘过。 One follows his karma through.
日月如逝川, Days and months slip by like water,
光阴石中火。 Time is like sparks knocked off flint.
任你天地移, Go ahead and let the world change-
我畅岩中坐。 I’m happy to sit among these cliffs.
另外,寒山除了自身境遇、身世之迷吸引大批学者研究之外,其诗中体现的驳杂丰富的禅理哲思更是一大魅力所在。如“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22]这句,从佛家转世轮回说来看,需“船”渡人方可达“彼岸”,“船”的意象或许指绝境中的一线生机,即佛教信仰,积德行善以谋来世福祉,“岸”则象征了一种安稳、庇护,更是一种修为的圆满,“此岸”代指今世,“彼岸”则指来生,此处的“两岸无船”可理解为一种生存困境——“信仰危机”。而在西方,“船”的意象就与《圣经·创世纪》里的“诺亚方舟”构成“意象和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两次大战、工业化带来的人的异化、经济大萧条,都使众多清教徒深感“获救”无望,无法成为诺亚方舟式的“选民”而焦虑苦闷,寒山诗则在情感和精神上引发了这种共鸣。
正是寒山诗“言不尽意”的基础性文化精神的存在——玄妙精深的禅理哲思,使之不断的被“误读”,衍生出新的时代精神。当时,不仅以斯奈德为代表的译者和诗人群体,甚至于美国民众也以读懂中国诗的禅理为荣,他们对寒山和充满禅机的寒山诗颇有好感。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泽的第一部小说《冷山》(Cold Mountain)扉页上就写着:“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Cold Mountain:There’s no through trail”,[25]引用了“人问寒山道,寒山道不通”这句,小说发表后于1997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2004年又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近年来还有来中国拍寒山纪录片的“寒山迷”,称中国之行为“A Pilgrimage to Cold Mountain”。按照布鲁姆“影响及误读”的说法,寒山诗在美国广泛的“误读”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对美国文坛产生的影响,“言不尽意”这一诗学命题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如意指不确定性、审美的模糊性等,仍然值得深究细敲。
四、结 语
综上,笔者通过对“言不尽意”这一中国古典诗学命题从两个层面的探讨,即“点到为止”以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境的永恒理想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致“诗无达诂”式的意指困境,可以发现其对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思维上的影响,从庞德到斯奈德,从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到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都可发现“言不尽意”现代性的痕迹。中国古典诗歌的文艺之美恰恰就体现在“言不尽意”这一诗学精神营造下的似是而非、似悟而惑、似达未达、似有若无之中,这种文化精神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现代乃至后现代诗学所追求的表意的极致。
猜你喜欢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