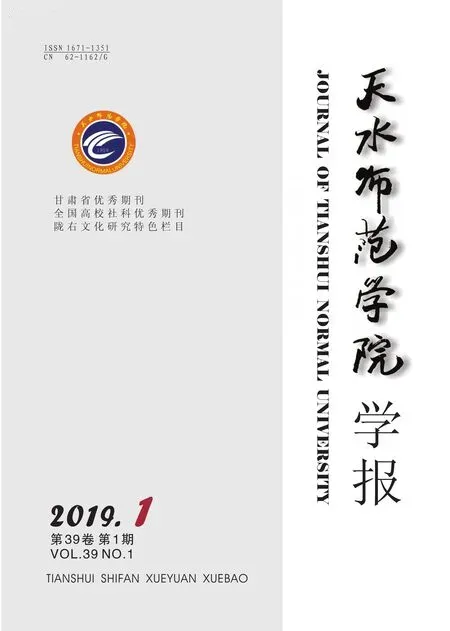论《世说新语》中神童的名士化倾向
2019-01-20李文辉
李文辉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世说新语》中出现聪慧儿童少年的条目共49则,涉及12个门类。其中包括《言语》14则、《政事》1则、《文学》9则、《方正》2则、《雅量》2则、《识鉴》3则、《赏誉》4则、《品藻》2则、《夙惠》7则、《排调》4则、《轻诋》1则、《假谲》1则。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魏晋名士的隽言逸行,展现了魏晋士人恣意任性、率真旷达的精神特质,因而被视为风流名士的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塑造了一群天赋异禀的儿童少年,与人交谈时他们往往能引经据典、机捷应变,其言行神姿颇有魏晋名士之风。关于《世说新语》中早慧儿童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归纳神童特征并分析其出现原因;[1-3]二是借《世说新语》中对儿童的描写反观魏晋时代人们的儿童观;[4-5]三是考察《世说新语》中有关神童的描写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对现今儿童教育的启示。[6-7]学者对《世说新语》中聪慧儿童的名士化倾向关注相对较少,本文试从相关条目入手,探讨魏晋儿童在谈玄、对答时所展现出的名士化倾向,并与后世“世说体”小说进行对比,考察《世说新语》中神童的特征及形象的独特性。
一、谙熟玄理、善于清言
魏晋名士风流与其时玄风大畅息息相关。《世说新语·文学》前六十五则谈到儒、法、佛、名理诸学,并涉及大量清谈内容,形象地展现了魏晋学术发展概况以及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魏晋谈玄之风源自东汉末年的太学清议,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臧否人物的清议一变而为辨析名理的清谈。鲁迅认为:“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8]能清谈方可称为名士,而想要清谈必须通晓玄理,《世说新语》中有大量条目涉及儿童少年谈玄,从他们的家庭教育、与人辩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准名士”对玄理的精通。
一方面,《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少年在家庭教育上受玄学熏陶。《德行》第三十六则记载了谢安与夫人的对话,夫人认为谢安未曾亲自督促教导孩子,而谢安则表示“我常自教儿”。谢安所谓“常自教儿”意指他以身教儿,而非用言语。魏晋早慧的儿童少年正是在像谢安这样的长辈的身教中,对玄理耳濡目染。以《夙惠》第一、第四则故事为例: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箪,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箪,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夙惠1)[9]587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至、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暝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夙惠4)[9]591
当陈寔与友人谈论玄理、顾和与时贤清言时,陈纪、陈谌和张玄之、顾敷都充当了听众,他们凭借超强的记忆力,能将主客双方的议论完整地复述出来。正是在长辈清谈影响下,陈氏兄弟以及张玄之、顾敷等世家子弟自幼便能辨析名理。《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两则王修向父亲王濛询问清谈双方胜负的故事:一是谢安与王濛清言良久,谢安离去后,王修问父:“向客何如尊?”王濛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二是刘惔与王濛谈论玄理,王修在听完双方论辩后问父亲二人孰优孰劣,王濛言:“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王修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逐步成为清谈名家,同时也能看到少年王修的勤学好问,聪颖过人。
另一方面,《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儿童少年极富思辨性的话语,这与他们对玄理的谙熟有着莫大关系。早慧少年除了听长辈玄谈,也参与清言活动,如王弼自为主客数番、许询与王修共决优劣、谢朗与支道林讲论至相苦。在实践活动中,少年们发展了思辨精神,因而其谈吐也十分辩证,富有智慧: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言语2)[9]56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友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夙惠3)[9]590
徐孺子将“月中无物”与“人眼中有瞳子”加以比对,来说明月中无物未必极明的道理,无怪乎刘辰翁评价“此语极未易”。[10]34关于日与长安孰近孰远的问题,司马睿“不闻人从日边来”和“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两种回答皆言之有理,与驳难时自为主客而皆能自圆其说颇为相似。从少年们的言谈之中,不禁令人感受到他们的聪颖机敏,而这正是建立在他们对玄理熟识的基础之上。
精通玄理、善于清言是成为名士的先决条件,世家少年们在长辈熏陶中逐步掌握玄学知识,其谈吐极富哲理,令人惊异不已,表现出向名士靠拢的意味。
二、举止大方,应对从容
魏晋时代士人颇为重视器量,其美化说法则是雅量。时人赞赏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气度,《世说新语》中专设《雅量》一门来说明雅量的具体内涵,其中谢安闻小儿辈大破贼而言行不异于常、谢安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两则故事展现了谢公的风流儒雅和处变不惊。《世说新语》中颇多对天才少年镇定自若、从容应对的描写,符合魏晋名士所论雅量的部分特征。
其一,魏晋时期的儿童少年也曾置身于血腥杀戮之中,面对突发状况,他们往往临危不乱、镇定自若。以孔融被收、王羲之诈熟眠之事为例: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5)[9]58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7)[9]855
刘义庆将“中外惶怖”与“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色”加以对比,从而衬托出孔融二子的从容不迫。当孔融希冀能保全孩子时,其子却从容道:“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孔融儿子可谓幼而有识,故裴松之云:“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9]58八九岁的孩子能清楚地认识到局势的发展,其所具有的洞察能力已在成人之上。《世语》记有相同故事,其中二子的回答是“父尚如此,复何所辟”,相比之下《世说新语》中“覆巢之下,复有完卵”更能展现孔融二子的沉着镇定。王羲之在无意间听到王敦谋逆打算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保全。此处暂且不论故事真实性,仅就文本而言,通过刘义庆对故事的选取和改动,使我们能清晰感知此一时期儿童少年在面对变故时的处变不惊。
其二,《世说新语》中所描绘的儿童少年在面对长辈的提问时通常能巧妙地化用经典,应答有理有据,沉着冷静,令人信服赞叹。如: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言语27)[9]91
孙盛为庾公记事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言语49)[9]109
中朝小儿和孙放灵活地运用《诗经》予以作答。中朝小儿为父乞药,主人以疟疾多不病明德君子来反问小儿,中朝小儿借《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1]35之语,巧妙地回答主人的问话:因“疟”与“虐”谐音,“为疟”即“为虐”,犹言恶作剧。中朝小儿的回答既维护了父亲的德望,又表现了小儿的反应敏捷和修养之深,因此王世懋评中朝小儿“转语佳甚”。[10]52孙放跟随父亲前往猎场,面对父亲的上级庾亮“君亦复来邪”的提问时,孙放脆生生地答道:“无大无小,从公于迈。”[11]238-239此语出自《鲁颂·泮水》,本意是指不论官职大小都跟随鲁僖公出行,全诗意在称颂鲁僖公的才略美德。孙放借《诗经》表明自己虽然年纪小,但也要跟随出行,同时孙放此语有将鲁僖公与庾亮类比的意味,变相称赞了庾亮德才兼备,王世懋“小儿语,乃胜简文”的评价十分中肯。
《世说新语》中不乏化用前代典籍的例子,如郑玄挞家婢、王子猷以“未知生,焉知死”答桓冲等,此类故事置于成人身上便足以教人称赞,当其主人公置换为孩童时,则更令人拍案叫绝。中朝小儿和孙放在面对长辈提问时落落大方,借助《诗经》使得回答义深意隽而又耐人寻味,他们年纪虽小,却颇有先秦朝会之遗风。《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少年面对生死巨变超脱镇定,化用典籍巧妙对答,幼有成人之度,若非年龄所限,俨然已是魏晋名士。
三、恣意洒脱,不拘礼规
魏晋时代幽默戏谑精神勃然而兴,大抵与儒家思想在汉末遭受崩溃,而玄学思潮风起云涌以及士人个性才情的解放和独立人格的出现有关。儒家宣扬的忠孝仁义在波谲云诡的乱世暴露了其易被篡改的虚伪一面,因此魏晋名士多通过言语对前代恪守的君臣父子加以戏谑,一逞口舌之快。《世说新语》首揭孔门四科,可知刘义庆仍旧坚持从儒家传统出发,《德行》中也收集了王祥、周翼、祖光禄、范宣等人年少行孝的例子,但很明显此类故事并不占主流。书中更多展现了魏晋士人诙谐幽默充满情趣的生活,对少年儿童也不例外,他们同风流名士一般采取调笑的态度对待礼法,言语之间充满智慧的灵妙。
《世说新语》中的少年在调笑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对名讳的戏谑。早慧的儿童少年多出身世家大族,姓氏门第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也常常拿名讳来开玩笑: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言语43)[9]105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排调33)[9]804-805
两则故事分别讲述了杨氏子和孙放对自家名讳的维护和对别人家讳的调侃。第一则故事中孔君平借谐音之故逗杨家儿子,称杨梅是杨家家果,杨氏子则不甘示弱,顺着孔君平的话便说孔雀是孔家家禽。第二则故事则写了庾园客和孙放以父名为戏的故事,庾园客直呼孙放其父的姓和字,孙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庾园客又言“诸孙大盛”犯了孙放其父孙盛之名,孙放也毫不客气的以“诸庾之翼翼”犯庾园客之父庾翼的名讳。如此数番以名讳相调侃,与晋文帝、陈蹇、陈泰和钟会的调笑如出一辙。所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12]少年们的行为固然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特定环境下又显示出了他们的能言善辩与活泼洒脱。
除了犯讳,魏晋神童对纲常礼法也有所逾越。《言语》中载有孔融二子和钟毓钟会兄弟盗酒而不拜之事,两则故事大体相似,孔融小儿子和钟会因偷酒本就不合礼数,故见父不拜,从中不难看到他们对父子伦常的稍稍逾越。孔融在伪礼教盛行之际便对父子伦常加以大胆否定:“父之于子,尝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13]孔融此语对礼教行孝进行了彻底颠覆,孔融二子和钟毓钟会兄弟见父不拜虽不至于上升到枉顾礼法的程度,但他们显然并没有完全按纲常礼法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孔融二子和钟毓钟会兄弟盗酒故事中出现了与魏晋名士联系紧密的意象——“酒”。魏晋名士多喜饮酒,前有孔融《难曹公制酒禁》为饮酒辩护,后有刘伶《酒德颂》揭示魏晋文人嗜酒原因。《世说新语》中也有大量对饮酒的记载,如张季鹰的“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的“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名士或通过饮酒达到逍遥的境界、或借助饮酒逃避现实,流风所被,少年们也开始效仿,因而出现了盗酒而饮的情况。余嘉锡认为两则故事“盖即一事,而传闻异辞”,有学者对刘义庆记载这两则相似故事的动机表示怀疑:“它仅仅是《世说新语》粗疏的症候,还是一种类似于《圣经》那样的强化手段呢?”[4]86刘义庆对盗酒之事的重复记载虽未必是刻意强调,但至少说明魏晋时期儿童违礼不是个案,我们从中既能看到他们的聪颖活泼,也能感受到一种类似魏晋名士的恣意洒脱。
四、聪颖早慧,形象独特
关于早慧孩童的奇闻异事,后世“世说体”小说中也多所记载,这些故事既与《世说新语》一脉相承又有所新变,儿童少年的名士化倾向几乎不见于后世“世说体”著作。不同时代人们对神童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这也从侧面突显了《世说新语》中聪颖儿童的独特性。
“世说体”小说与《世说新语》在刻画神童时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世说体”小说更注重展现儿童在经略诗赋等方面的造诣,而非玄谈。一方面,后世“世说体”小说更多表现儿童的才思敏捷。如何良俊《语林·夙慧》记桓驎十二岁赋诗,张纯、张俨、朱异三童随目赋物,陆从典八岁援笔拟回文,李泌赋方圆等故事。《儿世说》作为专门辑录儿童故事的“世说体”小说,其中专设《属对》一门,记载了詹会龙①安忆涵《〈儿世说〉考论》依据《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杂志》收有宋人詹会龙见宋高宗事、“金”“会”二字字形更接近两点,认为《说郛续》本《儿世说》中“詹金龙”当作“詹会龙”。、[14]万鏊、李东阳、程敏政孩童时与长辈对诗或联句,表现了他们的捷思神悟。此外,这些儿童往往博通经典、记忆超群,如《语林》中的黄香幼时熟读经典,精究道术;陆倕问虞荔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儿世说·强记》展现了长孙绍远、贾逵、王粲等人超强的记忆力,其中第六则特意提到“昭明五岁能读五经,顾野王七岁读五经,张九成八岁颂六经”。[15]虽则《语林》中也记载了孙思邈“弱冠善谈老庄,兼综释典及百家之说”,[16]卷二十二8但“世说体”小说更侧重表现儿童对诗赋文章、儒家经典的熟识,《世说新语》中儿童与人谈玄驳难的情景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儿世说·文学》第三、四、十二则记祖莹夜晚燃火读书、范注家贫燃薪写书诵读、陶弘景灰中学书,其他“世说体”小说中也存在大量昼夜苦读的勤奋儿童。可见后世“世说体”小说中的神童在经略诗赋上的造诣更多源自勤奋刻苦,有别于《世说新语》中在长辈的熏陶下掌握玄学知识。
其次,《世说新语》中儿童越礼违礼的行为在后世“世说体”小说中几乎消失殆尽。“世说体”小说中聪颖孩童对礼法的恪守主要体现在尊长行孝、遵守礼节两个方面。第一,“世说体”小说中出现大量孝敬至亲的儿童。如《续世说》中记袁君正因父亲生病而专侍左右,昼夜不眠;郑善果得知父亲去世时悲恸擗踊,不能自已。除了有直接的孝行,神童往往还精通《孝经》,如《儿世说》中《文学》第一则记庾子兴五岁苦读《孝经》,视“孝”为德之本;《言志》第四则载独孤及幼时读《孝经》且有志于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孝经》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17]后世“世说体”小说中所录神童行孝之事,大多都是《孝经》纪孝行章、事君章、丧亲篇等的具体化,如《儿世说》单列《至性》一门表现孩童对父母的至孝恭敬,可见后世对儿童在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我们将钟毓钟会兄弟盗酒故事中的“酒”视为魏晋名士风流的一个独特意象,则在“世说体”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孝经》也可看做是士大夫德孝观念的象征。第二,后世所记早慧儿童大多尊礼守节。《儿世说·方正》中张元六岁不肯就井边洗浴,言:“不能亵露其形于白日之下。”《语林·夙慧》中沈友以“君子讲好,会宴以礼”拒绝华歆登车而语的请求,可知神童对礼仪礼节的遵守。再如《语林》中苏颋即席改赋,巧妙避讳:
苏颋年五岁时,裴谈尝过其父。颋方诵庾信《枯树赋》,避“谈”字讳,因易其韵曰:“希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皆叹异之。[16]卷二十二9
《枯树赋》中“今看摇落,凄怆江潭”的“潭”字与裴谈之“谈”同音,苏颋为讳嫌名而改为“凄怆江浔”,易其韵而读之。苏颋避讳既可见其文思敏捷,亦可见其对礼法的恪守,与《世说新语》中以名讳互相攻守戏谑的事例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擢第拜官逐渐成为“世说体”小说中神童的标识。《唐语林》载刘晏八岁献《东封书》,后拜秘书正字;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后拜东宫卫佐。《儿世说·文学》记杨炯中童子科,授校书郎,十一待制弘文馆;贾黄中六岁知台阁事,七岁神童及第。《语林·夙慧》中有杨亿十一岁授秘书省正字的故事,宋太宗问其离家是否想念父母,杨亿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父母。”这些儿童在君臣父子伦常、立身扬名方面的较早领悟被视为聪慧的表现,官方通过拜官授职的方式对其早慧加以认可。而在《世说新语》中,很少有条目提及儿童被授予何种官职,拜官与否也不是衡量儿童聪慧的标志。
综上可知,《世说新语》中的聪慧儿童善玄谈、会戏谑,他们身上带有更多魏晋名士的洒脱超逸。而“世说体”小说中的神童则富有文采、刻苦钻研、尊礼守制,更接近后世士大夫归于正统,走向仕途。在魏晋名士风流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由于长辈的言传身教,《世说新语》中的这些神童在聆听父辈清谈中培养出极强的思辨能力,在与人交谈时往往能机智应对。他们在与人论辩时甚至会利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对父子伦理纲常也并不完全遵守。这些都与魏晋士人洒脱超逸的言行举止相契合,显示了《世说新语》中儿童少年的名士化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世说体”小说更注重展现神童的德孝与才学,没有刻意突出其名士化倾向,这也从侧面凸显了《世说新语》中聪颖儿童的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