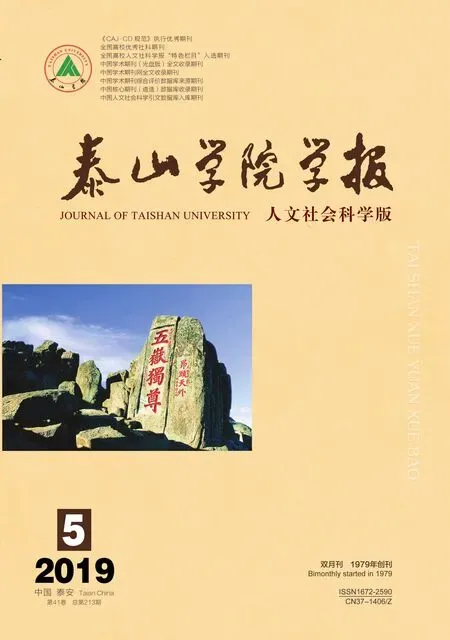创伤文本的诗性见证与身份建构
2019-01-20黄峰
黄 峰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20世纪90年代起,耶鲁大学凯茜·克鲁斯(Cathy Caruth)、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学者努力将医学领域对精神创伤的研究(策略及成果)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具体分析文学创作中的创伤主题,这类研究活动被西方学界统称为“创伤研究”(Trauma Studies)。我国学界对诸如“伤痕文学”有着类似的研究,聚焦于相似的叙事策略与情感倾诉。在这类研究视域下,创伤已不再是外在的肉体创伤,亦不会很快被治愈,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1]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伤事件并不等同于由此而来的创伤体验,创伤文本对创伤事件的叙述亦不等同于其他领域(历史、医学乃至政治)的记录,创伤文本具有基于文学领域的独特性。
一、对个体创伤体验的不断言说
最早关于创伤的记录来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针对头颅部位损伤而进行的医学实践,当代英语中的“创伤”(trauma)一词即由古希腊语中的医学词汇“τραμα”演化而来,很长一段时间均是作为医学术语来使用。但在19世纪现代心理学尤其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创伤”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包括个体肉体上的外在创伤,更侧重于个体精神上的内在创伤。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等著作中强调由于外在事件所造成的内在创伤,具有不可治愈性,对个体行为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创伤研究即认为作家创作时,乃是出于对创伤事件以及创伤体验(traumatic experience)的不断回忆或重温。此处有关创伤主题的书写不是回避过去,而是一种想象性倾诉,是要将过往某段特殊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体验予以想象性呈现。故而,创伤文本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文本如何将创伤体验进行诗性表述。
这其中,最常见的言说对象是个体(作者)的不幸体验,也有更大氛围下遭遇不幸经历的整个集体。虽说作家的创作灵感不一定都是源自自身的不幸遭遇,但对于创伤文本这一独特范式来说,作者确实处在对某种不幸遭遇的编码式书写中。因此,创伤文本的诞生首先在于作者自己所承受的创伤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变化。作为来自现实处境的不同作者,彼此的遭遇虽各不相同、各有根源,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什么样的创伤性事件,最终留给个体的都是无法言明的创伤体验,所以创伤文本在进行诗性言说的过程中,其言说的重点正是对创伤体验的呈现,而非单纯叙述一段过往的创伤事件。由此论之,创伤体验自身的特点往往转化为创伤文本的结构性核心要素,下文以不同作家及创作为例具体分析。
首先,创伤文本见证个体创伤体验的持续在场。个体(包括作者及文本主人公)在遭遇创伤事件时,往往都处在突发状态下瞬间地被动经历,因此无法抗拒创伤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以至于由此而来的创伤体验成为一种铭记在心的深刻记忆。这种体验或记忆对个体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潜在影响,本来可能是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就转入全新的心理状态:孤独、恐惧、逃避、自卑、愤怒等等不安情绪都是典型的症候。从创伤研究视角看来,也就意味着作家在创伤前后会发生巨大反差。作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早年生活充满幸福,有温柔的母亲、活泼的哥哥,有普希金带来的文学书籍、童话故事的陪伴。“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家庭悲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家中的悲剧(母亲去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极不愉快的回忆。其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2]很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摆脱持续在场的创伤体验,后者已经被铭刻至生命的深处,故而其创作实践就具有创伤文本的常见形式:主人公往往具有不幸的经历以及不完整的人性和心理。
其次,创伤文本反映了个体创伤体验的不断延迟。对于个体而言,虽然内在的心理创伤往往较长时间内都不会明显呈现出来,但当个体遇到类似处境时,早先的创伤体验就会再度呈现,也即创伤体验的持续在场性,同时表现为它总是不断地延迟自己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不会受到时间延长的降低。“事件并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3]如以创伤研究视角入手,可从《旧约》关于“献祭以撒”的经典故事(《创世记》22:1-19)中发现以撒成年后个性的根源。当以撒还是儿童时,耶和华神曾为了考验其父亚伯拉罕是否信仰坚定,故意命令他将其独生子以撒作为燔祭品献于自己,亚伯拉罕没有任何迟疑就在第二天带着以撒前往献祭地点,并真的亲自将其捆绑起来准备杀了。《旧约》在叙述这段故事时,用意在于强调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的坚定信仰,却没有提及献祭过程中以撒有何反应。不难想象,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以撒而言无疑是十分恐怖的经历。虽然后文没有提及以撒对该事件的回忆或创伤体验的呈现,但我们却可从以撒成年后的性格上看出端倪:没有主见,如父亲替自己挑选妻子、晚年时分被妻子和儿子雅各联手欺骗等等。对于以撒而言,献祭一事带来的创伤体验并没有被治愈,而是潜藏下来,一直延迟至晚年还依然影响着他。
第三,创伤文本反映个体创伤体验的重复再现。由于创伤体验的延迟性,所以它并不会彻底显现,也不会是一种显性的持续在场,但它总会在类似处境下重新凸现出来。就如同回忆一样不断被重温,不断被言说,重点在于重复。因此,创伤文本对创伤体验的书写往往具有普遍的重复形式。德国19世纪早期作家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在同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大潮中颇为另类,其创作多带有神秘、怪诞的特色。对此,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Brandes)点评道:“霍夫曼的命意是病态而古怪的。”[4]这种病态的书写并不是霍夫曼刻意为之,从其个人经历来看,或许是他最常态化的书写模式。霍夫曼两岁时就父母离异,父亲从此带着另一个孩子不再与之相聚,这种离别情绪一直潜藏在他的内心深处[5]。在创伤研究看来,霍夫曼自幼而来的创伤体验是其成年后创作风格或范式的真正根源,其笔下主人公不断地重复陷入相似的困境中。比如《沙人》的主人公纳撒内尔从小就遭受过失去眼睛的恐吓,长大之后(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自己的眼睛;《赌运》中如命运一般的赌博活动紧紧地纠缠着所有男性主人公,所有男性都重复着类似的遭遇。据此而言,霍夫曼有关创伤主题的多次书写,体现的恰是自己对创伤体验的重复性言说。
和历史学家不同,作家虽然没有对创伤事件进行客观的记录,但不代表会完全忘记,他们反而会以虚构的文学创作——营造噩梦、回忆或类似处境等——予以象征性呈现。对于他们而言,每一次书写都是对创伤体验的一次见证。因此,创伤体验不论是源自作者的真实体验,还是对主人公经历的艺术虚构,都搭建起创伤文本的创作动机与创作内容。于其中,创伤文本成了界限模糊的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纽带,成了过往经历的诗性见证者。虽然这种见证本身也意味着无休止的重温创伤,甚至带有强迫读者一起体验的话语把持力。
二、对集体记忆的拼图式再现
创伤文本诗性见证的对象除个体的创伤体验之外,还包括有着同样遭遇的一群人关于创伤体验的共同感受。个体遭遇的创伤事件虽然各有各的原因或表现,但对诸如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压迫、流离失所、种族主义等范围更大的创伤事件而言,它们会给更大的群体带来类似的创伤体验。“文学作品扮演了为读者提供叙事的关键角色,这种叙述不是直接的指义性的,而是提供一种接近历史和记忆的模式。”[6]透过创伤书写,我们看到的一种普遍化的危机处境或历史遭遇,此时的创伤体验不仅是个体难忘的痛楚,也是同一类人关于不幸的集体性感悟。对此,创伤文本有关群体性创伤体验的书写,就有了见证集体记忆、铭记历史危机的创作意义。
将创伤文本研究视角从个体的单一体验转移至更大规模的集体性体验时,无论是记录战争创伤的反战文学,记录洪水之类的灾难文学,还是广泛涉及性别歧视、种族屠杀、殖民统治等题材的反压迫类文学,都是基于对特定人群之不幸遭遇的共同书写。对此,相比较创伤文本对个体创伤体验的单一叙述,只是对个体记忆片段的重述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Halbwachs)更强调记忆本身的集体性特征,即任何记忆都不是独立的,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性场合而自成一体。所谓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指在更大范围内有着相似经历的众人关于某一段历史的共同记忆,虽然因为个体的差异,这份共同记忆在不同个体那里有着不同的体现,但任何个体记忆都是集体记忆的一份拼图。因此,对于个体而言,任何不幸的创伤体验都不是封闭的个体遭遇,而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定经历。尤其当创伤事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时,必然会有更多的个体有着相似的创伤体验,他们会共同叙述着关于过往的相似体验。此时,关于创伤主题的书写,就是对不幸的相似遭遇的共同见证,也是对这段集体记忆的公共性言说。它关于创伤体验的诗性见证由此而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对集体记忆的拼图式再现。
呈现集体记忆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创伤文本在内,诸如图片、影像、雕塑、绘画等形式,都具有铭记事件、保存记忆、见证历史的效果。但不同于其他形式,创伤文本在见证集体记忆的同时,必然也是一种诗性见证,而非对客观材料的如实记录,所以隐喻性往往是创伤文本的又一特征。由于创伤体验的在场性、延迟性与重复性,它并不会在事发当时就被完全理解或掌握,相反它会在以后的日子中不断复归。创伤文本通过隐喻的形式予以指涉,将历史的不同碎片编码进情节中,而非直接客观的呈现。对于读者而言,透过这种诗性叙述,自然可以发现创伤主题所隐喻的历史坐标,或可说任何创伤体验都是历史的个性化产物,反过来自然可以由关于创伤的集体性体验反推出共同的危机遭遇。因此,从集体性维度审视创伤体验,就意味着文本分析必然考虑社会历史因素。读者可以藉由文本对集体记忆的拼图式再现,而与过往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及创伤事件产生“关联”,虽然这种关联只是一种认知上的关联,但至少起到了延续见证的效果。
以此为切入点来看,上文提及的霍夫曼创伤文本的创作根源,就不仅仅来源于他从童年开始的不幸体验,也来源于当时社会背景下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不幸体验。“1813年,霍夫曼在德累斯顿经历了多次小规模战斗和一次大会战;他亲临到战场,身受过饥荒和一次随着战争而来的瘟疫——一句话,这个时期所有恐怖现象丰富了他的想象力。”[7]战乱、分裂、落后,这些标签是19世纪德国很久以来都具有的特点。和欧洲主要大国相比,德国限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致于长久以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当法国爆发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德国敏感的知识分子却只能沉浸在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进行谨慎的精神探索。在这种情况下,“霍夫曼连同他描写的所有稀奇古怪的鬼脸,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8]可见,不光是霍夫曼,同时代的整个德国社会都在经历着类似的生存处境,其创伤文本对创伤主题的强调也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体验,而是隐喻着当时整个民族生活处境中的普遍体验,也是对有关这段经历之集体记忆的诗性见证。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于1954年出版小说《解冻》,该书塑造了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如工程师索科洛夫斯基、柯罗杰耶夫以及老学者维鲁宾等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受过不同形式的迫害,对日后成长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内心深处均有着无法排遣的伤痛。从创伤研究的视角分析,《解冻》正是一部创伤文本,不仅作者有着多年的流亡经历,遭受过来自国内政治方面的严格审查,更为主要的是《解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不幸现实、一批人的共同记忆。书中虽然只是叙述苏联一个边缘小城市中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不幸经历,却有着对当时粉饰太平、回避矛盾等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该书引起一批同样敢于揭露现实矛盾的作家们的共鸣,成为引领“解冻文学”新倾向的奠基之作。这类文本对过往的共同言说不仅仅是对个体体验的艺术再现,更是对整个群体有关创伤事件之记忆的集体性述说。
简言之,创伤文本所承载的集体记忆本身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而来自对现实处境的真实体悟。也正是拥有共同的体验与记忆,某些群体的人们才有着类似的身份特征以及书写倾向。就此而论,创伤文本的文学意义不在于对单个创伤事件的记录或再现,而在于将散落在过往的历史碎片拼贴式重新组合,起到了对有着类似遭遇的同类人的记忆召唤,成为维系彼此关联的情感纽带。这份诗性见证,在当下充满喧嚣、解构自身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具有意义。
三、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意义
创伤文本虽然不同于历史文献资料,但其社会学意义依然可以通过它对过往创伤事件的言说或见证予以呈现,这种呈现可以起到类似历史记录一样的特殊效果:抵消时间的流逝所造成的记忆消解。可见,创伤文本除见证之外,还拥有另一层意义,即对当下及未来的勾勒或预设。创伤文本不只是再现、反思或控诉过往的不幸,更是一种危机中的持续突围,着眼于对未来的憧憬,它可以通过叙述过去的方式来作用于当下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创伤文本用书写创伤的方式(诗性的叙述)甚至起到了理想中的社会改革(甚至革命)作用,以此来实现医学意义上的治愈效果:超越持续在场的创伤体验。故而,对创伤文本进行审视时,要留意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力,其一是留意文本对个体及群体之创伤体验的诗性见证,其二是留意文本对个体及群体之身份属性的重新建构,从后一方面中读者或可见证新一轮的言说努力。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身份”(Identity),这是他们立足现实联系外界的文化坐标。但理解“身份”的方式却有两种,“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闭塞;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造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未完全结束。”[9]对此,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强调身份并不像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毫无问题,“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10]。可见,后一种身份[10]研究方式无疑更加辩证,也更加合理,没有哪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固定不变的,都会随着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变化。这样一来,有关身份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敞开,有待世人不断对其进行“生产”。
在创伤研究看来,一旦创伤事件发生,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身份必然会发生变化,新我从旧我中脱离出来。换言之,身份的重新建构,不仅见证了那一瞬间的创伤,也预兆了日后受创者的发展方向。而作者关于创伤主题的诗性见证,也就不仅包含一种对过往的拼图式见证,也有关于个体及群体文化身份重新建构的预设。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创作实践中一贯保持着对黑人女性遭受各式创伤的谴责态度,将父权、夫权及种族主义下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予以大量揭露。但沃克并不是仅仅停留于对创伤事件的重述上,哪怕这其中有着自己真实的创伤体验,她在创作中更多地在探讨黑人女性的出路问题。创伤体验不是停留在对记忆中往事的回溯上,反而成为自我认知、建构新身份的助推力。以《紫色》(The Color Purple)为例,书中塑造了一位屡遭重创的黑人女性西莉亚。西莉亚还未成年时就遭到继父奸污,身心备受打击,婚后则遭到陌生丈夫的持续虐待,完全丧失自我。但从创伤研究来看,该书书写的重点不在于对创伤事件的刻画,而在于叙述西莉亚如何不断超越创伤体验的过程,也即身份的不断建构过程。西莉亚最终得以摆脱旧的受创者身份,转而拥有独立、勇敢、自信的新身份属性。无疑,《紫色》以及类似创伤文本超越了创伤本应具有的沉郁氛围,转而赋予了女性整体在未来发展的新希望。
创伤文本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意义,还体现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对非当事人身份的建构上。随着时间的延长,对遭遇创伤事件的个体或群体而言,往往随着他们的不断离去而造成创伤体验或集体记忆本身的逐渐散去。此时,再对过往的创伤事件进行叙述时,哪怕只是一种隐喻式指涉,都会产生将逐渐失真的创伤体验移植至当下社会的叙事学现象,其结果自然是对当代读者(非当事人)的身份建构增添新的质素。这样看来,创伤文本的结尾既是完成式的,也是敞开式的,它期待着有关过往的历史被持续地见证下去。德国作家W.G.塞巴尔德(W.G.Sebald)在二战结束时刚刚一岁,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大轰炸、大屠杀之类的战争悲剧,但深受家庭以及整个民族有关战争的集体记忆之影响,他在创作时就常常将这一集体性创伤事件作为人物的生存背景,很多主人公都是遭受战争创伤(哪怕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不幸角色,比如《异乡人》《奥斯特里茨》等作品。故事自然都是虚构的,毕竟塞巴尔德自己也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他却通过转述的形式,将过往的创伤体验继续保留下来,继续言说着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塞巴尔德让他的读者感觉到大屠杀在当代欧洲文化中的渗透性和不可避免性,证明了我们都被牵连进它的(后)效果之中。”[11]在“热衷于失忆”的当下,这种对集体身份不断进行建构的行径,让远离创伤事件的当下人们最终发现现实中的生活依然离不开创伤体验的持续影响。
记忆的本质是抵制遗忘,所以创伤文本书写创伤体验,同样是为了抵制遗忘。而勿忘过去的意义,则在于现今人们该如何面向未来。这点上,创伤文本和诸如反思战争、恐怖活动、殖民行径的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通过对当下人们的持续影响,不断塑造这新时代下的身份特征。“(创伤体验的)本真面貌——由于它的延迟呈现与滞后诉说——不仅与已知事实相联系,还要与我们行动与预言中的未知部分相联系。”[12]因此,创伤文本不仅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个人及集体创伤体验的再现,更搭建起面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对于非受创的当下读者而言尤为如此,历史的厚度与广度亦得以持续性扩充。可见,围绕创伤主题的文本实践,其旨归在于加深对人类文化进程的认知,在于更宏大的叙事目的:以超越创伤体验的形式代替对以往人类所走弯路的纠正。
结语
对创伤的叙述是当事人对抗不幸最悲壮与无奈的行为,但也是最充满智性与希望的行为。因为,创伤文本藉由对过往的见证与对身份的建构,起到了两方面的叙事效果:一方面,抵制着时间的单线性维度,起到类似证词的记录,虽然只是一种主观性的拼图式记录;另一方面,抵制着文本叙述的封闭性,不再局限于创伤事件,而着眼于超越创伤事件及体验,成为一种对未来持续敞开的叙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工业时代的科技文明并没有将人类送进美好的彼岸,反而依然让人类深陷隔阂、分裂、破碎等异化状态中。此时的人们尤其需要关注各式创伤带来的复杂影响,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言,有关创伤的文学实践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反思的精神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