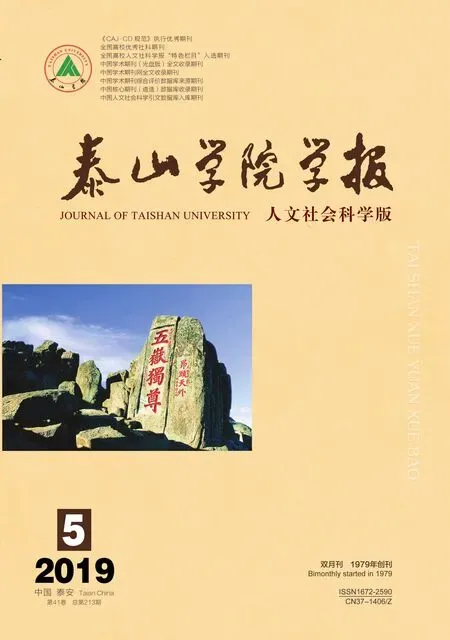儒家的以义取利思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塑造
2019-01-20张文彬
张文彬
(泰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商业和商人阶层的活跃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出现的必然结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序》中引用《周书》上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这段话客观地指出了农、工、商、虞四业在国家和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实施上均存在重农抑商倾向的情形下,提出“商不出则三宝绝”的论断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既客观明智又明确有力的肯定。在漫长的商业发展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化,涌现出了大量智慧仁达的代表人物,如管仲、范蠡、白圭、吕不韦、胡雪岩等,与此同时,因地域纽带或是行业联系而形成的商帮也应运而生,渐次兴盛。历代商业与商人阶层的繁盛抑或衰微总是与内外部条件息息相关,除却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时局治乱的影响之外,商人们在思想与行为上的内外约束条件对个体、家族、商帮的事业兴衰至关紧要。这些对于商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内外在约束随着历史文化的积淀,逐渐形成了极具丰富内涵的商德,其中以义取利思想在传统商德文化中处于主流地位,影响甚至是支配着商人的商业实践。商业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同理,商业道德的形成和流布必然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对于古代商业道德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在商业活动中集中表现为以义取利。当下该思想对企业家精神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一、以义取利为核心的商业道德:渊源与流布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同时《论语·述而》又记载,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由上观之,孔子肯定“欲富恶贫”是人之本性,但又提出富与贵必须以道得之;如果符合道义即便是“执鞭”之类世人认为的微贱之事也可以去做,如果用不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所谓富贵则是不可取的。
同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由此可见,荀子同样肯定了“欲利”和“好义”都是人之本性,不能简单的否认,但是要做到“义胜利”,决不能“利克义”。由此可见,以经世利民主旨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不漠视人的取利动机,只是强调应当以义取利。这在“子贡赎人让金”与“子路拯溺受牛”的两则记载中体现得尤为深刻生动。《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1]陈少明先生认为:“子贡赎人让金”是一“思想史事件”,且是在秦汉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思想价值的事件。[2]这充分证明了以孔子为圭臬的儒家绝对不是一味追求道德完善的迂儒,而是以社会为本位并正视人性中的取利欲望,这一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儒家的以义取利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指导着人们的商业实践活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商业伦理道德方面也极为推崇以义取利。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的大实业家涩泽容一提出“《论语》之中有算盘之理”,“算盘可因《论语》打得更精,而《论语》也可借由算盘来发扬真正致富之道”。[3]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但致富的根源和所用的方法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
二、以义取利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引领与规范
以义取利思想几千年来在我国乃至受中华文化圈影响的日、韩等国一直处于主流商业道德的核心地位,那么通常认为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们为何会奉儒家的“以义取利”为其圭臬呢?根本原因在于它为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发挥着引领、规范、调节商人行为和商业活动,促进公平交易、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以义取利思想肯定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正视商业和商人的价值,这应该是该思想能成为传统商业道德核心价值的前提。毋庸置疑,商业活动本身需要利润才能持续运行,商人也需要利润才能安身立命进而扩大规模,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史记·货殖列传》就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但是在中国古代商人是经常受到轻视乃至打击的,例如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中严厉地指出:“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当然任何极端否定人的趋利性的思想与商业的规律背道而驰,不会为商人群体所真心接受,也自然不能成为商业道德的指导思想。在普遍存在轻商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中,儒家能客观清醒地肯定人取利的欲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以义取利思想强调获取利益必须遵循一定的道义,如果违反道义、唯利是图则是不可取的,会受到来自官府、行会或是民间法方面的制约。以义取利思想一方面适应了商人行商赚钱的营利目的,为商人经营商业谋取利润提供了精神和价值方面的皈依;另一方面又为商人取得利益划定了边界,起到遏制商人为取得利益而采取违法、违约、违背社会公益等行为的作用,能比较有效地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这与儒家思想中经世济民的情怀是一脉相承的。儒学有积极入世的人文主义情怀,当然这方面孔子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圣贤。杜维明先生在其《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一书中就认为:“自我的真正实现,虽然肇始于家族的环境之中,却要求我们把自己的关系扩展到家族结构范围之外,从而超越裙带关系,从而得以和更大的群体建立有意义的联系。”[4]例如晚清巨商胡雪岩就将以义取利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他身为商贾却热心善行义举,设立粥厂、收葬暴骸,还于1864年创办义渡,渡江者不收分文(原来官渡和民渡都收费,还经常发生舟船倾覆),义渡的船只靠人摇风助,若是碰到风浪或是大潮,南北两岸悬挂白旗,封江停渡。那么他的利哪里来呢?他在修义渡之前就在其必经之路修建了药店等店铺,来往的人多了自然生意兴隆。又如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乃是籍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
三、以义取利思想弘扬的现实必要性:繁荣与责任
以义取利思想在古代漫长的商业实践中发挥了灯塔和车轨的双重作用,在我国古代重刑法轻民法缺乏统一的民商事法律规范的情形下,以义取利为商人们提供了精神皈依和行为规范,这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离不开经济的活跃与繁荣。而实现经济繁荣必须靠制度激励驱动。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理性地指出,“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并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5]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6]我国先贤孟子也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些论述说明,一个国家持续的经济繁荣必须建立在正视人的合理欲求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闪烁着理性光辉的论断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得到认可和实行,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还大有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儒家的以义取利思想不否认市场参与者的取利动机和行为是客观清醒的,是社会经济繁荣的意识形态基础,正确解读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大力弘扬以义取利思想对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积极性,促进经济持续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另一方面,仅仅肯定和激励企业家的取利行为是片面的、危险的。在约束缺乏的条件和环境中,片面逐利会造成人性的扭曲,进而危害社会和人民群众。众所周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众多负面问题。例如,道德失范、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贫富差距扩大、物欲追求无度、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利克义则乱”。解决之道在哪里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因而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施规范上,“取利”必须以“义”为统领。“义”是包含了法律、道德、文化等诸多内涵的高度抽象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追求应当内化于企业家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内心,并外化成企业家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目标。
四、以义取利思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塑造:儒商与创新
当下以义取利思想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工商业日趋发达的潮流中社会需要越来越多以儒家以义取利思想为底色的现代企业家。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将培养企业家队伍与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同步谋划、同步推进,鼓励支持更多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实践中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学者们一般将具备这些素质和情怀的企业家称为“儒商”。儒商文化是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于什么是现代儒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做了丰富的论述。例如,马涛认为“儒商”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商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商人,具有“人本主义”的经营观念,崇尚“见利思义”的商业美德和服务社会的人生观[7]。杜维明先生把儒商定义为“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个企业家,他还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关心文明的进步”[8]。其实无论哪一种儒商界定,以义取利、经世济民是儒商人格和行为特征的核心内容,在当下仍然需要大力弘扬儒家的以义取利思想,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培养塑造既具有儒家人文情怀又具备商业才能的现代儒商。现代儒商既要传承儒家的伦理价值,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弘扬教育,政府层面发挥好各类宣传渠道的作用,弘扬正气和正能量,发挥优秀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惩治力度,让各类市场主体清楚地知道,以义取利才能真正实现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义取利不仅能实现个人、家族财富的合法累积,还是财富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