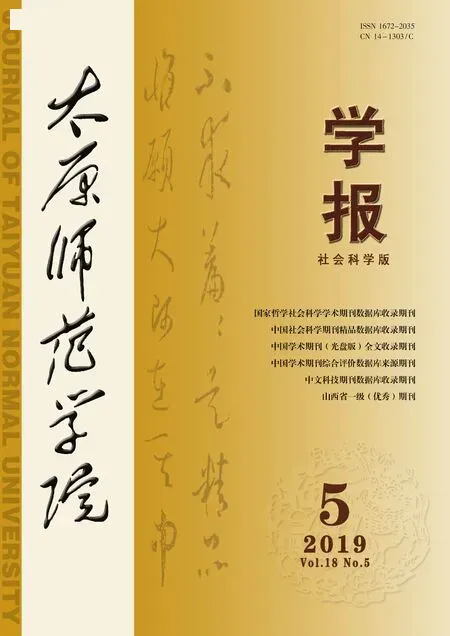清初大同镇裁革始末探析
2019-01-20杨永康边志鹏
杨永康,边志鹏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明朝建立后,为抵御蒙古势力南下袭扰,明廷在北部边疆依托长城一线设立了九个军镇并驻重兵镇守。“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1]20。九边军镇在明代实质上是一种镇戍体系。大同镇即为明代九边军镇之一,地处山西北部,紧邻京师,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景泰帝朱祁钰曾称:“大同,系极边紧要藩篱”[2]4154。正德、嘉靖年间,大同镇战事尤为频繁,明朝官员在大同镇不断增筑新堡,号称九边之首。隆庆年间俺答封贡之后,明朝准许蒙古方面“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羁縻之术”[3]1421,大同镇自此后战事虽日渐稀少,但因辖区内大小市口有十余处,控制住了明蒙之间的重要贸易通道,与蒙古诸部的贸易规模雄冠九边,很快成为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清朝混一长城内外,其地位才逐渐下降,最终遭清廷裁革。目前学界关于大同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大同镇的设置过程、防御体系、重要战事等方面,对于大同镇在明清易代之后的演变情况研究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梳理。清廷入关之后如何处置大同镇?大同镇的裁革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清廷的绿营兵制与明代的镇戍军制有何关系?这些问题的厘清对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山西行政区划的变化和军事建置沿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明亡清兴之际的大同镇
清军在入关之前,为了解除南下攻明的后顾之忧,清太宗皇太极接连对蒙古各部用兵,迫使蒙古林丹汗远遁青海,1635年(崇祯八年),清廷彻底统一漠南蒙古,“明未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4]8494,明朝九边军镇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尽臣服于清朝。
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席卷中原,很快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政权,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皆已纳入清朝版图,大同镇等明代九边军镇成为内地后,其军事防御作用开始下降,存在的必要性也进一步降低,清廷便着手对明代遗留的九边军镇进行裁革。顺治元年(1644)六月,宣府巡抚李鉴上奏清廷,希望能够尽快整顿宣府镇繁杂的局面,他说:
上谷一府,在明朝为边镇,在我朝为腹里。前定经制,兵多而员冗,今宜急议裁汰。查得宣镇原额经制官军七万六千九百二十九员名,索之簿籍则有兵,用之战守则无兵。总由前朝法纪废弛,无核实之政也。日来索饷者纷纷,宜早定经制,抚、镇、道、协以及各路堡应设营马步兵若干,应支月饷若干及将领月廪若干,均应酌立成规。至于冗员,如宣府城内有万全都司,有管屯都司,又有巡捕都司,今宜照大同例改设知府,而以征收屯粮之事归并于府官,则管屯之都司可裁也。在城管粮同知加以缉捕一衔,则巡捕都司又可裁也。保安、延庆两州,斗大一城既有州官,又设守备,似宜裁去守备,而以城守之务,专责正印官料理。若永宁县,距柳沟止二十里,而有两参将,尤属滥冗。似宜裁去永宁之参将,专其责于县官。东路一隅设总镇又设两协其间,宜留宜汰,尤宜急议。怀来一城内有道有厅,又有参将,守备亦属赘疣,似宜裁去参将而留守备,以司城守。若援营之兵有名无实,不如简其精壮者付之守备,而以道厅为之提挈。兵马既减,钱粮出纳有数。其旧设同知、通判多员,亦宜量加裁减,归并所司议行。[5]卷五63-64
李鉴本为明朝降官,深谙明代边镇之弊,他上奏的内容主要针对明代九边中宣府镇的裁革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前朝遗留的边镇这一庞大的军事体系,给清廷统治地方带来极大的不便。首先,明代的边镇在清朝已经成为腹里,丧失了原先的边疆守御职能,存在的必要性自然降低。其次,宣府镇虽然有大量士兵,但并不能真正地用于作战,导致人浮于事,纷纷吃空饷,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而且边镇所辖的很多城堡内武官设置过多,职能重叠,兵多将冗的局面亟待整顿。其整顿思路大体上是先对镇上的旧军定下经制,即将旧军中可堪任用的兵员编入清朝的军队,成为“经制兵”,使兵士员额固定下来,为清廷守卫地方;之后将各堡中多余的兵丁以及职能重叠的武官如守备、参将等直接裁汰,武官事务归于府官,从而促使前朝的军镇行政化,由地方官治理。
大同镇与宣府镇同为明代九边,自有相似之处。大同镇成为清朝内地后,其裁革思路也大致如此,但九边的裁革并非一蹴而就。“国初尚沿明旧制,其蓟、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明代在九边之列。顺治初年,于宣府、大同仍专设有总督、巡抚、学道、总兵等官。于延绥设有巡抚、总兵等官,密云为顺天巡抚所驻,并设总兵等官。蓟与临清各设总兵等官,并为重镇……嗣后各员陆续裁并,移驻各地方。仍如府州县之制,不复称为镇”[6]755。由此可见,清廷入关之初根基未稳,在边镇事务上依然沿袭明朝建制。大同镇作为中原屏障,京师右翼,紧邻蒙古地区,军事地位重要,清初还需用以防御个别对清廷不臣服的蒙古部落。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摄政王猎至蹇家庄,会报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行猎,向我边界。于是集诸王大臣议,遣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固山贝子拜尹图、公傅勒赫、岳乐、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统兵戍守大同”[5]卷四一331。明亡清兴后,虽然内外形势已发生变化,但大同镇还暂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原先的军事防御地位,清廷对其裁革尚未过多触及。
促使清廷加快裁革大同镇步伐的重要因素是姜瓖之变。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继派遣英亲王阿济格、博洛等清军统帅驻守大同后,清廷又“命多罗郡王瓦克达、固山贝子尚善、吞齐、公扎喀纳、韩岱等率兵赴和硕英亲王军前,戍守大同”[5]卷四一331。清廷在大同地区不断增兵的举动引发了早已降清的故明大同镇总兵官姜瓖的恐惧。顺治元年(1644)六月,姜瓖刚刚归顺清朝,清廷便对他十分猜忌。摄政王多尔衮指责姜瓖“议委枣强王以国政,使续先帝祀,大不合理”[5]卷五61,随后又告诫姜瓖“洗心易虑,管总兵官事如故。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5]卷六68。姜瓖自以为功劳卓著却屡遭压制,因而对清廷久怀不满,当他看到清廷能征惯战之将一时之间齐集大同,疑对己不利,越发恐慌,于是在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趁清廷官员出城,闭门举旗反正,尊南明永历正朔,“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5]卷四一332。到后来,这场反清运动已经蔓延至山西全省与邻近省份陕西等地,发展成北方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清复明运动,并威胁到京畿,给清廷造成巨大的压力。姜瓖据守大同城,清军久攻不克,摄政王多尔衮率军亲征、剿抚并用也未能取得明显成效。至城中粮食绝尽导致发生内变,“伪总兵杨振威等斩瓖并其兄琳、弟有光,以其首来降”[7]825,清军才攻入城中。多尔衮对大同镇的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深为忌惮,下令除了杨振威及其家属之外,“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5]卷四六365,给大同城造成极大的打击,大同城骸骨遍野,附近朔州、浑源等地的人民也悉遭屠戮,“移镇阳和,大同废不立官”[8]446。但后来因为“阳和一城,仅仅斗大。以势度之,虞其孤也”[9]1966,在顺治八年(1651),宣大总督佟养量又复请移治大同,得到清廷允准。
二、大同镇旧军的改编与军堡的裁撤
清朝初年大同镇爆发的“姜瓖之变”虽然被清廷平定,但因其声势浩大,掀起了北方反清复明运动的高潮,事后又因“郡属城堡俱隶大同镇,官弁多逆瓖旧员”[10]102,使清廷深感威胁,唯恐遗留后患,遂于平定变乱后的当月立即着手对大同镇大刀阔斧地裁革。顺治六年(1649)九月,清廷开始了入关之后对大同镇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顿:
丁丑。更定宣大二镇官兵经制,宣大总督标兵二千名,分二营。中军副将一员,兼管左营事中军守备一员。右营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旗鼓守备一员。掌印都司、管屯都司、巡捕都司各一员,俱移驻阳和。阳和副将、中军守备、右卫副将、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一千名。阳和道、分守道、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二百名。大同城操守一员,驿兵一百名。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路参将、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四百名。右卫、山阴、应州、马邑、高山、聚落、怀仁等城,守备各一员,兵各二百名。宏赐、镇川、拒墙、镇边、破虎、灭虎、镇羌、将军会、杀虎、迎恩、破鲁、保安、拒门、威虎、镇门、镇宁、灭鲁、镇鲁、保平、守口、牛心、西安、乃河、云岗、镇口、败虎、阻虎、平远、威鲁、宁鲁、云石等堡,大水、瓦窑二口操守各一员,兵各一百名。[5]卷四六368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在清朝初年的裁革,首先是对大同镇旧军的改编。顺治六年更定官兵经制后,原先大同镇的明朝旧军被改编为“经制兵”,兵将皆有了定员和正式地位。“经制兵”即是指被编入清朝新设的绿营军队,绿营兵制是清朝初年建立起来的制度。清军入关后,随着占领区域扩大,八旗军军力有限,无法同时承担作战和镇守占领区的任务,于是清廷将明朝的降兵降将改编,建立了一支汉人军队,这支汉人军队也按照八旗军的标识形式,采用绿色旗为标志,故称为绿营兵或绿旗兵,绿营在清朝是固定下来的制度,与八旗军同时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两大正式军队。绿营兵除了作战之外,还负有警察职能,如征粮、捕盗、维护社会治安等。“绿营规制,始自前明。清顺治初,天下已定,始建各省营制”[11]3891,可知绿营制度也是来源于明代。据罗尔纲著作《绿营兵志》,清代绿营制度效仿的正是明代的镇戍制度。清代的绿营军队中很多武官的职称来源于明代镇戍体系中的武职,如总兵、参将、游击等。
大同镇的旧军被改编为有经制的绿营兵后,大同镇虽然还称为镇,但与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镇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首先表现在“镇”的不同,明代的大同镇是明代镇戍体系中的镇,这种镇仅仅分布在边疆和其他要害地方,在全国数量少但每个镇的军队规模都很庞大。而清代大同镇只不过是清朝绿营兵制中的一个建置单位,清廷出于控制地方的需要,在内地各个行省均设有绿营建制,为清廷守卫地方,因而这种镇在各个省份都有分布。其次,明代九边军镇属于战时体制,因而“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4]1866,清朝在明代镇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绿营军队都是经制兵,清代“绿营提镇以下,悉易差遣为官”[11]3263,大同镇的总兵官、参将、游击等武将在清代已经有了正式的品级,是常驻地方的正式官员,有正式地位,与明代的差遣性质也不相同。明代大同镇总兵官负责大规模作战,尤其在明初“明以公、侯、伯、都督挂印,充各处总兵官”[12]1445,权力极大,地位显赫。虽然明朝在后来为了防范武将专权,极力抑制总兵官的权力,使之在明中后期“位权亦非复当日”[4]1866,但作为高级武官,整个国家中担任总兵官的人数有限,大同镇总兵官能够指挥大同镇的所有兵力对敌作战。而清代总兵官的权力已无法与明代相提并论,总兵官只不过是绿营兵制中的作战单位“镇”的一个统领,“大同镇总兵官一人 (驻扎大同府),管辖本标官兵、分防各营”[13]991,总兵官直接管辖每个镇的绿营兵,这些兵称为镇标兵,镇标人数有限,镇的总兵官权力较小,清代像这样的总兵官在全国数量很多。清代大同镇总兵官的地位也不似明代尊崇,明前、中期总兵官和总督、巡抚地位平等,明代总督、巡抚是边镇的一种差遣官,并非正式的地方大员,代表朝廷对总兵官起到牵制作用,明后期渐渐开始压制总兵官的权力。清代总督、巡抚是常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总兵官在绿营兵制中位居总督和巡抚之下,全面受其节制、听命行事,已是固定制度。通过顺治六年更定官兵经制后,大同镇旧军被改编成有经制的绿营兵,明代大同镇的驻军体系已被清朝的绿营体系代替,两者完全不同。
将大同镇的明代旧军改编后,随着这一地区战事平息,清廷将大同镇各城堡中多余的士兵也加以裁汰。一些城堡军事地位下降,守官也随之降级。明朝时“尝言大同士马甲天下”[14]1993,经过清初顺治六年(1649)大规模更定官兵经制,大同镇的官兵人数较之于明末已经大为减少,一些重要城堡的军事防御力量被大大削弱。关于大同镇所辖各城堡在明代的驻军人数,成书于明末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有相关记载:聚落城设官兵737名,应州城设官兵790名,怀仁城设官兵378名,山阴城设官兵529名,高山城设官兵737名,马邑城设官兵329名,更定经制后,以上各城均只设官兵200名。明代镇羌堡设官兵1 053名,宏赐堡设官兵607名,镇边堡设官兵722名,镇川堡设官兵679名,拒墙堡设官兵420名,镇鲁堡设官兵245名,守口堡设官兵466名,镇门堡设官兵512名,镇口堡设官兵311名,镇宁堡设官兵302名,瓦窑口堡设官兵468名,平远堡设官兵406名,保平堡设官兵321名,灭虎堡设官兵537名,将军会堡设官兵601名,乃河堡设官兵341名,西安堡设官兵229名,迎恩堡设官兵455名,败虎堡设官兵434名,阻虎堡设官兵473名,威虎堡设官兵467名,破虎堡设官兵700名,牛心堡设官兵434名,保安堡设官兵487名,宁鲁堡设官兵392名,威鲁堡设官兵416名,破鲁堡设官兵320名。顺治六年(1649)更定经制后,这些军堡均只设官兵100名,远远少于明亡以前的驻军人数。可见,清廷对故明大同镇所辖各城堡的兵员裁汰力度非常大。应州城、怀仁城、山阴城、马邑城、聚落城、平鲁城、高山城因位置较为重要一些,顺治初年依明制暂设守备未变,只减少了驻军人数,而其他各堡的守官职级则下降,如镇羌、宏赐、镇边、镇川、拒墙、守口、镇门、镇口、瓦窑口、平远、保平、灭虎、将军会、迎恩、威虎、破虎、牛心、保安、宁鲁、威鲁、破鲁这些军堡在明代设守备,更定官兵经制后,全都改为操守。关于守备与操守的职级孰高孰低的问题,明朝天启年间,有大臣上奏关于边镇的守卫事项,曾提到“用操守任之,则事权太轻。今宜设守备,以资弹压”[15]卷八三4024,清朝基本承袭明代建制,在明清时期防守城堡的武职体系中,操守的官阶明显要比守备低一级,裁撤守备以操守代之,说明大同镇所辖城堡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已大不如先前重要。顺治七年(1650),又进一步对守官降级,“改设守口、镇川、拒墙、威鲁、破鲁、破虎、败虎、阻虎、云石、乃河诸堡及杀虎口、瓦窑口、大水口操守为各把总”[6]1095,守官由操守降到把总。当年,又“裁保平、镇羌、镇鲁、灭虎、云冈、牛心、迎恩、西安、镇口诸堡各操守”[6]1095。顺治十年(1653),“裁威远城防将、守备,止设把总一人”[6]1096,顺治十一年(1654)“裁大同操守”[6]1096,顺治十三年(1656)“ 裁宣大总督”[6]1096,手握边防重权、设立近二百年的宣大总督自此不复存在。后来又“裁镇门、宏赐、镇边、拒门、灭鲁、威虎、将军会、平远诸堡各操守”[6]1097,大同镇的军事防御力量由此在顺治年间被严重削弱。到顺治十七年(1660),不独大同镇,九边“自西宁以抵宣大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5]卷一三六1049,九边重镇本依托长城而设,大量兵员遭裁汰后,无人守护城堡以致于各处长城颓塌,明代九边重镇的规模已不复存在。
康熙年间,清廷频繁用兵,大同镇本身已非征战之地,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屯兵、养兵,为战事提供兵员、马匹和粮草。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与噶尔丹开战之初,清圣祖玄烨令“选素习征战、人材壮健、善于步行、能用大刀连节棍者二千人,戍守大同、宣府,以备明春有事时调遣”[16]卷一四九645。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以见在京城喂养之马驼,驱往大同等处饲秣”[16]卷一五七727。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已征服漠南蒙古,在康熙年间通过“多伦会盟”和三征噶尔丹,又收服了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清圣祖玄烨对此颇为自得,曾谕扈从诸臣道:“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完固矣”[6]2005。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曾奏请修复长城,清圣祖斥责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16]卷一五一677-678可见,清朝虽然同历朝历代一样,也曾在北方面临其他游牧民族制造的冲突,但统治者处理方式较为得当,对修筑长城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同镇等明代九边本就依托于长城而存在,清廷不重视长城,原明代九边各处城堡亦置之不理,守堡兵丁在康熙年间也进一步遭到了裁撤。在此期间,大同镇所辖一些军堡的守官由把总降至千总,兵丁人数较之原先更加减少。例如,“威远城原设把总一员,守兵九名,长夫四十名,站军四十名。康熈三十六年改把总为千总”[8]525。康熙五十八年(1719),“裁聚乐城把总,改设千总一人,兵一百二十九名”[6]1097,“裁威虎城把总,改设千总一人,兵一百二十七名”,两城驻军减至200人以下。“裁瓦窑口堡把总,改设千总一人,兵七十八名”[6]1097,“裁破鲁堡把总,改设千总一人,兵八十二名”[6]1097,“裁阻虎堡把总,改设千总一人,兵七十二名”[6]1097,多数军堡的军士在康熙年间已减至100人以下。
雍正年间,清廷继续对大同镇各堡兵员进行裁革。雍正九年(1731),“左卫城千总一人,兵一百二十名。威鲁堡千总一人,兵八十二名。宁鲁堡把总一人,兵六十七名。破鲁堡把总一人,兵七十九名。破虎堡把总一人,兵六十六名”[6]1097,官兵人数再次削减。雍正十年(1732),“井坪城原设守备一员,马战守兵一百五十一名。雍正十年改守备为都司佥书,实在经制官一员,马战兵十二名,守兵一百三十九名”[6]1098。“瓦窑口堡兵二十二名,合原设兵共一百名。镇门堡兵二十八名,合原设兵共一百十二名。守口堡兵三十九名,合原设兵共一百二十名。拒墙堡兵十六名,合原设兵共九十六名。镇川堡兵二十九名,合原设兵共一百名。威鲁堡兵十名,合原设兵共九十二名。大水口堡兵六名,合原设兵共七十二名。云石堡兵十九名,合原设兵共九十八名。镇羌堡把总一人,兵五十六名。镇边堡把总一人,兵七十名。迎恩堡、威虎堡把总各一人,兵各四十六名。将军会堡千总一人,兵五十六名”[6]1098。可见,到了雍正年间,清朝已建立八十余年,战事减少,清廷对大同镇的裁撤范围已涉及原先所辖几乎所有城堡,这些城堡守官的级别大大降低,或由操守降为把总,或由把总降为千总,守兵数量大规模减少,一些明代重要的军堡在此期间守城兵丁竟裁至十名左右,其职能仅在于维护治安,而非用于作战。
除裁汰各城堡的冗余官军外,大同镇在清初被裁革的另一方式是直接将其所辖的军堡裁撤,废弃不用。清朝初年,大同镇的很多军堡被裁撤。大同镇有名的内五堡、小五堡在明代军事地位极高。“嘉靖十五年,筑弘赐等内五堡(弘赐、镇川、镇边、镇河、镇虏堡是也),二十三年,又筑镇羌等小五堡(镇羌、拒墙、灭胡、迎恩、败胡堡是也)”[14]1998,五堡筑成后,“堡外墙堑一新,虏不敢近”[1]27。如此重要的五堡,在清初绝大多数已被裁撤。至迟在雍正初年,云西堡、威平堡、威远堡、马堡、残虎堡、祁河堡、铁山堡皆已废弃不用。[8]447
三、大同镇军事辖区的行政化
清朝蒙汉一统,疆域扩大,大同镇由北疆前沿要地成为内地之后,军事色彩淡化,原先边镇的军事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必然要行政化,由地方官来治理。大同在明代军事地位重要,“为九边要害地,去寇最近”[8]446,除大同镇这种镇戍体系外,还存有都司卫所制度,“大同镇城高拱完固,内设山西行都司,管辖东西二路一十五卫所”[1]27。卫所制是明朝开国以来的主要军事制度,从京师到地方皆设卫所,卫所由都指挥使司管辖。“都司,掌一方之军政”[4]1872,所辖卫所负责“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诸杂务”[4]1872,卫所辖有大量人口、土地,与当地的府、州、县互不统属,实质上是一种和州县并行的行政机构,主要职责在于养兵、练兵,负责军队的日常事务,遇有战事“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4]1872。洪武后期,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位居都司卫所之上,节制北部沿边卫所。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唯恐藩王坐大,于是将北边藩王势力削尽,派大将充任总兵官,镇守北疆,沿边都司卫所悉听总兵官节制。永乐元年(1403),“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17]319,这是大同由大将镇守的开始。后来随着战事频繁,边防日重,总兵官开始长期镇守地方,“七年置镇守总兵官,大同遂称镇”[8]446,这是明代大同镇成立的标志。此后,沿边要地均如大同,设置总兵官长期镇守,九边军镇由此形成。
九边军镇属于镇戍体系,总兵官和其下将领如参将、游击等在后来虽然由于战事频繁成为常设的武职,但由于九边属于战时体制,这些武职并无正式品级。如正德年间,“升游击将军、延安卫指挥同知阎勋为署都指挥使”[18]2305,由此可见,九边军镇中的官军同时拥有卫所中的武官身份,而卫所中的身份才是其正职。九边中的武将一般由卫所官军充任,卫所制度正是九边镇戍体系形成的基础。九边镇戍军队在明代中后期防御蒙古和女真游牧民族南下,极大地巩固了明政权。山西行都司及其所辖卫所听命于大同镇,由镇来节制,声势、地位渐渐不如大同镇显赫。但都司卫所一直到明末也没有消失,一方面因为卫所制度为朱元璋创立,作为祖制不方便取消;另一方面,卫所依然具有提供兵员、保障后勤等作用,具有与州县相似的管理军政等行政职能,都司卫所和大同镇两者彼此依托,互为依存。
清朝建立统一政权后,“臣服漠北,内安外宁,兵戈不试,关外卫所旷闲,官弁渐次裁汰”[19]12。清朝自有其军事制度,“国朝以八旗精兵平定海内,按部分统,拱卫京师,其于居重驭轻之道,固已得矣”[19]12,又效仿明代镇戍体系建立了绿营兵来巩固统治,对于前朝的军事制度,自然无需保留。清朝初年,卫所与州县并行,在行政管理上较为混乱,给清廷的统治带来极大的不便,清廷入关之初就开始把这些明代遗留的卫所归并为州县,由地方官统一治理。
大同地区的卫所也在清朝初年开始裁并,顺治七年(1650)八月,清廷命“裁并大同后卫于前卫,高山卫于阳和卫,镇鲁卫于天城卫,云川卫、聚落中、左所于左卫,玉林卫、高山城中、右所于右卫”[5]卷五十400。雍正二年(1724)四月,清世宗下令:“今除边卫无州县可归、与漕运之卫所民军各有徭役仍旧分隶外,其余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20]卷十九313。雍正二年(1724)八月,山西巡抚诺珉奏请:“山西掌印都司一官,专司督催屯粮,兼辖卫所。今卫所现在议裁,钱粮、刑名原系藩臬二司兼理。请将该都司及都司首领经历,一并裁汰”[20]卷二三375,清廷从诺珉之请。雍正三年(1725)五月,清廷开始将大同地区的卫所大规模归并为州县:
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宁武府管辖。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移原驻阳高通判驻府城,俱隶大同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宁武县管辖。朔平、宁武各设知府一员。宁武府设同知一员,右玉等九县设知县九员,典史九员,宁武设巡检一员。裁太原府中路、西路同知二员,右玉等卫守备十员,宁武等所总十三员。从原任山西巡抚诺岷等请也。[20]卷三二495
经过雍正年间的行政区划改革,明代设置的卫所所剩无几,仅留的一些卫所也不掌握土地、人口,仅仅为清廷负责漕运等具体事务。大同地区明代遗留的卫所也均被裁撤,“向之列屯卫者,今皆改为城邑”[21]24。原明代山西行都司及其卫所的辖区和大同镇的防区基本一致,只是都司卫所负责军政,大同镇负责作战,职能不同。随着这一区域的广大卫所裁并为州县,明代大同镇辖区的各个军堡自然也随之纳入州县,日常事务不再服从于武将,而听任地方官治理,大同镇由此成为内地的行政区。原辖区内的各个军堡如威远堡、破虎堡、威鲁堡、宁鲁堡、破鲁堡、拒门堡、保安堡、威虎堡、败虎堡、迎恩堡、阻虎堡、乃河堡已归新设朔平府行政区管辖,威远城、云石堡、云阳堡,牛心堡、红土堡、黄土堡、威平堡归并朔平府右玉县,并改为民堡,[19]13由百姓居住,不再设防,逐渐演变为普通村落。高山城、威鲁堡、宁鲁堡、破鲁堡、拒门堡、保安堡划归朔平府左云县管辖。雍正十一年(1733),威虎堡、将军会堡这些昔日的重要军堡裁归平鲁县,也改为民堡,不再驻兵丁防守。有些城堡如镇边、镇川、宏赐、拒墙堡依然划归大同府治理,仅驻有少数绿营兵丁,以维持治安。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镇由此在清朝雍正年间,基本裁革完毕。后因承平日久,原先军堡内仅有的一些负责治安、巡防的兵丁也被继续裁汰,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山西巡抚明德奏请朝廷“大同镇所属各防,从前因系边境,设兵过重。今久成内地,宜量裁改……俱下部议,从之”[22]146,加速了军堡的民化趋势。往后“大同镇总兵官本标中、左、右、前四营,分防杀虎口一协……参将十有一人、游击四人、都司十有九人、守备十有八人、千总四十人、把总八十四人、兵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人”[23]435,清代大同镇合计有绿营兵丁18 648人,远远逊于明代的八万之众。
四、结语
总而言之,清廷裁革前朝遗留的大同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明朝建立之初,大同地区就设置了都司卫所,永乐年间在卫所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九边镇戍体系,大同镇由此成立,与明朝相始终。明朝前期大同镇有力地捍卫了京师和中原地区的安全,明朝后期又承担了对蒙古贸易的职能,在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但它在清朝初年内外一统、蒙汉一家的大背景下,从北疆前线转而成为内地,军事地位开始不断下降。清廷平定“姜瓖之乱”后,开始着手裁革大同镇的军镇体制。首先,清廷以明代镇戍体系为基础,“因明制而损益之”[23]422,建立了绿营兵制,绿营军队中吸纳并改编了原大同镇的明朝官军,为清王朝戍守地方,之后又裁汰了多余的兵丁,大同镇的明代旧军由此被清廷瓦解。其次,对于构成大同镇防御体系的各个军堡,清廷先将其守官不断降级,削弱其战略地位,然后将这些军堡废弃或转化成民堡,原先构成大同镇防御体系的军堡和长城由此也丧失了作用。最后,将这一带原先由卫所管理的军事区域设立为府州县,由地方官治理。从顺治六年(1649)改大同镇旧军为“经制兵”,到雍正三年(1725)撤卫所、设府县,清廷裁撤大同镇用了将近八十年的时间。明代其他边镇入清后也大致经历了这种由边疆到内地的演化过程,经过清朝长期的经营,“九边各置郡县,无有边鄙之殊矣”[9]1966。
清廷对九边的裁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九边军镇是明朝对蒙古军事上防御和经济上封锁、控制的屏障,大同镇等明代九边的裁革也意味着原先蒙古地区与内地隔离、封锁状态的打破。九边裁革后,蒙汉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不再局限于边镇中戒备森严的市口。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不久,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被彻底纳入清朝版图,山西巡抚倭伦请求允许山西商人出杀虎口外赴蒙古经商,虽然无此先例,但清圣祖认为“内外之民俱属一体”[16]卷一九31043,倭伦的建议对商、民均有益处,于是允准。康熙年间,蒙古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也请求于边外扩大贸易,并希望“边外车林他拉苏海阿鲁等处,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6]卷一八一939,于是,“昔为蒙古人游牧之场,康、乾以来,均由汉人陆续开垦”[12]1332,清廷对中原汉族民众进入蒙古草原的限制也逐渐放松,地广人稀的蒙古地区由此得到开发,中原与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便利、频繁,双方关系也更加密切,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