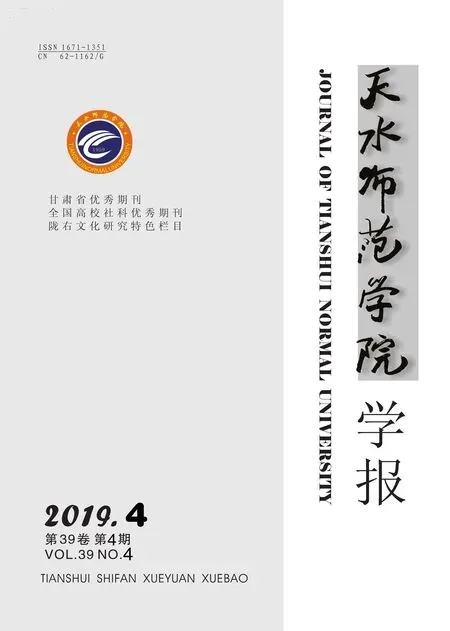城市经验与文学话语中的“城—乡”关系想象
2019-01-20张继红
张继红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741001)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乡村和城市是最基本的两种居住形态。如果说乡村是人类逐水而居、定居农业后的结果,那么,城市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条件和居住空间得到改善的产物。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到城市,从古代到现代,这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谈及西方中古城市化的历史演进时,卡尔·马克思曾作出过这样的判断:中古时代是从乡村(庄园)社会形态开始的,然后逐渐进入了乡村与城市的对立阶段,而“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1]480的历史,也是人类逐渐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空间感受、城市价值认同的过程。
城市的出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商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标志。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程度越高,它利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和效益也就越高,其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就更大。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城乡对立到城乡交往,再到城市化的历史化过程,这一过程凸显了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特征,也是文学“城—乡”关系想象的现实基础。
一、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想象
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想象和建构方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想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历久,是因为远至宋代,中国已经产生了作为消费和生产意义上的城市①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成型在唐代既已完成,论者通过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领土变化、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城巿和城巿化的动力,并通过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内部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等论述了该观点。见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0年版)中的论述。,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从彼时起,文学的城市想象既已开始,及至19 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工业资本的进入,现代工商意义上的城市已开始在中国兴起;弥新,是因为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近四十多年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存在,而城乡转型则是中国社会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问题”的焦点,这一深刻的变化在文学书写中都有丰富的表现,因而探讨有关城乡差异背景下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想象、揭示与建构,仍然是时下当然而又必然的话题。
进一步看,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举足轻重,它关涉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印证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形态。“城—乡”关系是基于城乡二元社会基本结构的一种相互关系,包括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元素所形成的对立冲突、接触和解、交往融合等复杂关系,以及由上述诸种关系所引发的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物资交换、心理交流、价值碰撞等多元立体的要素互动。如何处理、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道路选择问题。[2]那么,现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点何在,其矛盾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作为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想象与建构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书写、回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历程的?……诸多问题的追索都需要我们简略梳理和描述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从中西“比较城市化”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乡村与城市的转变,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由来已久,但各自对立的焦点却不尽相同。雷蒙德·威廉斯曾在《城市与乡村》中说:“将乡村与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3]1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和城市生活方式也有诸多表现形态,不只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单一的生活方式,所以,威廉斯认为“乡村生活方式”,包括“猎人、牧人、农夫和工厂化农场主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其组织包括了从部落、领地到封建庄园等不同的形式,既有小农和佃农阶层,也有乡村公社,既有大庄园和种植园,也有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农场”。[3]1进一步看,即使是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英国,在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发展,甚至流血和动乱后,才将一个农业基础牢固的国家改造为一个工业城市国家。一些新兴的城市(如伯明翰、利兹、利物浦)等,是“乡村工业发展即所谓‘原工业化’的结果”。[4]268至20 世纪末,在工业、经济、金融等行业,英国才称得上一个现代城市国家,其标志则是用金融操纵经济行为,银行业和保险业渐趋成熟。这不仅可以用资本比较,还可以从这一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选择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漫长过程。[4]268而且城市的形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首都、行政基地、宗教中心、集镇、港口、商品集散地、军营、工业集中区”等。[3]1与城市相对的概念则是乡村,与乡村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村庄。村庄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具有不同时期特征变迁的历史维度,它“在大小和特征方面各有不同,村庄内部又有聚居和散居之分”。[3]1很显然,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别特征非常明显,但是,即使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转变,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3]2基于上述城市认知和乡村情感,英国文学也在整个国家基本完成城市化后在整个一代人的时间,仍然是乡土文学。[3]2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定居空间,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经验,它们在人类学、社会学、知识史以及文学书写方面的交互特征仍然是两种经验在不同时空、不同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期的典型显现。
古代中国的城市具有农业社会的市镇特点,尤其在近代以前,中国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乡土社会,现代性仍处于萌蘖期。首先,乡土中国的交往环境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从无数次的小摩擦里淘炼出来的结果”。[5]6其次,“乡土中国”这一提法是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产生以来才逐渐形成的。换言之,乡土中国的“被发现”则是在近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不断的接触、碰撞之后才被确认的。因为在没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烛照、没有中国现代化历史征程的视域下,我们无从“发现”乡村,也无从获得切身的城市经验,也就没有与乡土社会作为参照的另一种传统,更没有将乡村解释为现代城市的“异己”的理论基础。
正是20 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才促使现代社会中“城—乡”关系问题不断凸显,也促成了文学对城乡社会交往的书写以及对“城—乡”关系的自觉思考。
二、城市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审美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是在19 世纪中后期。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无论从词源还是城市功能来看,明显有别于传统社会形态里出现的“城市”。从词源意义上看,中国古代的城市,侧重“城”的功能及意义,其功能主要是军事防御和权力保护。早在先秦时期,诸子学说和经学典籍中都有关于城的记载,比如《孟子·公孙丑下》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墨子·七患》中强调“国有七患”,而居于七患之首者乃城郭不坚,沟池不固:“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吴越春秋》亦有类似的观点:“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6]177在上述文献中,常见有“城郭”的记载,一方面说明当时城郭之制的流行,另一方面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城”与“郭”相对应,而非“城”与“市”相关联。按照今人在《辞海》里的梳理和解释,“城”有三种内涵,一为“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二是“唐边戍名”,三为“修筑城墙”,[7]352用作动词。费孝通先生也说:“‘城’本意是指包围在一个社区的防御工事,也即是城墙”。[8]360从上述词义梳理来看,作为军事防御工程意义上的城与“市”并不合用。在这一阶段,与“城”相关联的词语主要是城墙、城池、城门、城垣、城隍等。
这里的城,显然是在军事和政治意义而言的,而与交往意义上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相应的城市日常生活经验。在唐代的文学典籍里逐渐出现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城郭之内与之外的审美描述,其意义逐渐超出了单纯的军事防卫和政治保护意义上的空间范畴,且城市的经济基础仍然根植于农村,但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相对的富足和繁华程度已让从事男耕女织的乡下人惊奇和羡慕。晚唐诗人杜荀鹤写的《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①此诗的创作语境可参看《附录·诗人小传》有关杜荀鹤生平。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唐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人,出身寒微。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乱后山中作》)的生活。对流离百姓和朱门生活有深切的同情,与杜甫诗歌在题材选择方面接近。相关资料参考了萧涤非、程千帆等撰:《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4-1361页,第1410页。”该诗通过面有饥色、身着苎麻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养蚕人的贫困状况与人世荣华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诗人杜荀鹤诗歌同名的、宋代诗人张俞的五言诗《蚕妇》,其立意与杜荀鹤相同,较为鲜明地道出了城与乡的巨大差异,诗歌写道:“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如果说杜荀鹤写出了贫富差异,那么张俞则写出了鲜明的城乡差别。尽管诗中的“城市”并非今天社会空间意义的城市,而是行为意义上的“进城入市”,即作者到城里买东西(市),回来后为城里与乡里的物质差距所震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再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系列诗,始终表达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悲悯与同情。此后有关于农人物质生活的描写都是从这一角度来书写的。及至清代,《红楼梦》中进入大观园的乡下人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使得城乡差别的文学表征更具形象性、象征性。刘姥姥一出场,就被描写得粗手大脚,面如菜色,目光短浅,生活困窘②但到大观园被抄检后,刘姥姥因感恩贾家的待见而回报贾府。写其“救巧姐”报恩的内容,足见作者对乡下村妇在情感与道德上给予的足够肯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城乡差距表述和“进城”主题所表明的立意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可见,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确道出了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即城市之于乡村的优越、乡村对城市的羡慕,以及由此引发的城乡差距对作者的震惊。不过,这种审美意识尚未上升到城与乡的冲突与对立关系。具体而言,古代诗歌中的城乡关系,并非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等的本质关系。换言之,虽然城乡差别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士大夫对“城中人”的批判,其主要的原因是传统军事防御意义上的城市并不能提供生产资料,即它不是生产性的城市,而是消费性的城市,这样,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产品必须以“以乡补城”的方式流入城市,以供给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城中人”。他们是城池的守护者,是政策的制定者,是有谋的“肉食者”,相对而言,城乡社会各尽职守,各具社会结构功能,城与乡在差异中自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其主要的功能性特征是“市”,即其生产、交换、消费的空间场域,而不是军事防御、人身保护意义上的“城”。随着城市手工作坊和自谋生路的知识人的出现,城市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特征逐渐加强,其现代性内质也逐渐清晰。由于城乡可供交换的物资增加,“乡”对“城”的想象也逐渐增多。在唐代文学中出现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文学表述,所寄寓更多的则是对农人的理解与同情。但作品中作为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仍然具有自然空间意义上的平等性和正义性,即在“自在的自然”(马克思语)的意义上,城与乡并不存在资本、经济意义上的根本性冲突。也就是说,在“自在空间”这个意义上,工业和农业的交换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城与乡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相成”的一体两面。
但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城乡的对立、冲突被强化,与此相关,文学也表现出城乡对比的鲜明特点。单就前者而言,“分工引起商品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交换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9]390马克思通过商业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的分离,科学地论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预见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可能。就中国城乡关系史而言,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变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从“相成相克”到城乡对立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相成相克”的、“相关一体”的平衡状态被外来工业产品的大量倾销而打破。[5]353自此,城市(都市)不再消费大量的农副产品以反哺农村,更严重的是,都市(特别是沿海大都市)舶来大量的“洋货”,那些批量生产的机器工业产品倾销国内,严重冲击了国内手工产品销售。同时,城市开始借机器生产技术,生产出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比如丝织品、棉麻产品。农副产品和农村手工业产品因国外和国内工业产品的挤压而滞销,农村经济迅速破败。而农村破败的直接原因就是都市对外来机器、技术以及工业产品的吸纳与行销,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不但失去了往日的供销关系,反而城市因其工业化生产基础,很自然地引入更先进的工业生产机器和技术,生产出大量可替代农副产品的替代品。由此,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城市(都市)则成为农村的异己,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冲突空前强化,城市甚至成为农村生死存亡的决定者。生产力的改变相应地制造出新的空间,新“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语)必将引发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从而形成新的空间认知,这种状况得到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1930 年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就是对这一现状形象的概括和广阔的展现,甚至是新文学以来文学城乡叙事中最为集中的反映,农民(蚕农)农产品的贱卖、滞销使得他们对工业、城市以及外来商品非常憎恨。当然,这仅仅是城乡发展走向异路、出现矛盾的一种文学表现方式。在1940 年代,费孝通先生则从社会学和经济史的角度作出判断:“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向了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演下去。这是一切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5]353不无可惜的是,费孝通先生期望的城乡“相成”的城乡关系至今并未实现。后来,因为城乡相隔的制度原因,城乡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出现了恶化,乡村社会的城市空间认知也因此异常敌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城市经验由贫富差距、城乡矛盾上升为城乡对立。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关系中的矛盾与对立,以及在1950 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背景下将如何发展,乡村(农村)能否获得主流话语讲述和建构的历史合法性?
三、城市空间改造与“城—乡”关系想象
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意识,城市被认为是被包围、被占领的空间,而乡村因为蕴藏着被压迫阶级翻身解放的思想和愿望,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中获得主流话语讲述的历史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对城市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空间改造,具体表现为对农村和农业实行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这两种改造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城乡之间的互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互动相对较少,甚至城乡之间的隔膜和障碍越来越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设立障碍的最终结果是……城里人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城里人一等。农民倾向于承认其生活低城里人一等。”[10]663工业“大跃进”时期,由于城市工业扩大生产,大量农村劳动力通过招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了一个高峰期。但是没有科学指导的工业“跃进”带来的问题日趋明显,城市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远远低于城乡青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为了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缓和工业跃进带来的城市过分拥挤而引起的人口、粮食、就业等问题,1960 年代初期,国家从政策层面积极鼓励城市青年男女“上山下乡”。“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的盲目行为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发出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并且对农村青年提出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1]在这一指示下,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参加劳动生产,即中国知青史上的“上山下乡运动”①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由政府引导的、鼓励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劳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人口迁移运动。毛泽东曾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新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实际上,“上山下乡”的观念在五十年代既已出现。1955 年,以北京城市青年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志愿者,远赴关东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上山下乡运动到“文革”开始时达到高峰。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方式逐步返回城市。未能回城的青年将自己的遭遇归因于农村的拖累,因此,城乡之间的误解增多,城乡矛盾进一步增加。相关论述参考了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观点。。按照政策的规定,这个活动是自愿的。政府鼓励满怀理想的青年人献身于建设农村这一光荣的工作中去。曾出现了城市呐喊、农村呼吁、政府鼓励、领袖号召的轰轰烈烈的下乡局面,以实现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人生理想。在空间认知范畴内,农村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用这些理想化的术语表述时,到农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认:这是一种献身行为,言下之意是农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10]663其中已暗含了农村低于城市的先天因素,所谓的“自愿”的成分逐渐减少①在这个运动期间,从1962年至1968年,约有120万城市青年“下到”农村。1968年后,这一活动规模大大增加。1968年到1978年间,12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这个数字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1%。不过,此时运动自愿性逐渐减少。见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等,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2007年重印),第663页。。部分未能回城的青年,将自己的个人遭遇归因于农村,因此,城乡之间的误解日渐增多,城乡矛盾进一步增加。城乡关系在政策引导和个人志愿之间不断错位,城乡空间的矛盾和对立再一次突显。这也是“知青”小说一贯的主题。
进一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国社会性质也随之改变,相应地,由于民间乡土话语逐渐被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所取代,“乡土文学”也开始向农村题材的小说转变。乡土文学中的乡村、乡情,民俗、民情等内容因社会主义改造而弱化,甚至“自动离场”。写农民思想转变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马烽的《韩梅梅》等等大量小说,往往以先进/落后人物、“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旨来结构小说②也有少量的作品将“路线斗争”和“乡村伦理”作结合、对比,以突显新政权、新思想,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偶尔会涉及到人物与城市、县城、镇、区等“非乡村”的社会空间关系,但这些空间往往是作为学习上级文件、接受革命教育、开展思想改造的公共话语场所,而非生活化的个人空间,其功能是实现上传下达的中间部门,而不是生产、消费的社会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话语转型直接影响了文学主题的变化和空间的感知。从新文学的乡土主题变化来看,比如“革命话语”对“启蒙话语”的取代,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里的启蒙话语在“城—乡”关系上所指的主要是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即以城市来批判乡村,通过民主、科学的观念批判、改变国民的愚与弱。在启蒙视野下,整个乡村社会保守、愚昧,并有“三座大山”的压榨、“四大绳索”的捆绑,需赋予新的思想。但是,在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笔下,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潜隐在乡土社会中真的、美的、善的质素,那是在启蒙话语盛行时代的另一种声音。
在革命话语取代启蒙话语之前,农村/乡土题材的作品,更多则为表现乡村社会内部的关系,而在革命话语进入农村之后,民间话语的生存处境相对尴尬。出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需要,这个时期农村题材的作品,要么就是土地改革,要么就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话语对民间话语的重组,具体而言,即公社化、集体化的革命思维开始介入、改造乡村内部的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被革命话语所取代。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中,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路线斗争”或阶级关系。相应地,在翻身与解放、锻炼与改造的革命主题引领下,小说叙事中的农村空间关注的不是作为普通百姓之间的乡村内部关系,而是依附于经济和阶级等的乡村外部关系。也就是说,那些家族的、亲情的、血缘的、乡邻的、乡里的等等民间乡村话语,要么被取代,要么被重组,而维系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比如乡规、相约、族规、伦常等行为规范的伦理意义很难发挥作用。在农耕传统文化中,这些乡规、乡约的价值核心是作为道德体系和文化精神的“礼”③这种乡规、乡约的价值核心是“礼”,按照费孝通《生育制度》《乡土社会》《乡土重建》里的观念,是指如下三层内涵:一为节制人的生物性的社会制度,一为一套道德体系和权力结构,一为一种文化精神。,它是礼治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代为执行行政监督、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一是乡绅,主要负责协调乡村事务和官民关系,二是民间伦理,以维系基础家族、血缘、亲情关系及邻里关系,[12]93-95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政权的干部,比如村支书、村社主任,或者合作社主任,或是一个生产队队长,以代表新政权实现管理老百姓的行政功能。“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叙事便以一种革命的规约取代了传统的乡规、乡约,在农村空间内部人际关系出现了革命性变革和重组。
所以,中国新文学在发生期已表现出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冲突,也凸显了作家现代性体验的价值取向④当然,亦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的城乡二元价值和城乡对立是从唐代既已开始,且城市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话题。此论参考了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0年版)的观点论述。。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内战争和社会政治等原因,城乡互动的关系被制约和遮蔽,甚至在20 世纪50~70 年代,中国社会对城市、城市文化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令人欣喜的是,近四十多年(自1978 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波折,不断修正“左”的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城乡大众的日常生活观照的合法性得以保证。随着制度层面的城乡流动壁垒逐渐被破除,城市化进程在各种话语交锋后再次启动,单一的“城—乡”关系渐趋走向多元交往,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冲突与对话成为这一时段文学表达的总体特征。以此为起点,“城—乡”关系已成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极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极其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与此相关,“城—乡”关系书写也再次成为文学表现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语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