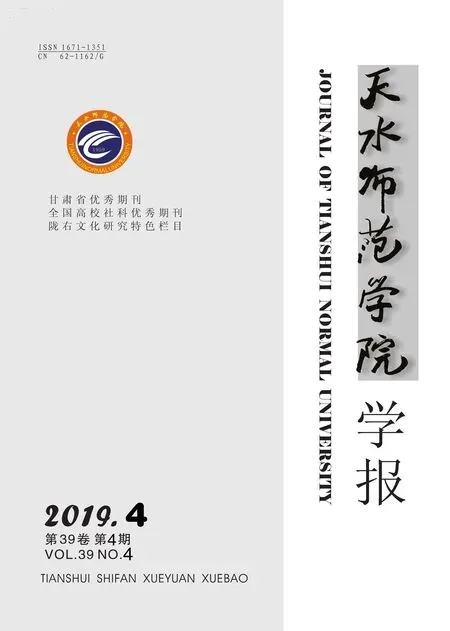从“张国臂掖”到“生态屏障”
——河西走廊由农返牧的历史契机及其地缘政治学意涵
2019-01-20王勇,荆琦
王 勇,荆 琦
(西北师范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河西走廊上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类型、地缘政治密不可分,离开河西走廊,单独谈论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显然是不得要领的。河西走廊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脉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西与新疆交界,南以祁连山与青海省相接,北有北山山系与内蒙古毗邻。河西走廊的地势南高北低,按地貌特点可分为3个区:祁连山地、河西走廊(绿洲区域)及北山山地,其中,祁连山地与河西走廊的关系最为密切。解开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钥匙不仅在祁连山本身,更主要在于河西走廊。
一、农牧分化·“长城之谜”:泛中原农耕区的合并趋势是秦帝国形成的内在动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牧大分化的开始。秦始皇一方面将泛中原农耕统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则通过建造万里长城(从山海关到甘肃临洮)将游牧经济集中“挤压”到长城以外,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体两面。因此,长城可被视为一个具有规模化效应的农牧分界装置。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泛中原地区的许多小诸侯国之间通常都存在着大片的“隙地”,这些“野外”空间为游牧民族的活动提供了便利,使得每一个在此定居的农业国家都极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和掠夺①如果没有过密化,即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那么相邻社群之间“隙地”的存在便是很正常的现象。周振鹤先生的研究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就存在着大量“隙地”,以至于使许多进攻邻国的军队经常出入于无人之境。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6页。。哈·麦金德(Mackinder H.J.)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提到:一个富庶的定居农耕地区,从来都是周围毗邻的蛮族人觊觎和劫掠的对象②哈·麦金德的原话是:“一个富庶的文明社会是对征服者有诱惑力的地区。”详见哈·麦金德(Mackinder H.J.)《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页。。显然,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下,单个从事定居农耕的小诸侯国往往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各诸侯国之间进行联合防御的信息成本和交通成本也很高。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游牧民族力量的发展壮大,各诸侯国在争霸的同时,也开始面临更为强大的共同外部敌人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春秋战国时期,泛中原农耕区的各诸侯列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合并的内在动力和历史趋势。因为合并以后的中原农业国家,才有可能消除“隙地”,并有能力对西北游牧民族进行规模化的防御。
然而,秦统一六国,在造就了规模化的中原农业国家的同时,也激起了长城之外众多游牧部落联合起来以共同对抗中原农业国家的“野心”,这个难题其实就留给了后来的西汉王朝。在西汉设立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被从事游牧经济的月氏人所占领,是一个水草丰茂、适宜畜牧的地方。这时的河西走廊实际上也是青藏高原,尤其是靠近祁连山的河湟地区与蒙古高原,甚至是西域之间将游牧经济相互联结的“高速通道”。汉帝国显然面临着来自“大西北”——即青藏高原、蒙古和西域地带随时可能联合起来的游牧民族的强大攻势,力量上的不对称格局仍然存在,这样的“天倾西北”之势,确实是悬在新生的农业帝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汉帝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危机,实际上也就是更早以前西周的地缘政治危机,[1]秦并六国以及修筑长城,解决了东周列国所共同面对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却给此后的汉帝国留下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因此,大致可以说,历史上中原农业国家的致命威胁几乎都来自西北方向突然变得强大起来的游牧人群。
但是,汉帝国要想彻底解决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危机,就必须依靠军事手段把定居农业拓展至陇西乃至河西走廊这些生态相对脆弱的区域,并借此对自由活动在青藏、蒙古和西域等广阔地带的游牧民族进行分隔和钳制,以防势力强大的游牧帝国的形成。这样一种地缘政治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中国的国家建构。自此以后,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在河西走廊乃至整个长城地带,都面临着政治安全与生态安全之间的两难选择,哪个朝代的统 治者能够平衡好这个矛盾,哪个朝代就能长治久安。
二、由牧转农·“张国臂掖”:河西走廊由牧转农是汉代农业国家向西拓展的必然代价
对于游牧民族的致命威胁,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就已经在“白登之围”中亲自领教到了。只是汉初的统治者还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边患问题的能力。汉初以关中为本位(以“关中核心区”“关外直辖地”和“关外王国”为主要格局的政治地理)的政治策略,虽然为国家的休养生息确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避免了重蹈秦朝亡国的覆辙,但是,随着东部诸侯内部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及边疆异族对帝国威胁的持续增加,尤其是匈奴的不断入侵,汉初构建的政治地理格局到武帝时代已不能适应帝国所面临的内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通过拓疆、“广关”等一系列措施,在对汉初的政治地理格局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以“大关中”、“关外内郡”和边疆区为主要格局的政治地理。[2]于是,打通河西走廊,就成了汉武帝时期地缘政治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汉武帝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自张骞往返西域后,先后派霍去病等西击匈奴,并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
对于河西走廊由牧转农的历史背景,《汉书·地理志》曾做了详细的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3]1612“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3]1613《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4]2479同年夏,霍去病再次深入河西走廊,对此地匈奴各部进行了致命的打击,“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两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4]2480
草原上的军事征伐胜利后,如果弃而不守,胜利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农业帝国的军队要想长期驻守在远离中原腹地的西北草原地带,就必须进行军事屯垦,实现食草自给。因此,改变草原上传统的经济形态,即由牧转农,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史载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是唱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样的谶语退却的。也正是此时,河西走廊开启了第一次长达数百年的重要的社会转型——从游牧转向农耕。河西走廊由牧转农的历史代价无疑是血腥而巨大的,同时也留下了远遁的游牧民再回头夺回失地以实施报复的历史循环。因此,长期控制草原的难度,其实远远大于一次性占领草原的难度。汉军借鉴了西周时期类似“井田制”的经验,进行军事屯田,即先驻扎下来,垦殖农田,并自力更生,长期坚守,然后修建军事工事、烽燧和边墙等防御设施,借此便可步步为营,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逐渐拓展。事实上,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的开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汉代的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历史政治版图上中原农耕空间向西拓展的一块“突围区域”。转牧为农,屯垦驻守,以点控面,扎实推进,这就是农业国家向草原戈壁和沙漠地带拓展的不二法门①从物理政治学的视角看,以农耕空间去征服草原空间的办法,就是将平滑空间纹理化或网格化。详细从哲学层面的论述,可参见吉尔·德勒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557页。事实上,在物理世界里,也常常可以见到通过纹理化或“网格化”设计、设施来控制各种“流”——水流、沙流、人流等等,以防范其危险后果。比如,青藏铁路格尔木沿线附近随处可见的“石垒阵”,是用来缓减并防控流沙淹没铁轨的设施;水库内外侧斜坡坝体以及公路旁斜坡山体上的网格状砌砖,则是用来缓解水流或雨水的冲刷力的;火车站前入口处的弓形的线隔通道,是用来控制庞大的旅客流的进站流速的。这些设计、设施,在本质上都是用来对各种各样的流所实施的捕获装置,目的都在于将速度纳入在可控的范围内。在德勒兹看来,“国家”也就是类似于这些设计、设施的捕获装置。。
军事力量在河西走廊长期驻扎下来以后,有两个显著的效果:其一是开辟出了进一步向西域拓展的陆上通道,使深入内地的中原农耕区域与西域得以互联互通。河西走廊上较为完善的驿运和后勤保障系统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其二便是“张国臂掖”,即所谓断匈奴之左右臂而张帝国之左右臂,隔断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的纽带,弱化各自的力量并分而治之。一般而言,单个的、小股的游牧部落的快速移动并不会对中原农业国形成太大的威胁,但是,广阔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旦联合为更大的部落联盟,进而形成游牧帝国时,就会对中原形成极大的压力和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当西北方向的游牧部落形成一个广阔的扇形包围圈时,中原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原军队需要长期驻扎在草原地带,并且还要实现“联通”和“隔离”之一举两得的政治功能时,河西走廊上主导性经济类型转变,即游牧经济向定居农耕或农牧兼营经济类型的转型便是势所必然。
定居农业,移民实边,军事城镇以及边墙烽燧体系的建立,都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从祁连山北麓由上而下辐射到走廊绿洲和谷地的水网,也为河西走廊由牧转农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和基础性条件,使自流灌溉得以可能。因而,草原变农田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诸如屯垦驻守、粮草自给、以点控面和攻防有余等,这些需要有稳定的“根据地”才能积累起来的国家“实力”,在游牧经济的背景下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河西走廊由牧转农是汉代农业国家向西拓展的一个必然代价,当然也包括了生态环境上的代价。不过,从当时的地缘政治视角来衡量,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三、由农返牧·“生态屏障”:河西走廊由农返牧是当代中国“国家养生”的明智选择
从综合自然环境禀赋来看,河西走廊绿洲区域宜农宜牧,但更宜牧。有史料记载,历史上凡是黄河变得相对清澈的时代,都是正值西北地区游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事实上,河西走廊农业和牧业的交替变迁曾经出现过多次,代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两种力量在此反复“拉锯”,[5]这或许就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自调适的一种表现。如前所述,从汉代开始的河西走廊第一次由牧转农的历史进程,是由当时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命——“联通西域”和“隔离蒙藏”——所决定的,由此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据史载,自明清以后,随着移民不断增加,河西走廊农业活动加剧,导致今天内陆河上游地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减少,冰川面积缩小,雪线上升,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中游的绿洲地区,农田盐渍化、荒漠化,水质污染,古城址废弃;下游地区终端湖消失,沙生植物枯萎,物种减少,沙尘暴肆虐。这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河西走廊在历史上被长期过度开发的累积性后果。当然,冰川面积缩小、雪线上升也有全球气候变化,即“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从地形构成上来讲,河西走廊由祁连山地、绿洲区域及北山山地三个板块组成,依次称为甲区、乙区和丙区②当然也有另外的分类观点,比如依河西内陆流域自南而北可分为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平原)、北山山地及内蒙古高原(西端)四个地貌单元,依地貌分为南部山地、中部绿洲、北部荒漠区。。在三个板块之间,海拔高度依次降低,年均降水量依次减少,年均蒸发量依次增加,年均气温依次升高,年均日照时间依次增加,地下水资源分布依次减少。河西走廊付出生态环境代价的发生逻辑大致如此:首先是乙区,即海拔最低处的绿洲农业的开发,人口开始增加;接下来,一部分人口开始被挤压至甲区,即祁连山南麓至走廊绿洲之间中程海拔高度的冲积扇(坡地),并以牧业和狩猎维持主生计;再接下来,随着这部分区域人口的增加,其中的一部分人口会被挤压到祁连山北麓高程海拔地带,并向林区讨生计。与此同时,乙区即海拔最低处绿洲区域的人口也开始逐渐向丙区,即北山山地(戈壁沙漠)迁移垦殖。这是一个人口压力从乙区分别向甲区和丙区不断传递的生存链条,也体现了祁连山生态压力不断增加的过程及祁连山的雪线不断上升的过程。源头的压力其实正是来自乙区,即绿洲地带的农业开发,当然也包括了近代以来的工业开发。绿洲地带的农业和工业开发,在耗尽了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中下游的地下水后,开始向上游挺进。[6]
2007 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其中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是:“流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垦荒地。流域上游海拔2600 米以上地区要退耕还林还草,流域沙漠沿线5~10 公里区域内要采取退耕、搬迁、封育等措施恢复生态。”[7]从今天来看,河西走廊由牧转农的地缘政治使命——“联通西域”和“隔离蒙藏”——已经基本实现。因为今天蒙藏地区的牧区,均已划界定牧,广域游牧已经基本转变为局域轮牧或定居定牧,所谓蒙藏两区游牧民联合起来对中原施压的“传统威胁”已经不复存在。[8]但是,今天的河西走廊,联通西域乃至中亚的地缘政治使命,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今天河西走廊沟通蒙藏、联通西域的交通与政治功能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有所增强,只是,威胁这一交通大动脉安全和畅通的因素,已不再是蒙藏地区的游牧民,而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祁连山日益上升的雪线。如果河西走廊被沙漠吞噬,或者河西走廊上的城镇失去了生活用水,那么就等于中国的腹地失去了生态屏障。先不论河西走廊在“一带一路”上发挥联接欧亚大陆的时代功能不能实现,就连联接青藏、新疆、内蒙和内地进而“团结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功能也会丧失。目前,已建成的出疆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路就是河西走廊,另外,由于河西走廊地形狭窄,管道、公路、铁路、电力、通信等众多工程均由此通过,河西走廊已越发拥挤,生态安全已成为这里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天的河西走廊及祁连山的生态安全问题,实质上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战略安全问题。
2010 年12 月,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西北地区主要规定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并给予特别保护,彰显了真正的“法律理性”。尽管法律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预防可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但是,桑斯坦教授却认为,遍历现代世界各国,许多需要发挥预防功能的法律原则是瘫痪性的。风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可能预防全部的风险。应对预防原则进行重构,设立灾难预防原则,即对重大风险进行预防,并在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注意相关法律措施的成本。[9]这显然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提醒。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重大成本进行“预防”的地区。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当代中国应该预防,并且是可以预防的重大政治风险。《规划》将其作为重点予以规定,体现的便是其非凡的“法律理性”。[10]
地缘政治学并不鼓励国家为了扩张而“四处拼命”,而是提醒要进行“国家养生”,在不透支综合国力的前提下稳步“成长”。[11]既然今日的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区域已经伤痕累累,大西北的生态屏障地位岌岌可危,那么,就要让这一地带先休养疗伤,待恢复元气之后,再图发展,进而使河西走廊再度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中的“贮存地”。[12]河西走廊可借助于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历史契机,实现由农返牧的转型。如前所述,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河西走廊上的人类活动及其经济类型、地缘政治密不可分。祁连山和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整体考虑,统筹兼顾,如果不改变河西走廊上绿洲农业的开发模式,祁连山的水源涵养作用是无法持久保持的。只有当绿洲农业转型为种草放牧时,地下水才会逐渐恢复,从而可以保证中游和上游地下水的充盈。
河西走廊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入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河西”文化,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民族就是如此。[13]同时,河西走廊亦为农牧交错区,历史上其地风俗亦与中原迥异。因此,河西走廊上的农民变牧民,从文化习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从祁连山北麓至河西走廊绿洲,再至内蒙古干旱草原之间,依海拔高低,依次呈现出的历史地理文化类型大致是:藏文化(半农半牧)、汉文化(定居农业)和蒙古文化(游牧文化)。此地处于绿洲地带的汉文化(定居农业)与毗邻的牧业文化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很容易向牧业文化转型。另外,河西走廊要摆脱对传统农业和工矿业的发展路径依赖,实现弯道超车,可重点发展光电和风电新能源等特色产业,以及牧家乐等旅游产业,这样可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光热资源和风力资源在河西走廊上是真正的“原始丰饶”,通过光伏和风电来“捕获”和开发这些资源,就可以形成对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的替代性新型产业,从而引领河西走廊产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可循环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河西走廊上实行退耕还草,国家的农业补贴转变成牧业补贴之后,当地农民的边际收益会随之增加。从甘肃国土资源的自然禀赋来看,宜牧类土地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祁连山、甘南及中部黄土区。[14]前文已经提到,尽管河西走廊宜农宜牧,但从长远来看,更适宜畜牧。众所周知,河西走廊绿洲上的土地用于农耕时,高度依赖于祁连山的融雪以及地下水的灌溉,像陇东那样的雨水旱作农业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近年来,河西走廊已经出现了资本控制下的制种玉米产业全覆盖的局面,这是一种对河西走廊水土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的产业,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商品化,口粮和蔬菜几乎完全不自己生产了,大都要通过货币购买,这显然不是长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是农业尤其是资本农业对河西走廊地下水造成的严峻的压力。如果河西走廊上的绿洲由农业转型为牧业,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对地下水资源消耗的压力,当然转型后牧业的经营模式,尚需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过度放牧和将来由农转牧后,盲目引水灌溉扩大绿洲面积以承载更多牲畜的情况,都会引发植被破坏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因此,实现草畜平衡基础上的可持续牧业尤为重要。历史上,关于牧业文明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之间正相关性的诸多案例,也值得特别关注。
对此,任继周先生提出了相关方案。任先生认为,“从农业系统的角度分析,持续维护祁连山林、草、苔藓灌丛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把原有的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改造为山地-绿洲-荒漠耦合系统。利用绿洲的耕地,生产优质牧草,供应山地和荒漠,缓解草原的放牧压力;绿洲通过草田轮作,避免土壤盐渍化,同时吸引山区的家畜来育肥,开展草畜产品深加工,提升整个系统的经济效益。”[15]
这就是说,山地-绿洲-荒漠的系统耦合是祁连山水资源保护的关键措施,在交通运输成本大为降低的今天具有了更高的可行性——河西走廊本身就处在交通大动脉上,历史上在河西走廊进行屯垦,以实现粮食自给和“以守为攻”的初始使命已经不复存在了,加之今天河西走廊上的传统农民进行个体耕种,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没有规模效应了,因此,农转牧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河西走廊农民的产业转型有多个渠道可供选择,比如,在戈壁草地上辅之以光伏产业,即“种光田”,以及利用成功的“草方格”经验进行沙漠种草等,将传统的“农牧民”身份转型为现代的、产业化的“生态民”。
四、河西走廊的经济地理类型与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主题相依存
前文多次提到,从大历史角度审视,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河西走廊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相应的经济地理类型密不可分,而河西走廊的人类活动以及相应的经济地理类型又与中国国家建构和成长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主题相伴随。从今天来看,河西走廊当初由牧转农的地缘政治使命——“联通西域”和“隔离蒙藏”——已经完成,而新时代的地缘政治使命却日益凸显并迫在眉睫——经由“国家养生”来保障西北政治生态安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现。[16]因此,有必要借助于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历史契机,适时通过由农返牧来偿还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区域的历史“生态欠账”,恢复其西北“生态屏障”的地缘战略地位。这显然是新时代河西走廊地缘政治战略主题进行及时调整的一个明智选择。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从历史维度和发展模式以及发展理念的角度进行深刻反思,不进行河西走廊民生以及发展模式上的整体性反思,只是强调严格环境执法,严格问责,以及单纯实施禁和堵的办法,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所以,环境治理的功夫其实在“治理”之外。
法国史学家谢和耐曾经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形成机理有过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文明显得似乎与一种发达的农业类型有关,而这种农业又几乎完全局限于平原与河谷地。在汉地或已被汉化的地区,大山从未被开发过,并且始终是另一类居民的领域。”当农业和牧业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结合起来之时,“东亚却是世界上在牧民界与耕农界之间作出明确分界的唯一地区”。[17]27显然,谢和耐是从“小中国”的视角来界定中国的。事实上,今日的中国是跨越长城内外的大中国。但是,谢和耐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理解大中国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大中国为什么要在牧民界与耕农界之间作出明确分界?这是因为,有了这个界分,就有了“西北水木”与“中原农耕”的自然的经济地理上的分工。如果没有西北水木这一“水源地”,也就没有中原农耕这一“受水区”,正是这种紧密的依存关系的存在,才使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下来。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黄仁宇式的“大历史”的解释,但是却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启示。[18]1-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生命之源”。传统中国人的国家信仰就是“社稷”信仰,就是对土地和山水的神圣崇拜和虔诚护持。人类是天地之子,是大地母亲的子女,栖息地是一切物种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一旦栖息地破坏了,物种也就灭绝了。“西北虽然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却是国家稳定,统一和安全的中心。”[19]81-90恢复祁连山和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希望和信心所系,就是美丽中国的国际名片所在。今后,行驶在河西走廊——“欧亚大陆桥”——高速铁路的中欧国际列车上,人们也许会透过两侧的车窗,惊喜地看到一望无边的茵茵绿草代替了荒凉的沙漠戈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西北师范大学潘竟虎教授考释发现,《敕勒歌》描述的景象就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南山(阴山)的疏勒河边;能隐没牛羊的草只有一种,就是生长在河西碱性土壤草原上的芨芨草(白草)。也就是说,《敕勒歌》的原产地,就在河西走廊。详见潘竟虎《敕勒歌描述的景象究竟在哪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54573-984682.html.的情景就又会回来了!
五、余论:“通道政治”与“通道经济”的文化整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欧亚)视域下的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新思维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作出了“八个着力”的重要指示: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升综合实力;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扎实做好“三农”工作;着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1]
这“八个着力”重要指示中,“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是“八个着力”的总抓手。既然是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那就一定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要在一个战略大背景下思考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就甘肃论甘肃,不能就甘肃发展论甘肃发展,至少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欧亚)视域下思考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要把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愿景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十九大报告中第十二部分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专门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和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有关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发现、发掘和诠释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新思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打开了灵感涌现的智慧视窗。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欧亚)视域下思考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可以从时间地理学的方法论视角切入。甘肃是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这已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在“通道”前加“黄金”来修饰,是有主体性视角的区别的,换言之,是“过路人”眼中的黄金通道,还是“当地人”眼中的黄金通道?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从时间地理学和大历史视野看,可以说甘肃兴于通道,也衰于通道,这与通道上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速”有关,比如今天我们常见的路边店即是如此。路上要素流动的速度与路边店的兴衰密切相关——速度慢,则有上路也有下路,店铺生意兴隆;速度快,则上路多而下路少,行者多穿越而过而不驻留,道路仅成了“过路人”眼中的黄金通道,店铺生意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退。车马载信时代的甘肃,之所以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是因为通道上的要素流动的速度较慢或适中,当地人为过路人提供安全食宿和服务,过路人为当地人留下“消费”与文化或技术信息,于是,“通道政治”与“通道经济”才相得益彰。
然而,进入高铁时代、空中客车时代和网络信息时代,甘肃的“通道政治”与“通道经济”之间悄然间出现了一些内在张力,“通道政治”逐渐失去了“通道经济”的内在滋养。通道上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开始快速“穿越”甘肃而较少驻留,甘肃逐渐成了欧亚大陆上“旅行者”眼中的“黄金通道”。当进一步发展到“欧亚都市岛”时代时,“西安—乌鲁木齐”更可能成为节点城市而遗忘兰州,也就是说,从“马蹄下的丝绸之路”到“车轮下的丝绸之路”,再到“铁轨下的丝绸之路”乃至“机翼下的丝绸之路”,很可能会出现丝绸之路“黄金段”的单方面繁荣——“过路人”眼中的黄金通道。旅客快速“穿超”河西走廊而较少“驻留”,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局的时间地理学原因。
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甘肃一方面不能让自己承担的传统的地缘安全和民族团结这一“通道政治”使命异化,另一方面还要兼顾“通道经济”的目标。这是一个难题,但是困局中也蕴藏着机遇,出路就藏在甘肃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之中。让过路的人流多停留一会儿的办法是文化吸引——以中西合璧文化为纽带,以“作为欧亚文明古道的甘肃”为名片,经由文化找回人类的深层情感方式,这就是甘肃对世界人民的最大吸引力。表层生活方式与深层情感方式的冲突,正是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文化是久远传统,是真正的深层情感方式的载体,是当今人类最需要的东西。交通通信的便捷化,带来了空间消费即空间资本化,谁占有最优空间,谁就占有了先机。人类空间(时空)消费对象的顺序通常是从自然风光到文化调适。甘肃坐拥着世界上最丰富、最多元的文化遗产即人类深层情感方式的文化载体。甘肃的“原”字号产品多,“初”字号产业比重大,这两个“字号”正是可以转化为优势的所谓“劣势”。经由文化整合,欧亚互联互通时代的甘肃有望再度迎来“通道政治”与“通道经济”的相得益彰和全面繁荣,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欧亚)视域下的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新思维。
然而,实现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那就是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