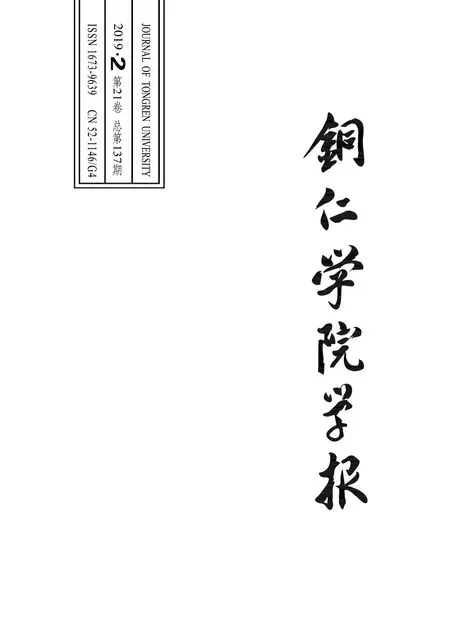聚焦叙述、圆形人物与“无用的细节”
——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艺术手法赏析
2019-01-20曹源
曹 源
( 1.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2.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面对不幸,弱者只会哭泣,而强者却能掐住命运的咽喉从而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侯乃铭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近年来创获颇丰。继长篇小说《樱花飘零》、中篇小说《可怜的我》《镜中之影》之后,他的第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最后的梦园》于201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向笔群教授在序言《未来社会:人性与兽性搏击——序侯乃铭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中,认为该小说反映了“未来社会的人性与兽性搏击……触目惊心的故事背后,凸显出作者对人类未来的生存思考”[1]1,这个评价和把握是非常准确到位的。在我看来,《最后的梦园》的成功之处,除了思想主题的深刻,它的艺 术手法也是可圈可点。下面就小说的艺术手法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进一步挖掘这部小说中所蕴藏的丰富内容。
一、多视角下的焦点叙述
叙述视角与叙述焦点是叙事学当中的两个不同的概念,通俗地来说,前者是从观察的角度看,讲的是谁在看;而后者是指看什么、看谁。叙述焦点相当于天平的支点,它用来衡量两边是否平衡;或者相当于圆周的中心点,无论圆周中的射线或者扇形怎样移动却始终围绕圆心在运行。《最后的梦园》的叙述焦点正是故事主人公江屾,开头写江屾来到故事发生地江城接受谋杀任务,中间写江屾摧毁了 野生动物保护区“梦园”并脱出险地,结尾写刑满释放的江屾走出监狱。小说以江屾为圆心,以他雄壮的出场与悲壮式退场为弧线画出了一个规整的圆,毫无疑问,整部小说的“看点”都集中在江屾身上,这就是焦点叙述。
研究叙述焦点,首先一点就是要明确叙述视角,即通过怎样的叙述视角来达成焦点叙述的目的。因为“叙事角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方面,关乎讲述整个故事的方法技巧,不仅仅考察观察者是谁,同时也要考察观察者的态度立场”[2]134。《最后的梦园》第1章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而其他的11章则主要采用的是非限制性视角,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
小说中运用第三人称(江屾)的视角叙事,通过他观察的眼光最终将整个故事引发出来:
江屾走进电梯,控制面板上除了开关门键,就只有一个按键,按键上写着两个红字“地宫”。江屾果断地按下了“地宫”键,接着电梯便朝下驶去。“叮!”大约二十秒之后电梯停了下来,江屾走出电梯,走进一条通道,通道大约三十米长,墙体洁白,上面每隔四五米有一盏大灯,地上是深红色地毯,通道的尽头是一扇门,门上依然有指纹识别器,江屾走到门前输入了右手的指纹,门却并没有打开,而是提示他继续输入左手的指纹。[1]2
门打开了,江屾走了进去,里面很宽敞,是一间大型豪华办公室的布局,门对面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靠椅上坐着一个女人,她身边还立着一个秘书模样的女子。这两个人江屾都不陌生,坐着的那位是他的老板的夫人名叫唐慧婷,而站着的那位是她的私人女助理蒋夏。[1]2
第一段引文中,江屾“控制面板上除了开关门键,就只有一个按键,按键上写着两个红字‘地宫’”,听到“叮”的一声,感觉电梯停下来的时间为“大约二十秒”;第二段引文中,江屾看到“门对面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靠椅上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身边还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女人”。这种感官体验只有当事人江屾才能体验,而且他也只能体验到自己的体验,对于别人的体验他无从感知,这就是叙事学上所谓的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
其实,这种把视角限定的方式早先在《水浒传》中也曾经出现过,金圣叹将其定义为“影灯漏月”[3]163,这一叙述技巧的诞生冲击着之前存在的叙事方式。关于这一点,陈平原认为将视角限定在第三人称之上的艺术技巧在现代的小说中已经成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并逐步地将原先常用的非限制性视角取而代之[4]191。杨义对此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叙述视角的变化发展,主要是取决于人们逐步丰富的情感以及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2]150。
毋庸置疑,这部小说第一章采用江屾这个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是成功的。江屾接受梵天集团总裁夫人唐慧婷的雇佣,参与谋杀亲夫温世杰及其情妇们的计划。至于唐慧婷策划这起谋杀案的原因,因为小说第一章采用的是江屾这个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江屾刚开始一无所知,自然,读者刚开始也是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慢慢听了唐慧婷的口述,读者才和江屾一样得知原来是丈夫温世杰背叛了她,而且温世杰还要修改遗嘱分割本属于她和三个子女的财产,她故而痛下杀手。巨大悬疑之下的谋杀动机抽丝剥茧般慢慢浮出水面,令人惊心动魄,这样一种视角的采用一开始就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想象。
(二)非限制性视角
但是小说除了第1章之外,其他的11章更多地采用的是非限制性视角。所谓非限制性视角,有人把它比喻成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眼睛”,作为观察者来说,他就像一位能够预知一切的先知一样,站在居高的位置,仿佛全部事物尽收眼底。例如:
温世杰有一家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叫梦园,江屾早就知道,本来这片数千亩的原始森林相关部门是想砍伐掉一部分来做一项工程的,可是温世杰最终还是捷足先登以高价买下了这片森林,然后又从相关部门那里搞来了新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许可文件,很快这里就成了温世杰个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1]14
这位女郎不是别人,这是后来成为温世杰妻子的唐慧婷。唐慧婷与温世杰不同,她出身豪门,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名头最响的军政要员之一,常年在成都任职,母亲是某国有银行广州分行的副行长,她在家中又是独生女,父母都对她十分溺爱。[1]18
眼前这个女人江屾是有所耳闻的,她叫徐捷,曾经是某侦查兵部队的女兵,在她所在的部队中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以拳脚功夫凶狠而闻名,曾经在一次师团的比武中她一个人凭借一身厉害的拳脚功夫一口气连续击倒四五名大汉,因此在部队得了个母老虎的绰号。[1]7
野生动物保护区“梦园”的创办经历,温世杰妻子唐慧婷显赫的身世,温世杰保镖兼情妇徐捷的武功,以及其他众多情妇如何被温世杰收编等情节,叙述者都能收归眼底,成为了近乎无可匹敌的存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小说中人物的一切活动都逃不出这双“上帝的眼睛”。
《最后的梦园》采用的正是陈平原所谓的“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口吻”[4]67,西方传奇小说也经常采用这样一种非限制性视角叙事,《最后的梦园》也因此彰显了它的传奇色彩。
无论是“梦园”谋杀案的策划,还是人物与动物的生存博弈,叙述始终都是聚焦在江屾身上。作者手中高举明亮的聚光灯,他照耀着江屾一路前行,即使偶尔打照到其他人身上,但一俟该人完成其造型,聚焦的灯光依然在江屾头顶高悬,以主人公江屾一人的行动带动全部外在情节的发展。
既然有焦点,那么也就有盲点。盲点通常是主要光线无法照射的区域。《最后的梦园》中江屾女儿江娇娇在美国医院动手术的情况是盲点,江屾在江城市第五监狱三年有期徒刑的服刑情况也是盲点,其中的具体详细的细节小说都没有提及,究其原因,因为这些都不是小说想要表达的重点所在,这就避免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枝蔓;同时也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促使读者发挥阅读作品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作品是由作家的文本与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两个部分构成,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5]。
总之,不管小说是采用何种视角,我们都能发现小说叙事依据时间顺序在行进,始终聚焦江屾“所见、所闻、所感”而展开。这种焦点叙述的好处是它更利于情节的突出与集中,更利于加强叙事作品的叙事张力,有效地避免了因枝蔓多而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弊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在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操作方面也是把控得当,比如对温世杰等人的身世介绍都是通过倒叙的方式来完成的。
二、圆形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人物性格给人的不同审美感受可把人物区分为“扁平”和“圆形”两种,扁平人物性格单一,而圆形人物性格复杂。“当所创造的人物为了不再表达单一观念时,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一段近似于圆的曲线,这样所创造出来的人物谓之圆形人物”[6]。
既然作者手中的聚光灯始终高悬在主人公江屾头上,那江屾必然就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作者在江屾这个人物身上给予了更多的审美理想。江屾是一位从中东最动荡的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部队退伍的特种兵,武功高强。他之所以接受谋杀任务,完全是为了赚取救治瘫痪女儿的高昂的治疗费用才不得已而为之。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接受了任务的他,内心是复杂的。当他得知自己谋杀的对象温世杰修建“梦园”是为了穷奢极欲生活的丑行之后,江屾对他是鄙视憎恶的,而且下定决心痛下杀手,所以他会在2048年中秋节这个时间刻度上毫不犹豫地亲手摁下了摧毁“梦园”这个象征温世杰“帝王梦想”的机关。但是当他亲眼见到温世杰被棕熊米莎杀害,温世杰众多无辜情妇们遭受的种种惨状后,他又心生恻隐之心,开始行侠仗义。我们很难用“冷酷无情杀手”抑或“行侠仗义英雄”来定义他,只能说他两者兼备。小说中的他一直纠缠在金钱与道义、兽性与人性的两难选择之中,呈现出“圆形”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为了成功塑造江屾这样一个“圆形”人物形象,作者主要通过以 下两个方面的手法完成。
(一)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刻画
江屾是小说文本中的一个看点,江屾的言行也正是作者认真思考过并赋予他的,在聚焦他外在言行的同时,还深入他隐秘的心理活动,例如:
江屾心头暗想:“好谨慎的女人,把我找来这里究竟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哎!算了,不管那么多了,为了让我女儿娇娇能够好起来,别的也想不了那么多了!”[1]2
他(指江屾,笔者按)在心里对自己说:“庄小蝶是无辜的,她并不是温世杰的女人,她现在这样都是我造成的!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她平安出去……”[1]63
江屾自以为自己在战场上见惯了生死,生离死别对他而言早已麻木,可此时此刻他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抑制住自己夺眶而出的泪水。[1]107
唯有江屾独自一人坐在洞外的山坡上,望着西方殷红的晚霞出神,此时此刻江屾的心绪很乱,这些天他目睹了许多人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死,与他纠葛颇深的郎蓓蓓临死前的那一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娇娇手术是否成功也让他感到焦虑的,万千的思绪与苦恼如潮水般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让他苦恼不已。[1]115
通过江屾的心理活动可以得知,总裁夫人唐慧婷即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但为了“女儿娇娇能够好起来”,他也不得不违心地答应;“庄小蝶是无辜的,她并不是温世杰的女人,她现在这样都是我造成的!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她平安出去”“这些天他目睹了许多人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死,……万千的思绪与苦恼如潮水般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让他苦恼不已”,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心灵深处人性与兽性博弈之激烈,可见人物性格非单一化,而是颇具复杂性。
“人的意识既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的制约,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7]。故而现代小说创作越来越重视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甚至出现了意识流小说。《最后的梦园》直接通过对江屾隐秘心理活动具体而细微的描写,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真实感,不仅可以诱导读者去自我体验,而且能够使读者更加清楚地洞察人物的思想,体验江屾在金钱与道义、兽性与人性两难之间进行选择时的挣扎与痛苦感,而“圆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借此一步步完成塑造。
(二)写“美人陋处”的方法
专写“美人陋处”的观点是脂砚斋提出来的,《石头记》就是一个应用的典范。例如对“金陵十二钗”的描写,除了注重描写这些美人的美貌智慧之外,还特别突出了黛玉尖刻的一面、宝钗板正的一面、探春薄情寡义的一面、妙玉孤癖的一面,写“美人陋处”正是脂砚斋采用独到的眼光发现、总结出来的一种艺术手法[3]259。这种艺术手法与福斯特提出的“复杂的性格是圆形的,难以把握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就《石头记》来说,它最终塑成的人物并不是严格的圆形,还有着重突出的一面。《最后的梦园》中主人公江屾就是这样的圆形人物,而且还带有“陋处”,是带有“陋处”的圆形人物。例如:
说唐慧婷想请江屾帮她对付一个人,如果江屾答应,他女儿一切的医疗费用都将由唐慧婷承担,如果江屾不答应或者把事情泄露出去,那他将丢掉工作甚至更糟。于是万般无奈的江屾只好应允。[1]4
自从妻子阮萍去世之后江屾就再没近过女色,今晚如郎蓓蓓这般如花貌美的尤物主动送上门来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抗拒的。[1]78
江屾因为“女儿一切的医疗费用”与生怕“丢掉工作甚至更糟”而把自己的良知卖给了魔鬼,面对“郎蓓蓓这般如花貌美的尤物”时他欣然接纳,这就是江屾的“陋处”,理性让位于感性,欲望战胜了克制,江屾身上原始的动物性一面显露无遗。
当然,作者对“美人陋处”的描写是相当节制的,而且也不是小说的浓墨重彩,小说中更多的是描写江屾如何行侠仗义,特别到了小说结尾:
次日江屾带着录音笔去警察局自首时,原本十分棘手的案件很快就被专案组破获了,不出江屾所料,阮萍母女所所遭遇的那次事故果然和唐慧婷与蒋夏 有关,……最后法院判决唐慧婷和蒋夏无期徒刑,并没收其所有个人财产,而江屾由于其协助调查有功且主动认罪,所以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1]182
江屾最后选择了自首,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上述那些对于江屾受到金钱美色诱惑的描写,相比较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的正义立场来说,只能说是瑕不掩瑜,江屾这个带有“陋处”的准英雄人物形象并不因此而变得黯然无光,相反,这样的描述更加让江屾趋向于真实的存在,更加让读者觉得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
总之,在把江屾塑造成为“圆形”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这样两种技法不失为一种很凑效的手段,这样完成的小说会更加真实,同时也给人以更多审美想象空间。
三、说明性文字即“无用的细节”的大量引入
《最后的梦园》艺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夹杂了不少说明性文字,即“无用的细节”。
(一)说明性文字举例
如对“梦园”中豢养的棕熊米莎、黑豹、狮子拿破仑、网纹蟒蛇、美洲灰狼、老虎、鬣狗、食人鳄、豺狗、安第斯神鹫等种种野生动物的介绍,对杀死过一代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黑曼巴蛇、吃人的科莫多龙毒性的渲染,对独眼头狼的悲壮献身的评议,以及与这些动物相关奇闻异事等的介绍,等等。例文如下:
美洲灰狼虽然个头身体强壮,但是无论是胆量还是凶猛程度,甚至是捕猎技巧都不如蒙古草原狼。[1]88
它的学名叫湾鳄,主要分布在泰国、缅甸一带,当然它还有一个让人们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食人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兰里岛战役曾经让这种鳄鱼名声大躁,……最后岛上的数万只湾鳄都被引了过来,所以一夜之间日军就全军覆没了。[1]101-102
黑曼巴蛇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常年都盘踞在非洲各地的树木之上,在性格上它跟相对保守的眼镜王蛇不同,历来以性情凶暴而著称,不管是什么动物只要闯入了它们的领地,它们就会立刻发动突然袭击,梁露露就是误入了黑曼巴蛇的领地而招致了灭顶之灾。其次它的毒液号称是“世界第一剧毒”,即便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被黑曼巴蛇袭击过的人类依旧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死亡率。……后世的人们从毒性以及埃及艳后的性格上推测,她和她的侍女们用来自杀的那条蛇很有可能就是一条还未成年的黑曼巴蛇。[1]139-140
而且最可怕的是科莫多龙的那张嘴……因为这种动物长期以腐肉、同伴甚至是自己的幼崽为食,所以它的口腔中聚集了大量的高致命性病菌,一旦被它咬上一口,就算当时没死,那也会患上严重的败血症,最终导致死亡……[1]170
此刻那独眼头狼朝着高处一处山崖的方向望了一眼,它的眼神里充满了深邃与决绝。只见一只白狼正站在那山崖之上望着它,那白狼脚下还有着好几只小狼崽,它们也都在默默注视着独眼头狼,这白色母狼的意图很明显,它是想让它的孩子们看着它们的父亲是如何战斗是如何报恩的,无论这一战是生是死都可以让狼群的精神传承下去……[1]176
这些例子充分显示出叙述者在其描述的过程之中必定是对熊、豹、狮子、蟒蛇、灰狼、老虎、鬣狗、食人鳄、豺狗、安第斯神鹫等动物习性了如指掌,关于它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它们相关经典的历史掌故都心中有数,否则不可能娓娓道来,这充分显示了作者这方面知识的专长;而实时穿插的精妙点评,如“独眼头狼虽然死了,但狼群精神的传承也在这一刻悄然完成了”等,则升华了小说的格调与意境。
还有相关兵器方面的介绍。如对于温世杰高价拍买来的西伯利亚古董猎枪、瑞士锰钢军刀也是津津乐道:
这把复古的猎枪,本是多年前他与郎蓓蓓到圣彼得堡旅行时从一场拍卖会上买下的,这是一把当年西伯利亚老猎人使用过的古董,里面还装配了五十发猎户携带过的子弹。[1]68
这把军刀是温世杰当年在一场拍卖会上花重金 世界不能够很好地了解的基础之上[8]。就此而言,《最后的梦园》作者唯恐读者不甚了解,所以特意为我们补上了一堂野生动物学、兵器、佛学知识课。
“无用的细节”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是结构大于情节现象的一种体现。正如高行健所说:“结构大于情节,正如野兽大于老虎,尽管老虎是兽中之王”[9]。情节曾是传统小说结构的重要构成,有时甚至是结构的唯一一种方式。而随着小说艺术的不断发展,小说作家更多关注的是“非情节”因素,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与和平》中对道德的说教,以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后来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非情节小说,情节完全消失,例如一场对话,一幅生活场景,乃至一连串对某种事物的印象,都可以构成一篇小说。
同样,《最后的梦园》的创作也是如此,它并不以情节作为结构的唯一,大量“无用的细节”的引入就属于“非情节”因素,作者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非凡的见识,来吸引于读者。“无用的细节”的引入,看似偏离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使得叙事进程缓慢,但是它们在文本中的不间断穿插,却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更加饱和丰满的阅读感觉,读者通过这些所谓“无用的细节”,感觉到了阅读的兴趣与知识的魅力,达到“开卷有益”的目的,文本也因此更增添了文化底蕴的厚重感,故“无用”而成其为“有用”。
总而言之,小说的艺术手法呈现多样性,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多视角下的焦点叙述、圆形人物形象塑造、说明性文字即所谓“无用的细节”的大量引入等三个方面尤为突出。此外,小说《最后的梦园》的作者试图在原来创作基础上寻求进一步突破,例如序言中所提到的“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场景的转换与意识的流动共同构成小说的叙事场域”“摒弃作者以前一贯写实的创作手法,力图将虚实相间,着眼于未来,关注人类生存,使作品的立意具有文化的高度,对人性与兽性博弈的融合探索, 拿下的,一般的瑞士军刀用碳钢为材质制作的,但是这把军刀的材质可谓是与众不同,那是比碳钢要坚韧数十倍的猛钢,说它无坚不摧也不为过,据拍卖师介绍无论是铸造成本还是加工难度锰钢刀都要远远高于碳钢刀,还说当年的大唐帝国最鼎盛时期的唐军所装备的唐刀就是用锰钢为原料铸造的,而后来蒙古帝国横扫欧亚,所掠夺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也都是被拿来打造以锰钢为原料的兵刃。[1]82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得知,原来“大唐帝国最鼎盛时期的唐军所装备的唐刀”以及“蒙古帝国横扫欧亚”时使用的兵刃就是用锰钢为原料铸造的,这又涉及到历史方面的知识了。此外,小说在描述相关佛教的基本知识时也采用了说明性的文字,由此对人生终极问题展开探讨。如:
我希望鹰能把我叼去,如来前世割肉喂鹰,鹰后来成了佛祖的使者,鹰如果能将我叼去,我死后就能到极乐世界,在佛祖的脚下去当面向他忏悔了。[1]154
天雨虽大难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不渡无缘之人![1]159
这些说明介绍性的文字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大概占到小说文本总字数的1/10。
(二)“无用的细节”为何成为“有用”?
这些说明介绍性的文字,与故事以及故事中人物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联,但事实上它却又是文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部分,小说就会黯然失色许多。罗兰·巴尔特在《现实效果》(1968年发表于《交流》杂志)中称之为“无用的细节”。乔纳森·卡勒则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效果来考察“无用的细节”的作用,他认为这些部分将帮助读者产生叙述契合(narrative contracts)的作用。根据他的观点,这些成分的主要立足点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这样的语言单元在小说情节中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们却能够产生出一种良好的所谓的“真实效果”,这些成分能够使读者放心地像阐释现实世界那样阐释文本,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之中主观地认为读者将会对其所描绘的就使作品包孕着生命的厚度”[1]3等,其实也是该小说艺术手法上的出彩之处,这里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侯乃铭.最后的梦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2]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 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565.
[6]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7.
[7]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0.
[8]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89.
[9] 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