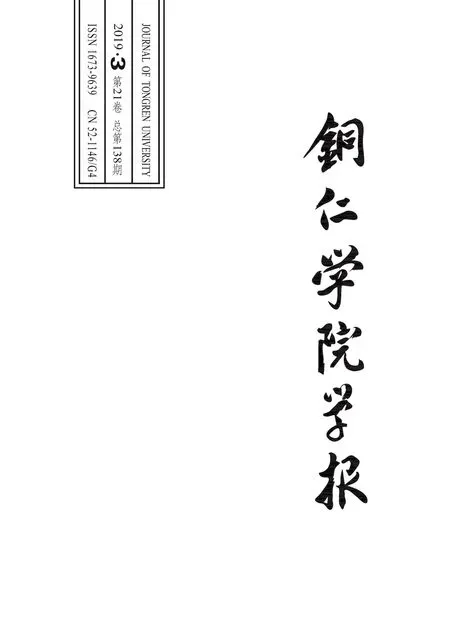古典诗学视域下的“险韵”现象
2019-01-19黄金灿
黄金灿
古典诗学视域下的“险韵”现象
黄金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诗韵学与诗学概念,“险韵”在当代古典诗学界受到普遍关注。所谓“险韵诗”,就是指押“险韵”这一艺术手法在诗歌结构系统中由从属地位上升至主导地位后形成的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险韵”与“强韵”“难韵”“僻韵”等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险韵诗”与次韵诗、独木桥体、联句诗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险韵”一共有三个典型历史文本,同时也由此产生三个代名词,即“竞病诗”“车斜韵”与“尖叉韵”,构成了我国古典诗学的特殊“险韵”现象。
险韵; 内涵; 诗歌类型; 代名词; 险韵现象
在当代古典诗学研究者的学术话语中,“险韵”是一个不时会映入眼帘的名词。例如,莫砺锋先生在探讨“王荆公体”的诗体特征时说:“王安石在押韵上也很下功夫,尤其喜欢在险韵上争奇斗巧。”[1]周裕锴先生在探讨宋人对声律的独特追求时说:“六朝唐的声律说提倡音韵的和谐协调,而宋人却有意识破坏这种和谐协调,下拗字,押险韵……。”[2]郑永晓先生在论证尤袤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时说:“如《次韵德翁苦雨》一诗能化俗为雅,又押险韵,也受到方回的赞誉……。”[3]“险韵”在当代古典诗学研究界被普遍关注的情形,使我们意识到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诗韵学与诗学概念。但同时我们往往又想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险韵”?它和古人经常提及的“险韵诗”究竟是什么关系?①古代诗人、诗论家津津乐道的“竞病诗”“车斜韵”“尖叉韵”到底是不是它的代名词?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或付之阙如,或未有定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即拟在古人具体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述的差异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对“险韵”与“险韵诗”的内涵加以界定,对其代名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进一步研究“险韵”与“险韵诗”提供有益参考。
一、“险韵”的内涵
我们拟采取以下步骤来探究“险韵”的内涵:首先,将“险韵”置于由与它近似的概念组成的特定系统中,通过分析它与这一系统中其他概念的异同,考察它的所指范畴;其次,重置一个新系统,即能容纳“险韵诗”而不是“险韵”的新系统,来进一步对“险韵诗”的内涵进行“再明确”;最后,将“险韵诗”置于更深广的理论视域中,探究其诗体属性,明确其诗体发生的内在动力,并为这一动力寻找学理依据。
(一)系统中的位置:“险韵”与近似概念之比较
将“险韵”置于“强韵”“难韵”“僻韵”“剧韵”等与它类似的概念组成的特定系统中,通过分析它与这一系统中其他概念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险韵”比“强韵”“难韵”“僻韵”“剧韵”等概念的内涵更清晰、指涉范围更小。在有些情况下,人们提到“强韵”“难韵”等概念时,指的却是“险韵”;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提到这些概念时其所指范畴却溢出于“险韵”之外。
“强韵”,是一个与“险韵”有着密切关系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如何,是研究“险韵诗”时必须辨析清楚的问题。通过对创作实际的考察发现:押“强韵”的诗未必是押“险韵”的诗,而凡是押“险韵”的诗都可被看作是押“强韵”的诗。“强韵”是一个大概念,“险韵”是一个小概念,“险韵”包括在“强韵”之内。凡是“勉力强押”的韵都可被称为“强韵”,如次韵赋诗、分韵赋诗、借韵赋诗中使用难押的韵部、生僻的韵脚等,都属于押“强韵”。《梁书·王筠传》里说王筠“为文能押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4]这当是“强韵”的最早记载。要之,“强韵”所指是比较宽泛的,惟有在一些特殊语境下它才可以特指“险韵”。
“难韵”就是难押的韵。它所指范围也比“险韵”宽泛。既然“险韵”押起来比较困难,自然也是一种“难韵”。也就是说,“险韵”一定是“难韵”,但“难韵”未必就是“险韵”。例如宋人孔平仲《戏为难韵同官和之》一诗:“稚柳将成线,残梅尚有柎。破春寒料峭,送晚角喑呜。地僻闲宾榻,泥深隔酒庐。此时愁寂寞,幽闷寄操觚。”[5]这首诗确是“难韵”,但不好说就是“险韵”。有些被称为用“难韵”的作品,实际上用的已经是“险韵”。这一点可举谢榛的一段话为证:“九佳韵窄而险,虽五言造句亦难,况七言近体。……虽吊古得体,而无浑然气格,窘于难韵故尔。”[6]九佳是“险韵”,谢氏也说他“窄而险”,后文又说“窘于难韵故尔”,言外之意也是把“险韵”视为令人受窘的难押之韵。
“恶韵”的范围也比“险韵”宽泛,但有时也会将其与“险韵”等而视之。明人姚希孟《韩雨公燕市和歌序》:“长吉、东野诸家,皆险于句,非尽险于韵也。齐梁间,王筠号能用强韵,而玄晖称其圆美,流转如弹丸。段柯古与客联句,多押恶韵,然而涩者使之滑,拗者使之稳,固是诗家斫轮手。”[7]这篇序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同时提及了“险韵”“强韵”“恶韵”,为我们揣摩它们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便利。从姚氏的表述方式来看,他更关注的是三者之间的共性,并没有强调它们的不同。可见,这三个名称之含义存在的区别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
“僻韵”就是生僻的韵。它所指的范围也比“险韵”大,但有时也可用来指“险韵”。清人尤侗有组诗《岁暮杂诗偶用僻韵》,一共30首,多用艰僻难押的字作韵脚字,是名副其实的“僻韵”。彭孙遹在这组诗后评论云:“选韵险,搜事僻,造语奇,古今来未尝有此一家,天地间不可无此一种。”[8]32毛奇龄评曰:“三唐无险韵律,韩孟第古诗耳。今险韵诗满长安,虽是习气,然谨厚者亦复为之。”[8]32诗人自称“僻韵”的诗作,被彭、毛等评论者不约而同地视为“险韵”,足以说明这两个名称间的关系。
“剧韵”的“剧”有“甚”“猛烈”之意。可见“剧韵”这个词也是用来描述难押之韵的。它与“险韵”也有密切的关系。《南史》载:“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饯饮,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9]1074萧恺作诗用“剧韵”,简文以其比王筠,而王筠是以善用“强韵”著称的。可见此处的“剧韵”实际可等同于“强韵”,而“强韵”与“险韵”关系极为密切。也就是说,“剧韵”也是一个大概念,而“险韵”依旧是一个小概念,“险韵”包括在“剧韵”之内。
(二)系统的重置:“险韵诗”与相关诗体的比较
由于“险韵诗”作为一种诗体与主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的“险韵”不同,故而我们需要重置一个新系统,即能容纳“险韵诗”而不只是“险韵”的新系统,来进一步对“险韵诗”的内涵进行“再明确”。次韵诗、独韵诗、联句诗都与“险韵诗”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在用韵方面都存在一些与“险韵诗”较为类似的情形。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发现,次韵诗、独韵诗、联句诗都与“险韵诗”有着较密切的关系。由于它们所押之韵都会随着诗歌创作具体进程的推进而变得越来越“险”,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态”的“险韵诗”。
次韵唱和的基本要求是和作的韵脚字及其出现的次序要和首唱之作基本相同。次韵与“险韵”的关系,简单来说,当诗人选择一个韵部(即使是宽韵)进行次韵时,它们往复唱和的遍数越多,这些韵脚字组词就越难,那么本来不生僻的韵脚字也显得难押了,最终这些字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也变成了“险韵”。何况有些人在首唱之时就用极险僻的字或难以组词的双声、联绵字押韵,然后再要求别人次韵唱和,这无疑使次韵显得非常棘手,而次韵之作一旦出炉,它押韵之“险”必然是超过前作的。
“独木桥体”与“险韵诗”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所谓“独木桥体”就是独韵诗,即是作诗时要求整首诗只用同一个字作韵脚。从明代谢榛的一首押“灯”字韵的独韵诗即可见这一诗歌体式的特点。该诗共押了34次“灯”字,每次押韵组成的词或短语都各不相同。可以想见,诗人作头几句时还很轻松,越往后作会越觉得这个韵“险”。同样,这种“险韵”也无法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于“独韵诗”这种形式。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也是“独韵诗”,从艺术上看,它比谢榛此首结构更合理、语意更加完足,情感也更加深挚。
联句诗与“险韵诗”也有一定的关系。诗人们联句时,选定一个韵部押韵,联的诗句越长,该韵部里的剩余韵字就会越少,最后那些平时鲜有人用的生僻字也不得不拿来押韵,这就与“险韵”产生了联系。例如由韩愈、孟郊、张籍、张彻共同创作的《会合联句》就是如此。此诗押“肿”韵,而且未尝出韵,将《广韵》上声卷2肿部所收韵字用去了三分之一左右。韵部中的常用字几乎用尽不说,像其中的“踵”“恟”“蛬”“尰”“拲”“蛹”“氄”等都是很难押的险僻字。如果将这一技法推到极致,那这首诗也就可被视为“险韵诗”了。
(三)主导与核心:“险韵诗”的诗体演生规律
探究“险韵诗”的诗体属性,也是给它下定义时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将其置于更深广的理论视域中加以观照。通过这一观照我们会发现,“险韵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体,有属于它自己的诗体发生动力。只要能找到这一内在动力的学理依据,它就不必依赖于任何其他诗体而存在。笔者一开始倾向于将“险韵诗”归入“杂体诗”这个宽泛的大类中。理由有二:一、皮日休《杂体诗·序》就曾提到押“强韵”的问题。而“强韵”与“险韵”是有关联的,这为我们提供了将“险韵”也归入“杂体诗”的可能性。二、鄢化志先生《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一书虽没有对“险韵诗”进行特别论述,但书中介绍的“双韵诗”“柏梁韵”“促句换韵体”“独木桥体”“翻韵诗”等,都是用韵方面特点鲜明的“杂体诗”。[10]这也使我们倾向于将“险韵诗”归为“杂体诗”。然而,这样做仅是从押韵这一单一的角度来考量,若考虑到“险韵诗”中还有许多像五、七言律诗这样的“正体诗”,就可能会造成某种混乱。国外理论家的理论表述或许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例如美国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主张将诗歌进化看作一个系统内的成分变化,这些变化与一个“移动中的主导物”的功能有关:
艺术手法的等级制度在一个特定的诗歌种类的构架之内发生变化;此外这种变化还影响诗歌种类的等级制度,同时还波及艺术手法在单个种类之间的分配。最初是次要的、或从属变异的样式现在占据了前台的显著位置,而规范化样式则被推到了后面。[11]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就可给“险韵诗”何以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型这一问题以合理的解释。当押“险韵”仅仅作为构成诗歌这样“一个有结构的系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因素的时候,它自然没有资格被视为一种类型,但随着诗歌的进化,它的位置在“艺术手法的等级制度”中由次要的、从属的地位逐渐的“转移”到了“前台的”“主导的”地位,那其它的“规范化样式”对它的规定作用就被新兴的主导特征冲淡了,当这一主导特征被普遍认可的时候,它就被赋予了成为独立诗歌类型的合法性。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一段论述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每一个时代,那些相同特征的核心总是伴有数目很多的其他特征,不过人们并不看重这些特征,因此,它们对于把一部作品归入一种体裁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结果便是,根据人们对一部作品这种或那种结构特征之重要性的判定,这部作品可以属于不同的体裁。[12]
根据托多洛夫对“特征”的理解,无论“险韵诗”中有正统意义上的“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不能影响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因为以“险韵”为核心特征建立起的“险韵诗”完全可以“伴有数目很多的其他特征”,当“险韵”这一特征“并不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人们当然可以不看重它,但等它一旦成为核心,它就有了成为一种类型的资格。掌握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给“险韵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险韵诗”,是指押“险韵”这一艺术手法在诗歌结构系统中由次要、从属地位上升至主导、核心地位后形成的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
二、“险韵”的代名词
莫砺锋先生曾在《杜甫诗歌讲演录》中指出:“诗歌研究中经常讲到险韵,所谓险韵,就是这个韵部里收的字比较少,所押的韵脚又不是常用的字,押起来比较艰难。我们说押险韵有两个典型的历史文本,有两个代名词。”[13]莫先生认为,这两个典型的历史文本,一个就是由苏轼首倡的“尖叉韵”,另一个就是曹景宗的“竞病诗”。周裕锴先生不同意这一说法,曾撰《说“竞病”——宋代文人赞誉武将能诗的习惯性套语》一文加以商榷。周先生的结论是:“‘竞病’并非诗押险韵之典,更非押险韵的‘典型的历史文本’,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文人称赞武将能诗的习惯性套语。”[14]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观点说明“竞病诗”具有多维阐释的空间,而莫先生指出“竞病诗”和“尖叉韵”是“险韵”的两个典型历史文本,是“险韵”的两个代名词,这一说法则不误。但需要补充的是,“车斜韵”也是“险韵”的一个典型历史文本,一个代名词。故“险韵”一共有三个典型历史文本,三个代名词,即“竞病诗”“车斜韵”与“尖叉韵”。
(一)“竞病诗”:“险韵”的代名词之一
文学史上率先被后世推为“险韵”代表作的是曹景宗的“竞病诗”。《南史》卷55载:“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9]1356的确,景宗此诗写得神采飞扬,把一个凯旋将军的气度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景宗赋诗分到仅剩之“竞”“病”二字,却能“操笔斯须而成”,已足令人刮目相看。更为巧妙的是,他不仅将“竞”这个险僻的韵脚和笳鼓竞奏的军乐鼓吹场面联系起来,还将必须押的“病”字和“霍去病”这个专有名词结合起来,既合韵又不失自己的大将身份。这样的佳作,当然会赢得“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的荣耀,以致后来“竞病”成了押“险韵”的代名词。
之所以说“竞病诗”在后代成了“险韵”的一个代名词,是因为后代有许多人将它当作“险韵”来看待。例如,宋人张维《明水寺》:“险韵吟竞病,怪语作危了”;陈造《次韵解禹玉》:“槃礴臝前笔未落,竞病韵险思不悭”;清人卢见曾《长歌行题董曲江内甥邗江归棹图小照》:“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竞病”;陈宗达《春日文子先生招同王大鲁山西园限韵》:“即今韵险等竞病,催诗火急聊推戡”;顾耀《赠方鹤仙》:“险韵何妨限竞病,硬语直欲僵侯刘”;茹纶常《狐岐途中即目漫成兼呈同游诸公》:“遐赏契烟霞,险韵谐竞病”;夏之蓉《过十八滩》:“险韵夸竞病,谐谈杂尔汝”;章藻功《徐秠绪诗曰小序》:“竞病之韵险而弥工,危了之词叠而尤妙”;赵怀玉《丛桂轩梅树下小饮用东坡松风亭下梅花盛开韵同杨秀才作》:“竞病那怪韵角险,剥啄不愁吏打门”。②上述例句中,人们都是把“竞病”当作“险韵”来看待。下面就这一问题再作三点补充:
首先,“竞”“病”二字本身并不好押。因为它们不仅都是仄声韵,而且“竞”这个动词也不易组成合适的短语,“病”字更是个不适于在喜庆的宴会场合使用的词汇,而曹景宗能将它们巧妙地融入自己的诗歌韵脚中,又能与自己的将领身份和宴会的主题相契合,实属不易;更何况,即便“竞”“病”二字在后人看来并不算生僻,但结合当时的“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的创作情景来看,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动态的险韵”。曹景宗的“竞病诗”虽然在具体创作情景上与白居易不同(见下文),但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
其次,后人多用“竞病”一词来表示押韵的艰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宋诗中就有很多。例如戴埴《和王教暮春出游》一诗有“竞病安能赓,振纸空瑟簌”之句,程俱《叔问览北山小集用叶左丞韵辱惠佳篇推与过情良深愧戢次韵奉酬二首·其二》一诗有“老罢应难夸竞病,诗狂时复赋车斜”之句,李彭《次韵答季智伯弟》一诗有“句分竞病应难敌,家有封胡可解忧”之句,刘克庄《居厚弟和七十四吟再赋·其三》一诗有“已老安能歌竞病,从初不合识之无”之句,等等。③这些都是对“竞病”难于押韵的强调。像程俱、刘克庄这样典型的文士,在诗作中提及“竞病”,并不是为了赞扬武人能诗的壮举,而是侧重于其难于用作韵脚的特征,来谦言自己诗才有限。
最后,在后代的文献中,曹景宗即兴创作“竞病诗”这一事件,经常被拿来当作“武人能诗”的典范看待,但这并不妨碍将之视为押“险韵”的典型。“竞病诗”的确是后人吹捧能诗之武将的门面语、口头禅。可是,我们不能因之就认为后人提及“竞病诗”时就只有这一种用意,而否定“竞病诗”作为“险韵”代名词的重要作用。更何况,武人能即兴作诗很可贵,武人能在即兴作诗时押“险韵”更可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并不相互排斥,认为武人能押“险韵”,不仅不会削弱“武人能诗”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反而能够加强之。
(二)“车斜韵”:“险韵”的代名词之二
文学史上第二个被后世当作“险韵”代名词的是“车斜韵”。白集中有一组名为《和春深二十首》的诗,是和元稹的。这是一组五言律诗,每一首都依次押“麻”韵中的“家”“花”“车”“斜”四个韵字。元稹在原倡中连作了20首押同样韵字的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更惊人的是,白居易又和了20首押同样韵字的诗。须知道,“家”“花”“车”“斜”虽然是较为常见的字,但要组成40个词义、句意都不能雷同的诗句,是极为困难的,这既需要诗人具有非同凡响的才气,又需要诗人具有惊人的知识储备。刘禹锡见元白唱和得热闹,一时技痒也作了20首来次元白的韵。这组名为《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的诗,必须要避开40个别人用过的词汇或短语,另外再组成20个词汇或短语,其难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对自己的《和春深二十首》的用韵之奇已经有了自觉的认知。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曾说:“瘀絮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15]“韵剧”就是押非常艰僻的韵,“辞殚”则是说因韵脚的牵制而产生了言尽词穷的困境。经过元、白、刘三位大诗人的唱和,押“家”“花”“车”“斜”四韵的组诗,成了备受后人瞩目的诗歌话题,它与曹景宗的“竞病”之作一样,成了人们涉及“险韵诗”话题时几乎必谈的佳话。宋人谭昉遂有“车斜韵险,竞病声难”之赞,特别将“车斜”的“险韵”特征指示出来,并将它与曹景宗的“竞病”之作相提并论,肯定了它在“险韵”创作历程中的地位;胡宿《谢叔子杨丈惠诗》也有“句敲金玉声名远,韵险车斜心胆寒”之句;魏了翁在论及欧阳修的诗歌成就时,也指出“家花车斜之诗”是“庾辞险韵”;杨万里《和萧伯振见赠》曰:“车斜韵险难为继,聊复酬公莫浪传”;元人何中《次雪溪上人秋兴韵》曰:“挥尘微言穿溟涬,题诗险韵趁车斜”;清人谭宗浚《遂初楼赋》曰:“车斜则险韵争斗”。④说明他们都对“车斜”的险韵特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同时也正是他们在作品中不断地揄扬,使“车斜韵”成了“险韵”的代名词之一。
(三)“尖叉韵”:“险韵”的代名词之三
文学史上第三个被后世当作“险韵”代名词的是“尖叉韵”。苏轼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是有名的“尖叉”险韵诗的首创之作。王安石有和作《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皆“叉”字韵。这5首足见王安石诗才,但他仍意犹未尽,又作《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除王安石外,苏辙见东坡此作后也曾作《次韵子瞻赋雪二首》。东坡见自己的作品反响颇多,又作《谢人见和前篇二首》进一步将这次竞技推向高潮。王安石意欲与东坡争个高下的“尖叉”险韵组诗的创作,是“尖叉”险韵诗反响热烈的重要表现。这次竞赛的结果,从后人的裁判来看,荆公是略输一筹的。方回曾评东坡之作曰:“偶然用韵甚险,而再和尤佳。或谓坡诗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气雄,下笔前无古人也。观此《雪》诗亦冠绝古今矣。虽王荆公亦心服,屡和不己,终不能押倒。”[16]907又曰:“和险韵、赋难题,此一诗已未易看矣。”[17]准确拈出了它们的“险韵”特征。
清人王培荀曰:“自东坡用尖叉韵后,多踵之者,欲因难见巧也。”[18]《唐宋诗醇》曰:“尖叉韵诗,古今推为绝唱。数百年来,和之者亦指不胜屈矣。”[16]906由此可见模拟、追和之盛。“尖叉韵”也被后人反复提及,最终成了“险韵”的代名词之一。例如清人就常常提及:斌良有“尖叉险韵拈”之句,陈夔龙有“尖叉险韵挑灯续”之句,晏贻琮有“险韵直欲凌尖叉”之句,胡醇有“相与险韵分尖叉”之句,罗汝怀有“或斗险韵拈尖叉”之句,孙惟溶有“尖叉韵险费寻思”之句,施补华有“险韵欲斗尖叉才”之句,王韬有“联诗韵险限尖叉”之句,吴翌凤有“频将险韵斗尖叉”之句,等等。⑤可见“尖叉韵”的确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三个“险韵”代名词。
“竞病”“车斜”与“尖叉”,这几组字并非极为生僻,所属韵部也并非十分险窄,为什么它们在后世会成为“险韵”的代名词?笔者以为,用“动态的险韵”这一概念可以回应这一问题:“竞病”本身只是较险,但在分韵赋诗的动态过程中则会越来越险;“车斜”“尖叉”本身亦只是较险,但在次韵唱和的动态过程中也会越来越险;更何况,一个韵字险或不险,有时候并不取决于它的生僻程度,而取决于它有没有相应的典故可用,能不能组成丰富的词汇或短语。
综上所述,“险韵”是一种对押韵要求极高的诗歌创作技法,“险韵诗”是押“险韵”这一技法在诗歌结构系统中由从属地位上升至主导地位后形成的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险韵”一共有三个典型历史文本,同时也由此产生了三个代名词,即“竞病诗”“车斜韵”与“尖叉韵”。
注释:
①“险韵诗”在古代也经常被提及,例如(宋)李清照《漱玉词》有《壶中天慢·春情》一首,云:“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明)戴澳《杜曲集》卷3有《过云庄险韵诗成剪烛共酌再限五韵》诗;(明)董说《董说集》卷11有《雪中促友人险韵诗限雪灭铁诀四韵》诗;(明)郑鄤《峚阳草堂诗文集·诗集》卷7专立《遯斋险韵诗》之名,录诗百馀首;(清)李驎《虬峰文集》卷19有《书吴凌苍险韵诗后》一文;(清)褚人获《坚瓠集·三集》卷3记录险韵创作趣闻,直接题为《险韵诗》,等等。
②上引9例分别见:(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30《溪堂集》,(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10,(清)卢见曾《雅雨堂集·诗集》卷下,(清)王昶辑《湖海诗传》卷9,(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10,(清)茹纶常《容斋诗集》卷9,(清)夏之蓉《半舫斋编年诗》卷7,(清)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8,(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集》卷1。
③上引4例分别见:(宋)陈起《江湖后集》卷9,(宋程俱《北山小集》卷10,(宋)李彭《日涉园集》卷8,(宋)刘克庄《后村集》卷31。
④上引6例分别见:(清)彭元瑞辑《宋四六话》卷4,(宋)胡宿《文恭集》卷5,(宋)魏了翁《鹤山全集》卷51,(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元)何中《知非堂稿》卷5,(清)谭宗浚《希古堂集·乙集》卷1。
⑤上引9例分别见:(清)斌良《抱冲斋诗集》卷17《良乡丙舍喜见腊雪拈查初白梅雨旧句试和二十四韵》,(清)陈夔龙《松寿堂诗钞》卷8《和答徐花农阁学同年·其四》,(清)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卷148晏贻琮《雪中小集环碧山房戏仿聚星堂故事得沙字》,(清)丁宿章辑《湖北诗征传略》卷20胡醇《谒苏端明遗像》,(清)罗汝怀《绿漪草堂集·诗集》卷9《和蝯叟即事示杨性老索和之作次原韵》,(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47孙惟溶《次韵奉和宾于五十自寿诗再题一截句》,(清)施补华《泽雅堂诗二集》卷9《和子相咏雪》,(清)王韬《蘅华馆诗录》卷2《夜雨小集青萝山馆·其二》,(清)吴翌凤《与稽斋丛稿·登楼集》之《二十七日华父招饮再次其韵》。
[1] 莫砺锋.论王荆公体[M]//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40.
[2]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28.
[3] 郑永晓.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略论[C]//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420.
[4]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85.
[5]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2:420.
[6] 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21.
[7]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806.
[8] 尤侗.西堂诗集[Z]//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鄢化志.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7-298.
[11]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M].刘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41.
[12] 茨维坦·托多洛夫.诗学[M].怀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1-82.
[13] 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9.
[14] 周裕锴.说“竞病”:宋代文人赞誉武将能诗的习惯性套语[N].新民晚报,2009-08-30.
[15]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21.
[16] 乾隆,编.唐宋诗醇[M].香港: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17] 方回.瀛奎律髓[M].合肥:黄山书社,1994:525.
[18]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M].成都:巴蜀书社,1987:387.
“Obscure Rhymes” Phenomenon in the Vision of Classical Poetics
HUANG Jincan
( Graduate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
As an important poetry rhyme and poetic studies, “Obscure Rhymes”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contemporary circle of classical poetics. The so-called “Obscure Rhyme Poetry” refers to that the artistic method “Obscure Rhymes” in the poetic structural system become an independent poetry type from a subordinate position to a dominant position. Concepts “Obscure Rhymes”, “Strong Rhymes,” “Difficult Rhymes”, “Devious Rhymes” are both different and related. “Obscure Rhyme Poetry” has a level of relationship with Subrhyme Poems, Sole-rhyme Poems, and Joint Authorship Poems. With three typical historical texts, “Obscure Rhymes” has three pronouns, namely “Jingbing Poems”, “Chexie Rhymes”, and “Jiancha Rhymes”, which also constitute the special “Obscure Rhymes”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obscure rhymes, connotations, poetry types, pronouns, obscure rhymes phenomenon
2019-03-30
黄金灿(1988-),安徽凤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与文献。
I206.2
A
1673-9639 (2019) 03-0016-07
(责任编辑 肖 峰)(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