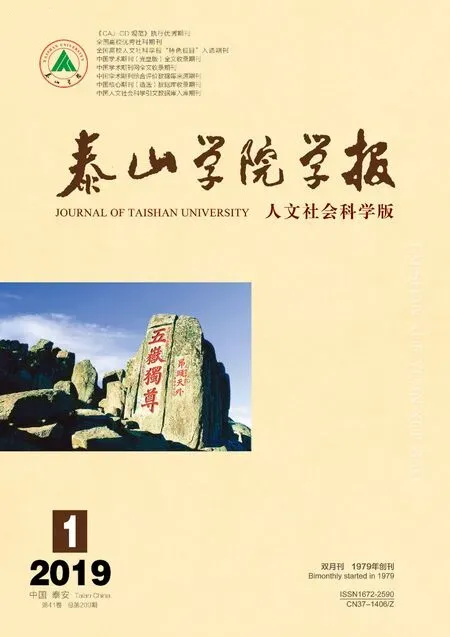读《谈龙录》札记三则
2019-01-19陈汝洁
陈汝洁
(淄博市桓台县 税务局,山东 淄博 256400)
康熙四十八年(1709),赵执信(1662-1744,号秋谷)著《谈龙录》一书,对诗坛领袖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的人品、学问、诗作、诗学嘲诮百端,标志着“王赵交恶”①公开化。《谈龙录》一出,赵、王之争遂成为清初诗坛一大公案,轰动当时影响后世。清代以来,《谈龙录》一书刊刻不绝,②屡屡为研讨清代诗学者所提及。
笔者读《谈龙录》有年,每见相关资料,即作札记。前曾于《赵执信著述探微》《赵执信与顾小谢》等文中刊布两则,③今不揣谫陋,再择三则刊布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一
《谈龙录》第一则云:
钱塘洪昉思(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此事颇传于时,司寇以吿后生,而遗余语。闻者遂以洪语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说以相难。惜哉!今出余指,彼将知龙。[1](P5-6)
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文中“司寇”,指王士禛。纪昀著、林昌评释《增订河间试律矩》一书书前《诗说》曾节引此则中王士禛、赵执信语,并加按语云:
赵宫赞《谈龙录》云:“新城司寇论诗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鳞一爪而已。’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
按:两先生之谈龙不同,而旨则同。耳食者妄欲有所轩轾,乃夏虫不可以语冰也。愚谓渔洋所言,诗之神韵也。秋谷所言,诗之格律也。无格律则神韵无所附,无神韵则格律竟成硬本子。是业公子高之所谓龙,非真龙也。其说相成而非相悖。读是集者能与格律中求神韵,则规矩在而巧寓焉矣。[2](P3-4)
“业公”应作“叶公”。此段仅节引王、赵之语,未引洪昇之言,所加按语更是不通之甚。从《谈龙录》来看,引发洪昇议论的是“嫉时俗之无章也”,即三人谈论的是作诗章法问题,与“神韵”“格律”无直接关系。故此段按语,纯属误解。今人周振甫解读此则颇为清晰,其《诗词例话·完整和精粹》云:
这里指出对诗歌的文艺性的三种看法:洪升要求完整,像画龙,要把整条龙画出来。连它的首尾鳞爪都不能忽略。王士禛反对这样求完整,要求精粹,认为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只在云中露出一鳞一爪,就是只要把最精粹的部分写出来就行了,不必求完整。赵执信认为完整和精粹两者是不可分的,画出来的龙虽然见首不见尾,只有一鳞一爪,我们却可以从这里看到完整的龙。心目中有了完整的龙才可以画出一鳞一爪,才可以通过一鳞一爪来反映龙的全体;离开了完整的龙去画一鳞一爪是不成的。也就是精粹要从全体中来,离开了全体就谈不上精粹。这三种看法,赵执信的看法是最完整的。[3](P12-13)
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一文中也曾引用《谈龙录》此则,他解释说:
洪昉思重视“全”而忽略了“粹”,王渔洋依据他的神韵说看重一爪一鳞而忽视了“全体”;赵执信指出一鳞一爪的表现方式要能显示龙的“首尾完好宛然存在”。[4](P90)
宗白华的解读与周振甫一致。宗氏在征引《谈龙录》此则前有这样一句话:“清初文人赵执信在他的《谈艺录》序言里有一段话很生动地形象化地说明这全和粹、虚和实辩证的统一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4](P89-90)这句话中将“《谈龙录》”误作“《谈艺录》”、将“第一则”误作“序言”。《谈龙录》一书第一则以洪昇谈诗起首,最末一则则以谈洪昇诗结束,④虽是诗话著作,却也首尾呼应,颇见匠心。
二
《谈龙录》第四则云:
顷见阮翁杂著,呼律诗为“格诗”,是犹欧阳公以八分为隶也。[1](P7)
赵蔚芝、刘聿鑫《谈龙录注释》注解此条云:
格诗:指律诗以外包括古调、乐府、歌行杂体诸体的古体诗。据《带经堂诗话》引《渔洋文》:“《唐文粹》所取诗,止乐章、乐府古调,而格诗不录。”[5](P13)
书中征引《带经堂诗话》中所引《唐文粹选诗序》注解此条,盖以为《带经堂诗话》为赵执信所见“阮翁杂著”。实属误解。《带经堂诗话》系乾隆间张宗楠编辑,张氏自序作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知此书不惟成于王士禛身后,并赵执信亦下世十馀年之久,赵执信何以能见此书?其实,赵执信所云“杂著”,系王士禛笔记《居易录》。《居易录》卷十二云:“《鼓吹》《三体》惟录格诗,气格卑下,《众妙》《二妙》亦然。”[6](P3904)《唐诗鼓吹》专选七律,《唐诗三体》选七绝、七律和五律三体,王士禛称之为“格诗”,故赵执信嘲诮王氏作为当代大家、诗坛领袖居然不明诗歌体制。
“欧阳公以八分为隶”一句,《谈龙录注释》征引冯班《钝吟杂录》语作注解。其实,赵明诚《金石录》早已指摘欧阳修误以八分为隶书。《金石录》卷二十一云:“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 ,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7](P394)《谈龙录注释》注解此条应征引《金石录》。而王士禛《居易录》亦曾言及世俗误以八分为隶,是书卷十七云:“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隶书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为隶,何其不察耶?”[6](P4001)王士禛书中嘲诮世俗不明书体。《谈龙录》“是犹”一句即隐指《居易录》此条。言外之意,王氏不明诗体,自嘲尚且无暇,还有闲嘲诮他人不知书体!《谈龙录》此条,本是加一倍写法。《谈龙录注释》未能注出《居易录》其书,读者即难以领略赵执信作文用心之深细,并此条之嘲讽力度亦减半矣。
三
《谈龙录》第二九则云:
或问于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学博于王,而才足以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1](P15)
赵执信在此条中肯定王士禛为大家,能与王氏匹敌的是朱彝尊(1629-1709,号朱垞)。文中关于王、朱才与学的比较,似本《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云: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8](P615)
王士禛在世时诗名极盛,山左多以田雯(1635—1704)匹之,江南多与宋荦(1634-1713,号绵津山人)并举。赵执信不以为然。所谓“他人高自位置”者,即指田雯与宋荦。《谈龙录》第十则即讥讽田雯“诗中无人”⑤。而于宋荦将《绵津诗钞》与《渔洋诗钞》合刻为《二家诗钞》,赵执信尤为鄙薄。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云:“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士禛)、宋(荦)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赵归寓后,书一柬复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9](P98)自《谈龙录》出,朱、王并称,遂为定论。
“朱贪多,王爱好”是赵执信对两位大家诗作的批评。清代以来,赞同赵氏此评者有之,如梁绍壬、陈仅;反对此评者亦不乏其人,如清人翁方纲、近人姚大荣。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云:“‘朱贪多,王爱好’六字,恐二公亦无以辨也。”[10](P269)
陈仅《竹林答问》云:“‘王爱好,朱贪多’二语,实为二家定评。”[11](P2256)
梁章钜《退庵随笔》一书曾记其师翁方纲(1733-1818,号苏斋)对赵执信的批评。是书卷二十一云:
自赵秋谷有“朱贪多,王爱好”之说,后人多资为口实。苏斋师尝言:“汝自腹俭耳,朱何尝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尝爱好。”实为棒喝。窃谓今之学诗者,正当以“爱好”学王,以“贪多”学朱,则方将讲求声律,博综故实之不暇。则此两言,转可为学诗者之阶梯,又何所容其排击者?[12](P547)
钱仲联《梦苕盦诗话》记姚大荣⑥反驳赵执信言论。是书云:
自赵秋谷诋其贪多,耳食者乃从而吠声。近人姚大荣始驳之曰:“赵秋谷《谈龙录》论诗,颇议竹垞贪多,《四库提要》韪之,夷考其实,殊不尽然,将谓使事多则隐僻滋累耶?此自博洽者长技,不足以为竹垞病。竹垞文擅名雅洁,惟诗亦然。意以率辞,辞必副意,殊少浮艳涂饰之习。将谓篇什多则榛楛未剪耶?全集存诗一千七百馀首,(内如《闲情》三十首,仅存八首;《论画》二十六首,仅存十二首之类,具见剪裁。)益以裔孙墨林暨冯登府所辑集外稿,约四百首,仅二千一百有奇。稽其编年,自十七岁始,至八十一岁止,六十五年间,得诗仅此,不可谓多。(陆放翁自云:‘六十年间万首诗’,迨后又添四千馀首。竹垞规之,仅得其四分之一。)将谓长篇多则阅者易倦耶?综核全诗,无论古近体,五十韵以上,尚不多得,百韵尤属稀见。全集具在,可覆检也。然则秋谷所谓贪多者,殆专斥《风怀二百韵》言,举一以概其全,秋谷所评未为公允。”姚氏此论至当。[13](P679-680)
翁方纲没有正面谈王士禛是否“爱好”、朱彝尊是否“贪多”问题,反而讥讽赵执信“腹俭”“不要好”,显得颇为情绪化。姚大荣故作不解“朱贪多”之“多”字为何指——用典多、篇什多还是长篇多?然后自问自答,逐条反驳,以为朱彝尊诗用典多不为病、篇什并不太多、长篇有但也不多。姚氏提及《四库提要》赞同赵执信“朱贪多”之说,其第二条驳论篇什多、第三条驳论长篇多,具是针对《四库提要》而发。《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曝书亭集》云:
至其(朱彝尊)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禛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惟暮年老笔纵横,天真烂漫,惟意所造,颇乏剪裁。然晚境颓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论彝尊矣。[14](P2345)
《四库总目》说朱彝尊中年以后之作“长篇险韵,出奇无穷”,是说其长篇多;晚年诗作“惟意所造,颇乏剪裁”,是说其篇什多。姚大荣辩驳说,《曝书亭集》存诗“仅二千一百有奇”,且“具见剪裁”,“不可谓多”。又说,“综核全诗,无论古近体,五十韵以上,尚不多得,百韵尤属稀见。”可知四库馆臣之说并不符合《曝书亭集》实际。邓之诚也以为“朱贪多”是讥诮朱彝尊诗作多,其《清诗纪事初编》说朱氏“诗篇极富,赵执信因有‘贪多’之诮”[15](P748)。《谈龙录注释》注解此条云:“贪多:追求数量,放松质量。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共计古今诗32卷。在清初诗人中,他是一个多产作家。”[5](P77)如朱彝尊的创作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赵执信是不会将他目为大家的。所以,如此解释,并不正确。其实,从《谈龙录》此条称述朱彝尊博学来看,赵执信所言“朱贪多”应指朱诗用典多。翁方纲讥讽赵执信“腹俭”,也正可印证他认为朱彝尊腹笥广博。姚大荣认为朱诗用典多是“博洽者长技,不足以为竹垞病”,也承认朱诗用典多。
梁章钜说“正当以‘爱好’学王”,是曲解赵执信“爱好”本意。赵执信所言“王爱好”,是说王氏诗作雕饰过甚,反伤天真。吴梅村谈诗文创作亦持此论。谈迁《北游录》记吴氏语云:“诗文举业,俱不可著一好字。胸中稍著,则伎俩见矣。凡古人得意之处,非古人得力之处,惟深于文者知之。”[16](P96)吴氏此论可作“王爱好”注脚。《谈龙录》评吴雯诗也说“天姿国色,粗服乱头亦好。皆非有意为之也”[1](P16)。正是赞扬吴雯乃“深于文者”。
注释
①王士禛与赵执信两度交恶。据《谈龙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赵执信酒后谈及王士禛《南海集》首章和次章感情不真,诗中无人,有人转述于王士禛,使王氏大为恼火,这是两人“致疏之始”。第二次大约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赵执信酒后指摘王士禛所作《子青墓志》,对其门人朱缃的文学才华揄扬过甚,且文中前后有矛盾之处,并直言王士禛的文学功绩不能与韩愈、苏轼比肩,这让王士禛的侄子王启座等很不高兴,事后转述于王士禛,引发王士禛的强烈不满。详见陈汝洁《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实》,载《赵执信研究丛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5页。
②《谈龙录》刊刻情况,见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又见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0页。
③《赵执信著述探微》,载《泰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赵执信与顾小谢》,载《淄博师专学报》2018年第1期。
④《谈龙录》末则云:“昉思在阮翁门,每有异同。其诗引绳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对其篇幅,都无生气。故常不满人,亦不满于人。”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⑤赵执信《谈龙录》云:“德州田侍郎纶霞(雯),行视河工,至高家堰,得诗三十绝句。南士和者数人。余适过之,亦以见属。余固辞,客怪之。余曰:‘是诗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风景,征引故实,夸多斗靡而已。孰为守土?孰为奉使?孰为过客?孰为居人?且三十首重复多矣,不如分之诸子。’客怃然而退。”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⑥姚大荣,字丽桓,号芷沣,贵州普定人。著有《马阁老洗冤录》《惜道味斋说诗》。《惜道味斋说诗》初刊1931年《庸言》杂志第一卷第九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收入王培军、庄际虹《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钱仲联《梦苕盦诗话》所记姚氏反驳赵执信言论不在《惜道味斋说诗》,钱氏未注明出处。钱仲联选、钱学增注《清诗三百首》朱彝尊小传亦曾征引姚大荣言论,见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3页。